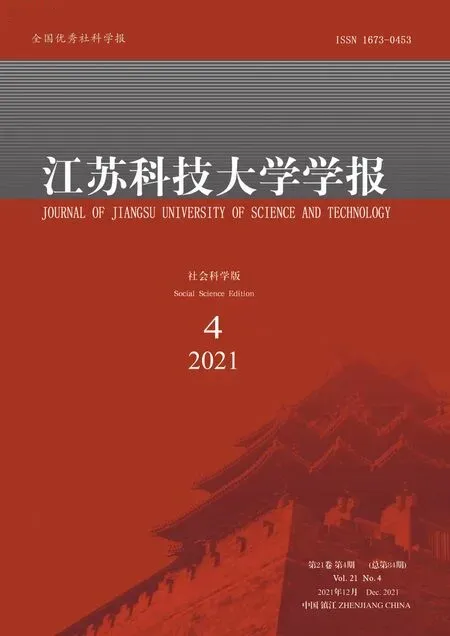清初诗人题咏帝王书法的言说方式与“圣君”政治
李开林
(太原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帝王书法”是指历代皇帝(包括部分皇子)留下的书迹,也称“御笔”或“御书”。清初许多诗人或因先祖受赐前朝帝王书迹,或身在现场得以获观当朝御笔,于是题写了“论书诗”和“论书文”,以抒发对帝王书法的评价。这些诗文题咏表达的历史、艺术信息丰富,是帝王书法研究不应忽视的一环。清初诗人朱彝尊(1629—1709)、王士禛(1634—1711)、査慎行(1650—1728)受赐、获观了较多明、清两朝帝王书迹,他们因此结撰诗文以示珍视和纪念。其诗文既表达了显豁的颂美和感恩之情,也蕴含了隐晦的复杂心态。笔者拟从诗人题咏帝王书法的诗文入手,分析其言说方式,探讨其背后隐藏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和新朝定鼎之初的真实心态和历史观,并尝试揭示诗人性格、心理中某些稳固、深刻的气质和特征。
一、 帝王书法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有关帝王书法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不少,主要是收集和汇编历代帝王书迹,如洪丕谟的《中国历代帝王书法欣赏》、黄全信的《墨苑奇珍:中国历代皇帝书法珍品》。进入新世纪以后,帝王书法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帝王书法的风格、渊源以及影响,如杨丹霞的《试论清康熙帝书法的渊源、分期与影响》。近年来研究成果剧增,且具有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往往是结合历史、社会、地理、文化等因素讨论帝王书法的意义,如刘东芹[1]、常建华[2]、刘重喜[3]以及张函[4]等。这些文章重在剖析帝王书法确立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揭示帝王书法对士大夫心态、艺文思想走向以及巩固皇权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
总的来说,帝王书法研究成绩斐然,但亦有不足之处。
一是现有研究对受赐、获观御书之人的观感评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从“接受者”视角开展的研究阙如。帝王书法的受赐者或获观者撰写的诗文题咏散见于诗人的别集中,易被研究者忽略;部分研究者持论偏颇,认为“现今我们去评价帝王书法的艺术价值,不是去看他的商品价值,也不是看人们对它的批评意见”[5],完全摒弃了“观者”的态度和思想;还有研究者试图“抛开帝王一切政治功绩或历史污点”,“赤裸裸地仅审视帝王的书法艺术,得到一个无主观色彩参与的纯粹的价值认识”[6]。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帝王书法”的创作、接受和品评是一个完整链条,不能选择性地无视其中任意一环。同时,人生、社会是艺术的生存土壤,谁也无法强行将它们剥离,况且艺术的等级正是人精神生活的等级[7],仅仅就艺术作品论艺术,而完全不涉及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心态,这样“纯粹”的艺术评价标准是有待商榷的。
二是现有的对帝王书法的研究未能从对诗人所处朝代的研究上升到对诗文背后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的揭示。如聂国强关注清初诗人朱彝尊对明代三位帝王书法的评价,认为朱彝尊对他们大力推崇和赞扬,但未提及朱彝尊的评价中同时夹杂了惋惜、悲痛等复杂情感,其中的缘由也并未探及[8]。
如果把朱彝尊对明、清两朝帝王书法的评价进行比较,会发现更为宏大的图景。朱彝尊曾目睹明代万历(朱翊钧,庙号“神宗”,1563—1620年在位)、天启(朱由校,庙号“熹宗”,1620—1627年在位)和崇祯(朱由检,庙号“思宗”,1627—1644年在位)三朝皇帝的御书,往往下笔凄怆。进入新朝后,他获观康熙(爱新觉罗玄烨,庙号“圣祖”,1662—1722年在位)御笔,感恩、颂赞之情溢于言表,对前朝帝王的追思、怀念及对本朝皇帝的膜拜、臣服都只是表面,最根本的乃是诗人“呼唤圣君”的深沉情感。朱彝尊如此,其他清初诗人王士禛和査慎行亦是如此。这是一种超越了时代和个体身份限制的民族心理特征,不仅具有认识过去的价值,放在当下语境仍具有其思想意义。
二、 清初诗人受赐、获观御书的基本情况
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等清初诗人得见明代御书,主要是因为其先祖曾供职于明廷,帝王书迹出自家传;诗人得见清代皇帝御笔则是因为入仕清廷,或是受赐,或是赐观御书。清初的顺治(爱新觉罗福临,庙号“世祖”,1644—1661年在位)与康熙这两位皇帝皆善书法,乃至“东宫暨诸皇子皆工于书法”[9]4315。王士禛不由赞叹道:“本朝家法,真唐、宋、明以来仅见之盛事也。”[9]4315大略来说,诗人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越近,越可能多地获观或者受赐御书。
朱彝尊获观的帝王书迹有“神宗皇帝御书”六字、明熹宗天启皇帝手敕三通、明思宗崇祯皇帝御书、清康熙皇帝御书《兰亭》以及清康熙皇帝书“惠爱”二字;王士禛获观或受赐的御笔有明万历皇帝书“苍松古柏”四字、清顺治皇帝书“敬佛”二字、清康熙皇帝书“存诚”“清慎勤”“格物”“带经堂”“养素”“地平天成”“笔端垂露”等大字,以及皇子胤礽(1674—1725)书“山水清晖”、胤祉(1677—1732)书《广济寺碑文》等;查慎行获观或受赐的有清康熙皇帝书“程子视箴”、《大学》经传、《泊舟惠山》诗、“知稼轩”“无逸斋”“谦尊堂”“日知堂”“敬业堂”匾以及“福”字等。
从御笔书写内容上看,皇帝制书多援引儒家经典诫勉臣子,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满清政权定鼎中原之初,其政治地位尚未巩固,满汉关系相当紧张,因此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措施,如设“博学鸿词科”、开“明史馆”等安抚其反抗情绪。将御笔赏赐群臣,也是拉拢汉族官员和学者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受赐臣子的反映来看,御赐书作达到的效果十分理想。受赐之人无不视此举为“奇遇”“异数”或“艺林佳话”。如王士禛在得赐“存诚”大字御书后说:“从今不羡钟王迹,曾向云霄捧御书。”[9]886可见,清廷统治者借助书艺很好地传达了雅意右文的态度和立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士人心态,使之臣服于皇权,达到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目的[10]。
三、 诗人题咏御书的“言说”方式与“圣君”政治
皇帝书法所实现的政治教化作用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研究共识,但必须看到的是,诗人对御书的诗文题咏不仅反映出他们对当朝皇帝的赞誉、感动和拜服,更是在隐曲地传递心声:真正令诗人折服的不是“帝王在文化话语权上的绝对权威性”[4],而是一个持久的文化传统——对圣君的呼唤。
作为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儒家哲学将国家想象成一个大家庭,“天子”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个人通过修身可以齐家,国家的家长——“天子”通过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以家庭模式为核心的儒家式民主[11]100。相较于君王抽象的“最高权力”,社会更看重占据最高职位的人的品格[12]149,因此“君主”或者“帝王”的智慧、能力和品格至关重要。圣君在位,便可达到社会和谐。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想以及民主实践方式在根本上即是一种“圣君政治”。政治之“治”意味着君与民在情感上获得了一致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对帝王权威的被迫服从,而是对“圣君的呼唤”获得了回应,以及圣君最终降世的由衷喜悦。这才是汉族知识分子面对帝王书法时最幽微的感情——“圣君”情结。只是诗人的言说方式独特而精致,让这种感情藏在了文字背后,故必须深入探究,方能触及诗人最真实的心灵。
(一) “羲画尧文”说
从朱彝尊、王士禛、査慎行三人的诗文看,他们题咏御书是最常用的言说方式之一,是将当世君主追比远古贤王,论及最多的是伏羲和尧。传说伏羲创制了八卦,被视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尧是上古部落首领,从尧开始有了“君主禅让制”,因而尧也被司马迁认为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史记·五帝本纪》)的圣君。伏羲和尧的身上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君主治理国家的范式和愿景——君主应以“人文教化天下”,并且能够“推举贤明”。“人文教化天下”和“推举贤明”可合二为一,最终归结为“圣君政治”,这种思想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动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的传统让人们渴求贤君能代代接续,进而实现清明政治和天下安泰。这种思想贯穿于诗人对帝王书法的评价中——诗人对明、清两代皇帝差异迥然的言说方式,表面上反映的是诗人的态度变化,本质上体现的却是由“圣君政治”的断与续所带来的情感起伏。
这一点在朱彝尊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朱彝尊的先祖曾供奉于明廷,故其所见明代御笔较多。当朱彝尊目睹“神宗皇帝御书”六字时说,“桑田沧海市朝迁,盛事今来未百年”[13]841,叹惋世事变迁、盛世不再。朱氏家族对明万历皇帝有较为特殊的情感,朱彝尊的祖父朱国祚(1559—1624)在万历十一年(1583)中举得进士第一,达到了家族科举仕宦的巅峰。因此,朱彝尊看到万历皇帝御批的“廷对策”之后,回忆自己的祖辈“经纶文采”,睹物而情伤,但这种“惋惜”之情与其说是对御笔真迹飘零的感慨,不如说是对明代皇帝因荒政导致亡国的悲哀。这种感情在朱彝尊评价明熹宗天启皇帝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书迹时尤为明显。
朱彝尊所见明熹宗天启皇帝手敕三通乃是历经战火存留至今的手札,亦属难得。但这三封手敕的内容是关于祭祀、造坟等事,与国家治乱没有紧密关联,所以朱彝尊在文末特意指出天启皇帝当政未能慎终如始,导致宦官专权而埋下祸患。至于他的书法技艺,朱彝尊则一笔带过,直言其“不工”。此时的朱彝尊是理性的,笔墨中饱含对皇帝因庸碌无为而导致权威丧失、加速王朝覆灭的冷峻批评。
朱彝尊在评价明朝末代皇帝思宗崇祯的御书时,情感流露最为真实和痛心,“高生载拜陈御书,对客还从乱离说。当歌欲言不得言,相视无声但呜咽”[13]916。朱彝尊回想起崇祯帝即位后励精图治,铲除阉党,但“此时图治苦不早,此日忧勤古稀少”[13]916。一切为时已晚,个人再怎么努力也已无力回天。“可怜珠囊玉轴零落归人间,使我恍惚咫尺觐天颜,不禁涕泗流潺湲。我欲问天公,天公醉未已。鹑首翻然下赐秦(逆闯僭都咸阳),古来恨事多如此。问君涕泗何为尔,独不闻尧幽囚舜野死。”[13]916“尧幽囚舜野死”表明了“圣君政治”在明代的彻底终结,朱彝尊为这位末代皇帝流泪,更是对明代诸多帝王未能慎终如始、背离贤君之道感到深沉哀痛。
朱彝尊对明代皇帝书迹的评价所反映的最深层的思想内核是“圣君”传统在明代丧失带来的痛感,幸运的是,“羲画尧文”的贤明政治在新朝得以复睹。朱彝尊瞻仰康熙皇帝御书大字《兰亭》时激动地说:“臣闻邃古之初,首传羲画。结绳而后,丕焕尧文。河则龙策告期,山则螺书遍刻。禹功甫奏,爰题岣嵝之碑。周道方兴,厥有岐阳之鼓。”[13]607康熙皇帝被认为是“古今所未觏”[14]的“圣君”典范,其庙号也恰为“圣祖”,所谓“羲画”“尧文”“禹功”“周道”都象征着“圣君政治”在新朝的重新接续。另一位诗人查慎行在获观康熙御书时也大量地使用这一言说方式:
尧文纷焕采,宓画久穷源。[15]786(《二十日召赴行宫钦赐御书程子视箴一幅恭纪十六韵》)
羲画传家法,尧章焕丕基。[15]817(《是日赴东宫召观洒睿笔口授书法兼蒙赐扇恭纪十六韵》)
尧典推明德,汤盘视袚躬。……羲画传同远,箕畴演并崇。[15]819(《赐观御书大学经传恭纪二十韵》)
画传羲易筹图秘,念切周诗稼穑勤(御书知稼轩、无逸斋)。[15]876(《东宫名赴西园赐观皇上御书匾额大小二十有九恭纪七律八章》)
尧文开盛世,羲画掩前王。[15]895(《恩赐御书敬业堂扁额恭纪十六韵》)
“羲画”本指伏羲画卦,象征“人文”的开始,故说“久穷源”。“尧文”“焕丕基”“纷焕采”指的是尧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贡献。他“推明德”,将君位禅让给有贤德的“舜”,让“圣君政治”得以延续,故说“开盛世”。诗人善用“比兴”,以先王的一切功德比附当今君主,藉此褒美御书的无与伦比,表现出对皇权的崇敬与臣服。这固然可被视为诗人取悦帝王的美颂谀辞,但如果说“美颂”之辞是迫于皇威而作的功利性虚饰,那么深藏其中的对“圣君”降世和回归以及汉民族的理想政治传统得以重生的喜悦则是真挚的,诗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志显然更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尊重祖先与文化英雄的儒家民主模式是一种真正的“先贤的民主”[11]110。“尧文羲画”说正是汉民族追思先贤的政治思维之体现。诗人借助它从时间、历史的角度表达了对当今帝王书法的肯定,而另一种方式——“云汉天章”说则是从空间、上下对立的角度再次确认了“呼唤圣君”的民族心理。
(二) “云汉天章”说
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君臣关系决定了皇帝的书法必须以无可挑剔和指摘的姿态傲立于任何一个专业书法家之上,占据最高地位且不可撼动。由此,诗人评论御书的诗文似乎成为言不由衷的逢迎文章。其实不然,才思敏捷的诗人依然会保持诗人的本色,他们的诗歌仍是艺术创作,仍然能够做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这些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借助比喻、类比等表达技巧,在展现御书淋漓元气和神明光华的同时,巧妙、含蓄地道出诗人彼时的真切感受。诗人们最喜爱使用的象征是“云汉”“日月”和“星辰”:
光同五纬,丽并三辰。[13]607(《御书大字兰亭颂》序)
倬彼云汉,丽矣星辰。[13]607(《御书大字兰亭颂》)
宝题银榜,若云汉之章于天,在下者莫不睹矣。[13]608(《御书赞为李都运使作》序)
维天有汉,丽于秋旻。[13]608(《御书赞为李都运使作》)
云汉烂天章,典谟布方策。[9]464(《世祖章皇帝御画渡水牛,戏以指上螺纹成之,赐中官某臣,从黄州通判臣宋荦得观,恭赋一章》)
银河直与宸居接,无数蛟龙起墨池。[15]789(《南书房敬观宸翰恭纪》序)
星斗天垂象,山泉帝发蒙。[15]819(《赐观御书大学经传恭纪二十韵》)
殿合香风浮墨气,河山秀色映天文。[15]876(《东宫名赴西园赐观皇上御书匾额大小二十有九恭纪七律八章》其二)
晨曦烛地光相并,列宿周天数有余。[15]877(《东宫名赴西园赐观皇上御书匾额大小二十有九恭纪七律八章》其四)
迸散繁星悬两曜,尽收千派纳长江。[15]877(《东宫名赴西园赐观皇上御书匾额大小二十有九恭纪七律八章》其七)
目炫管中窥日月,梦回衣上带云霞。[15]877(《东宫名赴西园赐观皇上御书匾额大小二十有九恭纪七律八章》其八)
这些华美的辞藻和精致的修辞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诗人对皇权的膜拜,但这种观感仅仅停留于表面。风格是心境的外化,这种言说方式背后有更深层、更稳固的民族心理在起作用。诗人笔下灿烂的伟大不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光环,更是一种顺应天道的“圣君政治”所释放的辉光,以及诗人对“圣君政治”的敬服、感动之情。面对御书,诗人找到了最佳譬喻方式,君主被反复比喻成“云汉”“日月”和“星辰”,这说明诗人对“圣君政治”的渴求,揭示出中华民族深刻、稳固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倾向。
在传统文化语境里,皇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宇宙秩序在尘世中的对应者[12]30,皇帝的御书应是“天道”的笔墨呈现——日月丽天,璀璨光明,既象征着君主的斐然文采,又暗示其卓越的政治才干,是“圣明”之君。这与在下瞻仰的臣子正好构成了一种“天与地”“上与下”的关系和秩序。如朱彝尊所言:“自瞻御墨,尽在下风。”[13]607查慎行亦称:“臣慎行亦得随诸臣后,仰瞻天日之光,洵有生之奇遇,人世所罕觏者也。”[15]787“臣于拜观宸翰之下,仰见我皇上神功圣德,冠绝千古者,更有蠡测焉。”[15]788又言:“九重日月无私照,有目皆容仰面看。”[15]790这些表达皆展示了诗人对皇权趋同和臣服的心态。
这些言说方式与《诗经》里讴歌周文化的颂诗相似,必须被“精确地复述”,因为“毫不偏离”的赞美是对整个王朝繁殖和再生“哲王”能力[16]的肯定。“圣君”在古代的政治体制下具有创造盛世的决定性作用,诗人们对于“圣君”的呼唤和颂扬超越了一代人、一个历史时期并内化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心理和感情。这些心理和感情绵延千年、经久不变,具有区别于一般特征的强大力量。
(三) “超越书圣”说
朱彝尊的《〈御书大字兰亭颂〉序》洋洋洒洒近千言。序的开头罗列了从古至今留下墨宝的帝王,他们当中虽“间有工书”者,但“莫由造极”,而当今圣上游心翰墨,“睿藻光华,曜六文而首出。奎章景铄,包八体以高鶱。翠珉表阙里之庭,银榜遍名山之宇”[13]607。诗人颂扬康熙帝不仅兼善各体,而且创作数量众多,无论是在宫廷之内,还是在名山庙宇之中,都可见御书真迹。这与事实相符。君主留下墨宝不仅是文化行为,也具有政治意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统治方式[2]。从朱彝尊的评价来看,这种方式效果卓著。因此朱彝尊赞叹道:“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无双。”[13]607随后,朱彝尊以“书圣”王羲之为比照,凸显康熙帝书法之精妙。王羲之是“冠书家而独立,集字学之大成”[13]607的人物,兴酣落笔留下了醉本《兰亭》,不仅自己酒醒后再难以复制,后代的名家好手也难以企及,“冯、汤、赵、葛,各有临摹。褚、薛、颜、杨,终难仿佛。且偏旁之互异,或肥瘦之失中”[13]607。但朱彝尊认为康熙帝临写的《兰亭》完全超乎真迹之上:“皇上御帝鸿之墨海,掞汉殿之璇跗,用襞宫笺,特书禊序。作擘窠之字,悉中准绳。挥垂露之毫,不踰规矩。得心应手,入化穷神。虽曰临书,实超真迹。”[13]607诗人认为皇帝虽然是临写《兰亭》,但却“超越”了真迹,“超越”了王羲之。
事实上,《兰亭》被誉为古今行书第一,不仅因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杰作,《兰亭》向世人昭示文人区别于普通民众的艺术创造力,彰显了士族的身份和尊严。而朱彝尊称康熙帝“虽曰临书,实超真迹”,并非实指皇帝书艺有多么高超,而是对帝王缔造盛世能力的肯定,“近瞩荣光,欣逢盛际。对昭回之灵汉,俨咫尺之天颜。敬缀芜辞,用扬懿美”[13]607。“盛际”是文眼所在。对皇权的臣服和膜拜,源于对社稷升平、“圣君王道”得以延续的欣悦之情。王羲之“遗法可循”,故皇帝可以“手追心慕,入妙通神”[13]607,但“鹅墨之沼,浮沫成沦”[13]607。华美的艺术背后须有最高人格,对君主来说即是贤德贤能。这是艺术创作最强有力的支撑力量,“昔贤列宿,我后羲轮。昔贤百谷,我后沧津”[13]607。这种由“昔贤”到“我后”的推进、衍化之力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与发展的动因,展现这种强大“生命力”的艺术理应获得至高地位。
朱彝尊又称:“有丹有雘,有徛有陈。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鳞。有赫宸书,镇兹海垠。三光轇轕,七采璘彬。吉云环卫,元气弥纶。如稽山寿,于千万春。”[13]607这是诗人对生生不灭、孕育万物的大自然的感悟。对“圣君”的赞美和呼唤,正是对“生命”的礼赞。因为“圣君”爱民、保民,能够延续汉文化的血脉,能够激发汉民族的勃勃生机。造诣最高的艺术品表现的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揭示的是本民族最深刻的气质和本能。王羲之的《兰亭》美则美矣,然而不免流露“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17]、感慨生命短暂的悲意,而朱彝尊从帝王书作里品味出的是蓬勃、充沛的生命力。从此角度看,康熙帝的御书未尝不可超越书圣王羲之而置诸其上,诗人对康熙御书的评价既是最艺术的言说,也是最接近本质的深刻诠释。
四、 诗人评价书家之书与帝王之书的角度异同
论及道德行事和文章艺事二者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以及“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 “德行”是评价书家之书和帝王之书的皆适准则,甚至是首要标准。在德行之外,孔门四科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政事。对于帝王而言,政事显然是成为圣君的必要条件,处理好政事与艺文之间的关系是圣君应具备的素养,圣君应兼具健全的人格、清明的政治以及高超的艺术修养。
朱彝尊认为康熙帝极为擅长处理二者关系,“我皇上日新盛德,天纵多能。四海同文,治轶唐虞之上。万几余暇,心游翰墨之中……圣矣我后,万几维勤。一有余暇,翰墨必亲……恒出万几余暇临仿法书”[13]607。帝王在完成繁忙政务之余暇,其翰墨游艺才能显出从容优雅的气度和正大光明的气魄,“乃握乾符,乃阐坤珍。倬彼云汉,丽矣星辰”[13]607。作为一位统治了国家61年的君主,康熙书法的艺术水准和成就的高低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思想导向、艺文政策是否有助于国家的治理和文化的延续。因此,对于帝王而言,应以政务为重,翰墨娱请宜排在“万几”政务之后,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康熙的书法作品也不会得到很高评价。
对于癖好木工而贻误朝政的明天启皇帝,朱彝尊则用含蓄笔法提出了批评:
朝野相传,帝天纵巧慧,能手操斧锯,造轻车小屋,万几不理,以是威权下移。今观三勅,书法虽不工,未尝假手司礼内监,初政犹然。逮先公及福清叶公先后去位,中官始无忌惮,诏旨不自帝岀,而朝士之祸烈矣。然则否泰之反,类由于大小之往来。三勅似无关于治忽,而天启初终之政,论世者所当辨也。[13]553
天启帝弃“万几”政务不理,专心扮演木匠的角色,导致客氏和阉党专权、惑乱朝政。朱彝尊不“为尊者讳”的背后是对天启帝玩物丧志、本末倒置的荒政行为的批评及对明朝“圣君之道”渐失渐远的痛心。
对比朱彝尊对明崇祯皇帝御书的评价,“即如此书书法丽,远过师宜官楷钟繇隶”[13]916,其真正意图不在夸赞崇祯帝书艺之高,而是肯定他履行帝王职责的尽心与能力。崇祯帝不好女色,几乎一心扑在重振朝纲、中兴明朝的事业上,所以朱彝尊赞其:“万几余暇乐事存,爰有妙翰昭乾坤”[13]916。书法对帝王来说是“余暇乐事”,对帝王书艺的评价也应聚焦帝王是否具有日理万机、心怀天下而鞠躬尽瘁的道德行事,而不应斤斤计较于点画笔墨。但可惜崇祯有“圣君”潜质,却无“圣君”时运,这种遗憾也是朱彝尊评价崇祯帝书法时的感情基调。
五、 结语
清初诗人在对明、清帝王书法的题咏中流露出本民族性格中一种深沉的感情——对于圣君的呼唤。诗人们对明代几位帝王书法的哀婉之情,是对于圣君传统中断的悲痛,而对清代帝王书法的赞美,尤其是对康熙书迹的褒扬,实际表达了对圣君降世、缔造盛世的喜悦。诗人通过追比远古贤王的“尧文羲画”说、在下瞻仰的“云汉天章”说及与《兰亭》相比较的“超越书圣”说传达了汉族知识分子心中圣君的形象:圣君应当像远古贤王一样,以人文化成天下,保证贤能之才能够继承“圣君政治”的传统;君主既要像日月丽天般光辉圣明,还应处理好德行政事与游娱艺文之间的关系。帝王书法不因帝王出身而高贵,而是因帝王的圣明而高贵。这正是清初朱彝尊、王士禛等诗人评价明、清帝王书法的根本题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