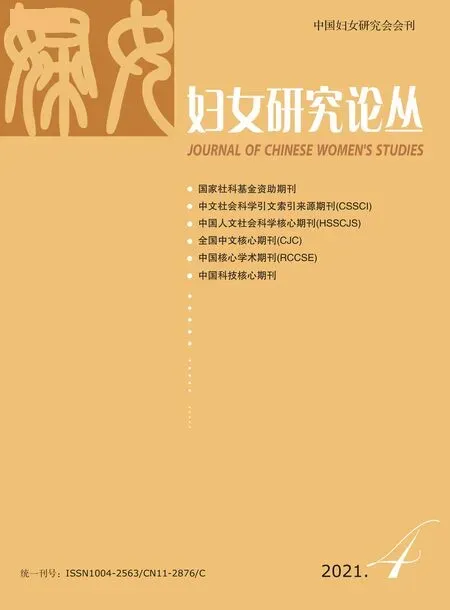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丁玲精神转向研究
——基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乡村图景的考察
潘炜旻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一、引言:主体锻造与精神性文本
丁玲谈自己,或是研究者论丁玲,都不限于将丁玲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作家,这是因为丁玲的一生与中共革命有着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出生于清末、成长于五四浪潮中的丁玲,受五四诸多观念感觉影响,在“极容易对一切不满”[1](P 238)的彷徨、苦闷生活处境中,抱持着“以天下为己任”“济人民于水火”[1](P 305)的志向;大革命失败后,意欲探寻“中国、人民出路”[1](P 230)的丁玲思想日益左倾,之后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经过慎重考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丁玲辗转延安,后参与1942年的整风运动、1946年的晋察冀边区“土改”实践,努力适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实现思想情感改造……丁玲的生命历程恰与中共革命实践兴起、探索与展开的过程相互对应,丁玲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正内嵌于她这一不断变迁的生命历程之中。而在这一与中共革命相伴相随的历史进程中,丁玲展现出的生命经历的曲折性与丰富性,与中共革命形成了“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2](P 11)的复杂关系。这使得丁玲被学界视为“不简单”[3]的对象,成为重谈20世纪中国革命浪潮中值得被反复讨论且需要被复杂化的人。而且,学界尝试在丁玲与革命同行的框架里,不断追寻丁玲的逻辑、左翼知识分子道路、革命文艺体制等诸多命题(1)参见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第5期;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何吉贤:《丁玲与中国作协》,《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冀望通过这一个体的生命经验与文学书写,透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思索更为深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问题。
环顾革命作家丁玲与中国现代革命复杂交织的一生,其生命状态呈现出两个特征:作为革命者,丁玲尝试不断破除自我与民众的隔阂,探寻“与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浮沉”的“沉入人民”[1](P 230)的路径,从而使其生命展露出独特的勇毅与韧性;作为作家,丁玲的文学写作一直保持着为中国人民、社会进步负责的严肃态度,而且希望通过不断“突破自我的生活圈子”[1](P 225)以拓展文学创作的宽度与深度。正是丁玲作为革命者与作家的这种内在心灵冲动,以及她在这种冲动下做出的重重调适与践行,使得“主体改造”“精神转向”成为丁玲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折射了丁玲与革命相始终的精神演变过程。为此,有研究者敏锐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丁玲那样,其革命生涯的演绎是由一次次的转变所组织起来的”[4]。但是,整体把握丁玲不断转变的生命历程,其最重要的两次主体改造,恐怕是她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逐步发生的精神转向,以及1942年受《讲话》影响参与“土改”实践引发的主体变更。20世纪30年代的“左转”,使丁玲从五四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左翼作家乃至“党的螺丝钉”,在写作上则将描写对象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投向时变中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抗争的工农大众。1942年《讲话》下的转向,则促使丁玲在既有左翼立场上调整主体状态,在乡土基层展开革命实践,从而使其从左翼作家转变为基层革命实践者,使其文学书写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
考察丁玲革命生涯中的这两次重要转变,其相同之处在于皆带有外部政党政治引导、内部丁玲自身响应的双向互动性质;其不同之处在于丁玲于1942年《讲话》下发生的主体改造,背后背负着更强的政治压力。根据丁玲的追述,她在整风运动期间经历的并非是完全平顺的自我改造,而有时“感到某种痛苦”[1](P 252);而且,伴随党内对丁玲1933年南京囚居历史的审查,这种政治压力也在不断加剧[2](P 252)。这使得1942年丁玲开启的主体改造,最初不完全出自自主自愿,确实存在承受政党政治压力的面向。但是,自1944年丁玲解除党内的审干压力、有意识地开展自我“挖心”“反省”[5](P 267),1946年开始从事长时段的“土改”在地实践,丁玲不仅经由这一主体革新过程完成了其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而且将1942年政党强力要求下的主体改造逐步内化为坚定的认同。正是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丁玲,肯定《讲话》开启的“文艺工作者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6](P 108)的路线,反复申言知识分子参加群众斗争生活、放下自我感情与趣味、培养与群众“血肉相连感情”[6](P 151)的必要性,从而化身为“新中国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改造典型”[7]。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丁玲,亦是不断为《讲话》辩护,申述《讲话》在“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生活”[1](P 223)等方向上的价值性,以及《讲话》在思想转变上给她带来的推动力[8]。那么,经历了1942年与整风运动苦痛的磨合、1946年长时段的“土改”在地实践,中共革命给丁玲的生命究竟带来了什么,从而使其对于主体改造的信念变得如此执着?如果说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自我革新之后,将文学书写的焦点对准“都市知识群体之外的工人和农民”[9],丁玲在1942年展开又一次主体改造之后,同样将农民视作文学书写的对象,那么建基在这两次主体改造之上的文学书写之间存在何种异同关系?这些问题,关涉丁玲在与革命同行过程中与革命政治演进形成的复杂关系,丁玲主体由左翼立场向革命实践转变、由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主体逐步过渡,丁玲文学写作由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化的进路,构成本文背后的意识与关怀。
倘若我们把《桑干河上》置于上述言及的“丁玲主体由左翼立场向革命实践转变、由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主体逐步过渡,丁玲文学写作由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化”的视野中来看,《桑干河上》是丁玲生命中重要而独特的作品。而且,它启发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重新解析《桑干河上》。其一,《桑干河上》不完全是一个封闭性的文本,更是一个敞开性、过程性的文本。它是丁玲受《讲话》影响引发主体改造后的产物,与“丁玲主体改造”共同形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事件。有学者指出,1942年《讲话》的“针对性超出了文艺”,其主旨并不限于文艺配合政治,而是指向“在革命深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革命主体应具备什么样的认识和实践条件”[10]。就此而言,“丁玲主体改造—《桑干河上》写作”可以成为《讲话》与革命主体互动这一结构下意涵丰富的代表性事件:一方面,它自上而下地显示了《讲话》对“革命主体如何深入中国社会、文艺如何与现实深度结合”这一议题而作的设想、探索;另一方面,它自下而上地体现出丁玲作为革命作家积极配合此构想而开展的尝试性摸索,具象化了《讲话》调适革命主体的过程与效果。其二,《桑干河上》不纯粹是一个文学文本,更可以成为丁玲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主体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精神性文本。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呼应左翼大众化运动号召,决意以农村农民为叙写对象;1948年的丁玲在主体革新基础上,写作了反映“中国农村、中国新人”[11](P 47)的长篇小说《桑干河上》;20世纪50年代的丁玲根据在地实践的经验,发表关于深入乡村基层与农民大众的系列思考,这一过程浮现出丁玲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变迁的精神历程。而《桑干河上》则是丁玲这一精神史转向过程中过渡性的文本,遗留了丁玲这一时期精神转折的痕迹。就此而言,倘若我们采用更宏阔的视野、更多元的视点重审《桑干河上》,考察其在革命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生成条件,探寻其形式背后含藏的作家的精神状态,或许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拓深对于丁玲主体革新过程的认知,撑开对于《桑干河上》文本的读解。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丁玲的整体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状况:一方面,对丁玲1930年“左转”后至1942年《讲话》前作品的研讨要更充分,推进更深广,并特别关注丁玲“一些有争议性的作品,诸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夜》等”[7];另一方面,已开始愈发关注丁玲整风后的主体状态、创作状况,但相较于《讲话》前丁玲的研究,学界对《讲话》后丁玲的探讨仍存在可以延展的空间。至于当下的《桑干河上》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主要采取两种阐释路径。一是从作家作品论出发探析《桑干河上》对“土改”运动的叙述(2)参见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现代中文研究》2014年第6期;王碧燕:《“土改”开创的“政治空间”与有待完成的“翻心”实践》,《现代中文研究》2020年第4期。。这些讨论往往视《桑干河上》为自足的文本,着力于将文学文本与革命历史进行对勘,探析该小说如何叙写“土改”政治运动。这些讨论的价值在于,开启了对《桑干河上》更历史化的阐释,丰富化了对《桑干河上》细节的读解;这些讨论的问题在于,往往将作品视为相对独立封闭的文本,既没有深入考察《桑干河上》在历史中的生成过程,亦没有注意到作家主体对文本的干预过程。二是细致辨析《桑干河上》中交织的多重话语,呈现丁玲与革命政治的复杂关系(3)参见刘再复:《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这些研究的价值之一在于,打开了被过度政治化解读模式所捆绑的作家作品研究,不再将革命作家的作品看作对政治理念的一元论意义上的复述,而是引入差异、裂隙、不确定、压抑等范畴,将文本视为一个多种复杂因素的耦合过程,由此复杂化了《桑干河上》的文本呈现。但是,这些研究采用文学/政治龃龉框架,通过将《桑干河上》纳入此单一视角,探析丁玲主体对政治话语的屈服与反抗,则既有可能忽略丁玲生命在革命映照下更丰厚的面向,也似乎无力回应中共革命何以能够深刻浸润丁玲。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尝试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主体与文学书写的互动关系为轴线,将《桑干河上》纳入丁玲长时段的写作演变脉络之中,通过对读《桑干河上》与丁玲早期文学书写方式的差异,探察创作《桑干河上》时丁玲变更了的感知结构。而本文之所以要把“感知结构”纳入考察焦点,是因为透过丁玲不同时期及创作《桑干河上》时的感知状态变化,可以间接看到丁玲主体状态的变动,中共革命渗透丁玲的过程、方式以及程度。不过,意欲深入探究《桑干河上》与丁玲早期文学的关系,仍需借助一个具体而微的观察支点,为此,本文择取丁玲对“乡村图景”的构造为切入点。在丁玲小说中,乡村图景往往由自然风景、空间场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空间场景”是农家人日常生活的空间,“自然风景”则是环绕村庄的乡土景致。一方面,丁玲借助这两个异质部分,在农村小说中拼合出完整的乡村图景,并形成贯穿性的乡村图景叙写脉络;另一方面,不同阶段的丁玲对乡村图景的构造方式显出微妙变化。而丁玲这种“绵延—断裂”的农村图景书写状态,恰恰提供了这样一重可能性,即透过丁玲小说中乡村图景的嬗变,探讨形式变更背后蕴藏着的更深广的意涵。
二、自然风景的变更与新感知结构的重构
(一)左翼立场下的多重困境
本节试图以“自然风景”为切入点,勾勒丁玲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作品对乡村景致的构造。正如研究者所言,对“乡村风景的书写”,是丁玲“前期文学创作具有贯穿性的线索”[12]。而在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转”后写作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更显出她“对于土地的粘性和农村风景的爱好性”[13]。比如,在丁玲“左转”后写作的《田家冲》(1931)中,丁玲的叙事重心在于勾勒出生于地主阶级的三小姐与家中乡下佃农的互动、对农村革命运动的介入。但在叙写过程中,丁玲却有心为叙事的铺展点缀大量均质化的田园风光,并通过它们在小说中的不断复现,构造出安定、纯美、罗曼蒂克的桃源仙境。但遗憾的是,这些乡土景观与小说中不同身份人物的感觉机制、心绪转折,往往缺乏内在关联。因此,这些同质、浪漫化的田园景致与小说的乡村灾难主题、苦痛氛围相撕扯,淹没了农村现实的复杂性。为此,两年后的丁玲对自己的创作状态做出反省,检讨自己乃是在“用中农的意识”[5](P 17)去认知农村,对农村境况、情感的体察都存在问题,这导致她把农村描写得过于秀丽安定,其文学实践与现实情势产生较严重的偏离。但是,虽然1933年的丁玲对自身状态、文学形态做出省思,但主要活动于上海亭子间的她并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深入乡村、重塑现实感的路径(4)根据丁玲回忆,她在左联时期主要参与的是编辑《北斗》、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学演讲、工人文学小组等活动。在左联时期,丁玲与工人尚有一些较为密切的互动,却匮乏与农民深入交往的机会。参见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这使得丁玲之后的书写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比如,丁玲的这一书写状态,同样映现在她更晚创作的《团聚》(1936)中。在小说中,丁玲亦运用相似笔法勾勒出一幅幅审美式的自然图景,在这些自然图景中,乡间风物、生活滋润着人物,人与人形成亲密、依赖的关系。但这些自然图景与小说情节(绅士家庭衰败)的推进、整体的悲剧气氛多少有些偏离,这使得它们的功能最终演化为“为故事垂下不相协调的浅色农村幕布”。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显现出的书写形态,很深透射出左翼立场下丁玲的主体困境: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接受左翼理念,意欲以乡村衰败为文学叙事的布景,但此时的丁玲暂时无从获得深入乡村基层的进路,未能建立起对农村真切、深厚的感知。这使得丁玲在文学书写时无法为其农村认知框架赋予乡土生活的实在感,最终导致其小说中衰落的乡土认知与明朗的农村图景之间往往闪现出难以弥合的裂缝。
叙述拖沓、结构散漫是丁玲早期小说以此方式构造自然风景所引发的诗艺问题。而透过丁玲对风景中人/景关系的描写,则可更深瞥见其自身状况性。例如,在以南方农村水灾为题材的《水》(1931)中,当丁玲刻写弥漫着紧急灾变、民众沸腾情绪的场景时,仍有意识地去描摹四野风景的动向。丁玲对这些风景的描写,有些意在渲染嘈杂、恐慌的氛围,内嵌于场景、人群中;有些却出自自身审美情致、抒情意兴,跳脱于小说情节、氛围之外。这意味着当丁玲以农村农民为核心展开“新的小说”[14]创作时,她没有彻底抛开自我意识,完全滚入灾祸中村庄人的心境、情感之中,以内在视角勾勒出灾难中民众的生命之痛。冯雪峰曾指出,“(《水》)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与感情”[15],可谓敏锐。丁玲的这种书写状态也同样显现在她抵达延安后创作的《东村事件》(1937)中。在小说中,通过构造月色遍满、幽谧的夜晚山林之景,丁玲引出主角陈得碌。这个忧郁的年轻人孤坐于山野间,并凝神眺望地主赵老爷的屋子:
在山的那边,月光丛浓密的树丛罅隙处漏下一片片银光洒在软软的泥土上,洒在矮矮的乱生着的草地上,和一些石块上。这些石块都很大,因为年代久了,上面满印着图案似的松针形的花朵,也有一些淡淡的鸟粪的遗迹。在一块石块上,傍着树根的地方,孤独的坐着一个人。
他愿意看那稳稳睡在脚下的一大片房子,这被苍翠群山环抱的一所粉墙大瓦房。它显得甜美酣适,而睡在它前面的那片大打谷场,在一排垂柳之侧,镜子一样,像一泓湖水。偶尔看见一星火星渔火似的闪耀一下,倏忽又消灭了[16](P 136)。
此处,丁玲运用比拟手法(以“睡”指代“坐落”)、采撷纯真意象(诸如粉墙大瓦房),将赵老爷的“大瓦房”置于静谧、恬淡的风景中。但是,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同样表现农民视域中地主李子俊的家,却使用平实、客观的笔触点出李子俊家的院子、走廊上的狗、台阶、万年青的瓷花盆:
他们几个轻轻的走了进去……栓在走廊上的狗,跟着汪汪的吠了起来。他们几个站在空廓的院子里……那女人忽的跑下了台阶,就在那万年青的瓷花盆旁边,匍匐了下去[17](P 159)。
潜流在这两个文本叙述差异之下的,是农民审视地主心理的异质性:在《桑干河上》贫农的视域里,流淌着困窘民众长期忍受经济差异所造成的局促与怯懦。但《东村事件》中陈得碌的“眺望”,在触及地主家的“甜美酣适”时,却流荡出意味深长的欣赏情意。面对粗暴占有未婚妻的地主,陈得碌流露出这种心态颇有些怪异。在《暴风骤雨》(1947)中,同受压迫的老孙头望见地主韩老六家的黑大门楼时,泛起的是“对地主不屑、怨怒与恐惧交织”的混杂心理[18](PP 9-10)——这里,老孙头的情感输出贴合人物的形象设定、社会身份。但在《东村事件》中,陈得碌的心理与其憎恶地主的形象却形成了一道错缝。这不经意的、细微写作裂痕,透露着丁玲不仅没有以内在于农民的视角展开书写,而且与其状写对象横亘着情感隔膜。
此外,陈得碌徜徉的这片山林之景富含雅意、满载抒情,也与普通农民对其惯常生活的乡村世界的感知显得隔阂。而且,丁玲有时会使陈得碌以游离于核心事件的姿态,咀嚼周遭风景及其意境。比如,正当陈得碌、王金与赵老爷尖锐对峙时,丁玲却荡开一笔,细写陈得碌望见院子里密密的梧桐叶、阳光与阴影、阴湿土地。陈得碌这些瞬间性的细腻视点、心灵震颤,与小说怨怒的农民角色设置、紧迫叙事节奏显然不完全契合。而除了陈得碌,《东村事件》中的陈大妈、桂姐、老幺等角色,也拥有这种相似的感触诗意空间、徘徊于忧郁的敏感心灵。因此,这些农民共享了用审美式风景关照村庄的感觉方式、被孤寂萦绕的怅惘情绪。《东村事件》中农民的这种感觉、情绪状态亦可于《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我”的形象中寻见。在小说中,初入村庄的“我”携带着一种寂寞、苍凉的心境,这种心境被人物所观之景暗示而出。如丁玲描写“我”寻觅贞贞之途,将一片风景纳入“我”眼中:
山上有些坟堆,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边有些断了的石碑,一个人影也没有,连落叶的声音都没有……天边的红霞已退尽了,四周围浮上一层寂静的、烟似的轻雾,绵延在远近的山的腰上[16](P 229)。
这些山中坟堆、断裂石碑的意象,堆砌出一派荒凉与落寞的景致。它们与“我”失落的心境相通,暗示出“我”刹那间的隐秘心灵,因此为“我”所觉察。可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知识分子“我”与《东村事件》中的农民,虽然社会身份不同,但感知、情绪结构却相一致——皆以诗意眼光审读着萦绕村庄的雅意风景,孤独守护着自我为阴郁缠绕的心境——这就使得《东村事件》中农民的感知结构,多少弥漫出文人寄情山野、排遣愤怨的意兴。而在《桑干河上》描摹民兵队长张正国“极目四望”村庄空灵风景等笔触中,我们仍能在人物身上隐微寻见这种未被彻底排挤出的感知结构。不过,丁玲对这样的人/景、人/情关系叙写却颇为克制。这表明,多年后丁玲意识到,这种感知结构不足以充分涵盖基层民众与其生活世界形成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向左转”的丁玲,虽然积极响应左翼话语号召将观察视角伸向农民,但还没有明晰意识到这些和她生活在相同时空中的人们,因地域区隔、历史遭际、生命轨迹等的分别而有着与自我不尽相同的对于生命的别样感受;而且,为了抵达这个活力、饱满的生活世界,左翼作家需要先行搁置自我意识,顺势进入他们的生平际遇、认知结构、情感世界等,才能由此真正深入他们的生命状态。正是这种意识状态最终左右了丁玲对基层民众感知结构的观察,使她更专注于捕捉农民趋近于自我审美、意趣、感受的生命面向。当丁玲将这种有局限的现实体察植入文本,又使其笔下的农民始终是被自我意识所过滤的单薄的农民。而丁玲自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这种现实感知、自我意识,对其主体成长、革命实践、文学创作都可能带来一定的损伤:对于作为主体的丁玲而言,这种相对封闭的自我感知方式将会形成一个围困自我的牢笼,即使自我看似不断接触外界,此外界也将是永被特定感知“截图”后的外界,并不具备深度突破自我的功能。对于革命者丁玲而言,如果总是被围困在这种自我感知之中,将阻碍她视农村农民为需要用劲深入的异质对象,影响她以更内在、多面的视角审视农村农民,并最终导致她难以真正触及基层形态、翻转中国现实。对于丁玲的文学而言,她渴望深入大众与中国现实,但这种感知方式和表述机制却使她反而疏离了大众与现实,这多少限制了她对社会现实深度和广度的开掘。
在丁玲早期小说——诸如《田家冲》(1931)、《团聚》(1936)、《东村事件》(1937)中,乡土风景如同独立变幻的空间,时常疏离于小说中的人物,其功能演变为提示读者注意情节所铺展的农村布景。但到《新的信念》(1939)中,乡土风景与人物的对抗性逐渐消融。丁玲这样引出她的人物:
走过几排疏疏的树林,在平原那端,静静地躺着细柳村。沿村的堤上有一排杨柳,叶子都脱落了,在冬天的劲风里,枝条乱舞着……一小队一小队的乌鸦,飞过来,在村顶上打了一个圈,投入山坡上的枣树林立……[16](P 161)
这是一派不同于丁玲往昔小说的象征化风景:一方面,它表征日本兵侵略村庄后肃杀而惨淡的境况,并营造出故事的基调与氛围;另一方面,它与陈新汉的出场遥相呼应,暗示出人物在探寻亲人是否生还时交错的悲哀、惊惶心理。丁玲笔下风景的这种状态——与小说整体意境、人物内在心理相互扭结——贯穿于她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小说之中,表明此时的丁玲试图借助自然风景更为深入地开掘村民的内在情绪与心灵。而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丁玲有意识地转换了她20世纪30年代构造风景的形式:在《田家冲》中,丁玲是以质朴、轻快的洗炼手法描绘风景——“太阳晒在树顶上,从微微皱着的水里看见蓝色的天,天上又飞着淡淡的白云”[19](P 368)。但在《夜》(1941)中,丁玲同样描写云朵,却运用“厚重”“靛青色”等语汇予以层叠修饰;描写天空,不仅叙述天“快黑了”,也勾勒云层上“淡黄色的水波似的”“变换着的”光线,展现天空的晦暗与阴郁。这里,丁玲是如此敏感于自然变幻,注意为意象添加繁复的前缀修饰词,并通过意象的相互配合呈现出有韵味的意境。这种强化意象、意兴的构造方式,增进了风景与人物隐微心境的勾联,但也削弱了风景的写实性。
不过,尽管风景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变更,但20世纪40年代初期丁玲感知、书写农民的方式却未发生本质变化。这一点,比读丁玲整风前写作的《夜》与其整风后写作的《桑干河上》可见一斑。《夜》是丁玲于1941年2月至3月在延安县川口区农村体验生活时写作的小说,以新人边区乡指导员何明华为事件主角。对于何明华,有研究者曾运用社会史视野厘清了他的“前中共身份”,指出他曾是陕北传统社会底层男性“站年汉”;梳理了何明华的成长过程,申述他是通过参加赤卫队、加入共产党而从“站年汉”逐步转变为新政权的基层代理公家人[20]。不过,在叙事推演过程中,《夜》关切的却既非何明华作为新政权下新人汇入革命的成长历程,亦非何明华作为乡指导员在乡村推展艰苦工作的步骤与环节,而是他私人欲望与公家人理性意志间的冲突抵牾[3](P 241)。这使得在《夜》的叙事线索中,何明华作为民主政权干部的身份演变成抽象符号,他参与解放区基层乡村的行动事迹被简略滑过,他与三个女人间的朦胧情愫转而成为叙述的动力。丁玲对《夜》中基层革命干部何明华的刻画与其整风后对新人的塑造颇不相同。如丁玲整风后创作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等报告文学,无不是在细致叙写解放区新人的养成经验及培养机制[21],反映出丁玲观察解放区新人视角的变迁。而在《桑干河上》中,暖水屯村农会主任程仁同样面对私人情感与公家人身份的纠缠,丁玲却十分克制对程仁个人情感纠葛的书写。这种节制涵纳了丁玲对农民感知结构新的理解,因丁玲后来觉察到将“风月、友情、恋爱、女人”作为主要谈论对象,是部分知识分子从自身意趣、悠闲情绪出发对农民做出的简化认知(5)丁玲曾在多处批判知识分子趣味的问题性:“什么叫艺术,你总以为是那些美丽的词藻,幽雅的情致……但这些书表现了一个时代,它教育人民……这些要素是我们肯定艺术性的最重要的东西”;“知识分子喜欢绿杨城郭,他们喜欢肥美的庄稼;有的知识分子喜欢谈风月,谈友情、恋爱、女人,他们喜欢谈天气,谈村子上的事,谈打游击,谈土改,谈整风……这怎么能说是人家的短处呢?是自己的趣味太停留在悠闲的知识分子的情绪上了”。参见丁玲《在前进的道路上》《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等文,载《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丁玲的这种批判存在疏略之处,因为农民并非不论及此类私情、欲望,只是其感受、表达方式受制于乡村伦理、文化传统等要素而与知识分子有所差别[22]。但是,这种省思又提供了一种读解丁玲20世纪40年代初期写作状态的视角: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丁玲从自我原有感知、审美、情致出发裁剪农民生活、情感的方式,并未在40年代初期获得真正突破。这进一步说明,虽然丁玲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吸纳左翼话语转向描摹农村农民,并且在辗转延安后始终遵循这一写作方向。但是,此时“住在窑洞”尚“不知道如何下到群众中去”[1](P 193)的丁玲始终没有明确意识到,她在左翼立场下发展出的现实感、自我意识,有时会成为她内在感知农村农民的屏障,限定她的社会现实感,因此不能充分指引她深度抵达基层群众与社会。正是囿于这种意识,在主体状态层面,即便丁玲1936年奔赴延安后生活在农民中间,并拥有多次流动下乡、深入农民群众的契机,尚没有转换意识、开放自我的丁玲很难真正深进农民的生命世界;在写作层面,拘于强烈的个体意识与审美趣味,丁玲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将农民的状态与行动、农村的图景窄化,并收束到自我意趣、自我审美之中。
(二)现实感与自我意识的调适
依据丁玲回忆,受到“左联”大众化运动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她已在话语、情感上认同农民,并致力于写作“工农大众、普罗文学、无产阶级”。但是直到经历《讲话》,丁玲才认识到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存在多方隔膜,左翼作家需要转变为革命实践者,以政治政策为中介进入基层社会,重建乡土经验与社会感知;作家需要在这一深入基层的过程中内在地感受农村农民,转换固有的“感情、兴趣”[8],以“真正表现工农兵”、构造出新的文艺形态。而后,在经受了煎熬的整风、审干之后,丁玲带着践行《讲话》方向、自我重塑的意识下到延安边区的农村、工厂采访,写作了系列报告文学——《田保霖》《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被称为“新的写作作风”。对此,已有诸多学者探析了丁玲这些报告文学的新质所在(6)参见刘卓:《“新的写作作风”——探讨丁玲整风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路杨:《“新写作作风”:报告文学的再生产机制》,《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不过,相较于丁玲1944年及其之前流动而短暂的下乡、问访活动,丁玲1946年参与的晋察冀土地改革运动,对她产生了更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段“土改”经历中,丁玲开始真正转变为一个基层革命实践者,并在被“土改”运动迅猛搅动、政治情势颇为复杂的基层社会中,更深消化、巩固、探索着《讲话》开启的诸多意识与方向。
丁玲参加晋察冀“土改”运动的经历要稍向前追溯至1945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9月,党中央即派出几批干部团奔赴东北。丁玲等亦决定组织延安文艺通信团前往东北,计划一路停留采访、写作通讯报道,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和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1945年10月中旬,丁玲、陈明、杨朔三人一道从延安出发,于12月抵达张家口。就在丁玲等待晋察冀中央局安排前往东北时,国共内战爆发,通往东北的交通中断,丁玲只好暂驻张家口。就在丁玲滞留张家口期间,1946年5月4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即在晋察冀根据地内普遍铺开。敏感的丁玲立即对五四指示做出积极响应,“向晋察冀中央局提出要求参加晋察冀的土改工作队”。自此之后,丁玲开始了不间断参与土地改革的实践,从1946年7月陆续持续至1948年6月,历时将近两年。可以说,正是依托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区文艺生产体制,丁玲得以以外来中共干部的身份深度介入乡村基层。仔细考察丁玲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的“土改”经历,可以将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46年7月到9月以河北怀来县、涿鹿县为中心的“土改”;1947年5月为期半个月以冀中行唐县一带为中心的“土改”;1947年11月到1948年4月以解放后的石家庄获鹿县宋村为中心的“土改”[11](P 45)。但是,丁玲参与每一段“土改”的状态、与不同“土改”地构建的关系并不相同。首先,在河北怀来、涿鹿县,在内战紧急形势下,丁玲初次在基层展开政治实践,对农村工作“很外行”[11](P 97)、“不大胆”[1](P 179)、没有形成太多“接近群众的办法”。因此,当时的丁玲只是“在旁边当顾问、参谋、出主意”[6](P 392)。但是,这段“土改”经历给丁玲创作《桑干河上》提供了村庄与诸多人物原型。其次,在冀中唐县一带,丁玲采取走马观花式的旁观策略,意图了解“走群众路线的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作用。这段生活虽然没有为《桑干河上》提供太多直接材料,但仍然发挥了潜在的作用。再次,在石家庄获鹿县,丁玲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深度“土改”。当时的丁玲是土改工作组组长,负责一个乡、五个村子的“土改”工作,并且以宋村为自己负责的中心土改点。在政治形势复杂的宋村,丁玲进行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系列“土改”工作,工作艰苦、深入且细致。经历了这一实践过程的丁玲,在把握地方社会层面“比当地干部还要熟悉当地情况”[23](P 105),在心态层面则以为“当村长或者支部书记”比“写文章”更有兴味。这一段“土改”经历对丁玲的写作颇为重要,因为直到这一段“土改”工作结束,丁玲才最终完成《桑干河上》,并在重新检讨1946年“土改”经验的基础上修改了《桑干河上》的原初写作计划。以上梳理充分说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是丁玲自觉践行《讲话》深入工农兵方向、投入乡村基层、参与革命实践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间段里,丁玲虽然自觉到自己的作家身份,并在“土改”期间穿插了对《桑干河上》的写作,但她确是以基层干部身份深度参与乡村工作为基点(7)根据陈明回忆,1946年的丁玲并非是带着写小说的意识参与土改,而是在土改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写作长篇小说的构想。参见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而且,在这一“土改”实践之中,丁玲对于农村工作方法及地方社会,经历了从“完全外行”“无法深入群众”到“极熟悉情况”“人缘非常好”的渐进深入过程。正是以政治政策为中介对基层社会展开细腻摸索的状态(8)《讲话》要求“文学配合政治”“文学以政治为中介理解现实”给革命作家提出的多重挑战性,参见何浩:《“搅动”—“调制”:〈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使得丁玲这一阶段的“土改”经历与其之前的下乡经历展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桑干河上》的持续写作、反复修改、最终完成,则伴随了丁玲这一长时段的革命实践过程,叠加了丁玲多段土改的经验,带有很强的“深入生活”的意味。
1946-1948年间的丁玲曾作为革命工作者专心专意投入基层,“与民众一起滚,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同忧戚、共欢乐”[1](P 226)。当丁玲暂时从“土改”实践中退出,咀嚼消化这些生活经验写作《桑干河上》时,她的自我意识状态和文学写作形式皆在有意无意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丁玲对《桑干河上》中风景的构造就与其整风前的书写迥不相侔,闪现出丁玲这时期主体状态的微妙变动。总体上看,《桑干河上》对风景的构造显示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丁玲仍旧颇为留意对乡土风景的细腻描绘,这使得乡村景致成为《桑干河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在“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中,为了铺陈暖水屯村民管控果子的事件、渲染事件中民众跃动的情绪,丁玲构造出一个“肃穆、清凉”的果树园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内部,丁玲调用重重浓重的意象——薄明的晨曦、不安带甲的小虫、喧噪的鸟雀、摆荡的树枝、润湿的果子、耀眼的露珠、透明变幻的薄光、流荡的新鲜香味,经由视觉、听觉、嗅觉多感官的交相配合,勾描出一派“葱郁”“富厚”“明丽”的立体乡村风景。这些乡村风景又与暖水屯村民“晴朗的笑声”“喜悦的感觉”相激相荡,共同烘托出村庄中为“诗歌的情绪与生活的热情所支撑的浓重气氛”[15](P 286)。依照丁玲的自述,《桑干河上》中的“果树园”并不直接取自现实,而是基于“在上面做文章”的意识而想象、虚构出的。这种虚构意识、刻写方式恰巧表明,丁玲延续了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对乡村风景的高度关注与特别兴致,依旧执着于精细勾画乡村风景。但是,与丁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不同的是,一方面,《桑干河上》对乡村风景的书写是相对克制的,丁玲乃是以人物状态为核心,将风景作为渲染人物心境、性格特征的手法,而且,丁玲并没有把风景作为农民对其乡村世界的核心感知;另一方面,丁玲虽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风景构造方式,即关切外部风景与人物内部心境的互相表征性,但抛开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趋于象征化的风景写作模式,从而使风景逐步向写实化倾斜。
第二,或许更重要的是,《桑干河上》描写风景的方式与丁玲之前小说刻画风景的手法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体现在丁玲对风景意象的择取、对乡村风景的感触、对风景与人物关系的理解皆与之前大不相同。如丁玲这样细描顾涌归来时沿途村庄的风景,这种书写闪现着丁玲新的现实感的获得: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黑又湿。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17](P 6)。
这片乡土风景与丁玲此前创作的小说存在很大差异。首先,丁玲摒弃具有观赏性的、雅致的乡土景观,转而择取密切勾连农民农事生产的意象,诸如稻穗、泥土、水渠、菜园等。这种意象的更转,彰示着丁玲对村庄图景、农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新观察与新理解:覆盖农村周遭的审美式风景逐渐退却,以农事为核心的村民/村庄关系正在浮出。其次,丁玲采用与20世纪40年代初期小说有别的写实主义手法,通过细腻描绘稻穗的密集、泥土的质感,着意于雕琢土地的肥沃、农作物的丰产。这样的风景图象抹去了风景的审美特质、作为心灵对应物的风景抒情性,渗出一种村庄生活的实在感。而这种风景图象中包裹着的人与景、人与情,均剔掉了外部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姿态,跃出了村庄内部人对其扎根的生活世界的喜悦感知。再次,在丁玲舒徐自如的笔触之间,跃动着一种新的对农作物、土地独特的敏感性:通过捕捉丰收时节多样的庄稼——稻穗、谷子、高粱、玉茭,丁玲构造出被精细规划、显出多重空间层次的具象的土地;通过视觉、嗅觉等多种感官的立体配合,丁玲描摹出身临庄稼丛的农民对于土地多向度的感受。丁玲的这种“敏感性”,喻示着她体认农民感知结构、基层民众与其外部世界关系的变更:村庄自然对于村民而言,不止是赏析、情绪纾解的对象,更是他们坚实生长、心手改造、与性命息息相关的场域。此外,从张裕民望见葫芦冰、李宝堂观看果子的场景中,皆可以寻见这种从乡人内在视角出发的风景,这种风景里裹挟着他们与“土地深切的关系”、与村庄自然更为丰厚的连带。透过《桑干河上》的这些风景写作痕迹,恰恰可以捕捉到这时期丁玲意识状态的调整:写作《桑干河上》的丁玲已在对基层社会的探索中体悟到农村的多面性与农民的丰富性,因此决意掷开自我固有的感知、审美、趣味,更深地进入农民的生活情感世界、感知结构。就在丁玲不断深入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她不仅获得了对农村农民新的认知,而且重构了自我原有的感知结构。正是这种被拓展的感知结构,使丁玲得以采用新的贴近农民视角、钻入农民内在心理的方式展开更扎实的写作。
以上梳理了丁玲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初期及《桑干河上》对乡村风景的书写、丁玲感知结构的变迁过程;同时勾勒了丁玲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立场逐步转向1946年革命实践的过程。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丁玲即主动吸纳“左联”推动的文艺大众化理念而以农村农民为摹写对象,并且在抵达延安后始终热忱遵循这一方向,但在1942年《讲话》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抱持左翼立场的丁玲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在叙事话语、主观情感上认同农民;而无法意识到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横亘着多面的隔膜,革命主体因此需要推展大量艰苦工作、反复磨炼才能深度抵达这一丰富的异质世界。直到受《讲话》激发,丁玲才开始逐渐反思其左翼立场下的现实感与自我意识,意识到作家主体需要转变为一个革命实践者,以政治政策为媒介触碰复杂的基层社会,以此重构自我的社会现实感。1946年的丁玲正是带着这些被重塑的意识,以中共外来干部的身份投身于“土改”实践,在基层社会的运作逻辑中校验政策执行的正确与偏差。当丁玲以这段深度扎根基层的生活为素材写作《桑干河上》时,其文学书写便产生了有意无意的重要转变,尤其是丁玲对《桑干河上》中的风景构造与之前颇不相同,渗透出她对乡土、村民、“景—人”关系更深厚的理解。丁玲的这一书写转折表明,1948年的她在基层社会的磨砺中,已觉察到农村农民是一个需要自我不断用劲深入的对象,因此她竭力放下固有的自我意识、深入农民的生活世界与感知结构,最终由此重构了自我原初的感知结构。透过丁玲的这一精神转变过程,恰恰可以看到《讲话》对于丁玲的一重重要意义:《讲话》在丁玲原有的左翼立场上调整她的现实感与自我意识,破除她原有的现实感,使她觉察到自我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隔膜;打破她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她顺着政治实践的铺开进入基层社会,先行搁置自我意识、体贴深入对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丁玲在《讲话》前并不缺乏可以与农民建立深度关联的契机,但只有在经历了《讲话》的调适后才真正获得了这种扎根基层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说,《讲话》带来的现实感、自我意识的调整,对于作为革命者和作家的丁玲来说皆意义重大:对于革命者丁玲而言,只有调整原有的现实感、自我意识,她才能觉察到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并由此展开严肃谨然的摸索、细致的革命实践,从而使自我能够扎实介入基层社会;对于作家丁玲而言,只有调整这种现实感、自我意识,她才能意识到农村农民的丰富度,并在探索这种丰富性的过程中拓展自我的生活经验与感知结构,从而使文学书写与现实更深度结合。
三、空间场景的构造与新现实感的生成
(一)隔膜感的渐进破除
上一节旨在讨论丁玲不同时期小说对自然风景的构造,这一节则尝试围绕空间场景考察丁玲不同时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丁玲早期乡土小说对乡间自然风景有集中性的描摹,却往往疏于构造农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比如,在丁玲“左转”后写作的《田家冲》中,丁玲有心将叙事的着力点落在地主阶级出身的三小姐与乡下佃农一家关系的动态演变上,意欲描绘三小姐的革命教导在普通佃农家中激荡起的涟漪:伴随三小姐的到来、离去,一种刻苦的生命态度、新的生活信念正在困苦的佃农家庭中奋力生长。但是,在小说中,丁玲勾描佃农心绪心境被搅动的过程,却不是通过革命者对大众生活具体、细致的行动介入,而是运用三小姐的宣说、品格、教养所牵引出的感动力。于是,这位缺乏革命行动力的三小姐便只好出没于包裹着怀旧、忘忧风景的山坡、田野、树林;或在幺妹栖身的茅草屋宣说含蓄的启蒙理念。因此,《田家冲》中的空间场景,不仅与人物性格、行动并不密切交集,而且其丰富度与细腻感远不及小说中的乡村景致,这使得《田家冲》呈出的“以风景为轴心”的农村整体图景多少渗出一种单薄感。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丁玲尝试以“从地主女儿转变为前进女儿”的革命者为摹写对象,但她却无法写出具有更深连带的革命者与大众关系、具象的革命者介入基层的行动方式。丁玲的这种书写状态,既彰示出左翼革命话语感召下丁玲的热力,又透视出她直面乡土的无力感:面对时局转换中的新现实、新对象,丁玲虽然持有“真实的材料”,却无法为新人新事赋予更生动、细腻的日常细节。在丁玲同时期的其他乡土小说中,大众的生活空间则近乎隐没不见。如在以农村水灾为题材的《水》中,丁玲意欲展现水灾中民众“无名的”汇集及其抵抗自然、压迫时所爆发的“群力”。但在具体描绘过程中,丁玲将无法分辨出处的人物对话,洪水、锣鼓、哀嚎、骂詈交织的沸腾“声音”[24]视为小说的重心;而将支撑对话、声音展开的堂屋、堤坝、镇子此类空间,仅仅作为抽象、模糊的标识性地名——这使得人物的生活细节、细腻行动、鲜活性格都没有在这些空间中被展开。冯雪峰因此指出,“(《水》)是在于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15](P 252),不可谓不确。
但是,丁玲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中透射出的书写状态,却并非丁玲早期非乡土题材小说的写作状态。比如,在《梦珂》(1929)中,经由梦珂的身份转换、步履移动,美术学校、姑母家的大别墅、梦珂栖身的房间、电影院、无政府党人聚居地、大东旅社、园月剧社等都市生活空间在纸上跃然而出。这些“现代教育空间、普通市民空间、上流社会交际空间、消费娱乐空间”[25],汇聚成繁密的空间集合,构筑出一幅“繁荣又堕落”的都市图景。在这些空间内部,器物群与人群结构成立体、具象的场景,共同铺陈出梦珂对“纯肉感社会”的绝望体验。由此可见,在《梦珂》中,空间不是抽象、模糊的标识性地名,而是以其实在感、内外两维,参与小说的情节推进、旨趣传递与人物塑形。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9)、《日》(1929),则以莎菲、伊赛起居的公寓为空间中心。这些空间既是都市女性匿身的生活空间,亦是繁华大都会中被隔断、幽闭的空间,而人物终日闷处其间,不惮烦地重复毫无意味的行径——昏睡、幻想、恋爱,莫名地感到疲乏、厌憎、烦恼与无望。因此,这些空间与人物、行动结构成了立体的动图,暗示出都市女性空虚消沉、百无聊赖的生活样态,烘托出有热力却被阻隔的都市女性形象,彰显出后五四时代女性的生命困局。透过《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日》中的精细空间场景、人物举止、心灵辗转,可知长期在都市生活的丁玲,对大都会空间中都市现代女性性情、生活方式的熟稔;由此反观《田家冲》《水》等文本,则可见出匮乏于乡土经验的丁玲对农村、农民的隔膜。正是这种隔膜,造成丁玲早期乡土小说的多面困境:描摹的整体农村图景过于空洞、单纯、安定;不能在立体的日常空间、生活细节中雕刻出有厚度的农民形象;对革命者在农村基层展开实践的行动力描写过于薄弱。由此可见,虽然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响应左翼号召、转向描绘工农大众、以乡村萧条为叙事背景,但由于她长期寄居在城市,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无法获得深度介入乡土社会的机遇,她对中国乡土社会虽然有观念上的认知,却匮乏扎实、真切的经验体认;她对农村农民虽然持有同情心,但这种感情不仅抽象而且存在很深的隔阂。正是因此,多年后丁玲检讨自己这一时期的写作,批评自己虽然“很早就写过农村”,但“对于生活在农村里面的人物,真正农民的思想、感情、要求”,“还只是一些抽象的表面的了解”[15](P 81)。
“左联”时期主要活动于上海亭子间的丁玲,并没有获得与农村农民深入接触的在地机会。而丁玲得以深入农村、与农民展开频繁交往,是在她1936年进入陕北延安之后。对于丁玲而言,陕北是一个与她既往生活判然不同的异质空间:延安“城小”,“党、政、军人数也不算多”,“周围全是农民”,实则是一“农村环境”。生活环境的变化,又逼促丁玲锻炼出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建立起她对农村农民更深厚的察知:只要你一“走出机关,无论你干什么,总要和农民打交道”;而且,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八路军的声誉”是不足够的,而必须要与农民“搞好关系、和他交朋友”,使他“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1](P 81)。除此之外,延安时期的丁玲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接触工农兵大众的机会。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达成后,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从事宣传工作。丁玲被任命为该团主任,率领团员们辗转于陕西、山西等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在街头演讲贴标语、为当地群众作巡回演出、慰问八路军战士,历时约10个月。又如1942年2、3月,因为与萧军、舒群在编辑《文艺月报》时选稿意见不同,丁玲决定退出《文艺月报》的编委,并向张闻天“申述了工作中的苦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决定离开文协到延安川口区农村体验生活。丁玲在川口农村体验了为期约1个月的生活,并在这次下乡过程中写作了短篇小说《夜》。由此可见,转入延安之后的丁玲,因为环境的转换,得以获得多次下乡机会、与农民展开频繁交往。不过,总体考察丁玲这时期的状态,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虽然获得了与农民密切来往的机会,但她始终是以流动的状态而非以在地实践的方式介入村庄。丁玲这样“流动”的状态,缓慢拓展了她的农村生活经验,也多少限制了她对乡村基层的观察。另一方面,《讲话》前的丁玲尚未经过意识的调适,这使得持有左翼立场的丁玲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横跨着深远的隔阂,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放下固有的意识去贴近理解基层群众。带着这种现实感与自我意识踏入乡村基层的丁玲,不仅很难真正深入乡土基层,而且不易从多次下乡经验中积淀起更丰厚的社会感知。
不过,外部生活环境的变化、反复的下乡经历,仍然增进了丁玲对于农村农民的感知,同时促成了她文学书写的缓慢转变。比如,与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转”后的乡土小说不同,丁玲进入延安后以乡村为背景的作品——诸如《新的信念》(1939)、《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夜》(1941)等,对农民日常生活空间的筑构有所递增,对人物与空间关系的描绘趋向细密。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村公所、窑洞、杂货铺、教堂;《夜》窑洞中的灶、猫儿、孵豆芽的缸、炕角上的篓子、院子外的牛栏……构成一幅不同于丁玲之前小说的复杂化农村基层图景。这意味着延安时期的丁玲,通过在山区奔走、多次下乡,开始建立对乡土基层、农民生活形态更深厚的身体感知与体察。不过,在这些小说中,相较于空间场景,丁玲对自然风景的叙写仍更充分,而且她没有将书写自然风景的耐性、激情注入空间场景写作。如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展现老太婆“倔强灵魂的塑象”[15](P 242),使之浮现在她对自我伤痛、耻辱的公开言说中。小说在推进时,则将女性人物意识的觉醒、成长作为核心线索[26]。在丁玲这样的构思中,空间场景本身并不重要,涌动在场景中老太婆的话语、其与周遭人的情绪共构才是描绘的重心。同样,在《夜》中,丁玲对何明华形象的建构,主要不是依靠人物动作与举止,而是依托其在返家途中、与妻子争吵中的发散意识、心灵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何明华生活的空间仅仅只是故事布景,空间中何明华与妻子交锋时起伏变换的情绪才是叙写焦点。但在《桑干河上》中,丁玲描写顾涌的“归途”,却有意为人物编排一系列的动作,借此牵引出“中农”顾涌沉默、稳重、勤劳、谨慎、隐忍等多面的性格。丁玲前后写作的差异表明,《讲话》前的丁玲在塑造人物时,不仅颇为关切农民的心绪心理,而且意图运用心理剖析的手法塑造人物。在这种状况下,丁玲尚未明确形成将空间场景作为重要、独立部分加以勾画的意识,亦没有注意到空间与农民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丁玲对空间、空间与农民关系的这种理解方式又进一步说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丁玲在构造乡村图景、理解农民的感知结构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将审美式自然风景作为农村图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对其生活世界的核心感知。
(二)在地实践下的突进
上文提及,《讲话》对于丁玲的影响在于调整她既有的左翼立场:破除她原有的现实感,使她觉察到自我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隔膜;打破她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她先行搁置自我意识、内在地深入对象。正是经历了《讲话》带来的这种意识调整,丁玲决意离开知识分子局限的圈子,将自我“投向更广大的人民”[27];决心在顺承政治实践方向介入中国社会时,暂时放下固有的自我意识,努力深进基层群众的生命世界。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中共的“土改”实践对于丁玲而言,不仅是一场关涉经济分配、重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更是丁玲以中共“土改”运动为依托进入乡土基层,重构自我感知结构、社会现实感的锻炼场。在经历了这一“土改”实践之后,当丁玲写作《桑干河上》时,其书写状态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呈现在上文述及的风景描写方式中,也展现在丁玲对小说空间场景的构造里。丁玲塑造空间场景的“转变”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空间场景的独立营造开始成为丁玲的关注点。前文提及,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更为着意的是农村人的心绪心理,她尚未明确形成将空间场景作为重要、独立部分加以描绘的意识,亦没有注意到空间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考察《桑干河上》的整体写作,丁玲却在其间打造出了多个村庄异质空间:以钱文贵、李子俊为核心的地主家庭,以董桂花、赵得禄等为代表的先进农民之家,女巫白银儿的神秘空间,还有果树园、学校、合作社等诸多公共空间。《桑干河上》中的这些异质空间展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就空间内部而言,这些空间与村庄村民各自的经济状况、身份地位、性格特征形成纠结难分的关系,因此形态各不相同,呈露出多样性。比如,丁玲刻写暖水屯女巫白银儿的生活空间,有意择取“飘香的香烛”“烧尽的纸钱”“沉沉的红绸帐”“绣字的白飘带”等意象烘托出一副神秘诡谲的景象,暗示出白银儿特殊的身份。丁玲塑造村小学教员胡立功生活的空间,则选取“孙中山石印像”“毛主席画像”“‘为人民服务’标语”“墙上的作文和图画”“挂着纸花的霸王鞭”[17](P 108)等意象,暗示出胡立功的小学教员身份、多面兴趣、正直品性与盎然活力。透过丁玲的书写状态可知,这一时期的丁玲对“空间”形成了更丰富的理解:生活空间对于农民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颇为重要;空间与农民关系密切,因为空间不只是农民日常栖居、活动的空间,更是被农民各不相同的职业、爱好、品格所共塑的空间。丁玲注意到农民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喻示着这一时期的她已注意到农民生命丰富的面向,对农民的生活世界、感知结构产生了更深厚的体察。第二,就整体村庄而言,《桑干河上》中的这些众多空间集合,组成了相当密集、权力化的公私空间集合,拼贴出立体的整体村庄图象,浮现出埋潜于基层的错综社会关系。丁玲对一个村庄如此多面的观察,表明依托政治政策在地实践的她,开始注意到村落中的诸多空间及其背后的复杂性;而且在深度介入村庄的过程中,逐渐把握住暗涌于村庄之下的复杂权力格局。概言之,《桑干河上》对村庄多重空间的敏感、对空间更丰富的审读,写映着“土改”后的丁玲对农民感知结构的感受日渐丰厚,对乡村基层社会复杂度的感触日益深刻。
其次,除了增加对空间场景的构造,《桑干河上》亦力图增进人物与空间场景的共构性,这使得空间场景逐渐演变为丁玲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丁玲意欲通过制造特定空间,勾勒活动于其间人物的行径,渲染出人物内蕴的心境。如丁玲这样描写董桂花初见杨亮时的心情:她当时“只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背心”在院子里松土,在“看见”穿制服的杨亮后,便不顾劝阻“跑”进屋里要给杨亮端高粱米汤;当她再次出来时,已顺便“把那件破背心脱了,换了那件唯一的白布单衫”。通过构造屋里、屋外场景,状写董桂花拿米汤、换衣服等系列行为,作者暗示出她初见外村人拘束、尴尬的驳杂心理。这是丁玲“从行动、生活细节中塑造人物”(9)丁玲曾在多处谈及这种“表现方法”。参见丁玲:《谈文学修养》《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经验的文学表达。《桑干河上》的这种人物心理叙写方式,与丁玲早期乡土背景小说有所差异。如在《新的信念》(1939)中,对受邀上台、宣说耻辱记忆的老太婆刹那间的心理,丁玲不厌其烦地将之叙述出来:其写老太婆望见熟人“老远招呼她”,感到“一种新的感觉稍稍使她有一阵不安,似乎是羞惭,实际还是得意”;听到上台的邀请,她觉得一种“说不出的羞愧和为难”,但又“突然有了勇气”;而当她走上主席台,在高处望见密密杂杂的人头,她又“有些昏眩”,不知从何谈起。由此可见《桑干河上》《新的信念》的差异:前者旨在使人物以行动言说自我心灵;后者则依赖作者“代替”人物作心理分析与叙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丁玲在《桑干河上》中放弃了后者——它仍是小说构造人物心灵的重要手段;而是说在丁玲之前乡土小说中并不常见的心灵构造模式,在《桑干河上》中愈加被关注。这使得《桑干河上》中的农民形象,较之丁玲之前刻画的农民,获得了细腻的行动与生活细节。由此可见,“土改”后的丁玲已开始有意识地变换她对于农民的观察:丁玲试图更进一步深入农民的生活世界,琢磨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举止、语言方式、性格特征,扩展其观察农民的视点。而正是这种观察状态、视角的转换,使得丁玲在《桑干河上》中构造出了更立体鲜明的农民形象。
概言之,对丁玲的创作做一整体性的回顾,可知其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民日常生活空间,或疏离于人物及其行动,或沦为无足轻重的标识性地名。丁玲早期的这种写作状态,归根于她对农村生活经验的缺乏、对农村农民的隔膜。而延安时期的丁玲,则开始逐步深入农村基层、民众生活,积淀起对乡村基层更丰厚的体认,这使她笔下的空间群也更为繁密、精细。但此时的丁玲尚未意识到空间与农民的复杂关系,形成用“空间场景雕塑人物”的意识,这些空间因此未被充分述说。但是,经历了长时段的“土改”历练,当丁玲以这段经验为素材写作《桑干河上》时,她在意识和写作上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丁玲开始注意到一个村庄中多样、复杂的日常空间,以及空间与农民的密切关联性。因此,丁玲不仅在小说中制造出诸多村庄公私空间,而且依托“空间—行动—心灵”的共构刻画出立体的农民形象。丁玲在《桑干河上》中呈现的意识、书写转变表明,将自我深度投入“土改”实践的丁玲,对农村农民皆产生了突破性的理解。第一,在历时长久的“土改”过程中,带着“研究政策正确与偏差”[6](P 109)意识的丁玲把握到了基层复杂的政治情势、农村工作推展的艰难度,并在艰苦的在地实践中建立起对基层复杂权力格局深切的体会,由此拓展了她对乡村基层社会的认知。第二,在“土改”过程中,与农民反复打交道的丁玲开始愈加熟稔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且有意识地扩展观察农民的视点,将目光投射从农民心灵扩大至人物举止,由此建立起更立体、多面感知农民的眼光。丁玲的这一状态表明,“土改”实践对于丁玲的一重重要性在于,使她在以“政治政策”为中介摸索村庄内在肌理的过程中,拓深了她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社会感知”。不过,仍需指出的是,丁玲之所以能够深度介入乡村,并在实践中获得现实感与经验的推进,建基于《讲话》开启的主体改造之上:只有当丁玲放弃原有的现实感、开放固有的自我意识,使自我更深地卷入被政治搅动的农民生活、村庄风暴之中,她才有可能形成对村庄内部复杂权力格局、村民生命世界多层面的体悟。
此外,强化农民生活空间、转换自然景致的总体书写状态,也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对农村现实的认知已发生很大变化:在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转”后写作的乡土小说中,审美式的自然风景核心承载了丁玲对单纯、安定的农村世界的想象。在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初期小说中,自然景致同时承担两个主要功能:一方面,它依托其象征性成为人物情绪、心境的对应物;另一方面,它作为农村自然景观成为丁玲农村认知图景的一部分。但是,伴随这时期丁玲现实感觉、文学写作的演变,其描摹的农村图景不再仅仅由自然风景构成,农民多样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也逐步步入视野,映照着丁玲农村图景认知的微妙变更。在《桑干河上》中,丁玲试图将诸多与农事生产相关的意象纳入乡村自然风景,从而使外部审美式风景转变为村庄内部人所感知的农村日常风物;同时,小说对村庄不同处境村民的生活空间展开扩张性的书写。伴随这种写作方式的急剧变更,丁玲笔下的农村图景显现得更为立体、完整:整个乡村被别致的乡村风景、农村作物、生活空间等不同板块包裹,而且褪去了早期单质、明朗、空洞的表象,裸露出复杂、厚重、凹凸不平的内质。丁玲的这一总体文学书写转变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对于乡土社会的认知、把握愈加复杂、深化,而正是丁玲在《讲话》、“土改”后拓进了的现实感,增进了《桑干河上》刻写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广度。
四、结语:主体改造的复杂性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1948年诞生的《桑干河上》,背后皆存在一个纵深的历史生成脉络,呈现的皆是一种过渡性、探索性而非完成性的状态:对于丁玲而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她是被《讲话》、“土改”两个重要历史环节所逐步打造的丁玲,经历了较为剧烈的精神变迁;对于《桑干河上》而言,生成于1948年的它作为一个尝试性、开放性的文本,是丁玲调适自我状态后创作的作品,融入了她精神转向的痕辙。而本文以这种“生成史”的视角审视丁玲、《桑干河上》,意在指出《讲话》、“土改”实践对“丁玲主体改造—《桑干河上》写作”这一事件的关键作用。其一,《讲话》对于丁玲而言,是一个具有思想启发性的政治文件。它的作用在调整丁玲固有左翼立场下的现实感与自我意识,使她意识到自我与基层社会的严重隔膜,催促她先行搁置自我意识,依托政治实践艰苦深入对象世界。正是以《讲话》对主体意识的调整为基点,丁玲顺着政治实践的方向进入乡村基层,才能突破她1942年前虽多次流动下乡却始终不能扎根基层的困境。其二,“土改”对于丁玲而言,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基层咀嚼《讲话》意识、在政治政策指引下探索基层社会的锻炼场域。可以说,当丁玲带着经由《讲话》开启的意识,搁置自我意识进入被政治运动激烈搅动的基层社会,她既在重新摸索基层社会、民众状况中校验了《讲话》的说法,最终又用切实的实践经验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如丁玲20世纪50年代关涉知识分子与群众、工作事务与文学写作等关系的表述,即基于丁玲在“土改”过程中积累的生命体悟,不少观点实则溢出了《讲话》的内容。其三,就丁玲的整体创作而言,其文学书写与中共革命历史、自我主体状态形成了相互磨合又互为促进的关系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丁玲文学书写演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倘若没有1942年《讲话》开启的精神转向、1946年借助“土改”急剧积累的乡土经验,丁玲很难在1948年创作出长篇小说《桑干河上》。正是借助主体改造、政治中介、在地实践等因素的相应配合,《桑干河上》成为丁玲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写作颇为关键性的文本。
“丁玲主体改造—《桑干河上》写作”作为《讲话》与革命主体互动结构中的典型个案,具象化了《讲话》、“土改”实践调适革命主体的过程与效果。而透过上文呈现的丁玲精神状态、文学书写的迁变过程,恰恰可以看到《讲话》、“土改”实践对于丁玲的调适效果。20世纪40年代的这一系列历史环节,为丁玲的左翼立场、自我构成、文学书写带来了以下三个正向性维度。一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即持有左翼立场的丁玲而言,《讲话》、“土改”实践潜在回应了她渴望与基层民众密切结合的心灵冲动,深化了丁玲原有的左翼立场。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接受左翼立场,意欲在话语、情感上建立对工农大众的认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没有意识到左翼立场下的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隔阂,自我需要做出诸多调适才能贴近基层群众的生命世界。这使得1936年奔赴延安后的丁玲,虽然拥有多次流动下乡、深入基层的机会,却始终没能真正深进乡土社会。直到在《讲话》的调整下,丁玲才转变现实感、自我意识,依托政治运动展开在地实践、重新认知基层农民与乡村社会。由此可见,《讲话》、“土改”实践启发丁玲找到了更扎实深入中国现实、基层群众的方法,并由此深化了她固有的左翼立场。二是对于丁玲的自我状态而言,《讲话》、“土改”实践带来的意识调整与现实经验,拓深了丁玲的自我构成。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曾受到“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影响,尝试将写作视角投向农村农民。但是《讲话》前的丁玲在感受、叙写农村农民时,实则并没有真正放下自我、内在理解农村农民,而常从自我趣味、审美出发来感受、叙写农村农民。在这种状态下,丁玲很难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碰中,借由外部对象的丰富性突破自我。直到受《讲话》激发,丁玲才开始逐渐破除自我、参与革命实践、沉入对象世界之中。当丁玲开放自我卷入被政治翻动的村庄中时,她不仅获得了对于农村农民新的认知,并且借此拓展了自我的感知结构、丰厚了主体的构成。也正是依托这样一种主体改造方式,丁玲开始真正脱开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状态,逐步向社会主义主体过渡。三是对于丁玲的文学书写而言,《讲话》、“土改”实践带来的并非是简单化的主体性压抑、文学性丧失,更有文学把握、刻写现实能力的增进。丁玲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左翼视角,既有开拓性又有限制性的面向:一方面,左翼视角使丁玲将书写范围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转向抗争的工农大众,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社会观察的视点、拓展了其现实感知力;另一方面,这一视角下有缺陷的现实感、自我意识,却时常阻碍丁玲以更内在的视角感受、捕捉农村农民的复杂性,又多少限定了其社会现实感。正是左翼视角既开拓又限制的双面性,规约了丁玲文学刻度现实的深度。《讲话》则尝试在丁玲固有的左翼立场上继续调整其精神状态,既保留其冀望与基层民众结合的意识与冲动,又转化其存在缺陷的现实感、自我意识,从而使其能够凭托政治运动进入基层社会、重新认知中国社会。正是《讲话》对丁玲左翼立场下这一主体困境做出的建设性调整,增进了其在“土改”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力,进而拓展了其文学刻写现实的能力。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语境中逐步生成的对《讲话》与丁玲、《桑干河上》关系的几种认知。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当革命的合法性、革命文艺的先进性均遭到质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如何阐发《讲话》、整风运动与丁玲的关系曾一度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这一学术风向转换中,学界形成了以下两种较为典型的关涉《讲话》与丁玲关系的认知。一是部分学者倾向于在政党政治规训革命主体的意识前提下,将丁玲的主体革新作为政治干预作家自由的典型案例,或暗中否定丁玲主体改造的必要性[28],或探寻丁玲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龃龉[29]。细察这些论述,其价值在于指出了1942年革命语境中丁玲主体改造缘起的被动性,描述了丁玲主体改造过程的艰难度,由此揭示了《讲话》与革命作家形成的某一层关系。但是,这些论述从政党组织干预作家自由观念出发来阐释《讲话》与丁玲,似乎很难解释为何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始终坚执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也难以回答丁玲在《桑干河上》中呈现的自我感、现实感的扩展。由此可见,这种说法忽视了丁玲与《讲话》的正向性关系,并进而简化了丁玲与中共革命政治的复杂关系。二是部分学者尝试突破压迫/反抗叙事模式对于丁玲与《讲话》关系的解析,声言丁玲乃是为毛话语这一“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所感召而逐渐认同《讲话》与整风,并由此开始自觉适应此规范而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3]。一方面,这种论述突出了主体改造运动中丁玲主动性的向度,指出了《讲话》、整风可能具有的正面性;另一方面,这种论述没有具体论及《讲话》、整风的正面性所在,使得丁玲对于《讲话》的认同变得抽象而单薄,从而简化了丁玲精神转向的厚度。就此而言,本文的具体工作是尝试提出《讲话》给丁玲精神转折带来的正向性维度,并且细致辨析这些正向性维度如何深化了丁玲的左翼立场、自我构成、文学书写;本文的根本意旨是希望通过复杂化《讲话》与丁玲精神转向的关系,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丁玲与《讲话》关系、20世纪40年代革命历史中的主体改造运动提供一种补充性、多面性的视角。不过,虽然本文反复论证了《讲话》、“土改”给丁玲精神转向带来的正向性向度,但这并不意味写作《桑干河上》的丁玲的主体改造过程已经就此完成,也不意味这种主体改造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理想方式与形态。只是说《讲话》所提供的主体改造路径,对于特定历史状况中的丁玲而言,确实开启了丰厚自我构成、深化现实感知等这样一些具有建设性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