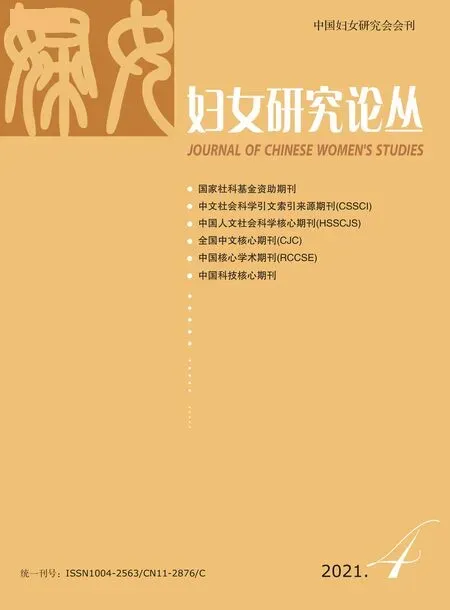性别、民族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五朵金花》中的旅途叙事与公路形态
张 泠
(纽约州立大学珀契斯分校 电影与媒体研究系,美国 纽约 10577)
电影《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呈现了某种关于寻找的旅途经验,在当时的中国与海外都广受欢迎。它曾在46个国家放映,对中国电影史与大众文化记忆影响深远(1)《五朵金花》在1960年于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电影“银鹰奖”(王家乙)与“最佳女演员奖”(杨丽坤)。见李奕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视点与主题》,《电影创作》1997年第1期,第69页。。影片中,白族男青年阿鹏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苍山公社寻找他心爱的金花——阿鹏与金花在前一年的“三月街”节相遇相爱,约定今年再见。金花为了考验阿鹏的诚心,并未留下具体地址,而“金花”又是白族女孩常用的名字,于是阿鹏一路上遇见了几位同名却并非他意中人的金花,她们都是各行各业的模范,有积肥能手、畜牧员、炼铁工人和拖拉机手。在经历误会、错过、延迟与失望之后,阿鹏终于见到了“真正”的金花——苍山公社的副社长(2)这种男主人公在去见爱人/对象的路上因不断帮助别人而延迟约会、但因他的美德而引向美好结局的叙事,也出现在比《五朵金花》早一年上映的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中。。他们在初会的蝴蝶泉边再次对歌,在群众的围拥祝福中,影片结束。《五朵金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片,赞颂社会主义建设、农业集体化、民族团结及妇女通过参加生产劳动而获得解放。
若以“电影类型”的框架来讨论《五朵金花》,它通常被视为有少数民族文化色彩的喜剧与风光音乐片,即“成功的歌舞喜剧,以描绘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和采用丰富多彩的民歌和舞蹈而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1](P 25)。20世纪60年代的相关讨论将喜剧电影分为两大类,即讽刺性(暴露性)喜剧和歌颂性喜剧。《五朵金花》与《今天我休息》(鲁韧,1958)常被视为歌颂性喜剧的代表作、凝结着社会主义喜剧因素的新样式。在当时的评论者看来,《五朵金花》被列为歌颂性喜剧主要由于其“更多运用了幽默、诙谐、风趣,恰当地运用了误会巧合等手法,别具一格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丰富美好的生活面貌,独特地处理了喜剧矛盾”[2](P 13)。影片生动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载歌载舞的日常生活画面,也呈现了云南的明山秀水以及劳动于其间的社会主义新人。
呈现出某些“公路叙事”特征的《五朵金花》公映于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1957)出版两年后,这当然只是冷战世界两端历史的巧合。《在路上》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文化标志,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路电影与亚文化运动的先声。尽管这种并置看起来有些荒诞,但我认为《五朵金花》可被作为“社会主义公路电影”来分析研究。正如美国学者尼尔·阿切尔(Neil Archer)所言,我们通常“后见之明”地辨析某些影片的“公路电影”特征,而这些特征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并非最重要的因素[3](P 5)。因此,我将《五朵金花》作为“社会主义公路电影”,置于全球冷战背景下,探究与挑战英文学界中电影与媒体研究领域界定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公路电影”主题与风格界限的可能性(3)关于“公路电影”的英文著述,见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Cohan,S.and Ina Rae Hark(eds.),The Road Movie Boo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Devin Orgeron,“Revising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Road Movie:David Lynch’s The Straight Story”,Journal and Film and Video,2002,54(4),PP.31-46;Katie Mills,The Road Story and the Rebel: Moving through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6;Mazierska,E.and Laura Rascaroli(eds.),Crossing New Europe:Postmodern Travel and the European Road Movie,London and New York:Wallflower Press,2006。。如果说美国公路文学与电影是一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现代现象,是个人流动与自由及反社会主流的缩影,那么《五朵金花》则暗示了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囊括民族团结、性别平等、农业集体化与社会建设,以及文艺的大众化实践——位于社会的主流。
实际上,当代“公路电影”研究已经超越美国中心的思路,有更多研究关注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与欧洲的公路电影,介入社会、文化与政治议题,如后殖民创伤、身份探寻与跨国迁移等(4)相关英文研究见Michael Gott and Thibaut Schilt,eds.,Open Roads,Closed Borders:The Contemporary French-Language Road Movie,Intellect,2013;Veronica Garibotto and Jorge Peérez,eds.,The Latin American Road Movie,Palgrave Macmillan,2016;Nadia Lie,The Latin American(Counter-)Road Movie and Ambivalent Modernity,Pickle Parnters Publishing,2017;José Duarte and Timothy Corrigan,eds.,The Global Road Movie:Alternative Journeys around the World,Intellect,2018。。建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五朵金花》与“公路电影”分析框架的对话,不仅能够为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与交流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将复杂化“公路电影”类型的地理政治学与历史维度。此外,该框架有助于提出一些重要的观念性问题:《五朵金花》中深具社会主义意味的性别与民族呈现如何不同于其他“典型”的西式公路电影?影片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如何与其主题和风格互动从而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然而极具表现力的公路电影形态?自然、劳动与音乐如何在影片中被编织进与公路叙事相关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典型的欧美公路电影范例如1965年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狂人皮埃罗》与1969年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逍遥骑士》的出现,基于欧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路基础设施的修建、私人汽车的逐渐流行及公路旅行作为中产阶级(尤其年轻白人男性)游弋于主流社会空间边缘的象征。一方面,可以说是个人主义关于“自由”与自我发现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资本主义在特定阶段对人心理造成的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五朵金花》中,阿鹏与两位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绘画与音乐工作者辗转于苍山洱海间,前者寻找金花与后二者民间“采风”(收集少数民族图案与民歌)交织,构成旅行的叙事根由与动力。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西南地区由于地势险峻、资源不足,基础设施仍在修建之中。影片中没有现代交通设施如高速公路,或交通工具如汽车与摩托车,影片中的旅行都是通过前工业形态的交通方式进行,如搭乘人工划的小船、坐马车、骑马、步行等。除了纵马飞驰的时刻,这些交通工具的迟缓速度一方面构成徐缓横摇镜头中的田园诗意,另一方面暗示出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紧迫性,与影片背景中主张加速工农业建设的“大跃进”构成复杂的张力。
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公路电影中盛行的男性危机、逃避型幻想、反叛的欲望与对速度的迷恋,《五朵金花》强调坚强开朗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如何参与劳动及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性别叙事与多数欧美公路电影有着显著不同:前者折射出保守的消费主义的男权中心体系(5)也有学者探讨过一些公路电影叙事中的女权主义因素与潜能,如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1928-2019)的《流浪女》(1985)与《拾穗者》(2000)。见“From Flanerie to Glanerie:The Possibilities of a ‘Feminine Road Movie’”,in 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而后者致力于打破这种商业电影模式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呈现出更具性别、民族、阶级平等性的乐观愿景。如在西式旅行/公路叙事(甚至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始)框架中,通常男性出门旅行而女性在家中等待;当前者不断探索新的时空彰显其主体性时,后者则被动处于静态时空。《五朵金花》中,尽管实施旅行与寻找的是三位男性人物,但并非意味着女性处于静止被动状态,如前所述,除了副社长金花忙于处理公社事务如水库建设、炼铁状况、社员结婚、“三月街”货物运输甚至社员工作与感情矛盾等外,其他四位金花都是各自领域的劳动模范,通过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生产劳动、社会建设体现出她们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领导力。
在公路电影中,公路通常也作为隐喻出现:进步、向前的线性逻辑。在很多美国公路电影中,一方面,公路可能暗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冷战时期的焦虑与恐惧,也给这些影片带来“一种独特的存在主义气质”(6)见Devin Orgeron,Road Movies:From Muybridge and Melies to Lynch and Kiarostami,New York:Palgrave,2008,PP.10-30;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P.144。;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美国高速公路的发展与延伸、公路电影中驱车飞驰成为视觉与感官奇观,也强化了一种美国国族身份[4](PP 39-41)。如果说多数美国公路电影中的时间维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悬置”,在《五朵金花》中则是可期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根植于当时充满干劲与乐观色彩的社会环境。探究《五朵金花》中性别与民族的主题如何被编织进公路叙事,会丰富我们对于公路电影的理解,并揭示位于电影核心的、隐喻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轮廓:在劳动人民的推动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向一个明朗的社会主义未来。《五朵金花》中这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隐喻,也可参照1959年1月1日《云南日报》社论中所言:“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我们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面貌,已经找到一条发展农业生产的高速道路。”[5](P 71)
《五朵金花》中的寻人与采风之旅,宣扬和巩固了一种多民族的无产阶级国族身份,这一点与典型公路电影中文化身份铸造的形态彼此映照但截然不同。这部电影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技巧上突出流畅的摄影机运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尚显新潮的彩色摄影,并杂糅音乐片、喜剧与公路叙事的样态,这些都使其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公路经验——乐观主义的旅途,穿行于壮美的山水、民间文化与社会主义公民之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将在三个层面展开讨论:首先,《五朵金花》所构建的多民族影像与社会主义公路叙事如何呼应了当时的民族政策及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运输等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五朵金花》中通过“公路叙事”结构统摄、民歌串起的旅途如何在呈现人与自然、劳动的关系中凸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最后,《五朵金花》这部在不同维度颠覆传统西式“公路片”的社会主义公路/路途电影如何不仅在民族关系而且在性别结构中体现出基于民族、性别、阶级平等与解放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及隐喻性的乐观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多民族影像与社会主义公路叙事
极具观赏性甚至轻松愉快的《五朵金花》在1959年被规划、创作出来有其特别的背景。那一年,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拍摄了约十八部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7)包括汤晓丹的《钢铁世家》(1959)与沈浮的《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等。。周恩来总理认为这些电影在宣传社会主义政策与文化方面有教育意义,但对当时电影界缺少优美动人、寓教于乐影片的状况很不满意。周恩来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1900-1995)表达了意见,建议拍摄一部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载歌载舞、基调欢快的喜剧。夏衍将任务交给了作家赵季康(1931-)。赵季康在云南居住了十年,熟悉少数民族生活,也有类似创作经验(8)接受这个任务之前,赵季康与王公浦担任背景为西南边陲的反特片《两个巡逻兵》(方徨,1958)的编剧,片中涉及汉族与傣族人民的互动。《五朵金花》后,赵季康与王公浦合作编剧了关于傣族女性的电影《摩雅傣》(徐韬,1961)。。据另一位编剧王公浦回忆,夏衍曾于1959年1月造访大理,对白族人民的生活与文化非常感兴趣,决定将白族人作为电影的主要角色[6](PP 23-27)。因此,《五朵金花》可以说是政治任务、机构运作与地方创作彼此协调的结果。
以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多元与团结为主旨,《五朵金花》的制作无疑也有国际想象存在。夏衍指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王家乙(1919-1988)担任此片导演。王家乙曾在法国短暂学过电影,并与法国导演罗杰·比果(Roger Pigaut,1919-1989)合导了中法合拍片《风筝》(1958)(9)罗杰·比果,法国演员、导演,曾与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拍摄旅行纪录片,如《瓦尔帕莱索》(1964)与《海岸之风》(1965)。。《风筝》也是关于“旅行”的影片:两个巴黎小朋友乘“魔床”飞到北京寻找一位寄送了“孙悟空”风筝去巴黎的中国男孩。影片赞扬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的儿童间的国际主义友谊。《风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合拍剧情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儿童电影,曾在一些欧美国家上映,包括法国、美国和英国。在冷战时期中国基本与美国、西欧等国家官方交流隔绝的情形下,《风筝》成为一个重要媒介,呈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五朵金花》也预期要在资本主义国家放映,但那些国家对社会主义讯息与文化传播管控严苛,因此影片中并未直接出现政治口号标语赞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寓党于人物形象之中”(10)王家乙写道:“影片(《五朵金花》)在印度放映,尼赫鲁(1889-1964)首相看了之后就说:‘这影片是说中国的三面红旗好的!’(三面红旗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全看明白了。”王家乙:《王家乙导演谈影片〈五朵金花〉创作》,《电影文学》2010年第1期,第146页。。这一点与王家乙拍摄时目标观众不仅在中国相关,也延续了他创作“旅途电影”的兴趣。王家乙也因为拍摄《风筝》的经验,对电影彩色技术有一定心得,而彩色电影当时在中国能够吸引大批观众(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彩色片为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黄沙,1954),在当时广受欢迎。。得益于拍摄《五朵金花》积累的经验,王家乙后来拍摄了更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12)王家乙此后拍摄了四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包括关于朝鲜族女性革命者的《金玉姬》(1959)、关于彝族人民的《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关于景颇族妇女的《景颇姑娘》(1965),以及关于傣族人民的《相约在凤尾竹下》(1984)。。
《五朵金花》中的社会主义公路叙事暗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乐观图景。这部影片也可被视为1949年以后拍摄的数百部“少数民族题材”剧情电影类型与主题的先行者。1949年以前关于少数民族人民的剧情片较为少见,其中之一是《瑶山艳史》(杨小仲,1933),被左翼知识分子(包括鲁迅)批评为“低俗”及汉族沙文主义。应云卫的《塞上风云》(1940)在抗战背景下鼓舞汉族与蒙古族人民团结抗击日本侵略。柳城指出,1949-1989年,中国拍摄了130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约占总数(约1800部)的7%,涉及23个少数民族。1949-1966年,拍摄了47部少数民族题材剧情长片,涉及18个少数民族的生活(13)余纪:《从“双百方针”到“新侨会议”——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黄金时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04页。见柳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漫评》,《电影通讯》1989年第8期,第7页。。这些影片的主要角色大都是少数民族中具有无产阶级美德——勤劳、勇敢、诚恳、智慧、无私、乐于助人——的人物(14)有些海外批评者认为,在这些影片中中国共产党与汉族导演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民众,将前者描述为后者的救星,这种看法多有不确,因为这其实是基于阶级的叙事来合法化革命目标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对汉族女性受害者的描述也是采用类似方式,如《白毛女》(王滨、水华,1950)与《红色娘子军》(谢晋,1961)。。《五朵金花》中的主要少数民族角色如金花们与阿鹏也是这些进步品德的化身,他们是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中理想化的新公民。这些影片的叙事通常讲述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经历的历史:阶级压迫与剥削带来的苦难与激发的反抗,外国势力侵略与殖民。因此,这些影片呈现的是超越民族差别与民族间等级制度的新型民族关系:以被压迫大众的阶级认同与解放的意义代替民族差别与等级。
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多民族文化作品背后是中国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中第五十条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7](PP 1-2)民族政策支持各民族权利平等及鼓励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如上文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7](P 3)在“十七年”(1949-1966)期间,少数民族人物及文化形象在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及其他视听与表演艺术中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15)各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地方也建立起各种少数民族表演团体,延续本民族文化传统。在《五朵金花》中扮演副社长金花的杨丽坤是一个来自当地歌舞团的彝族演员。关于这方面的英文研究见Chen,J.,Nation,Ethnicity,and Cultural Strategies:Three Waves of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Post-1949 Chin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2008,P.53;Elena Barabantseva,Overseas Chinese,Ethnic Minorities,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49。。响应官方政策,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都弘扬民族平等与团结,在银幕上构建出一种新的“多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民族关系。通过电影与其他大众媒介,这种新中国的多民族影像被迅捷地传达到大众心中,激发鼓舞了他们对新型民族关系的理解与实践。
《五朵金花》拍摄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然山水的现代化改造格局,以及公路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农业发展与改善(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1957年的报道称:“公路建设方面,七年来修建公路新增里程86775余公里……这些工程艰巨的公路的建成,沟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8](P 2)公路建设也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题材。据艺术史学者吴雪杉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全国美展中,公路成为广受艺术家青睐的画题,如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等[9](PP 71-82)。1954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从铁路、水运、航空、邮电等方面报道“发展交通运输业,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安力夫的文章《公路运输的面貌在改变着》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路建设的巨大成就:到1953年,公路通车里程比1950年增加了33%。新建公路的共同点为“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岳地带。这些地方过去很多都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和边沿地域,工程异常艰巨。筑路的军工、民工和广大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克服种种困难,和大自然进行搏斗……这种高度爱国主义的劳动热情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使我国公路建设迅速推进到新的地区”[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公路建设才是真正为了人民群众,使得“广大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认识了今天的公路是促进物质交流,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工具,与反动统治时期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都自动地参加了公路的整修工作”[11](P 10)。
安力夫的文章认为,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对沿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公路建设,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历来无法外运的土产品逐渐可以运到外地,从来少见的工业品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且不断增多。这些生动的事实,使少数民族人民深切体会到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受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公路建设[10]。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国营贸易机关正以各种努力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工作,凡力所能及的地区,均以等价交换甚至实行补贴的办法来组织物品交流,因此土产价格一般提高三倍或者四倍,多至十数倍。”[7](P 51)这令我们联想到《五朵金花》开篇与结尾场景的“三月街”盛会中,“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各族人民售卖本地土特产及购买外地生产的生活用品,贸易呈蓬勃之势。交通运输发展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得物品交流通畅且摒弃剥削色彩,尽管由于技术资源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是柏油或水泥路面,而是泥结碎石及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修建的级配路面,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9](P 76),如《五朵金花》中所呈现的那样。
相较之下,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产生的公路电影质疑国家与社会机构的合法性,憎恶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浪漫化自身的边缘位置、个人主义,甚至享乐主义[12](PP 38-40)。在多为白人男性中心的叙事中,也时见种族主义与男性沙文主义的态度,如尼尔·阿切尔指出“厌女”倾向及对“他者”(尤其是对少数族裔)的恐惧在美国公路电影中并不少见,公路电影本身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进步[13](P 5)。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公路电影如《五朵金花》担负着对国内观众的政治教化、审美愉悦功能及对海外观众的怡情与宣传意义,如强调社会主义政权、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及如今颇有争议的“大跃进”的合法性(16)关于“大跃进”的英文论述,见Meisner,M.,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6;程郁儒:《论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及其功能》,《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第59页。。学者柏佑铭(Yomi Braester)指出,这些政治运动与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和电影样式有一种映照关系:面对同样的群众,带有同样的目标,因此,“形式与意识形态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与某些政治运动相关的特色”[14](PP 119-140)。
《五朵金花》的拍摄只用了四个月,质量却丝毫未打折扣。它的叙事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宣传加快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步伐的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集体性水利建设与“大炼钢铁”都得到了体现。例如,阿鹏寻找的苍山公社副社长金花在繁忙的工地参与及指挥水库建设;另一位金花与爱人在炼铁厂,经过“祖传三代是铁匠”的阿鹏帮助解决了技术难题,终于成功炼出铁。影片中集体劳动与参与建设的社群感及性别平等密切相关,也映照着历史现实。在全国范围内,始于1957年秋冬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带来了大规模协作劳动,如朱羽所言:“兴修水利等需要大量劳动力集体参与、互相协作的项目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小生产者的劳动状态,从而带来了走出家庭、建构集体生活甚或军事化组织劳动的可能。”[15](P 193)当然,片中关于“大跃进”的讯息比较隐晦,如前文所述,部分原因是该片预计在国外放映,为了不在其他国家引起审查麻烦,以及不疏离对社会主义缺乏理解的外国观众、传达新社会的美好,这也就解释了夏衍为何对王家乙说:“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16](P 30)[17](P 34)
在赞扬《五朵金花》以欢乐喜悦为基调透露出对新生活的讴歌真诚可信的同时,评论者柳城指出,尽管多数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对少数民族人物有比较丰富的表现,强化了观众在心理、意识与美学体验上的认同,增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但这些影片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一些影片仅仅停留在风俗、服饰、语言表达等表面层次的表现上,没能真正进入到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层思考和探索上”[18](PP 7-9)。也有一些批评涉及这些影片中的主体性问题,因为除了演员外,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由汉族电影工作者编剧和导演。客观原因在于,与都市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隔绝及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多数少数民族民众在1949年以前很少有机会看到电影,识字率(无论是本民族文字还是汉文)较低,接受电影训练、进行电影实践的机会非常有限。随着1949年以后16毫米电影放映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各少数民族自治区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培养人才,拍摄影片,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进(17)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电影人才不多。至70年代,才有了更多训练有素的少数民族电影工作者,新疆、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地也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制片厂。少数民族导演如锡伯族的广春兰和白德彰,维吾尔族的吐依贡·阿合买德,蒙古族的云文耀、塞夫、麦丽丝、珠兰琪琪柯(1930-2011),等等。人类学者贝丝·诺塔(Beth Notar)的研究表明,1951年时,云南省只有1/10人口一年能看到一部电影,但到了1959年,因为有近四百个流动放映队,云南省平均每人每年能看到至少三到四部电影。见Chen,J.,Nation,Ethnicity,and Cultural Strategies:Three Waves of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Post-1949 Chin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2008,P.79;柳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漫评》,《电影通讯》1989年第8期,第7页;Beth Notar,Displacing Desire:Trave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51。。
如果说《五朵金花》通过公路叙事呈现的多民族影像呼应着当时的民族政策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历史现实,其公路旅途的意义又如何被影片的视听风格尤其是摄影与音乐所强调?片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歌舞,尤其经过再创作的白族民歌,都为阿鹏与李同志、孟同志沿途所闻,不仅串联起公路叙事,更体现出一种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的民间文化如何成为国族性的民族形式,且与当时文艺作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与政治意义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会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
二、民间音乐文化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
在世界各国的公路电影中,声音/音乐扮演了重要角色:映照人物情绪,强化变幻风景的壮丽,或与车速及影片视听蒙太奇构成的速度和节奏感共呼吸。这样的音乐有时作为叙事空间内的音乐(diegetic music)自车上的广播或其他设备播放,有时作为叙事空间之外的配乐(extra-diegetic music)。在学者大卫·拉德曼(David Laderman)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摇滚与流行音乐的盛行与叛逆性的青年文化密切相关,也为美国公路电影中常见的开车场景提供了叙事的便利与配乐的来源[4]。在其他一些非美国的公路电影中,混杂各大洲不同风格的配乐质疑一种欧洲中心的文化身份观[19](P 34)。在《五朵金花》这部社会主义公路电影中,音乐的呈现是满族作曲家雷振邦(18)雷振邦(1916-1997)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其中很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主题歌与插曲,如《五朵金花》中白族风格的《蝴蝶泉边》、《冰山上的来客》(赵心水,1963)中塔吉克风格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芦笙恋歌》(于彦夫,1957)中拉祜族风格的《婚誓》、《刘三姐》(苏里,1960)中壮族风格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他是满族人,在日本学过音乐,常到各地区收集民歌。《蝴蝶泉边》这首歌,雷振邦结合了剑川(阿鹏家乡)的白族曲调与大理(金花家乡)的“西山调”风格(李二仕:《〈五朵金花〉的“今点”意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影片勘景时,编剧赵季康与雷振邦决定将部分场景的对白改成对歌,这也是白族的风俗习惯,尤其便于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雷振邦将白族民歌非常高亢尖利(因在野外传播)的曲调调整得柔和了一些,以便于大众欣赏与传唱。所收集及改编后的白族民歌,因民间音乐传统而传达出一种欢快生动情绪及拥抱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的通俗感染力。影片内(音乐家李同志)外(雷振邦)的音乐“采风”涉及旅途,也涉及创造性劳动:奔走四方收集民间音乐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为基于社会主义体系内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公有制特征,尽管影片作曲署名“雷振邦”,这些音乐并不具有可牟利的私有“知识产权”,而是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因此,来自少数民族的、民间的、地方的音乐,可以成为国家的、民族团结与平等的非物质象征。这种融合不同民族形式的多元一体的国族想象,经由民歌与电影呈现的愿景强化而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并浸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以积极、明朗、乐观的态度呈现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新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关系。
与多数公路电影不同,《五朵金花》中的插曲并非只出现在无声源的听觉领域,所有歌曲承担叙事功能且发生在叙事空间内,更像歌舞片中的歌唱段落。片中除了配乐外,还出现了几首在影片上映后脍炙人口的插曲,如影片开始各族人民在“三月街”盛会齐唱的《绕山林》(白族称为“绕三灵”)、在洱海捞海肥的姑娘们所唱的渔歌、副社长金花的爷爷山上采药时所唱的《采药山歌》、阿鹏隔窗对畜牧场金花所唱的《唱个山歌扔过墙》、副社长金花想念阿鹏时所唱的《绣围裙》、歌唱家黄虹在邻近结尾“三月街”盛会所唱的民歌等。片中出现的插曲镶嵌于片头、片尾两次出现的主题歌《蝴蝶泉边》之间(19)《蝴蝶泉边》随着影片的大受欢迎而被广为传唱,女声部分由白族女高音歌唱家赵履珠演唱。她的演唱发音不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带有一点本地口音及鼻音,使得她的风格听起来亲切与“本土”。。这些歌唱段落有独唱、对唱、合唱,有时还伴有精心设计的群舞。片中歌舞场景的呈现也对应着社会现实——歌唱是白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他们表达与交流(如对歌)的重要方式。片头庆祝白族传统节日“三月街”的集体歌舞段落呈现出一定的剧场风格(集市忽而成为群众歌舞表演的舞台),同时又有极具戏剧性的货品交易与赛马活动。在片头的爱情场景里,四处寻找金花的阿鹏是通过跨越空间距离的她的歌声而找到她的。这对情侣在对唱中交换信物,信物都是自己的劳动成果:金花绣的荷包,阿鹏锻制的钢刀。前者象征着金花的美丽、灵巧、勤劳,后者象征着阿鹏对爱情的坚贞。若说荷包与钢刀是物质形态的信物,《蝴蝶泉边》则成为金花与阿鹏非物质形态的爱情信物。
《蝴蝶泉边》歌声的两度出现,不仅标志着影片叙事开端至结尾的变奏、阿鹏寻找金花旅途的终点,也开拓了一种电影声音空间。声音的多向发散性使得片中声音空间不仅超越线性的道路,也顺畅地联结了实景与摄影棚内拍摄之间的空间与认知的缝隙。沿着蝴蝶泉边平滑横移的摄影机强化了布景的超凡脱俗的魅力及华美的人工性。尽管几乎所有公路电影都是实景拍摄,有些具有纪录片式的粗糙质感,但《五朵金花》中的多数内景(包括部分外景如“蝴蝶泉”)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摄的。这种视觉上明显的人工性与影片的后期配音实践彼此呼应:片中所有歌曲由专业歌唱演员配唱,副社长金花扮演者杨丽坤的声音也是由声音演员后期配音的(20)这是因为杨丽坤无法讲标准普通话。有报道说周恩来总理两次带杨丽坤出国访问,勉励她早日学好普通话。刘连:《〈五朵金花〉幕后悲喜人生》,《人民文摘》2009年第6期,第11页。。此外,所有白族人物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非白族话,语言的缝隙也被弥合。在这样的声音实践中,电影容易被大多数其他民族观众所理解,也暗示多民族统一的国族性比地方文化的本真性呈现显得更为重要。
这种电影听觉空间与地理政治空间紧密交织。如果说在很多公路电影中,“公路”成为一种另类空间,“与主流的隔绝使得个人转变的经验成为可能”[20](P 5),这种方向和动力感可被描述为“离心的”,在《五朵金花》中,空间方向却是“向心的”:阿鹏路遇长春电影制片厂来的两位汉族文化工作者——画家孟同志与音乐家李同志——结伴穿行于苍山公社。他们穿过的是社会主义空间的政治想象,关乎公社作为集体与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意义。在苍山公社的曲线旅途通过阿鹏不断寻找金花而连接起不同地点——洱海、社管会、畜牧场、炼铁厂、拖拉机站等,这些旅途场景与地点不但被流动的配乐“缝合”,也由现代通讯与交流工具——电话——而连成一个闭合的线路(尽管金花与阿鹏一次重要的电话通话因马车拉断电话线而断掉线索,导致叙事中更多的误会与延迟)。前文提到的片中歌曲中,每一首都与某个地点相关(无论内景还是外景),如“三月街”、“蝴蝶泉”、山间、畜牧场与金花的房间等。若我们将“绕山林”视为“引子”、两度出现的《蝴蝶泉边》为阿鹏与金花的重头戏,与洱海相伴的渔歌、山间的《采药山歌》及畜牧场的《唱个山歌扔过墙》则串联起阿鹏等三人的旅途,通过他们的“听闻”、他们在场的主观性中介而传达给观众。金花在房中所唱的《绣围裙》则没有其他人物在场,暗示出一定的私密性和个人情感维度,以歌唱吐露心声成为与观众的直接交流,从而强化观众对这一人物心理状态的认同。静止的歌唱场景与流动的旅途交叉轮替,创造出一种张力,如歌舞片中叙事与歌舞场景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歌舞片与公路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有相近之处:结构于一路向前的运动与偶尔停下的场景,也如交通工具在公路上飞驰或停在某个休息区[21](P 94)。
杂糅喜剧、音乐片与公路电影的《五朵金花》中,两位来采风且帮阿鹏寻找金花的汉族文化工作者,一胖一瘦,一庄一谐,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有着历史与政治寓意。他们被当地人尊为“专家”,但作为文化的外来者,他们惊叹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之丰富。当他们一片好意要帮忙时,常因不太熟悉体力劳动而容易弄巧成拙,造成麻烦、延迟与误解。例如,他们因为不会赶马车,马拉断了电话线,导致阿鹏与金花的通话中断[22](P 40)。这两个人物创造了一种自嘲的喜剧效果。导演王家乙后来检讨说:“最大的缺憾是对两位艺术家的处理……在国外放映时,有外国评论说,中国内地轻视知识分子……没想到政治与政策性问题,当做笑料来写,这样的塑造是失败的、错误的。”[23](P 146)当然,拍摄时摄制组并未将两位喜剧人物设定为音乐家和画家,是担心音协与美协问罪,作曲家雷振邦与美术师卢淦说戏里人物就是他们二人,因此加上“长影来的客人”台词[22](P 40)。与片中的李同志一样,雷振邦到全国各地去采集民歌,有时会兴奋地听老乡们为他整夜唱歌,记下歌谱[23](P 145)。
协助阿鹏寻找金花同时,两位文化工作者的“采风”活动也是有目的的旅途——这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收集素材进行再创作,转化为文化动员力量的过程与实践。讨论到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与性别话语时,美国学者白露(Tani Barlow)认为即使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考者来说,文化是动员大众能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媒介,传统、通俗的“民族形式”被用来启蒙大众并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工作者如黏合剂,一种将不同社会因素联合在一起建设国家的社会凝聚力[24](PP 211-212)。类似地,在《五朵金花》中,改编后的脍炙人口的白族民歌与作曲家们(雷振邦与片中的李同志)作为文化工作者为影片的文化实践添加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元素。
除了两位文化工作者收集民间文艺形式的任务为载歌载舞的视听奇观及公路旅途提供了叙事上的便利外,《五朵金花》也承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与政治特色,这一点与绝大多数美国和欧洲公路电影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延续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他们也要通过向无产阶级学习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与工农大众互帮互学。这在《五朵金花》中体现为下乡采风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他们既是人民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学生”[25](P 289)。因此在影片叙事过程中,画家与音乐家不断向他们一路上遇见的人们学习且成功地转变了:他们可以自如地进行体力劳动,如将公社的货物装上马车,且跟阿鹏学会了如何娴熟地赶马车。在学者朱羽看来,这种“工农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流动过程旨在消除劳动群众“臣属性”问题,“构造新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生产’新的内在自然、新的心理机制、新的‘人性’,而非对于‘等级关系’的简单颠倒”[15](P 186)。而金花、阿鹏、采药老爷爷等劳动群众克服了对自然的恐惧而获得“主人”意识,克服了对“知识”的恐惧、破除了对专家、知识分子的迷信而获得对劳动—知识主体的全新设想[15](P 187)。
《五朵金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典范,颂扬坚韧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也呈现了“人物的升华”[26](P 69)与优美风景,以及在劳动中收获的爱情及同志情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与美学概念,尽管在苏联提出与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文艺有深刻影响,但中国根据本国文化资源发展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径。它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艺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非单一的概念与实践,其影响也延展到艺术创作领域且在不同历史时段经历过变化与转折(2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自1932年在苏联被提出后成为苏联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Katerina Clark,“Socialist Realism with Shores:The Conventions for The Positive Hero”,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27)。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04-1936)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ev,1901-1956)的《青年近卫军》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且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见Regine Robin,Socialist Realism:An Impossible Aesthe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 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它也并非照搬现实,而是要在发展的活力中表现一个“更真实、历史而具体的现实描述”;它是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总和[27](P 4)[28](P 57)。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预设艺术的社会介入与乐观意义,追求创造一种理想化的世界,以简单、明晰、易懂的方式与大众沟通[26](PP 53-69)。就《五朵金花》的电影风格手法而言,它显得中规中矩,摄影、场面调度、剪接等朴实流畅,为叙事、塑造人物、表达主题服务,力求视听语言不对观众构成挑战或引起格外注意。从这一点而言,与好莱坞主流电影中视听风格服务于叙事并无二致,当然后者更多为了掩盖电影制作过程的劳动及将更多观众吸引进叙事幻觉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前者则以通过电影方式为大众提供教育普及、审美怡情文艺作品为目的。这一点也与20世纪中后期欧美“作者”/艺术电影中不时出现的先锋实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电影手法迥然不同。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劳动对社会主义公民而言是一种道德与美学愉悦的源泉。它通常与田园抒情的美好、诗意以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模范人物如在大家庭的人情之美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因为浪漫主义被视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及社会主义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6](P 67),如周恩来总理赞扬《五朵金花》,“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新风格”[29](PP 52-53)。《五朵金花》创造的是比生活本身更美好的理想化世界,在顺畅的摄影机运动与充满抒情色彩的音乐之中得到强调。秀美的苍山洱海风光在缓缓横移的摄影机运动中呈现出卷轴山水画般的意境,点缀以五颜六色的繁茂花朵,这既是现实,又是被电影语言与彩色电影技术强化了的、充满诗意乐观色彩的理想化空间。
《五朵金花》中被“路途/公路叙事”结构统摄在内的“自然”,不仅事关影片中主要人物为少数民族的设定(相对于城市汉族居民,他们与“自然”更接近)、呈现的自然山水(与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地理位置有关),还有其他层次:在民歌中被寄托了人们情感而吟唱的自然,以及作为社会生产实践与作为生产资料与空间配置的自然,在这里形成一种和谐的政治“生态”(22)关于这几点,感谢朱羽在阅读本文文稿时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这里的自然山水之美,可以被外来的文化工作者如李同志、孟同志代表摄影机的视角隔开距离进行审美性的观照,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一社会结构下人类劳动活动的介入中与当地人形成更亲密的关系,因拟人化的“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被劳动者歌唱:金花与伙伴们在洱海捞海肥时齐唱着“劳动号子”般的渔歌;副社长金花的爷爷在山上采草药,唱着“采药山歌”:“采得山药除百病,人人乐呵呵”……被画家孟同志问道:“您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的山啊?”他说:“这是个宝山哪,到处是药材,能让它呆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在另一场景中,炼铁厂金花与姐妹们到山上找矿石,尽管遇到黑熊只能躲在山洞里过夜,但终究找到了高质量的铁矿石。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对后者的改造利用(但非涸泽而渔的剥削)中,主体性得以彰显。他们也通过歌唱这种劳动的艺术表达获得了“一种主体的尊严感,甚至带来超越此刻体力劳动的解放感”[15](P 202)。
关于乌托邦与公路叙事,学者也曾论及美国公路电影中将社会批判编织进一种略带游戏色彩的乌托邦主义,构建汽车旅行带来的流动性、速度、自由与自我发现。这种公路电影叙事或呈现“一种同质性与国族凝聚力的乌托邦幻想”,或是“社会矛盾与反动政治的反乌托邦噩梦”[20](P 3)。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黑色电影”(films noir)中充斥着反乌托邦视角下的公路旅程,后来的美国公路电影则展示出一个主流公共想象中更加乐观与乌托邦的版本(23)Katie Mills,The Road Story and the Rebel: Moving through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6,P.38;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6;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37.。显然,美国公路电影中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的叛逆型乌托邦精神与《五朵金花》中的截然不同,后者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路叙事的隐喻性化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朝向未来,本质上进步与乐观,结合与改造了民间与传统文化资源;它杂糅地方文化形式并赋予其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功能:动员大众。在学者托马斯·拉胡森(Thomas Lahusen)看来,所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情节”走向是一种目的论的“完成任务”,而“主要结局”会告诉大家这个暂时任务完成后,还要面对未来的任务(24)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Régine Robin,Socialist Realism:An Impossible Aesthetic,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42-63;Xudong Zhang,“The Power of Rewriting:Post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n Chinese Socialist Realism”,in 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304;Ban Wang,eds.,Words and Their Stories: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Leiden,Boston:Brill,2011,PP.101-114.。
这一走向在《五朵金花》结尾场景中也显而易见:阿鹏与金花终于重聚,对唱《蝴蝶泉边》。另外四位金花与她们的伴侣及其他人物在花丛中出现,合唱一曲,祝福他们“白头到老同甘苦,地久天长永相爱”。这首朝向未来的歌,不仅颂扬持久不渝的爱情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种积极的情感,也将恋人的私会变成一种在社群人们亲切注视下的公共性情感,因此将个人的情感生活结合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诉求中。多数西式公路电影倾向于维护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抗拒传统家庭价值与新教工作伦理(25)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10。也有一些特例,如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电影《史崔特先生的故事》(1999)。德文·奥格隆(Devin Orgeron)认为在这部电影里,公路作为离开与回到结构的方式,是社群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道路是重聚而非反抗的空间;一个合群与沟通而非隔绝与沉默的空间。此处传统的家庭被高度赞扬且比六七十年代公路电影中对自我发现的强调更为重要。见Devin Orgeron,Road Movies:From Muybridge and Melies to Lynch and Kiarostami,New York:Palgrave,2008,P.34。,中国社会主义官方逻辑则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确保社会稳定性与生产力。因此,在《五朵金花》中,五位金花都有爱人,拖拉机手金花的婚礼也是影片的重头戏:因其地方习俗的奇观性及引起阿鹏对金花误解的戏剧性。金花与阿鹏的爱情故事富于浪漫色彩地暗示了一种社会主义家庭与未来添丁的图景,在这种呈现里,这些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基于性别和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及一种隐喻的持续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设想密不可分。
三、体制化的性别话语与社会主义道路
公路电影通常被视为“男性的类型”,因其男性中心的叙事与意识形态逻辑,甚至常有“厌女”倾向。这或许在意料之中,因为性别这个社会构建通常关联着等级森严的空间与行为的政治、历史实践与认知,如“史诗”叙事中通常男性在外游历而女性在家等待。流动性常被视为主体性与自由的象征,美国公路电影中男性角色通常享有更多特权,他们驱车自由穿行,独自或与男性伙伴体验自我转变或救赎的历程,而女性人物通常只是被动的乘客或他们的欲望客体(26)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3-144;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121;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20.。用学者蒂莫西·科里根(Timothy Corrigan)的话说,公路电影类型传统上专门聚焦于男性,女性则是缺席的[30](P 143)。然而,社会主义公路电影如《五朵金花》中的性别结构截然不同。尽管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如五位金花与她们的社员姐妹们)并非积极的旅行者,但她们代表着具有主体性的新型社会主义公民,积极参与生产劳动,发展妇女主体性,同时为社会主义发展贡献力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少数民族女性的解放与独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27)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工作者拍摄了多部关于少数民族女性自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影片,如《边寨烽火》(林农,1957)、《摩雅傣》(徐韬,1961)、《阿娜尔罕》(李恩杰,1962)、《景颇姑娘》(王家乙,1965)等。,回应着推动性别与民族平等的官方政策。金花作为少数民族女性干部,也是官方政策的一种折射,如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于1951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大纲中就强调,“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7](P 83)。学者王玲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国内多称作“妇女解放”“性别平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阶级斗争、民族革命与经济发展等议题齐头并进[31](PP 595-608)。1949年后,它成为官方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化的充满活力的实践,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核心政治议题息息相关。这一点不同于第一世界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女权主义实践:基于个人主义与争取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间杂被边缘化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声音。
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如何组织妇女劳动力时,白露指出,女性在公共领域和集体生活中付出劳动动员了一种根植于共同工作的大众主体性[24](PP 211-218)。在鼓励女性参与集体劳动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打破传统男权结构下的劳动性别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内”等),使得性别解放与其他政治与社会诉求如女性的阶级与经济解放密切相关。这种性别政策也令人想起恩格斯的理论:“只要她还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被局限在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妇女让其与男性平等就不可能。”[32](P 184)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改变性别角色和推动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至关重要。另一电影案例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是《李双双》(鲁韧,1962)中的进步妇女李双双,与其保守落后的丈夫相比,她政治觉悟更高,对公共事务更热心也更有能力。在关乎妇女的叙事中,健壮刚毅的社会主义女工形象在这一时期的视觉媒介中颇为普遍,对广大妇女起到鼓舞作用,《五朵金花》也不例外。《五朵金花》中,女性角色没有像美国公路电影的男主角那样开汽车或骑摩托车旅行(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中,这些都与男性与技术关联),但她们是出色的积肥能手、畜牧能手、拖拉机手和炼铁组长。和重工业或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打交道,传统上被视为男性专利,但她们信心十足地挑战这种劳动分工——尽管女性与重体力劳动的关系在片中的确被浪漫化了(28)纪录片《女拖拉机手》(沙丹,1950)与剧情片《女司机》(冼群,1951)、《马兰花开》(李恩杰,1956)、《笑逐颜开》(于彦夫,1959)中的女性都是经过刻苦努力,克服多种困难,最终胜任了传统的“男性职业”,如拖拉机手、火车司机、铲运机司机、建筑工人等。。虽然“大跃进”如今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激进的、颇有争议的运动,但奥地利学者金伯利·曼宁(Kimberley Ens Manning)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很多中国妇女认为这是妇女解放的高峰时期,因为“大跃进”为动员妇女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33](PP 138-156)。
自1958年起,中国政府号召农村妇女更大程度参与工农业生产。一些家务劳动被社会化(如成立集体食堂、托儿所及洗衣、缝纫小组等),妇女被部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与有偿劳动而获得经济独立,“同工同酬”也被提上日程。这使得她们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尊重,在工作中培养彼此支持的社群,也拓展了社会空间,使得她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甚至成为领导者(小说和电影《李双双》是呈现这些面向的典范之作)。同时,妇女也通过意识觉悟、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的提升为国民发展做出贡献。在将政治道德化的趋势中,这些具有先进意识的模范女性劳动者是新型公民社会主义理想的化身,银幕上下皆如此。如《五朵金花》中,五位金花都是各行各业的模范,在社会主义意识与职业技能方面都非常出色。阿鹏的爱人金花更是苍山公社的副社长,她高效无私地处理社里的各种事务。女性人物金花们被影片着重描写,她们的爱人退居次要位置。金花们被呈现为泼辣爽朗、勤劳能干、无所畏惧、勇于且善于表达想法,女性劳动主体的自信溢于言表。
《五朵金花》中积极乐观、自信能干、大公无私、富有健康美的少数民族劳动女性形象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性别与民族话语与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学学者梅根·布莱森(Megan Bryson)的研究表明,“五朵金花”形象为白族妇女提供了不同的榜样:一种现代社会主义的白族女性性征,取代类似忠贞、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美德”[34](PP 147-148)。金花这些女性模范也影响了几代中国劳动女性。女性社会地位与自我预期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认知有着长期的重要作用[33](PP 138-156)。社会主义女性既是《五朵金花》的核心人物,也是目标观众——它曾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放映[35](P 6)。《五朵金花》也成为动员大众的有效方式。20世纪50年代,大理白族地区与其他汉族地区都出现了无数以“金花/银花”为名的劳动竞赛。例如,陕西省的“银花赛”即是为《五朵金花》所鼓舞,宣传在棉花种植方面的当地妇女劳动模范。那里的妇女传统上只做家务,被局限在家庭空间,在农村的性别与阶级层级关系中被边缘化。《五朵金花》甚至激发越南人民开展类似竞赛以提高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受到列宁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29)Gao Xiaoxian,“‘The Silver Flower Contest’:Rural Women in 1950s China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in Zheng Wang and Dorothy Ko,eds.,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Oxford:Blackwell,2007,PP.164-182;秦家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重评〈五朵金花〉》,《思想战线》1977年第6期,第88页;李二仕:《〈五朵金花〉的“今点”意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第93页。。性别平等的话语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象征。
四、结语
《五朵金花》在地方、国家与国际层面都有丰富延展的生命。它在1959年首映与1978年重映时,都曾引发云南当地与全国观众的热烈反响。白族观众尹明举写道,1959年《五朵金花》在昆明上映时,24小时不间断滚动放映仍满足不了观众要求,作者看的是凌晨五点场。1978年《五朵金花》重映时,“每个电影场、院都像赶三月街一样热闹。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只要有盛大节会就少不了放映这部电影,歌曲则每天都响彻大理城乡”[36](PP 26-27)。1960年东北三省举行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新片展览周时,《五朵金花》等影片上座率达100%或95%以上。观众的热烈要求使沈阳、哈尔滨两地影院不得不增加放映场次。春节期间,竟至通宵达旦地放映,仍不能满足观众要求[37](P 9)。一位白族观众赞扬人物乐观热情地投入生活与劳动,“劳动带来爱情和幸福,把一穷二白的大理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幸福的乐园”[38](P 41)。少数民族民众对《五朵金花》这样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接受部分成为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想象与重构,以及他们生活与文化经验的一部分,加强了他们的自豪与尊严感。白族观众尹明举回忆看完《五朵金花》后余兴未尽的交谈,同学们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白族真好!”他写道:“从那时开始,‘金花’便成了白族的一张最醒目的名片,无论在国内国外,任何一个白族人只要说:我是从‘五朵金花’的故乡来的,人们就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了。可以说是这部影片在世界范围第一次给白族树起了一个艺术形象,给了白族一个叫得响的名字:金花”(30)例如,景颇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结婚时,会放映《景颇姑娘》来招待亲戚和客人。见李二仕:《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5页;尹明举:《第一次让全世界都认识白族》,《大理文化》2009年第1期,第26-27页。。人类学学者贝丝·诺塔注意到如今大理很多年长的村民还会自豪地看《五朵金花》,因为他们的家乡出现在这部著名电影里。他们从未对白族文化在影片中的表现有什么批评[5](P 79)。《五朵金花》的文化遗产也被大理政府用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大理有家名为“五朵金花”的电影院,每天为游客放映这部电影,并催生一部自称“《五朵金花》续集”的电影《五朵金花的儿女》(郝晓源、张进战,1990)[39](P 98)——片中的公路旅途与半个世纪后的旅游在此联结——副社长金花的女儿在片中是一位导游。
正视“公路电影”的国际性与跨国性而非一个本质上“美国”的电影类型有助于提供一个有效的概念框架来重新思考电影史上的另类公路电影以及当代公路电影中触及的新的主题与面向,如迁徙与身份、移民与离散、音乐与记忆等。旅行、运动与跨界是自电影史早期就备受关注的议题。一种充满活力的形式感与多数公路电影密切相关,如片中呈现的高速运行的交通工具带来的运动性、速度快感、不断变换的视野以及快速蒙太奇段落。然而,正是现代交通技术的缺席与非机械化的(或说更自然有机的)旅行方式使《五朵金花》显得独特:平滑、优美、缓缓横向运动的摄影镜头强化了苍山洱海的全景绘画感。影片描绘了一种更为传统的交通方式与不同于“垮掉的一代”的“青年文化”:浪漫爱情在此作为一条线索,编织进影片的讯息,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道路的崇高目标。《五朵金花》中,交通工具(如马车)并非私有而是公社的公有财产,两位长影来的客人可以随意使用。当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叹息机器如何异化了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及机械化的流动性带来的身体与社会的代价[40](P 9),《五朵金花》中的中国描画了一幅朝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热忱乐观的道路。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及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主流商业类型电影中也出现了更多公路叙事(31)如《站台》(贾樟柯,2000)、《走到底》(施润玖,2001)、《寻枪》(陆川,2002)、《旅程》(杨超,2004)、《在路上》(张菁,2004)、《千里走单骑》(张艺谋,2005)、《芳香之旅》(章家瑞,2006)、《练习曲》(陈怀恩,2006)、《男人上路》(刘小宁,2006)、《赖小子》(韩杰,2006)、《寻找智美更登》(万玛才旦,2007)、《红色康拜因》(蔡尚君,2007)、《落叶归根》(张杨,2007)、《香巴拉信使》(俞钟,2007)、《寻找阿依阔勒》(侯克明,2009)、《西风烈》(高群书,2010)、《人在囧途》(叶伟民,2010)、《太阳总在左边》(松太加,2011)、《转山》(杜家毅,2011)、《飞越老人院》(张杨,2012)、《后会无期》(韩寒,2014)、《心花路放》(宁浩,2014)、《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李睿珺,2014)、《路边野餐》(毕赣,2015)、《冈仁波齐》(张杨,2015)、《诗人出差了》(雎安奇,2015)、《失孤》(彭三源,2015)、《皮绳上的魂》(张杨,2016)、《冥王星时刻》(章明,2018)、《撞死了一只羊》(万玛才旦,2018)、《阿拉姜色》(松太加,2018)、《过韶关》(霍猛,2018)。跨国公路电影有在意大利和中国拍摄的《消逝的星星》(Gianni Amelio,2006)。,不过已与《五朵金花》截然不同。
电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媒介与文化形式,可以超越其地理空间与历史背景做“长途旅行”。《五朵金花》曾在“冷战”时期“旅行”到46个国家,在“文化外交”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家乙之前拍摄的《风筝》一样,传播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正面影像,加强了国际主义团结。20世纪60-70年代,《五朵金花》与长影出品的另一部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的歌唱风光电影《刘三姐》(苏里,1960)在港澳及东南亚上映,因其美好的山水、民歌与人物引发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响,成为“冷战”时期中国大陆争取南洋华人支持的重要文化媒介。1960年,《五朵金花》与其他一些中国电影在伦敦上映,评论者赞扬它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愉悦”,是“抒情性与现实主义的重新结合”[41](PP 84-86)。《五朵金花》中暗含的国际视野与想象使得其对国内外观众都有巨大吸引力——它展示了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美好的风景、公民与人情,王家乙回忆说,《五朵金花》的最高目标是让中国和外国观众“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周恩来总理也赞扬此片“歌颂了我们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人,歌颂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23](P 145)。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国际观众创造一个国家影像,是社会主义中国自我宣传的方式,是在充满冷战政治敌意的世界获得国际认可的努力[42](PP 74-84)。各国人民与文化团结的意识象征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本质上国际主义的现象[43](P 106)。《五朵金花》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公路电影的国际主义元素相遇与重叠,创造出一种旅行世界的多层次流动。在“冷战”的全球框架下重新解读以《五朵金花》为例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呈现形态及其独特的政治与美学意义,在“后/再—文化冷战”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更为复杂的今日尤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