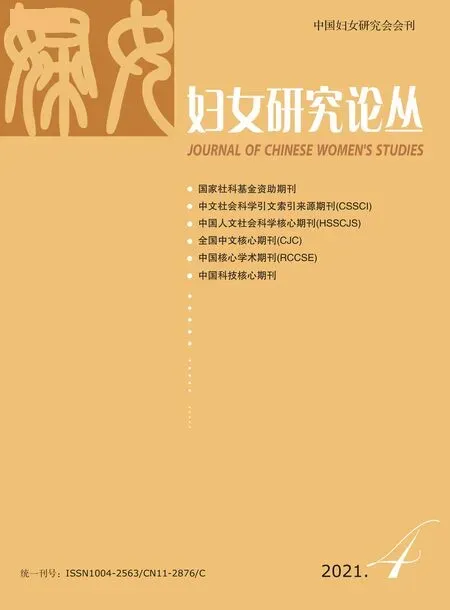明清社会的职业妇女:以稳婆身份的分流为中心
顾 玥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香港,999077)
稳婆在中国古代女性生育活动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元代陶宗仪所著的《南村缀耕录》中,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三姑六婆”这一庞大的群体:“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1](PP 318-319)这些称谓背后所指代的是不同女性工作者明确的职能分工(1)如《坚瓠集》中就有对于“三姑六婆”各自工作职能进行辨别的论述:“卦姑,今看水碗、乌龟、算命之类。师婆,今师娘,即女巫也。药婆,今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但虔婆未知何所指。”[清]褚人获撰:《坚瓠集》,载《清代笔记丛刊》(第二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三姑六婆”的职能往往是互通的,如为人接生的稳婆也会从事兜售堕胎药的营生,媒婆在一些案例中从事着发卖人口的工作。“稳婆”这一称谓在元代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接生者”的角色直到此时才出现,事实上,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稳婆在过去也被称为收生婆、坐婆、产媪、老娘等。
现有对于稳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她们与接生、胎产相关的工作,此外,士人阶层对于稳婆群体从道德和医疗层面上的抨击也是前序研究所重点关注的话题(2)有关稳婆在中国古代妇女生育活动中所扮演的医疗照顾者的角色,以及她们在胎产领域做出的贡献,李贞德、梁其姿、洪有锡与陈新丽等人在其研究中曾深入讨论过。而关于稳婆形象的塑造以及士人和精英阶层对于这一群体的抨击,在张璐、许璟梓以及顾玥等人的著作与文章中都曾深入讨论。详见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梁其姿:《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载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洪有锡:《先生妈,产婆与产科医师》,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张璐:《近代稳婆群体的形象建构与社会文化变迁》,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许璟梓:《明代〈三言〉小说中的“三姑六婆”形象》,《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顾玥:《明清笔记小说与医案中稳婆形象刍议》,《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1期。。至于稳婆承担的接生以外的诸多职能,包括甄选、辨验、监管等工作,虽然目前尚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但也有学者提出过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如在《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一书中,衣若兰指出,由于稳婆的专业使其有机会频繁地接触女性身体,并深谙妇女的身体结构,因而在明清社会时常会被委以验身或监管女犯的工作[2](PP 71-72)。徐晨光在《清末民初北京城稳婆合法性论述:以法令与地方档案为例》一文中则基于对法律条文和地方档案的研究,揭示清末新政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稳婆在社会中的合法性[3](PP 89-94)。事实上,稳婆的衍生职能如其接生工作一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明清时期,受到社会风气与社会需求的影响,稳婆的衍生职能产生了重要的转变:官府开始将稳婆纳入人员编制当中,并与之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而这种转变使得明清时期的稳婆群体具有了职业妇女的特性。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职业妇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职业妇女”的定义脱离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所衍生出的女性主义思潮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存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从事劳动的妇女并不少见,她们创造了实际且可观的经济价值。女性从事的养蚕、纺织业甚至成为一些地区的支柱产业。在明代的《几亭外书》中曾提及当地妇女“嬉怠成习,布缕皆易于外境,以故日益贫”[4](P 315)的情形,直到官府干预才逐渐改善,并基本做到自给自足。纺织业不仅可以满足家庭所需,某种程度上还能生产剩余产品,为地方上的赋税做出贡献[5](P 319)。至少从宋代起,中下阶层妇女就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着大量的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在“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下,家庭的兴旺反倒很多时候取决于女子的劳作成果[3](PP 189-191)。那么这些女性劳动者是否可以被囊括在职业妇女的范畴中呢?
中国古代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为其所在的家庭创造经济价值。事实上,女性会用她们的工作成果来换取少量的钱财或者等值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衣物等,其本质上还是用来贴补家用的。换言之,“女性的工资仅仅是补贴家庭支出,因而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职业地位;并且她们也不可能持久地工作而反抗家庭事务确定下的身份。”[6](P 199)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通过桑蚕、纺织以及务农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却并未脱离家庭经济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工作之间并没有建立某种长期且稳定的联系(3)而在江南织造的绣娘、织女虽然从事着相同的手工业劳动,但是由于其工作性质和雇佣性质,使她们有别于在家庭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妇女劳动者。。而对于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被教导以拥有优秀的女红技术为荣,并将其与自身优良的女性品质相联系,但是其从事的手工劳动并非创收性的工作。上层社会女性不必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这事实上也是一种特权阶层表达其社会地位的方式[4](P 190)。
中国古代缺乏职业妇女,这似乎是过去妇女史研究中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定认知。事实上,那些脱离家庭生产模式而谋生的女性从业者或许稀少,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从未缺席。梁其姿在研究明清慈善组织的著论《施善与教化》中曾提到育婴堂的乳妇,她们离开家庭到育婴堂以哺育弃婴为生计。她们在后期甚至联合起来占据善堂,以对抗负责管理她们的男性,这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对于中国古代职业妇女的刻板印象[7](P 5)。当然,传统社会中的职业妇女并不限于此:例如明末清初以教书及出售诗画为生的“闺塾师”黄媛介,她以自己,而非杨世功之妻或是其他男性家庭成员的亲友身份游走于江南的城镇中,并极力寻求被雇佣的机会。作为一名职业艺术家,她的确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8](P 131);又如谈允贤这样有家学渊源的成功的女性医者,她的家庭虽然并不需要她利用医术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但是早年的经历已经令其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行医获得社会认可[9](PP 256-260);除此之外,当然还包括那些游走在大街小巷的“三姑六婆”们。这些职业妇女除“家庭身份”外的“其他身份”,正是通过其所从事的工作被社会认知和接受的。其中,为官府服务的稳婆可以作为职业妇女的典型。在明末清初,稳婆为民间或官方机构从事着甄选、辨验、验尸/伤以及伴押、看管工作,这种与官方的联系更好地映射出稳婆的职业与身份是如何被社会识别和接纳的。本文将着眼于稳婆在官府中从事的诸多衍生职能,介绍这些工作的形成与侧重,讨论在明清愈发强烈的性别隔离意识下,稳婆接生以外的工作如何变得官方化,以及她们如何被纳入司法勘验制度当中并获得固定的收入。这可以被视作一场重大的转变:这一时期稳婆的身份也产生了分流,清代政府希望从法律上将民间接生的稳婆与官府中承差服役的稳婆进行区分,后者的身份被纳入贱籍。从中可以看出,官方并不鼓励这种脱离家庭、在外谋生且拥有固定收入的职业妇女群体的形成。
一、明清稳婆的官府工作
由于接生这一本职工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稳婆群体对于女性的身体有着特殊的话语权。相较于男性医者,她们灵活运用着性别的优势以获取孕妇、产妇及其家人的信任[10](PP 46-55)。诸多稳婆的衍生职能就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产生的。其中的一些最初并非由官府委任,而是因民间需求应运而生的。那时稳婆的接生工作与为官府承差服役的工作之间界限并不明显。直到清代初期,这种自下而上的、愈发强烈的需求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稳婆的官府工作才获得法律上的肯定。稳婆承担的接生以外的工作职能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甄选
在皇宫中需要甄选奶口、宫女、女官以及妃嫔时,稳婆往往会在其中扮演甄选者的角色,以辨验应征者是否存在隐疾。如宛平、大兴两县的衙门在甄选奶口时便会“博求军民家有夫女口,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夫男具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仅三月者,杂选之,仍令稳婆验无隐疾,具结起送,候司礼监请旨”[11](PP 285-290)。此外,一些稳婆也会被留用在宫中以备不时之需:“就收生婆中,预选名籍在官,以侍内庭召用,如选女则用以辨别妍媸可否,如选奶口,则用等第乳汁厚薄,隐疾有无,名曰稳婆。”[12](PP 301-302)嘉靖年间选取宫女的条款印证了稳婆确实参与其中:“顺天府转行宛大二县,拘带稳婆于是日寅时,赴馆听用。”[13](P 37)稳婆由于从事接生工作而对女性身体更为了解,使她们成为担任此类工作的不二人选。
有时为官府工作的稳婆也会从甄选者转变为被甄选者。维多利亚·卡思(Victoria Cass)在介绍明代京城礼仪房医婆、稳婆和奶口的论文中曾提到,明代的北京女性开始从事包括诊脉医、乳母、稳婆、医婆、药婆、仵作以及巫师等不同的职业[14](PP 233-245)。事实上,这一时期如若宫中妃嫔有孕,会提前在民间进行相应人员的选拔,其中主要包括医婆、奶口和稳婆[15](PP 83-84)。稳婆被遴选入宫,为之后的接生工作做准备,而她们虽然得到了官方的聘用,却往往是短期和一次性的,在婴儿出生以后稳婆就会被放出宫去。工作本质并没有脱离与胎产相关的基础职能,因而在此不做赘述。
(二)辨验
辨验妇女的身体可以说是出现在明清世情、笔记小说中最为常见的稳婆职能。官府案件、民事纠纷中时常会涉及在室女与外男有染的情况,往往需要稳婆辨验女性是否依然为完璧之身,辨验结果则直接影响案件走向。当然,在一些时候老媪、嬷嬷或家中女性长辈也会代替稳婆充当这一辨验者的角色,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稳婆在此类情境中占居主导地位。例如,在明代笔记小说《双槐岁钞》《焦氏笔乘》以及《明书》中都记载的名为“木兰复见”的故事中,主人公为自证清白主动延请稳婆为其辨验。这属于一次性的民间行为[16](P 416)。而在《古今奇观》所收录的一篇名为“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故事中,地方知府因判案需要差人寻来了当地的“老实稳婆一名”以辨验当事人是否为处女[17](PP 540-564)。这里的稳婆并非在政府机构中长期供职,仅仅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应招,收生依然是她们的主业。当然,到了明末清初,稳婆多重身份混杂的情况随着官府对于稳婆需求的扩大也发生了转变。明清作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可以清楚地展现出稳婆从接生者到官府工作者这一角色演变的轨迹,这将在下一节着重讨论。而相比民间记载中淡化辨验过程的特点,一些官方的材料特别是从衙役视角出发的记载则更侧重于验身的过程以及注意事项:“若是处女,劄四至讫,劄出光明平稳处,先令稳婆剪去中指甲,用绵札。又令死女母亲及血属并邻妇二三人同看,验是与不是处女。令稳婆以所剪甲指头入阴门内,有黯血出是,无即非。”[18](PP 239-240)这些勘验流程从宋代就已经出现,并沿用至明清时期。
此外,一些涉及阴阳人、男变女、女变男的案例也会在笔记小说中时有出现,如《广阳杂记》中载一妙龄女子忽变男身的奇闻异事[19](P 23),又如《奁史》中兼具男女两体的阴阳道士[20](P 1899)。忽如其来的性别转变和违背常理的性别特征往往会带来周遭的质疑以及一系列连带问题。而在这类事件中,辨验性别的职能可以说是稳婆检验女性是否依然为完璧的工作的一种衍生。中国古代严格的礼教意识曾令医者抱怨在为女性病患诊疗时需要用帛幔盖在手臂上切脉,以避免直接的肢体接触,并通过层层帷帐观测病人的面色,使得医家必备的“望闻问切”无法施展[21](P 17)。这样的性别隔离意识在明清时期更加固化,想要让男性完成查探私处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由女性来完成。由于稳婆长期从事着收生相关的工作,这使她们对于女性的身体比其他人更为了解。而同为女性医疗从业者的女医群体虽然对于女性身体也有着令人信服的话语权,但是她们的身份往往会为其开展辨验工作带来阻碍。明代中后期,编撰和阅读医学著作的女性明显增多,女医群体逐渐壮大。如撰写《女医杂言》的谈允贤、歙县名医陈邦贤之妻蒋氏以及医者徐孟容之妻陆氏等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她们的父亲、兄长或丈夫往往也是医疗从业者,这使得她们拥有深厚的家学渊源[2](PP 63-66)。换言之,女医除了医者的身份,更是懂得如何读书写字的上层社会女性。费侠莉曾指出,阶级的因素使得女医与稳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界限[9](P 266)。相较于前者,后者往往来自中下阶层,因而当她们在应对涉及性别转换和需要查探私处的案例时,礼教的约束力大大减弱,这为她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便。稳婆丰富的助产经验使得她们在辨验这一领域相较于一般妇媪更具有话语权,同时与女医群体相比,她们的身份更具便利性。这些特点令其扮演着具有说服力的勘验者角色,并给予令人信服的证词。
(三)验尸、验伤
在稳婆的诸多职能中,验尸、验伤工作是最能展现其技术和职业性的。事实上,她们在宋朝乃至更早时期就陆续出现在相关记载中。先秦时期便有参与检验的隶妾。到了宋朝,验尸通常由检验官与仵作共同完成,只有勘验到妇女下部时,才由坐婆参与[22](P 59)。宋朝的《洗冤集录》提及诸多颇为详细的女性验尸流程,如:“若妇人有胎孕,不明致死者,勒坐婆验腹内委实有无胎孕。如有孕,心下至肚脐,以手拍之,坚如铁石;无即软。”“若无身孕,又无痕损,勒坐婆定验产门内,恐有他物。”[14](PP 239-240)此外,由于量刑需要,《平冤录》中也提及关于胎儿死因以及月份界定的方法,涉及稳婆的参与:“堕胎儿在母腹中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淡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若月未足者,其身体必有生未全处,仍集生婆验之。”[23](PP 522-523)这些记载足以反映出,在明清以前,稳婆便已活跃在验尸这一领域当中。然而,虽然涉及稳婆的验尸方法早已存在,但是从宋朝到清朝,女性死者由男性仵作直接勘验的例子并不少见。
清代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此之前涉及对于女性死者进行勘验的记录中,稳婆虽然时常会应官府的传唤完成检验工作,但是无论是刑部还是地方官府的人员设置中都未找到稳婆的身影。这种情况在清初发生了改变。顺治十八年,皇帝准许在审理重案时,“有应检验尸伤者,移咨刑部,委司官率领仵作稳婆会同检验,填录尸格”[24](P 70)。稳婆以验尸者的身份参与到了刑部的勘验工作当中。在清代的《刑案汇览》中提及的刑部司务厅的人员设置中就已明确:“充补书吏皂隶人等,经承九十八名……稳婆二名,刺字人役二名,仵作二名。”[25](P 6)自此,稳婆被正式纳入政府的编制当中,这对于她们职业妇女身份的巩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她们作为女性验尸者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她们也因为这份工作获得了固定的酬劳。刑部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各役四季工食,仵作十八两,稳婆八两一钱,刺字役六两。”[23](P 6)这表明为官府承差服役的稳婆获得了一种长期、稳定且官方的雇佣关系,使得她们可以完全脱离家庭经济,将官府工作作为收入可观的主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稳婆立即被推广至地方,并被纳入地方衙役的编制当中,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在乾隆年间贵州司主事陆钟辉呈报的奏折当中提到,在相对落后和偏远的地区依然存在“人命相验不论男妇,总凭仵作当场唱报”[26]的现象。
除了验尸之外,验伤也是稳婆重要的工作职能之一。如在乾隆四十四年,步军统领衙门的奏报中提及,由于河南邓州民妇王焦氏控告其侄王维坤“图占产业”,“屡行逼伊改嫁”,更是“将伊吊打,割去左乳,刃伤胸膛数处”,因而传稳婆验伤,发现所控伤痕均属实[27](P 6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保留了许多清代刑部由稳婆画押的验伤单据。如“为韩刘氏臁肕并无青红晕色痕事”一案中记录道:
具甘结稳婆王氏今于
与甘结事依奉,验得韩刘氏右臁肕并无青红晕色伤痕,所结是实。
四月初二日甘结稳婆王氏[28]
又如在“为镶黄旗满洲新授西安都司敦伦欧伤契典家人张福身死并欧伤其妻张赵氏”一案中记录如下:
具甘结稳婆赵氏今于
与甘结事依奉,验得活妇人张赵氏右臂连右腿重叠木器伤,右膝偏右红赤伤一处,量斜长三分,垫扼伤,右腿偏左连近下重叠木器伤,左臂连左腿重叠木器伤,左腿偏右右手揿痕印,余处无伤,现怀九个月身孕,所具甘是实。
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具甘结人赵氏[29]
在清宫刑部女性验尸单据中,往往会由男性仵作与稳婆一同勘验并画押,并未出现由稳婆一人单独勘验的情况。那时的稳婆虽然已经获得一些职业认同,也被纳入了政府编制当中,但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她们的权力很有限。而上述女性的验伤单据,则是少见的由稳婆独立填写完成的报告。
(四)伴押、看管
如果说上述稳婆的工作职能与她们的接生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稳婆对于女性身体的了解使她们在甄选、辨验、勘验等活动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伴押与看管工作看上去与稳婆的本职工作的关联性并不那么明显。在《大明律》针对女性罪犯的条款中规定:“若(孕妇)犯死罪,听令稳婆入禁看视,亦听产后百日乃行刑未产而决者,杖八十。”[30](P 620)事实上,明清时期不仅会勒令稳婆看管怀有身孕的女性罪犯,对于情节较轻、案件在审、发配到其他地区的女犯,也大都会勒令稳婆伴押、看守,甚至还会出现将有诉讼在身的女性寄放稳婆家中等待传唤的情况[31](P 49)。《吏治悬镜》中更是对于清代女犯的囚禁制度作了明确的解释:“盗贼之妻,姦拐之妇,在官者,着老成媒稳婆看守。有亲者取保。无亲者,着有内眷之歇家收管。”[32](PP 31-32)在清末以前,对女性的监禁颇为慎重,往往通过责付制交由犯夫、亲属、邻佑看管,在少数不得不收监的情况下,也由稳婆陪同,对女犯进行保护[33](PP 100-109)。但是不难发现的是,相较于勘验甄选,伴押、看管的工作专业性并不强,与稳婆本职的接生工作联系也并不密切。有关这一职能的成因及其秉承的历史脉络,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着重论述。
二、清代稳婆身份的分流
明末清初,烈女节妇自杀的行为骤增,贞女现象在明朝后期形成了一种趋于极端的特点,女性一方面被社会风气裹挟,另一方面又从中获得自我满足,进而形成了一种自我塑造的固有模式[34](P 9,P 142)。有关这一时期妇女节烈的成因,既往研究中已经进行过充分讨论(4)如董家遵、芦苇菁、衣若兰、费丝言等人的研究。此外相关区域性节妇研究、学位论文以及期刊论文也对明清时期节妇自残、自杀、个人意志与行为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见董家遵:《历代妇女节烈的统计》,载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79年;[美]芦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衣若兰:《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费丝言:《从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洁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洁观的严格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98年。,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值得强调的是稳婆在这一时期有关勘验、辨验等相关工作的增多,一方面可以被视作对于妇女自杀风气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在性别隔离语境下对于潜在的自杀行为的规避以及对于妇女的保护。在前文中所涉及的官府职能中,民间私自雇佣稳婆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在验尸、验伤以及辨验工作中,虽然可以零星看到稳婆的身影,但是并不能展现出这是一种长期的、官方的雇佣行为,这些零星的、一次性的聘用无法使稳婆视之为主业,并依仗其糊口。
官府由于案件需要,故而从民间聘请替人接生的稳婆进行辨验,这种模式事实上削弱了稳婆的职业性,使她们的官府工作并没有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短期或一次性的勘验工作无法成为稳婆的主业,使她们放弃接生工作或是彻底从传统的家庭经济中脱离出来。然而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祝子志怪录》中曾记载了一件名为“二女生子”的奇闻异事:明成化年间,江宁县一在室女妙清忽然有了身孕,人们怀疑她与奸夫勾结,便将其送入官府。官府因此唤来了为江宁县雇佣的稳婆李氏为她辨验。
江宁县稳婆李氏看验得,妙清身系室女,尤恐不的。行取江阴县稳婆尹氏覆验勘,得妙清的未破体,鸡冠俱全[35](P 559)。
在这一案件中先后涉及两位稳婆的证词。江宁县的李氏认为女子怀有身孕却依然完璧这样的事情太过匪夷所思,与其常识相左,故而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于是官府又找来了为江阴县服务的稳婆尹氏再三勘验,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才算是有了定论。事实上,事情的成因是嫂嫂在与妙清偷欢之时,意外“将夫前行房事余精,过入妙清阴内”[33](P 559),不料最终导致妙清怀有身孕。可以看出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与稳婆之间一种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已经开始形成,许多地方政府也会有自己长期合作或者使用的稳婆。文中涉及的江宁和江阴县便属于这种情形。倘若两县在案发时才寻找民间替人接生的稳婆进行勘验,则此案只需在江宁县一处便可解决。
清康熙年间,贵州司主事陆钟辉在奏折中称述了京城与地方勘验妇女的差异:
在京刑部验伤,凡系妇女皆用稳婆。照依仵作如法相验,所以别男女,养廉耻法甚善也。至如外省州县,人命相验不论男妇,总凭仵作当场唱报[24]。
陆钟辉试图将刑部长期聘用固定稳婆的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以避免在案发时临时聘用当地接生稳婆的情况。将稳婆纳入地方司法勘验体制,更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地区以人员不足为由勒令仵作为女性死者直接勘验的情况。陆钟辉认为,让男性仵作在女子死后对于她们的身体检验是非,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基于这种考量,他向乾隆帝提议:
勅下刑部通行直省州县,凡遇检验妇女,照内部用稳婆之例,如或州县之内稳婆不谙相验之法者,设法教导俾其熟谙,给以工食,每州县设立一二名,以备检验妇女之用,庻男女有别,不独养廉耻于生前,且施恻悯于身后[24]。
地方府衙稳婆之职的设立,很大程度上仿照了明代仵作之职,将稳婆正式纳入编制当中。此外,陆钟辉还提到,对于地方上没有精通勘验技术的稳婆,则可令官府统一培训,传授技艺,这从另一个层面肯定了稳婆的勘验、辨验工作的专业性。而“给以工食”则确保为官府雇佣的稳婆可以获得固定的收入。陆钟辉提出这样的建议,字里行间是为保全妇女死后名节的惠民之举,其本质是这一时期日渐固化的性别隔离意识的外化表现。明清时期列女传记的数量激增,其价值导向也从对于女性各种“美德”的赞美转向了女性对于婚姻之忠贞和身体之贞洁的宣扬[36](PP 114-115)。无论是社会或是女性自身都时刻约束着她们的行为,避免与非直系亲属的男性产生言行特别是肢体上的接触。在这种性别隔离意识盛行的大环境下,稳婆在为女性死者验尸时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正如陆钟辉所言:“妇女命案出于斗殴者少,出于自尽者多,起在无知轻生者,尚当悯其廉耻,而况因奸不从守节自尽之妇,生前矢志完贞,身后男子检验是非。”[24]让稳婆而非男性仵作完成验尸工作,从根源上讲是为了回应死者及其家属的廉耻心和礼教观。
清末时期稳婆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在道光七年(1827年)礼部钦定则例中有一段关于稳婆子孙后代参加科举的规定。在这项规定中将稳婆群体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根据她们的工作内容(收生或勘验)进行身份的分流:
七年议定,民间收生妇女,地方官概不准勒派验奸,果无别项身家不清,其子孙应准其捐考。如系承差服役,传验奸情,迹类仵作,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查係身家清白,方准捐考[37](P 177)。
这是一项具有标志性且引人深思的规定。民间进行接生工作的稳婆即便受到了地方官府的传唤也不可以进行勘验工作。这意味着官府拥有专门的人员为女性进行辨验或者验尸,而她们正是那些被纳入政府编制中的稳婆。基于现有资料,尚无法确定法律条文的制定与社会现实是否存在着某种偏差,换言之,无论是稳婆还是官府都有可能会因为某些现实因素而在法律条文中寻找回旋的余地。不过相比法规的贯彻,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其制定法律条文背后的动因,即官方试图促成稳婆身份分流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差服役的稳婆子孙改业后四代之内都不可参加科举,这意味着她们的身份有别于民间接生的稳婆,落入了贱役的设置。在清代各县的地方政府对于差役的规定中,都会有仵作及随学仵作这样的人员配制。而这些正身差役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贱役,虽然在清代后期,政府也曾规定一些奔走力役须从良民中选拔,但由于这种规定要求服役的良民投入贱籍,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太强的执行力[38](P 79)。在此后人们对于为官府工作的稳婆进行论述的时候,可以看见对于她们身份尤为卑贱或是良家妇女不屑为之的讨论[39](P 73)。而这种“卑贱”与明清时期士人阶层对于稳婆群体从道德和医疗层面上的抨击有所不同,它更侧重于为官府工作的稳婆属于贱籍的认知。
从之前的论述可知,稳婆在民间的勘验工作颇具历史渊源,即便偶有官府传唤检验,她们也依然会在民间继续从事收生工作。到了明代末期,一些官府会长期聘用稳婆来为刑案中涉及的女性进行检验,却也没有明文规定这些稳婆不可继续从事接生工作,或者将接生和勘验的稳婆明确地区分开来。随着清代司法体制对于女性检验流程的日趋完善,负责收生的稳婆和在官府中任职的稳婆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群体,且不再互通。她们虽然依然共享统一的称呼,但是就身份而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根据清末礼部条例,如果民间收生的稳婆在偶然的情况下“经传验奸,情跡类仵作者,应比照丐户等情愿削籍之例办理”[40](P 9)。这样的条例使得民间接生的稳婆在由于特殊原因受到官府传唤替人验奸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由良转贱的问题。这也导致稳婆群体内部对于职能的分割和身份的分流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使得律例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约束,更是具有某种内动力的自我分化。
为官府服务的稳婆被划为贱籍,一方面是将她们彻底纳入官府衙役编制当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官方试图杜绝收生稳婆为官府服务的态度。从前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礼教观和性别隔离意识下,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府都对女性勘验者有着迫切的需求。当官府赋予稳婆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时,她们独立的社会身份无疑也获得了官方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稳婆们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矛盾体:她们的工作一方面为社会和官府所需要,另一方面在外谋生的职业妇女身份并不符合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规诫。中国古代的女性往往是置于家庭关系中被世人认知的,她们往往是某人的女儿、妻子或是母亲。然而,承差服役的稳婆们不仅受到官府的聘用,更重要的是她们脱离了家庭经济的模式,以独立的“人”的个体与社会产生了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女性游离于家庭关系之外的企图往往会遭到排斥[34](PP 53-54)。因而官方并不鼓励这种妇女在外谋生、拥有固定收入的职业模式的形成,并通过强调良贱的区分对职业妇女进行压制。
三、稳婆与官媒的混用
回到第一节最后遗留下的问题,伴押、看管的工作与稳婆本职的接生工作联系并不密切,它们又是如何出现并成为稳婆的衍生职能之一的呢?在此就需要引入明清时期官媒这一群体来进行说明。可以看到,清代一些文献材料中会出现将稳婆与官媒混用的情况,如在《居官日省录》曾对官府中稳婆的设置如此解释道:“凡有司衙门。设有稳婆。又名官媒一项。系隶中之尤贱。为良家妇所不屑充应者。专以伴侍犯妇而设。乃近来有司。因定例有妇女罪犯不致死。及实发驻防概不羁禁之条。往往发交官媒看管。”[37](P 73)在这段论述中主要强调了稳婆伴押、看管等职能,而对于颇具专业性的勘验、辨验等工作并未提及,这与稳婆的工作侧重并不相符。
有关官媒的研究,目前已有颇为丰硕的成果。官媒的设置最早出现于《周礼》,最初为官方婚姻管理机构,在宋元时期也从事与婚俗方面相关的工作[41](PP 119-125)。在宋代,官媒是由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设置并给予一定俸禄的媒人,她们是由乡社里掌管风化的长老推选出来的诚实可靠的妇人,在官府登记后,由官府统一管理[42](PP 91-92)。也有学者在总结元代官媒特征时指出,那时官媒的身份是半官方化的,她们属于“民”,却又有“官”的特征[43](PP 190-203)。这事实上为明清时期官媒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历史的演化中可以看出,官媒的职能主要与婚俗、人口发卖有关(5)吴佩林、张加培指出,官媒中或许也存在着非女性的情况,如光绪年间四川南部县的吴元清、廖发元、谢前春、吴源鸿,巴县的李茂侯。档案资料显示,“每逢春秋祭祀,以及朝贺火把、粘贴四门告示、遇有迎官接照、大差过境、支应纤夫,均归民承办。”而这些主要还是衙役的工作,涉及妇女或需要与妇女直接接触的相对较少,与传统意义上的官媒工作并不相符,值得进一步讨论。见吴佩林、张加培:《清代州县衙门中的官媒》,《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但到了明清之际,官媒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押解女犯向来由男役完成,并未作性别上的区分,乾隆九年有人提出,在长途押解之中,“恶劣解役阴加侮辱,明肆欺凌”[41](PP 119-125)。因此,山西按察使多纶奏称:“查各省州县均有官媒婆一项,监禁女犯,俱系伊等轮流值守,应即间接生的稳婆无法继续从事辨验、勘验等工作于此等媒婆内佥派伴押,逐程交替……如此则军流犯妇得免解役侮辱之虞。”[44]此后,伴押、看管等工作就成为官媒的主要职能。官媒在历史上从事着与人口发卖相关的工作,一些善堂招募乳妇时也会仰仗官媒的引荐[45](P 27),而官媒除了看管押送女囚犯以外,还对于奸犯妇女有发卖的权利[41](PP 119-125),这样的历史演化脉络相较于稳婆无疑更为连贯。事实上,在清代与律法相关的条文中,“官媒”主要与“发卖”“伴押”“看管”等词语相关联,而“稳婆”的官府工作则主要与“勘验”“处女”等词语相关联。
当然,正如稳婆会兼任官媒的押运工作一样,官媒偶尔也会从事检验妇女的工作[46](PP 69-77)。比如在清末有关良贱混淆的法律条文中就曾规定:“查收生妇女,专业生产。若处女犯奸探验真假,应由官媒应役。良贱不至混淆。”[25](P 12)在这里论述的内容与道光七年礼部钦定则例中有关稳婆身份分流的内容相似。不过在论述到为官府承差服役的女性衙役时,对于检验妇女之类应由稳婆负责的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也用“官媒”一词来代替,可见这一时期对于两者的混用。至于这种混用行为源于何处,以及为何稳婆会被赋予伴押、看管的工作职能,《大明律例》的条文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性线索。在有关“妇人犯罪”的条例中提及“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的情况,其明确提出如需对孕妇进行拷讯,必须待到其产后百日。“若未产而拷决,因而堕胎者,官吏减凡斗伤罪三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产限未满而拷决致死者,减一等。”[47](P 27)而对于犯有死罪的孕妇,则会让稳婆入禁看视,以确保产妇的健康状况,待其产后百日再行刑[47](P 27)。这种规定是对孕妇及胎儿的保护。在涉及罪犯为孕妇的情况下,稳婆对于女性身体的了解以及对于胎产的丰富经验便有了用武之地,她们也因此被选择成为看管者。作为较早提及稳婆看管和伴押工作的文献,《大明律例》中所涉及的工作内容还是与稳婆的接生职能紧密相连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入禁看管的工作与原本就为官府执行伴押工作的官媒产生了重叠,进而导致在清代的相关论述中,即便女性罪犯并无身孕,也会令稳婆参与到看管伴押的工作当中,最终导致清代一些史料中官媒与稳婆混用的情况。
从清末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发现,对于官媒的定义已经更侧重于广义上的女性衙役,而非狭义上的具体职能:“官媒为妇人之充官役者。旧例: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皆交其执行,故称官媒。兼看管女犯之罪轻者,如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地方,俱派拨官媒伴送。”[48](P 2115)侧重点的变换突出了这一时期性别意识的显著影响。无论是稳婆还是官媒,在清代末期都代表着相似的符号,即司法程序中的女性工作者。通过研读陆钟辉与多纶的奏章不难发现他们秉承类似的思想脉络:他们明确提及了官媒或是稳婆的工作是为了让女性免受“侮辱之虞”或是避免男子对于她们死后的身体“检验是非”。虽然也有学者在既往研究中指出,由女性官媒承接伴押工作以后,对于女性罪犯的凌辱并没有减少,甚至出现了变本加厉的事态[41](PP 119-125)。稳婆与官媒的发展虽然顺应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脉络,但让女性角色介入勘验或是伴押,从官方的角度出发是为了维护妇女贞洁的开明之举,避免了女性与陌生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肢体接触。事实上,在一些地区,无论稳婆与官媒是否被混用,至少展现出明末清初官府对于女性衙役需求的迫切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大趋势。一次性或者多次性的雇佣关系已经无法满足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在性别隔离意识的驱使下,都渴望着维护女性(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免于受到陌生男性的沾染和接触。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就了为官府承差服役的稳婆职业妇女的构建。
四、结论
明清空前增强的性别隔离意识催生了一些生活模式上的转变,人们开始渴望由女性来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以避免陌生男性与闺中妇人的接触,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需求,如明代女医的形成,又如本文讨论的稳婆。事实上,稳婆的甄选、辨验、勘验工作可以被看作由其对于女性身体的了解而产生的衍生职能。至于伴押与看管工作,则可以被视作稳婆与官媒混用的结果。事实上,无论在时人看来两者的职能和工作侧重是否相同,都无法否认清代政府将女性纳入衙役编制的迫切性。他们需要女性角色去完成男性仵作、衙役无法完成的工作,以满足民众对于性别隔离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为官府工作的稳婆因此具有了职业妇女的特征。有别于早期偶尔被官府传唤勘验或是将官府工作作为副业的情形,清代的稳婆被纳入衙役编制中,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她们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使其脱离家庭经济模式。与此同时,稳婆的身份也出现了分流,清代法律通过良贱划分,使民间接生的稳婆无法继续从事辨验、勘验等工作。这一方面是成为官府衙役后身份的必然转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体现出官方并不鼓吹这种妇女在外谋生、拥有固定收入的职业模式的形成,因而杜绝民间接生的稳婆继续从事官府工作,其本质还是希望女性回归以家庭为主导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