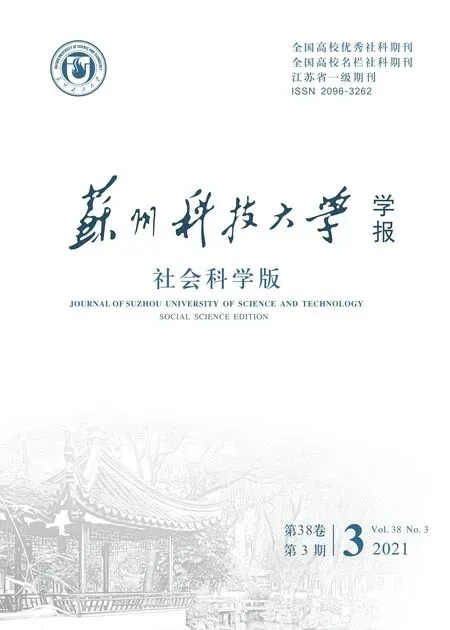董仲舒、司马迁灾异思想异同论*
赵 琪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09)
一、灾异思想成立依据之异同
灾异,主要是指自然灾害(地震、水灾等)和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日月食、流星等)。大体从周人起,人们开始在本为自然现象的灾异与人类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间建立起某种感应和联系,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灾异思想。[1]西汉时期,灾异思想盛极一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观念构建起一套系统的灾异学说。[2]言说灾异,成为西汉政治生活的鲜明特征之一。①例如,灾异与汉代诏书的关系,参见叶秋菊《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第119~122页;灾异与皇权强化之间的关系,参见孙喆《灾异:汉代帝王强化皇权之借用工具》,《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第126~130页。在相似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史学家司马迁与经学家董仲舒一样,也发展出自己的灾异思想。两人灾异思想间的异同,折射出经学与史学的不同理路。笔者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分析与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1.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经学依据
作为一名经学家,董仲舒是从儒家经典《春秋》中寻求灾异思想成立的依据的。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在回答汉武帝“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际,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3]2513这一关乎天人、古今的大问题时,董仲舒结合《春秋》所反映出的天人、古今关系曰:
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3]2515
这段话实际上回答了两个问题。其一,天人、古今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从“圣人法天而立道”至“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这段话可见,董仲舒认为天人关系实际上体现在古今关系之中,即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人通过取法上天所立的道存在于古今历史进程之中。而“孔子作《春秋》”至“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由人所制定的存在于古今历史发展之中的“道”又具备“天人”上的依据。可见,董仲舒认为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其二,天人、古今间的彼此关联如何能够实现。从上引“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中不难看出,董仲舒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正是上述天人、古今间彼此关联的最佳载体。这一点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符瑞》篇中所说的“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4]157-158是一致的,都表明董仲舒要为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寻求经学上的依据,即将天人关系的合理性建立在《春秋》经之上。那么,作为天人关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异思想,其成立的依据显然也在《春秋》经之上。事实上,董仲舒的上述思想对随后司马迁提出“继《春秋》”的思想主张是有深刻影响的。
2.司马迁灾异思想的经学、史学依据
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在谈及自己撰写《史记》的缘起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3296
随后,司马迁大段引用了董仲舒经学对《春秋》的理解来回答壶遂关于孔子为何而作《春秋》的提问。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段是: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3297
可见,司马迁的“继《春秋》”主要继承的是董仲舒公羊学的《春秋》。事实上,认为《春秋》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古今思想的观点,不仅是董仲舒、司马迁的私见,而且是当时儒家学者们的共识。[6]因此,司马迁的天人思想首先表现出继承董仲舒《春秋》学的特点,也就是以经学为依据。
然而,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其天人思想除了受当时的思想环境,特别是董仲舒经学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的来源呢?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引其父司马谈之言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也。”[5]3295司马谈认为司马氏的先人在周朝时便担任太史一职,而太史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天官之事。因此在司马迁看来,自己对包括灾异在内的天人关系的探讨正是对中国古代史官传统职责的一种继承。
那么,司马迁心中的史官传统对天人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史记》的《天官书》谈起。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开篇便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一整套天官理论。对天官理论的掌握,本是史官的传统职责所在,而司马迁对这套天官理论的重视本身,实际上已经表明他首先是承认天人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因此,司马迁在阐述完自己的天官理论后,接着说了一段总结性的话: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5]1342
显然,司马迁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感应与联系。因此,在经学外,司马迁又从历史和史官传统的角度,肯定灾异思想存在的合理性。
概言之,与董仲舒单纯以《春秋》经义肯定灾异思想的合理性不同,司马迁是从经义和史官传统两个角度肯定其合理性的。这种学说依据上的不同,是二人灾异思想互异的深层思想根源。
二、董仲舒灾异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灾异思想是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从《汉书·五行志》大量引用董仲舒、刘向、京房等汉儒称说灾异的事例得到明证。可以说,灾异思想是董仲舒天人思想中一个最主要的内容,故史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3]1317。因此,灾异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董仲舒的灾异思想体现了对汉初儒者灾异思想的一种继承。①关于汉初陆贾、贾谊等学者的灾异思想,参见赵琪《陆贾、贾谊到董仲舒的灾异思想演进略论》,《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02~106页。其要点有二:其一,人世祸福的关键在国君自身的行为,而衡量国君行为是否得当的最终标准则是民心;其二,灾异既然因国君的行为而起,故在现实的政治中,国君应当将灾异视为上天的一种示警,进而改弦更张。其次,董仲舒在汉初儒者灾异思想的基础上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呢?董仲舒先是试图从《春秋》中为灾异思想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春秋繁露》的《十指》篇可视为概括董仲舒经学思想的简明大纲,在该篇中董仲舒对其春秋公羊学的十大要指逐一罗列,而其中的“一指”正与灾异思想相关,即其所谓“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4]145,由此使《春秋》成了灾异说的理论依据。在确立了经学的理论基础后,董仲舒又将当时十分流行的阴阳概念纳入自己的灾异思想,为灾异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展开提供了途径。在《春秋繁露》的《同类相动》篇中,董仲舒详细阐述了这一套阴阳灾异思想: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故聪明圣神,内视反听。[4]360
董仲舒的上述灾异思想,对西汉的政治与思想均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曾对此论述道:
他(董仲舒)的思路与范式的影响却是深刻地、逐渐地显现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在一代又一代的解释与演绎中渐渐被接受,《汉书》一再指明他“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表明他的这种思想史意义。[7]
这是从西汉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董仲舒灾异思想或者说天人思想的地位和影响的一种总结。但是,从《汉书·五行志》的相关记载中不难看到,这套以阴阳为解释范畴的灾异思想本身在理论上是不严密的,具有相当的主观性。试举二例以为说明。
严(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齐桓好色,听女口,以妾为妻,適庶数更,故致大灾。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争,九月不得葬。《公羊传》曰,大灾,疫也。董仲舒以为鲁夫人淫于齐,齐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国君,民之父母;夫妇,生化之本。本伤则末夭,故天灾所予也。[3]1322
鲁庄公二十年(前674),即齐桓公十二年,夏,齐国发生了灾害。②这里的“灾”,《左传》《说文解字》都认为是火灾,而《公羊传》则认为是疾疫。《左传》的观点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5页。对于这一灾异现象,同为经学家的刘向和董仲舒的解释是不同的。刘向认为,灾异的指向是齐桓公的好色问题,齐桓公的嫡庶不分最终导致了其死后齐国的内乱。董仲舒则认为是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文姜兄妹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齐桓公姊妹的婚姻问题导致了灾异的发生。可见,刘向和董仲舒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即都将灾异指向齐国国君的婚姻、男女等伦理问题,在具体的指向上又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又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故火生灾也。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太子痤,应火不炎上之罚也。[3]1326
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宋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忧伤国家之患祸,积阴生阳所致。刘向则认为是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宋平公杀太子痤应“火不炎上”所致。显然,在这一案例中,不仅灾异所对应的历史事件不同,而且导致灾异的阴阳缘由,即“积阴生阳”和“火不炎上”亦不同。
类似上述所举董仲舒、刘向等西汉思想家们对灾异的不同解释,在《五行志》中还有很多。概言之,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继承汉初儒者在灾异思想上的基本观点,即以民心释灾异,以灾异为示警;其二,以《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将灾异思想的合理性建立在经学的基础上,从而为灾异思想获得一种理论上的支持;其三,以阴阳为范畴,以阴阳消长为分析手段,将灾异与历史事件相比附。由上文所引二例可见,就同一灾异现象,董仲舒与刘向之间无论是在导致灾异的阴阳变化上,还是在灾异所比附的历史事件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由此可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家的灾异思想,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这一理论上的软肋,西汉时通达的儒者亦已知之。据《汉书·张禹传》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多有吏民上书,以多次发生日食、地震来抨击王氏的专政。汉成帝遂问询其师张禹,张禹的回答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3]3351①据班固所言,张禹是因为惧怕王氏的权势而说了上述这段话。但是抛开张禹这段话背后的政治考虑,仅从论述的逻辑角度看,可以说是对汉儒灾异说的切中肯綮的批评。张禹的言论,可谓道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的灾异思想最大的症结所在。
三、司马迁灾异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司马迁从经学和史学两个角度肯定了天人感应存在的合理性。那么,他对所谓的灾异有怎样的理解?与董仲舒的区别与联系又何在?
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对春秋之前的天人学说是这么评价的:“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礻几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5]1342司马迁的这段话实际上有三层含义:第一,幽、厉之前的历史,因过于久远而缺乏完整的记载,即在历史的层面是不完备而有缺失的;第二,当时尚无完备的天官理论;第三,正因为前两个原因,孔子对当时的天象采取“纪异而说不书”的做法。这一做法与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所说孔子整理历史时“疑则传疑”[5]487的做法,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一种“无征不信”的史学精神。至于孔子的这种“无征不信”的史学精神到底对司马迁理解灾异现象有怎样的影响,下文将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关系时,司马迁在基本肯定《春秋》中的天象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整体形势相关联的同时,又对当时胡乱言说天人关系的现象批评道:“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5]1344由此可见,司马迁一方面对与客观历史进程相符合的天人关系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凌杂米盐”从而脱离客观历史进程的天人关系持否定的态度。概言之,是否与客观历史进程相联系,便成为司马迁判断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天人关系是否成立的根本标准。
与上述先秦时期的天人学说相比,司马迁在《天官书》中对秦至西汉时期天人学说的具体情况有更为详细的叙述。例如,司马迁认为,与秦统一六国至秦亡这一时期的战乱频仍相应的是“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的天象;与汉朝的兴起相应的是“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而平城之围则有“月晕参、毕七重”[5]1348-1349的天象出现。类似的例子《天官书》中罗列了很多,在此不一一赘举。在列举这些天人关系的具体表现后,司马迁总结道:“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5]1349可见,司马迁对秦汉时期与客观历史进程相关联的天人关系亦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天象可以预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从上述对各个历史时期天人学说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司马迁认为是否与客观历史进程相联系,或者说是否具备客观历史事实上的依据(从今日科学的角度出发,所谓的依据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是天人关系或者说灾异思想能否成立的根本条件。对此,司马迁在为《天官书》所作的《小序》中已经有所阐述,其言为“星气之书,多杂礻几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5]3306。因此,《天官书》所列举的灾异现象,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经过他推文考应、验于轨度,或者说经由客观历史事实的验证后才加以记录的。在他看来,孔子之所以对春秋之前的天象采取“纪异而说不书”的做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于那段历史缺乏比较完整的记载。这一做法所反映出的“无征不信”的史学精神,在司马迁对灾异现象的理解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即集中表现为用历史事实来检验灾异思想是否能够成立。
既然在司马迁看来,天象可以预示人事,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那么对于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们而言,便可以通过观察天象来反省自己的施政。这样一来,灾异思想便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亦有论述,其言为“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5]1351。司马迁认为,化解天象警示的方法是“修德”“修政”等切实的施政措施,至于祭祀求神则已是等而下之之策。由此更可见,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其重心始终在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人之上。
如果将上述司马迁对天象或灾异的基本态度与董仲舒的两相比较,则可以看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深层性的差异。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首先,司马迁和董仲舒都承认天人之间存在相互的关联,并且都将《春秋》经作为天人感应成立的依据;其次,司马迁和董仲舒都认为天象或灾异可以成为政治上的一种警示,将灾异的最终落脚点放在国君的德行上,即汉人所谓的灾异示警、灾变修德的思想。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特别强调,灾异思想是否能够成立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所谓“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和“幽厉以往,尚矣……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反之,我们从上文所引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对灾异的论述可以看到,董仲舒最为强调的是灾异在经学上的依据,强调灾异思想的理论性和权威性,其对灾异的解释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依据。例如,在上述所引的两个案例中,董仲舒都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政治准则来解释灾异的。
概言之,在司马迁和董仲舒的灾异思想中,灾异本身处在价值观念与历史事实的张力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历史事实,试图用历史事实检验灾异。虽然这种检验从今日科学的角度看实属迷信与附会,但对汉人随意言说灾异的现象无疑会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体现出一种历史理性的光辉。[8]董仲舒则更强调价值观念(所谓的经义的作用),试图用灾异起到“屈君以伸天”(限制君权)的效果,只是在这么做时将价值观念置于历史事实之上。如果说司马迁的灾异思想体现了历史理性的光辉的话,那么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则体现了政治理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