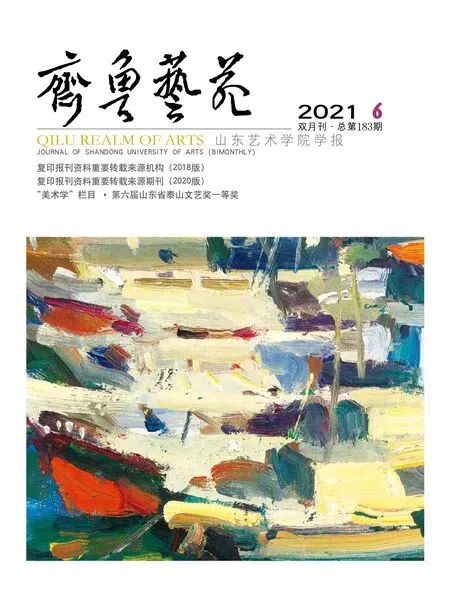赵玉琢老师作品读记
张丽华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赵玉琢老师存画不多,原因有三:一是经年潜心于教学研究和管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学生身上了,自然占去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并未存“敝帚自珍”之念,许多年动荡多有遗失;三是对自己要求过于苛刻,稍不入眼便随手丢掉或撕毁,所剩者当然无几。即便是所剩无多的画作,我得以系统地观览品读时也已经很晚了。今天重读这些画作,除了感慨岁月流逝的无情,赞叹老师艺术精神的纯粹与技巧的精湛,又平生出几分惊奇,品咂出些许感悟的五味杂陈。
许多画作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去大渔岛等地写生时的作品,在当初为学生时,只是高山仰止般的敬仰与崇拜,其实是看不出所以然来的。时光过去40多年了,经历了与老师相似的教学、研究、创作的过程,又到了和当初赵老师一般的年纪,再重读老师的作品,方看出许多当年不曾知道的端倪,参得其中的“三昧”。
我的绘画之路是从师从赵玉琢老师的素描开始的,当然会对赵老师的素描多投注几束目光。老师的素描是标准的学院派“苏式”素描,观念和方法出自于浙江美院留苏的全山石先生,保留着从契斯恰柯夫体系移植中国后最原汁原味的风格,画面所显示步骤的稳扎稳打、环环相扣,刻画观念和心态的严谨、扎实、鞭辟入里,画面节奏的抑扬顿挫,是后来逐渐走样变形素描教学“变体”样式所无法比拟的。与后来对苏派体系的怀疑直至蔑视相比,赵老师当时表现出无比的笃诚与坚定,这与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全面风潮有关,也与这一教学体系首先对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的渗透有关。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艺术院校在中国起步,到五六十年代稳固发展,苏式教学体系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科学性、严整性、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育体系可以说恩泽了中国艺术几十年。“文革”期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防修并未影响文化艺术界对苏联艺术观念和教育理念的借鉴汲取,中国现当代造型艺术中许多历史画、风俗画、主题性创作沿用的基本是巡回展览画派的路子,就连文学、交响乐、组歌、芭蕾舞也明显看出苏联艺术的影子。苏式素描能在中国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广泛的辐射力和深刻的穿透力,是其它教育体系与样式所难以比肩的。刻画之初的情感交流、情绪酝酿、激情积蓄以及表现欲望的培养,刻画过程中程序的控制、逻辑性思辨、科学规律的应用和艺术性处理,刻画完毕时又回归到精神性表现与文化意识的阐释,这是一套完整严密的教学体系,在掌握之后的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对物象的感受和艺术规律的把握以及个人素质,给以个性化应用,使其充分符合心性的倾吐与塑造。
赵玉琢的素描充分体现出这一体系的特点和魅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求真求实、实事求是的写生观念,它不以大幅度变形和过分怪异化处理为宗旨,而是使其达到“像眼睛看上去般真实与自然”,当然,这里的真实与自然是相对的,哪有绝对的所谓写真、写实!这毋宁说是一种态度与境界。其次,画面重整体修养、才智的倾注,调动全身心之积极因素,主动热情地对待一切,散发出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平时教学中按部就班式的步骤,条分缕析的心态和明净安闲的面貌没有了,代之以创造性和表现意味极强的抒写与宣泄,完全可以感觉出刻画时的速度与激情。再者,让人感受到的仍有无可挑剔的法度,情绪宣泄、情感倾吐中不忽略艺术性与技巧,这应该是赵老师烂熟于心的学问了,笔触间不经意带出的永远是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的精神性、情绪化和技术性的综合,是自由与规格的圆满统一。
赵玉琢老师喜欢用对比来强化素描的表现力。色调的黑白对比当然最明显不过,在黑白两极色中有柔美和煦的灰调子游弋其中,很好地丰富和调节了黑白灰关系;色调的节奏对比是隐性的,恰好与物体受光后呈现的节奏韵律相吻合,在这一和谐的关系中,赵玉琢强调出色调比值的跳跃性变化。黑白节奏实际是接受心理的调节,在经营黑白关系的时候,实际是在做着审美感应的调整。
刻画的详略对比表现出扎实有素的艺术处理能力和控制力,明暗交界线两端被详尽地刻画,色调不惜画到工具的极限,这样有利于深入,而向暗部、亮部的过渡,却逐渐走向概括。在大面积色调的铺陈中,赵玉琢使用了极端情绪化的用笔,近乎带出风声的笔触,是画面上不可或缺的元素,既为造型,又为造势。形象因之有了速度快慢、压力轻重和精致粗率的对比,画面有了表现神采、气质的气势与情绪,笔触所参与的实则是人物形貌的塑造,还有作者评价与表现激情的展示。
在形神关系处理上,赵玉琢老师总是把刻画的重点放在面部和手,放在神情、表情的刻画上,从赵老师捕捉并固定下来的形象看,模特是带有当时泥土气息的质朴的形象,正像赵玉琢素描风格所显露的质地一样,是生活中随处一瞥就见到的浑朴纯真的表情。这种质朴的品性不独指写生对象的身份,也不是依照形象施展的笔法,而是画面所呈现的格调。因为画了人,素描肖像直观地显露出作者写生的用意,老师是把模特当做“自然人”来对待、塑造的,是要画出情感的活生生的人。面部形貌之外,赵老师决不放过手的“表情”的刻画,无论是老民兵坚韧的手形、老农木讷的手形还是持月琴少女的手姿,都因其刻画的详略得当而各显性格、表情,直接参与了形象的塑造。与面部形象和手形成对应关系的衣服、道具和环境,则作相应的虚化处理,画面刻画的简繁详略用意是明晰的,处理手法是自然从容的。
由色调的准确性、精致化与刻画笔触的情绪化带出的质感对比,是赵玉琢素描的另一特色。质感是观察体验的用心与否决定的,是情感的粗糙还是细腻来体现的,是凭借表现能力的高低来实现的。依靠娴熟的素描技巧,赵玉琢完成了对质感的描述,画面因之显现出精到、精致、精彩的表现性和艺术魅力。质感实际是素描能力的试金石,它不是刻意为之的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的微雕式“死抠细摹”,而是能力、才情达到后无意识的显露,是素描实质内容一个侧面的体现。
对于结构的理解与呈现,赵玉琢老师除了顾及人物的生理结构外,更注意画面的形式结构,比如点、线、面,黑、白、灰元素的应用,明线暗线在构图布局中的调节,黑白灰节奏的调配,详略笔触的分布应用等,画面不是简单物象的再现,是两种结构和观看心理的苦心孤诣经营和在经营后流露出的符合本真天性的再呈现。
赵玉琢的素描格调是符合素描本义的,天然,质朴,真诚,不矫饰,不粉饰,不浮华,不卖弄,如果用中国画中对“格”的标准来框定赵老师的素描,当属于“逸”或“自然”的一格,因为从画面上一眼便可以看到画面后面的作者,看到纯净透明的艺术用心,看到为人从艺的诚恳态度。“逸”是作者身世、教育环境、修养修持决定的,而“自然”又是最难达到的一格,看似随手拈来的无意为之,实则是达到一定境界后的自然流露,任何刻意为之的执着追求都会影响自然品性的表达。一旦有了某种投机的机巧,艺术的用心即会大打折扣,想丢掉已经涂上的“面膜”,结果成了箍上的“面具”,谈何容易!赵老师这种格调的修持和保持,正是自然性情在绘画技艺中的真诚投入和不带任何功利意识的回馈。
赵玉琢老师把对素描的理解与领悟更多地教给了学生,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们,不管操手国画油画,不管担任院长主任,都承续着赵老师的素描原理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生活、教学、研究、创作。如果一个人一生非要做几件大事不可,对于赵玉琢老师,这便是他值得欣慰的一件。许多人往往只记得教过最后一笔技巧的专业指导老师,却很可能忘掉最初引领到艺术门槛的基础课教授者,殊不知这是他获得艺术能力的最初哺育,是踏入社会和艺术之路的第一口“母乳”。能把自己对艺术的感悟以基础课样式传授给学生,使他们有正确的绘画观、造型观,直至影响到艺术观、世界观,由此形成艺术基础教学模式,经数年完善形成一方领地巨大的文化“气场”,应该是赵玉琢他们那一代老师最宏大最可称道的“行为艺术”。赵玉琢与他同代老师的素描及其他奠基意义的基础课,代表了某一时段中山东艺术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这种宏观意识的素描及其基础课,才有了山东艺术学院富有特色的美术教育,才有了山东美术创作主体的创作面貌。坚忍不拔的意志,锲而不舍的毅力,精益求精的精神,尽善尽美的画风面貌,已化为山艺基础教育的文脉,成为与“闳约深美”并行不悖的学术精神。
赵玉琢老师的油画可分两部分:人像与风景。
几幅渔民的油画写生以绛色调为主,赵老师在以纯度极高的棕红色塑造形象,有的甚至有意不找冷颜色,一任饱和的暖色调呈现动人的光彩。有几位渔民我们同学是熟悉的,我们当时是和赵老师一起写生的,脑中的印象还鲜活着。赵老师似乎是通过一张张面孔在诠释着什么,比如人的存在状态,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人的精神风貌的注释,艺术家对人的相貌及心灵的解读,至少是在捕捉海上热辣辣的风和灼人的太阳,还有海边的鱼腥味,一副副绛红色脸膛固定下来的是海的广阔,辽远,深邃,显现的是山东人特有的热情、豪放、赤诚。
赵老师表现力极强的笔触在塑造表现女性时,则变得柔和起来,《半身女肖像》《小模特》《女人体》中的用笔趋于含蓄内敛,笔触的衔接有了丰富的过渡,这一则是因为课堂写生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二则是由对象的形貌神情和赵老师赋予的审美特征决定的。在这里,赵老师亦然保持着笔触的自然品格,在柔美温和的塑造中传达出娴静优雅的审美品性。
最打动我的是那幅肖像《女孩像》,这是一幅率意十足的“速写”,但由于充满了绘画表现激情而流露出洋溢的感情与才情。因为是短期作业,形象显得近乎粗率,但人物的形神却不懈怠,女孩表情平静,一双无邪的大眼睛闪着好奇的光,眉宇间有安逸闲适的心境,女孩的嘴唇有红润的光泽,与周边环境色融为一体,毫不突兀,这一切都是在赵老师写意般笔触书写中完成的。红头巾随意罩在小侄女头上,经赵老师几笔“拧”出,便成了孩子性格神情中一块明丽晴朗的色彩,由红色笼罩的暖色调是孩子花样年龄心境的折射,也是赵老师充满爱意怜惜之情的真实写照。
风景画中,让人感受到赵老师那一代艺术家腿脚的勤快和对艺术的执着勤奋,能画到这般娴熟通透的程度,当是有相当的写生积累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付出,与当下某些只会用照片作画的画家不可同日而语。在油画风景写生中,赵老师的笔触变得异常敏锐,风景画表现出强烈的概括性,为了整体,不惜把某些物象作平涂处理,不管是天,是地,是海,是水,只要整体需要,则以牺牲局部服从整个画面的大色调、大感觉为准则,所以画面有着干净利落、单纯洗练的风韵。赵老师依然使用着对比来加强画面的效果,除去素描结构和构成的点线面对比,又加进了色彩对比,赵老师喜欢用大片色彩概括物象,使之呈现整体的效果,大笔触概括出的色彩,得以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的光色变化和物象。在《清流漱石(崂山北九水)》中,前景的山坡、小溪、树林,远景的几重山峦,都在大笔触概括的大块色彩中,各居其位,各显个性,深重的投影和中景的暖色房子成为画面通风的“气口”, 笔触轻松随意,为画面深度中加进了人的痕迹与温情。我惊异于老师笔触的简练、准确,笔无妄下,胸中有数,有些笔触似乎不必过分调配就可获得意外的效果,然而大块的笔触并不忽略物象细节和色彩的丰富性,在关键处仍有可供品味的细节特征,如礁石的质感、舰船的结构、水天的色彩等。物象所有细节、质感完全是不经意间带出,而非谨细的描摹,这当然是气度和能力、素质使然。水是风景画中最敏感的形象,因其无形无色而成为最不稳定的元素,赵老师喜欢画水,画海,在水的画面上赵老师强调的是阴柔的个性,使水与山坡、小径、树林、山崖等各自显示不同性格。赵老师的海是大片色彩的概括处理,与山坡、礁石、沙滩、悬崖、天空等形成大的对比,有面积的对比,有明度纯度冷暖的对比,有笔触肌理的对比,有刻画精致与粗率的对比,在整体色调中,反射着微妙的色泽。因为有了水的描绘,画面平添了几分润泽与灵动。
看赵老师的风景画,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恣意放纵的笔触与笔触间反映出的写意意识,近乎于大写意般的用笔,使画面呈现一股潇洒的才情与英武气息。表现树冠时,几乎能看出饱和色彩点厾的痛快淋漓,使得树叶有了随风翻转的婆娑声音与姿态;画树干时,能看出草书般的笔锋转折帅意,树干有了挺拔的气势,有了情绪的恣意和生长的躁动;画山石时,是接近中国画“大斧劈皴”的用笔,有了笔触的切、削、砍、斫姿态,非有对形和色的准确把握和无挂碍的书写不能达到此境界。
如果从精神性角度观赏,在诸多风景写生中,我很喜欢《金色的麦田》这幅水彩画。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956年就已经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三等奖的缘故,说起来,我更喜欢这片能唤起我温馨记忆的金黄色,任何有过麦收体验的人都不会对此灿烂诱人的色彩无动于衷,金黄色带出的田野的清风和麦田的香气使我在赵老师画中驻足流连,后来在梵高的画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它,在米勒的画中见到时,已是迟后的情景了——三个老妇人像中国农民一样,在迄迄地拾捡着最后的麦穗,那情景,像极了晚钟声中停手祷告时的静穆与虔诚。赵老师的画是动人的,他采取的是一般的平视角度,这也是我当年手握镰刀观看麦田时正常的视角,满满一坡带着香气的金黄色就这样坦荡地展现在我眼前,也展现在赵老师眼前。赵老师的麦田有一种厚重的感觉,使很难用的黄色不浮,不泛,不粉,密实而丰厚,空灵而透明,几排单独挑出的麦穗俏皮地摇曳在前景,似交响乐中几声钢琴敲出的亮音,清脆而活跃。大片天空的渲染也是这幅画成功的关键,水彩画中,只能以蓝色衬出白云,但要衬得自然、滋润,又要使云朵有丰富的变化,赵老师用富有表现力的笔触描绘了这种变化,使得云朵天空微妙对比中显现“祥云”的意味。天地之间的点缀虽小,但却是必要的“点景”,起到了“点睛”的作用,黛色的孤山,密实的麦垛,渐渐远去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村庄里,或许正走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喻示着一个甜蜜、富足季节的到来。对于象征意义的“金黄色”,画家梵高和赵玉琢捷足先登了,他们是美的捕捉呈现者,不几天,从那片莫测的地平线上就会走来收割者(其中也包括当年的我),和米勒笔下的拾穗者,我们都是真正拥有这片金黄色的美的主人,有的求它的真,有的求它的善,有的求它的美。赵老师的这幅水彩凭借的工具材料是单纯的,手法是简练的,反射的命题却是宏大的,谁都知道小麦与人的关系,把它命名为“金色”,也不啻表现出对收获的希冀与期待,对劳动的珍视与尊重,对自然、对生存生命意义的祝祷与讴歌。
赵老师的写意意识贯穿在素描、色彩的整体追求中,似乎构成了赵玉琢艺术的美学品性,当与他广泛涉猎中国艺术和书法有关,这并非是对中国大写意绘画和草书表面形式的模仿,而是一种美学思想的汲取渗透,写意不是一个潦草的外在形貌,是一种东方艺术整体的美学范畴。赵老师对这种品性了然于心,在进行哪怕是素描色彩等西画创作时,也会自然地流露出这种追求。在《猎手》一画中,一种粗犷豪放的情绪洋溢其中,一老一少,风尘仆仆地向画外走近,上身沐浴在一片落日的余晖中,让人仿佛能听到打猎归来时那喜悦爽朗的笑声,画面以整体的暖色调和率性笔触感染人,大片重色衣服仿佛能看出“泼墨”渲染的用笔,写意笔触中传递着潇洒、富足、安逸和其乐融融的动人情绪。
说至书法,赵老师走的是优雅平和的一路,优美但不文弱,于恬静雅致中散发着凛然的骨气与风神。照理说,素描的“硬笔”、油画的“刷子”与中国毛笔分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一个是绘画,一个是文字;一个走形与色,一个走线;一个为具象,一个为抽象。虽然书法中有结体与笔画,有用笔与笔法,但决不等于绘画中的结构与笔触。我不知道这似乎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是如何在赵老师脑中手中统一起来的,只要看一看他运作几种不同工具,把脑中分属于不同文化属性走向的艺术恰好地统一起来时,就深感赵老师一代老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濡染的全面与深厚,不可小视。这也就是他能同时在素描和油画艺术中加进写意意识,在书法中追求整体气象的传达的原因。只要是艺术,是文化,它们总是在最高端的层面上找到相通的契合点。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把它们统一起来,最高端的那个有机而和谐的交融,也在等待着中外文化融会贯通的有缘人。
赵玉琢的书法追求整篇的线条氛围,线条行走的压力、速度,依照字义、字形所做的转折、顿挫,并不拘泥于某个字形某一笔画的婉转,而在通篇的位置经营和布阵置势,这也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的最好注脚。从格调上讲,赵老师的书法偏赵孟頫一路,这其实是最难把握的,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外露的特征,没有剑拔弩张的锋芒毕露,在绵里裹针似的面貌中,暗含着清癯、儒雅、不入俗流的骨骼,赵老师在不急不躁中推敲着字句行文之间的主题立意,经营着谋篇布局,酝酿着格调的气象神韵,散发着书法的文化气息,使毫无悬念的书法面貌透露出让人亲近但不媚俗的书卷气。
整体地看,赵玉琢的艺术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自然的格调,朴素的天性,学院派可品读可批评的经典型、学术性,长期坚持研究性而达到的画面的难度技巧,由娴熟技巧达到的精神性与文化意义。这就够了,一个人在30年教学之余能把自己的画作放在这样一个档位上,足以欣慰。画不在多,不在大(当然多和大更好),达到一定品位,给自己一份安慰,给人树立一个标尺,足矣。相对于动辄重复地拿出几十米大作的江湖气息,我更珍视赵老师的学院派和研究型画作,这是一种久违了的艺术格调,也是一种更接近艺术原本的难以坚守的艺术童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