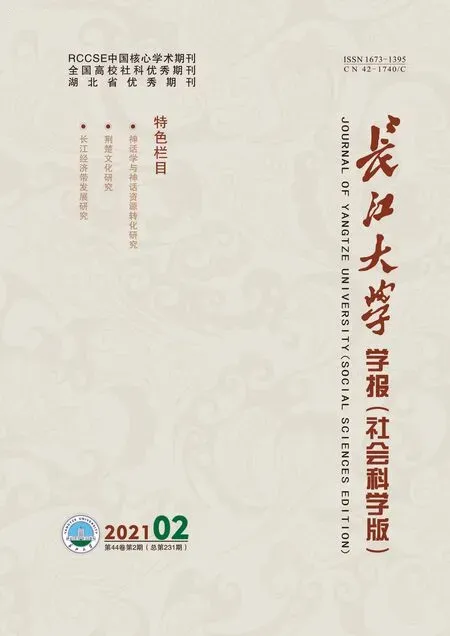民国正声诗词社述论
孙文周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民国时期,词人众多,结社活动频繁。据曹辛华教授《民国词史考论》,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诗词社团有499个。[1](P311)其中,抗战时期成立的正声诗词社,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诗词社团之一。目前,学界仅有彭敏哲《梅社女性诗群的形成与承续》一文[2]言及该社团,且为社团成立的概况描述,显得较为粗略。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正声诗词社的活动情况,论述其词学主张,揭示其创作主题并探讨其文学史意义,以期有利于民国社团研究的深入。
一、正声诗词社活动述略
1943年秋至1947年10月,由避难四川的沈祖棻与程千帆组织当时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就读的14名学生成立了正声诗词社。导师除程、沈二位外,还有高石斋、陈孝章、刘君惠等。“正声”二字,取李白“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诗意。该社活动以1944年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1943年秋至1944年秋,为社团活动之前期。社员虽为本社师生,但社作却兼有师、生及太老师辈的诗词论文与创作,既探讨学术又以诗词反映时事。据刘彦邦《抗日战争中的正声诗词社》[3](P6),社员最初五人,分别为金大中文系邹枫枰、卢兆显,国文专修科杨国权、池锡胤,农艺系崔致学,主要由卢兆显主持社务。1944年1月、2月,编印发行了《正声》第一卷第一二两期。第一期内容为:杨国权《论近人研治诗词之弊》(论著),卢兆显《南唐二主词汇笺》(书评),林思进《清寂堂诗钞》,汪辟疆《方湖诗钞》,邹枫枰《枫枰诗钞》,卢兆显《洁斋诗钞》,汪东《寄庵词》,沈尹默《念远词》,沈祖棻《涉江词》,杨国权《苾馨词》,崔致学《寻梦词》,池锡胤《镂香词》,汪东、易大户《词联选钞》。第二期内容为:夏承焘《答卢兆显君论李后主词书》,卢兆显《致夏瞿禅先生论李后主词书》(通讯),高文《草堂诗钞》,刘道和《珮蘅诗钞》,程会昌《玄览斋诗钞》,《高阳台》七首(沈祖棻、庞俊、萧参、陈志宪、萧熙群、高文、刘道和),卢兆显《海月楼词》,杨国权《苾馨词》,易顺鼎、沈祖棻《诗词联选钞》。因物价飞涨,第一期售书款不敷第二期印制费,仅出两期便停刊。1944年春,由于邹枫枰、杨国权、池锡胤三人即将卒业离校,程千帆、沈祖棻二师便推荐宋元谊(四川大学中文系)、萧定梁(金陵大学)、陈荣纬(金陵大学)、刘彦邦(金陵大学)等人先后加入诗词社。1944年夏,卢兆显、杨国权、池锡胤、崔致学四人编印《风雨同声集》,内容有:沈祖棻《序》、杨国权《苾馨词》(30首)、池锡胤《镂香词》(26首)、崔致学《寻梦词》(31首)、卢兆显《风雨楼词》(36首)。
1944年秋至1947年10月,为社团活动之后期。此期因老社员毕业后离开金大,新社员陆续加盟,故人员处于流动之中,但社团力量却较前有所壮大。同时,社团依托《西南新闻》《〈正声〉诗词刊》刊发师生及太老师辈的诗词文,继续学术探讨和诗词创作。据刘彦邦《抗日战争中的正声诗词社》[3](P9),1944年秋,华西大学的王文才和刘国武、四川大学的王淡芳和周世英、武汉大学的高眉生等5人先后入社。此后约两年间,每两月选一节假日,在少城公园茶馆或新南门外枕江茶馆聚会,多半由沈祖棻命题,因程千帆已于1944年中秋后应武汉大学之聘去了乐山。1944年秋至1946年春,《西南新闻》报辟《正声》诗词专栏,半月刊登一次。“每期至少有1篇不长的诗词论文,另外便是老师辈和社员们的创作,间也刊载非社员投寄的稿件。所刊诗词,一般都能联系实际,或感时伤事,或讥弹时政,或记述萍踪,或互相赠答,言词各抒情意,文风均以‘清明雅正’是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诗词界老一辈以至两辈的作家,除前述林(思进)、汪(东)、庞(俊)、萧(中仑)诸先生外,还有程穆庵、陈寅恪、沈尹默、刘永济、谢无量、向仙乔、沈渻葊、向仲坚、曾圣言、陈仲子、吴雨僧、缪彦威、殷孟伦、叶石荪、郪隐、罗髫渔、潘重规、李思纯、吴征铸、康彦葑等等先生的作品先后在《正声》上刊布。”[3](P10)1946年秋,《西南新闻》编发了正声新一期专栏。1946年冬,因编辑李定一离职,便不再发排正声社之诗词。[3](P180)1947年秋,社员凑钱编印《〈正声〉诗词刊》新一期,内容有:周世英《有宋词风探原及诸家之一种估价》(文录)、陈廷杰《晞阳诗稿》、殷孟伦《结桂簃近稿》、罗髫渔《和山诗稿》、沈渻葊《守约堂诗》、萧定梁《如水诗钞》、刘彦邦《步玄居诗》、林山腴《清寂词》、刘永济《诵帚堪词》、庞俊《石帚词》、叶麐《轻梦词》、沈祖棻《涉江词》、杨国权《苾馨词》、宋元谊《采菽词》、卢兆显《风雨楼词》、周世英《微云楼词》、刘彦邦《撷蕖词》、萧定梁《如水词钞》、宋元谊《四史载文比观》(附录)。1947年10月卢兆显病逝后,活动渐止。
二、正声诗词社词学主张与创作主题
正声诗词社社员多以词记录时代,表现出强烈的尊体观;同时,重比兴寄托,标举“雅正沉郁”之风。
一方面,推尊词体。正声社员,提倡以词表现时代。如杨国权,其在《论近人研治诗词之弊(代发刊词)》中要求强化词的现实功能,以词感怀国事,针砭时弊,赋予词更多厚重的情感。杨氏云:“南宋末季,谢皐羽、林景熙、郑所南辈,运当易代,痛切家国,故其发为诗歌,几为血泪所凝。词则白石、玉田、草窗、碧山,其咏一草一木,每抒身世家国之感,悲愤激烈之怀。……即以今日而论,东夷肆虐,神州陆沉,巨邑名都,多沦敌手,六年以来,攘夷之战,可歌可泣之事,固不乏书,而我号为诗人词人者,佥能以之入于歌咏,报章披露,时有所闻,观此则旧诗词之能表现时代,不言而明。”[3](P52~53)在杨氏看来,词不仅可抒一己之情怀,更可寄民族之精神。沈祖棻更是进一步表达对词体的重视。她说:“受业向爱文学,甚于生命。曩在界石避警,每挟词稿与俱。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处遭劫,而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此意难与俗人言,而吾师当能知之,故殊不欲留躯壳以损精神。”[4](P211~212)凡此,都体现了正声诗词社对词体的尊崇。
另一方面,倡导雅正沉郁。沈祖棻《风雨同声集·序》言:“壬午(1942)、甲申(1944)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沉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潘,所弗敢涉也。及门既信受余说,则时出所作,用相切劘,颇有可观省者。而綦江池、杨二生,宁河崔生、三水卢生,里閈虽异,交谊顾笃。以先后卒业之将别去也,爰共撰录平居所为,付诸劂氏,藉当相思之券,题曰《风雨同声集》,盖诗人相鸟鸣鸡之义云尔。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沉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跻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几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傥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绘相嘲让邪?”[3](P90)沈氏标举“雅正沉郁”之风,重视词之比兴寄托,强调词作对现实的关注与影响。正声社作,寄寓诗词创作之雅正观,与其社名取义“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相一致。前引刘彦邦“文风均以清明雅正是尚”,亦是此意。
正声社作,大都能联系实际,或感时伤事,反映时局之动荡,或抒发对故园和亲友的思念,现实感很强。因社作以词为主,故下文以词为切入点论述。
一方面,反映时局动乱。此类词作,兼及抗战、内战。反映抗战者,如沈祖棻、庞俊、萧参、陈志宪、萧印唐、高石斋、刘君惠等壬午(1942)岁暮于枕江楼酒集时所唱和之《高阳台》七首。当日席间,酒入愁肠,感时伤事,高石斋狂谈,刘君惠痛哭。次日,沈祖棻首先写出《高阳台》,余者皆和。沈词上阕云:“酿泪成欢,埋愁入梦,尊前歌哭都难。恩怨寻常,赋情空费吟笺。断蓬长逐惊烽转,算而今、易遣华年。但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3](P79)沈氏将对抗战失利、国土沦陷、人民流离的满腔悲愤一寄词中,慷慨悲歌。反映内战者,如沈祖棻《浣溪沙》组词六首和《鹧鸪天》。《浣溪沙》其一云:“何处秋坟哭鬼雄,尽收关洛付新烽。凯歌凄咽鼓鼙中。 谁料枉经千劫后,翻怜及见九州同。夕阳还似靖康红。”[3](P150)此词作于内战时期。其时,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内战又起。一如黄裳所说:“随着时局急遽的发展变化,词人笔下日益减去了纤细轻柔的韵致。终于出现了‘眦裂空余泪数行,填膺孤愤欲成狂’这样的声音”[5](P333)。
另一方面,抒发羁旅愁苦。卢兆显于1936年由上海入蜀,滞留成都7年,曾赋《临江仙》八首表达其羁旅相思之苦。卢氏在组词《临江仙》中将羁旅愁苦融化于粗线条的景物勾勒中,令人动容。如其一:“谁意江南年少客,生涯却付萍踪。飙轮惊浪过巫峰。簪云峦髻白,沐雨石鳞红。 霏雾千山催日暮,休悲前路蚕丛。只愁归棹更难通。江雨吹鬓乱,回首暮云封。”[3](P120)从中,我们不难感受作者的漂泊之苦,思归之痛。
三、正声诗词社的意义
抗战时期成立的正声诗词社,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彰显了沈祖棻对诗词结社活动的坚守,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的偏颇,而且师生砥砺,有利于社员学殖的增长,还延续了师道传承的优良学风。
其一,彰显了沈祖棻对诗词结社活动的坚守。沈氏一生,参与或发起组织的诗词社团(群体)有潜社、梅社、雍园词人群体、藕波词社、正声诗词社等。潜社成立于1926年,吴梅主盟,社员有唐圭璋、段熙仲、王季思、任中敏、卢前等。作为晚辈的沈祖棻,通过参与潜社,向师辈学习,从而为其今后的作词及更广泛的结社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1932年,沈祖棻与其他四位女同学(尉素秋、王嘉懿、曾昭燏、龙芷芬)成立了梅社,互相切磋,砥砺词学。由于多吟咏花、月、蝉、燕,故词风偏于婉约。随着抗战的爆发,沈氏流寓四川,并分别于1938年和1942年成为雍园词人群体和藕波词社的重要一员(除沈氏外,前者另有社员叶麐、吴白匋、乔大壮、汪东、唐圭璋、沈尹默、陈匪石等;后者另有社员孙望、庞石帚、萧中仑、刘君惠、高石斋、陈孝章等)。受时代影响,沈氏词风也由前期之清丽婉转变为深沉悲慨。作为藕波词社的延续,成立于1943年的正声诗词社则明确标举“雅正沉郁”之风,并以此引导和示范学生辈的填词。可以说,正声诗词社是前期之词社(潜社、梅社、雍园词人群体、藕波词社)和抗战之时代共同孕育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沈祖棻对传统诗词结社活动的持守。
其二,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的偏颇。杨国权在《论近人研治诗词之弊(代发刊词)》中,要求扭转新文学对旧文学的矫枉过正之风。他说:“今者,士号趋新,群言排旧,以为文学之作,旧则当废。自五四运动迄于今兹,念余年来,旧学陵夷,江河日下,诗词之道,几于绝响。……旧诗词非不能表现时代,亦非不能描写新事物,至其能否表现,及能否描写,则系作者之技巧,而非体裁之优劣,说者又未可以彼而易此也。……文言、白话,原无严界,期于描写真切,表达真纯,即为尽其能事。若其内容空乏,技术拙劣,则虽废弃旧腔,纯用新体,亦不得谓为文学作品。且所谓某种新文体之产生,必经千百年之改进,然后始臻完美,此即吾国所谓‘盖棺论定’,亦即西洋‘Testof the generation’(受时间之淘汰)者也。今日之新诗,吾人固未敢否认其存在之价值,然创造之时间既短,其尚须继续改进,则无可讳言。然则新体之生长,既未成熟,而旧体之创作,更不可废弃甚明。吾人鉴于近日研治诗词之弊,颇思有以纠弹,爰创斯刊,用资研讨,为书喤引,聊当嘤求,方闻君子,幸其教之。”[3](P52~55)以杨氏为代表的正声诗词社反对“五四”以来所谓“旧诗词为已死之文学”的偏颇观点,认为“文言、白话,原无严界”。社员卢兆显亦云:“情知新谱盈天下,却向人间理旧弦。”(《鹧鸪天·华西坝春感》)他们都提倡用传统诗词来表现时代,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增进对古人诗词的理解,以传承中华文化。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正声》诗词酌古准今,融通古今,师生风雨同声,共同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声。
其三,有利于社员学殖的增长。正声社员间的诗词唱和,固然有利于社员在诗词创作时的切磋和写作水平的提高,不必多言。除此,正声社员还以论文形式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从而有利于词学学殖的增长。就目前可见,这方面的材料有卢兆显《南唐二主词汇笺》《致夏瞿禅先生论李后主词书》,夏承焘《答卢兆显君论李后主词书》,周世英《有宋词风探原及诸家之一种估价》等。卢氏《汇笺》一文,既称赞唐圭璋所笺注之南唐二主词“笺注详赅,缕析无遗,……足供我辈楷范”,又指出唐著尚需商榷之处若干。周氏《估价》一文,认为“词无疆圉之分,实存演化之迹”,梳理宋词“嬗变同异之迹”“流别异同之处”。卢氏致夏承焘书就夏氏《南唐二主年谱》进行商榷,凡五处。夏氏复信认同卢氏所言之第二、三、四条,同时又对卢氏于第一、五条的相关论断进行了纠正和说明。另,社员刘彦邦曾言1944年秋至1946年春《西南新闻》报所辟《正声》诗词专栏(半月刊)每期至少刊发1篇诗词论文(见前引文),想必定有关于诗词方面的精彩见解,只惜此类文献目前尚未见。这些论文,对提高社员的词学素养及创作、欣赏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其四,传承了优良的学风。正声诗词社的社员是14名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社员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与以沈祖棻为代表的老师辈的指点休戚相关,体现了师道传承之优良学风的延续。沈氏词学与人品,承续业师汪东和吴梅。其《八声甘州》(记当时、烽映绛帷红)词序云:“忆余鼓箧上庠,适值辽海之变,汪师寄庵每谆谆以民族大义相诰谕。卒业而还,天步尤艰,承乏讲席,亦莫敢不以此勉勗学者。”[6](P95)其所标示雅正沉郁之旨,亦“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风雨同声集·序》),并将此贯穿于其指导后学之中。沈氏滞留成都时,对学生面授词艺。1946年秋离开成都后,更以书信循循善诱。其1946年11月11日《致卢兆显、宋元谊、刘彦邦函》云:“元谊弟应多读北宋作品,勿徒注意雕琢,以免辞胜于情。兆显弟作,情意深刻而不免流于生硬晦涩,有辞不达意之病,又觉情胜于辞。彦邦弟入手甚正确,尤须力屏粗俗、熟滥、轻绮诸病。昔孔子有才难之叹,今日尤甚。弟等当自强不息,勿负余望也。”[3](P171)此函强调“情”与“辞”在创作中的辩证关系,告诫学生在写作时既不可“辞胜于情”又不能“辞不达意”,应以情辞相称为尚。1946年12月31日《致宋元谊、卢兆显、刘彦邦函》云:“弟等近作,颇见进益,阅之殊慰。《鹊踏枝》五阕,揣摹《阳春》,颇能得其情韵,可喜也。惟第一首之‘终古人间世’,‘终古’二字,及第五首之‘烟水月’未妥,应改。第三首之‘无觉处’,‘觉’或是‘觅’之误。第四首‘梦华如月’似作‘月华如梦’较稳妥,或作‘梦痕’尚可;‘多’拟易‘都’、‘关’拟易‘波’,于上下文较有关联,以为如何?《鹧鸪天》诸阕仍学小晏,亦能不失规矩,偶有可斟酌处,适近患头痛,未能细阅指出,容后告。望能循序渐进,持之以恒,须志大而心虚,精勤不倦。修辞本于修身,植其根本而敷其枝叶,庶几日益能与于作者之林。此事甚难,尚待毕生努力为之,望弟等加勉!”[3](P173)此函对学生词作之遣词造句详细批改,并勉励诸生通过修身以提升修辞,以高尚之志达文辞之妙。又,1947年3月24日《致卢兆显函》云:“前作《蝶恋花》诸阕,大有进境,阅之心喜。……前此间徐天闵先生亦尝言及:‘文学之事,修养为难,技巧甚易。聪慧之士,用功不出五年可以完成矣。’蕙风亦言当于词外求词,所谓修养与学力是也。吾弟性情深挚,能思善感,已有根基,时加培植护持,当能卓然自立,不致华而不实,惟于文学技巧方面尚未能运用自如。此虽末事,亦非数年之功不办。且情意亦非辞不达,此文学作品赖乎外形之完整及作者表现之方法手段,亦极重要。望多揣摹古人作品及其表意达情、布局用字之法,先求通达,更言雕琢,此一般之次序,而为吾弟所尤当注意者也。”[3](P172)该函进一步强调修养与学力兼修,并指出应综合“辞”“完整之作品外形”“表现方法”等多种要素来表情达意。沈氏以上三通信札,以本自汪东、吴梅二师之“雅正沉郁”贯穿始终,其对后学的教诲,既关乎学养,又具体至词之用字,体现了师道相传的优良学风。
正声诗词社体现了抗战时期以沈祖棻与程千帆为代表的文学家继承与发扬文学责任感、使命感的自觉。在正声诗词社刊物上发表诗词文的,有学生、指导老师、老师的同事、老师的老师,可谓三世同堂,师道相传。正声,是正气之声,抒发了正直文人的家国之情。正声,同时又是雅正之声,以雅正沉郁为宗旨,纳不平之音于温柔敦厚之风。更为可贵的是,正声诗词社指出“文言、白话,原无严界”,用旧体诗词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时代,描写当下,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彰显了旧体诗词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