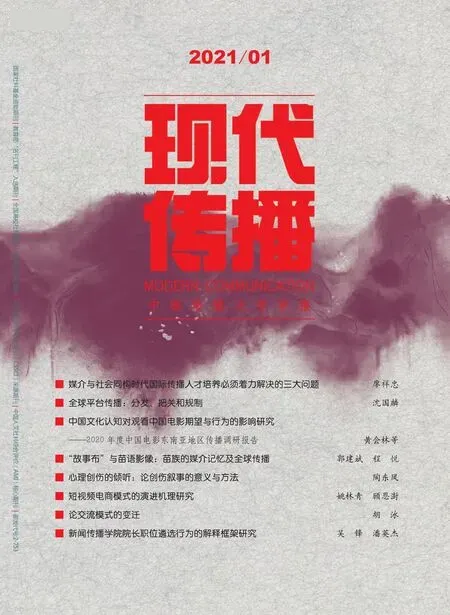原型观照、多重性格与悲情犯罪:刑侦类网剧的人物形象创新路径
■ 张智华 张 鲸
近年来,中国刑侦类网络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刑侦类网络剧因其关注现实、探讨人性的深刻内涵而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形象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是价值内涵的具体形象化呈现。随着网感观念的不断升级,中国刑侦类网络剧的人物形象有着新的发展变化,人物形象的这种创新构建不仅反映了这类题材网络剧的变化发展之道,也映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与网络剧创作的审美转向。
一、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形象的网感特质
互联网作为网络剧的艺术媒介,是“网络剧艺术创作理念和艺术思维的根源,直接指导着艺术创作的全过程”①。在对网络剧进行解读研究时很难跳脱网络自身的媒介属性。互联网的技术、文化、艺术等表达方式使得网络剧的艺术创造遵从于互联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相比于传统的电视剧和电影艺术,网络剧有着“网感”的天然亲和力,很容易与用户建立互动关系。王鹏举认为网感是对市场、对年轻人的思维和欣赏习惯的敏锐追踪,或者说是适应。②因此在人物形象方面,以年轻受众为主体的网络剧更加亲近一种青年亚文化审美的人物表达。与传统的破案题材电视剧相比,中国刑侦类网络剧的人物刻画更加突出一种反常规的设定,表现出较强的独创性。人物形象从出现便常有着反抗叛逆、个性鲜明、辨识度高的网感特质,如《余罪》中地痞混混形象的主角卧底余罪、《无证之罪》中冷血残忍的杀手李丰田等,整体呈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
初期的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形象丰富多彩,内涵表达浅层明快。但是随着媒介技术的融合革新、相关政策的引导规范以及创作审美观念的进步,网络剧的发展愈发成熟,在凸显网感表征的同时,网络剧对于自身艺术价值与文化品格的追求成为主流,网感观念得到升级。“提升网剧作品的艺术审美特性和思想深度,将涵于内的‘道’完美结合与形于外的‘术’,是网剧网感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所向。”③在这一过程中,刑侦类网络剧中人物的构建观念发生了改变,主角人物,配角人物以及对手(反派)人物都有着新的发展变化,同时叙事模式的升级与成熟,媒介融合的深度演进以及审美要求的全面提升,又给予了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创新的内在逻辑推动。中国刑侦类网络剧的人物形象构建伴随着网感的升级,进行着与传统刑侦电视剧不同的创新变化。
同时,中国部分刑侦类网络剧如《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受到海内外网民的好评,利用网络剧可以有效地在海内外传播中国文化。隋岩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指出:“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关键之所在。”④中国有9亿网民,世界网民38亿左右,网络剧的现有市场与潜在市场巨大,中国部分优秀刑侦类网络剧能够在海内外产生巨大作用,让海内外广大网民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从而有效地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二、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形象与审美构建的创新路径
格雷马斯根据二元对立原则提出了一种人物角色联系的符号矩阵概念⑤,根据角色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以主人公为出发点,可以将叙事作品的行为主体大致分为三类,主角人物、配角人物、反派人物(对手人物)。主角人物一般是故事的主人公,围绕着主角人物,配角人物常常与主角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关联,这种关联对于主角来讲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随剧情发展而变化。与主角成矛盾对立关系的则是反面人物即对手人物,二者则是绝对的对立面。三类人物形象因在剧中功能定位的差异而在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路径变迁。
(一)主角人物:从角色虚构到原型观照
主角人物是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塑造中的重中之重,主角人物是剧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形象。初期中国刑侦类网络剧的主角塑造更偏向于一种“全知者”的形象构建,主角们往往都拥有极高的智商,同时行为表现奇特,因此这类主角人物形象被赋予着一种超现实的特质。《暗黑者》中郭京飞饰演的犯罪学教授罗飞拥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但是性格怪癖;《无证之罪》的主角严良外号“阎王”,游走于黑白两道,能够使用目击者口中的描述以及完整准确地确定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心理罪》方木直接可以通过犯罪心理进行推理从而破案;《灭罪师》的主角唐朔同样擅长犯罪心理侧写方面,看一眼细节,就能够通过主观感觉进行推理。可以看到,发展初期的中国刑侦类网络剧主角人物拥有明显的“主角光环”加持,既能够快速掌握案件侦破的关键线索,又引导着剧情前进。这样的角色设定基本属于“上帝之眼”的存在。
对于中国刑侦类网络剧来讲,年轻观众存在天然的猎奇式审美期待,主角强大的自我能力能够获得观众的崇拜和认同,类似“上帝之眼”式的角色虚构能够引发观剧的畅快感,更容易与观众取得共鸣。但是,这种非常规、极端化的人物构建毕竟脱离实际,一旦主角身上的神性比例过大,便会造成角色的人性失真,削弱他们作为人的情感和行为。神性主人公更接近于福斯特提出的“扁平人物概念”⑥,扁平人物常常符号意味较浓,会给观众留下固定印象,但人物性格缺乏深度。
随着《白夜追凶》《破冰行动》《铁探》等剧的播出,中国刑侦类网络剧的主角人物构建开始观照现实人物原型,更加注重人物的真实性。《破冰行动》的创作者实地探访奋斗在前线的缉毒警察,以当代公安干警为参照对象,多数人物的创作都依赖于原型人物的素材。主角李飞一改前期刑侦类期网络剧中主角光辉睿智的形象,人物角色鲁莽冲动,敢于斗争,有点自以为是,却符合广大年轻缉毒警的真实形象,这样的创造更符合艺术真实的追求。《铁探》的主角塑造则直接依赖于真实人物原型,督察尚垶的原型是香港督察陈思祺,他为救伙伴而脑部中枪,终生被后遗症折磨,这一设定也成为尚垶这一形象独特的人物特征。因此,概念化较强的角色形象更适合前期剧集注重推理游戏化、猎奇性的叙事,但是现实责任意识的增强使得刑侦类网络剧必然需要通过更加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真实。
人物现实主义的归复更体现在角色身份的演变当中,刑侦类网络剧的主角从最初的大学教授(罗飞)、犯罪心理学学生(方木),到卧底(余罪)和边缘刑警(严良)、法医(秦明),再到刑侦顾问(关宏峰)和正式的公安警察(李飞、尚垶)。人物的身份变迁呈现出从群体疏离到体制回归的发展趋势。罗飞、方木的疏离身份定位,有利于人物通过另辟蹊径的反常规方式进行推理破案而不受司法、证据、体制的限制。但对于《白夜追凶》《破冰行动》中通过传统刑侦技法推理的关宏峰、李飞来讲,讲究证据,通过法律途径严惩真凶才是刑侦类网络剧展现真实生活状态的一面。可以发现,无论是主角形象的改变还是身份的变迁,其实都是主人公逐渐认同、归附主流现实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刑侦类网络剧整体发展的一个宏观方向。
(二)配角人物:从个性人物到多重性格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中,四元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和矛盾不对立两类关系,矛盾使角色之间产生联系,对立则进一步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除主角外,剧集中其他的角色都可以被归为配角。但在文中,配角独指与主角呈现矛盾但非对立关系的人物。
配角的设置本质上是为了服务主角,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和价值定位。由于主角人物的神性塑造,前期的刑侦类网络剧往往会削弱配角在叙事中的地位,但会赋予这些配角人物新颖的标签、奇葩的性格,使得这些人物同样与体制格格不入,但又极具表现力,与奇特怪异的主角形象相得益彰,构筑起了全剧的气质风格,符合青年观众的审美取向。因此,配角人物的塑造常常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色。《余罪》中余罪的“狐朋狗友”们的塑造各自有着独特的特点,如“鼠标”严德标突出赌博特色,口袋里常带着一副牌;“牲口”张猛是肌肉男形象,是众人欺负的对象;“花匠”汪慎修花心,有异性缘;安嘉璐则是学霸人设。这些人物的设置虽然个性化十足,但在角色的定位上通常有着主角塑造的辅助偏向,同时标签化过重,更多作为功能性人物推进叙事,难有深刻的价值承载。
警察形象往往是刑侦类网络剧的核心人物,但是一些警方阵营的配角人物则存在感更低,《暗黑者》中为了衬托主角罗飞的出场,案发现场尸检人员在测肝温、检查尸斑时的不专业性被夸大,导致剧情失真。为了反衬主角破案能力的强大,《无证之罪》的上司林奇等一众警员则事事依从严良的决定,对于主角来讲,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警探发现不了的关键证据等。总体来说,对警察职业的呈现不具有普遍性,警察更接近一种工具角色,作为主角生活环境的补充衬托,没有过多起到叙事推动的作用。因此,《暗黑者》《心理罪》等一批公安影视作品虽有着较高的收视率和口碑,但被业内人士诟病为“脱离警察而演警察”。
正如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言“唯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在主角人物弱化了个人英雄主义,归复主流现实的同时,配角人物开始寻求个性化突破。配角的存在不仅烘托了主角人物的人格魅力,更是参与构建了多层次的故事世界,与主角形成一种对照或者补充,丰富了故事的价值内涵。刑侦类网络剧的整体人物构建开始从单一英雄的表达转变为群像飙戏,次要人物逐渐走向舞台中心,人物形象逐渐圆形丰满,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人格,从个性人物到多重性格的转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角色的人性情感复杂化。对于人物的塑造常常采用二元对立的极化处理,但人性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很难将其极端化,精彩常在于情感的复杂化呈现。《白夜追凶》中刘长永这一角色映射着现实中工作能力一般、追求上位、圆滑世故的一类人。但在刘长永动机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心系女儿的慈父面容。这使得人物脱离了扁平化的标签束缚,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艺术的真实生动性来源于对生活本质的提炼概括,展现人物复杂情感的关键在于深入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发掘情感意蕴,展现人性之美。对比法医角色的塑造,《暗黑者》的法医梁音偏好“暗黑哥特风”,有自己的口头禅,平时装束浓艳奇特,角色特立独行,具有极强的反叛色彩与亚文化元素。而《白夜追凶》中高亚楠同样是工作时高冷严肃的女法医,但在生活中她却有着小女人的一面,高亚楠与关宏宇的每次见面都有着甜腻的互动情节,使得高亚楠这一角色充满了日常化审美的特色,贴近生活实际,缩短了梁音的距离感。
其次,角色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增强。《破冰行动》中的蔡永强,《白夜追凶》中的周巡、韩斌,这些人物能力出众,个性鲜明,但在某些时刻亦正亦反,使剧情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强了角色理解的陌生化,改变了之前众星捧月般的主配角关系,配角与主角紧密裹挟于主情节的发展之中,不再是叙事的附庸,更有自身的魅力呈现。《白夜追凶》的刑侦队长周巡虽然代表着正确的一方,却全程给主角关宏峰制造障碍,二人之间的纠缠关系构成了全剧戏剧性爆发的焦点之一。韩斌体现出不亚于主角的智商和能力,这一角色在出场时便拥有BOSS级别的气场,曾多次帮助关宏峰渡过难关。但自身的动机目的又让人怀疑,人物亦敌亦友的举动使得角色的具体身份神秘未知,这类人物自有一种矛盾性,因此更加吸引人的关注。
再次,角色有了更多的价值承载。刑侦类网络剧关注现实,传播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普法教义,承担了一定的价值责任。《破冰行动》《白夜追凶》等剧呈现警察与罪犯的正邪较量,刻画了一群服务民众、英勇无惧的职业警察形象,人物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真实呈现出当代警察的形象之美,推动了公安影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最后,刑侦类网络剧因演绎犯罪常常悲剧色彩浓烈,受害者是当代社会中罪恶行为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往往展现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引发观众的共情,从而折射现实、表达意义。《破冰行动》中的林水伯为救儿子以身试毒,堕入毒品的深渊。该人物身上呈现出亲情的缺失和命运的悲剧,他是违法者,但更是受害者和被救助者,林水伯真实反映了现实中千万“瘾君子”的真实生活——吸毒吸到最后生活落魄、家破人亡。剧集通过林水伯等人物的塑造,表现出毒品对个人与社会的危害,更加深化了正邪双方的矛盾对立。人物的悲剧命运可以唤起观众的共鸣,人物的境遇越加悲惨,则更加映射出毒品危害性的巨大。角色承载着创作者的态度,通过角色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中错误价值取向的批判,这也是现实主义作品该有的态度。可以看出,刑侦类网络剧的配角人物在创新发展中内涵更加丰富,角色塑造复杂多维,同时角色跳脱出单一定位,起到价值承载的深入作用。
3.对手(反派)人物:从人格缺失到悲情犯罪
刑侦类网络剧的角色分类可以大体分为警察、普通人、罪犯三类。同时在整体观念上可以通过二元对立原则分为好人和坏人,警察与民众代表着正义的一方,而犯罪者始终是其对立面,结局多数是悲剧收尾。罗伯特麦基认为:“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魅力和情感魄力,必须与对抗力量相适应。”⑦对手(反派)角色的重要性不亚于主角人物,主角和对手(反派)一般为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对手(反派)角色与主角的价值观相反,给主角造成各种障碍,优秀的对手(反派)角色反衬着主角人物的塑造。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初期的刑侦类网络剧在对手(反派)塑造上更偏向于直接展示人物的“本我”状态,而剥离“自我”与“超我”人格的均衡。本我作为人格结构的基础部分,是人直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组成。以“本我”状态为主的对手(反派)人物追求原始欲望的满足而拒绝压抑,较多展现其罪恶的一面。因此,这一时期对手(反派)的刻画多为社会边缘群体,其犯罪行为以及杀人手法常常戏剧化意味较浓,讲求仪式感和艺术性。《法医秦明》中的李大狗有恋物癖等怪诞的行为,杀人后习惯烹尸剥皮;《暗黑者》高智商犯罪团伙头子暗黑者(darker)按照死亡黑名单来杀人;《心理罪》“吸血鬼案”中的罪犯马凯患有躁郁症、妄想症,性情孤僻,内心扭曲。这些人物形象普遍具有精神缺陷或逆反人格,因人性缺失而导致邪恶犯罪,这是前期刑侦类网络剧对手(反派)人物的普遍特征。他们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生活存在,是一种无视法律与道德规则的存在。因而,刑侦类网络剧曾一度表现感官刺激,常常直接展示犯罪行为本身,画面多有血腥暴力场景。但随着政策规范的强化,一方面,刑侦类网络剧摒弃了大尺度博眼球的场面呈现;另一方面,观众审美需求的提升更加追求审美的情感共鸣与真实的观剧体验。“悲情犯罪”逐渐成为各大对手(反派)的犯罪缘由,情义与法治的两难抉择,往往是这类对手(反派)人物悲剧产生的根源。
《隐秘的角落》的成功在于深度剖析了人性中的善恶两面,追溯悲剧的根源,有着对角色现实境遇的深切洞察和解析。为挽救婚姻而杀人的张东升依然免不了妻子出轨的悲剧,因爱生恨是角色堕落的根源。张东升做出了违背正义的恶事,但是在细节方面体现了人性的温情与良知,在与三个小孩达成短暂的和解之后,对于小女孩的照顾帮助又容易引起观众的怜悯和同情。这一人物裹挟于命运的悲苦之中,冷血犯罪但又善心未泯,角色游离于道德层面“黑”与“白”之间,成为具有复杂的人性和情感的灰色人物。同样《无证之罪》中骆闻身患绝症,妻离子散,他以雪人名义杀人,为的是找出杀害自己妻儿的真凶。《白夜追凶》中任迪为救弟弟而绑架郭朋向警队施压,最终沦为罪犯。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悲剧中遭受灾难的既不是完全的好人(那会让人反感)亦非坏人(那会让人满足),而大多是因为某种错误而败亡的好人。”⑧刑侦类网络剧对敌手(反派)人物的塑造逐渐从恶的发掘转向善的毁灭,展现角色自身的现实悲剧性。这实际上是角色人性情感强化的表现。
可以发现对手(反派)角色的形象设定逐渐从边缘回归主流,角色同时拥有着三类人格,是个完整的个体,但犯罪的行为更类似于人物“自我”人格的抉择,在“超我”和“本我”之间艰难维持但最终失去平衡。“本我”所代表的情感欲念在抗争中战胜了“超我”代表的法治和良知理念,人物因此走向毁灭。
此外,以往呈现绝对对立关系的警匪双方开始相互交糅,“堕落警察”的形象成为刑侦类网络剧对手(反派)塑造的重要一部分,出现了罪犯卧底、黑警等角色。堕落警察的塑造打破了以往正义一方的绝对正派,角色塑造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意味。缉毒警们被形容为行走在刀尖上的舞者,他们常年面临着毒贩的威胁和利诱,警察堕落的实质是回归人本质的表现。《破冰行动》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警察,其中对于“黑警”的塑造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马云波这一人物的悲剧在于他极度痛恨毒品,但妻子为救他身中数枪,又不得已靠着毒品镇痛、解除痛苦。往日的缉毒英雄裹挟于情与法的双重矛盾中,被迫做出选择,但两个抉择无疑都引导人物命运的悲剧化转变。以马云波代表的“堕落警察”更是“好人沦落为坏人”的典型人物形象。对手(反派)随剧情发展成为逾加丰满且拥有自身命运的独立人格形象,因而能够打动观众,成为典型。
三、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形象与审美构建的内在逻辑
在网络剧的艺术发展进程中,网络剧的品质升级是内部文本元素共同创新的结果,文本叙事与人物构建紧密相关,网络剧叙事形态的创新演进引领着人物形象的更新变化。
(一)叙事演变中人物塑造的创新跟进
情节和人物构建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中,情节第一,人物第二,文本叙事给予了人物戏剧矛盾发生的环境,人物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典型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侦类网络剧发展的过程中,类型概念不断成熟,悬疑质感不断提升,类型意识的成熟是叙事升级的关键。刑侦类网络剧多以“主线案件+支线案件”的连续剧结构,主线剧情构建核心案件,关联主人公命运,通过总的悬疑点吸引观众的注意,支线剧情则开始呈现一系列其他案件。以《余罪》《暗黑者》为代表的刑侦类网络剧将精力放在了展现正、邪双方的主线对峙方面,着重体现主人公与对手(反派)的斗智斗勇。主角人物、对手(反派)角色的特质展现成为重点。因此,刑侦类网络剧尽可能展示了余罪、罗飞这一类人物的与众不同,同时作为对手(反派)的傅老大、暗黑者(darker)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质。
随着类型观念的强化,刑侦类网络剧更加注重主线与支线之间的关联紧密性,“主线案件+支线案件”的结构有了多线叙事和复杂主题发展朝向。这使得刑侦类网络剧极大地拓展了支线的剧情发展,在多线叙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拓展了故事讲述的维度,故事世界更加宏大,这为价值表达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无证之罪》一方面展现了以严良为代表的警方的破案行动,另一方面又展现了骆闻、郭羽等犯罪者们的心路变化。《白夜追凶》的支线剧情与主线剧情有着紧密的联系,案件反映当下众多现实问题,展现任迪、刘长永等小人物的众生百态。这种类型结构给予了刑侦类网络剧向内涵深度方面发展的空间,破案题材的内涵发展又增强了剧集挖掘人性深度,反映社会现实的价值意义。同时,叙事观念和模式的发展使得案情推理从犯罪画像刻画转而成为传统的刑侦推理,更加注重叙事细节的刻画而非情节作秀。“犯罪心理画像指的是对刑事案件的行为证据进行心理分析、刻画犯罪人性状与特征的过程及其刻画结果”⑨,这作为早期主要角色的刻画手段,能够凸显刑侦类网络剧主人公出众的能力和鲜明的特色,但是却有着推理断层的诟病,而传统的刑侦推理手法将破案所需的现场勘验、物证提取、法医检测、大数据统计等技术手段融入到紧张跌宕的叙事中,更符合真实的人物行为,人物形象更能体现出层次感。《白夜追凶》便是在人物各自的破案环境中体现人物的迥异性格。一方面,在推理方面,哥哥有理有据,破案如神,弟弟照猫画虎,但行为窘迫,漏洞百出;另一方面,弟弟冲动出格的行为又在追凶过程中表现出色,兄弟二人优势互补,形成叙事悬念的同时人物形象差异鲜明。
(二)融合生态下类型人物的对话借鉴
艺术媒介指的是“创作理念和艺术思维的根源,直接指导着艺术创作的全过程”⑩。电视媒介有着大众媒介的属性,承担着诸多的社会功能,这使得电视剧在创作上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传递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因此在人物构建方面,传统刑侦电视剧更加二元对立,正邪分明,呈现警察之间的冷暖情谊,表现罪犯的人性堕落,冷酷无情,具有警示教化意义。如《冬至》呈现了小职员陈一平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的全过程,《重案六组》塑造了一批优秀的警察形象。故事与人物情感紧密联系,用案件充分描画警察的悲欢喜乐,被称为真实的警察故事。网络剧与电视剧有着类似的艺术表征,但基于诞生媒介的不同而在美学表达和创作规律上有着鲜明差异。
近年来,随着融合态势的深化,电视剧与网络剧也开始在“表意系统和美学面向”上相互借鉴和靠近。人物形象是重要的表意符号,刑侦类网络剧的人物逐渐具有传统破案电视剧的人性共鸣和价值承担。这使得刑侦类网络剧小人物的悲剧感强化,对于犯罪堕落的过程有了详细的刻画。刑侦类网络剧从对于darker等反派人物极端异化的犯罪手段的渲染逐渐过渡对郭羽、马云波等的悲剧刻画。人物有着清晰的堕落轨迹,其结果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人物沉沦与法律威慑的直接展示有着更加强烈的警示价值。同时,《冷案》《白夜追凶》《破冰行动》等剧吸收了电视剧注重警察情感挖掘的特质,突破了前期刑侦类网络剧对于警察形象的平面化塑造,使得警察形象更饱满、更立体。
另一方面,融合趋势使得剧集各类型之间开始了创新借鉴。“类型+”模式成了网络剧发展创新的重要表现。理想化设置通常是早期青春剧主角的特质,青春爱情剧中的人物通常高颜值、气质清新,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在人物塑造方面,《美人为馅》《如果蜗牛有爱情》等剧开始将青春爱情元素融入到刑侦类网络剧中。《如果蜗牛有爱情》中王凯与王子文的选角更加贴近于青春剧的人物形象,注重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同时,刑侦类网络剧更多吸收了段子剧主角平民式的日常化审美。平民化角色打破了英雄式的角色权威,人物更加亲切真实。《无证之罪》中的严良婚姻不幸,生活窘迫,事业不得志;《破冰行动》中李飞鲁莽冲动,人物缺点明确。此外,《冷案》《铁探》等剧也改变了以往刑侦类网络剧女性角色对于男性角色的依附关系,有了“大女主”剧的特质,女性人物的角色地位和形象发生改变。《铁探》女主惠英红饰演的总警司万晞华雷厉风行,气场强大;《冷案》中四个警花则性格迥异,形象鲜明。不同类型之间的人物形象借鉴给予了刑侦类网络剧人物塑造的创新尝试。
注释:
①⑩ 张智华:《中国网络电影、网络剧、网络节目的初探——兼论中国网络文化的建设》,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② 黄启哲:《“网感”正悄悄改变中国电视编剧》,《文汇报》,2016年6月30日,第6版。
③ 周云倩、常嘉轩:《网感:网剧的核心要素及其特性》,《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233页。
④ 隋岩:《国家文化软实力》,《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3日,第2版。
⑤ 钱翰、黄秀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190页。
⑥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⑦ [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
⑧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⑨ 付有志:《解码犯罪心理画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