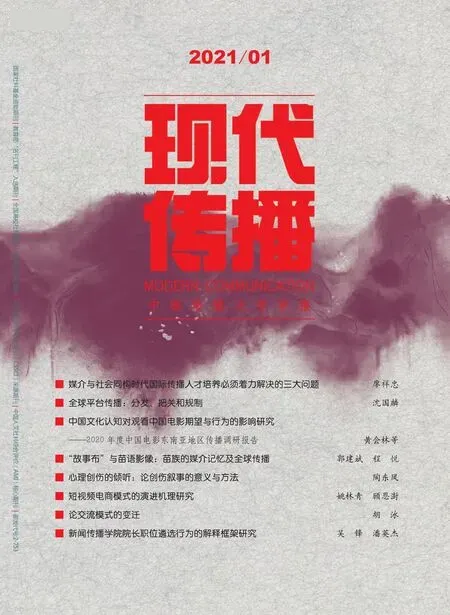全球与地方之间:“二战”期间我国大后方新闻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 梁君健
一、问题的提出:新闻纪录片与战争宣传
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大后方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流通和放映活动日益频繁,成为中国电影史和传播史中令人瞩目的现象。随着盟国之间宣传系统的迅速建立,中国大后方的相关机构也参与其中,不仅接收和放映了大量关于战争进程、军事训练和科技发展的海外新闻片,而且也生产了若干自制内容在国内外发行放映。对于这一特殊的传播现象,有学者已经将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战的重要证据。①然而,战时中国的新闻纪录片具体是如何借鉴了欧美国家的既有做法,在融入国际传播网络中又发展出怎样的本土化特征,仍然缺乏相关探讨。
新闻纪录片(Newsreel)是重要的新闻传播形态,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面向公众的围绕纪实图片展开的演讲活动。②正式的新闻片出现于20世纪初期。“一战”期间,电影和新闻片即在战时宣传中开始扮演突出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闻简报式的在影院传播的新闻片,这些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闻纪录片奠定了形态和观众的基础。尤其是当“二战”提供了引人瞩目的题材和内容后,新闻纪录片真正地成为一种主流媒介,不仅标志着媒介发展史中的重要时刻,③同时也将全球传播的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历史背景:“二战”时期盟国的战时宣传
新闻纪录片对于战争的重要功能在“一战”期间就得到展现。由于国际纪录片运动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农业安全署和英国壳牌公司为代表的将纪录片用于推广机构目标的成功案例,让纪录片所蕴含的说服力量从“二战”开始前就得到全球公认。“二战”期间,盟军各国都建立起以战争宣传为目标的制片和放映系统,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类似于通讯社的流通组织,相互交换素材和影片。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了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美国的战时信息处,以及英国战时信息部中的电影部门。
1942年6月13日,美国政府成立战时信息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除了电影审查之外,在美国本土通过国会图书馆电影计划(Library of Congress Film Project)来放映新闻片。④英国在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9月4日,就成立了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信息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MOI),并在建立之后不久下设电影部门。1939年12月起,改组后的新闻部电影处由克拉克(Kenneth Clark)担任领导人,将电影领域的具体工作目标制定为给纪录战争的影片提供海外发行的支持,以及针对中立国争取国际援助。1939年5月,加拿大通过国家电影法案(national film act),成立了国家电影局(Canadian Film Board,CFB),由格里尔逊担任负责人。电影局先后推出了两个系列的新闻纪录片,《前进中的加拿大》(CanadaCarriesOn)主要针对国内观众宣传加拿大在战争中的角色和努力,《世界在行动》(TheWorldinAction)则针对包括海外在内的更广泛的观众,主要处理全球性的事务和战争策略。
(二)研究问题:国际传播与本土观念的形成
中国是上述机构展开战时宣传的重要对象。早在“一战”期间,英国就开始尝试向中国发行自己的战时电影。从1917年9月到“一战”结束期间的15个月内,共有26部电影和35期官方新闻片发行到中国,这些影片在51个地方进行了593次放映,至少吸引了37万人次的中国观众。⑤这些战争影像拓展了当时国人对于世界局势的直观认识。“二战”期间,盟国延续和发展了“一战”时期积累下来的宣传经验,在策略制定和资源投入等方面将宣传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对于英美等国来说,基于“一战”而形成的战时对盟友的宣传工作,具有明确的策略和实际的目标;而由于国民经济和电影工业水平还较为落后,中国在抗战时期仍然大量进口包括新闻纪录片在内的西方电影产品,直观上看仍处于弱势和被影响的一方。
但是,在“二战”期间的战时宣传和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并不仅仅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传播实践和观念形成,往往来自多方的互动与协商,而非仅靠“冲击与回应”的模型所能解释的。到1943年前后,当时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者已经发展出比较系统的电影观念,体现出全球性的战时宣传与中国独特国情之间的融合。因而,考察国际传播语境下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纪录片(包括功能和生产放映方式十分类似的新闻幻灯片和教育电影)的传播实践,不仅有助于获得一个更为全面的有关“二战”与国际传播的历史图景,而且还能够较为细致地解答在中国战时语境中关于“新闻和电影是什么”以及“新闻和电影能够用来做什么”的观念认知。
二、宣传和动员:外部经验的吸收与改造
(一)中国的战时新闻纪录片机构
抗战时期,新闻纪录片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注意,各类机构都致力于制作和传播与中国抗战和世界战场有关的新闻纪录片。抗战前,国民党中央政府就仿照意大利和苏联开始了官营电影的建设,而抗战则是对这种体系的一个快速促成,不仅建立了“中电”和“中制”这两个战时官营电影的核心机构⑥,教育部门和军事部门也都积极参与到新闻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中。前者如1942年元旦成立的、以学校教育片和社会教育片的摄制为核心任务的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以及1942年由教育部第二组社会教育工作团改组教育部川康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后者则有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设的放映总队等。
除了政府机构之外,驻重庆的英美使馆均设有新闻处,承担向中国供给本国出产的新闻纪录片和教育影片的任务。两国使馆向中国提供的放映片目,主要是报道盟军战况的战时新闻片,同时还有部分展现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题性质的纪录影片。此外,两国使馆还负责联络和转交其他机构赠送中国的影片,如美国国务院赠送中国23部医学影片⑦、美国外科学会赠予中国的医学影片⑧等。另外,中国政府还联合美国与英国成立了“联合国幻灯电影供应社”,后改为“联合国影闻宣传处”,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美大使馆新闻处及英大使馆新闻处各派代表一人,组成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指派代表三国代表各一人负责推动处务⑨,首要任务是收集、制作和发行袖珍映片,并在全国各地建立放映站进行流通和放映。
(二)新闻纪录片的战时功能:军事教育与民众动员
和盟国类似,新闻纪录片对于战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其首要功能仍然是战争方面的。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军事教育和民众动员两个方面来达成。
新闻纪录片的制作和放映首先被视作一种军事行为。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之后,美国海军就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海军航空站开设了为期4周的摄影课程;1920年1月21日,美国海军在华盛顿的海军航空站设立了摄影学校。⑩“二战”期间,美国军方的制作机构美国陆军通讯兵摄影中心(Signal Corps Photographic Center)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电影机构,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共有2100人在岗,包括了280名军官、600名应征入伍的士兵,以及1300名普通工作人员。
由于资源匮乏,国民党的军队系统无法像美军一样组织起自己的摄制机构,用于军队教育的影像主要由其他机构协助完成。例如,1940年,由政治部管辖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设立了教育影片部,专门设计拍摄军事教育片,当年即完成军事教育影片《防御战车》《中国空军》《降落伞》《滑翔机》《步兵射击教育》等。相对于制作,中国军事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在部队展开教育电影和新闻纪录片的放映,前者主要用于军事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目标是提升士气。当时,慰劳总会向海外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就有专门的条目,要募集国币两千万元,用以为部队置办影片、放映机、幻灯影片等放映材料和设备。
除了直接运用于军事训练和军队士气鼓舞之外,新闻纪录片还被用以唤起国内外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我国对于电影与民众关系的认识,体现在“国防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电影界就出现了“国防电影”的探索。1938年1月31日,《抗战电影》的创刊号中刊登了一组总标题为《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文章,其中,唐瑜所撰述的电影在农村的问题直接阐释了利用电影动员民众、从而争取抗战胜利的设想。他说:“将来胜负的决战是在乡村,而不是在都市,因此,我们的国防电影的题材的采取应该是在发动农村的自卫游击战这一面,并且要大量地运到乡村去放映,否则,也不过是都市上少爷小姐生活的点缀品而已。”
利用新闻纪录片动员民众的观念也体现在一线摄影师的实践中。姚炘是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国营电影制片厂长,长期担任新闻片和纪录片的摄影师,他于1943年2月发表了《新闻片与纪实片——几年来从电影工作获得的一点启示》,将新闻片视作“最有力量的国防宣传”,“可以将伟大的战绩活生生地记载下来”。他举苏联纪实片《新世界的一日》为例,认为这“是一部动员数百位以上的摄影师,是一部为他们国防宣传很得力的纪实片”,整部影片“充满着年轻的朝气,与进步的表现,他的价值是实在胜过一部剧情片,他不但有艺术价值,他更有一种任何宣传所不及的宣传价值”。“宣传价值”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新闻纪录片的第一价值,是超过艺术价值的最高追求,而宣传的对象则主要是广大民众。
(三)小结:宣传、抗战与后发现代化
总体来看,中国战时新闻纪录片的宣传观念大体上继承了“一战”以来西方国家对于电影的认知,但同时具有自身的特征。“一战”时期美国的电影海报就已经暗示出,电影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人们的心灵和态度的有力工具。“二战”期间,格里尔逊发展出了他对宣传的标准定义:对形成理解、操纵认知以及指导行为的系统尝试。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期间他也一直把纪录片工作和教育宣传等同起来,坚持应当用带有情绪化的视觉效果去传达事实。
在接受与实践上述宣传观念的基础上,中国战时新闻纪录片的实践者们还形成了来自国情和观众群体的独特判断。大多数民众还不具备读写能力、无法从文字报道中获取信息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发展困境,电影成为了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利器”,被赋予了动员民众的高期待。因而,中国对于新闻纪录片在宣传价值上的认识,在说服公众支持战争的基础上叠加了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的期待。这与“抗战建国”的观念可以说是同出一辙,并且展示出了电影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象征价值。不仅是电影所展现的内容,更是电影本身,成为现代化的景观,激发了民众对于现代化的期待。
三、国际传播与全球秩序:作为中外沟通桥梁的新闻纪录片
(一)纪录片:电影的国际主义运动
“一战”之后,社会纪实电影运动与国际对话之间产生了密切关系,不同群体都开始将纪录片用作介入国际秩序的公共实践,从而形成了一股电影国际主义的运动。将纪录片与国际秩序进行结合,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纪录片创作的内在动力来说,20世纪30年代,格里尔逊在用纪录片探究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必然会触及当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话题,而纪录片则能够将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抽象的国际事务联系起来,提供一个全球性的叙事;从纪录片这一媒介的外部功能来说,它也越来越被赋予了向国际社会营销国家形象、沟通国际秩序的期待。也正是在这个观念下,在“二战”期间,格里尔逊主动地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出品的新闻纪录片中加入了对于战后的展望,借助《世界在行动》(TheWorldinAction)等系列纪录片去为全球观众呈现看待世界的新的视角。
作为“二战”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成果,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成为了国际主义的有效手段,它被用于为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相应的知识系统。联合国继承了国际纪录片运动的观念,先是继续借助已有的教育和纪录电影网络,进而尝试自己主导纪录片的制作,以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提供国际的讨论平台。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常规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讨论了全球性电影项目的议题。格里尔逊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个名为“计划中的制作部门,大众传媒用于和平”的提案,报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重建不同国家的大众传播系统的国际性计划。
(二)中国围绕新闻纪录片的外宣实践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二战”提供了一个沟通和建立共识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制作能力有限,但中国也基于自身历史和发展阶段参与到了纪录片的全球性的运动中,所秉持的观念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的区别。
首先,出于对外争取援助和支持的缘故,国民党政府的制作机构十分重视将中国抗战的新闻纪录片发行到海外,并且积极地为海外机构提供战时中国的影像,以供编辑到他们出品的新闻纪录片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影片是《我们为何而战》系列中的《中国为何而战》,影片的素材大量地来自罗静予带到美国的“中制”出品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成片用中英两种拷贝向世界各国发行。当时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苦干》的拍摄和放映。影片由美籍华侨李灵爱(当时国内报道中被写为“李玲蕴”)策划和筹资,夏威夷新闻记者史哥特拍摄,从1937年起断续拍摄了4年时间,记载了重庆大轰炸等很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画面。影片在美放映后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1942年首次设立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其次,当时国内的刊物还关注和报道西方国家的新闻纪录片和电影参与国际事务的具体政策和做法,为国民政府提供参照。在1942年10月,孙明经翻译了《美国电影国策之新纪元——罗斯福委梅乐德兼战时影片联络专员(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films)原函》,详细列举了美国战时电影的制度设计。1944年3月,翻译并刊发了《好莱坞纪事报》(Hollywood Report)1944年1月14日报道的美国政府训练电影使节和推进与电影界合作的诸多措施。1943年10月,刊发了综合国外各类资料的介绍性的文章《加拿大战时电影》,主要介绍了以《世界在行动》为代表的新闻纪录片对于战后建设方面的探讨。1944年3月刊发了罗静予应美国战时情报局所作对国内的短波广播稿《美国电影事业鸟瞰》,介绍了美国电影在战争和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结束上述广播时,罗静予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总结,将电影的意义提升到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的高度。他说:“如果每一个国家的国民,从小到大,便了解另一个国家,并且明白自己对于人类的义务,建立一个美丽世界的工作,也就很容易实现,电影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最有效的工具。”
(三)以跨文化理解为核心的外宣观念
可以说,在利用新闻纪录片展开外宣实践的基础上,除了直接的战争目标外,国人已经充分感觉到纪录片运动所蕴含的全球化的潜能,特别是认识到“二战”给中国的国际化水平带来的推动。相比于西方国家利用电影交流来维护和平和促进国际新秩序,中国战时的新闻纪录片观念则更加强调跨文化理解,尤其是促进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可。1944年最后一期《电影与播音》上所刊载的王绍清撰写的《中国为何而战的制作及其价值》尤其展示了当时的一种典型认知。他认为,从这部《中国为何而战》起,西方世界开始打破隔阂、逐渐了解东方的文化和人民,这完全是由于电影的优势。
此外,孙明经等还从教育电影方法论的角度,具体介绍了中国题材的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电影是如何具体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与交流的。在1942年的第六期杂志上,孙明经专门翻译刊发了《电影教育法案例:与中国儿童共同生活》一文,介绍了美国小学四年级学生通过反复观看中国影片而加深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的过程。孙明经的文章指出,电影已经成为促进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渠道,而中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世界的积极接纳。他认为,战后中国电影生产的题材应当“以我国地理及人文为主”,这不仅能够发挥电影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促进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的积极的跨文化理解。
四、结论:媒介观念的国际影响与本土特征
在“一战”时期成型的战时新闻实践的基础上,“二战”时期的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的影响。不同的国家都加入到这一实践中来,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种基于世界大战而形成的全球性的传播现象,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又并不相同。本文正是希望突破国别史和一元论的观念,不仅将抗战大后方的新闻纪录片实践看作中国抗战中教育电影、动员民众和抗战建国的一个篇章,而且在与国际新闻传播的整体结构密切互动的情境之下,考察中国在这方面的本土特征及其形成的观念遗产。
中国抗战期间的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传播与放映,比较完整地接纳了英美等盟国的普遍做法,并发展出自己不同的认知。首先,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原因,尤其是民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较低,新闻纪录片的视觉媒介的特质得到了强调。在当时的中国,它被认为是能够更有效地针对国人展开宣传的工具,并且能够在进行战时动员的同时促进中国民众的现代知识与国族观念的提升。其次,由于中国在战前国际地位较低,“二战”成了中国积极加入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契机,而新闻纪录片则在这种期待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跨文化理解。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均与当时中国自身的后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最后,中国战时新闻纪录片所发展出来的独特观念并非这一历史时期独有,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此后中国的纪录片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中,体现出历史的延续性。通过媒介去动员和教育民众,以及通过传播促进跨文化理解,成为了不同历史时期被中国各类组织和机构所共享和共同继承的观念资源,在很多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 Matthew D.Johnson.PropagandaandSovereigntyinWartimeChina:MoraleOperationsandPsychologicalWarfareundertheOfficeofWarInformation.Modern Asian Studies,vol.45,no.2,2011.p.306.
② Sumiko Higashi.Melodrama,Realism,andRace:WorldWarIINewsreelsandPropagandaFilm.Cinema Journal,vol.37,no.3,1998.p.42.
③ Stephen McCreery and Brian Creech.TheJournalisticValueofEmergingTechnologies:AmericanPressReactiontoNewsreelsDuringWWII.Journalism History,vol.40,no.3,2014.p.178.
④ Rich Underwood.Roll!ShootingTVNews:ViewsfromBehindtheLens.Oxford:Focal Press.2007.p.14.
⑤ Nicholas Reeves.FilmPropagandaandItsAudience:TheExampleofBritain′sOfficialFilmsduringtheFirstWorldWa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18,no.3,1983.p.476.
⑥ 虞吉:《中国电影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⑦ 《美医学影片出品者赠我国医学片》,《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9-10期合刊,封二。
⑧ 《美国外科学会赠我国医学影片片目》,《电影与播音》,1945年第4期,第102页。
⑨ 《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十月份通讯》,《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9-10期合刊,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