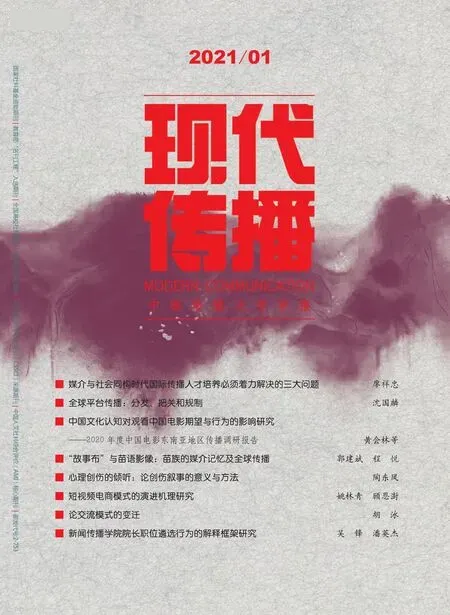论凝视型纪录片的沉浸性与反思性凝视
■ 周 兰 周 文
一、问题的提出
1929年,伊文思拍摄了《雨》,只有短短14分钟,他随即被赞誉为“先锋电影诗人”。今天,90年前的那场雨依然湿漉漉地下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雨》之后60年的1988年,在绝命之作《风的故事》中,伊文思的先锋探索走向了极致。同样是1929年,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问世。2014年,英国著名影视杂志《视与听》评选史上最伟大纪录片,全球300多位纪录片人投票,《持摄影机的人》毫无悬念位居榜首,甚至有权威专家评论,它代表了纪录片的未来。
拍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的纪录片数不胜数,但1992年罗恩·弗里克的《天地玄黄》一经推出便震惊世人,有人说,如果流浪荒岛,它将是随身携带的唯一影视作品。动物、昆虫、鸟类也是纪录片大家庭的主要类型,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一旦雅克·贝汉的《小宇宙》(又名《微观世界》)和《迁徙的鸟》、格里高利·考伯特的《尘与雪》横空出世,则呈现出“一览众山小”的局面。
世界纪录片浩瀚如大海,绝大多数都淹没于历史尘埃中,一小部分曾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但只有极少数得以超越时代、传之后世。上述作品都经历检验并成为永远的经典,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场普普通通的雨经由伊文思的《雨》就那么晶莹璀璨?为什么苏联极为平常的一天在维尔托夫的镜头下那么激情四溢?为什么在罗恩·弗里克的《天地玄黄》里,世界的自然地理、名胜古迹、宗教寺庙、城市、灾难等没有成为奇观的汇集,却成为深刻的哲学沉思和心灵拷问?为什么一个小小角落里的昆虫们能演绎出宏大的交响乐?为什么一提起关于鸟的作品你毫不犹豫就会想到《迁徙的鸟》而根本记不住其它?为什么一部表现动物的《尘与雪》会让人感觉恍如梦境?
简言之,为什么这些作品可以超尘脱俗可以如此纯粹?它们有什么共同点?表面上看,它们的题材、主题、表现手法、创作时代都迥然不同,但除去这些因素,我们发现,它们背后竟有惊人的一致性:创作者都有刻骨的“凝视”情结,每部作品都呈现为一种浓郁的“凝视”状态,而绝大多数纪录片都只是“看”。
二、凝视型纪录片
“辉煌的感性”(也称“灿烂的感性”)是法国著名美学家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审美对象是感性的辉煌呈现”①,“审美对象就是辉煌地呈现的感性”②。其中的感性,主要包括艺术作品的物质材料和形式必然性。所谓“辉煌的感性”,是指艺术作品的感性在遭遇具有良好审美知觉的欣赏者后,会强力爆发和华丽绽放,最充分地实现自身。杜夫海纳进一步指出,在宇宙论纬度,“辉煌的感性”展开的是一个“世界的氛围”,创造出的是彼此相异又共存的多个世界。而在创作者纬度,则表现为一种风格:除了技术层面的外形形式,最重要的是作为“真正的完形”的创作者的“世界观”,也就是作品呈现出来的创作者看世界的方式。
笔者认为,凝视是人类观看世界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凝视,就是目不转睛、聚精会神、专注投入地看。古今中外有关凝视的故事很多,其历史与人类同样漫长,抬头仰望满天星辰或许是人类凝视的真正开始,那是希望从浩瀚宇宙中建立坐标,寻找自我。现代有关心理的研究则指出,男女之间互相凝视超过七秒钟就会产生奇妙的情感反应。
凝视最经典的、至今不可超越的范本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小说虽然有《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重现的时光》等煌煌七卷,却没有完整、紧凑的情节,只是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包括童年、家庭生活、恋爱、历史事件等。但它不是普通的回忆,而是一往情深的凝视。普鲁斯特天才的想象力、感受力、敏感和细腻,使他拥有无与伦比的神祗般的眼睛和心灵。这双眼睛的凝视,既澄澈、透明,又深邃、高远,像阳光照亮了过去,令遗忘的事物如珍珠一样重新闪闪发光。有人说,普鲁斯特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一样,能按照名字认识森林里每一朵花、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个形状、每一个颜色、每一种香味,目光所及,它们像一个个音符一样自然涌现。《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展示了凝视对事物细致入微的柔情抚摸,其蚀骨入髓的感悟、超然的智慧、交错变幻的时空、宏大的架构、万花筒一般的缤纷世界,更体现了人类凝视可以达到的深度、高度和浓度,超越了哲学,也超越了宗教。
纪录片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可以按比尔·尼科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的论述,分成诗意模式、说明模式、观察模式、参与模式、反身模式、述行模式六种。比如观察模式,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直接电影将之推向了极致,要求创作者和摄影机像墙上的苍蝇一样观看世界,不可夹带任何个人情感,只能作为严格的旁观者和纪录者。参与模式以法国的真实电影为代表,刚好与观察模式相反,认为更本质的真实隐藏在日常表象的下面,需要创作者深入参与甚至刺激对象的生活。说明模式以一种科学、客观、权威、逻辑化的方式对世界进行阐释,诗意纪录片则以诗性的目光从生活中提取诗意。
六种模式从不同角度看世界,各有自己的功能意义,也可能互相融合。但是,如果要作品实现杜夫海纳“辉煌的感性”“灿烂的感性”,它们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对《雨》《持摄影机的人》《小宇宙》《迁徙的鸟》《尘与雪》《天地玄黄》等作品的研究,笔者发现,在通往这幅理想愿景的道路上,凝视竟是它们的共同路径,由此构成了极为独特的纪录片类型,姑且称之为凝视型纪录片。
凝视型纪录片是指纪录片创作主体(也包括欣赏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为一种凝视关系,凝视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作品呈现的状态,并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凝视叙事。
凝视叙事具有下面这些特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凝视是影片贯穿始终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线索,尽管作为创作者的凝视主体大多数都不在片中出现,但他的视线、情感一直在,并且主导叙事方向。第二,作品中特写、近景占比很大,甚至有许多大特写,这是凝视本身的物理现实性决定的,即凝视主客体之间距离大多比较近,《小宇宙》是极致。第三,片断化、非情节性、非时间性,这是因为在物理现实性外,还有更本质的内在性,即凝视是心灵在看,而心灵具有联想性、跳跃性。《尘与雪》《天地玄黄》都是这样,即便《雨》《持摄影机的人》《小宇宙》《迁徙的鸟》,看似有时间,但其中的每天、每年也是概括和抽象的。第四,整体节奏舒缓,固定镜头和缓慢运动镜头为主,就算《迁徙的鸟》有大量运动镜头,但因为主客体都在进行一致性的运动,即摄影器与鸟一起近距离飞行拍摄,所以,主客体之间依然是相对静止的状态。第五,无解说或少解说,或第一人称,或感情色彩较浓的提示性简洁旁白,凝视是私密性很强的活动,创作者希望观众与他一起静观,不受或少受外在干扰。
三、沉浸性凝视
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凝视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每天趴在河边凝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直至憔悴而死。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称之为自恋情结。笔者认为,这个故事揭示了凝视型纪录片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沉浸性凝视,即凝视来自创作主体(也包括欣赏主体),主体在凝视中沉浸于客体,客体是主体沉浸化凝视的反映。《雨》《持摄影机的人》《小宇宙》《迁徙的鸟》《尘与雪》等均属此类。在这些影片中,创作者强烈的沉浸性的凝视目光,情不自禁地暴露了创作主体不在场的在场,让我们感知到一个深情的意象化的凝视主体。下面,不妨对它们的凝视进行逐一考察。
伊文思的《雨》是他对阿姆斯特丹夏天一场雨的凝视。这本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小雨,但在伊文思的凝视之下,却绽放出了杜夫海纳所说的“辉煌的感性”。雨前,河面上波光粼粼,摇曳生姿;刚下时,雨点荡起一圈圈涟漪,像莲花一样盛开;雨大了,水花四溅,大珠小珠落玉盘。街上地面打湿了,如镜子一般照出车辆、行人的倒影;雨滴顺着车窗玻璃滑下,留下浅浅的印痕;透过雨水朦胧的车窗,是外面朦胧的街景、人影。雨后,排水口汩汩喷涌,屋檐挂着晶莹水珠,水面恢复平静。这是一首主要由特写、近景、俯拍镜头组成的雨的抒情诗,虽然不在画面里,但我们却明显感觉到伊文思伫立河边、走在街头,凝视雨的点点滴滴,沉浸于雨的世界,就像一个怀着淡淡忧伤的雨中漫步的诗人。
年轻的伊文思眼里带着忧郁,吉加·维尔托夫的凝视则满含激情。在《持摄影机的人》里,凝视从清晨开始,这是一幅静谧祥和的图景,透过白色纱帘的窗户,年轻女子尚在熟睡,街道空旷无人,流浪者睡在长椅上,树木在风中独自摇摆。白天是快速运转的忙碌社会,到处是充满运动感的现代工业文明,同时进行的有结婚与离婚、葬礼和新生儿出生等事件。下午至傍晚时分,则是娱乐休闲时一张张健康、快乐、喜悦的脸庞。这是对前苏联普通一天热情洋溢的凝视,许多人事物因为被凝视而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凸显出来,时至今日,依然光芒四射。当时,另有一部同属“城市交响乐”的片子《柏林——大都市交响乐》,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差异。《柏林》流于走马观花地看,最终只是一堆浮光掠影。虽然《持摄影机的人》也不乏快节奏的工业段落,但它更有细腻、深入和悠长的凝视,在人、事物上面,我们能深刻地看到目光、时间的停驻痕迹。不仅如此,该片的一大特色是,摄影师四处奔忙的身影、作为摄影师眼睛的摄影机镜头的大特写、剪辑师仔细挑选胶片上人物特写的镜头反复出现,更是以一种自我反射的形式直观地表达了创作者的凝视。
雅克·贝汉1996年制作的《小宇宙》(《微观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孩童般的凝视。在大自然极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蚂蚁洗脸梳妆,蜗牛谈恋爱,屎壳螂不屈不挠地推举比自己大很多的粪球,草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雨滴像炮弹一样落在泥土上,“茂草变成了一片森林,小石头就像高山,小水滴形如汪洋大海。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逝着,一小时像过了一天,一天像过了一季,一季像过了一生”。《小宇宙》的摄影师就像一个满怀童真的孩子,痴迷地蹲在那片草原,凝视长达十余年,才完成了这部与法布尔的《昆虫记》异曲同工的“昆虫的史诗”。
几年之后,《迁徙的鸟》再度惊艳世人。这次,从《小宇宙》的小小天地站了起来,雅克·贝汉的凝视越过大地山川,遍及整个地球的大洲大洋。与一般纪录片远远的长焦遥望不同,它是高空中咫尺之间的贴身凝视。为此,摄影师、航拍器与鸟一起飞翔,鸟的翅膀触手可及,鸟扇动翅膀的声音、呼吸的节律清晰可闻,而有些拍摄器就在鸟的身上,相当于与鸟拥有共同的眼睛。高山、草原、城市、森林次第退去,千山万水纷纷掠过,一直不变的是近距离的追随和凝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飞翔的凝视,在蓝天白云的高空,原野之上、群山之巅,一个自由与梦想的伟大意象。
格里高利·考伯特2005年的《尘与雪》是又一部典型的沉浸性凝视作品。影片展示了人与动物之间极端的亲密无间:人与抹香鲸在大海相拥而眠;孩童倚靠大象酣然入睡;白衣少年翻开书为大象朗读;印度少女一手贴心、一手抚摸大象;祖孙静坐黄沙,耳语低吟,身旁是温顺的花豹……土褐色的色彩基调犹如宇宙洪荒、天地初开的远古图景,如诗如火的旁白仿佛来自天界的回音,而画面缓慢得接近静止。没有时间,没有情境,没有声音。这是一个近乎神话式的伊甸园,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片永恒之地。《尘与雪》是一场梦中的凝视。
可以看出,在沉浸性凝视纪录片中,主客体完美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不可分割的互相映照的关系。在主体沉浸的眼睛里,客体华丽绽放;在客体灿烂的光芒中,主体显影为一往情深的凝视意象,就像那喀索斯的临水照影。
其中,主体全情沉浸于客体中,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伊文思迷失于雨,维尔托夫沉浸于日常生活的诗意,雅克·贝汉执著于昆虫小宇宙、迷恋于鸟的自由,考伯特陶然于梦境,他们进入的是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审美状态,自失于对象之中,忘记了他的个体和意志,仅仅只是作为绽放客体的镜子而存在。
而客体往往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优美特征,柔美、亲切、温暖、舒适、安全,与主体构成一种亲近、融洽、和谐的关系。这与下面要讲的反思性凝视有很大差别。同时,这些客体大多具备意象隐喻的功能,能够承载主体丰富的情感和思想需求。比如,雨,所谓“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小宇宙》,一个童话乐园;鸟,自由与梦想的象征;《尘与雪》,理想的天堂。
四、反思性凝视
古希腊还有一个神话,主角叫美杜莎,是一位蛇发妖怪,拥有犀利无比的目光,她的凝视意味着毁灭,随时随地可以摧毁被她看见的人和神。与那喀索斯的沉浸性凝视相反,美杜莎神话代表了凝视型纪录片的另一种方向:反思性凝视。所谓反思性凝视,它来自客体,是一种客体凝视,它对主体产生压力和对抗,引发主体不安和思索。下面,笔者将结合被称为“神作”的《天地玄黄》进行分析。
首先,反思性凝视来自客体,客体凝视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大的压倒性力量。
《天地玄黄》由导演罗恩·弗里克带领摄制组穿越24个国家,历时14个月完成,没有情节,没有解说词旁白,也没有现场同期声,只有大音希声般恰到好处、深入人心的配乐。除了现代城市文明是快节奏的延时摄影,整体都是运动极为缓慢的镜头,或者固定镜头,大多近似于静态图片,观众必须凝神静观。而内容却波澜壮阔,涵盖了气势磅礴的大自然、壮观震撼的宗教仪式、朴素的原始部落、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空前的人类苦难和贫穷,它们本来各自独立、不相关联,但被导演以深沉的宗教式的巨大悲悯融汇在了一起。这部作品几乎就是对地球和人类的凝视。但与观众面对《雨》《小宇宙》《迁徙的鸟》《尘与雪》的沉浸不同,这儿的凝视将陷入全新的遭遇。
影片第一个段落是喜马拉雅山脉和珠峰,共五个镜头,第四个镜头有缓慢的上移,其余都是固定镜头,就像几张摄影作品。同时,除了第二个镜头是一个深山腰部遥远寺院的半俯拍,其它都是接近平视的镜头,没有珠峰常见的高不可攀的仰视。其中第四个镜头是珠峰北坡,镜头非常缓慢地上移,直至视线与峰顶平齐,最后越过峰顶。珠峰的影像太多,但本片一出场就体现出一种完全迥异的气质,不关乎风光,不关乎风雪严寒,不关乎探险,也不关乎朝圣,只有长久的凝视。
但是,喜马拉雅和珠峰作为地球的最高象征,它昭示出这是一场最顶级的凝视,超于万物之上,是对天地宇宙的宏大凝视。凝视这样的对象,创作者和观众一方面似乎可以用平视镜头升华自己的视野,感受自己仿佛站在了与被摄对象同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关键,面对地球的最高象征,凝视者是否真的可以与之势均力敌而坦然凝视?显然不能。虽然几乎可以平视珠峰峰顶,但它的坚硬质感、磅礴凌厉、地球之巅的份量,却有一种先天的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使观看者觉得压迫,感到自己也处于被它凝视的状态。凝滞的固定镜头确证而且强化了这种效果。于是,这就成了一场创作者和观看者与客体珠峰的互相凝视,或者说对视。
与前面所述的《雨》《小宇宙》《迁徙的鸟》《尘与雪》等不同,跟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也完全相异,这儿的凝视,没有沉浸,没有温暖和惬意,没有天人合一的互相融合,只有异质性的对峙和客体凝视的压迫。
跟观众和创作者的凝视相比,《天地玄黄》里的客体凝视要强烈得多。当观众跟随摄影机站在夏威夷高高耸立的火山坑顶部边缘,脚下的火山坑硕大无朋、深不见底,旁边深黑色的灰烬冒着热气,无限深远处来自地心的红色岩浆在汩汩流淌;同样在夏威夷,白云一望无际,像海水一样铺天盖地,奔涌而来,转瞬之间,眼前的群山消失无影;偏远的大海边,古老的生物就像一个活化石蹲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些时候,与开片的凝视珠峰一样,观众很难像平时看风景那样以超然的心境来欣赏它们的壮美,因为你碰到了对方的强力凝视,那象征着地球洪荒伟力的火山坑、云海,还有穿越无数世纪时光的古老生物,它们如同可怕的黑洞一样正在凝视你,似乎时刻准备将你吞噬。本片中其它场景,如浓烟直窜云霄的科威特油田大火、触目惊心的巴西贫民窟、印度加尔各答的巨型垃圾填埋场、机械运转的城市文明等,这些人类巨大的灾难、悲伤、困境同样以客体的形式凝视着观看者。
不过,《天地玄黄》中更直接、更具冲击力的客体凝视来自人物,也就是人类自身。原始部落呆滞的土著民、巴西卡雅布族透过丛林向外凝望的小女孩、东京地铁熙熙攘攘人群中的女学生、印度垃圾填埋场里的女孩、泰国曼谷的站街女、柬埔寨一堆炮弹边的士兵、年老的修女、伊朗黑巾遮面的年轻女子、恒河边含泪忧戚的老人——所有这些人都直接面对摄影师的镜头,直接面对观众的眼睛。换言之,他们和她们都直接凝视着观众的凝视。除了这些现实世界的人物,还有来自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中的受害者的凝视。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柬埔寨金边监狱博物馆,作为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遍地是头骨、四肢骨,墙上是千千万万死难者的特写照片,他们和她们以悲伤、惊恐、绝望的眼神回眸这个世界,直视着观众,极具震撼力。
其次,通过客体凝视这一手段,反思性凝视纪录片的目的是促使主体反思自身。
20世纪最著名的凝视研究者拉康和他的发扬者齐泽克曾对客体凝视及其作用有精辟的论述。齐泽克指出:“拉康有两个凝视理论,第一个是从‘镜像阶段’的论文发展而来,第二个则是《讲座VI》。”与早期镜像阶段的主体凝视不同,拉康的思想在晚期发生了转向,强调凝视来自客体,以客体的凝视彰显主体的匮乏、贫困与分裂。“在拉康看来,主体终其一生处于匮乏、短缺、求而不得的状态,而来自客体的凝视正是一张诱惑的欲望之网,它诱捕主体的陷落,却也昭示欲望自身的空空如也;正是在客体凝视与主体眼睛构成的悖论关系中,主体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分裂、不稳定与不一致。”③
齐泽克认为希区柯克的电影完美地诠释了这种客体凝视的反思性。例如,《精神病患者》中著名的浴室谋杀,诺曼·贝兹将装有玛丽安尸体的小车推进沼泽地埋藏,小车滑进沼泽的过程中却突然停顿了。对此,齐泽克指出,这一销毁罪证瞬间的停顿场景,就像赫然的目光射向银幕前的观众,对观众进行着客体凝视。凝视的直接结果是,这一停顿竟然令观众心里产生了与诺曼一样的担心和焦虑。接下来,它引发不安,逼着观众审视自己看似中性的旁观立场,发现了自己与诺曼相同的欲望,自己的纯洁性因此被玷污。
所以,客体凝视的意义在于引起主体反思,“这一超验的、来自客体的、引发主体贫困的视线,为主体的另类认同、为艺术的反思性批判,开辟了新的理论场域”④。
本质上,反思性客体凝视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所以,齐泽克为自己分析希区柯克电影的文章取名为“在他咄咄逼人的凝视中我看到了我的毁灭”。同时,它更是一种解放性力量,促使观众反省自己的生存之境。
在《天地玄黄》中,不管是超人类的大自然,还是空前的人类苦难,这种来自客体的强大凝视都令人不寒而栗。面对地球天坑般的火山、飓风般的白云浪涛、与时间同行的生物的凝视,观众只能心怀敬畏,惊异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宇宙时空的古老和宽广,感叹人类的渺小,从而更好地保护大自然。而来自人类巨大苦难的凝视,尤其是那一张张生动鲜活却空洞、麻木、恐惧、无助、绝望的眼睛,像一把把利刃直刺进观众的心灵,对身处和平安全环境的群众产生巨大冲击。在印度的垃圾填埋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还有牛、狗、猪、猫,大家都心无旁骛、手脚并用地挖刨着垃圾中的可用之物。在这个垃圾场中,摄影师拍到两组凝视镜头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在她稚嫩却一直茫然表情的最后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展现了淡淡的、本能的羞涩。这是人类之殇、天地之殇,观众只有无以言表的悲怆、大恸,继而升华为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感和崇高感。
面对大自然和人间悲苦的压迫性凝视,《天地玄黄》的导演认为,宗教或许是一种重要的救赎方式,所以,片中展示了大量的宗教圣地和虔诚祭典。影片开头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全片第二个镜头,巨大的高山峡谷占据整个画面,视线的焦点被引往半山腰简陋的西藏寺院。与深色的看不到顶和边的绵延山脉相比,寺院就像几个积木玩具。但它的存在,使画面油然而生地发出一种力量,是对这个无穷压抑的蛮荒般的深山世界的打破和超越。一只雄鹰围绕寺院盘旋,增添了生机,凸显了寂寞,也升华了信仰。正是有了这个寺院镜头,后面紧接的镜头几乎平视地越过珠峰峰顶也就顺理成章,信仰的力量可以飞越无限。只有这时,人类才可以从容地面对所有对抗性的客体凝视。
五、创造审美世界
纪录片纪录现实、探索自然、挖掘历史,具有为时代存档、传播知识、社会教育等重要功能。而《雨》《持摄影机的人》《小宇宙》《迁徙的鸟》《尘与雪》《天地玄黄》等凝视型纪录片则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创造审美世界。
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认为,艺术作品在感性、再现、表现三个层面以外,还有一个第四维度,也就是艺术的最高价值应表现出形而上的特质,即审美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黑格尔、叔本华等认为美的本源是理念、意志所不同,杜夫海纳认为,一个审美的世界、一种宇宙论层面的“世界的氛围”更具有形而上学前景,审美世界比逻辑世界、科学世界、现实世界更有意义,更接近和显现真理,它可以使自我完满而深刻,并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基于此,杜夫海纳强调,艺术除了体现创作者个人和时代的精神,除了结构分析、美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浑然的审美世界,呈现宇宙论层面的“世界的氛围”。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无蔽意义上主客体分离之前的澄明的原初世界,即存在的真理,“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⑤。波兰现象学家茵加登在《论文学作品》中称之为围绕作品的一种独特气氛和光辉。也与我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意象世界”一致。
审美世界的核心是情感特质,杜夫海纳认为它是“辉煌的感性”之内在形式必然性的最高形态。“审美价值表现的是世界,把世界可能有的种种面貌都归结为情感性质。”⑥而这种情感是先验的,“审美经验的独特性在于情感的先验性,先验性贯穿审美知觉的始终”⑦。情感的先验性是主体和客体共有的确定性,并具有本体论的崇高地位,人与世界因此而相连相通,融为一体。就像伤春惜时、登高悲秋并不是所谓人类的移情所致,而是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先天都蕴藏有这种情感。
凝视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情感,因为它是用心在看,而不仅仅是眼睛。正因为这种深情看世界的方式,凝视营造的是一个“世界的氛围”,一个灿烂的整体,一个审美世界、意象世界。常态的看是点状或者线性的,但凝视却如同阳光和海水,浸润和渲染着整个世界。在这里,所有事物都相融相通,如同普鲁斯特建构的凝视审美大厦。
注释:
①②⑦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115、495页。
③④ 刘昕亭:《齐泽克的凝视理论与电影凝视的重构》,《文艺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0-101、102页。
⑤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册,孙周兴选,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
⑥ [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