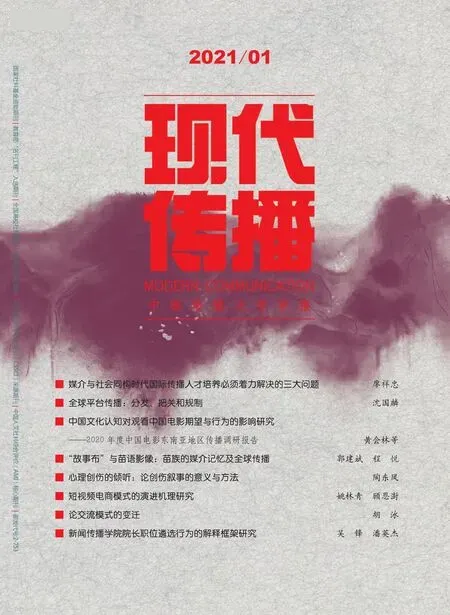从异化现实到超越拟态:后视镜视域下的网络直播
■ 王建磊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视听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不断演进,不但暗合了媒介的“补偿论”和“人性论”,还以全新的范式与媒介观成为人们情绪表达、社交行为、生活理念、集体行动等新的参考点——本文以此论断展开倒推,在后视镜理论视域下,将网络直播作为审视对象,来探讨一个类似传统媒体命运的话题:网络直播是继续内嵌于我们的社会结构蓬勃延伸?还是注定成为不远未来的后现代乡愁?
一、 倒退的后视镜:旧环境里的直播
后视镜(Rear-view mirror)的概念最早由麦克卢汉在其《开脑术》(1967)的演讲①中提出,核心意思是说环境中的人只能看见旧环境,而看不见新环境。旧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熟悉感和参与感,在旧环境的视线牵引下,新媒介均已以旧媒介为参照而出现。后视镜可以作为认识新媒介的方法论:即以过去的旧媒介作为索引来解锁新媒介。
正因如此,当我们开启了“后视镜”观照直播,大致可以追溯至电视媒介时代重新建立认知链:1936年11月2日,伴随着BBC对伦敦郊外一场规模盛大的歌舞的转播,真正应用意义上的电视媒介正式诞生了。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甫一开始就是以“直播”的形态出现的——前方的摄像机通过电缆把信号传给电视台,电视台同步把信号转播出去,再被个人电视机所接收——这种“一播而过”性与电视本身的构成装置密不可分,而其同步感强、真实记录的特点使其很快被投入到体育运动、政治事件、社会活动等领域,在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乃至人类登月等事件中大放异彩。可以说,电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了这一媒介的技术规范与认知标准:电视是与当下时空并行的媒介,其呈现的是此时与此刻的世界。
“同步性和真实性”带来的直播魅力不言而喻,直到现在日本有些电视台还保留着“直播广告”的节目:到了固定时间,模特拿着产品进行现场表演,每天直播的情形都与前一天有所不同,甚至出了差错都来不及弥补,这种保鲜极强的节目反而保证了观众的投入热情。尽管数字技术的进步早就改造了传统电视,“线性、单向性、一播而过”也成为过去时,但新闻直播和体育直播等形态依然存在着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它们所能提供的同步感,事件进程中的任何变故以及事件的终极悬念,唯有在直播中方可最快知晓——这种信息获取的“优先性”成为电视媒介在互联网时代显著的相对优势。不过,在电视直播的旧环境里,不能实时的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且内容传递与效果反馈的时间差也逐渐凸显用户控制权的不足。与此同时,直播的常态化也带来了经营成本的持续增加,尤其是大型直播给传媒机构带来了技术支持、工作分配与人员投入方面的压力,在日趋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下,电视直播不得不变得精致、庞大和繁冗,运营成本的提升和传播效果式微之间的持续失衡,某种程度上深化了电视媒体危机。
2007年6月,中国第一家弹幕视频网站:AcFun(简称A站)成立,2009年6月,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简称B站)以竞争者的姿态加入。以A、B站为代表的弹幕类型网站首先改变了内容传递与反馈分离的状况,比如用户可以随着视频播放的进度,第一时间看到其他人针对同一内容发出的评论,从而做出回应。回应的内容在时间上可能相隔数天,但在视频场景中则同时出现,相互呼应,营造了“无时空距离”的同步社交与观看仪式②。2014年1月1日,从AcFun弹幕网站中分离出来的斗鱼直播正式成立。随后,以熊猫、花椒、映客、虎牙为代表的直播平台进入公众视野。在国内,这股热潮裹挟着资本、用户(草根)和网红群体等诸多元素,成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技术与文化景观。在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地区,如美国的Meerkat、Livestream、YouTube Live、Twitch和Periscope(后被Twitter收购),韩国的Afreeca TV,日本的Niconico Live、东南亚的Yeye Live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17直播等也几乎在同一节点出现,共同构成了全球性行业浪潮。而伴随着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直播技术自然投映至移动设备(手机等)上,在实现移动式、视频化社交过程中进一步释放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介演进理论,网络直播的出现是对以往电视媒体以及其他网络视频形态的“补偿”,如降低传播成本,取消内容时长限制以及着力克服以往媒介“交互层的薄弱”等。在私人型网络直播(如秀场类)中,观看者往往能够通过文、图、语音等与直播者交互,影响直播者的表演策略或内容定位;在企业型直播(如产品发布会、教育直播)中,观看者能够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参与到信息发布中,形成多重时空的融合与对话等。另外,在交互体验层面,网络直播把互动的方式扩至全部感官的调动,连麦通话、语音指令、VR(虚拟现实)等技术形式融合进来,使互动的程度达到新高;再者,各式道具的开发应用成为最大亮点,这种虚拟的物设不但承载着一套复杂的利益分配体系,还在直播情境下变为最方便的交互载体,极大地提升了互动频率,实现了商业效益和传播效能的双赢。
综上,在后视镜所看到的旧环境里,网络直播无疑是具备超越性的。这一最初由技术引发的创新,又在技术主导下重塑了社会情景和传播生态,并赋能公众在他者的异度空间进行切换,享受“眼见为实”“实时反馈”“时空同步”等崭新的媒介体验。在当下的网络场域中,网络直播已然成为人与人、人与商品、人与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连接方式。
二、 “截断”的后视镜:走向异化的直播
如上所述,网络直播与电视媒介有着深厚的渊源,它放大了电视媒体记录、显示和再现世界的能力,改进了电视媒体单向性的不足,依照麦氏的媒介四律③,网络直播正是由电视“逆转”而来的,种种新的延伸与增强不断带给公众自信——在这样的技术包裹与文化氤氲中,人们往往被科技延伸的好处所麻醉,而媒介的“截断”机制(延伸的相对状态)恰恰是要提醒:网络直播的出现促使我们同之前的社会文化、个体生活等产生了哪些割裂?
伴随着各类直播平台成为资本的追逐对象,直播内容越来越趋向以“打赏”为目的,参与其中的男女主播在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之后,便不再从才艺和内涵上发力,他们迫不及待地被“同质化的网红长相和卖萌献媚”的获客策略包装得千篇一律,然后投入到“歌舞直播—用户打赏—平台分成”的流水线上。我们必须看到,因为普罗大众的参与,旅游见闻、商场购物、田间劳作、街头表演等不足为奇的内容呈现于斯,由于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加上创作者在思想、知识和媒体素养层面的差异,也导致输出的内容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即便不是“秀下限”的操作,当流水化的“C喱C喱”“鸭子舞”等充斥着网络视听世界,这些非事件、非共相的奇观影像成为普遍的表达方式,现实主义的本质真实就逐渐被奇观逻辑所取代。所以,当下的网络视频直播并不是真实生活的翻版、改良,而是经过视觉化修辞的伪经验生产。不管是作为纯个人娱乐,还是一种身心投入的严肃消费都清晰地指认:直播并不是生活的摹本,生活亦不是直播的写照,负载着商业驱动力和技术赋权的直播行为在看似真实的传播情境中却渐次走向图解真实、曲解真实、窄化真实的命途。在一切表演、虚构、设计显现得无比真实之际,现实图景与直播画面就愈发走向异化,走向割裂。
三、 “反环境”的后视镜:重塑场景价值的直播
认识到网络直播的文化弊端和其对社会认知的“截断”,在被技术殖民的“拟像”时代是极其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对技术发展保持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进而增强人们对媒介的控制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论也可视为应对媒介的“截断”机制提出的补救性措施——鉴于我们总是在事后才感知到媒介的真正影响和价值所在,那为何不直接营造出一个去掉复杂的现实干扰的人为环境?
1968年,麦克卢汉把这一构想在《通过消失点,诗画中的空间》一书(与哈利·帕克合著)中提了出来,并将其命名为“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or counter-environment)”④。“反环境”由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艺术家所创造,艺术家凭借对技术冲击力的天然免疫机制,人为修正了新、旧技术(媒介/环境) 交替过程中产生的感官失衡现象,故而能够成为预警系统的建构者,媒介影响的检验者以及媒介环境的批评者。⑤麦氏反复重申,“避开任何时代新技术的粗暴打击,充分有意识地避开新技术的侵犯——艺术家的这种能力是由来已久的”⑥。所以一旦由艺术或艺术家建构出一个“反环境”,那么其作为工具和标尺来检验媒介后果的功能就得以实现。“反环境”与“后视镜”一样,要求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对旧媒介进行审视,提供的同样是一种“回望”视线。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视镜”聚焦过去的坐标是现在,而“反环境”的坐标是未来。如按照“后视镜”的视角聚焦直播,要揭示的是网络直播与之前电视直播的功能差异,感受媒介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冲击;而按照“反环境”监测直播,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新媒介所创造出的独特价值究竟是什么,以使得它能够立足未来。
首先,站在未来的视角回望直播,可看到在技术的支持与改造下,网络视频直播成为包含了实时影像、弹幕文字、道具图片、用户控制面板等多种元素的超级媒介。即使除去参差不齐的内容,这样的媒介在交互性和可玩性上获得极大改善,而且所有的玩法和交互主体被安置在一个个直播间内,直播间成为人们的意识在场、数据在场的新场景。当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用户)在同一个直播间叠起层层弹幕,或使用道具支持打赏,或响应号召下单购买……这种情形让我们想到了凯瑞(James W.Carey)所言的“仪式”: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⑦。直播是把“观影和对话两种生活仪式重合在一起”⑧的仪式,通过此,“人类以互动的方式赋予这个灵动而又顽固的世界以足够的凝聚力(coherence)和秩序,并以此实现他们的意图……这是传播的仪式观,它强调的是创造一个有凝聚力的世界”⑨。直播媒介正是在营造社区活力方面不遗余力:一方面,主播通过公告和定期播出的形式向用户传达“约会意识”,又通过频繁的点名,感谢为其打赏的用户,最终达成凝聚着情感投入的召唤仪式;另一方面,用户则通过对主播才艺和容貌的认可而形成临时群体,又以固定语句如“老铁、双击、666”这样的网络表达强化共同体概念,形成相对稳固的守护仪式;最终双方借助“鲜花、豪车、飞艇”等商业符号完成数字签章,在一个个虚拟直播间形成凝聚,掀起狂欢。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言的中世纪“第二种生活”相比,在直播间这样的虚拟情境中,参与者更加注重在精神快感上深化狂欢的程度,比如随性自由的表达、纯欲望的宣泄或在虚拟部落中寻求群体的认同与共鸣。依此角度来说,直播间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生产信息,而在于重构了人们的交流情境,塑建出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仪式。
其次,按照麦氏的“反环境”理论,“艺术家在我们的社会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创造了反环境,并使我们对环境的感知成为可能”。这里的“感知”是人为地去挑战身处媒介情境而不知的“麻木”与“迷恋”,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对媒介后果进行检验,并提供对新媒介的真正感知。然而,也正是从艺术的角度视察:网络直播反其道而行,摒弃了各种传统艺术规范,不追求合乎影像传播的内在规律,同时将视线引向世俗的现实世界,“把源于日常生活中惯常事物的能指并置在一起,不刻意追求崇高的目的和高尚的品味”。每一位普通的(不带商业目的)直播创作者把吃饭、走路、生活、工作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搬上了直播,像是一出出诡异的“行为艺术”展演——这是否是更加艺术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学术界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批判其毫无意义;另一种则遵循后现代逻辑,认为这种无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换言之,这些普通用户无意中扮演了“清醒的艺术家”的角色,而这些无聊的场景及展演恰构成了直播的“反环境”——进一步窥探其中发现,尽管人们并不对他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有过多关切,但却对介入他者生活的“机会”充满兴趣,当网络直播充当了“技术介入”的方式,那些充斥着平凡琐碎的个人展示和夸张、离奇的噱头等没有必然联系的片段场景,却适时给无数个屏幕端外的用户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网络直播的普通践行者就是缔造“反环境”的艺术家(但他们自己对此浑然不知),他们使直播的真正艺术价值——“介入与穿越”昭彰显著。人们通过同步沉浸、即时对话、道具加持、感情投入等方式介入到他者的生活流,或瞬间穿越到此时异地的时空情景,沉浸式地窥视他者的日常生活,意淫帅哥美女的陪伴围绕等,进而使现实世界中的失意、压抑和苦闷获得短暂的释放。
在以上论述中,网络直播其一是创造了崭新的社交情境,其二是提供了介入与穿越的艺术功能,如果对这两者进行一个恰当的整合,本文倒十分乐意采用罗伯特·斯考伯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所使用的“场景(context)”概念,它是指“基于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提供的一种应用技术,以及由此营造一种在场感……与实时感知、实时搜索、实时处理等联系在一起”,有别于梅罗维茨“作为一种感觉区域,即信息流通型式的场景(situation)”。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越来越成为承载人的需要、生活空间、市场价值的新介质,网络直播技术的出现也极大丰富了场景的构成形态与功能属性。如当下大部分直播平台为响应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以“带货农产品”“直播特色旅游”“扶贫直播”等多种方式大力推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具体场景的打造所带来的“双效”后果是显著的。在具体的社会指向与政府引导下,直播平台在提升产品与用户之间的黏性,激发社群活力,提高人与人、商品与人的匹配度方面的价值得被深度挖掘,而用户也更愿意为这种特定的场景买单。此外,场景并非是对现实的解构,接入场景将成为政府、公司等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如西安交警网络直播车管业务,对接了公众(司机)对互联网政务的期待,也体现了政务服务的与时俱进和以民为本;又如某独立咖啡品牌在运营上采取直播和外卖结合的方式,用户可以亲眼看到咖啡制作的全过程,从而强化服务的专属感。由此而言,网络直播的场景价值不能单纯借助技术升级实现,还需辅以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等多重层面的规制与牵引。由于“反环境”在“后视镜”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环境预测的功能,即负责预判新媒介的发展走向——这也是“反环境”相比“后视镜”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此将场景构建赋予直播最重要的“革命性功能”:由普罗大众输出的直播场景具备开放性好、适配性强的特点,既可以让人们在繁芜的网络世界中自由穿越,又提供深度介入和干涉的手段,其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就是着力与各行各业融合共生,并藉此变现其社会、商业价值。
四、 流动的“后视镜”:回归工具理性的直播
“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着走向未来”——这句箴言告诉我们的是:后视镜作为一种媒介认知的工具,包含着关于媒介和历史的一切,也包括媒介当下的及长远的影响。可以说,后视镜理论最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回望”的视角,“以史为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学术反思路径。但要注意:后视镜只遵循一个时间线上的天然尺度,提供的参考坐标只有现在和未来。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历史,会再次麻醉我们对当下环境的感知,从而忽略新的向我们步步逼近的“窃贼”。因而,对“后视镜”的使用也要考虑到时代和概念产生的语境限制。
第一,后视镜习惯在“历时”的维度上使用,即在时间纵轴上移动,用以阐释媒介的演进规律。为了从这一传统视野中解放出来,或可增加一个空间维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在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流动、技术流动、符号流动等各种“流”的作用下,一种以流动为主要特性的新空间形态产生了,学者卡斯特将这种新空间形态称为流动空间,空间的“流动化生产”构成了网络社会最基本的空间实践。所谓流动化生产,针对直播而言,是指直播使人们或组织之间的交往行为不再局限于某一固定不变的空间。大街、火车、公园、演唱会……都被整合进虚拟直播间里供消费和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物理空间的塌陷:从上一秒的白宫到下一秒的难民营,从上一秒的哈佛课堂到下一秒的乡村小学,娴熟的切换式消费让时间消灭了空间。在直播的世界里,时间不再严格按照学习、工作、休息等模式进行线性区隔,也不再是标准化为抽象的数字,而是成为无差的永恒“此刻”。后果之二是进一步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场合的物理分界,尤其在移动直播的技术语境下,手机摄像头所到之处都有可能使原本的后区转为前区,这既开创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局面,也带来了大量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后果之三是空间不再是固定位置的物理地点,而是“和通信网络的节点相联系的区域构造,流动空间的结合和意义并不和具体的地点相联系,但是和处理特定通信信息流的通信网络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空间认知方式需发生转变,“今天的新型空间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真实的也是像素的……我们需要把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融态势做整体化处理,在真实的生活在向互联网上延伸,而线上的虚拟景观也在向线下渗透”的密集过程中,网络直播实际上生产的就是在同一时间连接不同地点的“新型流动空间”。
第二,“新型流动空间”的高频生产意味着直播对媒介本体的超越性。这体现在:其一,直播会超越“作为话语的新闻”——虽然直播的出现使每个人都能更方便地获得围观与表达的权利。“听某某是如何说这件事的”“看某某是如何评论谁谁的”此类的直播内容在无形中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热点,或者跟蹭一个又一个热点,一时间众声喧哗。可以说,网络视频直播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参与框架。但在流动后视镜的审视下,我们要力争跳脱“话语层面”的藩篱,否则还是以传统媒体作为标准予以回望,很难对现实有创新的解释力。其二,直播带来的空间堆积后果将超越传统媒体时代的“拟态环境”。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了“拟态环境”,指的是传播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拟态环境虽然以现实世界为蓝本,但又不是“真”的客观环境,不过,拟态环境通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决定了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今天的网络直播,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全景式、不间断的海量视频流信息(而非探照灯式的观照)“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较大限度地实现了传播内容和客观现实的一致性”,从而减弱拟态现实的影响,减少与现实世界的偏差。
第三,网络直播不只连接了虚拟与现实,输出、生成流动的空间,对接了软件与硬件,串联起主播、平台、公会等产业链上下游,还引领了从内容到服务的转变。尤其服务空间的庞大能指让我们更加关切网络直播的商业势能,当后视镜思维运用于更加广阔的空间场域,更有利于人们把目光瞄向现实世界。“现代生活已经发生在荧屏上……这决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当今的城市社会中,摄像镜头在一刻不停地记录人们的行动,无论是在大街上、购物商场、ATM的取款机旁还是高速公路上,人们的经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视觉化。而直播则是在世界视像化的基础上叠加交互,这对于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物流追踪等诸多领域来说,不失为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案。随着5G商用的普及,直播技术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基础设施的功用会被进一步强化。认清这一点,与其思考如何避免直播走向消沉,不如思考其作为一种泛工具式的存在,如何搭载各种不同的产业模块进行重组和融合发展。
总之,流动的后视镜打破了静态的时间视点,可以更加灵活地在现实空间中选择参照系。不管是媒介运用,还是娱乐、游戏、政务、教育等领域的使用,当我们把直播看作一种以实时互动为核心的技术工具,这才意味着重新回到了行业源点,才真正有可能在下一次技术革命之机,将直播作为基础工具重新集成。
五、 结语
总体而言,当我们透过后视镜回望网络直播时,等于从技术与文化的双面再度做出反思。在社会文化影响层面,网络直播展现出一定的高级娱乐样态和文化多样性,但屡屡踩线的行径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从而也导致监管机构持续对该领域保持高压。应该说,网络直播对现实的种种异化、离规必然不能持久,其创新方向离不开对社会文化和大众圈层趣向的正确把握;在技术演进层面,直播媒介对前沿科技的积极采纳及扩散,展现出良好的主体姿态,随着5G时代的到来,VR、AR技术的加持,网络直播可重塑未来的消费场景及生活场景,并适合率先引领人们沉浸到一个高度仿真甚至无需区分的立体世界中,从而代替一个个抽象的数据描述,生发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直播充满创新可能,未来会同时以基础工具和科技先锋的角色活跃于传播格局,深嵌于社会整体生态。
注释:
①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Me:LecturesandInterviews.EditedbyStephanieMcLuhanandDavidStaines.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Ltd.2003.pp.147-172.
② 谭雪芳:《弹幕、场景和社会角色的改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第140-146页。
③ 麦克卢汉于1975年在其《McLuhan’s laws of the media》一文中提出“媒介四律”:放大(amplification)、过时(obsolescence)、再现(retrieval)和逆转(reversal)。该文载于《Technology and Culture》,January,pp.74-48.
④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511页。
⑤ 刘玲华:《理解反环境——麦克卢汉媒介观的一个新链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44-52页。
⑥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ofMan,The MIT Press,London,p.65.
⑦⑨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2版),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7页。
⑧ 王晓红:《新型视听传播的技术逻辑与发展路向》,《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5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