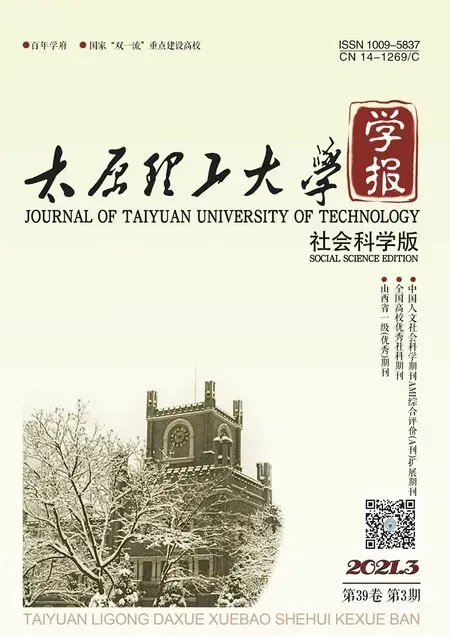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的国际借鉴及对我国的启示
李秉强,田 佳,余 静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3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这将会成为破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有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引。在COVID-19短期难以有效平抑、国际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制造2025”、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等目标的实现,要求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制造业,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不可逆转也要求我国持续地实施外贸驱动战略。由此,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实现协同推进就成为各级政府的必然选择。
关于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国内外有着大量的文献,大体可从政策演变、影响因素、国际借鉴三方面进行解析。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政策演变看,主要从产业视角和时间演变两方面展开:范文祥和齐杰[1]、彭星[2]、王寅龙[3]探讨了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悖的表现,傅耀[4]应答了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策如何助推产业结构升级;贺小勇[5]、仲鑫和金靖宸[6]、倪峰和侯海丽[7]、周建军[8]、李萍[9]、秦嗣毅[10]分别以入世、入关、历史演变的重要阶段为时间节点研究了各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演变。从影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调发展的因素看,通常认为应该重点考虑战略重点[7]、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11]、主要目标[12]、外交合作[13]、社会因素[14],以及其他国家政策[10]等。对于两者实现协同发展经验的国际借鉴相对较多,侧重于考查不同主体如何影响协调,如行业协会[15]、政府[8]、企业[16]。我国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进而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采取了组合政策以加快推进经济提档调整,而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同推进应该是重要举措,但目前没有检索到基于我国现实和国际借鉴进而提出应对举措的文献。为此,有必要在解析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提出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应对举措。
二、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同向驱动,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国际社会经常以贸易为手段对我国进行显性与隐性的制约,如2019年5月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床垫征收1731%的额外税率。事实上,我国自1995、2006年成为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被调查最多的国家以来,均分别连续25年和14年位列全球首位。对我国实施限制政策的主体,不单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还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近年已超越各发达国家,成为对我国实施调查最多的国家。究其原因,除“中国威胁论”被持续当作武器外,还应该与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非协调发展直接关联,故此有必要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解析。事实上,不同政策的目标导向直接制约着政策协调的绩效,而政策制定者是否统一会造成管理权限的差异,且各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为此,本文从政策目标匹配性、管理部门协调性、参与主体融入性等方面解析我国两大政策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目标匹配性
按照WTO规则,贸易政策要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而产业政策关注的焦点为国内产业的发展,即两者出现了国内和国际经济协调的目标差异,由此,特定国家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就应该是不稳定均衡。为促使本国产业发展而实施的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贸易政策,必然会随着产业政策调整而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与一个区域或国家更为关注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进而“委托—代理”难题的博弈在此凸显。从我国两大政策关系看,基于WTO规则许可视角,应该重点解析的是在国家主权范围之内,补贴政策、汇率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环境资源保障政策等方面与我国产业政策之间的适配性[5]。事实上,WTO规则中涉及的贸易政策,在农业、工业纺织品业、汽车产业(在我国属于幼稚产业)、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诸多方面与我国产业发展所属的阶段存在明显的差异[1],从而导致我国的贸易救济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性有待提高。由此可知,我国两大政策的目标存在显性相悖。
(二)管理部门协调性
我国的产业政策主要由发改委、经信委、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等联合发布,而贸易政策的管理机构为商务部及其相关部门。对于产业政策而言,通常为发改委和经信委牵头,其他职能部门在政策保障上给予配合,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循环系统,但这些部门与商务部及其相关部门不存在行政上的辖制关系。由此,政策决策者的不一致必然会带来行为上的非协同,表征为管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1)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贸易政策的管理部门,均会以维护本部门的权力边界作为行政指南,在协同两大政策过程中容易出现有效执行不到位的情况;(2)不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企业信息掌握程度上会存在显性的差别,特别是商务部及其相关部门对于企业信息的把握可能相对不够,在事前科学甄别、事中监管纠错、事后绩效评测和风险监管等环节难以做到有效预警和评判。事实上,辖区竞争和诸侯意识在我国各个部门普遍存在,而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出自不同部门,制约了两大政策作为一体化出现的可能,由此可见,管理部门协调程度亟待加强。
(三)参与主体融入性
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实现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对区域经济的了解与掌握程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微观主体和行业商会等中观主体积极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对接。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转变时期,但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的属性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我国诸多行业的龙头企业相当不明显,即行业代表性企业难以有效筛选。一旦遭遇外国或区域性组织实施非公平贸易政策时,不愿或无力上诉成为我国外贸中的痛点,这在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的驱动下会导致同类或同行企业发展受阻。在欧美国家,行业协会或商会的议价能力较强,特别是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能够积极应对“不公平贸易”[15],但我国该方面的相对缺失导致企业难以有效对抗不公平的贸易争端,且政府部门也难以有效掌握行业的发展动态。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政策的体内循环属性[17]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民众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反馈的渠道。这必然不利于两者实现协同推进,即参与主体融入明显不足,会成为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重要钳制。
三、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的国际借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知,产业发展与贸易举措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贸易政策通常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存在的,即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透视产业政策。从现有经济格局看,美国和日本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三经济体,美国经历了由农业国向全球霸主转变的过程,日本经历了二战后经济重建到快速崛起的过程,均与实施了组合式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直接相关,其两大政策协调过程有着较强的代表性。为此,本文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以产业政策为主贸易政策为辅简要说明两大政策协调的国际经验,以期为我国两大政策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一)美国经验
1.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演化
作为支撑美国建国以来发展的国民经济学说[18],具有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统一、利益和谐、国民银行等基本观点的美国学派植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且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产业政策也与该学派的主要理念一致[19]。从美国发展历程可知,其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还是自由政策与相关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环境息息相关,即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前提条件通常为:与其核心利益没有显性的冲突。事实上,自2000年来美国各届政府采取的贸易政策,如小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奥巴马政府的“两反一保”、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均呈现出较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6,12]。在具体分析中,可以以美国重大事件的时间点为临界值来入手。对于美国具体存在哪些重大历史事件,目前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罗斯福新政促使美国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泥潭,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导致美国霸主地位逐渐坍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制造业战略重调,均可视为美国产业和贸易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为此,以1933、1973、2008年作为临界值进行剖析。
第一阶段为1783—1933年,以高关税、发展幼稚产业、保护本国市场、行政指令发展特定产业为两大政策的主要特点。爆发于1776年的南北战争,其根本缘由为南北经济结构差异所导致的“工业立国”与“农业立国”的分歧[14],这在美国建国初期出现的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也可见一斑,且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论随后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战略。美国的高关税保护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直到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的高关税政策(《斯慕特—霍利关税法》)失败。但是,就总体而言,该阶段主要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并通过补贴等政策助推本国产业发展。
第二阶段为1934—1973年,实施了低关税政策,在产业政策上凸显对基础研究、基础技术与通用技术的扶持,以及强化国家安全的产业创新体系构建。在胡佛的高关税政策失败后,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互惠贸易法案》,开启了美国的低关税政策之路。事实上,全球经济大萧条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而实施低关税政策也有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从实际操作看,二战前后的主要举措是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以推进自由贸易[7]。如1962年出台的《贸易扩大法案》,旨在打开欧共体市场进而推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建设,这可认为是受到西欧、日本经济威胁而做出相应反馈的一种贸易举措。与此同时,通过马歇尔计划、洛美计划、道奇路线、第四点方案、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等,积极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开拓市场。
第三阶段为1974—2008年,是贸易政策的调整阶段。非关税取代关税已成为国际贸易政策的通行做法,由此美国采取了以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特征的新贸易保护政策。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是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日本、西欧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结果,为此实施了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且限制进口的“公平贸易政策”,以强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力度,如1974年出台的《贸易改革法》。在产业政策上,采取了加快创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创新发展市场制度体系、营造公平竞争和良好合作环境等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政策导向[11],同时凸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杜邦法案》(1980)、《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1982)、《创新美国》(2004)、《超越风暴》(2005)、《美国“竞争”法》(2007)。
第四阶段为2009年至今,以奥巴马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为基本标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制造业“空心化”等现象日益明显[15],这在次贷危机中得到集中体现,由此如何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鼓励先进制造业,成为美国近期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主旋律。事实上,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还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均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本国制造业而采取了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奥巴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皆以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实施国家创新为核心,并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为主要举措实施贸易保护。从现行美国产业政策体系看,总体可分为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他产业政策等方面,其实践基本融合了汉密尔顿的积极干预论和杰斐逊的有限干预论[8],如特朗普政府的产业政策呈现出保护主义、战略性减负、选择性干预等特征[20]。在出台《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者战略》等扶持本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同时,以“退群”为主要手段实施贸易保护和维护本国利益,如,在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武器贸易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组织。此外,COVID-19疫情出现后,特朗普政府积极加强“太关键而不能失败”产业的扶持,并将其政策着力点直指中国[21]。
2.主要经验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以服务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为主要导向。在1973年前以关税作为主要的贸易政策,之后则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这与全球贸易政策走向保持了一致,其政策逻辑是以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其采取产业政策主要是实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市场扩张、基础设施升级,而实施相应的贸易政策则主要是实现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贸易秩序。美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专业的协调机构。从政策导向看,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贸易政策主要服务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差异,这必然会导致两大政策在利益诉求上存在着显性的偏差。1980年成立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由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办公室更名而来),直接对总统和国会负责,是美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总谋划者和协调者,其主要职责是为贸易政策提供专家意见。两大政策由同一个部门制定,能有效地消除政策立足点不同所导致的矛盾。
二是相同的利益集团。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科技企业近期以Microsoft、IBM、Apple、Alphabet、Facebook、Amazon、Intel、HP、Cisco、Oracle等为代表,既影响着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其政治格局。事实上,2019年二季度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财富相当于中产和中上阶层的总和[22],而这些富有人群即为美国的精英阶层。产业政策的主要指向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而贸易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需要,由此这些精英阶层将在此起着主导的作用,即利益集团是相同的,进而有着较大的利益驱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实现协同。一旦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出现较大幅度偏差,精英集团会积极向美国的各级政府提出相应的诉求。
(二)日本经验
1.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演化
与美国经验相似的是,日本的产业政策也是与贸易政策融合在一起的。日本的真正发展源自于明治维新,但随后较长时间国际地位相对偏低,故仅从二战后剖析其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演化。对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哪些阶段,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百度百科认为经历了战后恢复、高速增长、低速增长、长期停滞等阶段[23],李萍[9]认为存在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两大阶段,陈建安[24]认为经历了复苏、高速增长、稳定增长、萧条、重振等阶段。从上可以看出,对于发展阶段时间节点的划分差异,主要集中在何时实现了战后复苏,但李萍[9]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基准的划分方法则有明显的不同。在随后分析中,基本采取了陈建安[24]的划分法。本文选择1992年作为日本“失落”的临界值,这与泡沫经济在1991年2月结束直接相关。
在经济复苏期(1946—1960),以恢复遭受二战重创的国内经济为目标。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物价飞涨、供需矛盾凸显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基本处于废墟与重建边缘,且在贸易政策上以服从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安排为主要导向。在政治体制改革、美国全面扶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独特文化等驱动下[25],在较好的工业根基和相对高的人力资本存量等现实基础下,通过价格控制、外汇管制、税收优惠、银行融资、金融倾斜等手段,集中资源发展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缓解国内尖锐的供需矛盾。在该阶段,产业政策以直接干预为主,有选择性地发展特定产业。从贸易政策看,基本遵从了“幼稚产业论”的政策主张,即国内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要求采取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战略。
在高速增长期(1961—1972),日本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61年的3.24%增加到1972年的8.42%。该阶段的产业政策以调整国内企业间关系为主,主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官民协调、大企业合并与整合、凸显新型支柱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重化工业驱动产业进步等方式[26],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对日本经济潜能的挖掘和产业结构的重塑起到了较好的指引作用。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主要采取了出口补贴和汇率补贴等手段,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以拓展国际市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
在平稳增长期(1973—1992),日本经济在全球的地位稳健提升,且在1992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5.36%。在该阶段,日本严格控制过度的产业保护和市场干预,其产业政策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由政府调控为主转为市场主导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将以发展重点产业为目标改成各大产业全域性发展;三是矫正主导产业的发展属性,即将侧重于发展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转向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从贸易政策看,进口政策主要围绕“开放国内市场”展开,出口政策以鼓励产业结构调整、凸显外向型产业投资、强化“海外投资立国”、援助带动出口等为主[10]。
在经济萧条期(1993—2012),由“平成景气”引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在较长时间没有走出经济泥潭,被称之为“失落的二十年”[27]。但是,学术界对日本是否存在“经济失落”,有着较大的争议,如张季风[28]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在该阶段,日本的贸易主战略由“贸易立国”转变为“投资立国”,即由贸易主导型向贸易与投资共同驱动让渡[29],在进行大量海外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如2007年日本在美国的专利授予率高达42.9%,而德国、英国、法国的专利授予率分别为11.64%、4.23%、4.03%[30]。从产业政策看,其实施了渐进式创新的国家主战略,以环保、生命科学、电子、尖端基础材料等产业作为主要突破口,加快科技创新的推进力度。事实上,日本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可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持续增加得到佐证,如2000—2012年间共有11位获得该奖项,其中,日本籍学者8位。
在经济重振期(2013年至今),以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作为发展的主站略[29,31],即实施大胆金融政策、宽松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战略,且在2020年9月上任的菅义伟也明确表示“继承安倍”的政策。此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均包括在经济增长战略中。从产业政策看,主要包括促进中小微企业或经营者生产率提升,通过强化企业收益和加大投资实现生产率革命,构建society5.0和颠覆式创新推动生产率革命等三方面,即生产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举措。从贸易政策看,主张以TPP规则作为引领,加快推进区域自贸协定战略[13],以加强与亚太、东亚、欧盟的区域合作为主要切入点,服务于日本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
2.主要经验
二战后,日本处于经济重建阶段,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提升后实力大为增强,但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导致其发展陷入了相对停顿,而近期又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作为战败国,日本在较长时间内没有独立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及其他政策,即使到目前,其主要军事力量依然称之为自卫队。受制于国内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互依存,而2000年通产省变更为经济产业省更是凸显了其对产业政策的重视程度。日本两大政策协调发展的主要经验如下。
一是有力的政策协同管理部门。经济产业省(前身为通产省)是日本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主要部门,管理着全国的经济、贸易、市场流通等各项活动,产业属性相对于贸易属性更为明显。经济产业省所属的经济产业政策局和制造产业局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发起方,所属的通商政策局为贸易政策的主要发起方。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出自同一个部门,能有效缓解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摩擦与争端。
二是有效的官民协作推进机制。日本重大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断发生,使得各级政府和民众具有相当强的危机意识[32],因此如何实现官民协作、官民协调就成了解决国内外各项事务与危机的重要方式,进而构建了相对完善和快速响应的官民协作推进机制。日本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作推进机制,以经济产业省为主导,囊括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退休人员等各方面的参与主体,能够较好地实现上传下达,凸显协调的成效与时效。
四、国际经验对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发展的启示
产业和贸易的相互依存性要求两者在政策上实现协同推进,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破解新常态、实现有效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而美国与日本的成功经验将为我国实现两大政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从我国两大政策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看,不同政策目标显性相悖可通过统一的管理机构实现协同。为此,结合我国实际和国际借鉴,从构建快速响应机制、提升制造能力、强化政策实效、改善内外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举措。
(一)加快构建政策协调发展快速响应机制
日本和美国能较为有效地保障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同驱动,其最为核心的应该是有着掌控两大政策的统一机构,如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日本经济产业省,能将两大政策非协同产生的矛盾进行内部处理。与此同时,由普通民众、学者、大型企业、工会、行业协会等协同参与构建了较为系统的中观、微观响应体系,特别是大型企业和行业协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认为美国和日本在响应机制上,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已经体系化,值得我国各级部门特别是中央部门深思。
从我国实际看,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者隶属于不同部门,不利于两者实现快速响应,这就要求中央政府采取相应的方式打造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命运共同体。如,建议在国务院设置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一职能部门,以此作为两大政策的法定协调机构;此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应该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激活两大政策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的各主要参与方且形成有效的响应体系,并据此形成扁平化的直报和信息反馈系统,提升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响应效能。
(二)强化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美国南北战争后奠定的“工业立国”战略,以制造业发展和产业转型调整为基本要件,组合实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特别是在较长时间内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以发展本国制造业,缔造了20世纪以来国家的强盛。日本二战后为促进国家实力提升,首先集中资源发展基础性制造业,随后在快速发展期以制造业提升作为国家主战略,其制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均以实现制造强国为目标。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经济停滞导致东亚的“雁型”梯度产业格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旨在通过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制造业升级,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目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属性相当明显,为制造业大国而非制造业强国,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粗放型制造业增长方式直接相关[2,4]。为此,各级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配合,侧重于制造业关键技术、关键领域的突破,强化我国制造业提升的内生和外生驱动,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属性,内外双轮驱动我国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
(三)凸显适度保护加快幼稚和战略产业发展
无论是高关税政策的“美国体系”对制造业的引领,还是多维贸易保护政策和战略保护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抑或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对冲我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33],其贸易政策的落脚点均为幼稚产业和战略产业。即使是2020年9月出现的闹剧式的Tiktok收购事件,也可视为美国政府组合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发展战略产业的结果。对于日本而言,二战后以战争破坏为名和以幼稚产业与战略产业为突破口,采取配套的贸易政策积极发展本国产业。
适度保护幼稚产业和新兴产业是WTO规则允许的,但对于如何界定从来都没有明确的边界,为此我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该用好、用足、用活这一国际规则,即应该在这两类产业上加大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开发力度。凸显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强化对重点和主导产业新兴领域的识别,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以幼稚产业和新兴产业政策为指引融合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如关税、补贴等),应该是我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层面。
(四)激发创新活力,营造政策协调内外环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产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是激发创新活力,佐之贸易政策以保障国内创新的持续推进。如,美国自二战后就把创新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力图通过组合政策实现高新产业的全球霸主地位;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强化创新,且在90年代的泡沫经济出现后,经济政策重点向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倾斜,这从2000—2019年日本出现了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可得到体现。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安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标志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为激发我国发展的活力,要从内外环境的优化两方面加快科技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分别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着手,通过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强化研发创新与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激发创新活力的国内产业基础上打造出适合创新的国内环境;在外部环境营造上,实施鼓励创新的贸易政策,加快引导创新型产品,以及知识产权、技改设备等的引入,凸显我国对创新的重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