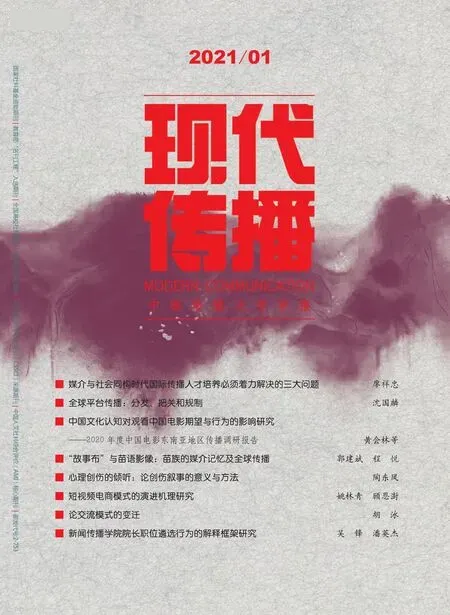走向人伦主义的关系本体论
——媒介深度融合进程中“媒介人”的人文主义思考
■ 李 智
人类媒介史不仅是一部媒介更迭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媒介融合的历史。基于人类已有的媒介实践,学界一般把媒介融合理解为媒介技术系统内部的融合。然而,如果立足当下最新媒介发展趋势,媒介融合则不再局限于媒介自身即各种媒介技术形态的融合,而是扩展、深入到作为与媒介打交道的媒介使用(操持)者的人身上。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媒介融合”之“融”是指媒介与人或人与媒介的融合,即媒介的人化和人的媒介化。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下,人与媒介相互趋近、互为彼此,合二为一而成为“媒介人”(mediator,或所谓“生物媒介”)。“媒介人”(“生物媒介”)的行将面世标志着媒介深度融合时代的到来。
一、从自然人到媒介人
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两大科学和技术在当代社会迅猛发展并日益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使物的特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人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模拟人类有机体感官的身体体验,赋予物以生物性和意识特征(包括理智能力即理性或逻辑思维能力和情感情绪),尤其是实现物的智能升级,形成“有机机器人”或“虚拟智能人”,使无机物有机化,使物在生理(生物性)和心理(精神性)两个层面上都越来越趋近于人。譬如,赋予机器以生物性,制造出具有生物性功能的类人机器人,像美国新近开发出用活的生物细胞为材料的生物机器人;进而,这些新机器类人通过深度自主学习,未来不仅可能具有独立意志和思想,更有可能会产生精神性的“自我”意识,从而成为人工自为者(agent)。另一方面,基因工程和人工装置的应用使自然人成为一个人工合成体(又称“赛博人”),即一个由人为设计而经过生理的和物理的双重改变的新种类——从自然(生物)人转变为被非自然化(即技术化)的“物质人”“技术人”“合成人”或者说“自造人”。诸如,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所倚赖的生物信息来源、改变人的遗传信息结构即人的生物属性,进而改变人的心理特征和理智能力;脑起搏器、心脏起搏器等人工装置的植入因容纳了非生物体而改变人的心理状态(包括理智和情感)。由此可见,人在生理(生物性)和物理(物质性)两个层面上都越来越趋近于物。综合来看,人与物相互构建、构成,相互改造、改变,彼此成为对方的延伸和对方不可分割之要素,并成就对方之为对方的可能性。在物与人不断相互趋近——物的人(性)化(anthropotropic)为人和人的物(性)化(materialization)为物——的跨物种演化进程中,人与物之间从目的—手段的对立走向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互利共生(symbiosis),进而达到“共同生成”(becoming-with)。最终,人(高级生物有机体)与非人(non-human,无机物机器、生物及一般物等)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日益模糊,且渐趋消弭。事实上,伴随着脑—机(人脑与电脑)接口技术的不断突破和脑机界面的逐渐消失,人与机器对话、互动,在相互作用、相互构成(互为嵌合)和共同升级、进化中终于融合、合一。由此,必然出现一种新型的人类——相对于现在的人类物种具有进化关系的未来的生命存在形式。
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新技术风起云涌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媒介技术日益转变成大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普遍性实践,人类进入到一个“万物皆媒”(人亦为媒介)的泛媒化时代。其重要的时代表征是:万物(包括人)的存在及其生命的本质不再在于其客观物质性,也不再在于其主观精神性,而在于其媒介性——更准确地说,是被媒介化性,即以被媒介所架构(framing)的方式存在着。对人来说,就是以被媒介所架构的方式存在于世,即所谓“媒介化(mediazation /mediatization)生存”。人因此而丧失了作为与物(对象、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性(地位)。在人的媒介化生存过程中,媒介与人或人与媒介相互趋近、相互内化,互为彼此、融为一体而具有同一性——媒介即为人,人亦为媒介。最终,人化的媒介或媒介化的人即“媒介人”或“生物媒介”得以面世。未来“人类”社会行将诞生一种新的社会“主体”(存在物)——“新人类”“后人类”(posthuman)①或所谓“超人类”(transhuman)②,他们便是这种媒介人。
人,从自然人到媒介人,大体要经历一个从“去生物性”到“再生物性”的技术化处理过程,先是让(自然)人脱离肉身(“离身”:祛除身体)而成为一种如“游魂”(discarnate spirit)般的纯粹的精神存在——被电子化、信息化、数据化处理的“电子精神”“精神数据”“数字化的我”(“内在的我”“精神的我”)、“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或非有机体的智慧“主体”——“2029年人类将能上传大脑的全部信息,包括感受、记忆和秉性,即使肉体不复存在,我们的意识、思维和情感将在云端延续”③; 然后,把这种信息化“精神”注入新的生物体内,与新的生物特性重新组合成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先抽离出物质、肉体再赋予建立在生物基质上的自然性或物质性具身形象的再“具身化”过程。这同时也是人类身(身体)—心(心灵)的双重技术化的过程,即主要由生物技术(如基因工程)来实施的人类自然身体及行为的技术化与由智能技术(如算法)来完成的人类智力(思维)和心灵(精神、情感)的技术化。通过对自然人类身心的双重技术化处理,人将成为一个被高科技产品——诸如各种人造器官、人造血液、人造皮肤、人造肢体、人造基因、人造精神、人造大脑等——所全副武装的人,由此,自然人演变成一种高度技术化的生物性存在(高级技术身体即智能身体或媒个化“存在”)——“媒介人”。
二、媒介人的人文主义危机
从自然人到媒介人的人类生命演化进程中,人类不断地超越自身的生物极限——纯粹的自然肉体及基于其上的本然性精神内涵都在变化。由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的介入和人工装置的植入,在自然(生物)进化和人工(技术)进化的双重作用下,人(包括体能、智能、情感意志力等)不断“增强”,人的性质包括生理性质和心理特性即身(肉体)—心(心智)两个方面因此而不断发生改变,以至于拥有一种全新的生物特性和截然不同的意识内容。至此,人在生物上的自我同一性和在精神上的自我同一性都不复存在。那么,性质改变后的人——媒介人,同性质改变前的人——自然人,是否是同一人呢,或者说,人的性质改变到何种程度上仍然是同一人,而改变到何种程度上就不再是同一人了呢?其判决性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在此,人类所遭遇到的这个自我同一性即身份认同问题关涉到了人类思想史上著名的忒修斯悖论(Paradox of Theseus)即身份认同或替换的悖论(假定某事物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它是否依旧是原来的物)。如同不断维修和替换木板及零部件的忒修斯之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不断改变生物和意识性质、特征的人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推而广之,不断改变生物性和精神性的人类是否还是人类,抑或变成“非人”或者“类人”?归之,“媒介人”还是人吗?
从根本上说,这里关涉到一个关于人的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抑或,人之为人的终极依据是什么。人(human being),当然是有人性(human)的存在者(being)。而人之所以为人,当然在于人性(humanity)即人的性质,尤其是人的原(本)来、根本的性质(本性)或者说特有的性质(特性)。归之,人在于人性,人即人性。关于人性,卢梭曾经宣称人的原始状态应该是“集一切于己身”的“纯粹自然的人”;而在当今时代,人们之所以对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所引发的危机和所带来的结局深表忧虑,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人类作为技术性存在在今天面临的自然人性(人的性质)改变、演化的恐慌和担心。正如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征服自然的最后一道界限”“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改变人类的自然本性”的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ukuyama)所言:“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④显然,福山深恐于基因工程给未来后人类带来的人性浩劫。对(现代)“技术统治”人类而人性“沉沦”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当属后现代主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他通过对“存在历史”的哲思,揭示了自然人类(本性)被技术“框架”(Ge-stell)“促逼”(逼索,Herausfordern)即被“加工”“计算”和“规划”的“退化”进程。⑤
几乎所有的人性问题都关乎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就是主张完整(完好无损)的“人性”和对“理想的人”“完全的人”“完美的人”“完善的人”——归根结底,“最具人性”的人(Humanitas)——的倡导、珍视和捍卫。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对普遍(普世或普适)而永恒的人性关怀的人本立场和人道取向,人文主义既是对人(类)自我的最基本的关怀,同时也是对人(类)自我的终极关怀。显然,无论海德格尔还是福山都是反现代技术的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是对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者。他们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乃出于对自然人性的改变(减损、沦丧和泯灭)的深切担忧和恐惧。显然,他们是以一种静止、封闭或自然的眼光看待人性,因而把自然人性本质化(固化)或自然化——同时也是美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正是在这种本质主义抑或自然主义的人性观的支配下,传统的人文主义者普遍视人性的一切改变、变化为退化,而倡导自然人性——“自然(不变)的就是好的”;甚至主张逃离、脱身于“尘世”,返璞归真,回归“伊甸园”,“回到古典(前现代)去”,以抵制、抗拒对自然人性的任何改变。面对人类技术化进程中自然人(类)及其性质——自然人性——的不可抗拒的非自然化亦即“退化”的宿命,这种抱持复古主义价值取向和田园牧歌式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文主义反思,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人性观。
三、媒介人的人伦主义意涵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及更先前的人类传播时代,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媒介始终是外在于人的,与人处于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达和社会媒介化(mediatized)程度的不断提高,在越来越强大的制度性媒介技术架构下,媒介与人之间的手段(工具)—目的的关系会发生颠倒,原本以自身为目的的“自为人”沦为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媒介实现其自我发展逻辑的工具,承受着来自异己的媒介力量的反对、胁迫、架构和统制。这就是现代人所遭遇的超越社会制度的、最为普遍的异化。不过,即便是心理上被媒介所异化而精神性发生改变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自然人,因为其作为自然生命的人本身的一种最根本性质——生物性——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的人之为人的自我同一性并未受到根本的损害。
进入媒介深度融合时代,伴随着人不断物化为媒介的进程,一方面,人与媒介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进一步加剧,人的异化趋于全面、深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不断物化为媒介的过程同时也是媒介不断人化为人的过程。在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双重转化而合二为一的过程中,一直作为主体的人首次成为被自我对象化和工具化(用于自身所规定的目的)的客体——“主体媒介”;而一直作为人的对象化工具的“为他者(为人)”的媒介首次成为以自身为目的的“自为的存在”主体——“媒介主体”。作为人物化和物人化的最终产物,“媒介人”(“生物媒介”)既是自身的“主体”,又是自身的“客体”,是主体和客体融为一体的客体化“主体”抑或主体化“客体”——其实,不再存在真正的主、客体,因为主、客体在融合中同时被消解。换而言之,“媒介人”既是媒介的主人,也是媒介本身,因而,它既表现为人的特征,也表现出物的特征,同时呈现出自主、自为与自然、自在的两个截然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方面。至此,从积极方面看,(媒介)人因为把媒介纳入自身并内化为自己,而不再有媒介外在于人而与之相对立。因而,“媒介人”自身不再遭受与作为他者的媒介之间目的—手段(工具)的关系颠倒所产生的异化。可见,在媒介深度融合时代,(自然)人的异化全面完成之日就是其异化彻底终结之时。但无论如何,这个既为媒介又是人的“媒介人”不再是自然人,因为其作为自然(生物)生命的人本身的诸多基本性质——无论是生物性还是基于生物性之上的精神性——统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至此,到底如何看待人的生物限度和精神限度不断被超越而引发的人的性质(人性)的不断改变呢?如何面对与当下的人类物种具有进化(抑或退化)关系的未来的生命存在形式呢?如果说传统的人文主义是朝向过去或历史的,它信奉和恪守着自然的人类生命和自然的人性,那么,今天面对人类自然生命力或精神生命力不断衰减、人类生命本体不断被技术化改变,人类自身行将达至一个根本性的关节点或者说进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临界状态——成为人(to be human)抑或成为“非人”(to be non-human)即“人”将不再是“人”,人文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吗?倘若还有,未来的人文主义该有何种内涵和价值取向?
从根本上说,这里所涉及的根本问题仍然在于,如何看待和判定人类从自然人到媒介人的演变或演化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的进化(发展)还是退化(衰退)过程?它表征和预示的是人类(生命)的终结还是再生?迄今为止的人文主义都以现成、既有的人——自智人诞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生理性质(生物性)和心理性质(精神性)上的重大改变的人——为对象;而在当下,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性质正在面临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人与非人共生、共融产物的“媒介人”的出现表明“人”的概念将不得不被重新定义,以(自然)人为出发点或中心的本体论假设(人本论)将在媒介深度融合时代彻底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依据。由此,以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为本体论基础的传统人文主义将面临严峻挑战。
传统的本体论,无论是人本主义本体论(人本论)还是物本主义本体论(物本论)抑或神本主义本体论(神本论),都是实体本体论,因为无论是“人”“物”还是“神”都被当作独立自在的、具有内在本质属性的实体看待,都被视为最本源、最具实在性的东西。然而,世间万物,本是无物常驻,尤其是在“流动”的网络传播构建的后现代社会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或都趋于“烟消云散”,唯一能剩下的或许是某种(些)关系或连接——整个世界日益凸显为一张关系(连接)网络。世界上,真正实在的东西并非物,而是关系。一切都产生、生成于关系,是关系建构、成就了物,而不是物结构、构成了关系。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讲,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越发显示出:“关系先于存在”,即先有某物置身于其中的关系,而后才有某物的存在及其所有属性;而并非“存在先于关系”,即先有某物的存在(属性),而后某物才拥有其关系。这是因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存在(即身份内涵)要由其所处的关系来赋予和界定,其所拥有的利益(需求)也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被确定——“关系”决定“是什么”和“有什么”。一个事物若脱离了关系或者说处于关系之外,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拥有。换而言之,“存在”即为“关系”,“关系”之外,毫无他物(“存在”)。譬如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其肉身、心灵、体力、智力、意志力等一切所有物都毫无意义——更别说金钱、财富、荣誉、地位等身外之物了。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绝对自持自居、自我占有的,一切都倚赖和维系于人的社会关系。正因此,所谓的人的“本质”(其实,人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无非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归之,“人”即为其“关系”。就人类世界而言,所有的物(包括时间和空间)都是社会关系中的物,所有的肉身或精神都是具有社会关系性的肉身或精神,因而都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和伦理性。相对于关系的先在性、本源性,任何个体、群体都彻底丧失了独立自在性或客观实在性。总之,相比于个体或群体等“实体”,“关系”才具有真正的本体性意涵和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种以关系为本体的本体论可以被称为关系本体论。
在关系本体论的观照下,作为个体的人,不再是传统人本主义意义上具有内在固有本质且绝对高于或优于“他者”(“非人”,如物或机器)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置身于社会关系中、一切由社会关系所规定和决定的关系性“存在”。人之所以为人,人得以拥有“做人的资格”,其存在(生存)或安身立命的依据不在于持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性质——无论是生物性抑或精神性,亦不在于作为某种特殊的生物实体或精神实体,而在于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性(伦理或人伦⑥性)。人的社会关系性(伦理性)才是人的本性或特性。换而言之,所谓“人性”,不是人的生物性(生理性),也不是其精神性(心理性),当然也不是人的物质或技术性(物理性),而是人的社会关系性(人伦/伦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与人的社会关系性(伦理性)相同——人性即为人的社会关系性(人伦/伦理性)。基于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性,只要人性——人的社会关系性在,“人”就在;只要人的社会关系不变,“人”就不变。由此可知,人,无论在生理或心理层面上其性质发生多大程度的改变,只要仍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因而其伦理或人伦的维度没有丧失,就仍不失为人——人之为人的存在理据依然是充分的。
若以关系本体论来观照未来人类或媒介的“现实”,作为“人”与“媒介”的深度融合,“媒介人”即为“媒介人关系”——在智能具身(肉身、切身)性(embodiment)、情境化、沉浸式的媒介人(生存)实践中构成的关系。因而,处于关系中、乃至于自身就是关系的媒介人依然是“在世存在”的。媒介人既是数字化生存、智能化生存,同时又是网络化生存。从自然人到媒介人的人类生命演化进程中,人的生物性和精神性虽然或因自然生命力或因精神生命力的衰减而发生改变甚或减损,或者说,所谓的自然人性和精神人性均遭到损害——其实,原本就不存在卢梭宣称的“纯粹自然的人”,但只要“媒介人”还置身于“社会”——为“媒介(人)”自身所架构的高度媒介(人)化社会即“(媒介)人类社会”——中,置身于社会关系(连接)网络之中,只要“媒介人”不把——也不可能把——自身孤立化为没有窗户的“单子”或纯净化为“缸中之脑”⑦或隐形人,其真正的人性——社会人性即人的社会关系性或伦理性——会依然存在,并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可能无限存续下去。因而,媒介人就仍然会是“(新)人”,是“(新)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若此,只要“媒介人”(关系)尚且作为“人”的社会关系性或人伦/伦理性得以存续,未来人类就可避免遭遇到自我同一性即自我身份认同的人文主义危机。
诚然,自人类诞生以来,首要地作为社会性和社会化的动物(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人恰恰是在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等各种关系形态)不断进化(优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其人性的——人性(内涵)一直在变化,但从未消亡,其“人性化”趋势也从未改变。由此观之,目前人类所面临和正在经历的人性变化无非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持存状态的延续。人类正在发生的从自然人到媒介人的演变,正是自然人通向理想人的一个阶段或环节,或者说,是自然人提升为理想人的一级阶梯。与之相伴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日趋发展为只在于社会性或“人伦性”(伦理性)的“后人性”(post-humanity)。这种“后人性”的人伦、伦理内涵将由“人”的人际交往规范转换成“媒介人”的“人际”交往规范(至于其具体的规定,则在“媒介人”编织现实与虚拟杂糅的关系网络的智能身体实践中已经初见端倪)。至此,主张和捍卫人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不会消逝,而只会以一种新的关系(非实体)为本位的形式得到弘扬。未来捍卫“最具人性”的“人”的人文主义将凸显为一种保守、恪守“媒介人”人伦的精神。因而,从根本上说,未来的人文主义就是人伦主义。
“媒介人”时代的新人文主义必须朝向未来,面向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凭借人的高度自觉性和自反性意识,重新理解人及其性质——人性——演进的意义,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持续关切和容纳人性内涵的不断更新、重铸、改造(视之为升级和优化),同时坚守人的社会伦理家园即人之为人的最后边界,确保向媒介人的进化沿着人性化(人伦化)的方向发展——使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发展始终以社会人性(人伦性)为主导,以符合和满足人性化即人的人伦化需求为理性选择标准,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未来生命的终极关怀。
四、结语
面对人类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自然人类被技术化或非自然化的限度何在?如何捍卫未来的人性?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的消极、保守和乏力,未来人文主义应该是积极应对、有所作为于“媒介人”的蓬勃兴起。为此,即尚未成为“媒介人类”的当下人类所要做的是:对人之为人的人性——社会人伦性(伦理性)予以界定和确认,对人类生命的未来形态做出合理的想象和规范,乃至于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人类生命共商机制的构建,并力求形成一套可以预测和引导包括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在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人化应用符合全球社会伦理即普世(普遍)地“人性化”的新人类生命规划。
可以预期,伴随着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在人类试图超越普通“人”的概念而变成另一种更好、更高级的生命存在的生命升级驱动之下,这个从自然人到媒介人的人类演化(进化)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人类始终走在不懈地追求人性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潜能的路途中。鉴于此,以关系本体论为基础的人伦主义观之,关切、维护和捍卫“媒介人类”自我认同、尊严、价值及人伦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历久弥新的。
注释:
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1985)、妮可思(Steve Nichols)的《后人类宣言》(1988)、佩佩雷尔(Robert Pepperell)的《后人类条件》(1995)、海勒(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1999)以及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后人类》(2013)等论文和著作相继提出了以人与“非人”(机器或动物和一般的物等)之间“共生”“融合”为本质特征的“后人类”概念。
② 1998年,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共同起草了《超人类主义宣言》,该宣言构想了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人类增强,即在未来不断拓展和实现目前大部分尚未实现的人类或人性潜能以及人的存在状态的惊人的和超越性的增强,甚或达至永生。该宣言蕴含着“超人类”概念。参见http://humanityplus.org/philosophy/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③ [美]库兹韦尔:《奇点临近:2045年,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④ [美]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⑤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4-954页。
⑥ 在此文中,“人伦”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特指中国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尊卑长幼之间的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
⑦ “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是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的一个知识论上的理论假想和思想实验:一个人(可以假设是自己)被邪恶科学家实施了手术,他(她)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她)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