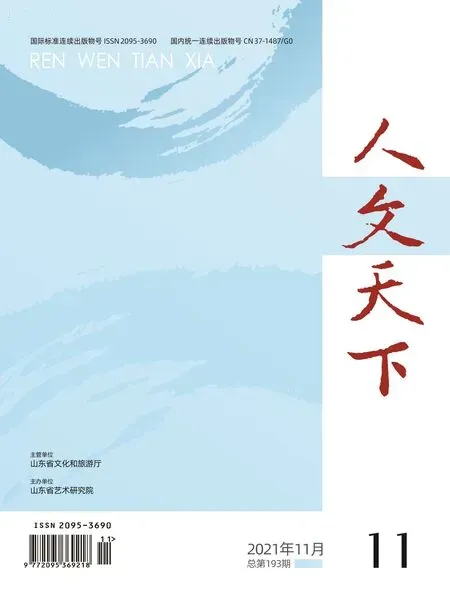由“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引发的三点思考
——乐什么、何以乐、乐有间
■邓曦阳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载:“(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16 页。这就是为后世儒者所称颂的“孔颜乐处”的出处。“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一发问直接引出对孔颜之乐“所乐何事”的思考,即思考孔颜“乐什么”?进一步就会这样发展:谈孔颜“乐处”,问孔颜“所乐何事”,思考孔颜“乐什么”,其中蕴含着一种预设,即认为孔颜之乐总是“所乐有事”或“因物而乐”。但问题在于,孔颜之乐确乎如此吗?这种“乐”的确是一种因果性的乐吗?此外,“寻颜子、仲尼乐处”这一说法还蕴含着一个预设,即将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并称,或者说认为孔颜二者之乐是同样的乐。但问题是,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确实无分别吗?以上是由“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引发的三点思考,下文将具体展开论述。
一、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乐什么”
受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这种说法的影响,在他之后的很多儒者对孔颜之乐“乐”的理解就是顺着“所乐有事”或因物之乐的思路来说的,这从对《论语》中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的“乐”的注解中就可见出:有人将“乐”解释为“乐贫”,即“因贫而乐”;也有人将“乐”理解为“乐道”,即“因道而乐”。
(一)乐贫
周敦颐寻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的发问,引发了后世儒者对于孔颜之乐“乐什么”的思考。一些儒者将这种“乐”理解为“乐贫”,为何解释为“乐贫”?这就要追本溯源,回到孔颜之乐的原始文本《论语》中。“孔子之乐”出自《述而》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子之乐”出自《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因孔颜之乐的表述语境皆是“贫”,而将其“乐”理解为“乐贫”是流于表面和浅显的。实际上,《论语》中“疏水曲肱”的孔子之乐与“箪瓢陋巷”的颜子之乐旨在表明,孔子虽处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贫境中,却亦能乐在其中;颜子虽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贫境中,也依然能“不改其乐”。
《朱子语类》中有关于孔颜之乐是否是“乐贫”的问答:“问:‘颜子‘不改其乐’,莫是乐个贫否?’曰:‘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794 页。《朱子语类》亦有云:“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第883 页。可见在朱子看来,孔颜之乐并非“乐贫”,其乐与贫无关。
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乐”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物质条件或环境与“乐”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就又需要分辨两个层级的“乐”:一种是物质之乐,一种是超越物质的精神之乐。孔颜即使处于贫贱之中也不为之所忧,而是“乐亦在其中”“不改其乐”,可见孔颜之乐皆非物质性的乐,而是超越物质的精神性的乐。所以,物质条件的优越与否也许是构成世俗之人乐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构成孔颜这样的圣贤之人乐的必要条件。可以说,“乐”并非仅仅由物质条件或环境决定,而是在于自身对待物质或环境的态度。
(二)乐道
若说将孔颜之乐从“乐贫”上解释过于肤浅,那将其理解为“乐道”则看起来更符合儒家的思想旨趣。“乐道”实则是对“乐贫”或“贫有何可乐”这一质问的进一步思考。《论语注疏》在对“孔子之乐”一章的注解中,即将“乐”解释为“乐道”:“此章记孔子乐道而贱不义也。”③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91 页。在对“颜子之乐”一章的注解中,引孔颖达的疏,也将“乐”解释为“乐道”:“孔曰:‘颜渊乐道,虽箪食在陋巷,不改其所乐。’”①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第75 页。《论语正义》引《吕氏春秋慎人》对孔子之乐中“乐”的注解:“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②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267 页。也将“乐”理解为“得道之乐”。对于颜子之乐,《论语正义》引郑玄注:“贫者,人之所忧。而颜渊志道,自有所乐,故深贤之。”③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27 页。也是说颜渊之乐在于其志于道,即颜子之乐也是因道之乐。此外,还引赵歧注《孟子》所云:“当乱世安陋巷者,不用于世,穷而乐道也。惟乐道,故能好学。夫子疏水曲肱,乐在其中,亦谓乐道也。”④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27 页。这一注解也认为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皆是“乐道”,即“因道而乐”。
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的发问方式,引导后人从因物之乐的层面来思考孔颜之乐,认为孔颜之乐总有个东西可乐,总是因什么东西才有乐,于是往往从“外面”去“寻求”孔颜之乐,或者说对于孔颜之乐的思考,走的是外寻的路,把孔颜之乐理解为“乐道”就是明证。“道”往往是一种外在的“天道”,由此追求人与天道的合一,即“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本身就蕴含着这样一种预设,即预设了“天人二分”,有合即有分,无合亦无分。从“乐道”层面来理解孔颜之乐,追求人与天道的合一,若是可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得道”,但有得就有可能失。所以这种“寻孔颜乐处”的外寻孔颜之乐的路子,即把孔颜之乐理解为“乐道”就存在“不恒定”的问题:“道”与“人”有二,即是能“合”亦有“分”的可能性;道之“得”也就伴随着“失”的可能性。因此,“乐道”这一孔颜之乐外寻的路子是一种还未达到极高明境地的“乐”。“乐道”之“乐”是一种因物之乐,即“有待”之乐,“有待”就意味着一种束缚,而非完全的自由。因此,“乐道”不可能是对孔颜之乐最好的诠释,它不符合孔颜“无待”的自由精神及“止于至善”的圣贤气象。
沿着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的思路,很多儒者将孔颜之乐的“乐”理解为“乐道”,即“因道而乐”,也就是把孔颜的“乐”理解为“道”的附属品或副产品,认为孔颜之乐是作为原因的“道”的结果,是一种因果性的乐。而据“天之道在人者则为德”这种观点,孔颜之“乐道”实则也就是“乐德”,或因体悟“道”而成就自身之德性而“乐”。所以,“乐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德性之乐,而这种德性之乐是通过自身修养努力以体悟外在天道而有的。换言之,这种“乐”是一种体道之乐、德性之乐、外求而得之乐,是一种由“道”而达到的境界,即一种“乐”的境界。
将孔颜之乐理解为“乐道”,将“孔颜乐处”视为一种“乐”的精神境界,出于儒家重德性和境界的精神旨趣,但这种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重视,却并不意味着儒家对平常生活的轻视,因为儒家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对德性和境界的追求并非是索隐求怪,恰恰相反,儒家正是在平常生活中、在平凡的事情中修养德性,追求至高的精神境界。其中,“极高明”说的是做事做到“止于至善”的境地,“道中庸”说的是行中庸之道,即无过无不及、不偏颇,不脱离现实生活。孔颜这样的圣贤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平凡的事情中达到止于至善的高妙境域。所以,若从儒家对境界之乐的追求来看,这种对乐的境界的追求和高扬,并非意味着一种对平常生活之乐的贬抑。①本文这一观点受张方玉“幸福在境界形态上的高扬,势必意味着幸福在生活形态上的贬抑”观点的启发,但本文对于孔颜“境界之乐”与“生活之乐”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参见张方玉:《孔颜之乐与罗素“幸福之路”比较——现代德性幸福的大众化何以可能》,《理论探索》2015 年第1 期。)
二、“仁中自有其乐”——“何以乐”
顺着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的思路,正如上文所言,有儒者将孔颜之乐理解为“乐贫”,更多人理解为“乐道”,无论是“乐贫”还是“乐道”,说的都是一种“所乐有事”或因物之乐的因果意义上的“乐”。除了将孔颜之乐理解为“乐道”(即“因道而乐”)这种被普遍提及和承认的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一种典型的观点——它是对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一思路的反思和深入,这种观点认为“仁中自有其乐”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1064 页。。
(一)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
“仁中自有其乐”这一观点,认为孔颜之乐是一种人人皆有的“仁”中“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如果说周敦颐的“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思考的是“乐什么”的问题,那“仁中自有其乐”这一思考相较于“乐什么”则更进一步,它思考的是“何以乐”的问题,即不仅仅停留在孔颜“乐什么”上,还思考了孔颜何以有此“乐”。若说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一思路将孔颜之乐的“乐”理解为“所乐有事”或因物之乐,那从“何以乐”或“仁中自有其乐”的角度来理解孔颜之乐的思路,则是将“乐”视为一种“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③本文对“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的看法受冯晨对“自得之乐”理解的启发:“‘自得’之意是说‘孔颜之乐’发生的基础不在自身之外,而是在于自己的仁心、本心。”但本文说“自有”“自在”则更强调“乐”的内在显发,因为“自得”之“得”蕴含着从“无”到“有”的意思,但“仁中自有其乐”的“乐”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潜在的有到实在的有,所以用“自有”“自在”来表述仁中之乐更为贴切。(参见冯晨:《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道德与文明》2014 年第5 期。)
刘黻问:“伊川以为‘若以道为乐,不足为颜子’。又却云:‘颜子所乐者仁而已。’不知道与仁何辨?”曰:“非是乐仁,唯仁故能乐尔。”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唯仁故能乐尔”说的就是“何以乐”的问题。《朱子语类》亦有云:“问:‘不改其乐’与‘乐在其中矣’,二者轻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在朱熹看来,颜子之“乐”并非“乐仁”,即是说颜子的“乐”并非“因仁而乐”的因物之乐,这种“乐”本身就在“仁”中,“仁”中自有“乐”,“仁”和“乐”不是一种先后因果关系,“乐”并非“仁”的副产品,“乐”就存在于“仁”中。《明儒学案》也持这种观点:“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第1064 页。由此可见,在程朱等人看来,孔颜之乐并非周敦颐及其后学所认为的“乐道”这种因物之乐,而是一种由人之仁心本体而有的“自有之乐”“自在之乐”。
“自有”或“自在”的“仁中之乐”,或者说由这种作为人的心之本体的“仁”而显发出来的“乐”,有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成己之乐”,也就是人由对自身仁心本体的认识或体悟而有的一种自我道德之乐,对自身“仁”的体验,也就是一种“成己”;第二个层级是“成物之乐”,指的是人在对自身的“仁”的体悟之上,进而将这种“仁”扩充至天地万物,从而有一种浑然与物同体之乐,这种将本心之“仁”落实到万物之中就是一种“成物”。冯晨指出:“‘孔颜之乐’的‘自得’意义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伴随自我仁心显发的过程所产生的‘愉悦’;一是使仁心落实到事事物物,扩充到天地的过程中产生的‘惬意’。”②冯晨:《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道德与文明》2014 年第5 期。
(二)外寻之乐与内显之乐
周敦颐等人的“乐道”之“乐”与程朱等人的仁中自有之“乐”,皆是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之乐,不过前者是从外寻而有的乐境,后者则是从内显的乐境。“仁中自有其乐”的思路突破了因物之乐,继而追问孔颜之乐“何以乐”的问题,这就由外寻转向内求。如上文所说的,外寻之“乐”与主体始终有“分”的可能性,或者说总是有二,有一种间隙;但由仁心本体内显出来的“乐”则是圆融的,这种“乐”本身就存在于主体之中,只是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由于“仁中自有其乐”,而“乐”最初处于一种隐而未发的状态,所以程朱等人就提倡通过工夫修养去涵养自身的“仁”以使其显发,从而自家体贴这种“乐”。这种理路跳出了周敦颐寻乐向外寻的路子,而提出“自得”的向内求的路子。或者说,“仁中自有其乐”这一观点超越了外寻的路子,转而向内求,即转向自身。
“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7 页。“自有其乐尔”表明了孔颜之乐的内在性。朱熹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7 页。“深思而自得之”在于强调对孔颜之乐的自我体贴,而不是专去孔颜处外寻。《朱子语类》载:“‘乐’字只一般,但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且曰“自理会得,方得”。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朱子语类》亦有载:“乐只是恁地乐,更不用解。只去做工夫,到那田地自知道。”⑥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明儒学案》云:“《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⑦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第1064 页。
由此可见,在程朱等人看来,孔颜之乐乃是一种“自有之乐”“自在之乐”,这种“乐”皆在于主体从自身的仁心本体中去求,而不是向外寻或到孔颜处去寻的“自得之乐”。这里要注意区分“自有之乐”“自在之乐”与“自得之乐”:“自有之乐”和“自在之乐”的“有”是本来“存有”的意思,“在”是本来“存在”的意思,二者都在于表明“乐”是“仁”中本来就存有、存在的;不同于“乐道”或因物之乐的“自得之乐”,“得”指得到,意味着从外面获得一种自身本来没有的东西。而“仁中自有其乐”之“乐”无需外寻,人人皆有“仁”这一心之本体,只需从自身的“仁”处去做工夫,涵养久了或工夫到了一定的境地,就能识得自己心中本有的“仁”,自然能“乐”,自然也就能体悟孔颜之乐那般“乐”。
因此,程朱认为孔颜之乐乃是一种由自身之“仁”而显发出来的“乐”,是一种个人内在体验,而非周敦颐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一种从外物得来的“乐”,一种因外物而有的乐。从“仁中自有其乐”来理解孔颜之乐,即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的仁心本体中自有之乐、自在之乐,即本来存在于人的仁心中的乐,只要对自己心中的“仁”有“觉解”①此“觉解”即冯友兰所说的“觉解”。所谓“觉解”,包含两个层面:一为“觉”,一为“解”。“解是了解”,“觉是自觉”,“人作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他于作某事时,自觉其是作某事,此是自觉,此是觉”。“了解是一种活动,自觉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自觉”即是一种主体“有意识”,“了解”是一种主体对对象的“认知”,而“觉解”即自觉其了解,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一切事与物——包括外在于人的事与物及人自身的行为或活动——有意识的认知和了解。(参见冯友兰:《新原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9 页。),即体悟自己的仁心本体就自然有孔颜那般的“乐”,识得孔颜之乐所乐何事,识得孔颜何以有此乐,明白孔颜那般“乐”无需外寻,只须在自身之中求。这种本来就存在于自身中的“乐”,就没有“乐道”所存在的“分合”与“得失”的问题。也只有这种具有“恒”和“定”的性质的“仁中自有之乐”,才合乎孔颜“止于至善”的圣贤境界。
三、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乐“有间”
上文提及,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一说法存在一个预设:即将“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并称,预设孔颜二者之乐是同样的乐。这就会引发这样一个思考:两者的确是无分别的吗?受“孔颜乐处”这一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后世学者忽略了两者的不同,而将其并称——从孔颜之乐的“大同”方面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也不能因其“大同”而忽其“小异”——孔颜二者之乐的“异”也许确是“小”异,却也值得留意,因为“小异”虽“小”,却依然是“有”而非“无”,或者说,二者之异固然小,但却真实存在,存在就不可无视其存在。
(一)“有间”:乐之“不改”与“亦在其中”
与周敦颐等人将孔颜之乐并称的观点不同,有不少《论语》注解者认为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乃是“有间”“有别”的。《论语集释》引《论语或问》曰:“且曰亦在其中,则与颜子之不改者又有间矣。”②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467 页。且引黄式三《论语后案》所云:“乐在其中,与颜子不改其乐有别。彼云其乐是颜子乐道之乐,此言乐在其中,谓贫贱之中亦有可乐。”③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68 页。《朱子语类》对于孔颜之乐也有类似的观点:“夫子乐在其中,与颜子之不改者,又有间矣。”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第884 页。这些观点就《论语》中论及颜子“乐”之“不改”与孔子“乐”之“亦在其中”的字面表达来表明二者“有间”“有别”。
这些认为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不同的观点,依据《论语》中颜子之“不改其乐”与孔子之“乐亦在其中”这样的字面表达差异,还对其不同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朱子语类》有云:“曰:‘孔颜之乐,大纲相似,难就此分浅深。唯是颜子止说‘不改其乐’,圣人却云‘乐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与圣人略不相似,亦只争些子。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又曰:“所谓乐之深浅,乃在不改上面。所谓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圣人从来安然。譬之病人方得无病,比之从来安乐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深浅,乃好。”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可见在朱子看来,颜子的“不改”之“乐”有一些“勉强”的意思,也就是包含着一种主体的努力,而孔子的“亦在其中”之“乐”则是自然而然的。《朱子语类》亦有云:“恭父问:‘孔颜之分固不同。其所乐处莫只一般否?’曰:‘圣人都忘了身,只有个道理。若颜子,犹照管在。’”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行夫问‘不改其乐’。曰:‘颜子先自有此乐,到贫处亦不足以改之。’曰:‘夫子自言疏食饮水,乐在其中,其乐只一般否?’曰:‘虽同此乐,然颜子未免有意,到圣人则自然。’”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第794 页。这里的问答之间所表达的依然是颜子之乐“有意”,孔子之乐“自然”,或者说,颜子之乐中尚且“有我”,孔子之乐则已然“忘我”而臻于自然的境域。
朱熹对孔颜二者之“乐”的分别的看法,实则也就是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所表达的意思,即认为贤人颜子与圣人孔子“相去一息”:“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从“乐”上来说,颜子之“乐”是“思而后得”“勉而后中”的,而孔子之乐则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这种思想就类似于冯友兰对“道德境界”中“贤人”与“天地境界”中“圣人”划分的思想,即认为贤人的道德行为还是有待努力和有意选择的,而圣人的道德行为则是无需努力和有意选择而自有的。“圣人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其道德行为不是出于特别有意底选择,此所谓不思而得;亦不待努力,此所谓不勉而中。”⑥冯友兰:《新原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87 页。“贤人思而后得,勉而后中。圣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⑦冯友兰:《新原人》,第187 页。
以上这些认为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是“有间”“有别”的观点,虽蕴含着对周敦颐及其后学将孔颜之乐视作同样的乐这样一种预设的反思,但其所提出的“有间”“有别”的观点只是基于二者“乐”之“不改”与“亦在其中”这一字面表达,而未留意实际上因二者之乐表述方式和表达语境的不同,因此并不能简单直接地从字面表达来判定二者之乐的不同。尽管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可能的确不同,但颜子之“不改其乐”与孔子之“乐亦在其中”却并不能作为二者“有间”“有别”这一论点的有力论据。下文对这种认为孔颜之乐“有间”观点的反思和批判,也仅仅是基于其“望文生义”这一问题来说的,而非针对“二者之乐不同”这一观点的批判。
(二)表述方式与表达语境的不同
为便于阐明孔颜之乐的“不改”与“亦在其中”的字面表达并不能成为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有间”的合理论据,需再回到《论语》文本中关于“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的直接表述,《论语雍也》记述了“颜子之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描绘了“孔子之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颜子之乐”的表述者是“孔子”,孔子说颜子“不改其乐”,“孔子之乐”的表述者就是孔子,孔子说自己“乐亦在其中”。所以,“颜子之乐”是他者的评述,而“孔子之乐”则是自己的直陈。可见,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的表述方式或角度是不同的:一个是他者视角的评述,一个是自身视角的直陈。
孔子对颜子之“乐”的评述,存在一个“比较”的语境,即“人不堪其忧”与“回也不改其乐”这样一种“世人忧”与“颜子乐”的比较。因此,颜子之“乐”的“不改”不仅仅是就颜子个人的层面来说,还涉及与世人比较的层面。正是在与世人对“箪瓢陋巷”这种环境的“不堪其忧”与颜子“不改其乐”的比较中,才更加凸显出颜子的贤德和精神境界。但对于“孔子之乐”,孔子则是在直接描述当时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心境。“夫子言此盖即当时所处,以明其乐未尝不在乎此而无所慕于彼耳。”①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67 页。在孔子直接陈述的自己的乐中,并不存在一种与世人之忧的比较,这与颜子之乐的表达语境是不同的。
“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的表述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为他者评述,后者为自己直陈;表达语境亦不同,即前者存在一种与世人之“忧”的比较,故曰“不改”,而后者则是对自己当时所处情境和心境的描述,并无己之“乐”与人之“忧”的比较,所以说“亦在其中”。若忽略甚至无视孔颜之乐二者的表述方式和表达语境的不同,而仅由颜子“不改其乐”与孔子“乐亦在其中矣”的字面表达而得出孔颜之乐是不同的结论,则是武断和荒谬的。若把“颜子之乐”他者评述的表述方式以及与世人之忧比较的表达语境作一种转换,那颜子之“乐”很可能也就是“亦在其中”之“乐”,这样就与孔子之乐没有分别。
《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孔颜之乐亦不必分。‘不改’,是从这头说入来;‘在其中’,是从那头说出来。”这种观点没有流于字面表达,而是从二者之“乐”表面的不同得出二者本质相同的结论。这种观点取消拘泥于“不改”与“亦在其中”的字面表达而有的对孔颜之乐的分别,这是有道理的,但却未进一步言明“从这头说入来”与“从那头说出来”具体如何,所以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也不可深究。
如上文所说,本文认为,若转换“颜子之乐”的表述方式和表达语境,很可能颜子之“乐”就和孔子之“乐”一样,皆是“乐亦在其中”。从前文所谈及的孔颜之乐是一种“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的层面上来说,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皆是“亦在其中”之“乐”:二者之“乐”都是从自身的仁心本体显发出来的乐,因此无论是“疏水曲肱”,抑或是“箪瓢陋巷”,因其对“仁”的觉解和体悟,都能够乐在其中,亦无所谓改与不改其乐。
若一定要说二者的分别,从“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的两个层级,即“成己之乐”和“成物之乐”来说,颜子之乐大概处于成己之乐的层级,即颜子的乐还是一种由体悟自己的仁心本体而有的乐,而孔子的乐则是一种“忘我”或“忘自身”的万物同体之乐。在此意义上,孔子之乐相较于颜子之乐是一种超越了道德小我,而达至天地大我的乐境。就“大同”与“小异”的方面来说,孔颜之乐皆是一种“自有之乐”或“自在之乐”就可视为二者的大同;而颜子之“乐”处于成己之乐的层级,孔子之“乐”处于成物之乐的层级,就可被视为二者的“小异”。
此外,二者的分别还可从“圣贤之别”来说。颜子之所以被称之为“贤人”,而孔子被称之为“圣人”,就在于二者的“无为”与“有为”,所谓“无为”“有为”也就是上文说的“勉强”或“努力”与否。颜子的乐境是“有为”的,需要不断地去做涵养工夫,需要时时戒慎谨惧,以使其显发出来的仁心不被遮蔽;而孔子的乐境则是“无为”的,是不待努力而自有的,也无需时刻涵养,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乐境。但颜子“有为”的乐境与孔子“无为”的乐境二者却并非无关联,可以说,无为之乐是对有为之乐的一种超越,无为之乐基于有为之乐而又高于有为之乐。在这种意义上,孔颜之乐皆是经努力涵养自身仁心本体而有的乐,但颜子之乐尚属于有意涵养的乐境,而孔子之乐则是超越有意而至于无意的乐境。
结语
由周敦颐“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这一说法直接引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孔颜之乐“乐什么”?有人将“乐”理解为“乐贫”,更多的人将其理解为“乐道”。无论“乐贫”抑或是“乐道”,皆是顺着“所乐有事”或因物之乐的思路来说的。这种将孔颜之乐从因果性上来作理解的思路是不合乎圣贤孔颜的精神气象的,因为这样一种因物之乐实则意味着一种有所待和不自由,蕴含着一种被动性。再者,“乐道”之“道”作为一种外在的天道,与人毕竟有分,所以这种因“道”而有的“乐”,于主体而言就始终存在一种“失”与“分”的可能性,换言之,这种“乐”还未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因此,这种“所乐有事”或因物之乐的思想理路就还不是对孔颜之乐的最好诠释,它对“乐”的理解还未能超越“物”的束缚而至于“无物”的自由境界。
由于将孔颜之乐理解为“乐道”(即因物之乐)这样一种解释进路尚未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所以就引发了对孔颜之乐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第二个问题——孔颜之乐是否是一种“无物之乐”?这就从外在的“有物”转向了内在的“无物”,也就是从对孔颜之乐“乐什么”这样一种外寻的专注,转向孔颜之乐“何以乐”的内求的发掘。顺着孔颜之乐“何以乐”的思路,有儒者提出“仁中自有其乐”这一观点,认为“乐”并非是一种因外物而有的乐,而是从人人皆有的仁心本体显发出来的内在之乐,是一种自在之乐或自有之乐。这种“仁”中自有之“乐”本处于一种隐而未发的状态,只有不断地去做工夫、去涵养本心之“仁”,才能够自我体贴,自有其乐。这种本就存在于人自身中的“乐”,就没有“乐道”所存在的“分合”与“得失”的问题,没有有待与束缚的问题。这种“仁”中自有之“乐”是一种自由的、无所待的乐。
“颜子、仲尼乐处”这一说法本身蕴含着一个预设,即把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看作是同样的乐,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孔子之乐与颜子之乐是否的确是无分别的?有儒者指出,孔、颜之乐是“有间”“有别”的,因为《论语》记述了颜子是“不改其乐”,孔子则是“乐亦在其中”,一个不改其乐,一个乐在其中,因而孔颜二者之乐是有别的。但这种说法忽略了《论语》中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的表述方式和表达语境的不同——颜子之乐是他者视角的评述,而孔子之乐是自我视角的直陈;颜子之乐中存在着一种与世人之忧比较的语境,而孔子之乐则没有这种对比。因此,颜子之“不改其乐”与孔子之“乐亦在其中”这种表述方式和表达语境都不同的字面表达,并不能作为二者“有间”“有别”这一论点的合理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