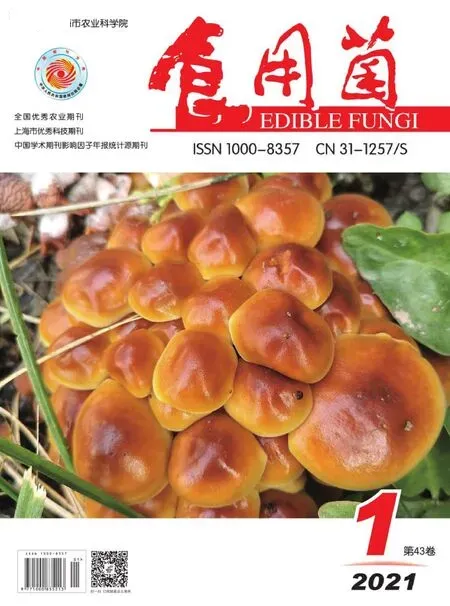建国后大型真菌史研究综述
栗成林 毛 娜 郭 恒 刘莹莹 程雁
(1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2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8)
大型真菌泛指菌、芝、蕈等具有肉眼可见伸手可采的子实体的真菌,中国对大型真菌认识和利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兴盛的时期,郭沫若所著《中国史稿》载:“妇女和儿童的采集活动仍然进行着……一些植物的块根和菌类,更是很好的食物。”[1]原始社会的人民把菌类作为裹腹的食物之一,从晚清起,我们开始把这种可以食用的大型真菌称为食用菌。由于农史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较少关注菌类,因此大型真菌的历史研究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型真菌史研究文献入手,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此对前人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
1 总论
大型真菌历史的研究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早期学者主要从宏观上对菌类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或从宏观上对某种菌类的栽培历史和文化进行探讨。刘波的“中国古籍中关于菌类的记述”一文(《生物学通报》1958 年第6 期),把古籍中关于菌类的记载分为五个大类,分别是菌类的名称、专著、毒菌鉴别和解毒方法、菌类利用和栽培。赵根楠的“我国古代对大型真菌的认识和利用”一文(《微生物学报》1980 年第4 期)在菌类文献记载中归纳出古人对菌类的认识、利用和栽培。刘波的“食用菌栽培历史考”一文(《农业考古》1983 年第2 期),认为至少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唐朝,就早已开始人工栽培食用菌。此外,对茯苓、香菇、草菇、灵芝等菌类的栽培历史进行论述。陈士瑜的“中国食用菌栽培历史初探”一文(《微生物学通报》1983 年第5 期),对古代食用菌栽培发展概况进行了概述,分为了草创、发展、成熟三个时期,并对古代食用菌栽培的技术成就进行了总结,指出日本的香菇栽培术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陈士瑜的“中国食用菌栽培探源”一文(《中国农史》1983 年第4 期),选取冬菇、木耳、香菇、茯苓、银耳、草菇、灵芝、平菇作为代表,探究其栽培历史。陈士瑜的“中国方志中所见古代菌类栽培史料”一文(《中国科技史料》1992 年第 3 期),全面探讨了香菇、木耳、银耳、草菇等菌类的栽培历史,挖掘出方志中大量的菌类的文献记载。刘茵华的“香菇栽培历史考”一文(《浙江食用菌》1996 年第3 期),由《农书》和《改良段木种菰术》的记载得出我国至少在元末明初时已经大规模栽培香菇。王强的“论中国古代的菌文化”一文(《中国食用菌》2015 年第3 期),认为菌类在中国古代文化有两种不同的象征,一种认为菌类是仙草,是祥瑞的象征;另一种认为是破败的凶兆。李静的“我国古代文献中冬虫夏草的考辩”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4 期),提出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最早记载于公元1400 年的《千万舍利》,并对古代文献中描绘冬虫夏草的诗话及其药用价值进行了论述。唐文昊的“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灵芝的论述”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 8 期),阐释“灵芝”“芝草”等菌类的涵义,考证了早期文献中的灵芝记载。李臻的“中国古代菌蕈文化中关于灵芝的记载”一文(《中国食用菌》2020 年第3 期),认为灵芝在古代菌蕈文化中代表着祥瑞、修仙密药、中医药材和维护统治的工具。
2 历史学
历史学领域的大型真菌史研究是当前的主流,主要依托于古代记载菌类的史书、农书、本草学著作、笔记小说等典籍和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图册。芦笛“《菌谱》的研究”一文(《浙江食用菌》2010年第4期),对大型真菌专著《菌谱》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进行了考证,梳理了《菌谱》《广菌谱》《吴蕈谱》三本大型真菌专著的传承关系。芦笛的“明代潘之恒《广菌谱》的校正和研究”一文(《食药用菌》2012 年第2 期、第3 期),则对《广菌谱》的内容进行了版本上的考据和校正。杨勇的“《吴蕈谱》中记载大型真菌初探”一文(《西北农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对《吴蕈谱》进行了注解和校释,将《吴蕈谱》记载的二十六种食用真菌形态特征、食味性、产时、产地分别校释论述。贾身茂的“《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大型真菌之史料价值”一文(《食用菌》2019年第2期),探讨《齐民要术》中“菰菌鱼羹”“椠淡”“缹菌法”“木耳菹”四款食用菌菜肴的烹饪方法和“蘧蔬”及“䓴”两物种。他认为《齐民要术》对北魏时期及前朝食用菌的烹饪技术和大型真菌物种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贾身茂的“《四时纂要》‘三月·种菌子’篇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食药用菌》2019 年第5 期),认为《四时纂要》的“三月·种菌子”篇种的“菌子”,其地域是在我国北方的渭河和黄河下游一带,可能是“鸡腿蘑菰”。贾身茂先生另一文“《王祯农书》‘菌子’篇之史料价值述评”(《食药用菌》2020 年第1 期),通过分析“菌子”篇的结构特点和内容,指出《王祯农书》对一些大型真菌的名称做了记载;对大型真菌繁殖的认识、生长的环境等方面作了阐述;转引和总结了三种大型真菌栽培技术及工序,是研究元代及前朝对大型真菌的认识、栽培及利用的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李苗苗、张迪的“《西事珥》中香菇栽培史的价值考述”一文(《中国食用菌2020 年第4 期》),从内容价值、技术价值和贸易价值论述《西事珥》记载的香菇栽培历史,提出从辩证思考的角度来看待古籍中的栽培技术。芦笛的“宋人笔记所见大型真菌史料”一文(《食用菌》2013年第6期),作者从宋人笔记中整理出大型真菌有关的史料,从栽培技术、物产和饮食、毒菌中毒和解毒、养生和医药、灵芝和祥瑞等方面加以阐述。芦笛的另一文“唐代藏医籍所载真菌药探析”(《食药用菌》2013年第4期),聚焦于古代藏医籍《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对其中竹黄、马勃、蘑菇、黄蘑菇和黑粉菌等真菌及其药性进行了探讨。陈士瑜的“四川《万源县志》之‘制白耳要诀’”一文(《浙江食用菌》2010 年第1 期),对《万源县志》中制作银耳的步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陈士瑜的另一文“四川通江银耳碑文三种之一‘玄祖庙碑’”(《浙江食用菌》2009 年第4 期),分析了“玄祖庙碑”的银耳碑文,充实了大型真菌研究的史料。张寿橙的“从《博物志》《龙泉县志》的有关记载再论龙庆景菇民的历史奉献”一文(《食药用菌》2017年第6期),论述《博物志》《山蔬谱》《龙泉县志》中香菇栽培和香菇砍花法栽培的特征,指出香菇栽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20世纪人类农业文明史的重要成果。芦笛的“明代经济食用菌在自然与社会间的周转及其意义”一文(《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阐述食用菌在明代皇室及民众之间的贸易流转,从社会史、经济史的视角解读食用菌多元的社会功能和历史意义,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型真菌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重点,目前主要有芦笛和贾身茂进行了相关研究。芦笛的“从旧海关出版物挖掘中国近代食用菌贸易史料(以1859—1863年为例)”一文(《食药用菌》2013 年第6 期),根据海关贸易数据得出中国曾从国外进口食用菌;清末的食用菌贸易注重区分干货和鲜货;国外输入中国的食用菌量大于中国外销的食用菌量。芦笛的另一文“法国双孢蘑菇菌种及其栽培技术传入中国之时间考”(《食药用菌》2014年第2期),将我国对双孢蘑菇菌种的引入和栽培时间向前推至1908 年7 月9 日。芦笛的“晚清食用菌史料举例—谭嗣同与浏阳麻菌”一文(《中国食用菌》2018 年第6 期),剖析谭嗣同 1897 年发表于《农学报》的《浏阳麻利述》一文,认为谭嗣同意在介绍和宣传家乡的麻菌栽培产业,《浏阳麻利述》在清末得到广泛传播。此外,芦笛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真菌学书目汇录”(《菌物研究》2016 年第1 期)、“晚清食用菌史料《种冬菇新法》探析”(《食用菌》2018年第4期)、“近代稀见出版物《四季栽培人工香菰简易种植法》中的栽培技术与商业营销”(《食用菌》2019年第1期)、“稀见民国食用菌宣传册《银耳之研究》概述”(《食用菌》2020年第3期),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型真菌史料进行了梳理。贾身茂等“西方近代食用菌菌种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一文(《食药用菌》2015 年第 1 期、第 2 期、第 3 期、第 4期),从栽培技术角度回顾西方食用菌菌种在我国近代的传播过程。贾身茂等“民国时期黑木耳生产状况评述”一文(《食药用菌》2017 年第4 期),根据《食用菌栽培法》《第三木耳及银耳栽培法》《生利指南》《齐齐哈尔木耳集散之状况》《木耳银耳金耳之成分及其营养价值》《发展四川农业论(上篇二)续本卷第二号》等民国文献中的黑木耳文献,提出黑木耳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引起业界的应有重视,生产技术基本上仍处于传统的粗放阶段。贾身茂等“民国时期茯苓研究与生产、运销概况评述”一文(《食药用菌》2017 年第5 期、第6 期),从民国时期安徽为主的茯苓人工栽培产区、技术、产量及流通的报告入手,介绍了民国时期茯苓的生产情况。贾身茂等“晚清报刊中真菌及大型真菌栽培文献史料价值评述”一文(《食药用菌》2018年第5期、第6期、2019年第1期),对晚清报刊上刊载的真菌和大型真菌栽培的40 份(专篇、专著或章节)文献做了整理,归纳为真菌基础知识;西方菌种栽培双孢蘑菇技术;日本香菇、松菌栽培法;中国传统栽培的五种大型真菌;中国的口蘑;大型真菌之《蕈》篇。认为晚清时国人自发性的翻译研究国外的大型真菌栽培技术文献,虽然仅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在生产技术没有得到普遍推广,但为之后真菌学在我国的发展和形成,大型真菌新法栽培的试验和传播,起到了奠基作用。
3 文学
大型真菌史文学性的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马松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冬虫夏草的记载”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8 期),分析明清笔记小说和文学作品中对冬虫夏草的描述,认为冬虫夏草以其特异性和药膳价值闻名于世。孙振涛的“《全唐诗》中的‘灵芝’文化意蕴考”一文(《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1 期),认为“灵芝”是《全唐诗》中一个重要的宗教名物,也与政治、伦理紧密连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刘海波的“中国灵芝文化的历史溯源与现实思考”一文(《中国食用菌》2020年第1期),在古籍文学作品中发掘灵芝的现实价值,认为灵芝文化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同样的研究文献还有曹波的“《全唐诗》中灵芝意象考证”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年第1期)、刘春梅的“唐人诗歌作品中的‘灵芝’意象”(《中国食用菌》2019年第4期)。吕胜男的“菇民隐语行话的文化语言学解读”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10 期),认为古代菇民蓬话具有秘密性、口头性、封闭性、地域性的特点。其主要涵盖菇民的生产用语、生活用语、动物称谓以及其他避讳用语,是民俗文化的体现。
侯红霞等“《永昌府文征》中食菌文化习俗记载”一文(《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11 期),认为食用菌产业在我国云南、缅甸从一个生活中的闲情雅致演变为重要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吴志鹏的“姜特立诗中菌芝探析”一文(《食药用菌》2017 年第4期),从南宋诗人姜特立4 首有关食药用菌的诗歌《香菌诗》《子陵濑》《人送岩桂之二》《感物》入手,分析认为《香菌诗》描述的是香菇,并非灵芝。
4 训诂学
大型真菌史的训诂学研究涵盖菌类的概念、字音、字形、涵义等方面,对于大型真菌史的名词定义和学术规范起到奠基作用。邱尚仁等“‘朝菌’沽训论”一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提出《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中的“朝菌”指的是木槿花。刘杏忠等“菌物之概念”一文(《植物病理学报》1993 年第4期),认为菌物包括了真菌、假真菌及黏菌。张树政的“关于‘菌物’与‘真菌’名词的辨析”一文(《微生物学报》1996 年第6 期),从翻译学角度探讨“菌物”与“真菌”的英文翻译的准确性。贾身茂的“真菌之概念”一文(《食用菌》2012年第5期),探讨“真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贾身茂的另一文“‘菌’的多音多义现象及发展和变化》(《食用菌》2012 年第2期),对“菌”的注音和释义进行了诠释,指出“菌”字随着科学进步和时代发展存在多音多义现象。贾身茂的“关于‘越骆之菌’与‘芝兰之室’的真实涵义”一文(《食用菌》2014 年第6 期),认为古籍《吕氏春秋》中“越骆之菌”的“菌”,是“箘”的假借字,指“竹筍”。《孔子家语·六本》中“芝兰之室”的“芝”,通“芷”,常指“白芷”“芝”和“兰”均指一种香草。该文为我国大型真菌史料的界定提供了新的思路。贾身茂的“《三礼》之《礼记·内则》中‘芝栭’的涵义及其发展变化”一文(《食药用菌2019 年第2 期》),认为“芝栭”的意思前期为木耳,到明代时指大型真菌。芦笛的“‘菌’字的早期含义探析—兼论《墨子》中的‘菌’字”一文(《中国科技术语》2016年第2期),指出“菌”除指菌类之意外,还用以形容矮小或芳香、表示部落名称或人名等,《墨子·迎敌祠》篇中“客菌冶之”“涂菌”中的“菌”释为翳蔽,《墨子·旗帜》篇中“菌旗”中的“菌”为食用菌类。
5 宗教文化
大型真菌史与道教有一定关联,“芝”“菌”是道家升仙体系的重要环节。陈士瑜的“道教与‘芝’菌蕈稗史钩沉之三”一文(《食用菌》1991年第2期),认为道教对于大型真菌的栽培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其蒙上了宗教神秘色彩。这既提高了大型真菌的地位,也限制了人们对于大型真菌的深层次研究。芦笛的“评道教典籍《种芝草法》的自然史价值”一文(《浙江食用菌》2010 年第1 期),认为《种芝草法》对“芝”的生物学认识内容较少,栽培“芝”的方法属臆造,自然史价值不高。芦笛的“道教文献中‘芝’之涵义考论”一文(《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2 期),认为道教文献对“芝”的大量使用使得“芝”成为了美好、神异、奇效的代名词和内丹修炼术语,变为了一个抽象化的概念。杨震山的“浙西南菇民宗教信仰研究”一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15 年),提出菇民信仰存在差异性,有契约化、组织化、非组织化等形式。栗成林的“抱朴子内篇中‘五芝’记载探析”一文(《食用菌》2019年第6期),也探讨了道家文化与大型真菌的关系。芦笛的“自然、宗教和隐喻:汉地佛教文化中的菌类”一文(《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从佛教文献入手,另辟蹊径。
6 杂项
除上述内容之外,大型真菌史的研究还有大型真菌考据、菌类饮食以及菌类地域性研究。陈士瑜的“中国古代‘芝草’图经亡佚书目考”一文(《中国科技史料》1991 年第3 期),收录77 篇亡佚书目,并对部分亡佚书目的内容和亡佚时间进行了考据。陈士瑜的“菌蕈字源考”一文(《中国食用菌》1992 年第1 期),对蓐、菰菇姑等音近的菌蕈名词进行了考据。陈士瑜的“中国古代菌类菜肴馔杂掇”一文(《食用菌》1985 年第1 期),从古籍中摘取了一些食用菌菜肴,展现出食用菌饮食文化的悠久历史。这类文献还有:贾身茂的“晚清《格致汇编》翻译传播西国名菜之一的‘菌类’”一文(《食药用菌》2013 年第3期)、李想等“松茸的饮食文化与烹饪技巧”(《食药用菌》2016年第4期)、李鹏等“猴头菇的历史文化溯源与食疗文化”(《中国食用菌》2019 年第12 期)。陈士瑜的“名人与菌”系列文献(《食用菌》1994 年第4 期、第 6 期,1995 年第 1 期、第 2 期、第 4 期、第 5期)、郭天希的“安徽历史名人灵芝养生之道”一文(《食药用菌》2015 年第6 期),讲述了毛泽东、张大千、曹靖华等名人与菌类的故事。
综上所述,大型真菌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于后期的延伸性研究打下基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真菌史的研究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大多是基础性研究,函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研究大型真菌的历史有助于丰富我国农史研究,开辟农史研究的新视野,有助于食用菌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在此希望更多的优秀学者可以参与大型真菌史的研究,拓宽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充分发挥大型真菌的自然科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