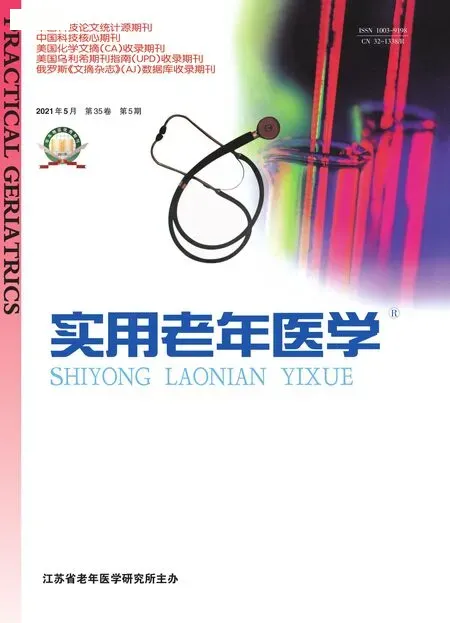PD-1抑制剂介导内分泌不良反应报道并文献复习
谈玖婷 付聿明 吴祥 沈德峰 刘婧 周佩华 刘超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PIs)的出现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这类分子通过阻断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或其配体(PD-L1)来调节抑制性免疫应答。但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免疫介导的内分泌系统不良反应在临床应用中并不是最常见的,内分泌腺体组织在遭到破坏后出现的症状不典型,多数病人病程隐匿,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腺体受损,遗留永久性功能缺失,少部分病人可能以内分泌危象为首发症状[1]。因此,内分泌irAEs需要得到肿瘤科医师及内分泌科医师的更多关注。本文回顾性分析4例老年肿瘤病人接受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出现的irAEs,以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提高对irAEs的认识。
1 病例资料
1.1 病例1 病人男,66岁,有高血压病史,BMI为26.5,2017年12月行“胃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胃窦黏液腺癌,低分化。术后化疗,2019年6月接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每21 d注射1次。首次使用前甲状腺功能(甲功)、皮质醇水平正常,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为11.7 U/mL(参考值为0~9 U/mL),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及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阴性。2019年11月,病人出现精神萎靡、全身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无明显头晕、头痛、视野缺损。免疫治疗后143 d复查上午8:00(8AM)皮质醇为0.18μg/dL、8AM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为1.3 pg/mL,促甲状腺激素(TSH)为36.73 pmol/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为2.36 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为3.79 pmol/L,TPOAB为19.4 U/mL,其余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垂体MRI平扫+增强未显示有转移或炎症迹象,甲状腺彩超提示内部回声不均。诊断与治疗:病因考虑为PD-1抑制剂介导的垂体炎累及垂体-肾上腺轴,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减);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评估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进行,评估不良反应为2级,予以泼尼松7.5 mg/d 口服及左旋甲状腺素(L-T4)50μg/d口服,暂停帕博利珠单抗。随访:经激素替代治疗后,病人症状逐步缓解,3周后复查甲功提示药物过量,予以L-T4减量,甲状腺抗体滴度无进一步升高;随访4个月,予泼尼松5 mg/d,L-T425μg/d维持替代治疗。
1.2 病例2 病人男,70岁,有高血压病史,BMI为31.6,2011年9月行“左胸探查术”,术后病理示左下肺中央型腺鳞癌,中-低分化。2019年8月接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每21 d注射1次。首次使用前甲功、皮质醇水平正常,相关抗体阴性。治疗2个月后评估疾病稳定。2019年11月起,病人出现头晕、记忆力减退、乏力等不适,无明显头痛、视力损害、怕热、多汗。免疫治疗后82 d复查8AM 皮质醇为1.11μg/dL、8AM ACTH为0.55 pg/mL,TSH为0.15 pmol/L,FT3为6.51 pmol/L,FT4为19.32 pmol/L,甲状腺相关抗体阴性,Na+为132 mmol/L,其余电解质、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性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垂体MRI平扫+增强及甲状腺彩超未见明显影像学异常。诊断与治疗:病因考虑为PD-1抑制剂介导的垂体炎,累及垂体-肾上腺轴;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评估垂体炎为2级,原发性甲亢为1级,予以泼尼松7.5 mg/d,暂停帕博利珠单抗治疗。随访:予以替代治疗后病人症状好转,泼尼松剂量降低至5 mg/d;未予以干预的情况下,甲功逐步恢复至正常范围,甲状腺抗体持续为阴性。病人于2020年1月死于肺栓塞后多脏器功能衰竭。
1.3 病例3 病人男,64岁,BMI为22.4,2018年1月行“食管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胃鳞癌。2019年4月接受帕博利珠单抗100 mg,每21 d注射1次。首次使用前甲功正常,TPOAB为89.42 U/mL,TgAB为201.4 U/mL(参考值为0~4 U/mL),TRAB正常,治疗期间病人无明显加重的乏力、纳差等不适,治疗后70 d复诊TSH为17.04 pmol/L,FT3为4.35 pmol/L,FT4为8.42 pmol/L,甲状腺彩超提示内部回声不均。其余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诊断与治疗:病因考虑为PD-1抑制剂介导的原发性亚临床甲减;评估为2级,予以L-T425μg/d替代治疗基础上,继续联合原免疫治疗方案。随访:目前病人已完成肿瘤免疫治疗13个疗程,评估病情部分缓解;前2个月TSH水平有所好转,但随疗程增加,相同剂量L-T4治疗下,TSH水平逐步升高,192 d复查TSH为19.95 pmol/L,TPOAB为157.1 U/mL,TgAB为473.6 U/mL,较基线升高,不除外遗留永久性损伤可能;随访7个月,予L-T450μg/d维持替代治疗中。
1.4 病例4 病人男,61岁,BMI为26.2,2019年6月行“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肺鳞癌,低分化。同年11月接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每21 d注射1次。首次使用前甲功正常,但甲状腺抗体未查。治疗75 d后病人出现乏力不适、纳差加重,查TSH为25.56 pmol/L,FT3为4.27 pmol/L,FT4为9.38 pmol/L,TPOAB为24.3 U/mL,TgAB及TRAB正常,甲状腺彩超提示内部回声不均。其余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诊断与治疗:病因考虑为PD-1抑制剂介导的原发性亚临床甲减;评估为2级,予以L-T425μg/d替代治疗,继续免疫治疗。随访:病人乏力症状改善;随访2个月,治疗后133 d复查TSH为10.71 pmol/L,FT3为3.22 pmol/L,FT4为9.65 pmol/L,TPOAB为25.7 U/mL,仍予L-T425μg/d维持替代治疗中。
2 讨论
老年肿瘤病人具有许多不同于年轻肿瘤病人的生理和病理特点,如老年人器官老化,生理功能逐渐减退,机体免疫能力和调节能力下降;加之多数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多重用药情况不可避免;老年病人肝肾功能、体脂变化可显著改变药物的分布、代谢和排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药物在老年病人中使用时更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加之老年肿瘤病人确诊时多为中晚期,以药物(化疗或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为主的非手术治疗地位尤为突出[2]。
免疫介导的内分泌疾病可发生于任何一个或多个内分泌组织,引起腺体破坏和下游靶器官的功能障碍[3],导致病人临床症状广泛,与归因于肿瘤疾病的症状(如乏力、纳差等)相似。垂体炎时,垂体MRI可能会表现为垂体的弥漫性增大,但MRI结果正常时并不能完全排除,本研究中病例1和2的垂体MRI均未见垂体异常。既往报道PD-1/L1引起的垂体炎,特别是仅出现孤立性ACTH缺乏时,可能并不会引起垂体影像学改变[4]。另一方面,内分泌irAEs中位时间高度可变,从42 d到5.5个月不等,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1个月[1, 3, 5]。因此病人接受免疫治疗后,若发生irAEs,不论是症状、影像学检查均有可能导致漏诊、误诊,值得临床医师重视。
ICPIs所介导的irAEs有一定的差异。本报道中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导致病例1和2发生垂体炎,且为孤立的ACTH缺乏,4个病例均发生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异常(thyroid dysfunction,TD),3例为原发性甲减,1例为原发性甲亢。有研究显示,单药治疗时CTLA-4抑制剂(主要为伊匹单抗)更易引起垂体炎,而TD在PD-1/L1抑制剂中更为常见[6]。Barroso-Sousa等[7]的荟萃分析显示,对比PD-L1抑制剂,PD-1 抑制剂具有更高的导致甲亢的风险;CTLA-4抑制剂及PD-1/L1抑制剂联用时,各类irAEs发病率均比单药治疗高。另有Faje等[8]回顾性研究显示,垂体炎中,垂体前叶比后叶更易受累;与接受CTLA-4抑制剂治疗的病人相比,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病人中孤立的ACTH缺陷更为普遍。这些差异提示免疫应答的复杂性,不同的ICPIs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接受相同类型ICPIs的病人同样可以引起不同的应答,这些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如CTLA-4在垂体中的异位表达、甲状腺组织表达PD-L1分子、分别激活效应T细胞的能力、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及补体通路的激活、病人本身基因多态性等[5-7]。
对于免疫介导垂体炎是否继续使用免疫治疗仍有争议。以2020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为代表的学者推荐2级及以上垂体炎的病人在症状缓解至1级前,应暂停使用免疫治疗[3, 9]。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免疫介导的垂体炎与原发性垂体炎相比,垂体增大可能更轻,甚至是短暂的和具有自限性的,如前文所述中PD-1抑制剂可能不会引起垂体增大,且垂体增大后几乎均可以恢复,因此1级及多数2级不良反应的病人在合理激素替代治疗基础上可继续使用免疫治疗,仅在垂体增大出现占位效应或内分泌危象时需暂停免疫治疗[10-11]。
ICPIs治疗后内分泌腺体损伤的恢复在不同的报道中具有一定的差异。垂体损伤后的肾上腺轴少有恢复,而在报道中,多达50%~60%的性腺轴或甲状腺轴损伤可以得到缓解[6, 10]。多数情况下,使用ICPIs治疗后引起的为破坏性甲状腺炎,故甲亢及甲减是同一病理下的不同临床表现。甲状腺毒血症通常有自限性,并可能转为甲减,甲减的病人多数需要终身进行激素替代治疗[7]。
器官特异性抗体(例如针对肾上腺、甲状腺、胰腺等的抗体)的阳性可能与器官损伤有关[5]。在本报道中,均明确累及甲状腺,其中病例1、3、4在ICPIs治疗前抗体阳性。部分理论支持ICPIs可以通过不同机制提高预先存在抗体或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或者通过提高针对肿瘤以及健康组织中存在的抗原T细胞活性来诱导irAEs[12]。目前,虽然临床证据提示器官特异性抗体可能与内分泌irAEs有关,但机制不明,且这种关联并未能完全得到论证。肿瘤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表位的交叉也可能是导致内分泌irAEs的病因之一[13]。有研究为了测试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遗传易感性与irAEs是否相关,对ICPIs治疗后累及多腺体的病人进行HLA单倍体分析,发现后者不是预测内分泌irAEs的可靠方法[11]。目前尚未发现用于预测内分泌irAEs的明确遗传学或临床工具,在这一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由于老年肿瘤病人的特殊性,导致其耐受性较年轻病人低,治疗方案选择受到限制。ICPIs通过改善肿瘤病人免疫状态的策略在老年病人中也可获得一定的疗效。随着ICPIs治疗的普及,内分泌irAEs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鉴于其病程的隐匿及预后的潜在不可逆性,建议在免疫治疗开始时即评估基础激素水平。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预测指标,但由于器官特异性抗体与内分泌irAEs发病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建议有条件的病人可以在治疗前完善相关抗体检测,以期评估内分泌irAEs的发生风险。同时,各类irAEs的发病中位时间高度可变,治疗全过程中都需警惕可疑症状,避免内分泌危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