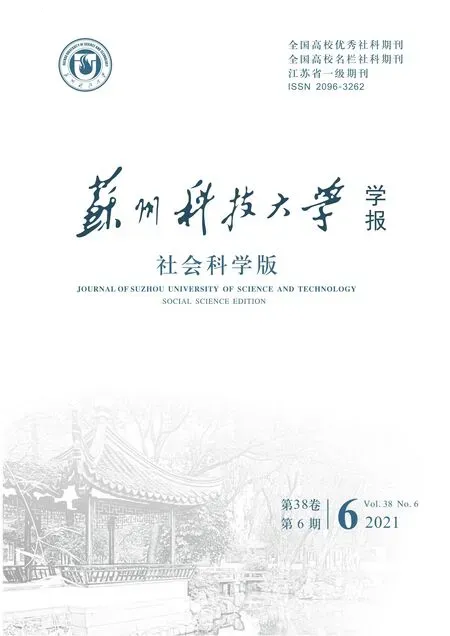常熟言氏与清代先贤言子祭祀的展开*
贺晏然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儒家的祭祀系统和祭祀活动既易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又往往成为思想与文化新方向的表征。近年来,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它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研究工作的拓展,儒家祭祀内部的多样性被不断揭示出来,既包括上层的被纳入国家祀典的部分,如文庙系统的孔子、周公、孔庙的四配十哲(乾隆后成为十二哲)、历代先贤,以及经过朝廷允准而从祀东西两庑的儒者;也有地方、家族或士大夫私祀的部分,如由地方官府或士大夫主导的对于无缘进入孔庙的先儒的祭祀,包括乡贤祠及由士人发起的各类私人祭祀活动。毫无疑问,孔庙及其两庑的从祀序列是这一祭祀系统的核心,相关的研究较多(1)学界此前对孔庙的研究并不缺乏,这里仅举几种代表性的论述。黄进兴的跨时段研究基本勾勒了孔庙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鸿林对于王阳明从祀的研究则展现了孔庙从祀的复杂情况。参见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杨联升、全汉昇、刘广京《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下)》,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581页;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6年第5期第167~181页;Chu Hunglam,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8, Vol. 48, No. 1, pp. 47-70。详细的学术史综述可参见田志馥《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32~40页。。此外,体现地方意志的乡贤祠也有相对充分的研究。(2)涉及明清乡贤祠的研究参见林丽月《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7~372页;奥崎裕司《苏州府乡贤祠の人々——乡绅の地域性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1982年第10期第49~60页;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和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8~123页;Han Shenghyun, “Reinventing Local Tradition: Politics, Cultural and Identity in Early 19th Century, Suzhou”,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c dissertation, 2005, pp. 155-514;韩承贤《明清时代的名宦、乡贤入祠样相的变化与其意味》,《中国学报》2006年第54期第347~378页。然而,对于历代先贤的祭祀,明清时期除了遍布全国的各级孔庙,还有经过国家批准并支持的由先贤后裔家族承担祭祀行为的专门祠庙。例如,祭祀孟子的孟庙(亚圣庙)、祭祀曾子的曾庙(宗圣庙)、祭祀颜回的颜庙(复圣庙)、祭祀子思的中庸庙等,十二哲也多有此类专祠。对于这类祠庙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近年来,随着方志、族谱等地方史料的不断发掘,对这些专祠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出现。
笔者关注的苏州地区先贤言子祭祀就是以地方祠庙为中心展开。康熙、雍正年间,先贤奉祀被逐步纳入朝廷的管理体系,由衍圣公、礼部、地方督抚学政等共同负责。[1]与此同时,晚明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先贤家族成为先贤奉祀的活跃力量。先贤祭祀既代表国家祀典的官方立场,又与新兴先贤后裔家族产生密切的联系,家庙和官祭的性质相互纠缠。先贤祭祀活动连接着中央、地方及家族,是理解活态的祭祀制度很好的切入点。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从奉祀制度方面对明清圣贤后裔展开讨论的(3)参见王春花《圣贤后裔奉祀生初探》,《清史论丛》2018年第1期第84~103页;李成《清朝奉祀生制度初探》,《清史论丛》2019年第1期第152~169页。,对先贤后裔家族活动实态的多样性关注较少。而事实上,家族的发展和地方的儒学传统深刻影响着先贤奉祀的实践。常熟言氏家族在先贤奉祀制度的框架内表达自己诉求的过程,不失为呈现先贤祭祀制度复杂性的有效例证。
一、言子后裔奉祀资格的变化
言子即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时吴地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子的言行散见于《论语》《孟子》《礼记》《史记》等。他在担任“武城宰”期间,曾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来回复孔子对其治理方式的疑问,是孔子门下将知与行结合得较好的弟子。今日耳熟能详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2]281等言论即出自言子之口,载于《论语》。《史记》亦载:“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3]由此可知,言子应是孔子晚年弟子。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言子被追封为吴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封丹阳公;咸淳二年(1266),封吴公;元大德年间,封吴国公。其吴人的身份成为言子祭祀中的独特议题。
言子在唐代即被纳入文庙正殿从祀的序列。唐开元八年(720),言子以孔门十哲从祀文庙正殿。所谓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2]742。这一名单在唐宋间逐渐形成四配十哲的序列。到了清康熙年间,朱熹被升为十哲之次,成为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有子升位,十二哲的局面最终形成。[4]在文庙从祀的队伍中,言子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明朝弘治年间,常熟出生的吏部郎中周木(1447—?)曾请求朝廷加强常熟地方的言子祭祀,这正与当时为孔庙圣贤设立奉祀生之制相呼应。周木通常被认为是常熟理学史上晚明时期唯一的代表人物,他的这次请求或可以放在明代地方儒学建设的脉络中来理解。[5]335礼部积极回应了周木的提议,认为“孔门弟子,惟偃生于南方,而北学于中国。南方学者得其英华,盖自偃始”[6]331。明廷拓建了地方言子祭祀建筑学道书院,并继续优免此前已设的数名言氏后裔奉祀生徭役。言子后裔以奉祀生身份祭祀言子的情况在明代一直持续,同时,周木之后不久,对于是否设立五经博士以供奉祀的讨论即已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漫长讨论,从明代正德年间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年间。
对言氏后裔是否应授五经博士的第一次讨论出现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直隶提督学校御史张鳌山题请苏州府常熟县言氏后裔荫袭五经博士一职。授予孔氏南北宗以外的圣门后裔五经博士始于明景泰二年(1451),最初只涉及颜、孟子孙,后来逐渐扩展到十三氏。[7]张鳌山在疏文中推崇言偃的功绩,将之与朱熹对比,希望为言氏子孙乞授五经博士一职,以挽救言氏苗裔不兴的现状(4)张鳌山的这次题请仅见于言氏家谱。[8]1。疏文对言子“吴公”的论述,比弘治年间礼部的论述更进一步,通过强调言子南方儒学源头的形象来为言子争取政治上的正当性。礼部对张鳌山的题请并无回复,请设五经博士一事显然终无所成。到了嘉靖二年(1523),刑科给事中苏州府人沈汉(1480—1547)再次题请荫袭,他的诉求与张鳌山相仿,主要是“照颜、孟、朱熹例,官其子孙一人以奉其祀”[9],还包括比照孟庙规制“改建庙庭”“为置祀田”,目的也是挽救言子日益衰落的族裔,使祭祀活动不至于荒废。对此,礼部虽以“子孙世远,难据授官”为由拒绝,但给予了修庙、拨田及优免杂差诸多益处。
嘉靖九年(1530),朝廷对先贤祭祀进行了礼仪上的改革,言子被改称为“先贤言子”。直到明末,这一设立五经博士的话题未再被提起,言子在常熟的后裔始终以奉祀生的身份主持言子祭祀活动。在朝廷婉拒五经博士之请的背后,是言氏,特别是言氏大宗在晚明的衰落。耿橘在《虞山书院志》中曾直言,嘉靖初年言氏嫡裔“下同编氓,贫穷不能自立”,他甚至将希望寄托于言氏小宗的几位子弟,包括言福、言禧、言逢尧等[10]。由此可知,常熟言氏嫡裔在此时段的奉祀活动是以地方官府和有地缘关系的中央官员为主导的,嫡系子孙的政治活跃性不高,家族的科举成就也不突出。若非地方官员的支持,言氏后裔很可能无法负担言子祭祀的重任。
清朝的建立和先贤奉祀制度的进一步确立为言氏争取五经博士一职提供了新的机遇,常熟言氏家族与新朝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互惠关系。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南巡抚汤斌(1627—1687)题请荫袭。此时,孔颜曾孟、仲由和朱熹、程颢程颐、周公、周敦颐等后裔均已世袭博士。汤斌以言子南方出身为由,论及他与孔门诸子弟的不同,阐释设立五经博士的合理性。[11]3可惜,汤斌在上疏的第二年便过世,请给五经博士一事不了了之。到了四十四年(1705)康熙驾幸江南时,荫袭五经博士一事才由言子后裔借面圣之机再次提出。《言氏家乘》就此收录了一篇先贤七十三世孙言德坚奏请荫袭的疏文[11]4。言德坚深谙先贤家族借面圣而获赐世职之道,在疏文中将荫袭一事渲染为王朝政治文化的表征,也流露出对“一门世世顶戴高厚”的向往。与言子后裔此前曾拥有的奉祀生资格相比,五经博士的设立显然将进一步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荫袭博士的一支在言氏家族内部以及地方文教事务中都会享有优势。但这次面圣并没有立时改写言子后裔的身份,真正的转机出现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彼时,江南学政张元臣上疏请荫言氏后裔,其疏文直指康熙三十九年(1700)先贤闵子、端木子后裔破例得授五经博士的事实,认为言子同在十哲之列,理应荫袭。张元臣由朝廷奉祀制度出发的提议得到准许,并由江宁巡抚王度昭(?—1724)会同衍圣公孔毓圻(1657—1723)共同查探言子后裔嫡派的情况[11]5。由于族谱与族人证言俱在,常熟言子后裔承袭博士一事终于尘埃落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先贤言偃七十三世孙生员言德坚世袭五经博士”[12]。言德坚之后,五经博士又在常熟言氏家族中传承数代。言氏承袭五经博士对此后常熟言子祭祀的发展影响深远。
通过梳理言子后裔奉祀身份的变化,可以看到清代言子祭祀是在明清两代先贤奉祀制度的框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言子奉祀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转化为家族争取政治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地方和国家之间政治沟通的管道。言子后裔奉祀资格的变化,使得家族借由言子展开更为丰富的地方政治和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从而改变了作为清初底层读书人的常熟言氏的家族命运。
二、常熟言氏与言子奉祀的展开
常熟言氏后裔虽然顺利取得了清廷的五经博士头衔,但实际上其嫡系身份也曾面临其他地区后裔的挑战。这种对先贤奉祀资格的争夺,在明清先贤奉祀制度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就言子后裔的情况来看,其奉祀资格之争是在康熙年间伴随五经博士的确立才开始出现的。例如,浙江山阴的言子后裔亦自认言氏大宗,山阴言述之子言然曾投状称:“先世以守越留居,久离坟墓,请如前明衢州孔洙让公爵与在曲阜者例。”[13]山阴言氏最终在朝廷认证过程中败下阵来。其未承袭五经博士的直接原因,很可能与朝廷在认定奉祀资格过程中对在地墓祠建筑的重视有关。浙江仁和人金甡(1702—1782)在《题山阴言氏大宗世系后》中曾道:“言氏,以在山阴者为大宗,其在常熟者支子也。”他对作为大宗的山阴言氏错失五经博士头衔的解释即与墓地有关:“其七十二世孙以守墓为重,援孔氏在衢之例,投牒礼部,固让于常熟之名德坚者,归则倡建专祠于越,以供祀事焉。”[14]关于山阴言子祠的记录已不可考,但是山阴言氏“让出”五经博士,并未帮助其获得如孔洙让爵般的声名,“嗟余忝有司衡责,振厉无能愧未遑”[15],此后他们在家族建设上经历了较长的没落时期。山阴言氏将这场落败美化为“让贤”,但他们显然很清楚五经博士身份对家族发展的益处,其编修族谱、倡建专祠、争夺五经博士的一系列操作,正是争取先贤后裔奉祀资格的关键。“让出”五经博士之后,山阴言氏继续倡建专祠,应该也是希望通过建立专祠而获得守祠奉祀资格,甚而取得奉祀生的资格。由此观之,“让贤”的解释似乎隐含着一股不甘的意味。对这些散居各地的言氏后裔,常熟言氏子孙始终保持警觉。胡克家(1756—1816)在为常熟言子后裔言如泗所作的《素园公墓表》中,提及言如泗曾为分居顺天、浙东及楚南的言氏增刻家谱[16]43。这一行为显然是在言子奉祀资格尘埃落定之后常熟言氏对大宗身份的宣誓。
和山阴的言氏后裔相比,常熟言氏在本地的发展并不显著。在清初言德坚获授五经博士之前,虽有奉祀生之设,但是对言氏各支科举的发展帮助不大。《言氏家谱》记载,常熟言氏在六十六世到七十世之间开始明确分化为数支。[17]9某些分支的划分与对不同家庙祭祀活动的责任相关,分化后不久各支渐有奉祀生之设。除了大宗县东家庙,较为重要的分支还包括文学书院、郡城学道书院等。文学书院一支相传以常熟文学书院的建立和附于书院的家庙祭祀活动为起始,自六十六世言弘业之后,以奉祀生或类似奉祀生的身份传承了数代。耿橘在《虞山书院志》中夸赞言氏小宗几位随其在书院讲学的弟子,如前所述六十九世言福、言禧,七十世言逢尧等均出于这一支[17]1-2。直到七十三世言梦奎等才开始从学新任的翰博言德坚,先贤专祠印官的特殊地位在家族内部开始显现。郡城学道书院一支,始自明隆庆年间六十九世言仲文迁至郡城,郡祠的奉祀生自七十一世言长春始设,奉祀资格在此支内断续传承了数代。由于出嗣关系,学道书院支与县东家庙大宗之间在七十六世前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言氏大宗所在的一支称“县东家庙长支”,传为明万历间邑令耿橘所定。从七十一世言森开始,明廷正式设立奉祀生。七十三世言德坚为第七十二世言煌第三子,被清廷任命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原设的言子奉祀生之职则多在言德坚长兄言德垕子孙中传续。言德坚少时,生活颇为困窘。常熟人王应奎(1684—约1759)在《柳南随笔》中称,言德坚“贫穷颠顿,糊口四方,最后授徒云间,离家几二十年矣”[18]62。言德坚的老师顾天申为诸生,也是一派天真放任的作风。对于久困生员身份的言德坚来说,以言子后裔争取五经博士的官职,是获取声名最为便捷的方式。言德坚此后在里中教学,有弟子张大受、陶正靖、严有禧等,其五经博士头衔成为时人最乐于记载的身份。五经博士在言子奉祀系统中占有至高的地位,可以参与地方奉祀生的认定过程,在本地言氏家族的发展中也拥有较多的话语权。按照规定,“言氏通组子姓,皆以该翰博为宗主,凡事悉听约束。设有争斗雀角者,该翰博自行处分。如在有司处讦告者,亦移文关取审理”[8]9。五经博士的至高家族地位还部分衍生到司法领域。
言德坚告休之后,由于其子兴早卒,以孙辈言如洙补为五经博士。如洙为言德坚兄长言德基三子言钧的长子,出嗣袭五经博士。雍正十二年(1734),言如洙通过礼部的考试获准承袭。此后五经博士的授予也遵照这种长子继承制度,在各房之间几乎没有竞争的状况出现,传承相对稳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先贤七十六世孙言朝枢由附生承袭。乾隆四十七年(1782),先贤七十七世孙言尚燮由附生承袭。嘉庆三年(1798),先贤七十八世孙言忠豫承袭,其因病呈请以弟忠益代理世职,嘉庆十三年(1808)礼部给札代理袭职。道光三年(1823),先贤七十九世孙言良爱由附生承袭,良爱子言家柱于咸丰十年(1860)殉粤寇之难,奉吏部议给云骑尉世职,未及承袭五经博士世职。光绪六年(1880),先贤八十一世孙,即良爱孙言敦道承袭五经博士,兼袭云骑尉世职,这是言氏有记载的最后一任五经博士。言氏后裔此支的子孙在整个清代的科举成就并不突出,任官并未逸出常熟的范围,这反而帮助他们有效地担负起在地的言子祭祀责任。
除了五经博士,言氏后裔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奉祀生言钧子言如泗。言如泗(1716—1806),字素园,与五经博士言如洙为同辈,是通过恩贡赐官的。先贤后裔通过参加临雍(5)乾隆三年以前,俱称“视学”,乾隆四十八年建辟雍,以后始称“临雍”。观礼可以获得这种特殊的生员身份。清顺治九年(1652),特送孔、颜、曾、孟、仲五氏子孙观礼生员十五人入国子监读书;康熙、乾隆年间,皇帝东巡,亲诣阙里,加恩五氏、十三氏子孙生员贡国子监,亦称“恩贡”。乾隆后,恩赐临雍观礼圣贤后裔(一般为五经博士携族人两名)廪、增、附生入国子监肄业,成为常例。言子后裔言如泗于乾隆三年(1738)通过观礼获补监生,充正黄旗官学教习,乾隆十三年(1748)任山西垣曲知县,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湖北襄阳知府,乾隆三十四年(1769)因失察属员罢官回里。言如泗曾参与修建言子墓,倡议修葺游文书院、西城书院和邑学,增刻家乘,著有《言子文学录》《言子家乘》《常昭合志》等。如泗之子朝楫、朝标均业儒,朝标更是清代常熟言氏的第一位进士,在科举上的成就超过父辈。言如泗恩贡的身份是此支在科举上逐步攀升的开始,言氏后裔对五经博士与恩贡生身份的追求,正与业儒的言氏家族长期经营的方向相吻合。与言如泗同时或稍后,常熟言氏子孙多次利用临雍的机会获得科举上的实利。值得注意的是,恩贡生主要集中于县东家庙一支及由此支出嗣的子弟,虽有别支子弟被授恩贡,但授予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随五经博士临雍观礼。类似地,县东家庙一支的奉祀生人数也远远超过别支。
常熟言氏后裔从明代的世远难据,到清初被授五经博士,言德坚一支是这场言子奉祀资格争夺中最大的受益者。五经博士的设立,使得常熟言子后裔由晚明大宗较为衰落的状态,迅速跻身家族的核心。获得五经博士头衔的一支,在家族和地方文化建设中都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利用奉祀和恩贡等手段将朝廷对言氏后裔的优待推及更为广泛的族人。在这一过程中,宗族开始成为言子祭祀最为核心的力量,言氏家族的在地经营对于维持其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对族谱的编撰,言氏后裔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言子在地儒学遗迹的发掘和恢复。例如,第一代五经博士言德坚主持了文学书院、言子宅等重修工作,言如泗等曾参与游文书院的重建并重修言子墓等。下节将对此做详细介绍。
三、言子奉祀的祠庙化
由于地望的关系,常熟与言子有关的儒学遗迹分布较多。随着清代先贤言子后裔地位的提升和言氏家族奉祀资格的确立,言子的相关遗迹被重新发掘和拓建。祠宇是清代先贤奉祀制度下认定嫡系身份的证据之一,也是争取奉祀生名额的基础。雍正初年对先贤奉祀生曾有规定:“先贤有祠宇处,查明嫡裔给予印照为奉祀生。”[19]明代以前,常熟本地的言子奉祀主要是围绕文庙祭祀空间展开,在文庙左近附设言子祠。明清时期,随着奉祀制度的逐渐形成,国家与地方的言氏奉祀生的增配主要是围绕言氏家族祭祀空间展开的。为此,言氏主持重修了先贤祠宇、墓地等遗迹,扩展出以常熟县言子故宅、家庙专祠、文学书院、言子墓为中心的祭祀建筑群。在奉祀制度的影响下,常熟本地及周边的诸多言子遗迹被有目的地修复和增建。在此过程中,为了增加奉祀生的人数,带有奉祀功能的先贤遗迹格外受到地方家族的重视。
常熟立言子祠,始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邑宰孙应时立祠,朱熹为记。[20]宝庆年间,言子祠移建文庙东侧,言氏后裔在左近享有居所并配给祭田,官给衣食,延师教导。文庙中的言子祠在建造之初即与在地的言氏家族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天顺三年(1459),知县唐礼修言子祠;成化二十二年(1486),知县祝献、教谕张景元复移建,时任佥事提调学校的杨一清(1454—1530)为之作序。清代康熙年间,知县赵濬重修,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御书“文开吴会”四字颁榜祠中。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时曾御书“道启东南”四字颁榜祠中;二十八年(1763)言子后裔言如洙修,题额曰“敕建先贤庙”;三十七年(1772)言如洙、言如泗重建文庙言子祠。文庙言子祠的存在是证明言氏祭祀传统的重要建筑,相关祠记等对言德坚康熙年间请设五经博士多有助益。
言德坚一支所据县东家庙,应是常熟言氏大支的家祠。明代以前,这一祭祀场所未受重视,仅有两任县令参与部分建筑的重修,这正与言氏此支在明代衰落的情况相符合[16]29。进入清代,随着宗族活动能力的提升,言森在顺治年间对此有所整修,并得到邑令周敏的支持。乾隆三十九年(1774),言如泗等进一步拓展了家庙建筑的规模,家庙专祠特设奉祀生一名[21]265。清代于历代先圣先贤及名臣名儒的墓地或祠宇所在地,设置若干奉祀生的名额,负责平日的祭祀活动。奉祀生不需要参加科举,但必须由所司祭祀的先人嫡系后裔充任。一旦成为奉祀生,便可得到一定的优厚待遇,因为奉祀生是生员,享有优免赋役的特权。自乾隆年间,通过参加临雍大典而入国子监成为常例,言氏子孙由这一方式获得恩贡身份的多出自县东家庙一支(见表1)。此外,奉祀生所属祠庙实际上也获得了半官方的身份,更易于争取各种地方资源。这是言子祠庙祭祀活动为家族子弟带来的现实利益。
文学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元至顺二年(1331),邑人曹善诚建,设山长主书院。明宣德九年(1434),知县郭南改建儒学西,巡抚侍郎周忱更其名为“学道”。明嘉靖十一年(1532),知县徐溁改为学中射圃。嘉靖末年,在地方士人孙楼(1515—1583)的请求下,知县王叔杲在言子墓不远处重建学道书院,不久便废弃。王叔杲的这次改建一般被认为是书院建筑之始。常熟人瞿景淳(1507—1569)为之作记,他在记文中将子游的儒学传统与地方教育相联系,希望扭转明初重祭祀而轻教育的风气,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县学重科举而轻实质的学风。[5]358万历三十四年(1606),知县耿橘迁建,又称“虞山书院”,申时行、王锡爵作记。耿橘在书院的活动被认为是理学在地化的实践。重修后的书院不仅传达了耿橘强烈的理学追求,其祭祀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书院居中的是子游祠,两庑镌贤哲像,东侧是学道堂,新建的弦歌楼院落附有子游祭祀空间。崇祯年间,知县杨鼎熙恢复,内存耿橘创建的有本、学道二堂。康熙四十六年(1707),参政马逸姿重修,他在记文中特地对言氏子孙提及“告尔子孙,肃奉蒸尝。俎豆修洁,黍稷馨香”[22],显然是在强调这一重建的书院建筑对言子祠祭的意义。这与《言氏家谱》中对文学书院“言氏家塾”的定性相呼应[17]3。雍正年间,五经博士言德坚重建之后,唯有承担祭祀功能的言子祠和莞尔堂留存,此后言子后裔多次承担了对书院的修建。到了咸丰十年(1860),书院独存祭祀建筑——言子祠。书院建立的初衷本是借言子文化身份阐扬儒家学术传统,到了清代,随着先贤奉祀的制度化和家族化,书院的祭祀功能甚至一度超越其教学功能。
正如上文所述,墓葬是常熟言氏争取言子祭祀权的重要保证,对言子墓的修缮从明至清有序进行。明弘治中,知县杨子器(1458—1513)曾表其墓。崇祯初年,巡按御史路振飞(1590—1647)再修。到了清代,对言子墓的重修更为频繁。康熙初,参议王儒重修墓道;二十五年(1685),知县杨振藻又修。雍正初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1677—1745)建石坊,题曰“南方夫子”,而苏松粮道王澄慧又筑墙垣卫之。乾隆年间,裔孙言如泗、五经博士言如洙等开始承担言子墓的修建工作,建御赐“道启东南”坊,又建遣祭文碑亭等[16]10;三十五年(1770)建亭供奉圣祖“文开吴会”额。随着言子后裔对墓园修建的参与,言子墓园逐渐成为言氏一族的私产。言氏子孙屡次拓修墓园,并在墓南建造祭祀建筑——松山房,园前有“道南泉”,取“道启东南”之意。对言子墓的一系列增建提升了言子墓的政治意味和儒家祭祀功能,也使林墓获得了稳定的奉祀生名额。在八十世孙言家鼎所辑《甲寅重修言子林墓纪事诗》的诸多诗词中即可看到修墓对增强言子文化影响力的推动作用(6)参见言家鼎《甲寅重修言子林墓纪事诗》,常熟市图书馆藏清刻本。甲寅应是咸丰四年(1854),八十世孙家鼎未曾承袭五经博士。。此后,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两江总督曾国藩拨款重修之前,言氏子孙都是祠墓主要的管理者和修建者。
除了祠堂与墓园,荒废已久的言子宅也在五经博士言德坚的主持下得以复原。言子宅在明永乐年间已废,晚明时一度成为天主教堂,在官方对天主教的打压下,到康熙年间言德坚任五经博士时,终有机会请复故宅。故宅“有司置木主而释奠焉”,将家宅成功纳入儒家祭祀系统。在六十七世衍圣公孔传铎(1673—1732)为言氏恢复故宅而作的记文中,言子故宅的住宅性质进一步减弱,孔传铎将之设计为南方文士习礼、诵习、观览的空间。言子宅在明隆庆间所得祭田也被追回[23],孔传铎寄望于言氏后裔能够依仗这百五十亩田地使言子奉祀持续不绝。衍圣公出现在言子宅复兴过程中,使得私宅的居住空间和礼仪活动都蒙上了强烈的官方奉祀色彩。实际上,言子宅的复兴不仅从思想上,也从制度上将言子祭祀纳入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祭祀体系,故宅奉祀生的设置也是基于故宅祭祀功能的重建。
在地方官府和言氏族人的协力下,常熟及其周边与言子有关的儒学遗迹被不断地挖掘出来。这些原本性质各异的遗迹,在先贤祭祀制度的影响下,开始向着先贤奉祀的核心功能转移。嘉庆、光绪等朝《会典》都记载了常熟县言子故宅、言子家庙、言子专祠、言子文学书院、言子林墓,分别设有奉祀生一名[21]265。由此可知,言子遗迹的祠庙化建设,正是对新朝先贤奉祀制度的现实回应。这些建筑的重修主要集中在常熟言氏七十五世言如洙、言如泗一辈,此时先贤奉祀制度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得益于五经博士和奉祀生身份的言氏县东家庙支,有效地利用对常熟、昭文等地祭祀场所的建设,将奉祀制度的利益稳定地传递给本支的家族后辈。
四、文学与儒学的消长
《论语》中孔子谓子游习于“文学”,此处的“文学”指涉较为宽泛。学界对言子早期“文学”形象的形成过程也有诸多不同的解释。[24]对言子思想的阐释固然受到早期文献记录的影响,但是到了明清,阐释的目的已经脱离了对《论语》精神内核的追求,被赋予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现实功能。在先贤祭祀制度不断发展的康熙年间,江南逐渐进入承平时期,也正是朝廷大力重建礼仪秩序的阶段,加上明清以来祀贤之风的兴起,地方儒家先贤祭祀愈发受到重视。此前的研究已经充分展现了作为地方文化标志的子游在理学发展过程中被不同的思想脉络形塑的过程。[5]325-398而明清以来更重要的形塑力量来自先贤祭祀制度的新变,在理学并不发达的苏州,儒家话语传统被以一种更为实用的方式建立起来。
言子所代表的儒家学术传统,常常被用以描绘区域文化风气。郡城社学之侧的言公祠重建于晚明,这次建造主要由申时行(1535—1614)主导。王世贞(1526—1590)在《重建言公祠记》中对言子所代表的吴地德与言的传统推崇有加,他曾赞叹吴地的文学传统由言子而拓展:“自是二千余年,而吾吴之文学遂以钜丽宏爽甲天下。”[25]虽然这里的“文学”并非专指文艺内涵上的文学,但显然王世贞并不否认言子的学术传统对辞章风格的潜在影响。
但地方对言子的期待显然并不仅仅停留在文艺上,以言子的学术源头为特征的文化表述逐渐渗透到地方学校的建设中。游文书院的重修即是一例。游文书院在虞山北麓,苏凌阿(1717—1799)在《重建游文书院记》中阐释书院的由来:“盖取汉书所谓游文六经之中,而又合于先贤子游之文学,此前人命名之义所由来也,溯自国朝康熙庚子,邑绅言翰博德坚、陶编修贞一诸人醵金购址,请于前观察朗山杨公爰创规模,嗣是拨田规画为师生膏火,数十年来鸿儒硕彦多出其中。”[26]此时已是清初言德坚得授翰博之后,从对“游文”的解释可以看到,言子学术对当时教育的影响方是地方士绅关心所在。这种以言子为南方科举基调的看法,在清代江南的学校中比比皆是。同治年间,李鸿章(1823—1901)为江南贡院所写的碑文称:“茅蒋以东具区、洮滆之壄,泰伯、仲雍、季札、言子之遗风存焉,温文而尔雅。”[27]他认为,正是类似言子的名儒造就了江南“冠冕半天下,丞相、御史、翰林学士之属,更仆不能数”[27]的局面。
在科举之外,清代以来言子祠祀的发展对言子身份的表达也有所影响。言子开始成为地方儒学格局乃至政治秩序的代表。在晚明言子祠的祭祀空间中,有从祀言子的本地名人十余人,在孔庙空间之外形成由孔子至言子而扩张至诸名儒的地方儒学传承的格局,通过祭祀空间的表达,进一步重申了对正统的儒家秩序的尊崇。[28]随之而来的是对言子形象的官方改造,其地方治理能臣的形象逐渐掩盖了“文学”的身份,成为清初言子祭祀所推崇的儒家官吏的代表。乾隆四十二年(1777)游文书院重修时,言如泗在重修的记文中便强调“言子流风,则思前贤弦歌之化”,将言子的政绩作为其事迹的重点之一。雍正二年(1724),苏州府常熟县由于人口、赋税繁多,分出其东部设立昭文县。雍正九年(1731)成书的《昭文县志》亦有言德坚、陶贞一等的参与。编纂者虽然在县志的序中盛赞子游“开南方文学精华”,但也强调了对地方“仲雍之礼让,言子之弦歌”的渴望。[29]昭文县后也新修言子习礼堂,并设有奉祀生一名。[21]265由奉祀生之设观之,言子习礼堂内应亦没有言子祭祀空间,国家奉祀制度与地方儒学传统正是在儒家礼仪的层面得到了统一。
与文人家族内的儒家礼仪活动不同,言子故宅和家祠等的奉祀活动必须被纳入先贤奉祀的制度体系中讨论。在地方上衰落已久的言子后裔,正是通过清初先贤奉祀制度得以复兴。常熟言氏县东家庙支的家族复兴几乎都来自奉祀资格的授予,这也进一步提高了清代言氏家族在地方事务和科举事业上的参与热情。反之,对言子地方形象的形塑也不免受到奉祀制度的影响而迎合清廷的需求。地方儒学的传统和新王朝的政治话语形成一个往复的闭环,相互给予政治论述的合理性。由地方文士构建的对言子祭祀活动的文化表述,虽然不免要凸显地方的儒学文化色彩,但更重要的还是回应清廷崇儒的整体设计。经过清早期先贤奉祀制度和地方儒学的建设,相关的论述已经越发成熟,先贤家族和地方儒学传承都被更深入地卷入清王朝的控制系统。
五、结 语
清初江南儒学遗迹的复兴,可以说是在清朝奉祀制度指引下,常熟言氏因家族利益做出的理性选择,虽然这种政策的施行是一种权力与精神交织的复杂的过程[30]。从清廷的角度来看,所谓“大一统”的局面绝非仅仅体现在疆域上,而是包含了借由文化政策的实施而达成的涵摄融合的局面。从地方家族的角度来看,为了适应国家先贤祭祀制度,对先贤遗迹和思想的再发现已经改写了地方家族、管理方式和历史话语的传统面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发明”。而处于帝王和家族之间的各级文士,他们既通过对言子传统的论述实现了强化江南地方文化符号的需要,又使得言子的传统更加切合于清初尊儒的官方主流思想背景。言子的地域色彩、言氏家族的发展过程都体现了清代江南儒学发展的特点。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言子奉祀可以成为窥视地方文化和朝廷制度互动的例证,生动诠释了清代先贤祭祀制度的发展如何从实践和思想上形成对江南地方社会的深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