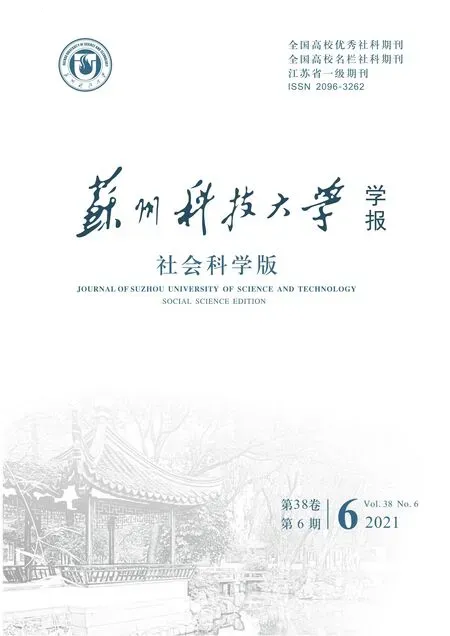昆剧现代戏《江姐》:在传统中“绣”出现代性*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近年来,现代性(Modernity)成为戏曲研究领域一个颇有热度的话题。它关涉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戏曲是现代戏曲?戏曲的现代性内涵何指?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戏曲作品是否天然地具备现代性?有学者提出:现代戏曲本质上“是现代人创作的具有现代性思想的戏曲”,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在于“用反思与批判等现代精神,平等、独立、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理念去观照并表现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心路历程”;其思想内容包括四个层面的表达:民族独立与解放,对专制制度下不公平、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反抗,人的个性觉醒与解放,人的存在困境与自由追求。[1]145-146这个观点也可以这样理解:现代戏曲如果不具备现代性思想,内容不在这四个表达层面,即使它产生于现代社会,也不具备现代性。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昆剧现代戏《江姐》,毋庸置疑,它具备并充溢着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品质。它用红色的文化底蕴、金色的昆曲“丝线”,在主题、形象、情感和美学形态等层面,精心“绣”出了现代题材戏曲的现代性。
一
这个取材于红色经典文学的现代昆剧作品,起意于2020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特邀编剧王焱根据同名苏剧演出本改编,2021年3月22日,苏州昆剧院《江姐》剧组正式成立,6月25日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成功。昆剧现代戏《江姐》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主创群(1)昆剧现代戏《江姐》出品人俞玖林是国家一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以擅演青春版《牡丹亭》柳梦梅而著名,此外还饰演过唐明皇、张君瑞、潘必正等角色,现为苏州昆剧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统筹为唐荣、周雪峰、杜昕瑛;剧本改编者是北方昆曲剧院曾获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及其他诸多奖项的著名编剧王焱;导演是表演和导演经验都很丰富的苏州昆剧院原党支部书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吕福海;音乐设计和配器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著名昆曲作曲家孙建安,曾多次获得各级各类作曲奖,现任苏州昆剧院音乐总监;音乐指导是出身于笛箫工艺世家的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理事邹建梁,曾多次获各级演奏奖;舞美设计钟婉靖,灯光设计徐亮,服装设计柏玲芳,均奉献过诸多优秀作品。该剧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江姐扮演者沈丰英、甫志高扮演者周雪峰均是国家一级演员,分别荣获第23 届和27届戏剧“梅花奖”;沈养斋扮演者吕福海、孙明霞扮演者沈国芳、蓝洪顺扮演者唐荣,均为国家一级演员;双枪老太婆扮演者杨美、唐贵山扮演者徐栋寅均是国家二级演员;华为则由优秀青年演员章祺扮演,束良、吴嘉俊、殷立人、吴佳辉等优秀青年演员在剧中分别扮演警察、秘书、烟贩子等角色。江姐的造型师是国家二级演员胡春燕。该剧6月25日首演和7月23日第二次公演时,江姐均由沈丰英扮演;9月24日中国昆剧艺术节的演出和10月3日江南文化艺术节的第一场演出,江姐由翁育贤扮演;10月8日江南文化艺术节的第二场演出,江姐则由杨美扮演。,演员在舞台上各司其职,配合默契,使该剧的演出焕发出耀眼的光辉。2021年7月23日,昆剧《江姐》在中国昆曲剧院第二次公演。这个日期乃是出自苏州昆剧院的精心选择,因为100年前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昆剧《江姐》紧密应和着建党100周年的矫健步伐,用昆曲歌颂英雄故事,以振奋民族精神,赓续红色基因。
全剧南北曲兼用,以昆曲的曲律形式诠释这一经典革命题材,但主题歌曲《红梅赞》和《绣红旗》却完整承袭了歌剧《江姐》中同名歌曲的歌词与曲调,只不过演员改用了昆曲旦角发声方法来演唱。当这两首为观众所熟悉的主题曲的经典旋律在剧场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舞台上缓缓展开时,昆剧现代戏《江姐》也以它刚健秀美的艺术形态,唤醒了年长受众深刻而美好的记忆,颂扬了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红梅”品格和“红岩”精神,从而“绣”出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最强现代性。
毫无疑问,歌剧《江姐》的成功改编与演出,与原著《红岩》本身酿就的“红岩”精神的深厚内涵密不可分。小说描写的共产党人那种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献身革命的浩然正气、宁死不屈的坚毅品格,在以革命先烈江竹筠为故事主人公的歌剧中得到了明亮、纯粹、突出和集中的表现。歌剧主要作曲人之一金砂,在羊鸣最先为阎肃作词的《红梅赞》第一句“红岩上红梅开”写出主题旋律的雏形之后,灵感顿发,加上甩腔唱法,融进江南滩簧音调和四川扬琴音乐,完成了《红梅赞》这首刚柔相济、浓情饱满的主题曲。金砂又将自己对狱中江姐期盼解放的喜悦与视死如归的意志两相交融心境的体悟设想,写成了柔和婉转、深情绵邈的《绣红旗》曲子。金砂1977年自川入苏,进入苏昆剧团工作并担任苏州市音协主席,直至1996年去世。昆剧现代戏《江姐》虽改编自苏剧,却保留了歌剧中《红梅赞》和《绣红旗》这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也有纪念金砂这位优秀的前辈作曲家的用意。7月23日晚,《江姐》在中国昆曲剧院公演结束时,舞台两侧幻灯字幕明确表示,借此剧的演出以纪念金砂。它表达的是苏昆人对前辈音乐家的敬意,对党的深情礼赞。
不仅如此,对歌剧《红梅赞》《绣红旗》词曲的推崇,还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经典所成就的“新传统”高度的一种继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用昆曲这一传统的艺术样式来表现现代红色题材《江姐》,虽然传统戏曲样式能否表现现代题材已不再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但是,如何将昆曲的传统韵味和题材的现代价值融合一体,是一个极有难度的编创工程。编剧王焱在改创时,将全部剧情提炼为《送别》《惊讯》《智取》《被俘》《斥敌》《绣旗》六折,将原有的3个小时长度压缩为1小时40分钟,这就加快了情节节奏,以突出江姐“智斗—被捕—牺牲”的主线;同时剧本采用曲牌体,凸显了昆剧艺术的核心特征,这就使得昆剧《江姐》与其他剧种的改编本有了较大的区分度。值得称道的是,该剧大部分用北曲来诠释主人公江姐形象,如在第五场《斥敌》中,叛徒甫志高前来劝降,编剧用了一支北曲【骂玉郎】(见图1),让江姐驳斥甫志高的卑劣行为。

图1
多用北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昆曲常用水磨腔以求柔软婉曲效果的印象,而给观众以铿锵有力、刚健不屈的艺术感觉。这无疑对英雄江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文学角度看,这里不过是用了三个典故加上排比修辞,形成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斥敌效果。但从音乐情绪看,又是一种层递与推进:首先,从节拍看,这一唱段用的是四分之二拍,本身比较短促。其次,从音符看,这三个句子起始字前以及“项伯”“秦桧”“吴三桂”三个人名后,都分别用了一个换气符,在“楚王”两字间又用了一个休止符,加强了曲词的顿挫感。最后,从音调看,第一句大多是中音,句末有三个低音;第二句全部是中音;第三句则大多是高音,四个中音全都是较高的6。三句唱腔实际使用了音乐上的“上行模进”手法,这就使得三个旋律相似的乐句在不同的高度重复出现,形成一种情绪激烈、声色俱厉的效果。在乐谱的“敌”与“到”字之间,编曲人特地加了Mono mosso,表示此处速度稍慢而力度加强,以充分表达江姐对甫志高的愤慨情绪。再加上选用的曲牌名【骂玉郎】,语义双关,江姐身陷囹圄时勇毅忠贞、宁死不屈的英雄品格,获得了坚强有力的表现。
即此可知,江姐唱段大多使用北曲曲牌,实际上改变了昆曲旦角以温婉细腻为主的演唱风调,演绎出这一形象超凡脱俗、不让须眉、以天下为己任、以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为信念的英烈风骨。这一女性英雄的铿锵刚健风骨,相对于传统昆曲旦角的艺术风情是一种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剧现代戏《江姐》很好地诠释了现代性的义涵,以昆剧的“针线”,“绣”出一片新天地。在这样一种慷慨激昂的基调中,该剧袭用歌剧《江姐》的两支经典主题歌曲《红梅赞》和《绣红旗》,既是一个理想信念的秉承,也是一种音乐风格上的调和。它们以其明亮而又细腻、激越而又婉转的曲调,在全剧音乐流程中起到了提亮情感与意绪的作用,就像红岩上的红梅,又是牢狱中的红旗,用一种灵魂的语言唱出了全剧的最强音。
编剧持有的理性认知,是昆剧现代戏《江姐》臻至现代性高度的起点。编剧王焱对昆剧《江姐》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是:“首先是昆曲的,然后是现代的。昆曲就像一条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河流,她跟哪个时代都不违和,她坚守自己的根本,同时流淌到哪个时代,便吸收与随顺哪个时代。这就是昆曲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2)此处所引编剧王焱的观点,为2021年8月6日笔者对王焱的电话采访,文字经王焱本人阅定。以下所引编剧王焱、导演吕福海(扮演沈养斋)、周雪峰(扮演甫志高)等人的观点,除特别出注外,均来自笔者对他们的电话采访,相关文字也分别请他们阅定,皆不再出注。在形象层面,王焱认为,江姐成为革命者而且始终不渝,是因为她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没有时代限制;而现代性“首先在于现代人的这种悲悯情怀对于当代人的启示上”。悲悯意味着现代人能从哲人的高度博观世间苦难,以日月光照天地的慈悲之心怜悯生命万物,自觉地救人民脱离苦海,将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视为当仁不让的重任。
二
昆剧《江姐》在演绎主人公江姐的悲悯情怀时,并不是单纯强调她性格中刚强坚韧的一面,而是在紧扣情节主线、快速推进节奏的同时,以饱满而细腻的词曲,刻画了江姐内心深沉的爱,从而在江姐坚毅品格和无私精神中渗透了浓郁的人性光辉。
这种爱,既体现在江姐奔赴华蓥山前,忍心将襁褓中的孩子托付他人照料时;也突出地表现在她去华蓥山途中,满心期待和丈夫彭松涛会面后并肩作战,却惊悉丈夫牺牲并远远望见丈夫的首级被悬挂城门而浑身战栗之时。江姐到了华蓥山,双枪老太婆率一众游击队员与她会合,尽力想隐瞒彭松涛遇害的消息,而江姐也拼命克制内心的悲伤,言不及情,最后终于控制不住,扑向双枪老太婆的怀抱中失声恸哭。一边是游击队员怕江姐伤心而绝口不提,一边是江姐怕众人乱阵、更不愿披露自己软弱也沉默不语,此时台上氛围压抑之至,殊不知却是感情风暴掀起之前的片刻安宁。江姐的扮演者沈丰英此时面部表情看似平静,却是一种满溢哀伤的平静,待她用圆场碎步扑向双枪老太婆时,观众席上寂静无声。无论是早已观看过歌剧或其他剧种的《江姐》的年长观众,还是从未看过《江姐》题材电影戏剧的年轻大学生,心灵无不受到深深的震撼。舞台上的平静,观众席的寂静,都是人性深度的最好证明。
这种符合人性的情感表现,并没有削弱江姐形象刚强勇毅的品格力量。第五场中,沈养斋以对孩子用刑来威胁江姐,江姐心中作痛,但想到的却是“抛下我一子,只为天下儿”,共产党人为天下百姓谋幸福的胸怀和信念即刻彰显。第六场中,江姐临上刑场之际,写信给襁褓中的儿子,编剧用了南曲【集贤宾】来表达她对孩子的不舍和悲痛,传达出一种悲戚惨淡的情绪,柔婉而深情,但江姐心中仍然激荡着舍小我而利天下的信念,说“将儿抛别,只为了千家宅眷”。随后江姐又向狱中姐妹道别,嘱咐她们日后孝敬父母双亲,新中国成立后努力为党工作。从母子生离之悲,到夫妻阴阳两隔之哀,再到母子死别之痛、姊妹诀别之伤,主演沈丰英非常到位地演绎了这一条缠绵悱恻的情感辅线,使之与情节主线彼此交织、刚柔交错,血肉饱满地塑造了江姐这样一位女性英烈的光辉形象。
主演沈丰英以擅演风流婉转、缠绵悱恻的杜丽娘一角而著称,这次出演江姐,扮相俊美英爽,发声清亮明朗,将江姐刚毅的品格与深情的意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沈丰英盛赞编剧善于根据剧中人物的情绪特征来选用相应的曲牌(3)2021年7月中下旬,笔者带领大学生暑期专业实践团队到苏州昆剧院学习,恰遇7月23日昆剧现代戏《江姐》在中国昆曲剧院公演,于是与学生们一道观赏了这场演出。本文所引沈丰英观点,均出自7月23日演出结束后笔者对她的现场采访,相关文字均经沈丰英本人阅定。,如最后一场为表达母子别离的悲戚而使用南曲【集贤宾】,就使得曲牌情绪与人物情绪紧密贴合。她认为,一个出色的演员,“在舞台上该安静的时候安静,该表达情绪的时候,要努力带动观众的情绪跟随自己的情绪而转变”。而她则竭尽所能去表演一个受众喜爱的人物,自然会深入观众的内心,也就会达到理想的舞台效果。
角色表演上的这种努力,也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江姐》题材中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甫志高。在以往的戏剧舞台上,这个人物容易被塑造成卑劣、猥琐、阴暗的小人形象。昆剧现代戏《江姐》中,周雪峰没有将甫志高一角概念化、脸谱化,而是融合昆曲“生”与“付”两种角色的技法,演出了这一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周雪峰工小生,有冠生、巾生角色的丰富体验。昆曲巾生潇洒、飘逸,血气方刚,书卷气足;冠生则是年龄稍长的生角,趋于稳重大方,台步和动作幅度大于巾生,速度稍缓;付角则多是有一定文化修养又有身份的人物,个性内向,念白缓重。甫志高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稳定的家庭生活,被捕后叛变革命,又来劝降江姐,人生道路和个性气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长篇小说描写这种过程容易,戏曲则大不易,因为戏曲长度有限,次要角色的戏份更有限,以有限之时长演绎个性变化之过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周雪峰却以其独到的设计和出色的表演,完成了这一变化过程。出场之始的甫志高,西装革履,年轻气盛,虽有些浮华,但态度很积极;叛变后的甫志高貌似稳重,以过来人身份“语重心长”地劝江姐珍惜年华,“迷途知返”;当解放军兵临城下、重庆即将失守时,又惊慌失措,苦苦哀求沈养斋带他一起逃亡。周雪峰将传统昆曲中巾生、冠生和付角的表演身段用在甫志高角色不同阶段的扮演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个由革命者到叛变者个性激变的过程。
关于这个角色的定位,周雪峰认为:“他是年轻人,又是读书人,不是说一定要叛变,只是革命意志不坚定,遇到敌人抓捕后,严刑拷打扛不住,就叛变了。我设计这个人物还是个读书人,不是很矫情化的人。劝江姐时内心很矛盾,羞于见江姐,但又被区长逼去劝,一直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从年轻浮华到意志不坚定,到叛变、劝降,过程化的个性变化通过阶段性的角色移位获得实现。周雪峰对甫志高劝降江姐时郑重而纠结的心态,尤其把握得细腻准确。编剧这时用了一支南曲【金梧桐】(见图2)。曲子用了四分之四拍,略见缓慢;每句开头都用了换气符,且起字均为半拍,又显急切。这段在演唱时,去掉笛子,只用单弦和琵琶伴奏,奏出了阴阳怪气的声调。周雪峰演唱时,真嗓和假嗓结合,谱中凡是中音5和6,都运用假嗓来处理,即曲词中“时”、“英”、“姿”、“华”(后一拍)、“零”、“识”、“饱”、“须”等八个字均用假声,其他字词均用真声。这样一来,这段唱腔便时高时低、时沉时升,飘忽不定。表面上看起来,甫志高劝江姐珍惜年华和学识,学会明哲保身,是为江姐着想;而真假嗓的交错运用,呈现出阴阳怪气的格调,恰能充分地表达甫志高身为叛变者的两面性。笔者闻声顿生“惊艳”之感,认为这一唱段是该剧中演员用音色、音调表现甫志高性格与心理的最精彩之处。
另一个让人拍案叫绝的角色是沈养斋。当然,这是一个反派角色。在红色题材的作品中,反派角色一般是阴狠、狡诈、残暴、贪酷的。沈养斋的扮演者吕福海却认为,沈养斋“不是没头脑、不学无术的大老粗”。这就与以往相关剧种中的这一人物定位拉开了距离。《江姐》故事发生在1948年春至1949年冬,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作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沈养斋,对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共军气势如破竹,我军兵败如山倒。”他的内心其实是比较焦虑的,但他有想法、有手段,有人在场时,他沉稳、冷静、狡猾、坚决;没人时也会暴露内心的隐秘与不安。第五场《斥敌》,吕福海上场时,绕过舞台中间靠后的办公桌,从中间往舞台正前方走,用了传统昆曲的圆场碎步,膝部弯曲度比较大,急促地冲向前去,再加上紧张愤恨的表情,非常传神地传达出沈养斋的阴郁、焦虑、急躁和戾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是表现沈养斋有别于其他剧作同一人物特点的精彩片段。最后当共产党已经打进重庆时,部下纷纷劝他逃去台湾,他让部下去,自己坚决不离开,作垂死挣扎。昆剧现代戏里沈养斋形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戏剧在当代的现代性特质。
曾有研究者提出,现代戏曲包含现代生活题材、情节整一性的文体原则、现代化的演出场所[2-3];但有学者认为,这些不过是“现代戏曲”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不是“现代戏曲”的当然的、必须的、本质的属性,决定一部戏曲作品本质上是否“现代戏曲”的关键是“‘现代戏曲’的精神内核,即现代性品格”[1]146。然而仅有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作为戏曲文学作品,人物可能是平面化的,而当人物呈现在舞台上时,当一个有主观能动性和舞台创造力的演员,用极富生命力的眼神、表情、唱腔、身段去表演这个人物时,剧中人物可能就产生一种激变,形象的平面性淡化,其立体化元素却被激发出来,形成人物的新特质。换言之,对党忠贞、重情重义和刚柔相济丰富了江姐性格的内涵;从文质彬彬、矛盾纠结到叛变失节、阴阳怪气,再到惊慌惧怕、只求自保,多种性格因素过程化地阐释了甫志高形象的内在流动;头脑清醒与佯装镇静的结合,刚愎自用与焦虑不安的糅杂,有人时与无人处行为动作、话语心态的截然不同,都强有力地表达出沈养斋性格因素的多面性特征。这就打破了红色题材现代戏在演绎英雄人物时的“高大全”模式,也不再拘囿于单一平面地表现叛徒角色的虚伪胆小、国民党军官的阴狠狡诈,形象内涵不再停留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4]的层面;而是凸显了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性。有学者描述过“戏曲新形态”八条,其中第五条是“注重塑造人物,突破人物描写的类型化”[5],与此处所说出自一样的思考,只是舞台上人物类型化的突破,更多要靠演员用思想和灵魂、用“手眼身法步”技法来演绎。
三
用昆曲形式搬演《江姐》这样一个传统红色题材的作品,最大的难题是文本改编。昆曲的创新如何在内容上进行?昆曲要不要、能不能改编现代题材戏?吕福海认为:“现在大家所谓的创新,多半是形式上的和表面化的,内涵上做的的确不够。因为昆曲历史悠久,常年做的就是传承传统,最难的是创新。昆曲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现代戏模板,能否反映当代现实题材,我们也在做积极的探索。昆曲今后必定会走上现实题材,如果永远不能,那么昆曲很难走得更远。”(4)本处所引吕福海观点,出自2021年7月23日笔者对吕福海的现场采访,相关文字经吕福海本人阅定。主创群对该剧是充分肯定的,觉得这是昆曲,又是“现代戏”,证明了改编的成功。 昆曲须采用“曲牌体”,这是昆剧的核心要素,也是昆曲剧本有别于其他剧种的剧本的本质特征。换言之,就是要用传统的曲词写作形式,来表现红色题材的内容,这就对编剧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古代戏和现代戏之间取得平衡,以更利于昆曲的发展?主演沈丰英认为,昆曲新编的剧本少,它的难处在于要用曲牌体,如果离开了昆曲的艺术本体,就不是昆剧了。而昆剧现代戏《江姐》的编剧王焱坚持用“亦古亦今”的原则来创作,在运用昆曲曲牌来表情达意时,绝无违和感。全剧有北曲,有南曲,有集曲,多处还采用南北合套,如劝降环节,甫志高【金梧桐】是南曲,随后江姐【骂玉郎】则是北曲,南北合套的效果,是在甫志高的阴柔纠缠后,凸显了江姐的慷慨愤激。
作曲人孙建安根据相应的曲牌、唱词的四声、人物性格和所处的具体情境等,设计每一段唱腔、音乐并配器,为《江姐》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甫志高唱【金梧桐】时去掉了笛子只用单弦和琵琶,江姐唱【骂玉郎】时字字铿锵、声声慷慨,均出于孙建安的设计。在曲白关系上,编剧王焱是这样安排的:“一方面保证昆曲的基本规律;一方面处理好唱和念的关系,把不好处理的地方交给念白。即使念白,也尽量保持昆曲的诗性特征,这样二度创作中就可以用韵白而不至于用普通话了。”在念白上,导演吕福海亦坚持以中州韵为主,但考虑到当代受众的因素,有一些地方也适当参照了普通话的发声。这些使观众普遍认同该剧的形式、风格都属于“昆曲”。
用昆曲搬演现代戏《江姐》,还有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传统昆曲“手眼身法步”这些属于“术”的层面的问题。该剧基于题材的原因,传统昆曲程式化的台步和手法要改造,水袖不能用,身段要调整,眼神表情的使用均要符合剧情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圆场”则要适当运用。在实际演出中,江姐、孙明霞、沈养斋等角色或多或少都用到了圆场碎步,这就又在技法的层面体现出该剧的现代性来。以演古代贵族少女杜丽娘而著名的闺门旦演员沈丰英认为:“古典戏中花旦、闺门旦都是长水袖,舞蹈动作比较多,流动性比较强;现代戏流动性的元素少一点,特别是现代革命题材的戏,刚硬铿锵的成分就要多一些。”昆曲表演讲究规范的程式,《江姐》题材却规定了舞台表演必然要冲破程式的束缚。沈丰英不畏挑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该剧在舞美、灯光、服装、造型、道具等方面的表现,也是值得称道的。主人公江姐高挑身材,短发齐肩,最后一场中一身蓝旗袍,加一件红色坎肩和一条白色长围巾,承袭了很多剧种演出时江姐的经典风格。为了配合这一风格,前面的几场中,江姐的衣服或为白底小蓝花的斜襟短衣、藏蓝色长裤,配一个蓝底大白花的手提布包;或为深蓝底小白花的斜襟短衣;或为米色风衣;或为纯蓝斜襟长褂,胸前两条从左肩斜伸向右下方腰胯部的红色鞭痕,右臂亦有一条。全剧服装简洁朴素而又庄重鲜明,很好地衬托了江姐这一女性英烈的形象。江姐和狱中姐妹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之余开始“绣红旗”。这是《江姐》题材的影视戏剧作品的经典环节,自然要突出表现。原著《红岩》中,江姐等人只是听说了“五星红旗”,但不知道五星如何分布,因此在红旗的四角和正中各绣了一个星。后来改编的各类剧种中,五星有四边分布的,也有标准分布的。昆剧现代戏《江姐》剧组采用标准的国旗,吕福海认为,这样设计“观众不会有异议”,而且“戏剧本身是艺术,艺术可以美化”。这种为受众群体考虑的艺术设计,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江姐》作为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元素的多元呈现。
昆剧现代戏《江姐》演出有没有什么遗憾?导演吕福海认为,《江姐》是2021年年初赶排的,如果有时间好好地磨一磨会更好,昆曲改编现在还是有点粗糙,音乐的配合,舞美的创作,还有待提高,目前正在进一步加工。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首先,昆剧现代戏《江姐》是产生于当代社会、当代人创作并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优秀戏曲。它选择江竹筠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牺牲小我的现代红色题材,歌颂共产党人的“红梅”品格和“红岩”精神,达到“现代性思想”的制高点。
其次,该剧用传统昆曲形式演绎现代戏曲,以其有限的舞台时长,塑造了性格内涵丰富的、动态发展的、立体多元的人物形象,打破了历来红色题材现代戏人物塑造中单一、静止、平面的模式,突破了类型化人物的窠臼,在个性化形象上拥有了“现代性品格”。
最后,该剧在对昆曲的诸多美学形态传承中做了改造和创新。它用曲牌体编写文本却又自创新风,袭用昆曲各类行当的唱念发声却又时时创造新声,在使用传统舞台技法之时又新增诸多当代元素,尤其在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审美层面突出了当代中国才有的红色因子,从而获得了美学的“现代性形态”。
要言之,昆剧现代戏《江姐》在传承传统中用红色底蕴和金色“丝线”,精心“绣”出了它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