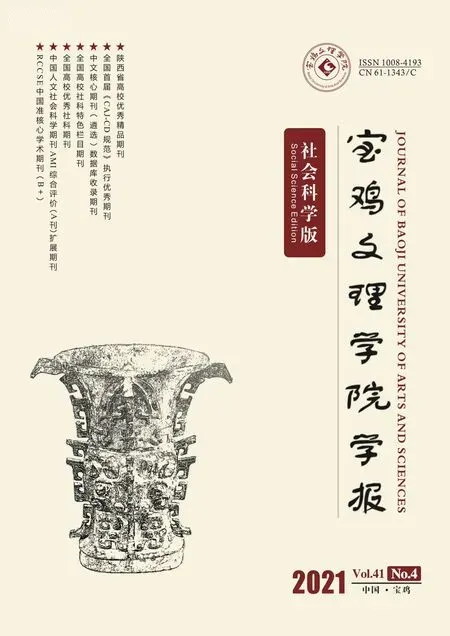嵇康对“君子”的解构与建设*
张盈盈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所,安徽 合肥 230053)
嵇康生长在魏晋时期的大环境中,他的思想与传统儒家差异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异端”。他激烈地抨击“名教”,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鲁迅称嵇康表面抨击礼教,实际上是把礼教当“宝贝”。在嵇康诗文中,提到“君子”大约三十余处,体现出其对儒家伦理道德真谛的坚持以及对“君子”的重视。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他与吕长悌绝交时说“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1](P230),这里的“君子”是指代他自己;他在《家诫》中以“君子”期许子女,可见他是用生命力行君子之道。魏晋时期的学风虽然崇尚道家,但是嵇康与“儒家”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晋书·嵇康传》称其“家世儒学,少有儁才”,《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载,赵至在四十岁那年“入太学,时先君(即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此外,在嵇康入狱期间,“太学生三千”曾上书为嵇康求情。在嵇康成学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守一经”“专一家”,而是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儒家与道家。因此,嵇康的君子人格的内涵也呈现出儒道融合型态,但万变不离其“儒”。
一、以“真”驳“伪”
“君子”一词由来已久,君子人格一直是儒者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模式发展到魏晋时期,受魏晋崇尚自然风气的影响,在人格型态上有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嵇康的君子观中。《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家世儒学”,但是他对君子诠释的路径很特别。嵇康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1](P402)在这句话中,嵇康对“君子”的内涵做了两个规定:一是“心无措乎是非”,二是“行不违乎道”。在《释私论》中他将“君子”与“小人”对比:“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而对于“小人”则以“匿情为非”。所谓“匿”,就是隐藏、隐瞒,也就是伪匿、不真。君子高贵的品质则是“贵乎亮达”,所谓“亮达”就是光明磊落,率真而为。可见,在嵇康的视野中,“君子”最突出的本质内涵是“真”。这个本质体现在他对“公”与“私”之辨的讨论中。
公和私则是指人对待自己思想感情的态度是公开还是隐匿。嵇康为了说明这种复杂的关系,举了一个“第五伦”的例子。第五伦是东汉士人,其身居高位,以清正廉洁著称,敢于公开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杂念。《后汉书·第五伦传》载,有人问第五伦是否有私心?第五伦回答说,他兄弟的孩子生病,他一夜“十往”,但是“退而安寝”。自己的孩子生病了,“虽不省视而竞夕不眠”,虽然没有去看,但是彻夜未眠。第五伦说也许这就是私心,但嵇康认为,“私”是指隐匿,第五伦毫不避讳地讲出来,是属于“无私”。对自己兄弟孩子探视而不关心是“是非”问题,公私与是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故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心)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虽欲之伐善,情之违道,无所抱而不显者,不可谓不公。”[1](P403)心中虽然怀有善念,但是隐而不宣,这也叫作“私”。情欲虽有不善,但能无所隐匿,这也叫作“公”。所谓“公”就是指公开内心的真实感情,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私”是指隐匿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即阴奉阳违之徒。不管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如何,只要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这都叫作“无私”。有私无私、有措无措是从本质上区分人善恶的标准。
“公私之辨”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讨论。“公”与“私”的关系涉及政治、社会、伦理等领域。自古以来“崇公抑私”是主流观点,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崇“公”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国之前,“公”代表统治者,“私”代表被统治者或者人民。如“天子”“封建君主”为“公”。“公”是古代圣王、君主遵循的准则。“国家”的概念出现后,“公”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这使得“公”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从伦理上讲,“公”与“私”涉及道德领域的区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立公灭私”的观点,“私”带有负面的色彩。《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子夏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致谓三无私。”[2](P1277)同时,孔子以《诗经》中的描述进一步颂扬了禹、汤、文王奉行“三无私”的德行,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圣王君主的追求。《吕氏春秋·贵公》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3](P20)若要社会安定与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公私的界限分明,“天下为公”、秉持为公是必走之路,这样会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可以看出,传统“公私之辨”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公私的讨论,其主流的价值必然以公为准,一般我们所谓的“公”,都被赋予了正当性,与之相对的“私”是要被抑制的,因其关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问题。
然而,嵇康的公私观,显然没有按照传统的路子来。在嵇康的伦理序列当中,“公私”比“是非”更为重要。他说:“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1](P403)事理也有好像错了却并不错,仿佛正确却并不正确的现象,故应仔细加以考察。其实,公私之辨即是真伪之辨。所谓君子“无措”为真,为公。“匿情”为“伪”,为私。可以说,在嵇康看来,君子最核心的本质是“真”。
那么嵇康为什么提“真”呢?因为他所处时代充斥着虚伪。这种虚伪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权者的虚伪。司马氏集团利用原本引导人们向善的道德名目,铲除异己,欺压百姓。阴奉阳违、口是心非之士太多。司马懿以服膺儒家名教著称,大倡“以孝治天下”。“高平陵政变”大批名士被诛三族,司马氏集团为了能够把权力牢牢握在手中,以名教的借口戕害异己,即便手上沾满鲜血,还要振振有词。司马氏废掉魏帝曹芳的罪名为“恭孝日亏,悖慢滋甚”,曹髦被杀的罪名为“不能事母,悖逆不道”。司马氏集团所标榜的“名教”显然是虚伪至极的,许多有识之士十分痛恨和厌恶。嵇康身为曹魏宗室的女婿,更是猛烈抨击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嘴脸。另一方面,嵇康所针对的“伪”是名教本身异化之伪。名教所倡导的伦理纲常与君子人格内涵是重合的。名教作为道德伦理规范的代名词,其内涵学界已广泛讨论。陈寅恪认为,“名教即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所宜奉行者。”[4](P182)余英时认为“名教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5](P358)。庞朴认为,“以名为教”是把符合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名目、名节并以此进行教化。[6](P391)名教的内涵由汉武帝时期的“三纲五常”发展到东汉章帝时的“三纲六纪”。所谓“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白虎通》曰:“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纲纪而旧目张也。”[7](P375)很显然,“三纲六纪”在“心性”的角度上更进一步丰富了“名”的内涵。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规范得一清二楚。诸父、兄弟、族人、诸舅是以有血缘关系的为主轴,“朋友”这一伦的加入,使得名教的内涵更为广泛。因为白虎观会议,把名教纲常用国家法典形式予以钦定,至此,“名教”就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尤其是在汉末察举清议制施行以来,“名”所产生巨大的号召力,让人们对其趋之若鹜,纷纷追求其“名”。因为拥有“名”的人可以飞黄腾达、名利双收,可升官、可发财。社会上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名士”,这一类名士并不是按照名教的道德修养获得的,而是通过欺世盗名。例如赵宣,“葬其亲而不闭遂,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于是成了“名士”,但是他这二十余年的服孝当中,却生了五个儿子。这些沽名钓誉之徒并不在少数,究其本质,是因为名教是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名教变成了仕途的敲门砖。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君子不是“真”君子,而是“伪”君子,以君子为标杆的名士由原本的“经明修义”到“刻情修容”,总之就是一字:“伪”!名教大厦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倒塌了。因此,汉魏之际选拔人才的标准变得多元化。儒家以名教标准、道德准绳的名声名节在此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曹操“唯才是举”,即一个人不仁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会被委以重用。这说明此时用人时在乎人的才智,不注重德行。汉魏之际的动荡不安,确实需要“有事尚功能”的准则,然而这对人们追求的人格模式也会造成影响。通常,我们会把嵇康所说的“真”与儒家所说的“诚”联系起来,二者有重合的内涵,但是嵇康所说的“真”,与道家所倡导的“自然”更为密切。从人格的角度上讲,“真”意味着回归人的“天性”,就像庄子说的“法天贵真”一样,这对儒家的君子人格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补充。
二、以“自然”解构“克己”
“伪君子”、伪名士的产生是时代造成的产物,当然,这也要归因于儒家君子人格自身的一些机制问题。儒家之君子讲“克己”“慎独”,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只要是不合于“礼”的行为,就要“勿视”“勿听”“勿言”“勿动”。遵循“礼”的规范从而达到仁与礼的统一是迈向君子的必经之路。这也“意味着礼成了人为的非出于自愿的强制性的命令”[8](P17)。强调道德自律,其关注点在于道德行为是出于自觉的,但并非是自愿的,因此,人们会为了好名声而造假,从而成为“伪君子”。由此,嵇康视野中的“君子”着重强调了“自然”这一特性。嵇康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铃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1](P402)“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伦理思想总纲。他对所谓“名教”妄图把自然人性束缚于伪善的仁义礼教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名教“非养真之要术”,因为要遵守其礼乐教化的规范,就要“克己”。
“克己”是“违其愿”,是反自然的。只有尊重人的内在意愿,才能体现自然原则。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1](P447)张叔辽作“自然好学论”,嵇康以《难自然好学论》对其进行了反驳。讨论“好学”与“不好学”和“克己”有直接的联系。儒家所讲的“君子之学”实际上就是“为己之学”。《论语》中有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做了进一步发挥,如《荀子·劝学》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对“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作出了具体的分野与阐释。“为学”的传统,一是古代儒生学以修身、为官的必经之路,也是统治阶层因教化、统治所需而倡导的,因此,由先秦到两汉,“以学为本”已然成传统,一方面提倡教化,另一方面如从贾谊的《新书·劝学》到徐幹的《中论·治学》,大多站在肯定的立场上肯定“学”。官方提倡“学”主要是为了推崇“教化”作用,这是汉代创立太学制度的宗旨,无论是曹魏、还是司马氏集团,这一点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对于“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嵇康认为,人类的本性好逸恶劳,世人所谓的“好学”是因为学可“以代稼穑”“学以致荣”,于是才“好而成习”,但是,这其实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世人以“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1](P407),但是嵇康却认为“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腐臭”。六经、仁义泛指名教,它的本质是“以抑引为主”,是压抑人类的工具。如果不对“六经”进行反思而盲目的尊崇,执书摘句、服膺其言并以此为修身法典,必然会造成上文所述之“伪君子”。嵇康所向往的文明时代是“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1](P447),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是“物理全顺”,人和社会等万事万物处于和谐自如之中。在原始的蒙昧时期,即使统治者未颁布礼仪法治,人们也自得其乐。然而,有了仁义与野蛮之分、有了人的阶层和等级之分、有了名分之分后,人类产生了有意为之的一些行为。诸如“始作文墨”“造仁立义”“制为名分”“劝学讲文,以神其教”,这对人类的文明以及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是人类给自己造的紧箍咒。嵇康说:“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1](P137)“前识”意为“先见”,比别人认识的早,即制礼作乐之人有的“先见之明”。《老子》曰:“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王弼解释为“前识者,前人而识也”。礼乐教化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的另一面即是对人的自然性的束缚和异化。嵇康反对束缚人性的名教,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外化于人的存在,过度的强调必然会导致人的自然性情被压抑。所以他提倡任自然。康中乾认为嵇康的“自然”是其所要追求的“本体”。他说:“自然有两重含义:一是人自己的自然之性;二是天地的自然本质。”[9](P144)这是嵇康哲学的目标和原则。任自然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它的另一种表达是“越名任心”。此“心”是“心不措乎是非”之“心”。它不以外界的是非毁誉等为念,而是根据自己的“心”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开展其生命活动。这个君子形象的设置,汲取了道家思想资源。所谓“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泊然纯素”“与天道为一指”,就是道家理想人格的形象。当然,所谓“任自然”之“自然”,并不是要追求人的自然属性或动物性,而是说追求人作为社会性存在之自然性。嵇康说:“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负其是。”[1](P403)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出现许多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情况,是人丧失了自己的自然本质。
嵇康反对“好学”并不是“不学”,而是主张君子要“适性而学”。所谓“适性”就是尊重人的自然之性。在嵇康看来,“好安恶危”“好逸恶劳”是人类的自然性情,为学不是站在人类自然性情的对立面去压制它,而是要认识到人类的自然本性后再去“为学”。首先,嵇康肯定人的基本生理之“欲”,这是自然之性的一种表现。饥而求食,困而求寝,这是维系人类生命的基本条件,这些皆“生于自然”[1](P296)。人类“循性而动”,没有掺杂任何智虑的杂念,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人不断满足自己欲望的动物性存在,会导致“役身以物,丧智于欲”。可见,嵇康并不同意没有节制的欲望。“循性”是对“嗜欲”的超越,即是循自然之性,具体的说是禀之自然、“归之自然”和“任自然以托身”。同时,人不为外物所役,理想的状态是“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耳、目、口、鼻等感官,依天性有“欲”的要求。心外物为活动对象的分别之“知”,会产生是非、好恶之价值判断,这种心“知”积存于心,久之形成主观成见。心有成见,从而有与人对立、竞逐之心。嵇康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所以嵇康反驳张叔辽说:“今之学者,岂不先计而后学耶,苟计而后动,非自然之应也。”[1](P407)即将“学”所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和各种好处都考虑进去后再学,这不是“自然本性”的表现,因为这种行为充斥着名利与欲望。为了达到名与利而学,一方面是“克己”,另一方面其心也不“淑亮”。
三、君子以“志”抗“命”
儒家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命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知命”指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命”就是人力达不到的极限之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无法超越的客观限制。对于“命”的追问源于古代人对周围发生的事件希望知道根本原因。人们不断在探索,或把这个原因归之于天,或者归之于神秘的力量,或是认为是宇宙运动的规律等等,种种解释就形成了一种命运观。[10](P147)从命运观来看,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家认为“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二者对于命运的理解都可以称之为命定论。君子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认为天命决定人事,知命的穷通、极限,但却不放弃主观的努力。所谓的“知命”更应该理解为人对命运的感知、体悟后所形成的人生态度。这对嵇康的命运观影响很大。
嵇康关于“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他与阮德如关于宅有无吉凶摄生的二论两答四篇文章中。阮德如作《宅无吉凶摄生论》,其观点是“宅无吉凶,惟重摄生”[1](P459),这是他继承汉代王充自然命定论思想。如王充说:“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11](P124)阮德如认为“夫命者,所禀之分也;信顺者,成命之理也”[1](P460)。嵇康将阮的观点归结为“命有定数,寿有定期,不可改变”[1](P474)的宿命论。嵇康还驳斥阮德如说,既然认为命有定数,寿有限期,那么如何解释“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1](P473)但是,阮氏并没有回答出“命何同言”“命何同短”的问题。孔子“慎神怪而不言”,不随便轻易地认为自己是“知变化之道也”,普通人更不能随便断言自己知神而言宅之吉凶。这是一种“妄求”的现象,应该窥探现象背后的深奥之理,对于未知的事物要勇于探索。嵇康的命运观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是时命,一是性命。嵇康曾在《幽愤诗》中说: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即穷困达通是注定的,我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幽愤诗》是嵇康在被长期关押时所作,单从嵇康命运的穷与达的态度来看,似乎很坦然。
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孔子身上充分显现。他一生都怀才不遇,带着学生到处奔波。《荀子·宥坐》记载:“孔子曰: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可见孔子对于逆境有着清醒的认识,贤与不贤是自身决定的,君子注重“求在我者”,即更加注重自身的修为与道德实践。 嵇康视野中的君子“知命”,体现出一种淡然与从容的风度。在《琴赋》中说“委性命兮任去留”,嵇康似乎并不在意生死寿夭,即“虽死生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和理自得”。他认为人能不能“尽性命”还要看人的主观努力,也就是说在力命关系上,注重人力。他在《养生论》中说:“似特受异气,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1](P253)嵇康认为,人禀气而来,是“禀命有限”的,必须“导养以尽其寿”。这是说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既不能长生不死,但也不会只有百年,只要导养得理,就可以达到“自身寿年的最大值”。即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1](P252)人禀受元气而生,厚度不一,可以通过后天养身以养寿命。嵇康所说的养生,是采取一种无心无意、顺其自然的态度。清虚静泰、养神的各种技术做到了,自然而然就长生了,不需要为了成仙而孜孜追求。
嵇康在命运面前强调人力,并以“志”肯定人力的作用。在《说文解字》中,“志”乃“从心从声,心之所之也”;《诗序》有“在心为志”。也就是说,“志”是个人自身对自己发展的意向。孔子肯定了“志”的作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时也规定了“志”的方向:志于道、志于仁。此后千百年,儒家都不曾将“志”抛离。嵇康吸收并改造了儒家之志。嵇康说:“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1](P544)“有志”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嵇康对“志”有着强烈的自觉。他说:“志在守朴,素养全真。”[1](P543)可知“守朴”、全真乃是嵇康固守的核心价值。《庄子·性缮》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按照庄子所说,古代所谓得志是指达到快乐自由,今之得志只是贪求逸乐,自我被物欲所蔽。嵇康融合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认为最高的守志,乃是人生在世,“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岂不自得”[1](P297)。这不是简单的如儒家所说的“立志”“行志”,而是“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装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1](P544),这是发自于内,不需要外力的规范与强制而有的“志”。在嵇康看来,作为人要有一定的志向才行。嵇康认为行仁义行义要进行思考与斟酌,以不伤害自身的生命为原则。无论个体处于何种境地,是穷还是达,都要守住自己的志向,保持节操,这就是“遂志”的表现。
四、“行不违道”的修养工夫
嵇康追求“游心太玄”的自然境界,但却掩盖不住他内心对仁义道德的坚持,因此,他所讲的“君子”既有儒家的君子人格以道德实践为基点的内涵,从内向外而扩充之强调生命的道德内涵和道德意义,又有“行不违道”的“弘道”理想。嵇康说:“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任心无穷,不识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1](P403)这一切都凝练在他的君子“行不违道”的修养功夫中。从“行不违乎道”可见嵇康的关注点在于君子之“行为”。
君子一生的志向便是以全部的生活活动实现道德价值。“君子”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仁义之性。道德原是出于人源发于内心善意,且表露于自身行为的道德实践,它既是自觉的,也是自愿的。袁济喜称嵇康是“从本体论上力主人性以澄明为本”[12](P209),他的人生论也是“将人性中最高的道德境界作为人的普遍性加以规定”[12](P209)。他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号称以“老庄为师”,在他的诗文中,多次出现对道家“游心太玄”的生命境界的向往。如“逍遥游太清”“饮露食琼枝”“远托昆仑墟”“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等等,以诗意的玄化意境将自己对道家境界的追求展现出来。在他的伦理思维中,道家“自然”的境界,是君子行道的出发点。在德行伦理学中,人的行为、情感、道德习惯都是被关注的重点,相对来说,“道德规则”的分量要弱一些。嵇康对君子行道做了细化的阐释。比如《卜疑》中的“宏达先生”有这样的特质:“恢廓其度”“常以忠信、笃敬、直道而行”[1](P235),即气度恢宏,忠诚、憨厚,任何行为都出于真诚,没有半点虚假。所以他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立足于天地之间。这其中,“忠和佞”“义和利”“诚和伪”“正和邪”之间的对立,选择前者或后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嵇康在狱中写了《家诫》,叮嘱其儿子所有的行为都要据“志”而行、与人交往要谨慎,诸如宏行寡言,立身清远。《家诫》的写作背景是嵇康入狱,自知不免才作此以诫子,想必句句肺腑,透露出殷殷亲子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自己一生言行的反思,这便是他心中真实的儒家仁义道德。鲁迅据此判断嵇康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可以看出嵇康对名教和社会礼法的重视。
儒家君子把孝作为实行“仁”的根本,这一点也体现在嵇康的“孝悌观”中。嵇康的孝悌观念体现在他对母兄的思念中。他说:“奈何愁兮愁无聊? 恒恻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郁结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茕茕, 内自悼兮啼失声。思报德兮邈已绝, 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咏潜藏,想形容兮内摧伤。”[1](P87)这首诗是嵇康对母兄去世后思念之情的描述,情真意切,声泪俱呈,深沉地表达了嵇康的悲痛心理。嵇康按照道德规范孝敬母亲,尊敬兄长。如他说:“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切。女今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1](P544)在《家诫》中,嵇康的语重心长,体现出他注重教养子孙。在“悌”的问题上,嵇康对吕氏兄弟用心良苦,力劝二者,希望吕氏兄弟不要反目,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兄弟之间“悌”的表现。当被反咬一口后,嵇康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表达了对吕巽的气愤与失望,其结尾说:“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1](P231)他的这些行为真切地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中注重孝悌人伦的伦理道德观念, 与其所谓的与自然为亲的竹林之游和逍遥物外的行为大相径庭。此外, 君子“行不违道”的特征还体现在嵇康的音乐修养中。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虽然以“和声”的特质否定了儒家传统乐教的“声有哀乐”,但是嵇康的乐论却以儒家音乐的移风易俗为归结点,认为乐教之本在于“心”,倡导在音乐审美中形成一种伦理人格,这也是他对君子人格的一种诠释方式。
结语
嵇康的君子论,不是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而取代儒家道德标准,而是关注道德动机以及如何行道,这提供了与德行伦理学对话的契点。如亚里士多德视野中的“德行”是来自生活中好的行为习惯,这个“德行”来自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但“行为”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并非强迫。之所以经过“理性”的考量,是因为行为不是“盲从的”,这种道德行为,更加契合人的内心所在。如嵇康说的“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错,而事与是俱也”[1](P235)。任心即是任自然,这种道德行为的发出,不是在心中思考后去践行,而是顺着内心去行动,其行为刚好与外在的道德规范相符合。这说明君子的道德行为是“随心”的结果,达到了行为动机与行为理由的统一。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打破了名教的束缚而又不失名教,并且赋予儒家“君子”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