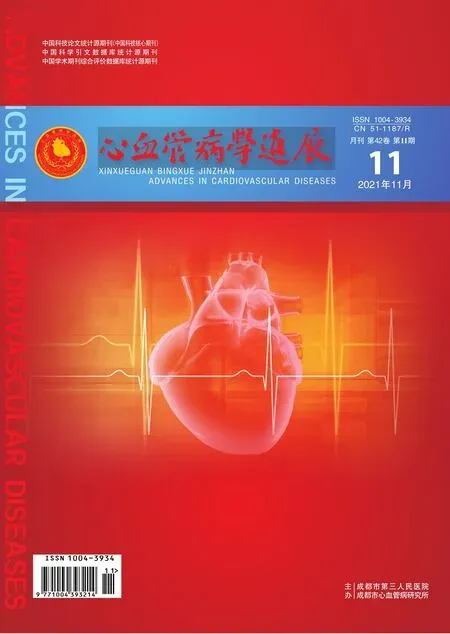肺动脉高压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新进展
陈秋宏 王春彬 吴奇,3
(1.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四川 成都 610500; 2.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四川 成都 610031; 3.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四川 成都 610057)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指由多种异源性疾病(病因)和不同的发病机制所致肺动脉血管结构或功能改变,引起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升高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继而发展成右心衰竭甚至死亡[1],其患病率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65岁以上患者的比例为10%[2]。
PH的病理生理机制较复杂,受遗传易感性、缺氧、炎症、DNA损伤、病毒感染和剪切力等多种致病性事件的影响[3],且发病率、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高。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出现右心功能不全甚至猝死,故早诊断、早干预和预后评估分层对提高PH患者的生存率、预后以及精准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右心导管检查是PH诊断的金标准,但其作为一种侵入性操作并不适用于筛查,目前用于PH筛查的非侵入性检查多为超声心动图,但其受设备及操作者的主观影响较大,存在高估或低估患者肺动脉压力和心输出量的可能,结果欠准确,因此,急需寻找既能进行PH筛查,同时又具有较高准确度的检测手段。生物标志物可从血液、尿液、粪便或呼出气体冷凝物等体液中检测,简单方便,成本低,而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临床进展和治疗疗效明确相关,为PH领域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现对PH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多肽/蛋白类生物标志物
1.1 脑钠肽和N末端脑钠肽前体
利尿钠肽是一系列具有类似分子结构并参与血容量和血压调节的激素。脑钠肽(BNP)和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的升高与右心压力负荷增加和心肌损伤有关,故可作为反映右心功能、PH预后评估和特异性治疗反应的标志物。BNP和NT-proBNP是迄今唯一在PH指南中作为风险分层和预后评估指标的血清学标志物,但其对预后分层的敏感度不高,特别是当其合并左心功能不全或肾功能不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2 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
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ST2)是白介素-1受体家族的成员,具有两种主要亚型:跨膜型ST2和可溶性ST2(sST2),其中sST2可充当诱饵受体,阻断白介素-33/ST2配体相互作用。sST2水平可反映右侧心脏的增大和功能障碍情况,sST2水平高的患者死亡和肺移植风险增加(HR=2.5,P=0.02)[4]。一项包含2 017例动脉型肺动脉高压患者的队列研究表明ST2与肺动脉压力和血管阻力成正相关,与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呈负相关。ST2增高预示死亡风险增加(HR=2.79,95%CI2.21~3.53,P<0.001)[5]。更有趣的是,sST2还有望鉴别不同类型的PH,Geenen等[6]的研究则表明,sST2水平在不同病因引起的PH之间存在差异,特发性肺动脉高压(IPAH)、结缔组织病相关肺动脉高压和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sST2水平均较健康人群不同程度地增高,其中以IPAH最为显著,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与健康人群相似。综上,sST2水平对PH的诊断、鉴别、危险分层及预后都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1.3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11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11(LR11)是一种在内膜平滑肌细胞(SMC)中表达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可溶形式的LR11(sLR11)在SMC快速增殖阶段可通过蛋白水解从SMC内膜释放并诱导SMC迁移,故血清sLR11可作为内膜SMC的循环标记,反映血管内侧SMC增殖和迁移的功能[7]。Jiang等[8]通过动物实验已证实LR11-/-小鼠对慢性低氧诱导的PH可产生高度抗性,LR11可调节SMC增殖,延缓内膜增厚,进而控制PH的发生和发展,并通过20例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PH患者的sLR11水平与肺动脉平均压(r=0.633,P=0.003)和肺血管阻力(r=0.580,P=0.007)呈正相关,sLR11水平可反映PH患者的SMC增殖情况,可用于预测疾病的进展。综上所述,sLR11可反映PH中SMC的病理状态,有望成为肺动脉重塑的生物标志物。
1.4 硒蛋白P
硒蛋白P(SeP)由SELENOP编码,是一种主要由肝细胞产生的分泌蛋白。SeP可调节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增殖,促进血管疾病的发展。过量的SeP会破坏细胞内缺氧诱导因子-1α和FOXO3a稳态,诱导PH-PASMCs中缺氧诱导因子-1α的组成性激活和线粒体功能障碍,予以SeP抑制剂治疗可降低SeP的蛋白质水平并改善PH症状[9]。PH患者的循环血清SeP水平较非PH对照组明显升高,且血清SeP水平较高的PH患者的全因死亡和肺移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血清SeP水平较低的患者,随访期间血清SeP水平的绝对变化与几个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密切相关,PH特异性治疗开始后血清SeP水平升高预示不良预后[10]。基于上述证据,SeP的血清水平可用作PH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补充硒可预防PH疾病发生和减轻PH症状[11]的观点相矛盾,可能由于SeP具有多种不同分子量的变体,加之既往的研究未采用新型的均相溶胶颗粒免疫测定方法,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1.5 小窝蛋白1
小窝蛋白1(Cav1)是小窝的结构蛋白,在脂肪细胞、内皮细胞和Ⅰ型肺泡上皮细胞中高度表达。Cav1以外分泌的途径分泌入血,可在血清中被稳定检测出。研究表明,Cav1与PH存在一定的相关性。Cav1-/-小鼠可表现出PH和右心室肥大[12],同时,在野百合碱诱导的PH大鼠模型中发现,其肺组织缺乏Cav1表达[13],且在IPAH患者的肺血管内皮细胞及总肺溶解物中Cav1的表达也降低[14]。Cav1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相关肺动脉高压(COPD-PH)患者和IPAH患者均表达下降,但IPAH较COPD-PH明显降低[(76.45±32.41) pg/mL vs(163.04±146.59)pg/mL,P=0.047],故Cav1可用于在COPD-PH患者和IPAH患者之间进行鉴别诊断[15]。若以血清Cav1 17.17 pg/mL作为诊断IPAH截断值时,灵敏性为0.59,特异性为1.00,血清Cav1对IPAH具有良好的特异性[15]。诊断IPAH时骨形成蛋白Ⅱ型受体基因(BMPR2)的敏感性极高,若将二者组合,有望提高IPAH的诊断准确度。
2 microRNA类标志物
目前的PH及PH模型研究表明miR-29、miR-124、miR-140、miR-204、miR-210、miR-1、miR-130/301、miR-138、miR-17-92、miR-21、miR-214、miR-223、miR-424、miR-23a、miR-130、miR-191、miR-19a、miR-145、miR-27a、miR-328、miR-1-2、miR-199、miR-744、miR-4632和miR-208等众多microRNA与PH密切相关[16-17]。其中miR-29、miR-124、miR-140和miR-204在不同模型之间具有相似表达模式,最有望成为PH诊断和治疗及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评估的分层标志物,现重点阐述此四种microRNA的研究进展。
miR-29在低氧诱导的PH模型中,肺动脉外膜成纤维细胞与野百合碱诱导的PH模型的PASMC均表达下调,参与肺动脉的纤维化[18-19]。遗传性肺动脉高压(HPAH)患者的肺组织中miR-29升高,使过氧化物酶体増殖物激活受体γ和CD36显著降低,加剧BMPR2相关的PH的临床症状[20]。且患有中至重度PH的患者血浆中循环miR-29的水平明显下调[21],miR-29可用于反映肺血管重塑和进行预后评估。
miR-124在PH患者和PH模型中的PASMC、肺动脉外膜成纤维细胞和肺动脉内皮祖细胞中均有明显下调的趋势,调控细胞的增殖和迁移[17,21-24]。miR-124参与肺动脉各细胞类型的分化及表型维持,是PH潜在的治疗靶点。
miR-140和miR-204在PH患者的肺组织和肺动脉内皮祖细胞及低氧诱导的PASMC中表达下调[17,25-28],且研究表明予以miR-140-5p模拟物补充可阻止PH的发生和发展[27]。恢复miR-204表达可显著降低疾病严重程度[29-31]。故miR-140和miR-204有望作为治疗靶点和疗效评价指标。
3 DNA类相关标志物
基因突变与部分PH患者发病相关,HPAH均为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目前已知的9个致病基因:BMPR2、BMP9、ALK1、Endoglin、SMAD9、BMPR1B、TBX4、CAV1和KCNK3,可解释50%~80%的HPAH和20%~50%的散发型IPAH患者的病因[32-34]。
此外目前研究表明基因SOX17、HLADPA1/DPB1、ATP13A3、AQP1、KLK1、GDF2、GNG2、COL18A1、CYP1B1、CBLN2、SMAD4、SMAD1、KLF2、BMPR1B、KCNA5、CYP1B1、GGCX和EIF2AK4的多态性也与PH密切相关[33,35-40]。
BMPR2是PH最常见的致病基因,可解释75%的家族HPAH及25%的IPAH散发病例。中国人群中BMPR2突变比例在HPAH和IPAH分别为53%和15%[41]。BMPR2编码骨形成蛋白2型受体,在调控血管增殖中起重要作用。与不携带突变的患者相比,携带BMPR2突变的IPAH/HPAH患者发病更早,临床表型更严重,预后更差[42]。TBX4突变是患儿发生PH的第二大最常见的突变[43]。ALK1和Endoglin是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相关PH最主要的致病基因[32]。在肺静脉闭塞症(pulmonary veno-occlusive disease,PVOD)/肺毛细血管瘤病(pulmonary capillary haemangiomatosis,PCH)家族中,发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基因突变,全基因组测序显示,在所有家族性PVOD/PCH,以及25%组织学确诊的散发PVOD/PCH病例中存在EIF2AK4突变[40]。对于临床疑似PVOD/PCH患者,如检出EIF2AK4双等位基因突变,有助于确诊PVOD/PCH[34]。SOX17增强子区域的遗传变异与PH的发生显著相关[35]。
此外一项包含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三种血统的多民族队列研究表明,CYP1B1基因与右心室功能相关[38];Damico等[39]研究也表明COL18A1基因可预测PH和IPAH的严重程度及死亡率(n=100,P=0.04);一项625例PH全基因组易感位点研究发现CBLN2突变显著增加PH的发生风险(OR=1.973,P=7.47×10-10)[44]。故基因检测可用于HPAH、低氧所致的PH和IPAH及儿童中IPAH和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诊断和鉴别,解释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指导疾病的治疗并评估预后,对患者家庭成员进行风险分层,以及指导产前诊断、结婚、妊娠、生产和婴儿保健等多个方面,前景广阔。虽目前伴随一些遗传歧视等伦理问题,但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将逐一解决。
4 讨论
尽管发现多种生物标志物与PH预后相关,但仍无反映PH或右心衰竭的特异性标志物。众多标志物中目前BNP和NT-proBNP最为常用,二者广泛应用于评价右心功能、PH危险分层和预测预后,但受年龄和肾功能等因素影响。
PH的症状隐袭,缺乏特异性,病因涉及多学科以及PH中心建立不足的因素,PH的诊断和治疗现状仍不容乐观。发现一个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对PH患者及早识别和分层尤为重要。目前有关PH生物标志物的大多数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存在患者和对照组人数少,患者群体异质性和选择偏倚等缺陷,仍需进行前瞻性研究验证。此外,生物标志物联合使用可能比单一标志物对PH有更好的诊断和预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