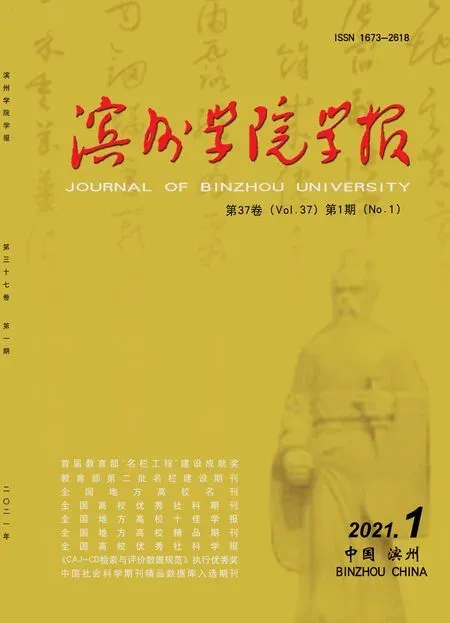《孙子兵法》军事哲学思想之心性学透视
陈二林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作为一部诞生于2500年前的重在探讨如何“战胜攻取”(1)《孙子兵法·火攻》。为简便起见,下引《孙子兵法》原文,均不再注明具体篇目。所引原文,主要依据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零先生的《吴孙子发微》、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丙安先生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钮先钟先生所著《孙子三论》对《孙子兵法》的校释本。的兵学经典,《孙子兵法》诚然没有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人在研究人怎样才能合于伦理与成就道德问题时,提出和推崇的那种“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者”[1]17的心性之学。(2)简言之,心性之学就是道德之学,其主要是从人的内在心性角度探研人成就道德的条件、过程与效果,与西方宗教意味的灵魂论与科学层次的心理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认为,在传统的心性三分结构即欲性、智性、仁性基础上,加进情性与灵性适成五分结构,以之诠释孙子的心性论,更为精准和贴切。但通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其也是切实地立足于人(主要指君主将帅)之心性世界而谈兵论战的,《孙子兵法》十三篇融入了大量的心性论内容。换言之,孙子军事哲学思想是以对人之心性问题的深刻洞察作为前提与“内蕴”的。
一、孙子心性论之结构与意涵
遍查《孙子兵法》传世本,“心”“性”二字各出现过一两次,不过没有连用情况。孙子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这种“夺心”“治心”之论,以前注家多认为其吸取了前贤“先人有夺人之心”之说,是“将之所主”的“本心”,强调要“常养吾之心”,“调治”“本心”,“治之有素,养之有余”,“善治己之心以夺人心者也”。[2]149而后世学者郭化若、吴九龙、李零、何新等,多认为其指代“决心”“意志”“理智”“心理”。应该说“本心”说虽综合但较抽象,而“决心”“意志”“理智”“心理”等说法虽具体却又不全面。而孙子“木石之性”之说,则主要是描述客观物质的特性,并不涉及人之性。(3)倒是孙武后辈孙膑明确从“民”的角度谈论了“性”:“用民得其生(性),则令行如留(流)。”(《孙膑兵法·奇正》)这表明,孙武子后人也愈来愈认识到人性问题或曰心性问题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
虽然孙子没有将“心”“性”二字连用,也似乎没有明确地从“人”的角度谈论“心性”,但通过对文本的整体解析,可以看到,他的军事哲学思想自始至终渗透和贯穿着精深的、独具特色的心性学内容。在其看来,君主将帅之心性世界具有包括欲性、情性、智性、仁性、灵性等多方面的复杂结构与特有意涵。
一是欲性。通观《孙子兵法》,“欲”字凡9见(4)参见杨少俊等:《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1页。以下《孙子兵法》用字次数统计均出自该书,不再注明。,主要意涵为名词“意欲”和动词“想要”。而与欲求相近的“名”“利”二字,尤其是“利”字也多次出现,高达51次。在孙子看来,人皆有名利欲求,君主将帅更是如此。正是诸如权力地位、土地财产、声色犬马等利欲目标,促使君主将帅们殚精竭虑地运筹帷幄、舍生忘死地驰骋疆场。只不过,贤明的君主将帅还能适时适度地满足部属的利益关切,公正严明地“分利”“货”“赏”,并善于将自身欲求与部属需求协调统合起来,以便产生“上下同欲者胜”的良好效果。而愚顽的君主将帅则往往任由私欲膨胀,结果招致“乱军引胜”,甚至“覆军”“亡国”。
因而,孙子对欲求的正负效应具有格外清醒的警觉,故而要求君主将帅要懂得调节与掌控自身欲求,行动时要有所选择、有所克制、有所敬畏,要“杂于利害”以“尽知”“利”“害”,即辩证全面地看待利害得失,谨防被人利诱威逼,要深得意欲之正,眼中心里要有大利、远利、全利、民意(5)《淮南子·泰族训》提出所谓“因民之欲”,《兵略训》云“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正是对孙武子“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与众相得”等精义的进一步发挥。,而不是小利、短利、破利、私欲,绝不能目光短浅、利欲熏心、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务必杜绝只顾个人喜好的贪欲之举。(6)据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见吴王》记载,孙武子在面见吴王阖闾时即郑重提出:“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可见,孙子对用兵作战的态度非常审慎和理性,反对君主将帅出于个人私利和囿于个人恩怨而轻启战端。换言之,孙子对君主将帅欲求的合理性有所肯定,同时又对其危害性发出告诫,实际上确立起义利双修、以道义与民意规约和勘定利欲的原则红线。
二是情性。“情”字凡7见,主要意涵为实际情况、诀窍要义、意旨与心理。孙子对君主将帅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洞隐而烛微。按孙子之论,由于情感是人之为人所不能舍弃的,如何正视和驾驭丰富多样的情感,以至于不汨于情,不湎于情,不滥于情,不使自身情感的天平严重失衡而始终能得情感之正,对于作为“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君主将帅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而,其告诫“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提醒君主将帅不可成为非理性情感的奴隶,受“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名”等偏狭固执情感的钳制与驱使,犯“走”“弛”“陷”“崩”“乱”“北”等过失“败道”,而要始终牢牢掌控自身情感向度,力戒偏执极端,合理管控负面情绪,绝不任其摆布。鉴于君主将帅的情感情绪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因而在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中,防止由于“性情偏执”而“运筹失度”[3]75,就成为君主将帅不得不常下功夫和深下功夫的一门“必修课”。
君主将帅不但要善于管控和主宰自身情感,避免被人利用而自食苦果;同时,还要善于利用先“亲附”后“行罚”即刚柔相济的情感手段,平时即注重对部属的情感教育与情感管理,以避免“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之被动局面;务必深谙“人情之理”,密切关注吏卒的情感动向与心理变化,紧急时刻又能巧设“险”“害”情境,调动、催生和激发部属“甚陷则不惧”进而产生“诸刿之勇”的积极情感及“深入则专”“无所往则固”的坚强意志,以便产生“携手若使一人”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非凡效果。(7)《淮南子·精神训》提出要“理情性”,强调“无益于情者不以累德,不便于性者不以滑和”,这同样强调了对情性进行调理的重要意义。
三是智性。兵家尚“智”,但《孙子兵法》中“智”字也只见7次,主要意涵为智慧、明智。不过,与“智”近义的作为“战争制胜的依据和战争行动的基础”的“知的诸范畴”[4]82-93,则出现79次之多。这是因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极端危险的领域,充满着智力的较量与角逐,需要将“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5]72。故而,《孙子兵法》十三篇,几乎篇篇谈“知”论“智”,自始至终洋溢着强烈的“求知”“崇智”的理性精神。孙子强调“先知”“尽知”“知兵”,并将“知”视为“思、计、行”的“总基础”,彰显了作为“知”的“结果”与“极限”[6]229-233之智性,在治国治军及作战善后中的重大意义。
治国治军作战诚然属于君主将帅的情欲活动,更是复杂繁难的智力活动。孙子对君主将帅的心智水平更是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因为用兵作战直接而深刻地关乎士卒生死、百姓祸福、国家安危与社稷存亡,这要求君主将帅要秉持非常审慎与高度负责的态度,严密而周全地“庙算”“伐谋”“用间”,绝不能疏于准备而又急躁冒进,绝不能心存侥幸而盲目行动,绝不能死守教条而不知变通,绝不能感情用事而任性而为,绝不能不顾全局而草率行动。孙子重视和崇尚智能,认为“智”是“明君贤将”“知兵”“知胜”的首要素养,贯穿“庙算”“伐谋”“作战”“料敌”“善后”全过程。大到安民抚众、伐谋用间,小到行赏论罚、战斗应急,都离不开智力的主导与参与,这些都是复杂繁难的“智”力活动。君主要有“将能而君不御”的开明远见,要保持“非利不动,非危不战,非得不用”的清醒理智,要力戒“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等不智之举;将帅要努力成为“知兵之将”与“智将”,绝不能因为自己的智力迷失而招致“覆军杀将”之恶果。孙子对无知而盲动、“无虑”而“武进”、有勇而无谋的冒失鲁莽行为,均持极其严肃的批评态度。可以说,在孙子看来,君主将帅如果没有“先知”“先胜”的高超智能,而只是一介独夫与赳赳武夫,那实际上在战争开启之前就沦为“已败者”了。所以,按孙子之见,要想“胜兵先胜”和“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就必须计高一着、智胜一筹、多谋善断,始终将高强的智力活动贯穿于治国治军作战善后的全过程,坚决摒弃“先战而后求胜”之侥幸心理与愚鲁行为。当然,孙子所推崇的“智”,绝非一般的“众人之所知”,甚至也不是“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之智,而是“不战”“全胜”的“无智名”的大智慧。
四是仁性。“仁”字凡3见,主要意涵为仁慈、仁义。按杨泽波先生之论,“仁性”是指一种“来自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个人内心的结晶”的“伦理心境”。[7]14当然,孙子所谓的仁性,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性的道德修为与“伦理心境”,其更多地与诸侯国乃至天下的整体利益相关联,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在孙子时代,各诸侯国竞相争强称霸,战争的残酷性已然显现,战争的投入与代价也与日俱增。孙子虽没有像儒家孔孟那般大力倡导仁德仁政,但也极力强调君主将帅要具有“安国保民”的仁道胸怀与价值取向,治军用兵要讲究“合文齐武”(8)曹操在注解“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时指出:“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注曰:“文,仁恩;武,威罚。”二者都申明了孙子在管理上主张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特质。,即将仁爱精神与法治精神结合起来,即使在“用间”的时候也要讲究仁义。当然,孙子所推崇和标举的仁义非小恩小惠,非妇人之仁,而是“全争天下”的大仁大义。换句话说,孙子之仁,不仅仅是指君主将帅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更主要的是指向诸侯国乃至天下大利。(9)《国语·晋语》有“利国之谓仁”之论,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亦有黄帝“已胜四帝,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之说,这都点明了仁性的利益指向。
五是灵性。“灵”字不见于《孙子兵法》文本,但与之字义相近“神”字却出现5次。依孙子所论,贤明的君主将帅还应具有远超“众人之所知”的地方,要有敢于打破常规、大胆创新、出人不意的灵思妙悟。此灵思妙悟表现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形人而我无形”,“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等等。但是,此灵性玄机又“不可先传”,“为不可测”,乃至“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具有“依据已有的经验直接领悟事物的本质,并迅速做出判断”[8]的直觉思维的特点,有些类似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感悟到真理的直觉”与“绝佳绝妙的想象力”[9]156-157。即是说,此灵性难以言传身教,没有固定套路模式可沿袭与效仿,更无法乞求于天命神意,而需要君主将帅在实践中,“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渐思顿悟才能获得。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为“兵形象水”且“战胜不复”,死守教条、不知变通者无法领悟“神乎神乎”“微乎微乎”之奥妙,而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能“谓之神”。(10)《淮南子·兵略训》亦曰:“变化之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可见,所谓“神明”,不是鬼神之谓,而是对一种高度灵活应变精神的推崇和赞叹。诚如姚振文所言:“这是一种玄妙的境界,它需要靠灵感而不是逻辑分析,靠悟性而非计算演练,它是超越感性经验而作抽象的把握,颇有些神秘,也颇有些模糊,然而对战争指挥者来讲,它至关重要,不可或缺。”[10]
二、孙子心性论是成德之教,更是成事之学
前有所述,按当代新儒家的讲法,心性之学主要探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可谓是成德之教。而对孙子来说,心性之学所要解决的不只是个体的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利益问题。换言之,孙子的心性论不仅仅指向和关注“主孰有道”“将孰有能”这般个体的道德修为与提升,更指向和关注“安国全军,唯民是保”如此整体的功利获取与保障。进言之,孙子的心性论是成德之教,更是成事之学,且成就个体之德,是为了更好地成就家国乃至天下大事。
据孙子之论,用兵作战须深明“五事”“七计”之道。即是说,顺天时、得地利、贵人和、重武备、尚谋略,是孙子所重视的“巧能成事”的几大要素条件。它们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其中“人和”最为根本。[11]因为天时、地利、武备、谋略诸因素,最终都要通过或取决于人的因素而发挥作用。而人的因素之要害处在于其心性问题,在于君主将帅能否调适和处理好欲性、情性、智性、仁性、灵性五种心性及其关系。因而,按孙子之见,君主将帅能否理顺心性逻辑与心灵秩序,能否妥善解决心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当下乃至未来的生死存亡。
孙子认识到,人皆有意多欲,贵在得其大“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趋势下,要求人们如老子所言“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三章》),显然不现实,也无法办到。在孙子看来,面临争强称霸的时势,“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取敌之利”,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君主将帅须将自身欲求调控在合理范围内,而且要时刻以民意为准绳、以大局为重,争取与民“同意”,“上下同欲”,才不至于利欲熏心与利令智昏,不受诱逼而远离危殆。更重要的是,孙子实际上亦如孔子对君主将帅提出了“克己”“修己”的要求,希望君主将帅要努力抑制一己之好恶,去除私心杂念,惟“战道”是从,“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始终将“安国全军”与“唯民是保”作为表达和确证自身意欲的恰切前提与终极目的,努力寻求个人、部属、诸侯国乃至天下利欲的“最大公约数”。相反,君主将帅如果贪图个人虚名(11)诚如斯宾诺莎指出:“好名是追求名誉没有节制的欲望。”“好名是助长并加强一切情绪的欲望,因此好名的情绪几乎是不能克制的。因为只要一个人具有欲望,他必然具有好名之心。”(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版,第162页。)可见,名利之心即是欲望的同义语,对其克制难度何其之大!,一任私欲膨胀,全然不知且不顾利害相生、祸福相依之道理,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则很容易“縻军”“乱军”,乃至“覆军”“亡国”。(12)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针对吴王阖闾“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之问,孙子断言“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者将先亡,而“公家贫,其置士多,主佥(俭)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者将“固成”,以至于吴王当即领会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历史的发展,与孙子的预测大致相合。可见,孙子对当政者私心太重、私欲膨胀的危害性洞若观火,具有先见之明。
因欲而生情,欲私则情偏。孙子明了,与君主将帅之欲求相伴而生的是多样易变的情愫。置身于争强称霸的滚滚潮流,面对各种各样的利欲诱惑,身处复杂多变的战场实景,君主将帅的情感情绪必然会出现大幅波动。因而,如何始终以家国乃至天下为念,把握和处置复杂易变的情感情绪,审视和确证自身情欲的合法性,引导其朝着理性方向发展而不至失之偏颇,杜绝只为一己私利、囿于个人恩怨而兴师动众(13)孙武之孙辈孙膑,也将“贪于位”“贪于财”“自私”等列为“将败”之主要表现。此正表现出历史经验、实践理性与家学渊源的一贯性。(参见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第178-179页。),严防由于情不能已而被人“夺心”以致铸成大错,就显得异常重要。当然,君主将帅不但要善于把握自身情感向度,使之保持均衡平和状态,摒除“必死”“必生”等极端情绪,力避“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等感情用事;同时还要善于调动、转化和管控广大民众以及部属士卒的情感情绪,避免其产生“无常”“不服”等负面情绪,使之保持旺盛“锐气”与昂扬斗志,善于将“亲附”“爱民”的情感管理与“法令”“素行”的制度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宽猛相济、严爱结合、信愚有别,这对于争取广大民众的情感认同、形成旺盛士气和强大战斗力,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14)克劳塞维茨亦强调了情感“对于保证理智的主导作用”的积极意义(尤其是“自制”情感),同时其对战争激情的盲目性、易变性与破坏性(“难以维持内心平衡”“往往失去理智”“推离正道”),又提出了明确的警戒。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册》,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第147-149页。)
缘情而开智,情迷则智失。孙子察识到,在较大程度上,君主将帅的情欲向度,影响其智力生成的方位及运用的范围。在他看来,君主将帅的智力水平对于治国治军作战具有重要意义,智力庸常或不擅长运用智力,乃是为君为将之重要缺陷。当然,孙子所推崇的“明君”“智将”,应是拥有大智慧而非小聪明者。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是说,百战百胜算不上大智慧,只有深谋远虑、兵不血刃而收服敌手者方为大智贤明者。(15)有学者推断,孙武正是借鉴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全胜”之策,乃至齐桓公先祖、齐国开创者姜太公先文后武、文武兼备、不战而胜的战略,而“推导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参见路秀儒:《美眼看孙子》,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117页。)对于有着深厚历史意识与家学渊源的孙武子来说,此语诚然不虚。孙子一方面强调智力的重要性,看到了“少算”“无虑”的极端危险性;另一方面又看到智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君主将帅为了炫耀智力而使用智力时就相当凶险。因此,在其看来,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应是“无智名,无勇功”的,即大智无名、大智无功。
转智而成仁,智低则仁薄。按孙子的逻辑,君主将帅对其智力生成和运用的考量,就已蕴涵着仁义的因素了。受夏商周三代由来已久的仁义思想的影响,虽处于社会动荡的春秋末期,孙子仍强调了仁义的重要性,主张君主将帅要倡导仁道义举。但是,孙子所提倡的仁义,不是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与当时治国安民、治军战胜的战略目标与具体实践紧密关联的。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人士所看重的仁爱之情与道义之举,孙子也从其兵家视角给予了特别的警惕,要求君主将帅在表现仁义时也要尽其智能地注意方法、限度与场合,展现仁德义怀时也要讲究时机与策略,防止“爱民可烦”式的滥施仁义或“爱爵禄百金”而“不知敌之情”式的误用仁义。同时,其也敏锐地认识到,仁义的实施对象也是内外有别的,仁义与诡诈可以并行不悖。
本仁而显灵,不仁则灵昧。依孙子所论,为了对治“无常势”的“象水”之“兵形”,君主将帅需要“善出奇”而“巧能成事”的本领,具备“神乎”“微乎”的灵性顿悟。然而,这一灵性顿悟的获取,又绝“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即无法乞求于神明恩赐,不可依靠类推比附与占卜迷信。进言之,这一灵性巧思不是天生就有,不会空穴来风,也不能坐享其成,而是源自“全争天下”的仁德义怀与超越“众人之所知”的远见卓识,并且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创获。它虽有一定的玄秘性,却不拜鬼神所赐;虽有一定的偶然性,却无法唾手可得;虽有一定的抽象性,却又具体实用。其应“悟自前人兵学精要”,“悟自自然社会生活”,“悟自战争具体实践”。[12]116-124一句话,此灵性妙悟是属人而非属神的。
由上可见,在孙子看来,一方面,君主将帅的情欲追求,是其智性生成、仁性展现与灵性迸发的自然前提;另一方面,君主将帅对情欲向度的确当把握,又须臾离不开智性支撑、仁性主导与灵性佐助。同时,君主将帅对仁性的确切表达与对灵性的精准捕获,又需要高强智力的支持,而智力效用的恰当发挥又需仁性的引导与灵性的辉映。反之,就会出现心性功能的紊乱。即是说,如果君主将帅不能有效管控其情欲向度,情绪上将出现大幅波动,情绪上的不稳定又会波及其正常的智力活动;而心智上的错乱,又会进一步加剧情欲脱轨的速度,并累及仁义情怀的恰当表达;而仁性表现的“遮蔽”“不当”与“无知”[13],则又殃及灵性顿悟的产生与斩获。反过来,灵性的优劣、仁性的深浅、智力的高下,又必将对其遂欲用情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贾林所谓:“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2]7正是对五种心性负向关联互动情况的生动说明。
质言之,君主将帅之欲性、情性、智性、仁性、灵性五方面,不是某一方面的“独角戏”,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须为用、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16)曹操在注解“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时说,“将宜五德备也”;张预说,“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贾林说,“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王皙说,“五者相须,阙一不可”;何延锡说,“全此五才,将之体也”,在注解“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时,又进一步说:“将材古今难之,其性往往失于一偏尔。故孙子首篇言'将者,智、信、仁、勇、严',贵其全也”。这说明,注家大多认识到孙子对将帅心性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君主将帅只有辩证系统地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具备“静以幽,正以治”,即“思虑冷静而眼光幽远、公正待人而严于律己”的“心理素质和情操修养”[14]305,才能不为欲所累、不为情所困,而始终为智所主、为仁所范、为灵所化,才能实现“不战”而“全胜”、“不顿”而“全利”的战略目标。相应地,君主将帅之贤明,则主要表现为情欲之正、智力之丰、仁性之准、灵性之明,五德皆备、心有所主而性有所定。只有如克劳塞维茨所谓把“智力才华和性情禀赋”等诸要素“和谐组合”起来的军事天才[9]138-158,方可称之为“明君贤将”。而将之“五危”“六过”,则多因情欲之失、智力之窘、仁性之偏、灵性之昧,即后来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智能缺陷”与“性情缺陷”[9]151所导致。
综上不难看出,孙子的心性论有着连贯一致的内在逻辑与丰富深刻的意蕴内涵,不仅追求德性的完善与人道的彰显,更追求利益的整全与事功的圆满,其是成德之教,更是成事之学,是更加广义的心性之学。
三、孙子心性论是其扬弃历史与体悟现实的主观反映
究极而言,孙子之所以能参透和洞明君主将帅内在隐秘的心性世界,主要得益于他对丰富多样历史经验的积极扬弃,对复杂变动社会现实的深切体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辩证系统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孙武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天下之无道也久”(《论语·八佾》)、“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动荡之世与转折时代。有识之士如管仲、晏婴、子产、老子、孔子等,知人论世,谈兵论政,为恢复天下“有道”局面而殚精竭虑。出身将门之后的孙子,更是认真总结“昔之善战者”“古之善用兵者”的历史经验,深切探察王室衰微诸侯力政、“胜敌而益强”的社会现实,亲力亲为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全过程,最终形成“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军事问题”[15],具有“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5]75的思维方式,在总结历史与深入实践中进行着卓越的理论创造。应该说,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复杂的社会现实,“是成就孙子及其军事思想体系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客观物质基础”[4]368,而辩证系统的思维方式则是其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支撑。
郭齐勇先生指出:“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一两关系的对立与平衡。”[16]中国思维所具有的这种整体观和阴阳观的特征,也即中国思维的系统性与辩证性,在孙武子基于历史与现实交织共生的时代大背景而洞悉君主将帅心性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和细致反映。这样的历史理性、切身经历及思维视角,大大有助于孙子对人之心性的性状、结构、功能与特质加以认真检视与剖析,对君主将帅每一心性本身及心性之间的关联互动情况进行辩证考量和整体探析;对其如何在深层次和宽领域上决定着君主将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而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治国治军与作战行动的优劣成败,给予深入探究与精准揭示。
由于孙武子具有敏锐的历史意识、浓厚淑世情怀、发达的辩证系统思维,始终将君主将帅置于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多维视角中加以审视和探析,这使得他的心性论表现出鲜明的继承性与创新性。他以缜密周全的心性逻辑为基点,支撑起疑天而取人、审时而度势、因敌而尚变、重德而保民、不战而全胜的成事体系,高扬了疑天惟人的人本精神、因革变易的因变精神、德刑相合的和合精神及保民惠民的民本精神[11],可谓是“以兵家的独特视野及思维方法,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与基本精神”[17],“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操、价值和生命力”[18]5。因此之故,孙子的心性论才既有一般心性学之共性,又有兵家心性学之特性,给人以深刻印象与无穷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