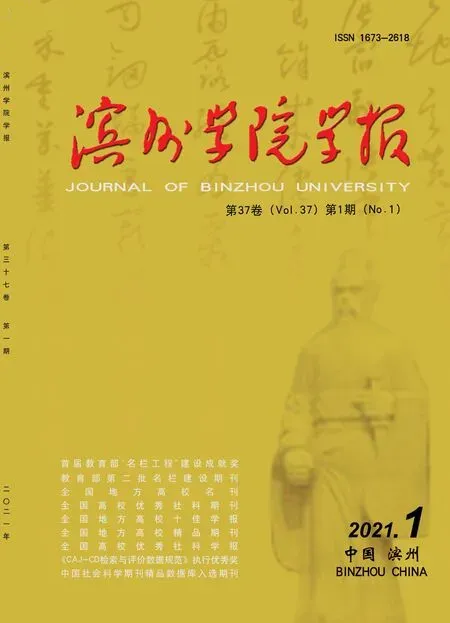《孙子兵法》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肖长亮
(陆军北京卫戍区,北京 100091)
系统科学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以及层次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1]。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较早地开展对系统学的研究,认为“系统就是整体”[2]。他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定性跟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科学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为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指明了方向。一般认为,近代系统科学源起于1945年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它坚持以系统观点分析研究问题,以系统论为方法论,以系统思维为基本思维模式。乌杰在唯物辩证法和系统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哲学这一新的哲学领域,并创建了系统辩证学科[3]。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运用系统科学思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军事上也是指导现代战争乃至未来战争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古代传统的思辨哲学中就有系统思维的朴素认识。《孙子兵法》这一兵学圣典,无疑是军事上开创系统分析战争的典范之作,孙子在开篇即提出“五事七计”的战争预测理论,使孙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提出战争预测理论的军事家[4]。在作战指导上,孙子从“形势”的力量积聚、“奇正”的战术运用、“虚实”的目标选择等多维层次和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述,这既是孙子对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的集成总结,又吸收了《易经》《老子》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哲学思想,体现了孙子善于从整体视角去认识战争,从联系的角度去指导战争,将战争筹划、作战指导、战术运用、治军选将等环节统一纳入战争全局进行一体谋划,体现了孙子的系统观。
从孙子时期使用冷兵器的方阵作战发展到今天的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战争形态的升级并未改变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研究《孙子兵法》中朴素的系统科学思想,对指导以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为特点的新的战争形态,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以“五事七计”为衡量指标的战争筹划
战争筹划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孙子认识到“兵者,国之大事”,需要从交战双方的战略全局和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分析。鉴于此,孙子开篇就提出了“五事七计”的战争预测理论,系统地分析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为战与不战或如何战提供决策依据。我国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继承孙子兵学“庙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算定战”的概念。据《练兵实纪》记载,戚继光在给部下讲授军事理论课时,提出“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戚继光主张的“算定战”就是要求“须在未战以前,件件算个全胜”,即将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都要一一算定并作以比较分析,由此得出己方“得算多少”来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5]。刘伯承元帅常说的一句:“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指的就是要把“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这“五行”谋定而后动,讲的也是同样道理。
《计篇》中,孙子从“道、天、地、将、法”的五事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的七计,对战争双方进行“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整体性分析研判,是于庙堂之上对战争胜负进行的全局预测。孙子对战争胜负的预测,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选取了“五事七计”这些在当时能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指标进行一体衡量,体现了孙子将战争看作两个国家系统之间的整体较量,这个系统包括了国家政治、气象条件、地理环境、指挥能力、国防动员、士兵战斗力和法度等要素。战争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扩大了的搏斗”,而是双方政治向心力、国防动员力、民意感召力、军队战斗力,以及战之地、战之日的天时地利等条件的综合较量。今天的信息化战争,作战样式已完全超越了冷兵器时代的方阵对决和机械化战争时期的平台对抗,各种无缝链接的作战网络将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作战域的武器平台融合为一个有机的作战体系,是一场全域多维的整体较量,战争胜负预测的复杂性远甚于孙子时期。但是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没有变,“五事七计”依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衡量指标,只不过体系对抗条件下的“庙算”无法只通过对“五事七计”的定性分析而确定“多算”还是“少算”,还要借助军事运筹学和计算机建模与仿真技术,开发计算机战争模拟系统进行战略战役战术推演,定性分析有了量化支撑,使现代战争的“庙算”结果更加可信。
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的《论持久战》,成功指导了中国抗战走向胜利[6]。其中,在“问题的根据”一节中,毛泽东借鉴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方法,分别对中日两国的战争潜力进行了系统分析。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日本在国度和人力、军力、财力等方面先天不足,日本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大国,中国是得道多助的。最后他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是进步对抗退步、正义对抗野蛮、得道多助对抗失道寡助的。在“乘敌之隙的可能性”一节中分析日本对中国过去十个月的侵略战争中所犯错误时,毛泽东又指出“计其大者有五”:一是日本逐渐增兵,得出日本对中国估计不足,且日本兵力不足;二是日本无主攻方向,在华中、华北方向平分兵力;三是日本无战略协同,表现为华中和华北两集团作战不协同;四是日本缺少战略追击力量导致失去战略时机;五是日本对中国军队包围多歼灭少。毛泽东在对中日一系列战争要素的系统分析研判后,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作战原则,“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给敌以歼灭和消耗,坚信中国的抗战在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后,一定会迎来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系统“庙算”才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指导,随后的抗战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二、以“因敌制胜”为作战指导的胜敌之策
战争对抗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正如英国国王理查三世的故事讲到的那样。在1485年的波斯沃斯战役中,理查三世坐骑的一个马蹄铁因战前少钉了一根马蹄钉,冲锋时马蹄铁意外脱落,导致战马跌翻,将马背上的理查三世摔倒,致使战场无人指挥,英国军队瞬间土崩瓦解,最终因这次战役的失败导致亡国。理查三世于战后不禁感叹:没想到一根马蹄钉竟然亡了一个国家。可见,战场上任何一个不确定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会引起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使一支庞大的军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战争史上淘汰出局。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信息反馈来有效控制这种不确定性,并力争将其为我所用。孙子在《计篇》中系统论述了战争预测的庙算方法,但要想把战前“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的取胜可能性变为胜利现实,还需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在兵力调动、战术运用和目标选择等各环节,做到“因敌制胜”,方能达成作战目标。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用了《形篇》《势篇》《虚实篇》三篇,从“形”与“势”、“奇”与“正”、“虚”与“实”这三个既辩证又统一的角度,从战争中的兵力积聚、指挥要诀、战术运用和目标选择四个层次,系统地论述了“兵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在战争准备阶段,孙子正是看到了不确定因素对取胜的重要性,在《形篇》开头首先提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即练兵备战应立足于自身建设,“修道而保法”,以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和法制保障,赢得民意支持,获得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打造对敌“以镒称铢”的绝对优势,形成一定的慑止能力,使敌人不敢轻易发起进攻。在战争部署阶段,孙子提出“择人而任势”。将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指挥调度军队对敌“策之”“作之”“形之”“角之”(《虚实篇》),一边观察敌之虚实,一边调整优化自身部署,形成对敌有利态势,做到“知彼知己”(《地形篇》)。在战争发起阶段,孙子主张“以正合,以奇胜”,面对敌“众整而将来”,要“先夺其所爱”,视情对敌灵活地“利之”“害之”,打乱敌之部署,“形人而我无形”,使敌摸不清我方意图,让敌“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迫使敌暴露其软肋,此时我方就可以“避实而击虚”,投入奇兵,集中优势兵力破击敌之关键节点,“兵之情主速”,快速达成“因敌制胜”的作战效果。在兵力投入上,孙子提出“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九地篇》)主张一旦开战,对敌兴霸王之兵,形成以碫投卵的绝对优势,从而给敌以巨大的心理压力,迫其崩溃。“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对今天的网络空间作战、太空攻防作战、体系破击作战具有重要启示,战场信息的多维交互、机动空间的多域扩展、体系对抗的全局较量,为兵力的虚实转换、奇正相生提供了更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可谓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兵制胜的典范之作。1935年1月,红军召开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率3万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入川陕边境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调集湘军、黔军、滇军、川军和中央军共148个团约40万兵力从东南西北多个方向,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和川黔边境地区[7]。红军以3万之众对抗40万敌人,如果一味硬碰硬,无疑是以卵击石。为了争取战场主动,毛泽东决定采取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战法,通过运动战跳出敌军包围圈,达成红军的战略意图。1月19日,红军因土城战役失利,直接北渡长江受阻,遂定于1月29日由猿猴场、土城向西一渡赤水河,意图经泸州、宜宾段北渡长江。蒋介石发现红军西渡赤水河后,急调川军加强长江防务,企图围歼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地区。面对敌军新的布防形势,毛泽东考虑到红军继续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防止陷入敌人新的包围圈,指挥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运动,吸引敌军主力到川滇边境地区,而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向东二渡赤水河,进入黔北兵力虚弱的桐梓地区,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重创黔军王家烈部,使蒋介石承受“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5]。蒋介石据此判断红军定会继续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遂调集所有驻川、黔各军,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以东地区。毛泽东鉴于敌军再次聚集,红军已失去主动权,马上指挥红军由茅台及附近地区向西三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开进,意图再次调动敌军。果然,蒋介石急调各路大军向川南疾进,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敌人上当后,毛泽东当即决定中央红军于3月21日晚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四渡赤水河,于3月28日突破敌军封锁,3月31日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城,做出“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假象,趁敌军回师救援之机,红军主力向南绕过贵阳城,借道敌防守空虚的云南,向西转至皎平渡等地北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示形动敌、避实击虚,以奇正相生之术,因敌而制胜的得意之作,对红军渡江北上,完成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
三、以“一人耳目”为集中统一的联合指挥
战场上对部队实施统一的联合指挥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将指挥员的指挥号令及时准确地下达给任务部队,又要将部队对号令的执行情况及时准确地反馈给指挥员。这一去一回的两个“及时准确”就是对指挥手段的基本要求,既要有时效性,又要确保下级正确领会上级意图,还要确保上级准确掌握下级的行动,如此才能实现对部队集中统一的联合指挥。现代联合作战讲求体系制胜,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系统科学思想,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指挥机关与任务部队之间、任务部队与友军之间的协同一致,实现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是实施指挥与控制的基本手段,而远在春秋时代,孙子就认识到使用旌旗火鼓的视听效果实现对部队“一人耳目”式的指挥与控制。
孙子在《军争篇》中,引用了《军政》的话:“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提出了“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的指挥原则。孙子说:“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意即使用金鼓旌旗是因为人数众多,为达成“斗众如斗寡”,就必须靠“形名”,靠集中统一的指挥号令实现“一人耳目”的指挥效果,使部队行军作战协调一致,使作战兵团在战场上实现密切协同、灵活机动。孙子提出“一人耳目”的指挥理念,体现了孙子把军队看作一个整体,把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看成一个人那样,对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做到快速反应,体现了作战指挥的整体性、时效性、协同性、统一性。通篇来看,孙子“一人耳目”的指挥理念也是对前文“因敌制胜”作战指导原则的回应,只有实现对部队“一人耳目”式的集中统一指挥,才能把静态的“形”转化为攻击的“势”,才能如愿进行“形人而我无形”那样的战场机动,才能自如地“以正合,以奇胜”,才能灵活地选择“避实击虚”。可以说,没有“一人耳目”的指挥,“形”就无法积聚为“势”,指挥协同不畅,就无法实现“奇正相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战机稍纵即逝,没有快速有效的指挥协同,也就无法有效地攻击目标。今天的指挥手段早已不再靠“金鼓旌旗”,但孙子提出的“一人耳目”式的作战指挥一般规律没有变,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现代战争中,随着武器装备的机动和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作战兵力呈现出跨域分布式的部署态势,一场战争的战场空间已同时涉及陆、海、空、天多个物理域,要实现对跨域兵力“一人耳目”式的集中统一指挥必须依靠有效的现代信息通联技术。2018年4月14日凌晨4时,美英法联军采取非接触远程精确打击方式,一体指挥分布于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的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1艘核潜艇、2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等海空打击平台,对叙利亚境内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等地的3处疑似“化武”设施,进行了异地多目标同步精确打击,整个打击过程仅持续1个多小时,共发射了105枚巡航导弹,除少数人为操控自毁和被拦截外全部精准命中目标[8]。这场在战后被美军称为“史上精度最高的战争”,动用了包括多型号侦察卫星、全球定位导航卫星和多频段通信卫星在内的天基信息支援系统,确保了异地作战平台协调一致行动。现代联合作战中,随着通信手段多样化,指挥信号灵活化,指挥层级扁平化,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数据链早已成为战场通联的常用方式,未来还可利用天地组网技术和卫星导航技术,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指挥通信网络,不仅可实现空间的协同,还可实现时间的精准一致,真正实现孙子“一人耳目”的联合指挥构想。
四、以譬如“率然”为行动效果的作战协同
技术决定战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战力量按照配属的武器装备和担负作战职能的不同,逐渐衍生出诸多军兵种,为使分散的军兵种共同发挥作战效能,又产生了“体系制胜”的作战原则,如我军提出的“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与美军提出的“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多域作战”等概念,都属于系统科学思想指导下的体系作战模式。孙子在春秋时代就产生了朴素的系统理念,认识到了体系制胜的重要性,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作战协同的早期构想。
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的观点。率然是一种生于常山之蛇,这种蛇的特点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将作战协同喻作“率然”,强调进攻时掌控部队要“携手若使一人”,通过这样高度的作战协同,实现联合制胜的作战效果。战争是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孙子将庞大的作战集团看成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强调对作战集团的指挥要像一个人那样,各支部队之间和不同的作战力量之间应互相策应,互相配合,互相救援,互为犄角。协同是联合作战的基础,没有协同就无法实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孙子讲的譬如“率然”式的作战协同原则,正适用于今天的“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通过构建网络信息体系,将位于陆、海、空、天的多域作战力量实现互联互通,一则可以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加快作战节奏,有效实现对时敏目标的打击效能;二则可以强化作战模块之间的协同配合,将多目标按照分配规则快速分发至不同的作战单元,协同一致对目标实施打击,可大大节省作战资源,减少作战损失;三则可充分发挥“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优势,达到守正出奇的作战效果。今天,美军提出的“全域指挥与控制”和“分布式作战”概念,即是强调通过网络信息体系实现作战力量之间的密切协同,实现兵力的分散配置与火力的集中打击,从而更好地消耗敌人,保存自己。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在孟良崮地区反向利用譬如“率然”的协同思想,利用敌人冒进之机,切断敌之协同,一举达成围歼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的作战目标。1947年5月,国民党军集中“三大主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为骨干组成三个机动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对华东我军主力实施全面进攻。为打破不利态势,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发起了孟良崮战役。5月11日,正当我军打算集中歼灭进犯沂水的桂系七军和四十八师时,获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整编第八十三师和第二十五师的掩护下,自垛庄北进,随后占领杨家寨等地,企图从中央进攻我指挥部所在地坦埠。于是,时任华野副司令员的粟裕果断割裂敌之协同,精心设计了“外围阻敌、内圈围歼”的战法。5月13日晚,粟裕令华野1纵、8纵之一部正面阻击七十四师,令1纵、8纵之主力从七十四师之两翼向其纵深楔入,以1纵第3师对外阻击敌整编第六十五师,以1纵主力切断敌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的联系,以8纵主力割断敌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的联系,完成外围阻敌部署。同时,又以4纵、9纵从正面扼敌进攻,令6纵于14日晨进至垛庄西南地区。5月14日,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预感被包围,准备向孟良崮、垛庄撤退。华野发现敌撤退迹象,迅即令4纵、9纵从正面发起猛攻,令6纵攻占垛庄截断敌之退路,以8纵夺占万泉山,同1纵、6纵打通了联系,至此在芦山、孟良崮地区形成对敌七十四师之合围。尽管蒋介石调动了10个整编师从四面八方前来救援,但在华野外围部队的阻击下,内围部队争分夺秒一鼓作气彻底歼灭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9]。这场被陈毅称之为“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战役,在粟裕的精心设计下,使国民党军四十余万部队首尾不得顾,内外不能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七十四师被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