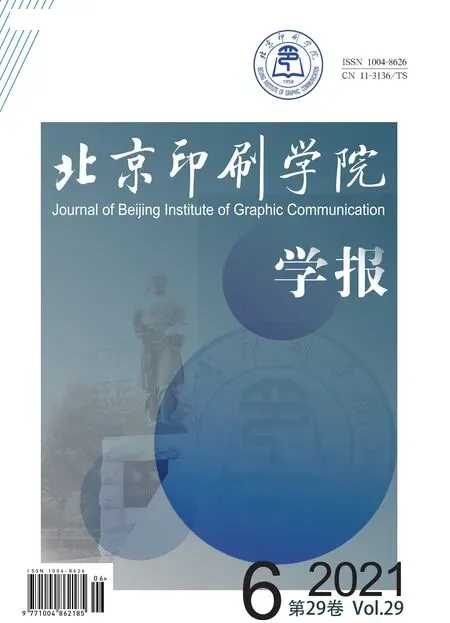从复调叙事看《呼兰河传》喜剧与悲剧氛围的融合
周一诺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萧红在战乱流离中历时三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注定是一代绝唱,它既是童真、美好、快乐的,同时也是荒凉、寂寞、悲哀的。它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在喜与悲这两条看似无法相交的绳索上把握契合的基准点,将所思所感渲染至两端,呈现出复杂、深刻而富有韵味的文化内涵。
《呼兰河传》的复调叙事对这种复合氛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创的“复调小说”是相对“独白小说”而言的,所谓复调或多声部,是指文本中存在两种处于平等地位的叙事声音,二者不时交锋、碰撞,这种叙事策略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思想层次。《呼兰河传》以儿童视角为主,但成人话语总是不可避免地穿插介入,在时空交错中,二者呈现出不甚相合的情感取向与思想节奏——即喜剧与悲剧氛围。在滑稽可笑的现实语境下,视角的冲突与转换揭示出潜藏其后的乡土民众的生存悲剧。民族苦难通过儿童的眼光传达出来,又在成人视角的诠释下走向深入,从而创造了凝结着血与泪的“童年经典”。
一、儿童视角与喜剧氛围
儿童视角以其立场的边缘性、情感经历的原始性和认知的“不理解”性[1],形成与客观现实的隔阂,从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呈现出天真纯粹、无忧无虑的童年景象。同时,处于本我和自我层次的儿童还遵循着以“快乐”为中心的行事原则,常常通过游戏认知世界,反映到文学中则是独具特色的喜剧氛围。
(一)陌生化效果
在《呼兰河传》中,人物或事件背后深藏着的偏见与恶意被懵懂幼稚的“我”忽略,只过滤出欢笑、稀奇与疑惑,从而营造了一个滑稽有趣的文本世界,形成了陌生化的阅读体验。
《呼兰河传》中的“我”是一个四五岁的女童,也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作品通过“我”的“有限视野”,展现了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和磨倌冯歪嘴子的“奇异”经历,创作了“三大人生特写”[2]。透过天真无邪的视角,世俗生活的怪诞与荒谬得以展现。在“我”眼中,小团圆媳妇懂得许多玩耍的花样,是个顶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可其他人都认为她“败坏风气”,是“早就该打的”;“我”坚信团圆媳妇没有病,她和“我”一起玩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街坊四邻却强调她肯定是被鬼缠上了,还要举行特殊的仪式“驱鬼”;“我”发觉冯歪嘴子的磨坊很冷,几乎和室外温度一样,因此在祖父面前为他说话,可周围的大人只顾着幸灾乐祸。在呼兰河城这个陌生的游戏空间中,“我”时时刻刻体验着陌生与新奇的感觉,而在天真无邪的注视背后,深藏着现实的戏谑与悲哀,形成了文学上的反讽效果。
(二)游戏精神
在游戏中,儿童可以逃脱成人规则的约束,获得主体自由,《呼兰河传》中的“我”就是一个具有游戏精神的顽皮女孩。祖父闲的时候,就时时缠着他,听说街上新来了个团圆媳妇,“我”喜出望外,饭也顾不上吃,就拉着爷爷去看,以为错过了热闹场面时甚至“差一点没有气哭了”;祖父忙的时候,“我”一个人也能自得其乐,一会儿睡在自己搭的布棚里,一会儿躺在蒿草里,好不自在。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童年期是一个充满压抑和焦虑的困惑时期,儿童发现他所处的世界是以成人为主宰的。面对成人的世界,儿童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3]。而当儿童开始坚守某种内心萌发的想法,并贯彻实践时,就会认识到自己拥有独立的人格,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当“我”顶着大缸帽当斗笠,洋洋得意地去找祖父欣赏时,却被父亲一脚踢翻,儿童的想象创造遭到了成人的抵制与扼杀,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当人们都相信小团圆媳妇崇了狐怪,所以大辫子一夜就掉了下来时,只有“我”敢于争辩说“是用剪刀剪的”;看到有二伯偷走了家里的铜壶和澡盆,“我”却骗母亲说没有看到,一般意义上,偷拿与撒谎都是需要扼制的劣性品性。但是,这里的“撒谎”除了童年的顽皮之外,还含有一种朴实的人道情感,因为“我”说谎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也暗含着一种为被欺凌者打抱不平的精神,具有更为自发和深厚的人性力量。总的来说,在天真童趣、悠然自得的喜剧氛围中,“我”通过儿童特有的游戏方式收获了主体的成长。
二、成人视角与悲剧氛围
事实上,《呼兰河传》中纯粹的“儿童视角”无法真正存在,作为创作主体的成人显然不可能完全退回儿童状态。由于叙事主体“我”不谙世事,难以体察周围事件的内在意蕴,成年叙述者总是适时介入,以成人视角审视环境,将儿童视角无法承载的情感与思想内容展示出来,并与儿童视角发生潜在对话,从而实现意义的升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挖掘出潜藏在喜剧氛围背后的悲剧特性。
(一)女性意识
“所谓女性视角,即用女性意识、女性经验观照作品。”[4]女性意识始终贯穿于成人视角中,在对呼兰河一幕幕女性悲剧深入描摹的过程中,也起到连接两种视角的作用,是“我”成长与独立的催化剂。
文本中处处都体现着萧红对呼兰小城女性悲惨命运的注视与隐隐的愤恨。前两章从风俗角度揭露了女性生活的“陷阱”,“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的哭丧传统、出嫁女儿回娘家团聚的艰难、节妇坊体现的男权色彩、时常发生的家庭暴力、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等等,都是成人视角的审视中被讽刺和批判的对象。而在后五章中,童养媳小团圆媳妇被婆婆虐待的惨剧、王大姑娘由于私定婚姻而被街坊四邻肆意诟病诋毁的过程等,从表面上看,是作为儿童的“我”的叙述,但偶尔“出戏”的叙述风格与批判意味还是传达出了成人化的透视眼光。如作品对胡家大娘婆婆义正言辞地“供述”自己虐待小团圆媳妇的详细记录:“一天打八顿,骂三场”“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昏过去了”“全身也都打青了”“用烧红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5]……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显然无法清楚记得这么多话,身为加害者,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也不会一板一眼地交代自己的虐待行径,这正是成人视角的细节加工。在胡家女性内部“斗争”中,成人视角的“我”深入体察了这一典型的女性悲剧命运,意识到在性别话语失衡的社会语境下,女性将被奴役的历史状态永久内化,形成了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观,自己则成为维持这种自我约束状态并强迫其他女性的精神傀儡,而胡家婆婆的话语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处于“听故事”状态的“我”则通过对悲剧的目睹与反思,促成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那极具洞察性与穿透力的眼光从成人视角切入,为读者深入解读传统女性的精神困境,同时又借用女童的懵懂视角,透露出如星星之火一般的希望:小团圆媳妇至死仍拒绝服从,她没有听婆婆的话乖乖等待,反同“我”玩起了游戏;王大姑娘不顾封建婚姻的束缚,与自己爱的人同居生子,即使面临四方诽谤,仍顽强生活。由此一来,即使是在作品对女性遭受多方摧残与压迫的悲惨命运的细致刻画下,读者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新生代女性坚韧不屈的品格与顽强勇敢的抗争精神,体会她们含着泪水微笑、戴着镣铐舞蹈的顽强意志,在悲剧命运中读出光明与希望。
(二)抒情笔调
萧红将个体情感寓于人事记叙之中,作为回忆主体的“我”总是有意识地对呼兰河的人生悲剧进行有限度的“冷处理”,通过淡远的笔调,传达融合了沉醉、留恋、同情、批判、厌恶等要素的复杂情感,“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5]
在《呼兰河传》中,除了作为参与者、旁观者和叙述者的“我”之外,再没有一个能够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在呼兰河的群像刻画中,体现了千百年如一日的停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尊崇古训的思维习惯、转瞬即逝的悲剧人物形象,都揭示出一种已经腐朽但仍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的精神结构,显示出深沉的文化批判力量,透露出一种不可战胜的绝望之感。
在讲述童年见闻时,作品的意蕴并未停留在事件表面,而是始终根植于萧红丰富的内心体验。“我”自始至终诉说着家的荒凉,并以“我家的园子是荒凉的”等书写延续这种基调,在一种绵延的忧愁与哀伤中将童年经历娓娓道来。同时,文章还将寓情于景的古典文学手法运用得清新自然,当黑夜跳大神的鼓敲响时,欢闹的民俗却引发了“我”无限的惆怅:“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如此悲凉。”这般情与景交融的人生感叹,为小说笼罩了一层朦胧的诗意,使得世俗烟火的片段也隐隐显露出细腻而又透彻的悲凉之感。
文章还以浅近简洁的文字组合传达了令人无限回味的凄凉感受。“以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5]在“做梦”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梦”的虚假,虚实相映,更添忧伤。直朴质感的语言背后,是剪不断的哀思,更烘托出凄美而浑化的氛围。
三、视角转换与悲喜融合
在《呼兰河传》中,“我”的情绪总是在童年与当下两个时空中穿梭,无形中创造了两种相互映照的生存体系,呼兰河的童年记忆在当下得到了延续,而这种延续又融入了作者对人的生命、人性等直指生命本质意义的思考,并因此呈现出一种永恒的价值意味[5]。通过视角转换,作品在自我建构与现实刻画两个层面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融合起来,沉淀出一种沉重而轻松、繁复而明晰、忧伤而明媚的奇特韵味。
(一)视角转换
小说中儿童视角多次巧妙地转变为成人视角,最突出的莫过于文本间隙不止一次出现的对于“荒凉”的感叹,这是以成人视角回望的作者。萧红是个异常敏感的人,极为重视内心体验,总能灵敏准确地感知那些最能触动隐秘情感的人或物,因此在回忆童年时常常会插入多年后的心理感受。这类抒情除了起到延续情感脉络与串联故事主题的作用外,还形成了一种间离的效果,使作者和读者都能够从原本欢快天真的近距离儿童视角中超脱出来,转而透过冷静克制而又不无哀伤的成人视角重新审视呼兰河这一“乐园”。原本由于儿童视角的边缘化形成的“漫不经心”或“轻描淡写”的描述,也受到这种超然态度的影响,使得懵懂、好奇、轻松愉悦等简单朴素的儿童感受转化成蕴含着同情、讽刺、悲悯等多种要素的复杂情感,实现了情感体验的升华。
叙述人称的变化也是成人视角自然切入与两种视角变换的重要形式,例如对小团圆媳妇婆婆的心理描写:“十吊钱可不是玩的……有一次她的儿子踏死了一个小鸡仔,她打了她儿子三天三夜。”[6]在这里,原本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闯入了胡家婆婆的人生,第一人称兼儿童视角下的惶惑不解变作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对其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这段心理描写展示了小团圆媳妇婆婆凶神恶煞之外的另一面:一生勤劳俭朴,生活不易。她扒豆子时伤到指甲,即使“肿得和茄子似的”,也坚持不买二吊钱的红花,一直到手掌胖成了“大簸箕”才狠下心来买。但为了给媳妇治病,前前后后竟花了五千吊钱,还落得“无限的伤心,无限的悲哀”。全知视角下胡家婆婆的心理活动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个愚昧封建的代表在让读者觉得可恨可笑的同时,也不禁感到可悲、可怜与可叹。由此一来,对小团圆媳妇悲剧命运的思索便从老胡家婆婆这单一的人物形象转移至对整个民族所受到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与代代传承而不自知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思上,在更为深沉的文化压迫中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历史性悲剧氛围。
(二)主体建构
童年时期的“我”具有一般孩子的好奇、任性、倔强、爱胡思乱想等特征,也萌发着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嫩芽。“我”关于故乡的记忆有五彩缤纷的河灯、热热闹闹的野台子戏、赶娘娘庙大会等趣味十足的乡土风俗,但也有永远填不上的大泥坑、浮萍一样短命的女子以及纷纷杂杂的口舌,如果说那些故土风情与童年记忆中的嬉戏有关,在一种“已逝去”的凄婉中透着浅浅的欢喜,那么后者则呈现出一种彻底的阴冷且沉重的批判气息。从观看冯歪嘴子的儿子打着灵头幡送母亲这一场面时“我”沉思与发怔的神态来看,彼时“我”的心中已经弥漫起一阵幽奇黑暗的感受,对于这座小城的是是非非,“我”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判断与取舍。
以“我”为中心,以个体意识为中心的美学悲剧,常常表现在个体与社会、环境、自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展现出受主体意识、欲望所驱使的行为过程受到阻碍或被摧残后的毁灭结果[7],萧红的童年始终浸润在这种状态之中。在亲人关系淡漠冰冷的家庭中长大,只有年迈的老祖父时常给予温暖与安慰。然而,面对个体与社会悲剧,年幼的“我”却早就形成了极强的抗争冲动,敢于反抗、敢于质疑大人的思想与言论,在混沌的空间里坚持自己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涂抹了悲剧氛围中的一笔亮色。生命是一场悲剧,失去了灵性的尘世生活令人沉沦麻木,但生命也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挣扎,生命本身是矛盾的,萧红是矛盾的,《呼兰河传》亦是矛盾的。童年回忆中的人和事太过普通,太容易被人遗忘,却恰恰体现了悲剧性的审美深度。惊心动魄的消亡,带给人崇高而悲壮的人生体验;淋漓痛快地宣泄,是某种特殊的精神愉悦;而无声息的生和死,则给人以凄婉幽长的悲凉感受。
处于孤独、寂寞中的“我”,在参与并目睹一幕幕小城悲剧的同时,已经将其内化为特殊的生命体验,化作成长的动力,而成人视角下的冷静叙述与思考则在无形中引导着“我”,使悲喜两种氛围于自我意识的萌发中得到充分的交融。
(三)现实刻画
儿童视角展现了富有童真童趣的喜剧世界,而成人世界则透露出寂寞荒凉的悲剧景象,二者交织渗透,使得文本于写实与抒情、温暖与寒凉、天真与成熟、感性与理性、希冀与失望之间持续碰撞,喜剧式的玩闹嬉戏背后,潜藏着悲剧式的痛苦、毁灭与悲凉。这使得小说超越了单纯的人事记叙,将童年与故乡的种种意象上升到揭露民族劣根性与人生苦难的精神高度。
在前两章中,萧红主要使用儿童视角,表现了发展落后、思想停滞的社会。呼兰河人的自我哄骗与围观兴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这表面上是喜剧性的,但成人视角的深入思索却将这种无价值的人生现象直接撕破:“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5]除了滑稽可笑的唱秧歌外,所有节庆盛典几乎都是为死者举行的。在这种臆想的空间中,人们逃避着一切现实性的恐惧与不安,将精神寄托在鬼魂身上,在逃避和自我安慰中逐渐麻木。
在小说后半部分的“人生写真集”中,客观描述转为主观呈现,读者跟随儿童视角的“我”,在限制性的见闻中感受充满灵性与童真的小城人生,但却也感受到了更为深刻的孤独、寂寞与悲伤。对于《呼兰河传》中的人物,成人视角的“我”忍不住冒出来评价:“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寒凉,因此而带来了悲哀。”[5]在表面欢笑与“和谐”的背后,是生活的艰辛与人心的冷漠,萧红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也给予了无限的理解与同情。
时代社会的残酷与底层人物经历的苦难往往在儿童视角与特殊的语言艺术中被淡化,从最纯粹的眼光出发审视种种不公与残酷,却能得到最为深刻的情感与思想体验,在长年累月的“日常化”中散发出悲剧的震撼力。例如在“我”眼中性情怪异但心地善良的有二伯,前期在“我”与祖父面前的双重态度和偷东西被嘲笑的场景令人捧腹,显得滑稽又可笑;而后期父亲将他狠打在地上,过路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唯恐避之不及,很长时间以后,“才有两个鸭子来啄食撒在有二伯身边的那些血”。冷静细腻的笔触下,看客的冷漠、父亲的狠毒、有二伯的不幸与痛苦与其之前滑稽搞笑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覆盖了一层厚重的悲剧氛围,也由此引发了读者对有二伯形象的重新审视,以至于对其阿Q式维护尊严的行为产生无限怜悯。
在“我”清澈明净的眼中,这个世界是纯粹美好的,也是充满不解与疑惑的,而在疑惑的间隙,成人视角则会对其进行解释,更为深刻地呈现出和谐背后的苦痛,快乐背后的孤独,留恋背后的恐惧与迷惘。
四、结语
虽然被逐出家园,成为一个失去家的孩子,但萧红始终追寻着逝去的故园。于是,《呼兰河传》从儿童视角出发,描绘了有着田园牧歌色彩的温暖童年,然而,这也是作者在痛苦中寻求精神救赎的创作,隔膜、孤独、死亡等内容必然存在,由此形成了喜剧与悲剧氛围交融的叙事空间。或愉快或滑稽的喜剧性衬托了人生悲剧的荒诞与痛苦,而哀伤凄凉的悲剧中却又隐隐夹杂着温暖与希望。
在漫长的漂泊岁月里,在情感与思想不断振荡的逃难途中,在家国沦陷、未来难料的境况下,曾经奋力挣脱的“家”已成为回不去的地方,但童年的回忆却时时在脑海中闪现,童年的“我”与现时的作者交叉闪现,在精神怀乡的同时抒写着民族精神的哀歌,低声召唤着潜隐的生命力。在一笑一叹中将儿童与成人读者一同引入复杂的“呼兰河世界”,引入关于民族、关于人性的思考冲击之中,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首美好童真而又深沉厚重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