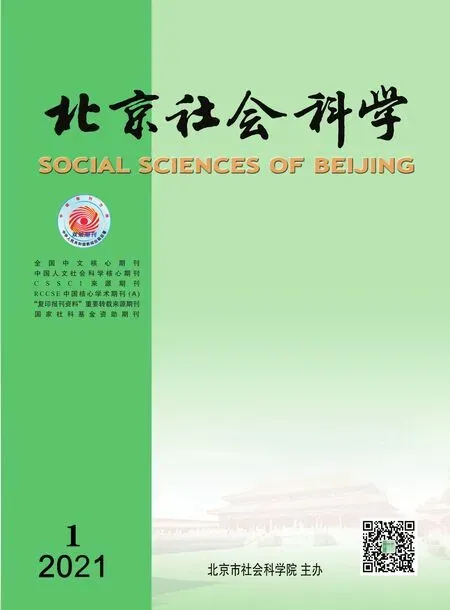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顾一凡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康熙朝经筵日讲始于康熙十年(1671),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期间共完成四书、《尚书》《周易》全书与《诗经》部分篇章的进讲。其中,《尚书》进讲采用外廷日讲与内廷侍讲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讫于康熙十九年(1680),随后,进呈讲义被汇纂为《日讲书经解义》,颁行海内。张英既是《尚书》进讲讲章的分撰官,又肩负《尚书》内廷侍讲的职责。在《日讲书经解义》成书后,张英亦将其精研《尚书》的治学心得著成《书经衷论》。藉由这两部同源经解,可以揭橥儒臣张英如何在编纂御览讲章与结撰个人著述的过程中,传达出不同的旨趣与深意。[1]
一、《尚书》的外廷日讲与内廷侍讲
清朝经筵日讲制度由顺治确立。顺治十二年(1655),在儒臣的反复谏言下,顺治降谕曰:“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2](P714)尽管如此,顺治仍将经筵日讲制度视作“明季陋习”,[2](P630)在位时仅进行六次经筵大典,日讲亦从未坚持,形同虚设。康熙与其父不同,他对经筵日讲格外重视,极力支持,不但在亲政不久便恢复经筵制度,并且命儒臣逐日进讲长达十余年之久。在长期的日讲过程中,进讲模式伴随君主的兴趣、机构的创设和经籍的意义而微调,在南书房设立后进行的《尚书》日讲尤为典型。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末,四书日讲结束,[3](P303)经筵日讲暂休。康熙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重开经筵大典。二十日辰时,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霭进讲“曰若稽古帝尧”与“克明俊德”两节,[3](P313)《尚书》外廷经筵日讲自此开始。与此前的四书日讲和之后的《周易》《诗经》日讲不同,四书日讲时康熙曾提议“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3](P181)亦曾要求在讲官进讲前“将此章书试讲,汝等听之”,[3](P273)但总体而言,康熙“覆讲”与“试讲”的次数极少,日讲仍以讲官进讲为主。《尚书》日讲采取先由康熙亲讲、随后讲官照常进讲的模式,并将此模式贯彻《尚书》日讲始终,换言之,皇帝在《尚书》日讲过程的参与程度较高。各部经典的外廷日讲一般在弘德殿举行,由多位讲官一同进讲。《尚书》日讲亦是如此,有时由喇沙里、陈廷敬、叶方霭、张玉书四人完成,[3](P331)也有叶方霭、张玉书两人进讲的情形。[3](P418)日讲按计划推进,每次阐发数节经文,以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日讲为例,是日进讲“呜呼慎厥终一节、王归自克夏二节、夏王灭德作威一节、肆台小子一节、上天孚佑下民一节、俾予一人一节”,涉及《商书·仲虺之诰》《商书·汤诰》两篇。然讲官们发觉“上天孚佑下民一节,原不应讲,进讲章单内错写应讲”,因而在讲毕后“欲检举”此项疏漏,康熙则认为“错误亦事之常,且系小错,不必认罪”。[3](P333)据此并结合其余进讲记录推想:其一,进讲内容以节为单位,不必在意篇章割裂;其二,由讲官“欲检举”“进讲章单”的失误推测,“进讲章单”并非讲官所写,进呈讲义或许也不是出于讲官之手;其三,“上天孚佑下民”节的讲章虽不应讲,却已备好,《尚书》讲义的完成进度应当比外廷日讲更快。《尚书》日讲偶尔因寒暑、巡视等缘由暂停,除此之外,几乎坚持逐日进讲。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尚书》日讲“应讲者已毕”,[3](P471)宣告完成;十三日,进呈讲义汇辑成书,名曰《书经日讲解义》,康熙为之作序,是书随即刊刻颁行。
《尚书》外廷日讲之所以与其余经典的进讲方式不同,采用皇帝率先亲讲、再由讲官进讲的流程,很可能是由于此时初设南书房,康熙在进行外廷日讲前,已在内廷[4]亲讲一过,并与侍讲儒臣讨论对经义的理解,分享对治道的启发,为外廷日讲的发言做足准备。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初衷[5]是选任“博学善书者”,在皇帝“观书写字”时“常侍左右,讲究文义”。[3](P296-297)据《南书房记注》[6]记载,康熙初召文臣入南书房侍读时,四书日讲几近完结,故康熙十六年年末的内廷侍讲以复诵《大学》《中庸》为主,皇帝间或而非逐日亲讲敷陈。[7](P24-27)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南书房文臣早于经筵日讲开始侍讲《尚书》篇章:“二十八日巳时,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亲讲《书经·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四章。”翌日,康熙再召张英入懋勤殿,“上亲复诵《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四节,又亲讲‘申命羲叔’四节”。[8](P3)此后,康熙亲讲数节经文、次日复诵前日所讲并接续亲讲此后章节的模式被延续,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尚书》内廷侍讲略早于外廷日讲结束。
与外廷多人进讲不同,南书房侍讲的任务由张英独力完成,在侍讲过程中,张英根据皇帝的亲讲内容,灵活作出回应:当皇帝见解公允时,张英多附和圣意。譬如,康熙认为“《书经》曾于往年讲读,今非不可多诵,因欲细阅讲章,期于通晓,未可率略看过耳”。张英对曰:“诚如圣谕,《尚书》乃二帝三王传心之要典,皇上诵读,必期精熟讲论,必字字辨析,真足见圣学之大矣。”[8](P3-4)
遇康熙勤勉好学、阐发新意时,张英不吝赞美之辞。如康熙复诵“在璿玑玉衡”四节时,提到前代历法错乱,而自己“曾讲究古法新法,故知其概”。张英赞曰:“汉唐交食,常多不验,至有晦日日食之事。惟本朝历法,交食毫无差爽,可谓至密。皇上留心于此,所言皆极精微,益见圣学渊广,尤得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之意也。”[8](P4)
若意见与皇帝有不尽相同处,张英亦勇于提出己见。康熙读《泰誓》篇时,提出“汤武之师,虽称应天顺人,然汤有慙德之惧。孔子有谓‘武未尽善’之叹,孟子亦有‘《武成》,取二三策’之语,盖以其处时势之变也”。张英则以为“先儒每疑《泰誓》为后人所附会,意盖谓其绝无含蓄而近于不恭,视《汤誓》气象不同矣。苏轼亦有‘武王非圣人’论,意亦指《泰誓》《武成》诸篇也”。[8](P15-16)
张英还有意将皇帝所讲经义引向治国理政之道。讲至“刑期于无”一句时,康熙以为“古来任人不任法,故常原情轻重,未尝胶于一定,所以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后世人情巧伪,日滋轻重大小,不得不断之一定之法,此亦势之不得已也”。张英补充道:“后世法由一定,所以使人不得任情高下,以防法吏之私,但亦须人与法相辅而行,然后能施法中之仁,而得古帝王钦恤之意也。”[8](P5)康熙满意侍讲效果,认为“《书经》讲解甚明,如此讨论,当有裨益”。[8](P7)合几种情形观之,张英并非逢迎圣意,而是据康熙亲讲的内容,作出公正平直的回应。
内廷侍讲与外廷日讲虽然在地点、人员、方式、意义等方面有所区别,但二者并非隔绝,日讲官应当知晓南书房侍讲的进度。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外廷讲官在完成《益稷》进讲后,跳过《禹贡》《甘誓》,开始进讲《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三节、“其一曰皇祖有训”二节,并在起居注中注明“其《禹贡》《甘誓》等篇,系另讲者,讲官俱不进讲”。[3](P332)在《南书房记注》的记载中,张英已于康熙十七年四月初四日至二十六日侍讲《禹贡》《甘誓》两篇,其中,康熙格外重视《禹贡》,多次借讲解经文与张英讨论古地位置与治河之道。譬如康熙亲讲“导弱水”三节时提到:“从来言治河者,谓宜顺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与之争。此但言其理耳。今河在七里沟,去海止四十余里,若听其顺流入海,既可不劳人功,亦且永无河患,岂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运道遂成枯渠,国计所关,故不得不使其迂回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时势与古不同也。”[8](P7-8)《禹贡》侍讲过程中,康熙君臣关于治水的讨论共进行五次。康熙在研读书经时,尤其关注经义与时事的联系,并从君王的角度分析论证,张英亦加以补充说明。相比其余各篇,君臣投入的时间精力尤多,或许就是日讲官所称“系另讲者”,因议论充分而不必再由外廷讲官进讲。
除此之外,外廷日讲与内廷日讲可能共用同一部讲义。如上文所引,日讲官依讲义进讲,当讲义错写进讲章节时,讲官并未及时纠错,而是照常完成进讲。《尚书》外廷日讲结束后,[9]讲义汇辑为《日讲书经解义》,随即刊刻颁行。[10](PⅤ)内廷侍讲虽以康熙复诵、亲讲为主,但仍需阅读讲章,如康熙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康熙“复诵‘二十有八载’五节,又阅讲章至‘询于四岳’节,有‘好问好察,乃大知之本’语。上曰:‘咨询固宜广揽,而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又不可不详加审辨也。’”[8](P4)《日讲书经解义·舜典》“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节下亦有相同表述:“盖人君图治之要,莫如用贤、理民二端。以天下为一家,而贤路无不广;以天下为一身,而民隐无不达。然非虚心咨访,多方采纳,则廉远堂高,安能尽天下之事而周知乎?故好问好察为大知之本。”[10](P21)可见南书房侍讲时所用讲章与日讲官进讲讲章无异。不过,康熙亲讲“济、河为衮州”九节时提出质疑:“朕阅注中所释九河,诸说纷纭,亦无确见,大约书史经秦火以来,上古事已难于考证,后人以意求之,岂能吻合?”[8](P6)而《日讲书经解义·禹贡》关于“九河”的注释有:“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八条支河,并河之正派,总为九河也,禹时在今河间府沧州一带地方。”“禹则当其(黄河)将入海之际,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为九河,使皆入于海。”[10](P66-67)并未提及诸家对九河的观点,而是“以六经为断”,此处不同于康熙经眼的讲义原貌,或在编校成书时据圣意修订。
康熙通过传统经筵日讲以及新设南书房侍讲,系统深入地考究《尚书》经义,并坚持亲讲、复诵、讨论,在各部经典的日讲中投入精力最多。此后的《周易》日讲与《诗经》日讲,虽仍以外廷日讲和内廷侍讲的形式同时进行,但康熙更为看重南书房文臣的侍讲,在日讲官进讲时不再亲讲。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六日,皇帝以“讲筵行礼进讲,为时良久,有妨朕披览书籍”[11](P317)为由,结束外廷日讲,但仍保留南书房侍讲,并在儒臣的陪伴下继续研读《春秋》《礼记》等典籍。
二、进呈讲义与《书经衷论》的渊源
在《尚书》的经筵日讲和南书房侍讲过程中,张英曾扮演重要角色:他不但是最早入直南书房的儒臣,负责四书、《尚书》《周易》等典籍的侍讲;同时担任日讲官起居注,是《尚书》进呈讲义的分撰官。《尚书》日讲完成后,张英将侍讲书经的心得见解结撰成书,康熙二十一年正月[12](P143)进呈皇帝观览,书前自序云:
臣自供奉内廷之初,正值我皇上讨论二典,讲贯三谟,穷究精研,无微不彻。由是而下逮商周誓诰之篇,靡不再四寻绎,凡昔人之所谓苦其奥博而难通者,皇上必深求义理之归,而亦不辞夫章句诵读之劳。……臣质愚学陋,寡识尠闻,每当讲筵余暇,退入直庐,伏读《尚书》,偶有一知半见,录以纪之,积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说,皆折衷于昔人之言。[12](P144-145)
通过张英的叙述,益见《书经衷论》与《尚书》侍讲的关联紧密,甚至可将是书视作内廷侍讲的衍生品。上文提到《尚书》外廷日讲与内廷侍讲或共用同一部讲义,且讲义并不一定由当日进讲讲官撰写,故进呈讲义的作者尚未可知;而对照《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的观点以及阐发方式,或可窥见两部著作的渊源。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因以库勒纳、叶方霭为总裁官,依惯例署二人领衔编撰。书前有康熙亲制《御制〈日讲书经解义〉序》,云:
朕万几余暇,读四代之书,惕若恐惧。爰命儒臣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说,荟萃折衷,著为讲义一十三卷,逐日进讲。兹特加锓梓,颁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圣王,志勤道远。然夙夜兢兢,思体诸身心,措诸政治,以毋负上天立君之意,夫岂敢一日忘哉
可知是书裒集各家学说,予以折衷定论。细言之,《日讲书经解义》各篇依《尚书》次序,解释篇名、背景后,按文意分节,先解每节主旨,撮其大要;次解节中文字,不分熟僻;再解此节句意,平正通达;终解本节内涵,引向治道。
以《酒诰》为例,《日讲书经解义》于经文前先列本篇的创作背景:“武王封康叔于卫,以其有商故都妹土之地,其臣民化于商纣之恶,酗酒败德,故武王戒勉康叔,欲其变易习俗,作酒诰。”[10](P276)《酒诰》首二节云:“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日讲书经解义》首先点明此段主旨:“此二节书,是举文王戒饬庶邦之言以发端也。”进而解释其中或生僻或熟悉的词语:“妹邦,地名,即商之故都,卫地也。穆,敬也。毖,戒也。越,及也,元祀,谓大祭祀。”又因《尚书》古奥,故将经文疏解为浅显易懂的文字:“武王曰:‘商纣酗酒,臣民化之,至于成俗,惟妹土尤甚。今汝往治其地,当以我诰诫之辞敷布于妹邦之臣民,以革其俗……”。最后阐发经义,云:“盖内而修己,外而治人,莫大于勤,明、敬、慎。多饮,则怠而隳事,昏而丧智,肆而越礼,损德莫甚于此,故圣王切戒之。”[10](P276-277)全书皆依此格式解经。
与之相对,《书经衷论》采用“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12](P143)“诠解大意而不列经文”[13](P581)的体例。全书共四卷,由314条札记组成,其中《虞书》63条,《夏书》32条,《商书》52条,《周书》167条,为张英侍直余暇积久而成。四库馆臣以为是书解经“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新义,……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清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曼衍者多矣”。[12](P143-144)
同以《酒诰》为例,《日讲书经解义》将此篇分15段疏解,《书经衷论》则仅有四条论述,分别讨论商纣之恶成于酒、人生嗜欲必禁绝、周以农事训诫子孙、惟刚德足以制私欲。其中“以刚德胜私欲”一则云:“天下惩忿窒欲之事,柔弱者不能胜,惟刚德足以制之,故《酒诰》之终篇告之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刚制于酒’。盖刚明之气足以慑服群私,如一将当关,而贼自退避,稍一宽假,则向时熟径又不觉失足于其间矣。天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乐于因循、惮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独戒饮云尔乎?”[12](P192)确似宋人解经语录,阐发《尚书》蕴藉的性理之学,语言平易,近于直解。
《日讲书经解义》和《书经衷论》作为御制经解与儒臣著述,体例自有分别,但书中文字却屡有相似之处。
首先,两部经解多处表述相同。例如《日讲书经解义》疏解每节经文时首先揭示此节主旨,而《书经衷论》重要篇章中往往以一则札记概括此篇各段大要,其中常有文字复现。试举一例:
《禹谟》首节史臣统言承谟之始。二节以下承克艰之谟,帝不敢任而归之于尧,益因帝言而又赞尧也。[12](P151)(《书经衷论·大禹谟》第二条)
此一节书,史臣叙禹陈谟之由也。(《日讲书经解义·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14]节)
此一节书,记帝舜然禹克艰之谟,因推广之,而归于尧也。(《日讲书经解义·大禹谟》“帝曰俞允若兹”节)
此一节书,伯益因舜以克艰归尧,因赞尧以勉舜也。[10](P31-33)(《日讲书经解义·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节)
合此后三句出自《日讲书经解义》之论点,即成《书经衷论》札记之言。
其次,《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多数观点相近。前者囿于篇幅体例,阐发观点较为简省,[15]后者则援引文献,予以扩充发挥,但所阐发的观点大致无异。如《日讲书经解义·甘誓》“大战于甘”节论曰:“史书大战,所以深著有扈之不臣。盖诸侯守国,尊王制,重民用,即所以敬天职也。夏王启以威侮、怠弃责之,可谓得讨罪之正矣。”[10](P89)认为夏王启以不敬天为由征讨有扈氏,得讨罪之正。《书经衷论》扩充为:“禹之伐有苗曰‘天降之咎’,启之伐有扈也曰‘天用勦绝其命’,帝王举事未有不称天者,况兴师动众之大乎?‘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正所谓天讨有罪也。天者何?理而已矣。古人最重天时,《尧典》首曰‘钦若昊天’,《舜典》首曰‘以齐七政’,今有扈之怠弃三正,乃不奉正朔,罪之大者。羲和之叛官离次,俶扰天纪,即有胤侯之征,故天之谨承于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12](P160)其观点与《日讲书经解义》一致,只是援引《大禹谟》《尧典》《舜典》《胤征》以佐证三代讨逆均因诸侯不奉正朔,较御制经解更为繁复枝蔓。
最后,两部著作在论证思路上常有相似之处。譬如《日讲书经解义·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节末云:“盖太康惟不能敬,故日流于逸豫。敬则能亲民,而民心固结;不敬则必虐民,而民心离怨。邦国之安危,惟在乎君心之敬肆,五子之言,可谓知本者矣。”[10](P92)指出太康因不敬而流于逸豫,终至失国,由是知五子之言为知本之论。《书经衷论》亦阐发为:“商周以前,人君以逸豫失国者,始于太康。今考其所由,大约外作禽荒是也。史臣记之曰:‘田于洛之表,十旬弗反。’内有强臣篡国,而乃躭于盘游如此。五子之中,仲康在焉,今观其言,知邦本祖德之重、色荒禽荒之非,其能肇位四海也宜矣。”[12](P160-161)同样强调太康失国主要由外作禽荒所致,而仲康知流于逸豫之非,更宜克承大统。尽管成书时间、编撰原则与体例不同,[16]但两部经解在表述、观点以及论证思路上往往暗合,不单同为《尚书》日讲的产物,并极有可能同出于张英之手。[17]
三、御定经解与儒臣著述旨趣辨异
经筵日讲作为皇帝研读典籍、考究经义的学习模式,富有好儒崇学的象征意义和教化作用。《日讲书经解义》作为日讲讲义汇编与御定经解,即便与《书经衷论》同出于儒臣之手,二者侧重点仍有不同,在阐发同一处经文时,讲官与著者身份的转换会使文字传达微异的旨趣,产生“异轨”效应。[18]
《日讲书经解义》由进呈讲章汇辑而成,疏解经义是其首要使命;《书经衷论》作为儒臣的个人著述,偏向关注古文文法,以此诠解《尚书》行文精妙之处。《日讲书经解义》在注解《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时,依惯例详解其中文字与句意,总结为“仰观天文,俯察民物,如是而春历无差,羲仲之职尽矣”。[10](P4)《书经衷论》于此处颇似评点文章之语,云:“此数语而详察尽矣,后世月令、历数诸书繁文夥说,有能出其范围者乎?于此可见古人立法之密,亦可见古人文字之简。”。[12](P146)又如《日讲书经解义·舜典》疏解“象以典刑”一节,谈舜维持天下之法,离章辨句,颇为繁琐:
舜摄位时,设为墨、劓、剕、宫、大辟五等之常刑,以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使人晓然共知,所以待夫罪之重者。然虽入五刑,而情犹可疑,法犹可议,则法遣远方以宽宥之,此重中之轻。五刑之外,有鞭刑,用之官府;有扑刑,施之学校,所以待夫罪之轻者。然入是刑,而情犹可矜,法犹可恕,则又许出金以赎之,此轻中之轻,所谓法之经也。若入于五刑,鞭、扑之中,或眚而过误,灾而不幸,此情轻可矜者,则不待流宥、金赎,而直赦之;或藉宠而有恃,不悛而再犯,此情重可恶者,则不许流宥、金赎而刑杀之,所谓法之权也……[10](P149)
《书经衷论》阐发此段经义极为精审,[19]并补充道:“文止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不复不漏,后世刑书繁重不能出其范围,洵化工之笔也。”[12](P149)此外,《书经衷论》评价《禹贡》“文简而事该,言约而旨明,错综变化,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12](P157)合观《尚书》所载誓师之词,云:“禹之词温,《甘誓》之词简,《胤征》之词烦,《汤誓》之词惧,《泰誓》之词慢,《牧誓》之词谨。《费誓》之词小,诸侯之体也。《秦誓》之词惭,霸王之略也。”[12](P164)张英为桐城派滥觞者,其文以六经为根柢,解经时亦不免加入对古文文法、文体的思考,这与《日讲书经解义》的解经要务略有不同。
经筵日讲本为皇帝讲论经史、启发治道而设,故《日讲书经解义》每节末的论说部分常引申至治国驭民之道;《书经解义》颇类宋人解经语录,释经多言及性理。譬如张英诠释《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曰:“惟危者如覂驾之马、放溜之舟,此心一纵,顷刻千里。惟微者,如水中之星、风中之烛,旋明旋灭,不可捉摩。惟精者,审择之明知也。惟一者,坚固之守勇也。先言惟精,次言惟一,便是自明诚之学。”[12](P153)而《日讲书经解义》论虞廷十六字,云:“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详言之。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先以治之之本传之。心法者,治法之本也。故其丁宁告戒有如此。”[10](P40)前者视惟精惟一为明诚之学,后者则以之为治法之本。又如《日讲书经解义·大禹谟》“可爱非君”节云:“舜曰‘可畏非民’,禹曰‘民惟邦本’,孟子曰‘民为贵’,民心从违,即天命去留,如之何不以民事为兢兢?”[10](P41)将民心与天命、治统联系。与之相对,《书经衷论》于此处引出对民之所欲与民心向背的思考,云:“‘可爱非君’,又曰‘慎乃有位’,圣人何尝不思永保天位为可乐哉?至桀、纣而始不知君之可爱位之当慎矣。‘敬修其可愿’,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也。至桀、纣而始不知人之所愿而咈民以从欲矣。”[12](P153)张英对体认性理、修身养性尤为看重,尝曰:“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20](P499)《书经衷论》所论亦属张英研习性理之学的心得,异于《日讲书经解义》有资于治道的旨归。
经筵日讲自宋至明一直是士大夫教化帝王的重要途径,[21](P96)讲官利用进呈讲章和当面进讲的机会,规劝皇帝效仿三代圣主,重视君主修养;而在著书立说时,安民重贤往往成为张英阐发书义的落脚点。如《皋陶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节,为皋陶陈安民之谟。《日讲书经解义》据此敷陈,认为教养安民与君王修身敬德密不可分:“凡安民必兼教养,皋陶不言养者,府修事和,既得其养之后,则政教为尤重。诚能敬以敷教,合乎秩叙之自然;勤以修政,期于命讨之各当。则民咸相安于典、礼德化之中,而不至有刑辟之犯,人主之所以修身、迪德者,即在是矣。”[10](P50)《书经衷论》诠解此节书义,云:“典、礼、命、讨四者,国家之大务,而一归之于天;天视、天听二者,人主之所凛,而一符之于民。彼愚贱其民者,其亦未之思乎?”[12](P155)指出敬天之务当符之于民,君主以愚贱视其百姓,既未思安民之义,亦失敬天之职。又如《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节,《日讲书经解义》解之曰:“此一节书是皋陶推广迪德之要在知人、安民,而禹深叹兼尽之难也。”并以为“禹此言,盖欲帝舜深思其难,而求尽其道也”。[10](P45-46)强调君王面对识人难题,应尽其道。《书经衷论》此处则讨论才德何为选任标准:“故尧知其不可以君天下,如鲧,如共工,如驩兜,皆当世所称有才人也,而天位之让终归之齐栗之舜,平成之功终归于勤俭之禹,自圣人如尧舜,尚不敢用有才之小人,而曰畏乎巧言令色,如此况后世之天下乎?”[12](P156)
《日讲书经解义》尽管被列入御定经解,但与《书经衷论》同出于儒臣之手。在诠解《尚书》经义的过程中,著者有意效仿历朝日讲官,不单扫清《尚书》文辞艰涩的障碍,尤重于引导帝王发掘书经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治国之道,并重视对自身品格德行的修养;与此同时,掩饰其研读《尚书》的心得感悟,将对文法的理解、对性理的体察、对安民的期许置于个人著作中,渊源极深的两部著作所透露的旨趣尤可涵泳。
四、余 论
综上,康熙执政之初曾醉心儒家经典,在创设南书房后,不但在《尚书》外廷日讲中亲讲经义,并在内廷复诵经文,与侍读文臣讨论斟酌。《尚书》日讲结束后,内、外廷共用的进呈讲章即时刊刻,冠以《日讲书经解义》之名;南书房侍读张英亦将研读书经所得撰成《书经衷论》,进呈乙览。虽然撰写原则与体例不同,但若将两部经解对读,其中文字复现、观点重合、论证相仿之处屡屡可见,加之张英同为进呈讲章分撰官和侍读学士的身份,两部著作或同出于张英之手。尽管如此,两部经解所传达的旨趣与用意略有差别,《日讲书经解义》侧重疏解经义,关注书经蕴含的治国之道,规劝君王修身敬天,《书经衷论》则看重《尚书》行文章法,借助性理之学释经,并流露安民重贤的期许,引发“异轨”效应。
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一节中,谈到康熙积极参与日讲,亲讲经义,因而“帝王和讲官的角色就被彻底地颠倒过来了”;讲官在与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失去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权,并成为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者,而非思想灌输者。[21](P103)通过对《尚书》外廷日讲和内廷侍讲情形的还原、对《日讲书经解义》《书经衷论》的渊源差异的考析,可以知晓康熙在日讲中积极议论,发表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主导日讲的推进,但侍讲文臣并非无原则地附和帝王心意,而是基于对典籍的研判和体悟,给出有益于君主治国驭民、修身养性的见解。康熙亲讲后,外廷讲官照常进讲,内廷学士与之讨论,士大夫对皇帝的影响依旧存在。至于道统拥有权的“争夺”,在这段“权力关系”中,文臣仍保有“引导”的戏份,不但在与君主的互动中保持己见,在个人著述中亦可以“自由”地诠解经义。[22](P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