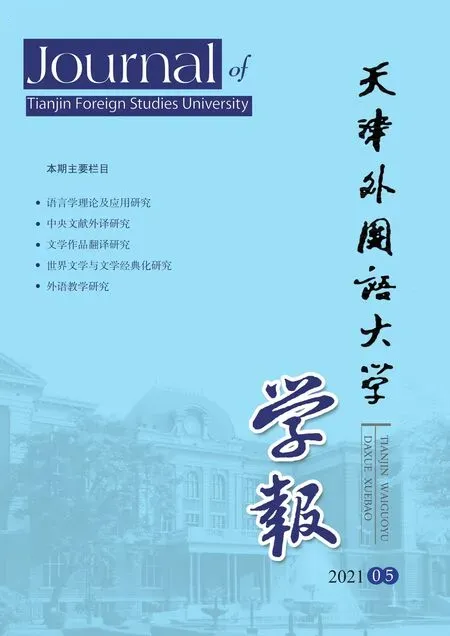译介、出版与批评研究
——诺曼·梅勒在中国的经典化
许梅花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一、引言
2015年,凤凰联动图书推出诺曼·梅勒文集,作者的名字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出现在每一部作品的封面。事实上,作为二战后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委实不需要如此造势为世人所知。他在25岁时就凭借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打响声名,之后一直笔耕不辍,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写下了近 40部作品,文类多样,内容庞杂,有小说、戏剧、电影剧本、诗歌、传记、政论文集、文学批评等,并开创了独特的“新新闻体”(new journalism)的写作体裁。他曾包揽美国每一个让人熟知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一次国家图书奖、两次普利策奖、一次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也曾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梅勒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以犀利的文风、锋利的笔头直指美国社会的阴暗角落,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言美国社会的文化变革,完全无愧于“美国意识的代言人”(Scott,1973:15)的称号。他也曾屡次招致非议,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美国文坛经典地位的树立。
哈罗德·布鲁姆(2005:21)在谈论经典时说:“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不可否认,梅勒作品的文学性与社会性已使得梅勒在美国位居经典作家之列,而他在中国的经典化远不如在源语文化中那样迅速与直接,因为“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托托西,1977:44)。外国作品想要在译入语国家被接受并奉为经典,抛开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不谈,在促成它成为经典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作品译介、出版及其相关批评研究。好的译介作品不仅能扩大读者范围,更能帮助文学研究者深层次把握文本,拓宽阐释的空间,推动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加速经典化的脚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作品研究的持续性又能促进译介活动的繁荣,帮助巩固经典的地位。因此,梅勒作品的译介、出版与批评研究对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经典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梅勒作品的译介与出版
据现存资料记载,国内对梅勒的介绍起步比较晚,大约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从1948年梅勒发表第一部作品《裸者与死者》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介绍尚属空白,究其原因,除了因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导致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与引进受到一定程度的掣肘之外,革命文学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且不论单个作家,甚至是“从1966-1971年,长达五年时间中国也没有出版过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孟昭毅、李载道,2005:390),直至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缓和,但见效甚微。
1978年,国内对外国文学的禁锢初显松动,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会议精神强调要“学习中外优秀文艺遗产”(洪子诚,2002:572)。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1983:185)同年11月25至26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议上周扬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对外国文学一定要学,而且要好好的学,认真学。要批判,首先也要学。……对于外国作家,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上有可取的,值得借鉴之处,就应该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科研处,1979:106)。
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欧美文学伺机而入,梅勒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范围里。国内对梅勒的第一次介绍始于陆凡先生,她在《文史哲》1979年第2期发表了《评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在文中比较了梅勒的存在主义与欧洲存在主义的差别。在该杂志的第5期她又发表了文章《美国犹太文学》,在文中她把梅勒、贝娄、马拉默德、塞林格和罗思并称为“当代最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陆凡,1979:55),同时介绍了梅勒的部分作品。同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19位当代著名或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梅勒的短篇《人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n,1951)赫然在列。之后王齐迠在文章《存在主义与美国当代小说》中提到了梅勒具有存在主义精神的作品,如《白色黑人》(The White Negro,1959)、《裸者与死者》、《一场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1965)。同年7月,美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了解美国文学提供了便利。可以说1979年为梅勒在中国的经典化打开了窗口。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与梅勒有关的介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见诸于《读书》、《译林》、《世界文学》、《外国文坛动态》等杂志对梅勒已发表新作、近况的介绍。董鼎山、陆凡、冯亦代等人都是当时活跃在各个杂志上的梅勒引荐者。董鼎山作为当时闻名海内外的作家曾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星期六评论》等报刊撰写书评时论文章,改革开放后开始为国内刊物《读书》每月写一篇“纽约通讯”,主要介绍、评述、剖析现当代欧美作家与作品,梅勒则屡次出现在他的文章里。仅《读书》杂志与梅勒密切相关的就有四篇。在《所谓非虚构小说》(1980年第4期)中称梅勒为名作家,并为读者解释了“非虚构小说”一词的来龙去脉,在《在野兽的腹腔》(1981年第10期)和《诺曼·梅勒与杰克·阿波特〈在野兽的腹腔中〉续记》(1981年第12期)中详细介绍了梅勒与阿波特的渊源,并两度称梅勒为名作家,在《〈古代的傍晚〉——谈诺曼·梅勒与他的新作》(1983年第6期)中指出梅勒的作品“也应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并预言“梅勒之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同时认为“说到美国文坛而不提梅勒,等于说美国全国而不提纽约”,随后介绍梅勒的新作《古代的傍晚》(Ancient Evening,1983),坚信它的出世“将更惊动各国的读书界人士”(董鼎山,1983:111-112)。除此之外,他还在《译林》和《博览全书》发表相关文章,如在《谈书·论事·话家常(六)》(《译林》1986年第3期)中用心推荐梅勒的作品《黑夜的军队》,在《二战文学四大家》(《博览群书》1995年第8期)中对梅勒褒贬分明,称《裸者与死者》是一部惊人的战争小说,但认为“后期著作有些粗制滥造,滥竽充数”,并批评《奥斯卡瓦尔德的故事:美国疑案》(Oswald’s Tale: An American Mystery,1995)“没有什么文学可言”(董鼎山,1995:13),在《一部独特异常的美国近代史——虚构、报道、思考、写照的缀合》(《博览群书》1998年第8期)中大力向读者推荐梅勒的作品《我们时代的辰光》(The Time of Our Time,1998),认为“无论如何,任何喜好文学的青年人,如果尚未涉猎这位作家的著作,应该花钱去买一本《我们时代的辰光》”(董鼎山,1998:14),并保证读者读后不会失望。
除了董鼎山的极力推荐和赞美之辞,陆凡也在《浅谈当代美国文学》(《译林》1980年第1期)中用了“当代优秀作家”的字眼形容梅勒,并在译文《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桑谈美国文学》(《译林》1981年第1期)中呈现了哈桑对梅勒的评价,在文中谈及哪些作家和作品最为重要的时候,哈桑认为梅勒应列入其中。冯亦代在《读书》上发表的《哈洛特的鬼魂》(1992年第9 期)用长文介绍了该部作品以及各类书评,在1995年第11期发表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美国疑案》中用极为详细的史料作为证据为梅勒在董鼎山的文章《美国二战文学四大家》中受到的批评辩解。其他一些介绍文章也不应忽略,如钱满素的《从美梦到梦魇——诺曼·梅勒的〈一场美国梦〉》(《读书》1983年第1期),仲子的《诺曼·梅勒〈古老的夜晚〉》(《读书》1983年第11期),海舟子的《诺曼·梅勒新作〈耶稣福音〉》(《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第6期),潘小松的《诺曼·梅勒五十年作品集》(《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5期)等。除以上文章外,有必要提及的是这期间出现的一些重要文学史专著对梅勒作品的收录,如在董衡巽、朱虹等人编写的中国第一本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简史(下)》(1986)中梅勒的作品被划分在二战后战争小说一类,在常耀信编写的英文版《美国文学简史》(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0)中战后作家这一板块也很有分量地介绍了梅勒。以上皆是当时文坛或是外语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对一个作家的偏好或是溢美之词都会成为外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风向标,这为梅勒在中国的经典性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内部支撑。
除了重要的介绍人物,知名刊物的主动推介也为经典的建构再添砖瓦。《译林》杂志在1980年第2期“外国文坛动态”栏目中将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梅勒排在第一位,并推荐其新作《死刑执行者之歌》(又译《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1979);在1984年第2期“世界文坛动态”栏目中推介梅勒的《古代的傍晚》,称他为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在1986年第2期“世界文坛动态”栏目中报道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48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提到的唯一一个美国作家就是梅勒,在1992年第4期“世界文坛动态”栏目中报道梅勒推出新作《玛丽莲·梦露传记》(Marilyn:A Biography,1971)。《世界文学》杂志在1980年第6期报道了《刽子手之歌》获得1980年普利策奖的情况,在1992年第1期“世界文艺动态”栏目中报道了梅勒的新作《娼妓的鬼魂》(又译《哈洛特的鬼魂》,Harlot’s Ghost,1991)问世,并评价“梅勒这位以揭露美国社会黑暗而著称的大作家至今仍然思想敏锐、言辞尖刻”(泰戈,1992:319),在1998年第1期“世界文艺动态”栏目中报道了“曾经作为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犹太作家”(海舟子,1998:315)梅勒的新作《耶稣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1997)的出版。《外国文学动态》杂志在1998年第5期公布了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图书的出版,其中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排在第一位。
由此可以看出在欧美文学大量输入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后,梅勒的名字一直频繁地出现在文学爱好者的眼前,这显然离不开以上权威人物的介绍和权威刊物的推广,当然也与梅勒所属的文学流派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改革的重心由乡村挪移到城市,从而导致由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向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而后现代文化即是这种转型时期的产物。“特定的社会文化格局会形成特定的文化需求、文化地位和接受语境,这些因素会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赞助人与译者,使赞助人与译者在顺应特定社会的文化需求,文化地位和接受语境的过程中完成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姜秋霞,2009:51)梅勒属于后现代派作家,国内的文化格局也为后现代文学的引荐培育了良好的土壤,最终促成了梅勒翻译文学的产生,为梅勒在中国经典化的真正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1990:47)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将占据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第一种情形: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者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学发展属于第二种情形,整体上迎来了翻译文学自建国后的又一次高潮,梅勒译介也随之迎来了第一次小高潮。仅1988这一年四部梅勒的作品就得以翻译到中国,它们分别是《裸者与死者》、《硬汉不跳舞》(Tough Guy Don’t Dance,1984)、《刽子手之歌》、《艳星梦露》。紧接着《一场美国梦》的译本于次年面世。1990年,《夜幕下的大军》的译本面世也再次为读者带来福音。三年时间里六本译作相继面世,足以窥见国内读者对梅勒的关注颇为热切。马原(1989:78)在《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1期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小说》中曾这样评价梅勒:“作为两次大战后美国最主要的作家,梅勒写出了大量颇为畅销的小说及其他读物,可以说他是严肃作家中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大读者群的当代小说家。他的《美国梦》、《黑暗中的军队》、《性的囚徒》、《刽子手之歌》以及《硬汉不跳舞》都是印数逾百万册的畅销书。梅勒是现代小说家的又一种代表,他的例子表明,杰出的现代小说家完全可以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完全可以是乔伊斯他们的反面。相信没有谁去认真怀疑梅勒小说的艺术价值,有谁想表现一下个性吗?”马原的肯定言辞再一次证明梅勒在读者群中受欢迎的程度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
然而,之后的十年有余,译界动向一直归于沉寂。虽然《夜幕下的大军》、《刽子手之歌》、《裸者与死者》分别在1998年、2000年、2001年重印,以证明中国读者对梅勒的热情仍旧不减,但没有新的译作出现或多或少延缓了梅勒在中国的经典建构步伐。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译作出现小高峰到之后十余年的沉寂很大程度是因为版权和文学思潮影响的缘故。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梅勒作品受到版权保护。而梅勒跟中国出版方之间也有些误会,不太想作品在中国出版。80年代后期海量欧美文学作品不断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坛作家也发起“小说革命”,他们倾向于以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创作,如马原、余华、莫言等。虽然他们都极其推崇梅勒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对他们影响最深的两位作家莫过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位不断被中国作家提起,自然也影响了很多读者的选择。
新千年之后,与梅勒有关的介绍性文章不如上世纪繁密,这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介绍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先前译本的出现使得中国母语读者远离了“只闻其人,不见其作”的年代,梅勒爱好者也开始对作品进行深度品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浓厚必然渴求更多译作,以便从整体上把握作家的创作特征和创作走向。然而,译介情况却不尽如意,除了2000年《刽子手之歌》和2001年《裸者与死者》的重印以及《一场美国梦》的再译,截止2007年为止只增加了一个新的译本《鹿苑》(The Deer Park,1955)。这期间也有一些选译文章刊出,如杨仁敬先生在《译林》2002年第5期的《美国名作家最早习作三篇》翻译了梅勒9岁创作的《火星人的入侵》(The Martian Invasion,1934),黄灿然在《书城》2003年第8期发表了梅勒的散文译作《畅销书》(Bestsellers,2003)和《托尔斯泰》(Tolstoy,2003)等。导致梅勒译介稍显停滞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 1997年《耶稣福音》出版后,梅勒在创作上几乎销声匿迹,十年没有新作问世,在外界看来不免有江郎才尽和过气之嫌;其次,对中国读者界、批评界、文学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成为大家阅读和研究的风向标,尽管梅勒多次被诺贝尔奖提名,却一直失之交臂;最后,梅勒的作品大部头居多,再则晚年创作的主题与宗教玄学相关,内容晦涩难懂,这对如今追求快餐阅读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沉寂持续到2007年,终于迎来转机。这一年对梅勒和中国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沉寂十年的他再出新作《林中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2007),小说讲述了希特勒的童年。该书一出版就遭到德国各界的强烈抗议,同时也让更大范围的中国读者了解了梅勒。《东方早报》、《广州日报》、东方网国际新闻等媒体都给予了相关报道。令人扼腕的是,同年11月10日,梅勒因肾衰竭与世长辞。全世界媒体争相报道梅勒去世的消息,美国著名作家琼·迪迪恩称他为“美国伟大的良心”,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表示他的逝世是“美国文学巨人的陨落”。《中华读书报》、《中国时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环球人物》等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梅勒的离世进行全面报道或转载,并进而介绍梅勒的生平和创作。自此更大范围内的中国读者开始熟悉这位文学巨匠。借着此股劲风,2008年《刽子手之歌》再版,2009年译作《林中城堡》面世。之后六年虽无新的译作出现,但《刽子手之歌》能在中国再版三次也是令人欣喜的成就,一方面说明该文本的经典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该译作质量上乘。当然图书的一版再版并不能说明该书是否为经典,但如果有经典价值的图书畅销能吸引读者和学者的关注,那么经典化一定会成为可能。
然而,经典的建构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2009-2015年间梅勒的译介似乎又陷入沉寂,又或许是在沉寂中蓄势待发。2015年,由文艺评论家肖涛牵头策划,凤凰联动和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诺曼·梅勒作品集》,收入《裸者与死者》、《硬汉不跳舞》、《鹿苑》、《林中城堡》、《巴巴里海岸》(Barbary Shore,1951)、《耶稣福音》、《夏洛特的鬼魂》、《古代的夜晚》、《我们为什么在越南》(Why We Are in Vietnam,1967),梅勒译介再次迎来高潮。除了前四本再版的译作,后五本全是最新译作。此次的发行力度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和研究梅勒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说明在过去的六年里梅勒并未淡出出版机构和译者的视线,而是等待时机厚积薄发,从而真正建构起梅勒的经典地位。恰如姜秋霞(2009:80)所言:“只有一种文学建立了庞大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文学输入国提供较为广泛的主题选择余地,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被广泛译介。”虽然美国文学历史不及英、法等国,但的确是人才辈出,出现了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美国文学良心”的梅勒,他的作品主题涵盖范围广,且处处针砭时弊,这样的作家完全值得译者和研究者的严肃对待。在出版人牵头的情况下,2015年梅勒作品集的全面推出便是水到渠成。正如同年徐贞在《英语广角》第3期发表的《梅勒主义的兴起——诺曼·梅勒访谈录》所提出的,梅勒作为一种主义已经在中国兴起,并大有燎原之势。
从以上对梅勒译介、出版情况的爬梳我们发现译者和出版机构在作家和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的基础作用和传播功效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仅仅将印刷物上架或是放在新媒体上,作家作品就能得到关注的时代已经过去。出版社在出版经典之前更要主动去发现、建构经典。除了出版机构这一“发现人”在外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的连接作用,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梅勒作品的批评研究
除了译者和出版机构在经典建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突出作品的经典意义,还需要“召开专家座谈会,或者请专家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或者进入大学的课堂,这对作品‘经典化’才会产生催化作用”(周百义,2017:11)。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梅勒一直都是文学评论界的核心人物。从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发表以来,关于他的评论和研究就从未中断过。从最初报刊杂志上的零星评论到如今研究专著近50部,博士论文达 30多篇就足以看出国外梅勒研究确实蔚为壮观。在美国南弗罗里达大学还专设“诺曼·梅勒协会”,创办专刊《梅勒评论》(Mailer Review),每年都会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比照国外,目前国内还未召开过梅勒专题讨论会,但对梅勒作品的研究却是如火如荼。截止目前已有近230篇研究文献问世,其中包含7篇博士论文、36篇硕士论文、4部专著,可见梅勒研究在中国已属于一个重要领域。
比对前面的译介轨迹发现在1979-2000年间梅勒研究的进度并未跟上译本出版的速度。1979年以前梅勒研究十分罕见,几乎是一片空白。1979年,陆凡作为第一位对梅勒作品进行正式评论的学者在《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评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比较梅勒的美国存在主义与欧洲存在主义的异同。自1979年后到2000年间,虽然《裸者与死者》、《刽子手之歌》、《硬汉不跳舞》、《一场美国梦》、《夜幕中的大军》的中译本相继面世,但研究论文并不多见,仅存的文献,如任绍曾、师华、黄铁池三人的文章也只是对梅勒的单个作品进行解读,研究范围和角度相对受限。
2000年以后,随着译本数量与日剧增,评论者有了更多自由阐释的空间,研究文献激增,梅勒作品也随之建立起自己的经典地位。从研究数据分析,出现研究峰值的年份分别是2007年、2012年、2015年,这与梅勒的过世和译本大批量的出现密切相关。从已发表的刊物看,有30多篇出现在CSSCI来源及其以上的刊物上,如《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等,这些刊物都是国内外语研究方面的重要刊物,前四种更是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专业刊物。从研究的学者看,谷红丽、杨昊成、邹惠玲、石雅芳、任虎军、张涛、陈娜、王刚、陈夜雨、许梅花等都是国内梅勒研究的重要贡献者,同时也是高校里的专职教师,这对梅勒在大学文学课堂上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谷红丽作为我国第一位系统研究梅勒的专家,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为切入点的博士论文《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于2003年写成,同名专著于次年出版,2009年第二部专著《理解诺曼·梅勒》出版。两部专著都得到其恩师杨仁敬先生的高度赞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谷红丽,2009:1)。她还在国内知名文学研究刊物上发表梅勒研究文章10余篇。邹惠玲和石雅芳既是梅勒作品的译者,又是研究者,对梅勒作品的评论和解读比一般研究者更具洞见,更为深刻,这为梅勒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余学者也有相关博士论文和研究论文,为梅勒研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从研究的角度看,大多数文献倾向于从存在主义、权利、暴力、创伤等主题与叙事特色方面去分析单个作品,其中尤以分析《裸者与死者》最甚。近来也有少数学者从犹太性和宗教观方面去关注梅勒,如乔国强、陈娜、石雅芳、许梅花等。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主要从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心理学等角度对梅勒的多部作品进行关注,并提出独到的见解,为梅勒在学界的经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国内梅勒批评研究,发现梅勒研究并不因他的离世或是未获诺奖而止步。相反,研究者因其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对相关作品不断进行多角度解读和评论,真正诠释了梅勒作为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文学经典的落地生根之处也在于此。
四、结语
综上所述,梅勒在中国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就译介和研究的文类来看似乎远远不够。梅勒的短篇、诗歌、政论文集等也能更有效地帮助中国读者和学者了解和研究梅勒,从而维系和巩固梅勒的经典地位。故而出版人、译者和学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共同促进显得尤其必要。总而言之,在经典塑造的过程中,译者、出版人和学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译者为学者研究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提供好的译本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学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能积极推动相关作品的译介和出版,这不仅对译者和出版机构辨识经典作品,对作品进行译介起到指导作用,还能帮助译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提高翻译质量,更能帮助读者提高对作家与作品的认识,从而拓展译本接受的空间。出版界作为连接读者和译者的中间媒介要更加努力地去抓住读者的期待视野,去识别、建构经典,为译者的文本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