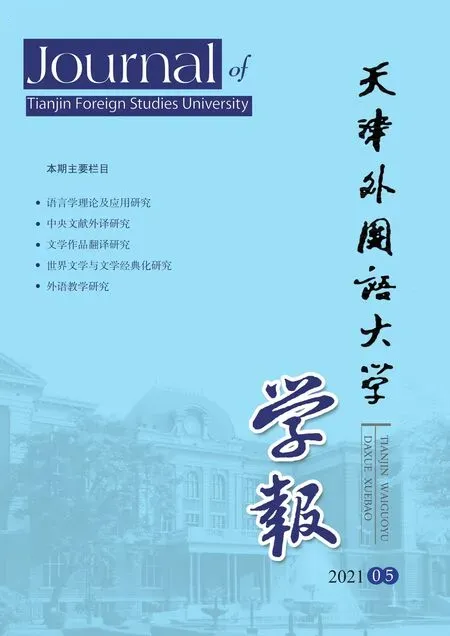芬兰符号学简述
埃罗·塔拉斯蒂
孙 婧译
(成都理工大学 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近年来,符号学在芬兰占有一席之地,这证明了在芬兰学术氛围中考察这一运动的特殊条件和性质是合理的。众所周知,符号学已经适应各个地方的传统,这促进国家符号学派的迅速兴起。
尽管已经存在发展这种运动的条件,但几乎不可能用其来概述芬兰的符号学派。在考察芬兰的符号学历史时,必须区分两种符号学:第一种是显性符号学,它明确地假定了具有特定符号学方法的符号学术语,因此在当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国际通用的“符号学”;第二种是隐含符号学,相互的接触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了显性符号学的发展,这又或许可以追溯及理解前期或者是与之相关的现象。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找和辨别符号学的先驱一样,发现了被遗忘的学者,这些学者似乎在这个时代之前突然成为符号学的象征,在芬兰也可能找到符号学的前身。
在国外,最著名的是芬兰民俗学派的代表可能是卡尔·克伦①和安蒂·J. 阿恩②,他们的声誉甚至一直传到巴西(雷纳托·阿尔梅达的《民俗情报》③为“芬兰学派”保留了整整一章)。
众所周知,安蒂·J. 阿恩提出的方法与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基础,就像贝拉·巴托克和佐尔坦·科达在音乐中使用伊尔马里·克伦④提出的民歌分类原则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将阿恩的方法视为引发叙事结构研究的方法之一(如参见克劳德·布雷蒙德的叙事逻辑或A. J. 格里马斯的语义结构)。即使在今天,芬兰的农学、民俗学和人类学也是他们对符号学感兴趣的最重要领域。在20世纪初,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科学背景之外,人们不得不提到作家亨利·帕兰德(1908-1929)的孤独形象,他在芬兰符号学的历史上应有自己的地位,他是向芬兰介绍俄罗斯形式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帕兰德在其瑞典发表的简短文章⑤中谈到了哲学、诗歌以及音乐中形式的问题,他甚至谈到情感的形式,即符号学。然而,由于22岁的帕兰德在立陶宛考纳斯读书时过早去世,因此未能在芬兰产生更长久的影响。此后,亨利·布洛姆斯解决了帕兰德与俄国形式主义思想接触的问题,而他的叔叔威廉·塞斯曼成为了这联系的纽带,他后来在立陶宛出版了一项美学研究——《瓦西里·塞斯马纳斯》,由齐蒙斯基亲自作序⑥。
在 6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和转型模型开始影响语言学时,人们在语言学领域可能会找到大量隐含符号学的证据(如帕沃·拉维拉的书《芬兰的真理与方法》⑦)。总体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实证主义倾向一直在芬兰的学术界中占主导地位,这尤其阻碍了欧洲符号学观念在芬兰的普及。
在哲学上,这种取向自埃伊诺·凯拉以来就很明显了,格奥尔格·亨利·冯·赖特在模态逻辑领域(如《范数和行为》⑧)的作品被视为属于隐含符号学研究,尤其是对符号学国际发展的影响,如他的理论对格里马斯符号学发展的影响。这也同样适用于贾科·欣蒂卡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但不包括他最近在《一月刊》⑨上发表的论文,他在其中揭示了皮尔斯哲学的游戏理论基础,并且可被视为皮尔斯哲学对于符号学的研究。
显性符号学在芬兰何时开始?首先,必须对芬兰科学生活的一个特征进行评论:蓬勃发展并在其他地方广为接受的学派或学派所持的看法,在芬兰可能仅有少数学者代表。小的规模当然会有一定质量问题,但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芬兰的显性符号学起步只有零星的少数几人。
第一篇论文最早是在60年代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对结构主义的评论。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也许还可以包括在芬兰出生的埃利康纳斯·马兰达所撰写的重要文章——《民俗学中的结构模型》。该文章于1962年在《中西部民俗学》⑩上发表,从概念上简要介绍了民俗学的结构研究历史,从安蒂·J. 阿恩制定的类型、阿恩·普罗普的功能以及汤普森的主题到李维·史特劳斯或邓德斯的主题。该文着重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神话思想的代数公式,尤其是各种中介模型的分析。而托马斯·塞博克的对切列米斯人十四行诗的研究⑪被视为整个调查研究的基础(请注意塞博克也是从芬诺·乌格里斯特开始的)。孔格斯-马兰达的研究不仅在民俗学领域,而且在文学领域都与后普罗普的叙事分析有关联。
在文学研究领域,简单来说,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开始出现于 60年代末,如尔玛·兰塔瓦拉所写的有关巴特和戈德曼的文章⑫,以及阿托斯·奥加拉的第一篇结构主义研究(《诗歌中基本语言概念的系统论》⑬,芬兰语)。在其他方面,奥加拉可能也是最早在芬兰大学中开始符号学教学的人之一。他的出版物与符号学的国际发展息息相关,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语言风格研究导论》⑭、《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导论》⑮和《文本理论导论》⑯。他最近的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讨论了歌德的教学思想⑰。这些所有出版物仅有芬兰语版本。
在 60年代末期,其他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兴趣。在哲学上,劳里·鲁蒂拉发表了《关于标志、含义和真相》⑱,这属于现象学符号学领域,在芬兰少有代表性研究。此后,鲁蒂拉讨论了艺术品的标志性特征⑲,反映了皮尔斯哲学的影响。
在那个时期的语言学中,提到了如伊萨·伊特科宁对赫姆斯列夫的词汇学的研究⑳。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芬兰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在早期阶段最佳评论文章可能是雷莫·安提拉和伊萨·伊特科宁的文章㉑,他们的论文最初是面向芬兰读者,计划发表在《世界各地的结构主义》一书。但是,由于该选集最终未能出版,因此该论文仅在赫尔辛基普通语言学系的专著系列中发表。
然而,在芬兰,对符号学的讨论直到 70年代初才变得更加活跃,部分原因是《瑞典文选》的传播㉒。这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芬兰是一个双语国家。除了芬兰语外,瑞典语也像基因一样嵌入芬兰的社会结构。翁贝托生态介绍了符号学研究㉓(缺席结构)和哥德堡认识论专家库尔特·阿斯佩林和本特·伦德伯格编辑的选集㉔。随后笔者用瑞典语介绍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文本。但是就法国结构主义(格雷马斯和克里斯蒂娃)来说,他们采取了一种略带批判的态度。同样遗憾的是,李维·斯特劳斯是通过翻译埃德蒙·里奇写的有关李维·斯特劳斯的生活和主要思想的书㉕来阐述思想的,并不是翻译其原始作品来介绍给芬兰读者的。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一篇文章被翻译成芬兰语。
法国结构主义的思想最先是由约翰娜·恩克尔传播到芬兰的㉖,她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与文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专家珀特·卡尔卡玛一起在奥卢大学工作㉗,后来被委任在赫尔辛基大学文学与美学系任教。
70年代初,所谓的“结构主义圈子”也开始在赫尔辛基开展活动,这最初作为一个完全非正式的阅读小组已有几年了㉘。这个圈子主要由哲学系的学生组成,它在每周的会议上讨论列维·斯特劳斯、福柯、艾柯、巴特斯、阿尔都塞、塞巴格、格雷马斯和拉康的主要著作。一些来自国外的符号学家也参加了会议,如维尔莫斯·沃伊格特(匈牙利)、鲍里斯·加斯帕洛(苏联)和克里斯汀·苏达(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圈子的第一个真正的选集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也是第一个芬兰符号学选集,其中包括阿托斯·奥加拉、萨图·阿波、埃罗·塔拉斯蒂、奥斯莫·库西、约翰娜·恩克尔、佩蒂·卡卡玛的文章,以上提到的均为符号学家。这个选集的标题为《结构论—符号学—诗集》,是由高迪亚姆斯于 1974年出版㉙(该书包含英文摘要)。这项出版工作受到热切关注,两年后芬兰教师协会出版了另一本选集㉚——《结构主义:研究与教学》(编辑是安娜·丽莎曼帕、基尔斯蒂马基宁、埃罗·塔拉斯蒂),该书重点介绍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的问题。
符号学讨论的增加也源于来自国外的符号学家的访问和演讲。1971年,受马蒂·库西教授的邀请,维尔莫斯·沃伊格特在赫尔辛基大学民俗研究所(即1978年之后的比较宗教研究所)做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结构主义的演讲(芬兰语)。另一个有影响力的访问是 1974年由瑞典语言和文学系组织的波兰符号学家和逻辑学家耶日·佩尔克的访问。
1978年,赫尔辛基大学音乐学系举办了一场音乐符号学研讨会,它最初是在一个非正式的体系内进行的,后来又成为了大学正式课程提纲的一部分㉛。来自加拿大的让·雅克·纳蒂兹在1978年访问了该乐队,并做了两次关于音乐符号学的演讲㉜。一年后,赫尔辛基大学受到A. J. 格雷马斯的访问,后者就巴黎的符号学派和神话学的法国研究发表演讲。后来,这两个讲座的演讲稿都在芬兰出版㉝。
近年来,对巴赫金的散文、巴赫金文艺复兴以及对他的复调小说和狂欢文化的讨论热闹起来。尔基·皮拉嫩㊱、佩卡·佩森宁㊲、亨利·布洛姆斯㊳讨论并阐明了巴赫金的思想。布罗姆斯是芬兰苏联符号学领域的领先专家之一,他发表了关于朱里·洛特曼的几篇论文,并将巴赫金主义的思想应用于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分析㊴。
到70年代末,出现了两篇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文章:《神话和音乐:美学的符号学方法》和《瓦格纳、西贝柳斯和斯特拉文斯基》,以及民族学论文《1900年至70年代冬季的塞纳河——朱卡·彭南娴熟的在普鲁威西湖钓鱼》㊵。前文中根据格里马斯的分析和同位素概念、布雷蒙德和普罗普的叙事模型以及李维·史特劳斯的思想提出了一种理论模型,用于研究神话与音乐的相互作用。在第二部分,该模型不仅特别适用于李斯特·瓦格纳和西贝柳斯的浪漫音乐美学,还适用于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时期,尤其是歌剧演说家俄狄浦斯·雷克斯。彭南的研究基于李维·史特劳斯和雅各布森的转换模型,其观点是这一文化的一般特征仅存在于结构深层而不是明显特征。
近年来出现了用符号学对诗歌的分析研究。其中马蒂·库西(芬兰民间诗作《马纳兰小姐》)㊶和埃罗·塔拉斯蒂(当代著名诗人伊娃莉莎·曼纳的诗)㊷的分析,都受到了包德莱尔文章的启发。李维·史特劳斯和雅各布森的“聊天”,皮尔乔·迈亚·托沃宁使用格雷马斯、洛特曼和罗兰·波斯纳提出的方法㊸,都对芬兰著名诗人艾拉·梅里洛托的诗歌展开了详尽分析。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彭蒂·莱伊诺对1855~1895年间芬兰诗人卡洛·克拉姆苏的度量标准的分析㊹,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及芬兰民间诗歌㊺中的头韵原则,这在广义的符号学意义上也可以归类为结构研究。
在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符号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但只有少数研究明确使用符号学的概念和方法。劳里·洪科(图尔库大学文化研究教授)和仲夏(赫尔辛基大学比较宗教教授)于197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人类学》㊻的教科书(芬兰语),其中的结构分析被介绍为当代人类学方法的中心之一。在彭蒂卡宁的研究中,有一篇方法论文章《深度研究》㊼,介绍了一种传播理论程序用于分析传统传播。在分析深层结构时,他区分了四个层次:纹理、样式、内容、结构,并在他的《玛丽娜·塔卡隆·乌斯科托》㊽(玛丽娜塔卡隆宗教)一书中应用了此研究方法(后来出版为《口腔保留曲目和世界观》㊾,他分析了一名卡累利阿女性的保留曲目,并展示了她是如何选择、改造和组合旧素材以形成新整体的。
在社会学领域,帕沃洛普宁首次介绍了结构主义思想。他在赫尔辛基大学已经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发表了几篇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斯莫·库西㊿的一致性理论研究,不仅受到哲学和社会政治学的启发,而且受到了翁贝托·生态的符号方法的启发。在人类学的背景下,必须提及尔基·佩基拉的硕士论文《民族音乐学的分析方法》(芬兰语),这是第一个将音乐符号学方法引入芬兰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研究的研究。
人类学领域充分反映了美国传统在芬兰的影响,这一点在语言学和哲学上更为明显。伊萨·伊特科宁出版了几本有关语言学研究中认识论问题的书,由此也隐含地触及了符号学问题。他在《语法理论和超科学》中讨论了语言概念、社会控制、语言可变性以及语言描述的本体论地位的哲学基础。目前他正在研究思想语言(心理语言/表示)的概念,这是任何符号/通信系统功能的共同标准。实际上,这启发了皮尔斯的思想,特别是在莱莫·安提拉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和《类比概论》一书中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讨论,安提拉更详细地研究了皮尔斯的符号类别图标/索引/语言领域的象征及皮尔斯的外展原则。安提拉说任何学习都必须通过外展来进行,这构成了理解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的基础,而这两者都需要在特定的具体文化和历史环境中使用人的智力。他在论文《概括、外展、进化和语言》中更加仔细地研究了外展的原理。
第三位研究符号学问题的芬兰语言学家是图尔库大学阿博·阿卡德米学院的尼尔斯·埃里克·恩克维斯特教授,他提出了一种结构上的文体学方法。在他的书中,最相关的也许是《语言文体学》和《语篇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尤其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恩克维斯特提出的文本策略概念非常有趣,不仅是因为它使人联想到由A. J. 格雷马斯开发的格纳拉蒂峰模型,而且还有自60年代末以来的恩克维斯特教学,他使话语分析概念在芬兰广为人知。
其次,“课程思政”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育素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有明确其肩负的德育使命,才可能将价值观教育融入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传道授业和价值引领双重目标。因此,在高校中,师德至为重要,应将教师德育意识的提升纳入日常培训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其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
在哲学领域,符号学在芬兰的出现主要是皮尔斯哲学对少数学者的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劳里·鲁蒂拉,还有来自图尔库大学的里斯托·希尔派恩在几场演讲(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这些演讲讨论了皮尔斯符号学。目前学界正在编写有关皮尔斯哲学的专著,理论哲学教授伊尔卡·尼尼洛托在赫尔辛基大学开设了皮尔斯实用主义课程。
符号学方法在文学、诗歌、音乐和电影等各个艺术领域的研究中被证明也是卓有成效的。也许可以将诗人卡里·阿隆普罗看作是一个前卫的结构主义者,他在6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诗集,题为《开胃酒,开放城市》,其诗歌在70年代末进入了区域性的“符号主义”。此阶段,他的作品有《卡尔佩亚·阿维斯图斯·韦伦基耶罗斯塔》(《淡淡血液循环的预兆》)和《图库:坦佩雷历史的画像》,后者介绍了历史写作的符号学部分,它表明了历史文献实际上是符号和符号学单位。在关于17世纪初芬兰哲学家西格弗里德·阿罗努斯·福修斯的生活和制度的散文诗中,阿龙普罗还使用符号学概念作为诗歌创作的方法。法国的让·鲍德里亚还对他的诗提出物体系统的有趣比喻。
符号学方法也在戏剧学领域进行了实验。在坦佩雷大学戏剧学院,卡里·萨洛萨阿里将格里马斯符号学应用于卡洛·戈多尼的喜剧演出。在音乐符号学中,埃罗·塔拉斯蒂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得益于韦斯屈莱大学音乐学院出版了音乐符号学的选集。自1974年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诗集出版以来,高迪亚姆斯出版公司已在芬兰出版了许多符号学研究,还出版了研究彼得·沃尔伦电影的《电影中的意义》,这是由电影中为数不多的芬兰的符号学专家——塔莫·马尔姆伯格翻译。
在视觉领域,即在对绘画、电影、电视和广告的符号学分析中,丹·斯坦博克、阿尔蒂·库萨莫、埃克基·休塔莫也有很多有趣的研究。《合成》(艺术相互关系研究杂志)成立于1982年,它由芬兰艺术教育研究学会出版,并连续出版了与艺术和美学符号学相关的研究。1982年还发行了一部专门介绍芬兰符号学的专刊,其中包括21名芬兰符号学家的论文。在这其中,应特别提及由奥斯卡·帕兰德撰写的有关叔叔瓦西里·塞斯曼的著作,他曾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教授哲学(至1963年),在立陶宛时被认为是一位准犹太人,在此期间,他与A. J. 格雷马斯进入了同一所大学学习法学。
芬兰的符号学派在1979年底成立了芬兰符号学协会,获得了更为正式的地位。该协会的主要目标是“作为芬兰符号学间联系的纽带,促进芬兰的符号学研究,与国际保持联系”,并在社会功能中特别强调了最后的这个目标。但是,它并非面向符号学的所有流派,只包括遵循整个国际发展的范围领域。
在国外的符号学机构中,学会与巴黎的语言研究团体和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的语言和符号学研究中心联系最为密切。自协会成立以来,主席一直是埃罗·塔拉斯蒂,副主席是亨利·布洛姆斯,董事会成员是佩蒂·阿洪、奥斯莫·库西、汉努·里科宁、尔基·佩基拉。
芬兰符号学协会于1980年8月在赫尔辛基组织了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主题是芬兰文化符号学。尽管之前曾有关于符号学的讨论(如于韦斯屈莱大学芬兰科学院组织的会议:1973年关于艺术哲学的会议和1978年关于图像概念的会议),但这次是芬兰符号学家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以明确的符号学术语进行讨论。这次座谈会不仅涉及芬兰文化的符号学,而且芬兰的符号学家还提出各种理论观点,并对芬兰符号学的现状进行了研究。
在大会之前发表的有关芬兰文化符号学的论文引发了不同领域的符号学专家的热烈讨论,因此专题讨论会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这些论文中有从神话和历史的角度对芬兰文化进行了考察,即民族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大会还详细讨论了各种艺术中的民族认同、艺术表现以及其他成为芬兰人的标志。大会期间根据不同的符号学框架分析了芬兰的文学文本、电影、历史小说等,组委会还决定在未来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专题讨论会。
芬兰的符号学不能被描述为一种非常统一的现象,也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流派。到目前为止,大学中的符号学教学还是比较零星的,仅仅是对这一学科感兴趣的个别教师。只有于韦斯屈莱大学将符号学基础课程列为常规课程。因此,这种教学的结果只会在几年后显现出来。
注释:
① Kaarle Krohn,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Oslo: Instituttet for sammenlignende kulterforskning, sero B: 5, 1926).
② Antti J. Aarne,Verzeichnis der Märchentypen(Helsinki: FF Communications No. 3, 1910).
③ Renato Almeida,Inteligencia do Folclore(Brasília: Companhia Editora Americana MEC, 1974).
④ Ilmari Krohn,Suomen Kansan Sävelmiä I-IV(Helsinki: Finnish Literary Society, 1893-1933); see also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Über die Art und Entstehung der geistlichen Volksmelodien in Finnland”(Helsinki: Helsingfors Akad. Abh., 1899).
⑤ Henry Parland,Säginteannat, Samlad prosa 2, Collected Prose, ed. Oscar Parland (Borgå: S. & Co.,1970).
⑥ Henry Broms, “Kaikki elämässä on vain muotoa”,Helsingin Sanomat, 8 July 1979, 17.
⑦ Paavo Ravila,Totuus ja Metodi(Porvoo: Werner Söderström, 1967).
⑧ Georg Henry von Wright,Norm and Action. A Logzcal Enquzry(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3).
⑨ Jaakko Hintikka, “C. S. Peirce’s ‘First Real Discovery’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The Monist,1980(63), 304-315.
⑩ Elli Köngäs-Maranda & Pierre Maranda, “Structural Models in Folklore”,Midwest Folklore, 12(Bloommgton: Indiana University, Fall 1962), 133-192.
⑪ Thomas A, Sebeok, “Decoding a Text: Levels and Aspects in a Cheremis Sonnet”, in Style in Language,ed. Thomas A, Sebeok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221-235; see also, by the same author:“The Texture of a Cheremis Incantation”, in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962(125),523-527.
⑫ Irma Rantavaara, “KirjallisuudentutkImuksen Strukturalistisista Metodeista”, inYearbook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Forssa: Finnish Literary Society, 1969), 5-20.
⑬ Aatos Ojala, “Sanataiteen lingvististen peruskäsitteiden systematiikasta” (with German summary)Virittäjä, 1968(2), 125-140.
⑭ Aatos Ojala,Johdatus Lingvistiseen Tyylin Tutkimukseen, 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Jyväskylä University (Jyväskylä, 1971).
⑮ Aatos Ojala,Johdatus Strukturalistiseen Kirjallisuustieteeseen, 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Jyväskylä University (Jyväskylä, 1971).
⑯ Aatos Ojala,Johdatus Tekstin Teoriaan, Public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Jyväskylä University (Jyväskylä, 1974).
⑰ Aatos Ojala, “Goethen Pedagoginen Provinssi”,Kasvatus ja sivistys,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at Jyväskylä University, 1980.
⑱ Lauri Routila,Über Zeichen, Sinn und Wahrheit, Studia Philosophica Turkuensia Fase. I, Institutum Philosophicum Turkuensis, Annales Universitatis Turkuensis series B, 1970(117).
⑲ Lauri Routila,Miten Teen Taiteesta Tiedettä(Turku: Societas Philosophica et Phaenemonologiea Finlandiae, 1979).
⑳ Esa Itkonen, “Zur Characterisierung der Glossematik”,Neuphilologische Mitteilungen, 1968(3), 452-472.
㉑ Raimo Anttila & Esa I tkonen,Finnish Structuralism: Present and Past(Helsinki: Department of Gener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976).
㉒ Kurt Aspelin & Bengt A. Lundberg,Form och Struktur(Stockholm: Bokförlaget Pan/Norstedts, 1971).
㉓ Umberto Eco,Den Frånvarande Strukturen. Introduktion till den Semiotiska Forskningen(Lund: Bo Cavefors, 1971).
㉔ Kurt Aspelin,Textens Dimensioner(Stockholm: Pan/Norstedts, 1972).
㉕ Edmund Leaeh,Lévi-Strauss(Helsinki: Tammi, 1970).
㉖ Johanna Enckell, “Onko strukturalismi uutta humanismia?” Pohjoinen, 1969(1), 7-9.
㉗ Pertti Karkama,Metodi ja Maailmankatsomus. Kirjallisuudentutkimuksen Suuntaviivoja(Oulu:Pohjoinen, 1974).
㉘ Jöns Carlson, “Strukturalistiseen Veljessarjaan!”Hälläpyörä, Hämäläisen osakunnan lehti 1974(4), 7-8.
㉙ Satu Apo, Johanna Enckell, Osmo Kuusi, Eero Tarasti, eds.,Strukturalismia, Semiotiikkaa, Poetiikkaa(Helsinki: Gaudeamus, 1974).
㉚ Anna-Liisa Mäenpää, Kirsti Mäkinen, Eero Tarasti, eds.Äidinkielen-Opettajainliiton Vuosikirja XXIII.Strukturalismi: Tutkimus ja Opetus(Helsinki: ÄOL, 1976).
㉛ “Musiikkisemiotiikan Kollokvio 1978” (A collection of student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s organized at the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University of Helsinki, unpublished material).
㉜ Eero Tarasti, ed., “An Interview of Jean-Jacques Nattiez”,Musiikki, 1978(3), 125-147.
㉝ A. J. Greimas,Lectures Held in the University if Helsinki(4-5 May 1979), Suomen Semiotiikan Seuran Julkaisuja I (Helsinki: 1979).
㉞ Mihail Bahtin,Kirjallisuudentutkimuksen ja Estetiikan Ongelmia(Moscow: Progress, 1979). (A selection of essays.)
㉟ A. J. Greimas,Strukturaalista Semantiikka(Helsinki: Gaudeamus, 1980).
㊱ Erkki Peuranen, “Bahtinin Sosiologinen Poetiikka”,Kulttuurivihkot, 1980(I), 16-28.
㊲ Pekka Pesonen, “Mihail Bahtin, formalisti, anarkisti vai marksilainen”,Tiede & Edistys, 1982(2), 39-52; see also by the same author “Uusmytologismi: näkökulma modernismiin. Venäläisen symbolismin‘mytologismin’ tarkastelu”,Kirjallisuuden Tutkijain Vuosikirja, 34 (Pieksämäki, 1980), 153-168.
㊳ Henry Broms, “Mihail Bahtin”,Parnasso, 1978(I), 26-32; “Carnivalized Culture”,Kanava, 1979(3),141-147; “Bahtin’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s a Form of Messianism”,Turun Sanomat(12 Feb. 1980).
㊴ Henri Broms, Osmo Kuusi, Olli Niitamo, Hellevi Yrjölä, “A New Database for Myths and Values”,forthcoming in a special issue ofSemiotica(Semiotics in Finland).
㊵ Jukka Pennanen,Professional Winter Seine-Fishing on Lake Puruvesi from 1900 to the 70s(Helsinki:Kansatieteellinen Arkisto 30, 1979).
㊶ Matti Kuusi, “Manalan neiti”,Parnasso, 1972(3), 129-134.
㊷ Eero Tarasti, “Strukturalistinen Analyysi Eeva-Liisa Mannerin Runosta”, inÄidinkielenopettajainliiton Vuosikirja, 1976(23), 151-158.
㊸ Pirjo-Maija Toivonen, “Aila Meriluodon Runouden Eksistentialistinen Rakenne.”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1978).
㊹ Pentti Leino, “Kaarlo Kramsun Metriikka”, inYearbook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Pieksämäki,1980), 7-91.
㊺ Pentti Leino, “Strukturaalinen Alkusointu Suomessa” (Structural Alliteration in Finnish), Diss.University of Helsinki, Forssa, 1970; see also Hannu Launonen,Hirvipoika. Tutkielma Unkarin Kirjallisuudesta(with English summary) (Pieksämäki: Finnish Literary Society, 1976).
㊻ Lauri Honko & Juha Pentikäinen,Kulttuuriantropologia(Porvoo: Werner Söderström, 1970).
㊼ Juha Pentikäinen, “Depth Research”,Acta Ethnographica Academicae Hungaricae Scientiarum 21(1-2), 1972, 127-151.
㊽ Juha Pentikäinen,Marina Takalon Uskonto(Helsinki: Finnish Literary Society, 1972).
㊾ Juha Pentikäinen,Oral Repertoire and World View.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Marina Takalo’s Life History(Helsinki: FF Communications No. 219, 1978).
㊿ Osmo Kuusi, “Yleinen Konsistenssiteoria” (A General Theory of Consistency) (master’s thesis,Department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