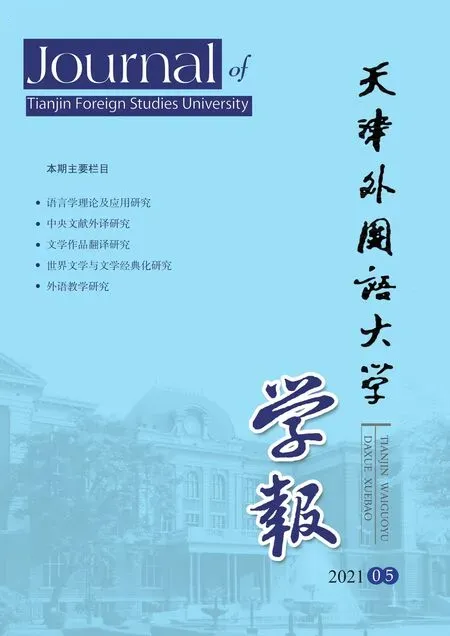“世界文学”的首创权之争
高树博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引言
长久以来,一旦提到“世界文学”,中外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将此词的首创权归于歌德。1827年的歌德谈话是所有学者探讨世界文学这一命题时必须征引的第一文献。事实上,这个根深蒂固的认识是逐渐被强化和经典化的,许多因素扭结在一起才促成了今日之局面。本文首先从接受史角度,描述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被经典化的过程。该过程的统一性在于不同语言(德语、英语、汉语)的学者始终不渝地坚持歌德对“世界文学”术语的绝对地位,对其价值深信不疑。与此相对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语言学转向以及学术方向的精细化(偶然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世界文学”术语的起源(尤其是谁第一个使用)反而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德国学者先后发表的词源学考古成果足以质疑歌德的首创权。详细展现新发现的材料及其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是第二部分的任务。全世界学者围绕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而产生的争论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世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鉴于论题、篇幅和传播路径,本文将撮其要者述之。
二、术语“世界文学”的散播
总体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在 19世纪中后期的德语文化圈及欧洲流行起来。然而,世界文学在后歌德时代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要而言之,德国的统一与撕裂和德意志主义/日耳曼主义的起伏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比较文学领域,第一本多语种刊物《全球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的创建者、世界文学理论的先行理论家匈牙利人胡戈·梅茨(Hugo Meltzl)在1877年发表的《比较文学当前的任务》一文难觅歌德创造“世界文学”一词这样的表述,但他倾心于歌德式(Goethean)世界文学。梅茨(Meltzl,2014:36-41)尖锐地批评了德国文学史家盖尔维努斯(及其追随者)所写的五卷本《德国民族文学史》(1835-1842)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来赞美德国在国外的文学影响和德国作家对外国材料的创造性使用是对歌德的误解。1899年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用德语发表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文的结尾声称是歌德创造了“世界文学”这个术语(Damrosch,Melas & Buthelezi,2009:66)。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称为“文学教皇”的纳粹主义日耳曼文学学者赫尔穆特·朗根布彻(Hellmuth Langenbucher)以主编的《世界文学: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小说、故事、诗歌》(Weltliteratur: Romane, Erzählungen und Gedichtealler Zeiten und Völker,1935-1939)杂志为阵地,领导了一场挪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来反对由世界观构造思想的运动,从而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以世界文学为中心,朗根布彻不遗余力地为德国读者量身制作旨在强化纳粹政治统治的德意志/日耳曼文学图景。但是1937年第25期献给歌德的《世界文学》才第一次提到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朗根布彻的评论《世界文学?》区分了世界文学和整个世界的文学(Mani,2014:156-161)。1940年《世界文学》杂志更名为《世界文学:报告、文摘、评价》(Die Weltliteratur: Berichte, Leseproben und Wertung,1940-1944),刊发的《德国性与世界文学》(Deutschheit und Weltliteratur/ Germanness and World Literature)一文以充满自信的感叹号替代了朗根布彻的问号。文章的作者中尉齐格蒙德·格拉夫(Siegmund Graff)抛出一个相当简洁的标语:“世界文学!歌德创造了这个词。”更重要的是,格拉夫确立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与希特勒的德意志国家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彻底实现了朗根布彻所津津乐道的军事化(ibid.:165-166)。自此世界文学异化为知识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叱咤风云。
1945年德国比较文学学者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1949:3)出版的标志性著作《歌德与世界文学》(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第一章“理念”开门见山指出歌德创造(coin)了“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作为献给施特里希七十大寿的文章之一,埃里希·奥尔巴赫1952年发表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起首第一句话点题讲到‘世界文学’一词,就强调所要谈者乃是‘歌德所说’的那个‘世界文学’”(杨俊杰,2016:18)。上述各种著述为推动歌德主义世界文学的固化作出了贡献。
然而,1987年魏茨的《维兰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和2008年沙莫尼的《施略策 1773年首创“世界文学”概念》先后在《阿卡迪亚》(Arcadia:Internationale Zeit schrift für literarische Kultur,德国比较文学期刊)杂志的发表对“世界文学”一词最初来源的既成观念形成了挑战,但是学界对这些新发现的采纳并非一蹴而就。
在英语资料中目前常见的以“世界文学”为主导关键词的专著、编著、指南、读本都将歌德视为世界文学的起源,但起初的情况并非如此。爱克曼编辑的德文版《歌德谈话录》于1836年分两卷发行。时隔三年后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就将第一卷译成英文并广受赞誉。然而,英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约翰·奥森福德(John Oxenford)抱怨富勒的漏译太多,几乎等同于删节,他重译的《歌德谈话录》全本(重排过对话的编年顺序)于1850年出版。在此之前奥森福德已翻译过歌德的自传《诗与真》(1846)。奥译本在英语世界不断重印,流传甚广,即使一百多年后亦是权威译本。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扛鼎之作《什么是世界文学?》虽然责备其翻译的不完整,有时不得不依从德文本,但是他却大量引用。他编选的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原典则直接取自奥译本。当朱光潜翻译德语版《歌德谈话录》遇到难解之处时,亦选择参考奥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奥译本以 world literature对译歌德的Weltliteratur(Eckermann,1906:455),这种处理是不是很快就得到沿用呢?事实并非如此。1886年比较文学先驱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Hutcheson Posnett)撰写的《比较文学》问世,第四卷命名为“世界文学”。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文献,因为波斯奈特首次提出了什么是世界文学这样一个命题,但他思考的根本不是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遑论将“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权颁发给歌德。仅从语言上我们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同样是世界文学,单从现有中译本我们无法发现它们的差异。实际上,波斯奈特(2015:345-353)所指的世界文学历史悠久,他在行文中通篇书写的都是带连字符的“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或许连字符形式可以追溯到歌德的通信者苏格兰哲学家、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据称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在当时就已被国外期刊直接引用,而卡莱尔则“将这一概念译成英语(world-literature)”(曾悦,2018:78)。可不要轻视这一符形之别,因为最近有关世界文学的论战就与此有关,如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文章《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a Hyphen)。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由此发现英文术语“世界文学”在词形学/语符学上的演变。达姆罗什(Damrosch,2014:42)所编《理论中的世界文学》的标题为What Is World Literature?,而未经修改的波斯奈特的原标题为What Is World-Literature?,如今前者是标准的英语书写格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英美学界对歌德主义世界文学的青睐。
如果施特里希的《歌德与世界文学》英译可以视为歌德专利的世界文学在英美散播的重要一环,如德裔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1987:17)197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就援引的是此书,来自德语文化圈在美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通过个人的学术魅力和高校体制将世界文学的歌德专利代代相传。例如,1939年移居美国的捷克裔学者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和1947年移居美国的德裔学者奥尔巴赫都曾执教于耶鲁大学。韦勒克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最重要代言人,他“成功地使自己所代表的新方向(形式主义——引者)最终在组建中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取得了强势地位,这一优势直接成为美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得以诞生的基础”(狄泽林克,2009:44)。韦勒克(1987:201)作于1955年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十章“歌德”里有如下一句话:“‘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是歌德首创的。”以韦勒克的地位、影响,他的前述说法在美国会被奉为圭臬毋庸置疑。1974年瑞士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Francois Jost)(1988:13)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说:“歌德能创造出世界文学这个词绝非纯粹出于偶然。”1986年约斯特(1988:1)在为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赞扬道:“歌德提出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词,那就是‘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德国学者魏茨1987年的考证在英美学界引起反响了吗?答案是否定的。1993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93:21)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宣称歌德新造的“世界文学”一词跟他的欧洲观有关。这是一本被称为“20年来唯一一本全面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论著,被欧美大学广泛采用作为研究生教科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委员会将本书列为该学科的第一本必读书。”(巴斯奈特,2015:扉页)由此可以想见在整个20世纪歌德主义世界文学理念是多么深入人心。
若说由于时间相隔太近和条件限制导致巴斯奈特无法及时吸收德语学界的新成果,那么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情况是否业已改观?不尽然,达姆罗什当是其中最突出者。令人惊讶的是,“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丹穆若什,2014:1)赫然成了达姆罗什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的导论之标题。不恰当地说,他的这个标题与格拉夫的标语异曲同工。在达氏著作的助推下,“世界文学,歌德造”几乎变成英语学界的常识。《劳特里奇世界文学指南》的导言坚持歌德是让“世界文学”变得通用的第一人,正文中的多数作者提及世界文学时皆沿用了歌德创造它的句式。该书从历史维度梳理世界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为《歌德:世界文学的起源和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约翰·皮泽(John Pizer)在正文中也写到歌德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一词的知识分子,并以注释形式提到阿帕德·贝尔奇克(Árpád Berczik)和魏茨(Weitz)的著述(D’haen,Damrosch & Kadir,2012:3)。关于歌德的认识延续到2013年达姆罗什、陈永国和尹星(2013:3)合编的《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其“世界文学的起源”部分的开篇(《歌德论世界文学》)之导读这样写道:“尽管同时代的赫尔德和斯塔尔夫人等人也都研究过世界文学的不同方面,但‘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却是歌德首创的。”2014年达氏所编《理论中的世界文学》的第一部分“起源”(Origin)所收录的第一篇作品依然是 1827年歌德与爱克曼关于世界文学的谈话。正文中coin一词与歌德的关联也如前所述。此类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从翻译施特里希的著作到后学径直使用coin一词,我们可以断定长期以来英美学者几乎潜在地认定是歌德将Welt和Literatur两词合二为一创造了新词Weltliteratur。
由此可见,“世界文学”在英语语境旅行时词源问题已经有了变化。实际上,《劳特里奇世界文学指南》收录的那篇文章没有完全反映皮泽的主张。早在2006年皮泽所著《世界文学的观念》(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一书的导言“什么是世界文学,为何在英译课程中教世界文学?”(他用的是Weltliteratur而非world literature)就留有篇幅述评世界文学的维兰德起源。皮泽指出,虽然魏茨没有给出确切的日期,但维兰德第一次使用名词“世界文学”的时间肯定早于歌德。他说从1987年起维兰德对“世界文学”的第一次使用在德语世界变成了公共知识,但它仅仅指向古代作品。皮泽道出的另一个实情是大多数美国高校从事世界文学英译的教师和学生肯定会觉得魏茨那么少的档案资料有何值得出版。皮泽亦坚持魏茨的发现无重大意义(Pizer,2006:1-2)。这似乎解释了为何他后来的前述文章仅把魏茨作为一种参考资料。后来皮泽的论断果然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在皮泽的著作里有两条注释是贝尔奇克的文章。他不以为意地说贝尔奇克宣称施略策1772年创造了“世界文学”一词(ibid.:151-153)。在施略策和维兰德之间,皮泽选择了维兰德;而在维兰德和歌德之间,他则选择了歌德。因为歌德世界文学的意义是如此不言而喻。皮泽的注释一度成为英语学界理解施略策的唯一来源(Kern,2019:3)。
2011年德汉出版的《劳特里奇世界文学简史》(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在概述“世界文学”的词源时指出,歌德创造了“世界文学”是不正确的。他简单地提到施略策和维兰德比歌德先使用“世界文学”一词,并否认他们对歌德的“世界文学”产生过任何影响(D’haen,Damrosch & Kadir,2012:5)。2013 年德汉与人(D’haen,Domínguez &Thomsen,2013:xiii)合编的《世界文学读本》对施略策和维兰德的处理与《劳特里奇世界文学简史》中相同。另一位同样擅治德国文学的美国学者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2014年所编《作为世界文学的德国文学》的导论里用两句话描述了维兰德世界文学观的内容。其中有一篇论述布莱希特的文章,则将维兰德的世界文学作为重要的比照对象,而施略策却只出现在注释里(Beebee,2014:4,106-114)。在其他不以世界文学为对象的著述里结论或许又有所差异。
我们对英语学界关于维兰德和施略策的态度所作的勾勒还是相当不完整的。面面俱到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1)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学者在当今英语学界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2)他们以教学、著作、(合)编著、刊物、(会议)论文等体制性载体来推广自己的成果,影响广且深;(3)他们与中国学界有持续的、密切的合作,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界是明星式的权威人物。从后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此问题上并非亦步亦趋,相反,擅长德语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对维兰德和施略策的世界文学观要比英语学界重视得多。
我们将大致呈现中国学界在“世界文学”词源方面的接受境况。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输入休戚相关。李华川(2002)曾谨慎地宣称陈季同(1852-1907,晚清著名外交家、翻译家)是世界文学观在中国的发轫者,而且陈季同因与法国人蒙弟翁(Foucault de Mondion)合著《中国人的戏剧》而被李华川奉为“近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五年后潘正文(2007:16)更自信地宣布或许受过歌德世界文学观的影响,“1898年,陈季同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但必须注意潘正文所引用的陈季同与曾朴谈话所说的是要“参加世界的文学”。显然世界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不能完全等同。后来的文学史证明前贤基本进行的是世界的文学实践。因而“世界文学”常常成为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总汇的同义词。
1922年郑振铎(2013:66-76)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统一观》主要援引了美国学者莫尔顿(Richard Moulton)的世界文学观点作为支撑。除了郑振铎的着力推介和借鉴外,梁实秋、陈钟凡、郭绍虞或高度评价或受益于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所勘定的文学演变模式(王波,2018:49)。转年郑振铎又发表了《世界文学》介绍1922年美国出版的著作《世界文学》,“尽管认为它‘十分的不完备’,但对它的‘新’给予了肯定,表现出他从世界角度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迫切渴望”(杨玉珍,2005:107)。应该说郑振铎对世界文学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1937年志在翻译歌德作品的周学普依据德文本选译出版《哥德对话录》,但该译本“由于接踵而来的战争,当时的影响就不大,今天更是难以再见”(爱克尔曼,2000:2)。周学普(1937:121)将我们所熟悉的那句歌德于1827年1月31日有关世界文学的谈话翻译为“国民文学在现今没有多大意义,现今正是世界文学的时期了,人人现在都不可不有所作为而提早这个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张隆溪,2020:57),朱光潜的学问和翻译惠泽无数学人。由《译文》杂志更名而来的《世界文学》在1959年7月刊发了朱光潜译《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录》。此译文包含两人1823年的谈话1篇、1827年的谈话2篇,有关世界文学的谈话当然在其中。在译后记里朱光潜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歌德在这里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需要,并且号召人设法促使‘世界文学’早一点来临。读者最好拿这番话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所说的话比较一下,便可以看出歌德是望得很远的。《谈话录》过去有节译本,早已绝版”(爱克曼,1959:124)。但他未注明前译者的名字。1978年朱光潜选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在大陆是通行本。在世界文学问题上该译本与20年前的译文有两处不同:(1)朱光潜在译注中已经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强调歌德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早20年”提出;(2)如果说之前他是赞扬歌德的远见,现在则是批判歌德以“唯心的普遍人性论”为基点,同时肯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经济和世界市场”为出发点(爱克曼,1997:113)。不久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的地位慢慢确立。蒋卫杰(1987:22)写道:“‘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文艺学中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最早是由歌德提出来的。”孟庆枢(1988:55)同样认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用语最早是由歌德使用的。”而作者的参考书目便是朱译本。同年任一鸣(1988:88)译出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话语,在译序里说:“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丰富了比较文学学科。”我们可以认为,自朱译本以来中国学界基本上默认歌德的世界文学专利权。
即使在新世纪,治英美文学、文论的比较文学学者大都赞同歌德的首创之功。各类比较文学教材都把歌德当作提出“世界文学”术语的鼻祖。这种看法必然源自朱光潜,当然也受英美流风的影响(郑振铎是重要的先导)。而当下治德国文学、文论的比较文学学者总算通过值得肯定的努力于 2014起以可见的实绩冲击着我们的现有认知,如贺骥、方维规、刘丽、卢铭君、张珂等。其中贺骥对魏茨和沙莫尼在“世界文学”词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阐释、翻译,是我们后文论述的关键参考资料。其余四位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都以不少篇幅论及施略策和维兰德对“世界文学”的使用,但总体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歌德的世界文学观,这一点倒与英美学界相似。
综合以上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对“世界文学”术语的传播简况来看,只有将来自不同语种的文献和成果综合起来才能拼出一幅完整的图谱。这充分说明世界文学研究是一项诸语种长期协作的事业。当然这也使世界文学现象变得愈加复杂。
三、谁是首创者?维兰德和施略策的争议
前文对“世界文学”歌德专利之说的历史回顾表明,不管是英语学者还是汉语学者对德语文化圈在“世界文学”词源层面的前沿追踪都会基于学术惯性、个人的兴趣和偏好以及现实环境所给予的条件。这完全无可非议,它也不是一个单纯学术限度内的问题,有一个无疑的基本前提是平等主义。如果德国学者主动与国外学界交流新发现则会体现出一种最低限度的世界主义,单向度的输入与输出都违背了这种精神的真义。德国国内对“世界文学”歌德专利论的塑造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密不可分。然而,当新的词源文献材料被陆续挖掘出来以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文学”一词在德语语境中所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来源于作家们所处的宏观历史语境,也深深地植根于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审美趣味选择。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文学的他律和自律之间的悖论以及文学工具论与评价机制对“世界文学”术语首创权认定的影响。
1987年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魏茨(Hans-Joachim Weitz,1904-2001)发表的《维兰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Weltliteratur”zurest bei Wieland)算是公认的第一篇对“世界文学”一词的词源提出异议的文章。但它不是一篇按照严格意义上的词源学考证模式写作的论文,因为魏茨并非事先作好预设,再找材料来佐证,而是他长期从事歌德研究所获得的一种偶然的、附带的收获。魏茨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著名戏剧家,另一个是歌德研究专家和歌德作品的编辑者,如《浮士德》、《西东合集》、《歌德论德国人》、《亲和力》以及歌德同玛丽安娜·封·维勒美尔和约翰·雅各布·维勒美尔的通信等。魏茨那篇短文仅有薄薄的三页纸,描述了维兰德那份载有“世界文学”一词手稿的流传、发现过程以及维兰德本人对“世界文学”的使用情况。
1946年达姆施塔特的作家兼记者赫伯特·内特博士(Herbert Nette)从一老妇手中购得几本老书,内有一卷是 1790年出版的维兰德译的贺拉斯晚期书信体诗歌《书信集》(Epistulae)。在《书信集》的译文前有维兰德1782年写给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维兰德是其子的教师)的印刷花体字献词。献词中有几处修改,Weltliteratur便属于增添之词。经内特的朋友古典语文学家、《阿卡迪亚》杂志创办人吕迪格尔(Horst Rüdiger)和书目学家、图书馆学家埃佩斯海姆(Hans Eppelsheimer)的鉴定,确证是维兰德的笔迹。内特本打算公布这个发现而未果,以致让维兰德手稿在达姆施塔特尘封了40年之久。1986年从内特处购得维译《书信集》样书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决定授权魏茨发布维兰德的手稿。档案馆馆长还嘱托魏茨对兹事撰文记之(贺骥,2014:177)。由于魏茨的短文意在勾勒手稿的前世今生,他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也许正是因为魏茨没有结合维兰德的著作进行必要的阐发以及维兰德在德国一度遭到的冷遇致使后来的研究者们往往轻视他的世界文学观的价值。而魏茨那个富有冲击力的标题足以动摇人们对世界文学歌德造的坚执。维兰德的世界文学仅有文献意义吗?否也。如果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是指向未来的设想,维兰德的世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指向过去/古代的事实,这为当下思考世界文学的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维度。
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一生集合了文学家、批评家、古典学家、翻译家、哲学家和出版家等多重身份。他是德国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占据着重要位置(Richter,2005:22-23),被称为“他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沉思最多的德国诗人之一”(利茨玛,2010:80)。而维兰德主编的《德意志信使》(Der Teutsche Merkur)是18世纪最有名的杂志之一(Beutin et al.,1994:138)。有意思的是维兰德的小说《金镜》(1772,1794)却“接受并化用”了《赵氏孤儿》的题材和体裁(邓深,2016:140)。维兰德的长篇小说《阿迦通的故事》(1766-1767)是德国第一部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它的主题和带哲学味的文风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路青德》、托马斯·曼的《魔山》、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那里得到延续(史腊斐,2013:97-99)。席勒、克莱斯特等也受到维兰德不小的影响。但维兰德的道德观念、民族情感和审美趣味常常与时代潮流错位,所以受到克洛卜施托克及其追随者和尼采等人的指责、攻击。按照范大灿(2006:195)的看法,“维兰德关注的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不太关心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特有精神,严格地说,他不是个爱国主义者,而是个世界主义者”。因此,“即使在他的最后时刻,这位诗人仍然在证明,启蒙运动的追求与世界公民之理想其实殊途同归”(克罗登,2010:422)。尽管遭到尖锐的批评,维兰德的世界主义使其免遭如尼采一般被纳粹主义滥用的厄运。对于维兰德钟情于古希腊、古罗马名家,师法英国、法国作家的创作行为和理念,德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海因茨·史腊斐(Heinz Schlaffer)(2013:97-99)的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视角:“渴望远离同胞是德国人的优良传统,托马斯·曼将这种现象称为‘德国人的自我厌恶’。……与之相适应的是,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崇拜让人诧异:17世纪他们热衷于效仿古罗马人和法国人,18世纪轮到古希腊文明和英国文化在德国大行其道——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德意志文化遥不可及的榜样。出于到异文化中寻找归宿的古怪愿望,在1800年前后,德意志人成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献,研究怎样理解外语文本的诠释学成了一门学问。(到了19和20世纪,德国人又将自我浪漫化,沉迷于种种神化本民族的论调思潮,于是即便在自己国家里,也觉得生活在别处了。)”由此看来,德意志人学习外国(包括东方)的文学、文化在启蒙运动时期是相当普遍的风气,维兰德既是见证者之一,也是重要的推动者、塑造者之一。毋庸讳言,作为后学和同道的歌德也共享了上述文化背景。
魏茨(Weitz,1987:206)认为,从构词来讲,“世界文学”一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维兰德首创。“世界文学”这个新词在维兰德的那份手稿与著作里仅仅出现过一次,因为无法确定手写批注体的具体日期,权宜之计是将时间区间划在 1790-1813年。维兰德比歌德先使用“世界文学”一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想从维兰德的那份手稿里获知他对世界文学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魏茨(ibid.:207)将维兰德手稿里有关世界文学的文字整理为:und diese 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ßu. Weltliteratur so wie von reifer Charakterbildung u. Wohlbetragen, die man aus dem Lesen der besten Schriftsteller,核心部分的中译文为:“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贺骥,2014:176)这个有点令人如坠云雾的非句子实际上是维兰德修改献词时所使用替换词的组接。这些本居于文本空白处的手写文字对应的打印稿句子是在陈述“最美好的罗马风格”的意涵。“魏茨坚称维兰德之概念已包含诗歌是人类共同财产的思想,已隐约具有歌德世界文学的核心观点,但德国学界对此持保留态度。比鲁斯、博嫩坎普、兰平等学者在论及世界文学概念史时均会简短提及维兰德,但均认为其概念与歌德之概念在具体用法和内涵上不能等量齐观。”(卢铭君,2019:28)贺骥则支持魏茨的断语,他通过综合性考察使维兰德的世界文学观不再是孤零零的几块碎片,而是变得丰满起来,这使他自己在此问题上独树一帜。他援引维兰德的《〈维兰德先生的文学作品集〉序言》(1762)、《民族文学》(1773)、《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1782)、《回答与反问》(1783)、《论宗教宽容》(1783)《世界公民共同体的秘密》(1788)、《论流芳百世》(1812)与“世界公民小说”《西诺帕的第欧根尼的遗著》(1770)、《阿布德拉市民的故事》(1774)等9篇著述作为支撑,力图重构维兰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并确定其意义。贺骥(2014:182)的结论是:“维兰德在此所说的‘世界文学’指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一流作家(贺拉斯、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等人)博览了古今各民族的文学杰作,掌握了世界文化文献,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乃是一种世界主义的高雅文学。……与赫尔德或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比,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对贺骥而言,维兰德的世界文学就是以普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文学杰作的总集。显然这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种世界文学观。无论贺骥的阐释是否有拔高之嫌,但他的方法和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从术语使用的规范性和频次来看,维兰德自然无法与歌德相比。我们也无法找到歌德沿用维兰德的确凿证据。但只要我们把世界文学本身看作一个复杂的范畴,就不应该忽视维兰德的维度。与其纠缠于维兰德与歌德有多少一致之处,不如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歌德对维兰德的心态是相当矛盾的,既有“历经检验的好感”,也有在维兰德墓前才能摆脱的重负(利茨玛,2010:12)。
如果就此判定魏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版权问题未免操之过急。因为时隔21年后从事日本和威尔士语文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沙莫尼(Wolfgang Schamoni,1941-)的《施略策 1773年首创“世界文学”概念》(“Weltliteratur”—zure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一文横空出世。沙莫尼在标题中使用“首创”(zuerst)一词既是有意模仿魏茨,向他致敬,也是对魏茨所笃定结论的颠覆。沙莫尼旗帜鲜明地以确切时间1773年标出自己的新见。从写作技巧来讲,这类标题简单明了,非常吸引眼球。沙莫尼对人们遗忘维兰德使用的“世界文学”一词的意义表示出不满。在完成对维兰德和歌德的世界文学观的简短审视后,沙莫尼(2018:3)首先强调的是“世界文学”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早歌德50多年。自此我们再也没有理由坚持“世界文学”的歌德首创权了。“世界文学”一词在施略策那里再也不是存在于险些被湮灭的手稿的边缘处,而是属于正式出版物里一个意义清晰的有关文学的完整句子。沙莫尼花了 11页篇幅从另一个维度以标准学术论文的步骤详细介绍、剖析施略策的生平和他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成因、内涵、偏见与意义。
比起维兰德,施略策还算有些幸运。2006年皮泽的《世界文学的观念》一书提及匈牙利学者贝尔奇克1967年的文章《论“世界文学”一词的发展和比较文学史的开端》(Zur Entwicklung des Begriffs ‘Weltliteratur’ und Anfänge 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经检索在该文第7页的一个注释里贝尔奇克指出,施略策1772年所著《普遍理论概要》(Vorstellung der Universaltheorie)第一次使用“世界文学”一词(Berczik,1967:7)。换言之,“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时间应该是1772年,发明者是施略策。但贝尔奇克没有列出施略策有关“世界文学”一词的原文和该词所在的页码。可能基于此皮泽半信半疑,便不自觉地轻视施略策的意义。因为皮泽(Pizer,2006:11)说即使“世界文学”的第一次出现可能早于维兰德,那它也只是存在于“一位寂寂无名的德国作家或遗失或被忘却的手稿里”。对此沙莫尼不露声色地表达了抗议,批评贝尔奇克既弄错了书名,正确的应该是《普遍史观念》(Vorstellungseiner Universal-historie,1772),又杜撰了“世界文学”一词的出处,正确的应该是 1773年出版的《冰岛文学与历史》(Isländischenfür die Literatur und Geschichte)。尽管贝尔奇克在文献材料的征引方面稍欠严谨,但正是通过他的著作皮泽才知道有个叫施略策的学者首先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英语学界也才对其有所知晓。
沙莫尼承认对施略策言论的发现权不属于自己。据他考证,早在1920年波兰华沙大学日耳曼语文学者伦姆皮基(Sigmund von Lempicki,1886-1943)的《从古代到18世纪末德语文学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wissenschaft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一书第二编的“历史学与历史研究”一章就引用过施略策《冰岛文学与历史》中有关世界文学的那句话:“中世纪的冰岛有一种独特的冰岛文学,除北欧外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它,但它和这个黑暗时代的盎格鲁-萨克逊、爱尔兰、俄罗斯、拜占庭、希伯来、阿拉伯与中国文学一样,对全部世界文学(die gesamte Weltliteratur)非常重要。”(沙莫尼,2018:14)纵览德国文化史理论,伦姆皮基对施略策的观点多有引述。作为普遍史理论的拥护者,施略策力图唤起德国人对北欧文化的兴趣。他高呼中古时代的冰岛文学(既是独特的,也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各种接触的产物)同样重要,就像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伦姆皮基反驳说冰岛学界已有衰败、陈腐、堕落倾向,施略策恐怕得作好辩护才行。伦姆皮基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世界文学’一词最早的证据”。尽管伦姆皮基的著作在1968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在哥廷根再版,但那时的德语学界似乎没有注意到伦姆皮基的引文(同上)。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歌德的世界文学权威是无可置疑的。或者究竟谁创造了“世界文学”一语彼时根本不是个问题。“世界文学”的首创权再度沉睡了整整40年,直到2008年沙莫尼的论文发表。经过贝尔奇克的误打误撞、伦姆皮基的无心插柳、沙莫尼的专题论证,“世界文学”一词首创者的桂冠毫无疑问必须从维兰德移交给施略策了。这也应该成为全球世界文学与文学研究界的公共知识。
与维兰德和歌德的身份不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略策(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①是一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种学家,哥廷根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被称为“世界史之父”。哥廷根学派拒斥传统的修辞性实用主义,而转向强调因果联系和系统编排叙述的新实用主义。施略策认为,普遍史“只是搜集、整理和叙述”历史事实(范丁梁,2019:154)。不同于英国普遍史作家的文学式书写,施略策“感到必须以一位逻辑学家和一位研究性历史学家相结合的精神状态探讨普遍史计划”,“他反思了世界上‘民族’的不同意义,民族的不同种类以及如何能研究这些民族。但这些反思并未解决世界如何安排的问题,仅仅凸显了问题的复杂性。”(梅吉尔,2016:8)在思考普遍史时施略策嘲笑不顾术语、概念的历史性沿革事实的做法。据称施略策是一个“聪慧的词汇创造者,他喜欢从古代希腊的词源词典中创造出一些新概念。他曾经在 1772 年出版的《世界通史》(Allgemeine Welt Historie)中讨论人类历史是否需要从词源学这一角度重新书写,以及历史学家是否需要关注民族、宗教、语言学的历史”(黄忠杰,2019:76)。因此,将“世界文学”首创权归还给他名正言顺。总体而言,施略策是在其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理念和框架下构想世界文学的。民族文学综合在一起形成世界文学。但这只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阶段性兴趣。
根据沙莫尼(2018:7)的分析,施略策持有的是一种复数的文学观念,即诗艺术、学识和历史的融合。这不过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观,有别于今日之狭义文学观。如果照此构想世界文学,其内容不可谓不庞大。当然这也给我们目前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文学自身的边界在变化,世界文学的边界是不是也应该随之变化?这会不会让世界文学命题愈加不容易把握?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历史地评价。沙莫尼(2018:9)认为:“施略策于1773年在哥廷根首次使用‘世界文学’一词,绝非偶然。通过与英格兰的紧密联系,哥廷根大学已成为当时最开放的世界大学。此外在18世纪70年代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读到带有‘世界’的合成词(世界公民、世界经济、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交通),现在这些合成词中的‘世界’指的是地理上的世界(地球),它迥异于前辈维兰德所说的世界。维兰德手记中的‘世界’绝不是‘此岸’意义上的世界,它指的是社交界(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这种意义上的一些词语,例如‘善于交际’或‘不谙世情’)。”通过这段话我们知道“世界文学”作为合成词在施略策时代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英国世界霸权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和哥廷根自身的世界性是孕育新思想的酵母。不可否认施略策本人的受教育经历、对世界文化、文明的广泛兴趣和他所拥有的多语种写作能力都使他具备了发明“世界文学”一词的条件,同时也区分了施略策与维兰德所指谓的世界的差异。换句话说,施略策的世界是可见的物理实体,维兰德的则是社会或精神概念,这种截然的二分未必可靠。笔者倒是认为,现代性的世界文学理念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施略策和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都包含着非平等主义的因素。前者贬损自己不了解的异族文化,后者则是精英主义取向。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沙莫尼(2018:12)说:“在今天,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市民的、精华性的‘世界文学’方案已经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而歌德提出的交流性‘世界文学’构想一直有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沙莫尼和多数人一样信赖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他究竟如何评价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世界文学概念呢?第一,施略策提出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合成性的世界文学构想”(沙莫尼,2018:12-13)。作为一位世界史专家,施略策可以循之合成一个新词。然而,该词于他似乎只是兴之所至。全部的民族文学等于全部的世界文学,这便是其朴素性所在。第二,沙莫尼(2018:14)将施略策在世界文学方面的贡献伦理化:“正直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施略策曾呼吁文学研究者应该放眼被忽视的剩余世界,考察那些实际存在的世界文学,并鼓起勇气展开‘强大的视野’,他的呼吁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那时边缘地区的文学对德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即使有著作谈到它们,也是为了展示作者的百科知识。显然施略策的呼吁未到得到多少回应。通观今日之势,行动的迫切性早已超过呼吁的姿态性。施略策以独特性为座架来推重冰岛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重要性,更符合后现代的整体思想面向。
魏茨和沙莫尼对德语词“世界文学”所作的词源学勘定一致意见是施略策和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都未曾滋养过歌德。换言之,三人各自独立地使用着“世界文学”一词。而区别作为词语的“世界文学”和作为术语的“世界文学”也成为英美学者捍卫歌德主义的一种路径。魏茨和沙莫尼的两种叙述构成了关于世界文学起源故事的相互支撑,而歌德在其中成为评判施略策和维兰德的唯一权威。这种悖论实际上折射出当下世界文学研究的一种思维定式——不是依据历史顺序,而是以逻辑为中心。有人认为:“施略策使用的术语更接近流行的世界文学观念。毕竟他关注多种文学传统的发展和民族文学的混杂性。然而,他的欧洲中心目的论取消了任何对抵达世界总体性的兴趣。”(Patten,2015:36-37)维兰德的手稿则被消解为词语,而不是概念形成的一环。如此一来,中译文章的题目添加“概念”一词是否恰当便见仁见智了。
假如又有新资料被发现,“世界文学”一词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会不会再往前推?这种追溯难道如某些学者所言是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吗?事实上,对德语词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进行词源学的追溯并非要否认歌德的贡献,相反使他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我们也不能认为魏茨和沙莫尼是小题大做。从以歌德为准绳的陷阱里跳出来,回到世界文学本身,悬隔既有成见,如其所是地显现,所有的学术史梳理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只有如此世界文学的谱系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它确实是一个最需要程序正义和现象学精神的领域。在施略策与维兰德之间,最短17年,最长40年;在维兰德和歌德之间,最短14年,最长37年,在施略策与歌德之间则是54年。这中间相隔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弥散着地缘、社会、文化氛围的最终变化。诚如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2017:1)所言:“在19世纪这个通常被人们合理地称作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世纪的时代里,各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关系便已出现: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等等。这一点并非当今历史学家在寻找‘全球化’早期踪迹时的新发现,许多19世纪的同龄人,便已将思想和行为边界的扩展看作他们所处时代特有的一种标记。”如果从施略策开始算起,我们更应该看到其中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这种连续性不是朝向以歌德为目标的进化,而是像所有的历史一样呈现出不稳定性、偶然性。而将维兰德放置在中间,历史的绵延才得以衔接。总之,对事实的描述和价值判断不能相互替代。
综上所述,在世界文学的谱系图上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家在处理同一概念时的差异,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世界文学起源的复杂性、丰富性。可以说这种多样性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西方学界对世界文学的不断重新定义(典型代表是卡萨诺瓦、达姆罗什和莫莱蒂)。从一个区域性概念到一个世界通用语,不同区域的学者基于各自的文学史数据调整了世界文学的时间指向性。在《世界文学的定位》一文中吉汉诺夫(2018:15)指出,如果从时间维度来确定世界文学的位置可以有三种选择:(1)“‘世界文学’(无论作为可验证的文本事实,或是作为观察和分析文学的透镜,还是作为一种学术话语)是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产物”;(2)“‘世界文学’自古已有之(可如果确实如此,又如何叙述‘古已有之’的‘世界文学’的历史?就这个问题可阅读尼古拉·康拉德和弗朗科·莫莱蒂的著作)”;(3)“视‘世界文学’为前现代现象,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民族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学’已是风中残烛(参阅波斯奈特、米哈伊巴比茨的著作,也可参阅安塔尔谢尔勃的著作)。”第一种在目前具有普世性。第二种和第三种是否能在维兰德那里找到部分证据,这实质上涉及世界文学的历史界限问题。对吉汉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世界文学应该是自我反思性的。“世界文学”的首创权之论并不止于文献学意义。至少在21世纪的世界文学理论之中我们能找到与施略策和维兰德所指相类似的点。前者扩大了世界文学的地理空间范围,后者拓展了世界文学的历史长度,这些正是不少当代模型的取向。可以说施略策和维兰德的世界文学言说迥异于歌德的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模型。毫无疑问,不管是从有关话语的丰富程度还是从影响来看,歌德乃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起点。
注释:
① August Ludwig Schlözer的中译名有史略茨尔、施勒策尔、施吕策尔、施洛策、施洛策尔、施洛采、施洛塞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