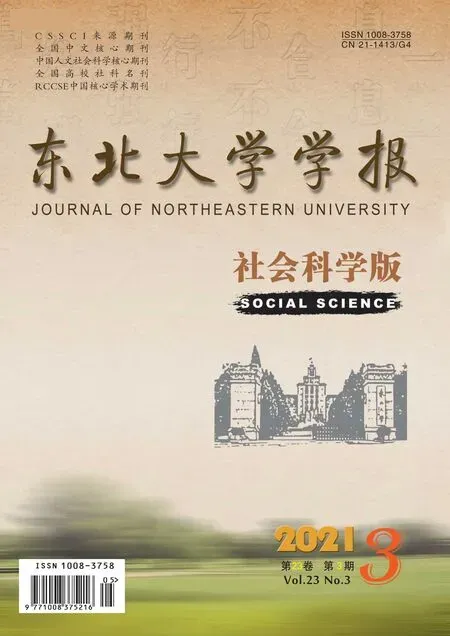整体评价视角下量的防卫过当的理论建构
赵 宗 涛
(东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发生的“昆山反杀案”“涞源反杀案”等争议案件引起了法律共同体的热切关注,“避免正当防卫的规定沦为僵尸条款”无疑已成为当下共识。在理论上,“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的可行路径有两种:一是扩张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为正当防卫权的行使创造更大的合法空间;二是拓展防卫过当的适用边界,即将值得宽恕处罚的情形尽可能认定为防卫过当。然而,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只专注于前一议题的研究,对后一议题则鲜有关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正当防卫制度价值的全面发掘。其中,是否承认量的防卫过当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
量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时间界限的情形,如防卫人将侵害人打倒在地后又继续实施拳打脚踢(1)从理论上讲,量的防卫过当包括事前防卫过当和事后防卫过当两种情形。但是,事前防卫情形从未真正产生过正当防卫权,不存在由“正当”变为“过当”的过程,所以应排除在防卫过当的范畴之外。。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法》第20条第2款只规定了质的防卫过当一种类型(即防卫手段超过必要的防卫强度的情形),至于量的防卫过当情形,应归属于防卫不适时,按照普通的故意或者过失犯罪处理。这种见解在理论界似乎已成公论。然而,司法实务中却不乏认可量的过当情形构成防卫过当的案例。
例1 龚少荣故意伤害案(2)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2017)桂0122刑初80号刑事判决书。。韦某1和龚少荣素有矛盾,某天韦某1酒后到龚少荣家滋事,被他人劝解。当龚少荣走回自己房间时,韦某1紧跟着进入房间并挑衅龚少荣,后者持刀挥舞予以警告。但韦某1仍上前将龚少荣压倒在床上掐其脖子,龚少荣遂拿起一把匕首刺中韦某1右背,随后又连续朝其左胸部捅刺了两刀,致其死亡。经查,韦某1被捅第一刀后已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和可能性。
例2 王某甲故意伤害案(3)参见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8)晋1182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2018年2月9日,王某甲和李某乙在家中发生口角。李某乙拽住王某甲的头发对其实施殴打,并用手机砸打王某甲,王某甲则拽住李某乙的腿将其推倒。李某乙拿出一把菜刀要砍王某甲,王某甲骑坐在李某乙身上,用手摁住其双手将菜刀夺下,并用手扇李某乙脸部。随后又用菜刀砍击李某乙头部、肢体,致其全身三十三处受伤。最终,李某乙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院认定,王某甲夺下菜刀时实际已经制止住了不法侵害。
以上案例中均存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事实,但法院并没有依照传统观点将此类情形当作普通犯罪处理,而是对防卫人适用了《刑法》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规定。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裁判,“恐怕主要还是考虑到了事情的起因是出于防卫,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亢奋、愤怒等可以理解的因素的存在”[1]。将具有这些可谅解事由的情形归结为量的防卫过当,将使防卫人获得法定减免处罚的宽恕,符合当前向防卫人倾斜的刑事政策。
其实,即便承认存在量的防卫过当类型,也并非将所有侵害终止后的反击情形都作为防卫过当处理。例如,当侵害人明显丧失侵害能力或者已经放弃侵害行为时,防卫人另起犯意实施积极加害的,此时事后行为与先前防卫之间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就不得评价为防卫过当。换言之,唯有在不法侵害结束前后的反击行为具有连续性的情况下,才考虑有无成立量的防卫过当的可能。实务中构成量的防卫过当的判例,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探究对超过正当防卫时间界限的情形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减免处罚规定的可行性,从而为拓展该条款的适用边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量的防卫过当否定论观点之反思
传统刑法理论不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类型的理由有多种,但根本性的否定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认为我国刑法规定只涉及质的防卫过当一种类型;二是认为事后防卫场合缺少正当防卫的前提,即“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两种理由表现出强烈的形式化的思维定式,抹煞了量的防卫过当的成立空间。此外,在坚持传统立场的前提下扩张防卫时间界限的做法,实则间接肯定了量的防卫过当的存在意义。
1. 片面解释防卫限度
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时间要件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在具备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限度要件的问题。“把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和限度要件混为一谈,并且把正当防卫是否超越防卫的时限作为考察其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因素之一,是不能赞同的。”[2]论者将时间要件仅仅限定为前提条件,而把限度条件局限于防卫手段的强度,就很容易得出刑法中只存在质的防卫过当一种类型的结论。然而,这种普遍理解其实是一种片面认识,以此否定量的防卫过当不具有信服力。
实际上,防卫时间具有作为前提条件和界限条件的双重地位。当其作为前提条件时,如果起初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实施防卫,则根本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然而,当侵害过程和防卫过程具有持续性时,就意味着在侵害“正在进行”这段时间范围内的反击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超过该时间界限的情形原则上不再是正当防卫了(4)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意义上的防卫限度应指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而手段强度和时间界限只是关于行为限度的分类。根据法条规定,只有行为过限+结果过限时才构成防卫过当。所以,即使防卫行为超过了时间界限,也不必然构成防卫过当,而是可能成立正当防卫。这是由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定决定的。。此种意义上的防卫时间则是作为界限条件存在的。在不违反《刑法》第20条第2款规范要求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将时间过限情形排除在防卫过当的范畴之外。其一,从规范文义来看,“必要限度”主要指行为限度,其内涵并不限于防卫手段的强度一种情形,将防卫时间的界限归入到“必要限度”的语义范围之内,在文理解释上不存在障碍。“因为从语言上讲,也是可以从时间的角度逾越这些界限的,而且当时也是一度以某种方式存在紧急防卫的情势的,紧急防卫的行为只是推迟出现了而已。”[3]其二,就规范实质而言,防卫过当应指防卫人在拥有正当防卫权的情况下,实施了逾越合法行使界限的防卫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的情形。在先前存在紧迫不法侵害的背景下,实施了僭越“正在进行”的时间界限的防卫反击,当然也属于逾越防卫权合法行使界限的情形。
2. 机械分割防卫行为
传统理论习惯于完全切断事后行为与先前防卫之间的联系,单独考察事后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而一旦单独评价事后行为,则必然会因为缺少“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一前提条件而得出否定结论。这种分割评价防卫行为的思维,某种程度上也与对正当防卫限度要件的片面理解相呼应。可以说,传统观点否定量的防卫过当,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分场合地对数个防卫行为实行分割评价。亦即,“只要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防卫人此后的行为就不再是防卫行为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犯罪行为”[4]。
然而,在现实紧迫的侵害态势之下,防卫人实施的一连串反击行为通常并非像“固体”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而是从一开始就如“液体”般流动发展的。即使其冲破了正当防卫时间界限的大闸,也无法消解各防卫行为之间自然的防卫关联性,更不能完全否认行为人主观上继续防卫的意思。例如,案例1“龚少荣故意伤害案”中,公诉机关提出,防卫人捅刺的三刀中,第一刀是防卫行为,后两刀不是防卫行为。法院却认为,连续的三刀时间间隔很短,整个行为过程时间也很短,应属于防卫人实施的一系列连续的防卫行为,而不应简单机械地分割评价。法院正是考虑到数个反击是连贯实施的,只抽取出后两刀行为进行单独评价的话,会显得极不自然,故而肯定了事后行为的防卫性质。又如,“涞源反杀案”中,检察机关提出,“王新元、赵印芝当时不能确定王磊是否已被制伏,担心其再次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又继续用菜刀、木棍击打王磊,与之前的防卫行为有紧密连续性,属于一体化的防卫行为”(5)参见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王新元、赵印芝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检方通报(2019.3.3)。。虽然防卫人在侵害结束后继续反击,但二人主观上仍具有防卫侵害的意思。正是因为防卫意思贯穿于整个防卫过程,检察机关才将其界定为一体化防卫行为。倘若强行分开考察,反而会割裂防卫过程的整体性。更何况,防卫侵害的意思和憎恨、激愤、恐惧等心理状态也不冲突,二者完全可以并存于一个防卫过程之中[5]。总之,机械的“唯时点论”的做法会无视各反击行为的客观联系,也会忽略防卫人主观防卫心理的连续性,并不可取。
3. 扩张时间界限的局限性
传统观点名义上维持着否定量的防卫过当的立场,但在处理个案时却可能通过宽松把握时间要件的方式,变相认可量的防卫过当的结论。例如,“金某故意伤害案”(6)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刑初字第371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提出,“不能仅凭侵害人停止侵害行为作为衡量侵害状态已终止的唯一标准,防卫人切实相信威胁已解除、自身确已安全的认知也应作为考量的标准”,即只有防卫人主观确信绝对安全才能认定侵害已经结束。本案中,法院考虑到防卫人在被长时间持续殴打之后精神高度紧张,即便实施短暂追击也是情有可原,而完全作为普通犯罪处理则会使其承受过重的刑罚。基于这种裁判动机,法院变通地将防卫人主观认识情况作为判断不法侵害是否结束的考察因素,实质地扩张了“正在进行”的时间界限,从而变“事后行为”为“事中行为”,将案件归入到质的防卫过当范畴处理。这种变通做法与承认量的防卫过当在结论上并无本质差别,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处理方式而已。倘若把“正在进行”扩张解释为防卫人主观上认为危险尚未排除,就十分接近于承认量的防卫过当了[6]661。
但是,这种解释技术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怎样界定“正在进行”的时间范围,都不得违背客观性判断的基本原则。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针对的是外部事实情况,且采用的是一般人标准,不论判断对象还是判断标准都表明其是一种客观活动。“将防卫人主观上合理地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融入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的判断所需要考量的问题范围,实际上是将不法侵害的结束所需要进行的客观判断与防卫人的主观判断相混同的结果。”[7]而在客观判断的界限内,实际可变通处理的空间又十分有限。因为认可量的防卫过当,主要是考虑到防卫人主观方面存在值得宽恕的事由。如果坚持对防卫时间要件的客观判断,则防卫人获得减免处罚的机会明显较少。与其如此,不如坦率地承认量的防卫过当,这样既有利于保持防卫时间判断的客观性,也可以应对更多的个案处罚困境,避免出现明显不利于防卫人的处罚后果。
综上来看,至少在规范层面,不能完全排斥量的防卫过当类型。对于防卫人实施了一连串反击行为的情形,也不能简单地分割评价事后行为和先前防卫,而要充分考虑防卫人主客观方面的联系,注重从经验上把握作为防卫过当评价对象的“防卫行为”的范围,从而将之与普通犯罪作出区别处理。
三、整体评价方法与量的防卫过当的证立
在急迫不法侵害消失以后继续实施反击的场合,是否要将各个部分的行为分开考察,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都会成为争议问题。考虑到一律分开评价侵害结束前和结束后的反击行为的传统做法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对防卫行为实行整体评价。由于整体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具备了成立防卫过当所需的前提要件。又由于“必要限度”的内涵包括了时间界限情形,故而存在构成量的防卫过当的可能性。
1. 防卫行为的整体评价方法
整体评价防卫行为是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的基本前提。有观点认为,整体认定防卫过当是将事后防卫的后果归咎于先前的正当防卫行为,此种逆向评价会使先前的正当防卫被追溯为违法,违反了罪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8]。这种批评有待商榷。论者显然采用的是评价结果“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即事先已得出不成立量的防卫过当的结论然后再寻求整体评价的方法肯定量的防卫过当。然而,如果将目光首先放置在界定作为评价对象的“防卫行为”之上,判断数个反击行为是作为一个行为整体还是数个行为把握,而后再考虑是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话,就不会得出“溯及违法”的结论。
笔者认为,在正当防卫的场合中,对复数防卫行为实行整体评价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确定评价对象的工作应当是在行为论阶段而非犯罪论阶段完成的任务。在刑法中,行为是法规范的评价客体,而违法或者合法则是法规范评价的结果。因此,讨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如果一开始不能确定行为的外延,就无法展开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评价。“行为论的任务主要是将值得纳入刑法评价范围的行为从案件事实中选取出来作为犯罪论的判断对象……当被选取的行为数量为复数时,还必须进而考察应当将其作分断处理还是统合处理。”[9]“行为个数的判断,是确定作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对象的工作,它不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本身,而是其前提”[10],故应在行为论阶段加以解决。当防卫人实施一连串的反击行为时,同样也要经过行为论阶段行为个数的整合,才能有效确定待评价的行为对象“防卫行为”的范围。
其次,行为者的主观意思内容赋予行为意义,行为的范围也主要是由行为意思的范围所决定[11]。当数个行为是出于一个行为意思而实施的,原则上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行为看待。例如,在同一场合基于伤害对方身体的意思连续实施数次击打行为,应当视作一个整体的故意伤害行为。如果切换到正当防卫情境,则基于同一防卫侵害的行为意思而实施的一连串防卫反击行为,也应作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把握。更具体地分析,通过整体评价方法确定的一体化的防卫行为,其实属于行为论中自然的行为单数类型。根据自然的行为单数概念,确定复数行为的“一体性”关系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素:①具有时间、空间上的直接联系;②是基于单一的动机实施;③表现为单一的事实发生(具有一个特定的目标);④引发的是构成要件性损害的量的增加[12]。在前述“王某甲故意伤害案”中,法院的裁判理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对比样本。“基于一个行为意志发动的防卫行为,在不法侵害结束后短暂时间内出于愤怒等原因实施的持续性、连续性防卫行为,可以评价为一体化防卫行为。”防卫行为的时空连续性、防卫侵害的行为意思自不必言,单一的事实体现在针对侵害人实施反击的事实,而损害的量的增加则正是指因防卫过当造成损害的后果,二者的对应性十分明显。可见,将整体评价方法定位在行为论阶段的看法,是具有合理性的。
最后,对防卫行为实行整体评价,也是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的要求。不法侵害人违反团结义务,主动使自己陷入法益冲突的状态,那么法律对其施加保护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由于不法侵害是引发并支配整个因果过程的肇因,所以侵害人不仅要对先前的正当防卫行为负责,还要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防卫人过度反应负责。只要防卫人实施的一连串反击行为不是特别异常,处在一般人预见可能性范围之内,就应将损害结果归于不法侵害人承担[13]。换言之,如果能肯定因为先前侵害而形成的紧迫状态使防卫人“处于对方说不定还会再次攻击这种不安之中,从而实施了追击行为的”[14],也应考虑将一连串反击行为当作一个整体的防卫行为把握。即使防卫人明确认识到侵害已经结束仍继续反击,只要基于真实的防卫动机实施的后续行为不是太过分,也不妨碍对防卫行为的整体评价。
至于整体评价防卫行为的考量因素,结合前述案例及自然的行为单数的构成要素,可以归纳为三点:防卫意思的同一性、防卫行为的紧密性和防卫行为的同态性。具体展开分析:①防卫意思的同一性,即数个反击行为是基于连续的防卫意思实施的。防卫意思是连接前后两阶段行为的纽带,也是前后阶段法律效果合并评价的前提。但这里的防卫意思并非严格意义上作为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防卫认识与防卫目的的总和,而是更侧重于单向的防卫目的(或动机)。倘若行为人在防卫过程中由防卫意思转化为攻击意思,则不得对防卫行为实行整体评价。②防卫行为的紧密性,即各反击行为之间具有时间、空间上的紧密性。该要素旨在表明,行为人是由于防卫势头过猛或者趁着防卫余势才实施的继续反击的,可以将事后行为评价为先前行为的自然延续[15]。反之,应认定侵害结束前后的防卫行为存在断绝关系,不得评价为一个整体行为。③防卫行为的同态性,即全部行为都指向同种法益,且各行为之间激烈程度不能过于悬殊。对于前者,如果数个行为指向的法益种类有别,则不能被同一个构成要件包容评价;对于后者,激烈程度明显不同的后续反击难以视为先前防卫的自然延续。
2. 量的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
考虑到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实行“必减主义”,除要求量的防卫过当具备前述的形式合法性外,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其具有实质合理性,即满足防卫过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根据。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乃是该场合中防卫人具有可予刑罚宽恕的正当事由。倘若从犯罪的本质是违法和责任的判断角度展开分析,则量的防卫过当中防卫人存在违法减少和责任减少的双重宽恕事由。
第一,违法减少。原本说来,分割评价防卫行为时单独的事后反击没有违法减少的机会。但是,当不法侵害结束前和结束后实施的数个反击行为被包容评价为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时,完全能够承认存在违法的减少。违法减少包括行为违法减少和结果违法减少两个侧面。具体而言,行为人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保全合法正当的利益而实施反击,具备了正当防卫的前提。从着手防卫到结束防卫这一时段内实施的所有反击行为,有部分行为处在防卫的必要限度以内,该部分行为及其造成的法益损害后果都是正当的,阻却了行为和结果的违法性。但是,不法侵害消失意味着正当防卫的前提不再存续,变成了行为人不得合法地干扰侵害人的法益[16]。侵害结束后实施的反击及造成的重大损害也就具有了违法性。这种部分违法的犯罪结构,在违法量上比完全的犯罪更低,所以,肯定量的防卫过当具备违法减少是合适的。
第二,责任减少。否定量的防卫过当的观点,最容易忽视防卫人责任层面的可宽恕性。量的防卫过当的责任减少,可以从防卫意思连续和期待可能性降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①防卫意思连续。防卫人面临急迫不法侵害时,只要是以一次应对不法侵害、保护合法利益的行为决意而实施一连串反击的,就能够基于存在连续的防卫不法侵害的意思这一事由,肯定存在责任的减少。②期待可能性降低。在正当防卫的情境中,不法侵害的持续作用力会对防卫人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形成无形压迫,影响其对真实危险程度的准确辨认,还可能造成其自我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所以,“在高度紧张、恐惧或亢奋的状态之下,要求受到不法侵害者明确地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以确定是否可以继续自己的反击行为也属强人所难”[17]。当然,并非任何案件中都必然存在防卫人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例如,在为第三人利益实施防卫的场合),所以,根本性的责任减少事由不在于期待可能性降低,而是防卫人具有连续的防卫意思。
此外,从刑罚目的角度分析,给予防卫人减免处罚的优待也符合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量的防卫过当情形中,防卫人出现过激反应可谓事出有因,其通常不存在明显违反法规范的意思,特殊预防必要性较低。而且,防卫人的行为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原谅,减轻或者免除其刑罚也不会起到鼓励他人效仿的作用,其一般预防必要性同样较低[6]656。
四、正当防卫与量的防卫过当的界限
我国学界通常认为,《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防卫过当,包括行为过当和结果过当两个方面。成立防卫过当不仅要求防卫行为本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且要求不必要的防卫行为确实引起了重大损害结果[18]。照此分析,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尽管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的时间界限,但尚未达到过当程度的,事实上不构成量的防卫过当,而只能认定成立正当防卫(下文具体分析)。就这一点而言,我国与同样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类型的日本刑法存在显著差别。日本《刑法典》第36条第2款规定,“超过防卫限度的行为,依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刑”。该条规定并不像我国刑法一样要求只有不必要的行为造成重大损害后果才能成立防卫过当,亦即,只要防卫行为超过时间界限就可以成立量的防卫过当。况且,日本刑法还规定了暴行罪,更意味着无重大损害后果亦可构成犯罪[4]。防卫过当法条规定的差别对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的意义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日本刑法中,虽说认定为量的防卫过当会比定性为普通犯罪更有利于防卫人,但犯罪的成立范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所以量的防卫过当至多只是发挥了“拓展防卫过当的适用边界”一层功效。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的规范设计却额外发挥了“扩张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的功效。我国刑法承认量的防卫过当,可以更大限度地激活正当防卫规定的适用,比起日本刑法承认量的防卫过当意义更大。
在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时,需要注意两点事项。一是只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防卫时间界限时,才有讨论量的防卫过当的必要。除此以外的情形,都不应考虑认定存在行为过当。二是只有当出现“重大损害”结果时,才可能认定结果过当,成立量的防卫过当。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造成轻伤及以下损害的,不属于重大损害”(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具体案件中防卫行为只是轻微超过时间界限且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情形,没有给予刑罚处罚的必要性,不必考虑是否成立量的防卫过当。
鉴于此,本文根据损害的轻重程度,将是否构成量的防卫过当的情形区分成三种:①不法侵害结束前的反击处于正当防卫限度之内,而侵害结束后的反击造成了重大损害后果的,应成立量的防卫过当。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防卫过当的成立要件,应无疑义。②不法侵害结束前的反击处于正当防卫限度之内,而侵害结束后的反击仅仅造成一般损害的,尽管这种损害是不必要的,但由于不能将之归入“重大损害”范畴,所以不成立量的防卫过当,否则会违反法条规定(8)1979年《刑法》第17条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按照该规定,上述情形无疑构成量的防卫过当,但现行《刑法》对此作出了修改,故无法径直得出肯定结论。。但严格说来,这种情形似乎也不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超过正当防卫的时间界限原则上就不再符合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了。对此,尹子文提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防卫时间的超越仅仅具有概念上的意义,不是真正的防卫过当[19]。本文赞同此种观点,认为该情况应认定为正当防卫。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具有防卫性质的行为如果不成立正当防卫就构成防卫过当,反过来,如果不成立防卫过当也应视为正当防卫,如此才能避免在两者之间形成处罚空隙。既然第20条第2款明文规定只有行为和结果双重过限时才构成防卫过当,则仅仅是超过时间限度(行为过限)而未造成重大损害的,就只能解释为正当防卫。将超过时间界限等同于超过防卫限度进而等同于防卫过当,乃是一种惯性思维,不符合现行《刑法》第20条的规定。③不法侵害结束前的反击处于正当防卫限度之内,而侵害结束后的反击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难以准确查明的,根据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得认定为量的防卫过当,只能成立正当防卫[4]。此外,现实中可能会出现质的防卫过当和量的防卫过当并存的情形,一般统合评价为质的防卫过当即可,不必严格当作两种防卫过当类型分别处理。
总之,对于一体化的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或者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认定构成正当防卫,有利于扩大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即使构成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防卫人也可以享受到减免处罚的优待,这又拓展了防卫过当的适用边界。
五、 结 语
我国刑法传统观点不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类型,实际上限制了对《刑法》第20条第2款规范意义的全面发掘。笔者提出,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只要是出于连续防卫意思实施的一体化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防卫时间界限而造成重大损害的,就构成量的防卫过当,应给予防卫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优待。在正当防卫制度中,个人保护原则是正当防卫的基本原则,其功能在于对正当防卫进行扩张[20]。承认量的防卫过当不仅是对优先保护防卫人利益的个人保护原则的重申,它同时也突出了“法不得向不法让步”的秩序理念。在我国刑法语境中承认量的防卫过当,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妥当且务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