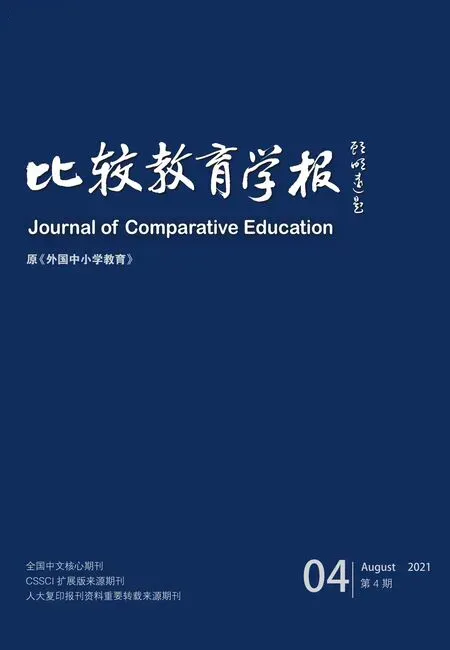国际与比较视野中的教师发展
——卢乃桂教授专访
卢 乃 桂 曾 艳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聘资深讲座教授卢乃桂先生是国际教师教育领域极富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创院院长、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讲座教授、研究院教育学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优质学校改进计划总监等职。曾获邀参与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美国)、Teachers College Record(美国)、Teachers and Teaching(英国)、《教育研究》(中国)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的编辑与发展工作。卢教授在美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具有丰富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经验,擅长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学术视角审视教师教育问题。2020年12月,卢教授应本刊之邀接受了此次专访。
一、新冠疫情与教师工作
曾:卢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就您的观察,当下全球范围的疫情给教师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教师专业性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呢?
卢:我觉得要谈疫情对教师的影响,需要先谈一谈疫情对教育系统方方面面的影响。疫情对于教育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觉得可以从社会、经济、教育三方面来看。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贫富差异进一步加剧,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带来的卫生需求、教育需求的经济能力不同,越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带来的伤害越大。最近我看到一份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有40%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将要削减他们的教育经费,50%中低收入的国家连提供基本的保护物资,比如洗手液、社交距离,都是没钱去做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有30%的国家根本照顾不到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在这些国家里面,只有40%的老师报告说在停课的时候整理装备、去做好分内的事。有钱的国家里面,有40%是能提供心理辅导的。其他的不用想,在富国里面的穷人也不需要想,他们需要靠社会福利、靠社工来支持学习。很惊人的就是上千万的学生连基本学习都没有,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上网工具,在富国里面,千万计的学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①UNESCO, UNICEF, & WORLD BANK. What have we learnt? Overview of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on national responses to COVID-19 [EB/OL]. [2021-03-31]. http://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702.这个是经济的方面。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性越来越强。疫情带来的隔离导致社会交往断裂,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情绪失控。最近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出来一个惊人的数据,疫情期间医院急诊中因为情绪失控的儿童数量急剧增加:5到10岁的孩子情绪失控率增加了24%,12到17岁的增加了37%。这都是怎么来的呢?人是一个社会动物,疫情带来的隔离导致他们的社会交往断了或减少很多了,所以孩子挺不习惯,有一些甚至自杀自残。在受教育者这个群体里面,年轻人受到的伤害是很清楚的。这是疫情在社会方面带来的严重影响。
第三,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就是学生学习机会丧失。全球学生失去的学习机会是多少呢?从疫情出现到现在12月这9个月中,②本次访谈时间为2020年12月,本文中所说的“今年”均指2020年。UNESCO所统计出来的就是总的学习时间少了4个月。在OECD这样一些发达国家中,少了7到19周的在校学习时间。疫情越严重停课越多。开始的时候是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其中也包括放假,在北半球的国家要放暑假),加起来7到19周是没有学校教育的,这是OECD的统计。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数据,Kuhfeld等人在Educational Researcher(《教育研究者》,AERA刊物)最近一期作了一个统计,评估疫情给孩子的学习带来多大的损失。只是从阅读和数学两科来看,他们发现阅读损失率大概是32%到37%左右;数学更严重了,大概是50%到70%多。①Kuhfeld M., Soland J., Tarasawa B., et al.. Projec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49(8): 549-565.这就是与损失了好几个月的学习时间直接有关的。
那么教师怎么样呢?这就谈到了疫情对教师的影响。疫情让在线教学成为非常迫切的事情。对教师来说,在线教学是全新的教学情境和教学要求。如果一个老师还想着拿着课本来教完这一课,然后给学生功课,希望他们能交功课回来,你去批改作业然后给他们回馈,已经行不通了,在线学习已经不这样了。现在不是我面对一群学生,我有选择叫谁起来回答问题,我能让他们在情感上有所感受。在线教学中,所有传统的方法、教师已经熟悉的方法都用不出来了。所以教师要考虑怎么去调整甚至设计课程适应在线教学的情境,在在线学习的情境下怎么去教,怎么去与学生保持社会和情感联系,怎么去引导学生学习等等。
此外,疫情带来了新的工作情境,要求教师及时调适多种角色。现在老师也在家在线工作,他们家里面有自己的孩子,同时要扮演的是家长和老师的角色,他们是有家的人,他们怎么调整这个身份呢?面对网上面的是几十个学生,在家里,自己的孩子在旁边玩,怎么去做?优先权给谁?老师在家也要督促自己的孩子上好自己的网、做好自己的功课,操心他们的老师怎么评价他们;同时老师自己也要对自己的学生做这个事。老师就要有分身之术了,这是最明显的。
其实,中国的老师碰到的问题,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也碰到了,大家都在说要想办法。我认为首先要做好Unlearning(弃常规或传统而求变)。我们整个系统可以说谁改变得快,谁就是赢家。
Unlearning是什么意思?过去我们说教师中心、学生中心,诸如此类的。但现在教师中心、学生中心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含义。学生就是电脑上面的一个格,一个老师面前有几十个格。你告诉我,你怎么把他们看成中心呢?能吗?不能说不可能,可能,但是老师要用新的心态、眼光、视野去看学生的学习。那就先要把以前的那一套都扔掉。这就是Unlearning。Unlearning是当下最重要的。当下整个教学专业中要做的就是“Undo(放弃常规或传统)”。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到Unlearning呢?这个步骤最少是两个,一个是Unlearn(放弃传统方式),一个是Learn New Things(学习新方式)。我举个例子,假定大家都有电脑,老师说你们要做功课,回去叫你的父母亲签字。这是传统的做法。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在系统里到了5点30分,在大家吃饭之前,老师跟这些学生碰一碰面呢?这怎么碰面?大家都回家了,就在ZOOM上面,花数分钟谈一谈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可能延长了老师的工作时间,但这个是可以考虑的。重要的是有一些新的做法,我们是可以利用科技来帮忙的。这只是一种建议,就是说新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好的,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去改革。我们不做吗?现在人家正在做,迫不得已地去做。在美国、英国是迫不得已地去做。
每一个教育系统跟每一个老师都必须有一种应变能力,这个应变能力包含了Unlearning。这个Unlearning不一定是要碰到在ZOOM教学才能用得上的。这个Unlearning其实是我们一种反思的过程,真的是要认真地去反省,我们有什么东西可能已经是不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哪一些是新的东西,我们真的要拿出来,万一需要用呢?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大家都想到是好东西的话,为什么不现在就用呢?
曾:您刚才讲的Unlearning,我理解也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教师也需要转换原有的角色才能迎接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您认为教师需要进行哪些角色转换以响应后疫情时代的教学要求呢?
卢:教师最基本的角色是一个Instructor(教练)。你不教,他怎么学?面对学习,教师的Instructor的身份是一定有的。教师作为一个Instructor,一定是包含多种角色的。第一个他是Designer(设计者)。在线教学里面呢,教师要重新看他们要教的东西,他们的教学计划要重新调整。他们作为设计的人,每一课的课程、教学方案都要重新去调整来适应在线教学。这个是他们突然之间增加了的身份。他们要重新设计教材、重新安排课程,在同一班学生里面对能力不同的学生怎么设计他们的学习。
另外,我们常说教师是一个Facilitator(引导者),但在疫情中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不是一个Instructor,作为一个老师你根本没资格说Facilitate(引导),你Facilitate什么?Facilitate Learning(引导学习)吧,Learning不是自动发生的,老师还是要教,老师一定首先是一个Instructor。但是,过去大家都是Person in Person Instruction(面授),有来有往的。现在的情况是:老师教,你看到学生在ZOOM低着头,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看什么,根本没有这个能量来兼顾。在缺乏面授的情况下、老师1个对N个的情况下,怎么教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Instructor的角色里面,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老师要知道学生的学习进度,这样才能教下去。现在网上教学的问题呢,容易失控和失联。失控就是你很难控制学生的注意力。失联就更可怕,失联了就是我们在ZOOM上一直看到有多少多少人,但实际上是,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多的空格(没人),老师们心里就慌了,这是失联的特征。学生根本不上网啊,他有很多理由不上网,你根本不知道他学不学。现在那个贫穷的社群里面,这种情况很普遍地出现了。
学生如果失联了,你怎么去引导他?这是另外一个角色了,引导者嘛,Facilitator,老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发挥出来。在疫情中的在线学习,教师怎么体现出引导者的角色?怎么体现给他们东西去做?虽然老师希望能帮他们,但很难,越来越难做。
最后,更重要的是Collaborator,教师作为提供社会支持的“合作者”角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这是对老师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怎么把老师跟同事之间、学生之间、家长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他们跟同事之间的联系保持下来,不让他们有社会隔离感。老师同样需要社交,让他的精神比较健康,不至于情绪失控。
曾:疫情确实对教师角色产生了诸多新要求,您认为当下的教育系统是否为教师的上述角色转换提供了充分支持呢?
卢:现在的教师没有能力去应对疫情带来的这些新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师范教育根本没有想到疫情这个情况会出现。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Support Structure(支持系统)给到老师和学生。老师只不过是这个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社工、辅导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家长,因为孩子在家的时间特别多。此外还有医护人员、清洁人员,这都是在疫情下的支持系统。
教师呢,他们既是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孩子们的学习,他们也应该有给他们的支持系统,帮他们生活工作维持下去。我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们跟同事、学生和家长的联系。失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失联会让老师碰到的问题就是Burnout(倦怠)跟困惑。
还要再强调一点,如果教师想工作得比以前更有效,使他们的生活更好,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Unlearning,重新去创造。现在大家想的都是基于以前的一些旧的、面授的方法继续做下去,但是疫情给我们一个机会再反思一下,疫情要教育界反思,要老师反思他们在教学方面有什么东西调整的,因为疫情还要再发生的,不会有了疫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会再发生。
曾:疫情确实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对教育和教师工作也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您认为教师需要特别关注哪些议题呢?
卢:首先是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社会情绪学习),包括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老师自己的时间管理、他的Delay Gratification(延迟满足)、他怎么考虑他人所需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老师要负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现在(疫情期间)要关心的是数学、阅读退步了,学生不见了,学习有所损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会学生社会情绪学习。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最清楚的就是教会他们要自爱,要他们关怀社区、关怀别人,知道他人的需要是什么;他们也需要有一些时间管理的技能,学会健康的生活。社会情绪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延迟满足怎么做。我想要喝一杯酒,但我已经喝了两杯了,我再喝可能对我的健康有影响,可能让我喝醉、开车碰伤人碰死人,导致一生遗憾,那我就先不喝,明天晚上再来,你能抵抗这个诱惑吗?
延迟满足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人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能力,有足够的Emotional Control(情绪控制力)去不做这个事。上个礼拜吧,在美国有部分州部分城市把学校关了。有人置疑,学生的学习是Essential(必须)的,你却因为疫情把学校都关了。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不想他们感染。但是酒吧却没关。对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学生学习重要还是喝酒重要呢?你不把酒吧关起来却关学校,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呢?当然是。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你把酒吧和餐厅关了,他们这些成年人跟你拼了。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美国的疫情非常惊人。回到社会情绪学习,有这个习惯呢,我觉得社会会好一点,人的生活也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教育上亟须面对的、大力推的主题,这个社会情绪学习是其中一个。
第二,教师的预见能力。教师要有一种能力,能预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每天跟着学生,不能跟学生面对面,不知道他们的学习进度,老师如何预见问题、预见学习问题,尤其是学生学习的进度,这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尤其是对中学的老师而言,如果我见不到学生,我怎么帮他在这个困境里面保持他的Perseverance(毅力)、他的抗逆力呢?我们怎么通过授课帮他保持他的毅力和抗逆力呢?如果我们自己作好准备,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狼狈。
第三,老师怎么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个很重要。像刚才说的,老师很难摆脱三重身份:作为老师、作为子女、作为家长(如果他有家庭的话)。他们的三重身份怎么好好地去处理呢?因为这些Anxiety(焦虑)、Stress(压力)加起来都会让老师很快地强化他们教学上的Burnout(倦怠)。
再者,就是如何在疫情中保障弱势学生群体的学习权益。在美国,过去两个月出现了1 600万学生没有在线学习的资源,没有iPad和Wifi,那你怎么学习?老师们怎么去预想,有什么办法?Learning Package(学习包)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呢?或者有什么办法让没有资源的学生也能学习?这是全球的问题,不只是美国、中国或者是英国的问题,这个是让人很吃惊的东西。
另外,以前学校是正式的教学场所,学生有需要的话就去外面的Tutorial School(补习机构),这是分得很清楚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学生他们的学习本来已经是落后的,疫情让他们更加落后。要帮这些人追的话,不是几个月的事,是几年的事,一分一分地追,如果他们愿意追的话。这时就看到Tutoring System(辅导系统)的重要性了。我们不能只靠老师来帮学生追,不是这样的。最近有一些搞教育的上市公司,让他们来搞了。他们是在市场上卖股票的,怎么可能做得好?可以让当地的教育系统来做,让学校跟一些Auxiliary Tutoring System(辅助性辅导系统)一起来帮助学生追。钱让公家出,可以让大学跟某一些学校共同来献计,政府找承包的统筹经理,这可能是一些组织,让他们来招聘和培训一些已退休的人士、将来要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去做这个系统,联合学校一起来帮着孩子追上去。现在英国已经在做了,英国建了National Teaching Program(国家教学计划)跟National Children Program(国家儿童计划)。国家教学计划下面的Tutorial(辅导班)就是要帮学生追上去。
总结而言,大家的处境不同,但是要往前看,我要Unlearn什么,Learn什么,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现在也要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倦怠,否则就做不下去了,要让自己健康;然后想办法去联系学生,学生还跟老师联系,就不至于绝望。虽然是在不同的处境中,但是大家要考虑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二、全球教育治理中的教师发展
曾:当前国际组织凭借大型测评工具(如PISA、TALIS等)对各国教育质量进行监测,对各国教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您如何看待PISA和TALIS这样的大型测评工具呢?它们对教师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卢:PISA跟TALIS只是Assessment(评估),评估什么呢?PISA只不过是针对学校教育制度的极小部分,就是在我们说的义务教育的终点考一考,看看义务教育到底要学生有哪一些的能力,我们来评估一下。TALIS本来的意图是说,教师那么重要,我们去看看他们的Professional Inclinations(专业倾向)是怎么样吧,比如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的工作、有多少老师自我报告自己是有准备的、他们愿意留下来从事这份工作、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面、他们的Professionalism(专业性)有多高等等。
PISA和TALIS其实是在一个教育系统各环节上Take a Snap Shoot of a System(拍快照),每三年或四年拍一次。但是这个快照现在的像素越来越高。你拍了一个照,居然要五个兆送过来,说明这个照片的含金量极高。如果我把照片放得很大,照片上的深浅颜色也是分明的。PISA和TALIS可能就是这个,能够让你从“照片”里看到一些东西,比如,我怎么能从PISA数学或者科学里面看到过去三年、过去九年的教育质量的变化;或者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就是要看你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来回答你的问题。总结来说,我觉得TALIS问的问题是不错的,找出来的结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如果光是排名意思不大。事实上,一旦将它进行排名就惨了,把有参考性的一个Assessment Exercise(评估活动)变成一场“世界杯”,每三年打一次。PISA和TALIS本来就是给一些办教育的政府官员看的,让他们去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所参考而已。如果把评估活动变成“世界杯”,注定这个评估是失效的。
曾:“快照”和“世界杯”的比喻很有意思。另一个与PISA和TALIS有关的话题是我国优质教育经验的输出。当前我国参与世界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尤其是伴随我国在PISA、TALIS等国际测评中的优异表现,再加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向外输出优质教育经验,如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至今已经实施了6年。有学者将之视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展现国家责任担当的表现;①张民选. 疫情下的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世界危机与中国行动[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43(2): 3-15.但也有一些人担心这一举动会被外界解读为“文化扩张”。您是如何看待我国优质教育经验的输出呢?特别是在教师发展的领域中,有哪些优质经验值得输出呢?
卢:我们要问自己,中国教育里面,从2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有一些什么是能拿得出去的?不是让人来学习,是让人参考的。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我们有一些好东西就放在这儿,让人来参考。有吗?要认真想了,不是凭空来的,是按照当时的情况、现在教育的现实里面,有哪些是我们做起来有参考价值的。
我举个例子,这个是跟PISA有关的。人家问上海的PISA为什么考得那么好?有人说这个可能跟我们教研系统有关。我们就要问:中国的教研系统是否真的是一股力量,是让人值得来参考呢?是的,不妨就放在那里让人来看。教研员是什么人?教研员跟学校、学校老师的关系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的Effectiveness(效力)在哪里?他们是怎么体现他们的效力的?等等,不妨去作一些比较清晰的调查。现在是各说各的,有一些人是很支持的,有一些是质疑的。但是教研员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从头到尾清楚道来,然后就说我们中国的东西其实是靠教研系统来提升的,得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它的局限又是什么,大家来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题目。有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但它是从现实出来的。
另外有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也是从现实出来的,就是德育。现在我们的德育我不觉得办得特别好,在现在来看。为何?说得很高,做起来不高,成效不知道。我关心的就是在现实里面所观察到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Character Building(品格培养教育)。品格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学会推己及人。“推己及人”这四个字、这个概念是另外一种要人学习的东西。“推己及人”再下一层就是Altruistic Attitude(利他的态度)和Altruistic Behavior(利他的行为)。如果是普遍被这个社群接受的,我每做一个事都要想想旁边的人,这是很难做到的,没多少人能做到所有的事。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倾向去想一想他人——推己及人的话,这个社会差不到什么地方。现在大家讲德育和品格培养,我觉得很好,推己及人是一个目标,延迟满足是这个过程里面的Sustaining Force(维系力量)。下个礼拜再去喝这杯酒吧,学期中妈妈才带你去迪斯尼乐园吧。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和我们的美德来结合,我们有很多可以体现在价值上面的东西,但这些谁来做?
这便要靠办教育的人把它接地气了。一般来说,我们想给人看的东西是很少接地气的,PISA跟TALIS至少是接了地气。我们刚才所说的也是接了地气的东西。我们如果真的觉得我们教研系统能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的学校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是可以让他们来看的,那么其中一些我想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些。
我们有不同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人看,问题是如何拿出来给人看,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把东西放在那里,让人知道。宣传也要适量地宣传,在网站里面去推动,让半官方的机构去推动;留学生的往来要更开放,一定要把门打开,不要因为他国有什么措施动作,反过来我对你更严厉。我把你要做的更开放,这才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保持渠道的畅顺。长远来说,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有利于我们把一些好的概念跟有用的东西让其他的人来参考。
这是不是输出呢?是不是文化扩张呢?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的,那就让它“扩张”吧。如果真的是对其他人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为何不做呢?如果只是为了提升国家名誉,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让大学来做的话,大学就在全球的教育市场里面,把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教育市场不一定是买卖的市场,教育市场可以是一个Theater for Operationalization of Ideas and Practices(理念和方法的实践场地),让人来去看到而用之的,也可以是一个市场,这是最关键的。人家参考了,用后有效果,有效果就有口碑,有口碑就有市场,就是这样。中国现在缺的不是钱,而是有更多人说愿意来看一看,来参考,所以这个最好还是保持开放。我觉得广纳、广派留学生,不断地输出、输入,延续不断地运转改进才是好事。
三、比较教育方法论与学科发展
曾:比较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国际比较教育著名学者George Bereday教授是您的导师。Bereday教授认为比较教育的目的在于从事外国教育的分析调查,以及系统地探讨外国学校的素质作为评估本国教育制度的参考。①Bereday, G.Z.F. 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M],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4. 4-7.他就此提出一套具体的研究模式,力图使比较教育研究更趋科学化。有学者称之为Bereday教授对比较教育的重大方法论贡献。②蔡清华. 教育大辞书2000 [EB/OL]. [2020-11-10].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5970/.③Wojniak, J. George Z. F. Bereday (Zygmunt Fijałkowski) and His Comparative Method in Educational Research[J].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18(48): 1-13.可否请您介绍这一模式,并谈谈这个模式对我国当下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启示?
卢:Bereday将比较教育研究分为Area Studies(区域研究)与Comparative Studies(比较教育研究)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含两个步骤:先是Description(描述),指搜集、描述所要研究国家各项教育措施的现状;然后是Explanation(解释),指进一步根据其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哲学及其他背景,分析其教育制度的形成因素,以便了解该国何以形成此种制度。第二阶段则是根据区域研究的结果,针对所要进行比较研究的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穿梭比较研究。此阶段又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Juxtaposition(并列),是将各国的资料按照某些相同或有可能互相比较的标准整理并予以有系统的排列,使人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从各国数据并列中发现其差异或规律性,形成下一步骤的研究假设,此假设即为比较研究中的Tertium Comparationis(比较点,或译参照点);第二个步骤就是Comparison(比较),透过Symmetric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Areas under Study(对于研究中各地区进行对称的来回穿梭考察),比较、思考、推敲、评价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之处。
关于比较教育是不是一个学科,这个争论了很长时间。它是不是一个学科呢?我是比较教育出身的,我觉得比较教育是一个Perspective(视野),是一个Approach to Underst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理解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的视角。
在比较教育里面,Bereday说的Area Studies(区域研究)就是Country Studies(国别研究)。区域研究是Comparative Analysis(比较分析)、Comparative Studies(比较研究)之本。没有区域研究是谈不上能比较的。比什么?你比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接地气。
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人说要赋权给学校,让他们办得更独立。就现在美国的情况而言,就是Charter School(特许学校)。将钱给一个集团,他们答应提高学生的成绩不就好了吗?但特许学校的Autonomy(自主权)不只是这样的。他们是拿着钱,他们还有独立权。最近有一个在纽约市的特许学校把卫生局局长告到法庭,说你没有履行你的责任,就是保护我们。他连CDC的主任也告上法庭了。办学的怎么会告政府官员呢?他在行使他的办学自主权。任何提出参考借鉴特许学校的人,他们知道在我们这个国情里面能有这样子的东西发挥吗?
回到Bereday提出的,区域研究是本。怎么去做区域研究呢?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事。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是用不同的态度、方式对待公开考试的。《经济学人》有一个报道,题目是“Testing Testing”(《“测试”的测试》),讲不同国家怎么对待考试。今年的12月,韩国有一波新的疫情正在发生,几天前韩国就说考试是公开让50万学生去考。那生病的学生(注:指感染新冠的学生)怎么办呢?政府把试卷送到医院的病房里面给学生去考。今年7月,1 000万中国学生要高考两天,延期了但还是要进行高考。报道说是考场里面设有一些隔离的地方,让原本住在病房的受感染的学生能在那边考。韩国和中国是照考。西班牙大学入学也是照考,但只考部分内容。有一些国家是调整了,意大利取消了笔试考口试,奥地利、匈牙利是考笔试不考口试。美国大学Advance Placement (先修课程)在考试里面缩小了考察范围。还有一些是取消考试了,英国、法国、爱尔兰都取消了考试。那分数怎么来呢?英国的做法是让老师来说这个学生值多少分,给得高了就调低,被人骂死了。
回到比较教育。有了那么多Practice(实践),一定要先把这些东西并列(Juxtapose)。例如,在疫情期间如何对待公开考试这个事情上,坚持不取消的、取消的、有一些是调整的,把这些实践并列了,然后把这些应对考试的实践分类。Bereday的观点就说在这个环节一定是要有学问的,要有学问你才能分类。
你收集了材料,然后描述它,这个是Bereday要我们做的。这个是基于区域研究,就是国别研究。国别研究做得最漂亮的,在我所读过的书里,有一位前辈Edmund King(埃德蒙·金)先生的著作Other Schools and Ours(《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这书应该是1958年写的,写的真漂亮,文笔好,描述很清晰,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但Edmund King是有其不足之处的,所以到了1964年,Bereday就出了《比较教育方法论》(Comparative Methods and Education)一书。他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并列了这些东西,但是你到底怎么才能有Symmetric Shuttling Analysis(“对称的来回穿梭比较”)呢?不是说原始的来回比较。最核心的还是要问我们现在常问的,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blem?(你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你没有这个Research Problem(研究的基本问题)你就衍生不出Research Questions(研究问题)。那么你的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疫情期间如何应对公开考试,如果我要做这个研究,刚才所说的国家有一些是不取消,有一些是取消,有一些是调整有关考试的。那么我肯定要问:考试到底对这些国家的价值何在呢?考试对教育的价值何在呢?如果我问出考试对教育的价值何在,作为一个研究的基本问题,衍生出不同的研究问题出来的时候,我基本上满足了Bereday要求我们有所参照的一个要求,有了它我们才能去做Compare(比较)。
很简单,又回到区域研究。描述国外怎么做的话,你只是说要取消、不取消、调整。但我们如果去深究比较他们的做法,如果我们是像Edmund King那样去了解一个教育系统,比如Other Schools and Ours那样,我们会看到他的历史跟文化,立刻有一点就很清楚了:中国、韩国谁也不能改高考。不是说要改革吗?说了十年改革了,但不会取消的,因为第一考试的地位太重要了,第二,现在我们说的常规Continuous Assessment(延续性评估)问题太多。我们以前选人做官就是靠这个考试,而官是高人一等的人。你承认不承认没关系的,事实是如此。所以在中韩这两个制度里面,考试是取消不了的。靠区域研究点出来这个结论就很清楚了。
回到中国,我们现在搞的比较教育研究,其实是外国教育的陈述跟评论,不是什么比较教育。我很少见到有人是按照Bereday这套方法来做比较教育研究的。Bereday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是一九六四年写的,五十几年前的,到了现在还没多少人能做到。Bereday还有一个要求是你要研究这些国家,你是要先在这里生活过的,你是要懂它的语言的。
我们的比较教育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留在国别研究、区域研究等最基本的层次上。像Bereday说的,我们真的是明白吗?真的是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带一路”,我们都明白这些国家是怎么回事吗?不一定。另外一边,有人提我们什么都是大数据,做全球性的比较。有一些人认为把数据量化就变成Empirical(实证的)了,实证研究就等于量化研究,这个是错的。“实证研究”就是实地去参考,挖出真相,这个就是实证研究。人类学学者的实证研究就是蹲在田野里。我们现在很多大数据,很多General(笼统)到连人、地、时空都不知道,拿着大数据就来了。其实我们缺乏的是中间老老实实地、很踏实地去做研究。有一些对外国教育的研究不妨多,这是第一步。其实现在在技术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在网上有太多材料了。
总结而言,比较教育首先是一个视野。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问我的研究问题是什么。一谈到研究问题,他的学术灵感一定是来自传统学科,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等这些传统学科里面。他的学术灵感、他回应的理论建设问题,应该就是传统学科里面的。所以我们要问搞比较教育的人,你的学科归属到底是什么。不是比较教育,比较教育是Perspective(视野)。你的学科归属是什么?是历史吗?那你读过Arnold Toynbee (阿诺德·汤因比)的理论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比较教育是一个视野,那你的学术灵感跟你的理论资源应该是从学科来的,因为比较教育来来去去都是比较。因为你有了传统学科的训练,你才能知道一些理论群里面的不同。你如果没有理论的资源,你就不懂怎么去回应理论、参与理论建设。这是我的看法。
曾:好的,卢教授,谢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