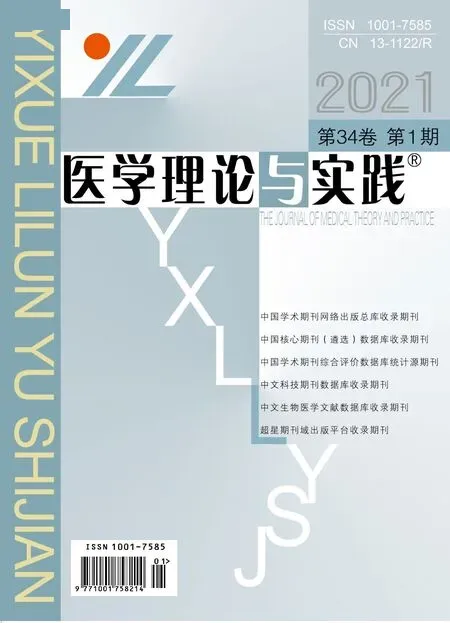炎症小体NLRP3在肿瘤中的作用*
阮 萍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病理科,广西南宁市 530011
炎症与癌症的相关性最早是在19世纪由Rudolf Virchow发现的,他观察到白细胞在肿瘤组织中的浸润,并提出癌症可能发生于慢性炎症部位[1]。慢性炎症在肿瘤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发生、生长、侵袭和转移。炎症微环境在肿瘤发生中已被确认[2]。因此,对炎症和癌症的分子研究为癌症的治疗方法提供了新的曙光。
炎症是固有免疫中的宿主防御反应之一。参与固有免疫的细胞可以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识别微生物间共有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及损伤和坏死细胞释放的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经典的固有免疫受体有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NOD)样受体(NLRs)、C型凝集素受体(C-typelectinreceptor,CLR)和维甲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I-like receptors,RLR)。它们位于细胞的不同部位,并识别不同的配体[3]。一旦这些传感器检测到危险信号,就可以启动炎症。各种固有免疫途径可能与缺氧、化疗、放疗或免疫攻击而死亡的肿瘤细胞释放的细胞成分有关。由肿瘤或肿瘤成分激活的固有免疫细胞可能通过招募效应细胞来诱导抗肿瘤免疫,或通过提供促炎环境来促进肿瘤的发展。炎症小体是一种新的固有免疫途径,大量证据表明,炎症小体在病原体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在肿瘤进展中的作用仍不清楚。
1 炎症小体概述
炎症小体是一种多聚蛋白复合物,其概念是于2002年由Jurg Tshoop首次描述[4]。炎症小体是由NLRs或肝再生增强因子(Augmenter of liver regenration,ALR)、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 associated speck- like protein containing CARD, ASC)和半胱天冬氨酶-1 (caspase-1)组成的蛋白复合体[2]。NLRs是识别PAMPs和DAMPs的固有免疫受体,在人和小鼠中分别分为22和34个亚型。在NLRs家族包括NLRP1、NLRP3、NLRC4、NLRP6和NLRP12。典型的炎症小体传感器还包括黑素瘤缺乏因子2(Absent in melanoma 2,AIM2)和pyrin[5]。ASC包含caspase激活和募集结构域CARD。一旦检测到特定的分子模式,包括NLRs、ALR或Pyrin的传感器就被激活,并通过ASC募集caspase-1的前体pro-caspase-1。被激活的caspase-1通过蛋白水解将IL-1β和IL-18的前体转化为促炎细胞因子IL-1β和IL-18,从而启动一种被称为焦亡的细胞炎性坏死。焦亡是一种依赖于caspase-1或caspase-11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其特征是膜破裂,导致细胞内容物释放。释放的IL-1β和IL-18触发炎症细胞的分化,进而可以诱导自身免疫反应或肿瘤进展[6]。因此,研究炎症小体与肿瘤之间的潜在机制很重要。
2 炎症小体NLRP3
2.1 NLRP3的结构 NLRP3是最具特征性且研究最深入的一个炎症小体。其主要表达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粒细胞、树突状细胞、上皮细胞及成骨细胞的细胞质内,在炎症感染和内源性刺激作用下,NLRP3表达上调[7]。NLRP3和大部分NLRs一样,由3个结构域组成: C端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Leucine-rich repeat, LRR)、中央核苷酸结核结构域(Nucleotide binding domain, NBD)和N-末端PYD结构域[8]。
启动NLRP3炎症小体需要两个不同的步骤,即转录和转录后水平的第一信号和第二信号。第一信号包括TLR配体,如脂多糖诱导的TLR4/MYD88信号,通过NF-κB的激活,进而诱导pro-IL-1β、pro-IL-18和NLRP3的转录和生成。第二个信号由PAMPs、DAMPS、ATP和尿酸结晶等多种刺激诱导,促进NLRP3-Asc-pro-caspase-1多蛋白复合物的形成。一旦激活,pro-caspase-1将被切割成p35和p10片段,p35片段随即将被加工成CARD和p20亚基。激活的caspase-1导致IL-1β和IL-18的成熟和释放,并通过切割Gasdermin D蛋白暴露的毒性N端与细胞膜的磷脂酶相结合,从而在细胞膜上形成孔洞来启动细胞焦亡[5]。
2.2 NLRP3的激活机制 NLRP3炎症小体可以被不同的刺激所触发,其激活机制主要有四种假说,包括钾离子外流、钙离子流量、活性ROS产生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及溶酶体损伤。
钾离子外流、细胞内钾离子浓度降低是NLRP3炎症小体激活的重要机制。细胞外ATP刺激嘌呤型P2X7ATP受体,并触发钾离子快速外流,募集Pannin-1半通道蛋白,诱导细胞膜相应受体逐渐开放。细胞外的NLRP3激动剂进入胞浆,与NLRP3蛋白复合物结合,并触发炎症小体分泌IL-1β[9]。几项研究证实,细胞外钾浓度的升高也会阻止NLRP3复合体的激活,而胞内钾浓度的降低则会启动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10]。研究表明,阻断内质网上的细胞内钙释放通道——三磷酸肌醇(IP3)受体,会减少钙离子流量,从而抑制NLRP3的激活[11],而在RPMI培养基中加入钙离子则会诱发钾外流和NLRP3炎症小体激活[10]。但也有研究者在比较NLRP3炎症小体激活中细胞内钾浓度降低和细胞内Ca2+增加的趋势后,发现NLRP3激活不依靠钙离子[12]。因此,钙信号在NLRP3复合物激活中的作用尚未清楚。
钙离子流入线粒体基质和钙离子超载所造成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及PAMPs和DAMPS、ATP等刺激物通过损害NADPH氧化酶和其他线粒体氧化系统,导致了ROS的释放,从而触发NLRP3复合物的形成。线粒体死亡导致氧化的DNA释放到胞浆中,随后介导了NLRP3的激活[13]。
溶酶体损伤和组织蛋白酶B的释放也是NLRP3炎症小体激活的原因。研究发现,包括硅晶和铝盐在内的颗粒可引起溶酶体损伤,释放并激活组织蛋白B,从而激活NLRP3[14]。
3 NLRP3和肿瘤
炎症小体是固有免疫系统中诱导pro-caspase-1活化和炎性细胞因子成熟的多聚蛋白平台。IL-1β的过表达除了与自身免疫病相关外,也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包括NLRP3、NLRP6、NLRC4、NLRP1和AIM2在内的几个炎症小体均可能通过调节固有和获得性免疫、凋亡、分化和肠道微生物而在肿瘤发生中发挥致病作用。NLRP3在肿瘤进展中的作用非常复杂。已有研究表明,在各种癌症中,NLRP3既有促癌作用,也有抑瘤作用。
3.1 NLRP3的抑瘤作用 在氧化偶氮甲烷—葡聚糖硫酸钠(AOM-DSS)诱导发生结肠癌的小鼠模型中,NLRP3基因敲除的小鼠更容易出现结肠息肉,并对AOM/DSS诱发的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高度敏感,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在显示出肿瘤加速生长并伴随着组织IL-18水平的降低。这些发现表明,NLRP3可以抑制肿瘤的形成,而IL-18与结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经AOM-DSS诱导后,IL-18-/-小鼠比对照组小鼠更容易发生肿瘤,这表明IL-18具有潜在的保护和抗肿瘤功能,包括修复结肠炎相关性结直肠癌中的上皮屏障损伤,而使用重组IL-18可抑制肿瘤的进展,这意味着产生细胞因子如IL-18可能成为结直肠癌的潜在候选治疗药物[15]。NLRP3在肝细胞癌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抑制肿瘤作用,与肝组织对比,肝癌组织中炎症小体的表达明显减少或完全消失,且炎症小体表达下调与肝癌的晚期和低分化等临床特征密切相关[16]。NLRP3在抑制肿瘤进展方面也很重要。NLRP3介导的IL-18通过诱导辅助T细胞产生干扰素-γ并增强T细胞和NK细胞的细胞毒作用,间接抑制结肠炎相关性结直肠癌的肿瘤进展[17]。此外,枯否细胞中激活的NLRP3通过释放IL-18,促进肝脏NK细胞的成熟和FasL的表达,从而抑制了结肠癌的肝转移[18]。在化疗过程中受损或死亡的肿瘤细胞释放ATP,刺激NLRP3炎症小体和IL-1β受体信号通路,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从而抑制肿瘤生长。此外,化疗药物如奥沙利铂无法诱导NLRP3缺陷小鼠细胞毒性T细胞的激活[19]。
3.2 NLRP3的促瘤作用 也有研究表明,NLRP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通过影响宿主肿瘤免疫、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及调节肿瘤微环境,从而推动肿瘤的发展进程。在肉瘤和转移性黑色素瘤的小鼠模型中,激活的NLRP3通过抑制自然杀伤(NK)细胞和T细胞,募集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从而促进了肿瘤的发生和进展。而沉默NLRP3使宿主小鼠肿瘤相关MDSCs的数量减少5倍,且效率降低,这表明NLRP3通过调节宿主免疫来影响肿瘤发生[3]。研究证实炎症小体复合体的主要成分ASC促进原代黑色素瘤细胞的增殖,将其敲除后,可通过抑制细胞增殖来预防DMBA/TPA诱导的皮肤癌发生[20]。NLRP3通过激活细胞周期素D1和诱导IL-1β的产生来影响肿瘤细胞的分化。IL-1β激活NF-κB,启动JNK信号转导,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侵袭和肿瘤进展[21]。近期研究发现,瘦素通过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和活性氧的产生激活NLRP3,NLRP3则通过诱导肿瘤生长、刺激细胞周期基因及抑制凋亡基因表达实现对乳腺肿瘤生长的调控[22]。NLRP3还可通过激活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CSCs)的途径,诱导肿瘤细胞的自我更新,加速肿瘤进展[23]。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是浸润至肿瘤的免疫细胞之一,在肿瘤淋巴管生成和增殖中起重要作用。TAMs胞浆内的NLRP3激活之后,IL-1β和鞘磷脂-1-磷酸信号的产生促使炎性肿瘤微环境的形成,从而有利于肿瘤的转移[24]。
化疗药物吉西他滨和5-氟尿嘧啶因激活MDSCs的NLRP3,产生IL-1,并诱导CD4+T细胞分泌IL-17,导致其药物作用被削弱,而吉西他滨和5-氟尿嘧啶在NLRP3或Caspase-1敲除小鼠体内显示出更强的抗肿瘤作用,表明化疗介导的NLRP3激活是肿瘤生长的正调控因子[3]。
NLRP3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可能取决于组织或细胞的类型。NLRP3在肠癌中展示了其抗肿瘤作用,但在胃癌和前列腺癌中却表现为促肿瘤的作用[3]。因此,需要使用条件基因敲除模型和药理学激活剂或抑制剂对NLRP3进行综合分析,以分析肿瘤中NLRP3活性的确切机制。
综上所述,近年来相关研究进展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NLRP3功能及其在宿主防御、疾病包括肿瘤发病机制中调控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LRP3在肿瘤发生和抗癌免疫中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但其在不同肿瘤类型,肿瘤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在肿瘤的形成、发展和侵袭中的作用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对其产生、激活和调节背后的分子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为相关临床肿瘤靶向药物及免疫治疗的开发提供新靶点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