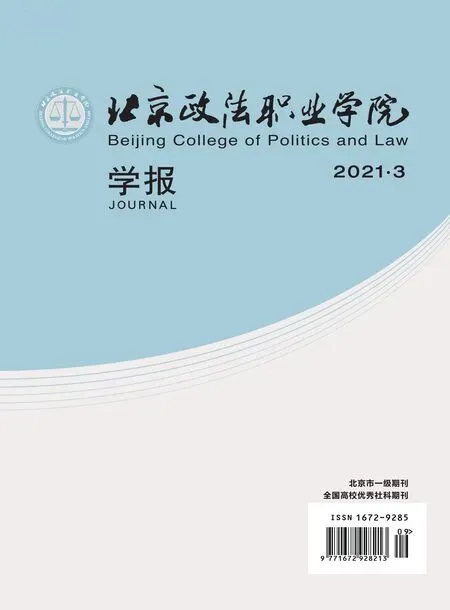场域理论下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践困境研究
——以Y市为例
何晓红 徐 苛 张 虎
1899年,美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并在芝加哥市设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于此,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少年司法制度和少年权利保护的重要性。虽然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差异明显,但对少年司法体系建设中,都将福利和教育注入其中,这与社会工作中的“助人自助”理念不谋而合。目前,未成年人涉罪经过公检法三个刑事诉讼程序进入社区矫正或监禁矫正时间长达半年以上。此阶段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将会受到巨大影响。“除了行刑阶段需要开展的社区矫正服务,公检法三个司法阶段也存在着社会工作服务介入的需求。”[4]席小华:《从隔离到契合: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华东理工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论文,第1页。随着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不断深入,少年司法和社会工作从隔离到亲和,在刚柔并济的“嵌入”结合中,实现司法社会工作实践的完善。
然而,在两者经历理念融合、服务介入、制度建构下,在偌大的司法场域中,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场域这一惯习视角下,社会工作者经受专业价值伦理原则下产生的自主性惯习,在司法场域的空间结构中极易与原有规则产生互动“博弈”,逐渐在“领导”为本的社会体制中,形成有着司法性情倾向的惯习,加之司法场域中涉案人员自身的复杂性,从而造成各种实践困境。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主要讲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相互关系。场域主要指外部行动者在其所在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惯习是指个人成长于所在场域中,被各种社会秩序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体现,是一种性情倾向;资本主要指在场域中可以使行动者展开博弈的,使整个场域有动力的资源组合,主要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根据场域理论的基本要素来看,在少年司法体系中,社会工作者所在的司法环境属于场域;社会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场域中习得一些行为观念、价值观等是个体惯习;社会工作者所拥有的经济情况、文化素养、社会关系和交往情况属于资本。
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引自国外,目前已嵌入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并生根发芽,形成众多分支。司法社会工作作为特殊领域的重要一支,其发展受到国外较大影响。 Robert Madden评价社会工作的司法介入指出,社会工作职业要想控制其未来,就必须致力于通过教育、倡导和积极的法律政策发展对法制产生影响。[5]Madden R G.Essential Law for Social Work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39.
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建立少年法庭后,社会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与此同时,更多人开始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并设立青少年心理机构。[6]T Maschi,M L Killian,“The Evolution of Forensic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Implications for 21st Century Practice,”Journal of Forensic Social Work,2011(1),p17.社会工作与少年司法的合作开始于雏形。威廉·希利博士最早用个案研究方法关注问题青少年的个别性,并相信他们是可以被挽救和感化的。[7]Lynn M Nybell,Jeffrey J Shook,Janet L ,Finn.Child hood,Youth,and Social Work in Transformation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9,p49.希利博士对少年司法中的再生性恢复功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74 年,美国颁布的《少年司法和犯罪预防法》规定了少年犯罪年龄、成年与未成年监禁环境的隔离等,由此,在少年司法政策中社会工作的作用发挥的愈加明显。[8]ClarkM,Peters,“SocialWork and Juvenile Probation :Historical Tensions and Contemporary”,Convergences.Social Work,2011(4),p355-356.于此,社会工作得以合规性存在于美国少年司法场域。
英国司法中的社会工作萌芽最早产生于慈善总会活动,之后社会工作便在司法体系中确定了法律地位,并开始重点关注少年司法。现代司法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主要是运用社会工作中的恢复性发展理念,认为青少年产生越轨行为主要是一些需求尚未满足。然而,英国当地局限于社会工作认知度不够,使得社会工作仍处于较为劣势地位。但由于社会工作关注社会问题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导向,存在一定的群众基础。社会工作者需运用专业性学习后习得的自主性惯习来应对司法场域中的不公平现象,需对青少年的各类需求加以评估以便在价值观引导下合理帮助青少年减少压迫。[9]Roger Smith. Crimin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2015(19),p210.
关于司法社会工作概念方面,“司法社会工作”于2002年在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开始提及。范燕宁、席小华首次将“‘社区矫正工作’定义为‘司法社会工作’,强调司法社会工作的主体、客体与服务内容”。[10]范瑞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文献综述》,《社会与公益》2020年第1期,第21页。后续也有学者(马姝、何明升、任文启、张善根等)对司法社会工作的概念内容有所扩充和整合,但大体都是在司法机关领导下,有序为有需要群体提供服务。
关于司法社会工作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包括合适成年人、参与听证、社会调查、个案帮教、心理疏导、被害人救助等。李岚林论述了作为刑罚执行的社区矫正和司法社会工作在理念、原则或价值观上有不同程度的重合或交叉部分。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在功能上可以弥补社区矫正中刑罚执行功能的不足。[11]李岚林:《司法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49页。姚建龙认为合适成年人即为“临时代理家长”[12]姚建龙:《合适成年人与刑事诉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3 页。存在,贯穿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法院审判阶段以及刑罚执行阶段。张艳荣运用赋权理论,阐述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合适成年人制度实行中的困境及在与公检法合作中合适成年人制度实行的权力关系。“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制度作为少年司法领域的特色制度,彰显出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现阶段司法社工的介入正是对人性关怀理念的贯彻执行,与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有一定的趋同性。”[13]张艳荣:《赋权还是剥权:司法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制度的困境分析》,中国政法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第8页。席小华提出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具体实施过程。社会调查中所需调查的内容分为两类: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14]席小华、徐永祥:《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0页。2020年,席小华又运用案例分析提出社会工作介入被害人救助的具体实务模式,“未成年人被害对其本人而言毫无疑问是巨大的灾难。大多数未成年人在被害后生理、心理、情绪等方面面临严重危机”。[15]席小华、李涵:《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服务模式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4期,第34页。她从接案方式、专业关系建立、活动开展、社会工作者能力提升等几个方面做出详尽建议。张善根从司法社会工作功能出发,认为“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更在于通过社会化司法在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的同时为未成年人融入和回归社会奠定基础”。[16]张善根:《司法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及其范畴——以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为中心》,《未成年人犯罪问题》2011年第5期,第46页。不同学者对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不同之地有了进一步解释和阐述,大体都表明了司法社会工作者介入司法场域不同实践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司法社会工作的研究从2002年左右就已开始,对司法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以服务实践领域为主,并无将司法社会工作纳入司法体系范围内来研究。在政策方面,目前司法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已有具体法律条文兜底。比起英美两国,国内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像英美两国,将司法社会工作不仅运用于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等,更运用于警务工作中。纵然司法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是历史和现实所需,但实践中也困境百出。文章将社会工作者放置于司法场域中做具体主体分析,用场域理论解释整个司法场域中,社会工作者如何获得倾向性惯习,并走出实践困境。
二、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的协同整合与冲突困境
(一)亲缘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首先,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的本质理念相同,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个体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少年司法以“柔”为主,注重涉罪未成年人惩罚的同时,更注重背后的再生社会化,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双重教育功能。社会工作强调弱势群体的“增能”和助人自助,在有效评估涉罪未成年人的需求下,能够看到涉罪背后的人格结构、家庭系统等,可以进一步有效的帮助司法部门巩固双重教育的功能。其次,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帮助预防并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更好实现再社会化。最后,少年司法注重青少年单个个体发展处遇,与社会工作中注重个别化原则而实行的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相近。另外,少年司法注重家庭教育和家庭职能,这与社会工作中家庭结构治疗以及依恋关系的正确处理有着相似的功能。少年司法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常常关注未成年人的中观、宏观系统,需要借助学校、社区等力量达到预防宣传,并找寻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亚文化圈”,这与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方法以及社会行政等间接方法有着相同之处。少年司法于法律严酷性上有所缓和,刚中带柔,认为未成年人涉罪行为的产生是其心理、生理、社会等需求未满足,从而要挖掘他们的需求并寻得相应的社会服务得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与社会工作评估未成年人需求问题,从而跟更进一步干预相似。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应进行非监禁化、非刑事化改革,分流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功能,急需有机构能承接分流后少年的社会服务和教育功能,这急需分流后有社会观护机构进行照管,而社会工作刚好可以承担起分流后的社会教育功能,满足分流制度的需求。”[17]杨旭、何积华:《少年司法与社会工作的协同与整合》,《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1期,第91页。
(二)刚柔相克:案主自决与司法强制
少年司法最为本质的特征即为司法的强制性、严厉性,这与社会工作强调案主自决,强调助人自助有些价值背离。社会工作者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事件中,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相信未成年人的可塑性,重点聚焦“优势”和“育人”,多以教育者、引导者、服务提供者、资源获取者、协调者等柔性角色出现,关注未成年人涉罪背后的心理、生理和社会需求状况,重点是引导的同时,挖掘涉罪未成年人的潜力,以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社会化功能。少年司法则以强制性的教育为主,柔性因素下的刚性惩罚不可少。另外,司法社会工作者由于角色需要,经常困惑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惩罚控制和再生社会化,会造成司法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功能混乱,影响服务效果。
三、Y市司法社会工作发展历程
Y市位于中部地区,是省域副中心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当地居民多在外谋生,未成年人多为隔代抚养。据2018年Y市人民检察院数据统计,Y主城两区每年未成年人涉罪达到100多例,下辖某个县市每年达到60多例。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本市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普遍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原因问题,就开始将社会调查制度运用于少年司法。2013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专章,规定了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2020年7月,《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加明确了将社会组织力量纳入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体系中。Y市人民检察院在刚开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帮教等过于形式化。司法具有强制性,缺乏温情元素。未成年人三观尚未成熟,强制性的审问关押极易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创伤,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在Y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听证会,邀请本地区高校法学教师作为专家代表,在了解到涉罪未成年人提审情况后,考虑到将社会工作的柔性注入少年司法体系中,充分考虑到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因素,运用合适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从未成年人的个体发展、依恋关系、家庭系统、朋辈群体、社会关系交往状况等做出综合的评估并有针对性的实行介入策略。加之国家也出台政策多次鼓励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参与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为未成年人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2018年,在Y市政协会议上,本地区高校教师作为政协委员也首次建议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中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并得到检察院明确可行的答复。至此,在Y市人民检察院的引导下,Y市两个主城区的检察院与本地区高校建立专业司法社会工作团队帮教组合,对本地区的涉罪未成年人做审前社会调查、帮教工作等。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力量在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和帮教中得到良好的体现。Y市人民检察院对司法社会工作是从刚开始的接受、怀疑到信任、赞扬,这一路成长实属不易。
目前,Y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将司法社会工作明确纳入未成人检察工作的重要体系中,在服务购买中也实现了长期有效的合作,Y市人民检察院也已经成为本地区高校的重要实践基地。
四、场域理论下Y市司法社会工作实践困境分析
根据场域理论的核心要素——场域、惯习和资本,可以将Y市司法社会工作实践困境分为行动者法律地位不明确、专业能力不足、各种资源尚缺三种情况。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
第一,在少年司法系统发展越来越完善之际,司法部门也认识到专业社会力量介入少年司法体系的重要作用。2013年《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到社会组织参与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然而,2020年10月《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修订之前,在法律条文中虽多次提及对未成年人的挽救、教育等,但没有明确提及社会工作参与少年司法这一问题。因此在早期,在司法场域中,司法社会工作的认知度较低,具有“不明确的合法性”。这种认知度较低,不仅体现在整个司法场域对社会工作机构的认知度较浅,更包括社会场域中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也较浅。另外,在具体实践中,司法社会工作对涉罪未成年人做社会调查和不予起诉后的社区矫正帮教工作,缺少与涉罪未成年人前后诉讼、提审的互动帮教环节,出现了漏管的现象。
第二,司法场域具有强制性,司法社会工作需在司法的强制性下发挥作用。从社会工作的目标来看,最终要实现服务对象的“自助”,服务过程的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整个服务具有较强的灵活变通性。而当司法社会工作需要干预的场域过小,灵活度较低时,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受到场域的限制。尽管在介入过程中,司法部门允许在特定的场域中根据服务对象和司法社会工作者的惯习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要在充分考虑法律背景的前提之下,加之对司法场域强制性的惯性思维下,探索性工作的展开实属不易。此种情况之下,司法社会工作开展服务将会面临很多束缚和困境。
(二)专业能力不足
涉罪未成年人所在的场域系统复杂多样,有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系统环境,其在不同系统中将有不同的需求。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来看,每一位孩子都是有潜力自我成长的,其涉罪行为只是一时需求尚未满足而走上的错误自我救治的方法,从而在错误的场域中习得错误的惯习,产生偏差和越轨行为。涉罪未成年人可能面临着失衡的家庭系统、不良的朋辈群体、较低的自我认同等,因此需求的多样化就要求司法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甚至,有的涉罪未成年人早早在社会浪迹多年,社会经验丰富,Y市地区高校的司法社会工作者作为在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生或本科生,并无经受社会历练,很难走进服务对象的心理世界并与之产生共情。加之,涉罪未成年人群体复杂多样的需求,这就需要司法社会工作者应具有较强的实务技能和工作经验。然而经验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学习,以及社会的淬炼,这对于司法社会工作者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外,司法社会工作者的自身抗逆力水平也有待提升。涉罪未成年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工作者 需要掌握的熟练技巧,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一个人的个人品质和抗压能力。司法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因为无法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实务过程中进展较慢等客观因素产生无力感,从而降低自我效能。然而,犯罪作为一种多种消极因素综合而来的行为表现,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并且在司法社会工作者的后期帮教矫正中,有6-9个月左右的具体期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司法社会工作者很难完全真正的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解决所有的需求和困境。多种问题难以解决会使得社会工作者产生无助和自我怀疑,从而造成专业的不自信、职业的懈怠等。
(三)各种资源尚缺
司法社会工作者的资源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当其进入司法场域,会由于经费问题、人才问题、信任问题等造成实践困境。首先,Y市的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由本地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授兼地区政协委员的发言倡议而来。在司法场域已经习惯固定的人员去解决少年司法问题,引入专业的司法社会工作力量,司法场域是持有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因此,在最开始的实践中,司法社会工作展开实务是完全按照司法部门的要求,自我的发挥空间很少。并且,在Y市政府机构和司法部门也并没有对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建立完全的信任机制。张树沁、郭伟和在对三个草根 NGO 组织性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我国草根 NGO 组织所面临资源性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后总体性社会中,虽然国家放松了对资源的控制,但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依旧抱有不信任的态度。”[18]张树沁、郭伟和:《去行政主导的草根NGO发展策略——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实证研究》,《东南学术》2012年第2期,第221页。因此,政府和司法部门对社会工作机构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另一方面,Y市的社会工作机构等NGO组织本身就依靠着政府补贴和救济而存活,自身的造血功能太差。这就导致了Y市司法社会工作在经费支持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其次,Y市社会组织中承接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较少,主要是由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形成的司法社会工作团队,理论经验丰富但社会经验缺乏,并且相对于Y市的每年的涉罪未成年人数来看,司法社会工作者的数量远远不够。跟深圳、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相比,Y市的司法社会工作2018年左右开始,发展时间较晚,多处于探索阶段,在借鉴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化推进磨合也是一大困境。
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是Y市未检工作的一大进步体现,在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工作中,提升涉罪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进程,着实对涉罪未成年人起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对司法的强制刚性也有一定的柔和作用。然而,Y市在将社会工作引入司法体系中也经历了从理念嵌入到服务购买再到制度建构的过程,其中困境也不言而喻。
在少年司法场域中,行动者所采取何种方式面对困境及解决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分析了司法场域中,涉罪未成年人系统的复杂性以及需求、司法社会工作者专业性困境、资源困境等,在不同困境中的寻求的解决方式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在困境出现的实务过程中,司法社会工作者多次自我怀疑,多次产生无力和恐惧,在督导的帮助和陪伴下,也努力克服不安和焦灼等非理性情绪,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和实务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