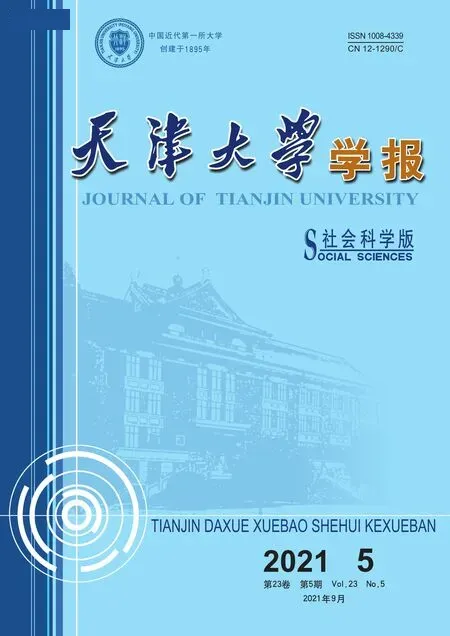西南地区清诗总集的诗史价值
方丽萍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玉林537000)
“诗史”最早见于唐代孟棨《本事诗》,言杜甫诗“善陈时事”,“当时号为诗史”。“诗史”的含义有二:一是“读之可以知其世”;二是诗情。杜甫之后“诗史”便成为评价诗歌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宋末汪元量、文天祥,明末清初的张煌言、钱谦益、吴伟业等人诗均获此评。
清代西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处于帝国边缘,经济、文化落后,一直被视作“荒徼蛮陬”。清代西南地区历史地位特殊,它是南明王朝抗清的最后根据地,是太平天国的发祥地,是改土归流主要实践区。清代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蛮荒面貌有所改变,作家作品大量涌现,总集、别集不断被编印出来,仅清诗总集就有近百部。四川有《国朝蜀诗略》《蜀雅》《国朝全蜀诗钞》《新繁诗略》《新繁诗略续编》《锦城诗存》等,贵州有《黔风》《黔风鸣盛录》《黔南六家诗选》《黔诗纪略后编》等,云南有《国朝滇南诗选》《国朝滇南诗略》《国朝滇南诗略续刻》《滇诗嗣音集》《滇八家诗选》等,广西有《檆湖十子诗抄》《峤西诗抄》等。“历代诗篇之不坠者,赖有此耳。”不同时期、不同选家,会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与偏好,但也会有时代、地域等共同特征。西南地区清诗总集有一非常突出的特征:叙事诗多,长篇叙事诗多,关乎当时社会政治及具体历史事件的长篇叙事诗尤其多。那么,是诗人热衷于创作这一类题材?还是选家倾向于选择这一类诗作?抑或其他?其中体现了清代西南地区诗歌总集的哪些特征呢?
一、 选家:“乡人言乡事,稍详原委”
地域性诗歌总集的编撰目的之一是保存乡邦文献、提升家乡文化地位。袁文揆言他之所以编订《国朝滇南诗略》是因云南兵燹,文献零落:“是集为乡人言乡事,稍详原委。高谊畸行,庶几共著”[1],“不急为搜罗,将使前人著作终于郁湮,岂非后死者之责哉?”[1]37罗瑞图为此集所作序时亦指出此书“不第见乡先达之诗文荟萃,兼可识其伟烈丰功,品量卓犖……实足以资考镜而备滇南掌故,诚于《通志》《滇系》外可为征文考献之助”[1]5-6。张凯嵩说他编辑《檆湖十子诗钞》是因为“诸君往矣,遗书经乱,或存或亡。余之钞诸君诗,虽未必藉以传于世,然亦足使世之读者于兹先睹,可得其概”,“他日考粤西文献者、论诗教者,必有取焉”[2]。
总集编撰目的之二是呈现地方诗歌发展的全貌。这一点总集的序、跋多有说明。如孙桐生花费长达40年的时间编订了《国朝全蜀诗钞》。他在回顾四川地区诗歌的发展历史,显示地域文化的自豪感时说:“汉则司马相如、杨子云,唐则陈子昂、李太白,宋则苏氏父子兄弟畅其流而汇其宗。元之虞伯生、明代杨升庵,咸以倜傥宏博之才,发为诗歌,故能掉鞅词坛,雄视百代”;“我朝制作明备,英贤辈出”[3]。表示要主动承担起传承地域文化的责任:“夫天下作者众矣,诗日出而日新。苟不自近者著录之,将近者亡而远者愈无征矣。”[3]1再如纳汝珍说他之所以编订云南地区诗集,“徒以地居边僻,表彰乏人,流传不远,以致主选政者采访不及,是亦地方文化莫大之憾事。而海内言诗者真以吾滇为无人矣”[4]。西南地区清诗总集的选家,往往追溯本地区诗歌发展的源头,然后一直讲到当下,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编撰者存史之失、补史之阙的愿望以及文化担当精神跃然纸上。
清代西南地区诗坛的面貌,往往也是通过几代人接续努力,薪火相传,最终在总集中得到相对完整、全面的呈现。如云南方面,袁文揆《国朝滇南诗略》首出,“其后昆明黄矩卿琮编《嗣音集》,石屏许麟篆印芳编《重光集》,相继赓续,天南风雅,灿然大备”[5]。随后陈荣昌的《滇诗拾遗》、李坤的《滇诗拾遗补》、王灿的《滇八家诗选》相继出现。王灿言说他之所以编订《滇八家诗选》,就是为弥补前几部总集“采访不周,只爪片鳞,不足以悉滇诗之美备”的遗憾。再如四川,首先是张邦伸编《全蜀诗汇》,几年后李调元《蜀雅》成,咸丰七年又有《国朝蜀诗略》,光绪五年有《国朝全蜀诗钞》等。在贵州,乾隆朝有《黔风》,道光朝有《黔风鸣盛录》,光绪朝有《黔南六家诗选》,宣统朝有《黔诗纪略》,之后《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编》等陆续编出。广西清诗总集的编撰,肇端于张鹏展的《峤西诗钞》,之后有张凯嵩的《檆湖十子诗钞》、梁章钜的《三管英灵集》,甚至余波漫衍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陈柱的《粤西十四家诗钞》和吕集义《广西诗征》等编订。正是在这样的接续与持续的传承中,西南各省的诗人队伍及诗坛面貌才得以完整存现。
西南地区诗歌总集的编撰者们还重视所处地域诗歌中所保存的政治史、制度史等方面的材料,认为这是地方性诗歌总集独有的优势,可与地方志等材料互补互证,《国朝滇南诗略》是“乡人言乡事,稍详原委”[1]54,“获是书者可以观乡先达之品量功烈,以及学术、经济、文章。即就此考献征文,亦足以备滇南掌故”[1]5-6。《播雅》意在“略备一方掌故”,“郡之山川风土、疆里沿革、旧城残垒,有所钩核,亦参他例,并借书之。其搜订之勤,别裁之审,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献烂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6]。也正因为有这样清晰的“存史之失”“补史之阙”的明确意识,西南各省的选家才将大量的关乎社会政治的叙事诗编选在册。
二、 诗家:“足资史册”“以诏后世”
清时的西南经济相对落后,民族冲突频发。南明小王朝最后的活动区域在西南,张献忠大西政权曾盘踞西南,太平天国也发端、壮大于西南。西南地区连岁战乱,百姓“出入兵间”,诗人生活之地更多动荡,如云南朱昂云:“阖门三百余口俱遭流寇。”南宁人段标麟云:“幼年为人掠卖,能自识其乡里,逃归。”四川人王新命记述:“年十二,遭献贼乱,全家被害。”费密云:“少遇献贼之乱,遁身西域。”他们亲历动荡和战乱,亲睹无数的死亡,笔下自然会有大量此类历史情状记录。如莫友芝《芦酒诗》《遵乱纪事》《哭杜杏东及其子云木三首》等。檆湖十子之一的朱琦“身更丧乱,所作类多悲悯人天,有杜陵诗史之目”[7]。朱琦本人也多次表示他的诗是记录历史,为后世提供镜鉴:“列圣伟烈神谟具在实录。臣窃不自揆稽首,谨述其略,被之声诗,以诏后世。”《檆湖十子诗抄》收录朱琦诗最多,共5卷382首,其中有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的诗作:《新铙歌》四十九章记载了清朝开国之初的多场战争;《感事》从“鸦片入中国”“粤人竞啖吸,流毒被远迩”讲起,对鸦片战争作了全景式记录;《老兵叹》借老兵之口展示了1895年台湾保卫战,林把总誓死守卫的豪迈、寡不敌众的无奈以及壮烈牺牲的场面都生动而细致地记录了下来;《定海纪哀》写定海城陷落后“三总兵”“寸喋无完尸”的惨状。此外如《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朱副将战殁他镇遂溃诗以哀之》《吴淞老将歌》《题金陵被难纪哀》等均是对当时历史大事的详细记录。
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有很多记述地方动乱的诗。如费锡璜的《昆阳行美叶令长先辈》写的是当地盗匪抢劫、屠戮百姓:“野赤云腥杀气横,血肉膏原收不得”,“七十二处烟尘荒,所在皆化为财狼”[3]25。还有歌颂新来县令在平定盗匪、造福地方的功勋的诗,如刘讷的《悼忠烈周二南先生》、何椿龄的《洋州城》等。这些诗中常有官员殉国、百姓遇害等的惨烈记录,如李崧霖的《明嘉州刺史朱公象先阖门殉难歌》:
荆门开,夔门开,贼如虓虎巴东来。瑞王死,蜀王死,大西伪号假天子。环薪惨害百千儿,堆砚几屠三万士。杀气黯淡天无光,河山破碎摇欃枪。飞炮雷轰激天怒,雄枭无乃真魔王。平羌江头血流水,士卒饥疲裹疮痏。巴筰烽烟僰道连,铁山瓦屋皆摧毁,黑云压阵刀光紫,白羽登陴鼓声死……[3]462
整首诗以时间为线索,记叙了朱仪护惜城池、百姓,最后全家共同捐躯的事件,满溢着诗人的敬佩与惋惜。
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记录“节”“烈”妇女的诗较多。《国朝全蜀诗钞》有李先复的《吊断臂烈妇行》、王汝璧的《赵州三妇歌》、宋锜的《孙孝妇诗》、李炳奎的《饿死行为泾县胡烈妇作》《王贞女诗》、潘元音的《杨家妇》《长寿女》等。一些当时的轰动事件成为一段时期内诗人关注的题材,如张献忠入蜀时四位“蜀王近侍”严兰贞、齐飞鸾、许若琼、李丽华殉死之事。王煓、张怀溎、车酉分别写诗记载这一事件。这些诗结构基本相同,首先追溯事件经过,然后发表感想:“争与烈皇殉社稷”“岂知烈女骨,万古犹馨香”。
除表扬忠、节、烈外,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动荡、混乱的描写,对百姓艰难生活的记录,对朝廷政策的批评等。龙启瑞的《纪事》描写“贼人”横行造成的人间惨剧:
慈母失爱子,老父寻幼孙。日暮倚高崖,遥望焚何村。仰天唯涕零,难对官府言。更遇风雨夕,灯烛不得燃。松枝蔽其顶,蓬茅围其身。足底闻流澌,拥树如穷猿。远聆兵马来,疑是贼营迁。纷如鸟兽散,既定复来还。寻声以相识,时复触尻肩。日出望里间,所至无炊烟。共言贼徒散,始复还家门。牛豕肉狼籍,鸡犬无一存。犁我田中禾,发我窨中钱。生计一以失,性命如倒悬。[8]
此诗描绘生动,议论剀切,堪称清代版的“叹息肠内热”。
再如赵士麟的《丁亥纪事》:
丁亥夏六月,流贼入我疆。兵戈起仓卒,官吏接踵降。哭声动天地,日星惨无光。老少各逃命,道逢虎与狼。四境恣杀掠,金帛满路傍。劫我作奴仆,束缚虑逃亡。举步或稍缓,鞭笞痛莫当。箐林影昏黑,倾跌心愈荒。惟期免敲扑,哪顾鸣空肠。暮夜集村坞,炙酒烹牛羊。凶锋有万状,喧呼拥平岗。醉后劓刖人,血肉溅衣裳,忧世刳孕妇,男女贯旗枪。求生固已矣,求死亦不遑。夜半人马寂,脱身匿丛簹。一步一惊顾,暗地呼穹苍。狐兔起蹊隧,荆榛长成行。踌躇奔城郭,呼纯缒垛墙。攀援似猿猴,四顾殊彷徨。亲戚闻我至,城头问审详。朋友闻我至,只手相扶将。父母向我前,拊背慰百方。坐定复移时,始知身未亡。努力去守陴,安能进酒浆。但得共相保,吾亲亦永康。[9]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大量细节描述战乱中百姓的被掠及死里逃生的经历。此诗写于赵士麟出任贵州推官不久,“时滇黔初平,公到任,抚绥缉捕,不遗余力”。此诗能令我们体会到他对百姓的感情,也说明了他“缉盗卫民有声”的主观原因了。
康熙年间费锡璜的诗有“古体直追汉魏”的赞誉,云南孙鹏的诗也有“纯是汉魏”之评。这里的“汉魏”,应包含有两重含义:1)如汉魏诗的质直、慷慨、悲凉;2)如汉魏般的动乱现实。《卖儿行》《水后寄城中故人》写百姓灾害之年卖儿卖女的惨痛,《穿灯珠老人歌》写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在米珠薪贵的动乱年代手艺无所用处,“指穿血出无人顾”“抱珠而泣”[3]25-26的悲惨命运。
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还有具体反映清王朝救灾措施的,如《国朝全蜀诗钞》中李的《劝捐》《粥厂》《施米》《减糶》等。《劝捐》写灾荒之年,地方官央求、逼迫当地富户捐资,富户与官府讨价还价的趣事。《粥厂》描写清代社会救助的具体细节,如施粥时男女分开,要登记名户,“门外传签如校试,门内点人核姓名”,人们得粥后的迫不及待,“盛以瓦釜掬以指”。粥厂辰时一过即关闭,“可怜后至防风氏,含悲忍泪垂头去”[3]375。西南地区清诗总集还有一些有趣的暴露、批判社会政治的诗,如《堰北水》:
修堤筑堰年复年,安得水势倒行还上天。决口乍塞塞口决,明年再请司农钱。[3]15
河水之所以反复决堤,是因为官府并不准备真正彻底治理水患。对他们而言,水患是财源,必须保证它能源源不断。此诗可谓直击灾荒本质,发人深思。有的诗对官府的批评非常尖锐、凌厉,如《贼来犹可》:
贼来犹可,官来杀我。贼来可避官难躲。蛟鳄不在深渊,豺虎不在深山。堂堂一何峻,阴风瘁瘁白日寒。杖底号声杖头血,死生只在呼吸间。同然为暴客,官更狠于贼。治贼不治官,贼究何由灭。呜呼!世逾乱,官逾劣,贼不尽,人且绝。[3]411
此诗以官与贼相对比,写官比贼还凶恶。“贼”本是被“官”逼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的良民,官才是一切乱世和祸害的根源。他们视百姓如草芥,任意鞭挞盘剥。诗歌结尾诗人不由悲愤地指出:如果继续听任官员为非作歹,老百姓就只有为“贼”或等死两条路了。
李映棻的《兵差行》与《贼来犹可》类似,属于深化的“官来杀我”主题。全诗分七解,记述如狼似虎的官兵到一地之后对地方的侵扰与破坏。最后一节写他们终于离开:
明晨吏报,兵差过净。县官侦之,房屋拆尽,库藏洗空,仓储无剩。如洪水冲,如烈火烬。害民害官,较贼尤甚。县官悲愤,仅余性命。哭诉大府,大府不应。不曰军士横,犹曰县官吝,办差不善已撤任。[3]570
县内已经如洪水漫过、烈火烧过般一无所剩。更惨的是上级官府非但不主持正义,惩处下属的胡作非为,反倒认为是县官吝啬,接待官兵不利,甚至撤销了地方官的职务。诗人从一小事件出发,活画出清代社会政治的混乱。
除战乱、灾荒、官场恶浊外,清诗总集中也收录有一些反映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及民族冲突的诗歌,如贵州苗民叛乱、云南回汉冲突等。《国朝滇南诗选》中的《钩辀行为苗民作》,追述苗族的起源,在表现苗族群众孔武有力的同时也称颂他们在“今上宽仁同天地”“简循良”的时代背景下的“猺獞戴德安荒要”的生平景象。此诗后评曰“考据枣枣,足备风土志”[9]251-252。《黔苗歌》亦属此类,编者称其“与玉峰少宰《钩辀行》伯仲”。此外《滇八家诗选》中钱沣的《疾疫悲》(四首)、陈荣昌的《食人叹》、李坤的《乡泪》(四首)均描绘云南底层百姓的艰难与乡村的衰败,可证史书“食货”之志。
这些诗中所述内容,均可以在相关的地方志等史籍中找到依据,基本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如《乐山志》所载张献忠入蜀时嘉州刺史朱仪全家殉难之事,与《明嘉州刺史朱公象先阖门殉难歌》所述完全相同。综上,这些诗严格描述历史真实,情感诚挚,态度鲜明,是了解和研究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宝贵的历史材料,也是理解历史中人的心态、情感、境遇等的文学创作,是活的、具体的有细节、有情感、有温度的用诗歌写就的历史。
三、 “诗”“史”之偏向:“实有昧于诗人之旨”
“诗”与“史”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诗歌追求含蓄蕴藉、雅洁传神、情意真切,而“史”则要求语言平实、叙述客观、立场中正、感情节制。我国古代诗歌从来就不仅仅只是自我情感的抒发,而是要承载社会政治内容,是儒者关心民瘼、干预现实、表达思想的工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也。古典诗学思想中肯定诗歌社会政治价值的表述很多,如“诗言志”“观风观俗”“文以载道”“文须有益于天下”等。同时,记录现实,为后世镜鉴也是诗歌的功能,因此,“诗”与“史”在中国古代是很难分开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同时也是无韵之《离骚》;杜甫是“诗圣”,而他的很多诗又有“诗史”之誉。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上毕竟只有一马迁、一老杜,其他的文人、诗人,在这美学向度截然不同的“诗”与“史”之间如何取舍?表现如何呢?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这些堪称“诗史”的诗歌,其作为“诗”的美学品格如何呢?这是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云南人杨廷理在为自己的文集《东游草》作序时说:“古人以诗纪兴,作者兴会淋漓,精光万丈。予以诗纪事,据事直书,漫无含蓄。”[10]他说自己所写诗内容、形式均与古诗不同,不是写自己的兴发感动,而是在纪事,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写得比较直白,不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不讲求意象,也不锤炼词句。杨廷理的这段话可代表清代西南地区诗歌中有“诗史”之称的诗歌的主要风格:随意、散漫,不追求雅洁,不在乎是否蕴藉、浑融,更不会刻意锤炼字句,写作的重心在“纪”——纪人、纪事、纪行,目的在“用”。如蒋琦龄的《途中自检所作诗》:
我诗强半纪行诗,自笑无才还自知。境以寂寥翻有事,情非感动不能奇。
劳人思妇应缘此,风物山川若助之。安得如椽燕许笔,体兼众妙用皆宜。[11]
他说自己写的不是才子之诗,认为关心民瘼的题材与传统的思妇征人、山川风物题材一样是诗歌的表现范围。他期待自己的诗歌能如张说、苏珽那样有现实的社会政治之“用”。
因为更偏向“用”的创作目的,所以西南地区的诗人不惮直接发议论,如朱琦的“知人能官人,安民邦乃安”[2]260,张问陶的“贼有先声如唳鹤,官无奇策任亡羊”[3]285等。为了更真实客观描述清楚事实,诗人在诗题下加较长的小序,详细介绍此诗所记之人、事的背景,如《国朝全蜀诗钞》中张怀溎的《狗皮道人歌》等。有时候还在诗中大量加注,如莫友芝的《芦酒诗》《遵乱纪事》《哭杜杏东及其子云木三首》等后皆附有千余字的夹注。这本身就是诗歌写作偏于“史”,追求叙述真实、全面、详细的表现。编选者在选编这一类题材诗歌时也多赞扬他们议论时政的句子,如孙桐生称张问彤“梦里还家兵世界,病中愁日闰支干”“心肝不死忧家国,诗句无灵愧弟兄”两联“新雅”[3]349,称陈仕骐“其佳句如‘一口难评天下事,十年错读古人书’‘一寒至此知途马,三匝无依绕树鸦’,俱有风骨”[3]501。因此,可以说,我们古典诗学传统决定了选家和诗人都会比较看重这一类有史传内容的诗歌,而这一类诗歌因为重点和目的都在记录历史,反映现实,所以有意无意间放松了对诗艺的锤炼。
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这类诗作形式上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古体,以叙事为主,叙事以时间为线索,以抒情、议论结篇。语言平实显豁,基本不用典。古体诗形式自由,写作者容易将诗写得松散、直白、冗长,出现“叙事详明,惜欠简净古峭”[11]494,“无文聊纪实”[3]369-370,认识价值高于审美价值的情形。其实诗人也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诗歌审美性不足,如云南的师范就曾十分坦率地说:
此四十二年中,晦明风雨则有诗,困厄疾痛则有诗,登山临水、折柳投桃则有诗。盖凡耳之所淫,目之所摄,足之所径,心之所游,无不于诗发之。触景萌析随事抒写,无遥吟俯唱之暇,无月煅季炼之苦,轻浅疏率,实有昧于诗人之旨。[12]
师范17岁开始写诗,几十年间从未中断,写得很快,也很多,缺少认真的锤炼推敲,所以自己都感觉到“轻浅疏率”。西南地区有很多诗人学杜,但基本做不到诗、史的融合无间,但能保证是用平实的语言清晰地叙述事件或人物,再发表几句直白的感想,离杜甫的“诗史”还有不小的距离。这样的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要求有不小的差距,不容易产生经典,也很难被广泛流传。
尽管如此,西南地区清诗总集中的这些诗,其主要价值不在审美,它为我们提供的是大量入乎其内、丰富真实的清代历史细节,从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面对历史苦难与动荡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及渴望有所担当的精神。它使得诗歌有了温度,有了浓郁的与客观历史叙述有巨大差异的人心、人情。而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成为研究清代的西南,研究西南诗坛,了解西南地区政治历史、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
也必须要说明的是,除诗史价值之外,西南地区诗歌总集还具备诸多值得研究的其他价值,如它是考察清代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的样本之一,从中可见西南地区清人的女性观、西南地区士人对主流文化的态度,西南地区的民族接触与融合问题,边疆与内陆、边缘与主流的文化关系问题,西南地区清人对唐宋文学、文化的评价与接受问题,理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等问题。再如,清人学术的集大成、文学的集大成在诗歌总集中的呈现,集大成之后的古典文学的言志、缘情两传统的文学接续问题,各自占比如何等。总之,西南地区的清诗总集也许别有洞天,浸淫其间,也许会发现一个新的更开阔的文学研究世界。
--западе Кита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