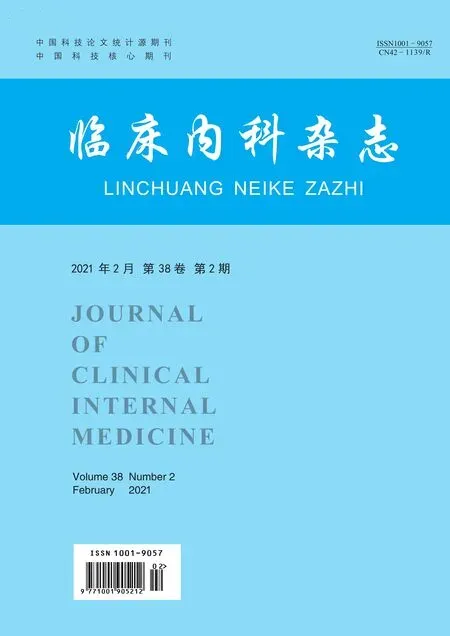克罗恩病肠道纤维化的发生机制
周峰 邓长生
克罗恩病(CD)是一种累及全消化道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肠病(IBD),为终身性疾病,全球范围内有数百万患者罹患CD。一方面,CD的肠道炎症能直接导致腹痛、腹泻、乏力和消瘦等典型症状;另一方面,CD的并发症、药物不良反应、手术后遗症及恶性肿瘤风险增加等也对患者产生间接影响。CD患者可出现狭窄、穿透、非狭窄/非穿透3种表型中的一种,每种表型对应不同的并发症。狭窄型CD患者的特点为肠壁增厚、肠腔狭窄,进而出现梗阻症状,需要外科手术干预,肠腔狭窄是CD患者的主要手术适应证[1]。
一、狭窄型CD的研究现状
不同CD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病程呈现较大差异性。近年研究表明,抗炎治疗对改善肠道纤维化有效,能够降低狭窄型CD患者的近期手术风险,但对其他并发症的治疗效果欠佳[2]。抗炎治疗仅针对肠道纤维化过程中的炎性因素部分,或影响纤维化狭窄病程中的诸多因素,其机制尚不明确。尽管目前开展生物制剂治疗已有20余年,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患者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治疗纤维化狭窄[3],且迄今还没有一种明确有效的抗纤维化治疗方法。对肠道纤维化发生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索新的治疗方法,降低CD患者外科手术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慢性肠道炎症是纤维化狭窄形成的基础病因,但由于并非所有肠道炎症都会进展为纤维化狭窄,因此促使炎症转变为纤维化进而狭窄的因素仍不明确。纤维化狭窄的肠壁厚度通常是正常肠壁的2倍以上。纤维化狭窄的形成是一个慢性过程,通常后期才表现出明显症状,因此很难在早期发现狭窄并对其进行干预。但可以肯定,纤维化狭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种细胞亚群、调节因子、患者身体状况及发病部位等均对这一过程的进展产生影响[4]。
纤维化狭窄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平滑肌层增厚及纤维化。病变肠壁各层的胶原沉积明显增多,尤其是黏膜下层可增厚2~3倍。浆膜下层的纤维化也会非常明显。黏膜肌层中纤维化和扭曲的平滑肌束相互混杂。固有肌层内间隔膜明显增厚并纤维化,但隔膜间平滑肌尚保持完整。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肠壁增厚的主因仍来自于平滑肌增生[5]。病变回肠肠壁各层平滑肌增生肥大较明显,而病变结肠肠壁中的黏膜下层和固有肌层的纤维化更加明显。另外,匍行脂肪也是CD病变的一个显著特征。匍行脂肪是指肠系膜脂肪包绕在病变肠壁周围,这些脂肪组织进入浆膜下层,接触外层固有肌,分泌出炎性因子助推肠道狭窄的进展[6]。
二、细胞在CD纤维化狭窄发生机制中的作用
在炎性狭窄部位可发现间叶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积聚和细胞学特征的改变,间叶细胞包括纤维母细胞、肌成纤维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它们对免疫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信号作出应答,同时也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反作用于免疫细胞。这3种间叶细胞均能分泌细胞外基质填充纤维化组织。
免疫细胞在CD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D患者非狭窄性肠黏膜中的免疫细胞,对于狭窄性肠黏膜中免疫细胞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显示,狭窄型CD肠黏膜中CD3+细胞明显增多,但其T细胞总数明显少于非狭窄型CD肠黏膜。儿童狭窄型CD患者肠黏膜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加幅度明显高于非狭窄型CD肠黏膜。同时,狭窄型病变部位巨噬细胞随着肌成纤维细胞的增生而明显增多[7]。
研究显示,部分T细胞亚群、B细胞及NK细胞等在纤维性狭窄黏膜中明显减少。CD是一种透壁性病变,炎性细胞不同程度侵入肠壁各层,对于黏膜层免疫细胞的研究明显多于肠壁其他各层,尤其对狭窄部位的免疫细胞功能及细胞间相互作用知之甚少。目前已明确的是,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在黏膜下各层浸润和增殖,巨噬细胞在纤维化区域明显增多,肥大细胞在黏膜下层和固有肌层聚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论均不完整,对于黏膜下各层次细胞的具体功能和细胞间相互作用仍缺乏了解[8]。
狭窄组织中主要包括3种间叶细胞,可根据3种标志蛋白——波形蛋白(vim)、肌间线蛋白(Des)和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进行区分,如纤维母细胞为vim(+)α-SMA(-)Des(-),肌成纤维细胞为vim(+)α-SMA(+)Des(-),平滑肌细胞为vim(+)α-SMA(+)Des(+)。免疫组化染色发现,狭窄部位黏膜下层和浆膜下层组织中α-SMA表达明显增多,提示纤维化组织中肌成纤维细胞积聚[9]。尽管黏膜层中纤维化改变非常少见,狭窄部位肠黏膜的间叶细胞的免疫组化染色仍有明显改变,如隐窝旁vim表达增加,固有层肌间线蛋白和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也增加,提示纤维化狭窄部位间叶细胞明显增多。当然,vim/α-SMA/Des这3种标志蛋白组合的分类模式仍显简单并缺乏特异性,更多的标志性蛋白正在被纳入,如纤维母细胞活化蛋白(FAP)[10],有助于间叶细胞的进一步细分。
三、纤维化组织中基因和蛋白的表达
肠壁组织中的细胞群有各自的相对比例、增殖部位和生物学功能。它们通过细胞间直接连接所产生的各种细胞因子而相互作用,对机械信号和微生物信号的感知更增加了这些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尽管纤维化组织中的转录基因和细胞因子种类繁多,但组织学层面的研究能给细胞及其分泌因子的来源研究提供诸多信息,有助于阐明狭窄的发生机制。
病理性狭窄的基本特征是平滑肌细胞肥大和纤维化。纤维化是细胞外基质沉积和降解失衡的结果,这种失衡直接导致胶原蛋白等大量积聚,而病变部位基因和蛋白(如纤维粘连蛋白)表达的改变则是纤维化的诱因,这些改变促进了肌成纤维细胞的迁入。同时狭窄部位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表达也发生改变,对于细胞外基质降解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MMP与其拮抗剂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TIMP)的平衡参与了CD纤维化狭窄的发生机制[11]。
肠壁中的各种细胞可通过细胞因子进行相互作用。狭窄肠壁中多种细胞因子表达发生改变,狭窄的结肠组织中抗炎因子白细胞介素(IL)-10表达增加,促炎因子IL-17、IL-6、肿瘤坏死因子(TNF)和多种趋化因子表达也有所增加;狭窄的回肠组织中IL-1β表达增加;狭窄部位黏膜层IL-1β和IL-17A表达上调,黏膜下层胶原蛋白分泌增多。转化生长因子(TGF)-β是一种主要的促纤维化因子,具有免疫调节能力,在病变肠壁各层表达均上调,研究表明,TGF-β主要由聚集的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产生[12]。
微小RNA(MicroRNA,miR)发挥着基因表达的负调节作用,一旦其调节作用失常,将影响很多关键的致病信号通路。研究显示,多个miR能够干预TGF-β信号通路[13],如CD狭窄病变部位的miR-141、miR-200和miR-429表达下降。因此,对尚未出现狭窄病变患者的基因表达进行研究,也许可预测其出现狭窄风险的可能性,对高危患者给予预防性治疗。
四、纤维母细胞及微环境与纤维化狭窄
纤维母细胞构成了连接组织,并分泌细胞外基质维持连接的稳定。胶原蛋白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尤其在纤维化狭窄部位。在损伤部位的生理性组织修复过程中,胶原蛋白替代临时纤维蛋白栓子,永久填充至受损组织中。通常情况下,机体一旦接收到组织损伤信号,就会启动自我修复过程,纤维母细胞被激活,进而增殖肥大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在完成修复后,纤维母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均出现凋亡。然而,在狭窄部位这种正常的修复过程会出现偏差,其原因为慢性炎性环境、微生物甚至食物等会给机体带来持续性的有害刺激,导致修复过程永久化,最后发生纤维化[3]。
研究活化纤维母细胞的刺激因素,就必须先了解影响纤维母细胞增殖和分泌胶原蛋白的细胞因子。这些刺激因素可以是机械压力的物理刺激、胞外基质的生物学信号、自分泌信号及旁分泌信号。狭窄部位的纤维母细胞较非狭窄部位增殖更加旺盛,可分泌更多的胶原蛋白[9]。
TGF-β由狭窄部位大量聚集的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分泌,并促进纤维母细胞产生更多胶原蛋白。纤维母细胞可表现出对TGF-β的过度反应,也可随着TGF-β不断活化表现出对其刺激的逐渐衰减。这种对TGF-β刺激的脱敏可能来自于内皮糖蛋白(Endoglin)补偿机制。另外,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1、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均能促进胶原蛋白产生。免疫细胞是这些刺激性细胞因子的主要来源,同时纤维母细胞自身对于这些刺激信号产生正反馈,进一步加速纤维化进程。狭窄部位的纤维母细胞凋亡程序更容易被破坏。IL-8是一种具有抗凋亡作用的趋化因子,狭窄部位的纤维母细胞在脂多糖(LPS)的刺激下分泌更多的IL-8,研究显示,toll样受体(TLR)4也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因此,CD患者黏膜屏障受损,也是导致纤维母细胞增长的重要因素[14]。C1q/TNF相关蛋白3(CTRP-3)是一种由肠系膜脂肪组织产生的抗炎脂肪因子,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天然TLR4拮抗剂。CTRP-3能帮助过高的IL-8分泌恢复正常,并减少其他促纤维化基因的表达。miRNA也能影响纤维母细胞的生长增殖,如miR-29b转染的纤维母细胞可分泌更多的IL-6、IL-8及多种抗凋亡蛋白[13]。
纤维母细胞反过来对周围的微环境也产生影响。纤维母细胞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作用于周围细胞,促进纤维化进展。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表达于狭窄病变部位,由纤维母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分泌,能够阻断免疫细胞与纤维母细胞等之间的作用,促进纤维化。前列腺素(PGs)在机体中发挥重要的生理学功能,狭窄部位的纤维母细胞合成PGD2明显增加,影响周围细胞的生物学功能。纤维母细胞同时分泌大量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促进血管生成,克服纤维化组织中的低氧环境[15]。
综上,纤维化过程起始于对黏膜损伤的良性修复反应,在特定的促炎信号及微环境下,出现活化纤维母细胞对免疫细胞刺激的正反馈,被炎症驱动的过程演变为促进炎症的过程。
五、肠道纤维化与其他器官纤维化
肠道狭窄病变的纤维化过程与其他器官的纤维化过程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如肾脏、心脏、肝脏和皮肤[16],最重要的特点是器官对持续或反复损伤后出现修复过程异常。与肠道纤维化一样,其他器官的纤维化也是与慢性炎症和肌成纤维细胞及细胞外基质的聚集。纤维化对所有器官损伤的最后结局都是器官功能衰竭,因此,对纤维化病程共性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多种疾病治疗的靶点。若能根除病因,肝纤维化过程可能会逆转,这为未来治疗CD纤维化提供了参考[17]。相对与其他器官而言,肠道纤维化也有自身特点:其他器官基本处于无菌状态,而肠道持续暴露于各种微生物、毒素及药物中;肠道是一个可收缩器官;此外,肠道中的纤维母细胞不同于其他器官中纤维母细胞。因此,对于其他器官有效的抗纤维化药物,并不一定适用于治疗肠道纤维化。
六、小结与展望
在CD患者中,修复肠壁炎症损伤的正常过程逐渐被扩大,难以调控并持续存在。这导致病理性细胞群出现,细胞外基质也持续累积,无法有效降解。与此同时,肌层细胞侵入纤维组织中,发生肠道狭窄直至肠梗阻。虽然目前已有不少治疗纤维化的手段,但仍有大量患者因纤维化狭窄而接受外科手术治疗。除了慢性肠道炎症,还有其他目前尚未可知的因素参与了CD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免疫细胞和炎性细胞因子虽然是启动纤维化狭窄的必要条件,但是狭窄病变部位的炎性活动度并不高[2]。纤维母细胞等非免疫细胞在病变部位明显增多,这些间叶源性细胞对纤维化微环境和狭窄形成具有独特影响。鉴于此,对于纤维化狭窄的治疗,不仅只是针对炎症和免疫细胞,也需要将间叶细胞纳入治疗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