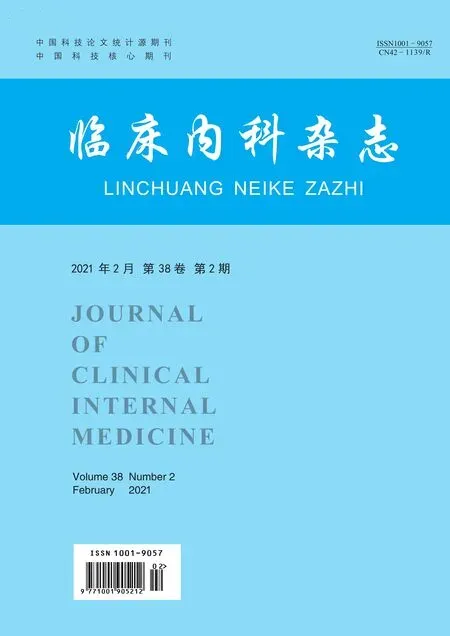克罗恩病与肠系膜脂肪
朱明明 冉志华
脂肪组织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被动储存和释放能量的器官,也被看作是主动的内分泌和免疫器官,可分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1]。目前研究发现,克罗恩病(CD)患者存在特征性的肠系膜脂肪组织(MAT)增生[2]。增生的MAT由肠系膜根部延伸,迁移至CD患者的肠道炎症病灶,向肠壁表面爬行样扩张,又被称为“爬行脂肪(CF)”[3]。CF作为一种高效的脂肪酸、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脂肪因子的产生者,在免疫和炎症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CD中CF也成为研究的热点,更好地了解CF在IBD中的机制和作用,将为寻求新的治疗靶点提供思路。本文对CD与MAT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克罗恩病与肠系膜脂肪增生
CD作为炎症性肠病的一种类型,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全层炎性疾病,可累及消化道任何部位,以末端回肠最为常见。上个世纪有研究发现,CD患者炎症肠壁周围存在异常的脂肪包裹,其从肠系膜附着处延伸,向小肠和结直肠肠壁表面爬行扩张,称之为CF,是CD的特征性表现[5]。CF的范围和肥厚程度与CD的疾病活动度、CD并发症、手术风险、疾病复发密切相关。Li等[6]采用CT观察CD患者术前和术后腹部脂肪组织的变化,发现高水平的MAT与术后CD早期复发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手术时肥厚的MAT常被外科医师用于判断肠管病变范围的解剖标志。有肠系膜脂肪增生的患者更容易形成肠腔狭窄,Mao等[7]认为这可能与增生的肠系膜脂肪组织分泌游离脂肪酸等介质,导致人肠成纤维细胞和人肠肌细胞的增殖有关。
在组织学上,CF表现为脂肪细胞体积减小、数量增多,同时伴有肌细胞肥大、纤维化、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血管周围炎性反应、血管壁增厚等组织病理学改变。与健康人群相比,CD患者肠系膜中脂肪细胞数量增加约4倍。除脂肪细胞(或前脂肪细胞)外,CD中的MAT还由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细胞外基质和丰富的血管组成[8]。
目前尚不清楚MAT是CD的始动因素还是肠道炎症造成的结果。尽管MAT中脂肪细胞体积减小,但抗炎细胞因子的表达更多,从而减少了炎性细胞的聚集,减轻了肠道的炎性刺激。此外,脂肪细胞的大量增生及肠系膜向肠管的包裹,除了可限制炎症蔓延,还可阻止肠道菌群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对受损的肠黏膜屏障功能起到补偿作用,限制全身炎症反应并降低穿孔风险。
二、克罗恩病肠黏膜屏障功能改变及细菌易位
在CD中,肠道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减少及淋巴、体液免疫异常均可导致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引起大量细菌移位,从而诱发系统的免疫应答。病变部位的MAT受到细菌和毒素的刺激而增生肥厚包绕肠管,以避免易位细菌的系统性播散,而脂肪细胞产生抗炎介质以控制局部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
近期,Suzanne Devkota团队[9]对手术切除的MAT标本研究发现了一组黏膜相关的肠道菌群Clostridium innocuum菌株,可持续移位至CF中并存活,认为CF最初可抵抗肠道损伤和细菌传播进入血液,但持续的细菌暴露又会促进MAT的纤维化,甚至导致严重的包裹肠道疤痕和纤维化形成。该研究更加支持了CF是CD的“果”的推论。
但也有不同论点认为肠黏膜损伤并不是CD发病的启动因素[10],该研究认为正常肠道内的细菌易位到MAT,由于基因层面的免疫应答缺陷,易感宿主MAT中的细菌不能被清除而引起慢性炎症,并将炎症逆行播散至肠黏膜,造成黏膜损伤和临床症状。而MAT作为易位细菌的储存器,提供了细菌大量繁殖并产生毒素的机会。但该假设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三、肠系膜脂肪与肠道固有免疫
脂肪细胞除了具有储存能量及分泌功能外,还具有免疫细胞的某些特点。MAT可在CD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菌群易位至肠系膜组织时,发挥其抗微生物的固有免疫防御作用。由于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受损,CD肠道的透壁性炎症使细菌能够转移到MAT中。前脂肪细胞和脂肪细胞均可表达功能模式识别受体,如Toll样受体(TLR)和核苷酸寡聚化结构域受体(NODs),它们通过释放一系列炎性反应和固有免疫的细胞因子来抵抗细菌。
TLR作为模式识别受体家族的成员,是识别肠道病原菌的主要受体,能够激活核因子(NF)-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等炎症相关信号通路,在肠道菌群介导的炎症反应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有研究证实,脂多糖刺激脂肪细胞、前脂肪细胞的TLR4后,能够增加白细胞介素(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CP)-1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经典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11]。
与TLR类似,NOD样受体也能够识别高度保守的非自身抗原。最近研究显示NOD激活与脂肪细胞分化有关[12],前脂肪细胞能够表达NOD-1和NOD-2受体特异性mRNA和功能性胞质受体,NOD-1和NOD-2受体已被确定为CD易感基因。
最近有研究显示,在IBD组中,肠系膜脂肪中辅助性T细胞(Th)1比例显著高于肠黏膜组织。只有回肠CF有明显的脂肪细胞增生并伴有T细胞浸润,与CD和UC中的结肠脂肪相比,回肠CF中调节性T细胞(Treg)和中枢记忆Th17细胞的比例显著升高,并发现疾病活动度与Th17/Treg细胞亚群的比例呈负相关[13]。
研究表明前脂肪细胞还能够转化为巨噬细胞,从而起到吞噬和抗菌的作用。单核细胞也可以通过MCP-1等的趋化作用,迅速在炎症反应部位聚集,并且参与组织的重塑。近期有学者发现C.innocuum菌株可通过M2巨噬细胞刺激组织重塑,从而导致脂肪组织增生来防止细菌的系统性传播[9]。
四、脂肪细胞因子
MAT中存在各种细胞,生成大量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及大分子物质,统称为脂肪细胞因子,具有内分泌、旁分泌和自分泌活性。在迄今为止已鉴定的脂肪细胞因子中,可能参与CD免疫炎性反应调控的包括瘦素、脂联素、抵抗素、内脂素、趋化素、胃饥饿素等。
瘦素是一种16 kDa肽,其分泌量与脂肪组织的量呈正比,主要内分泌功能是通过使下丘脑发出饱食感来调节食欲。瘦素可通过与TNF协同作用来激活巨噬细胞,并在嗜中性粒细胞中产生活性氧,发挥促炎作用。另外,它还调节Th细胞的分化,增加幼稚T细胞的增殖和记忆T细胞产生干扰素(IFN)-γ[14]。虽有研究发现CD患者MAT表达和分泌的瘦素明显增加,且UC和CD肠道组织中瘦素mRNA表达亦有增加[15],但多数报道认为CD和健康对照者之间的血清瘦素并无差异,这可能表明IBD中瘦素的上调仅出现在肠道内而非全身组织。
脂联素也是一种几乎仅由脂肪细胞分泌的多肽,具有抗炎和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脂联素水平降低可致肥胖,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另外,脂联素与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的发生有关。既往研究发现,IBD患者组织中脂联素的表达水平增加,而非全身水平[16]。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回肠型CD和远段回肠正常的CD患者相比,黏膜组织中脂联素的表达反而降低[17]。鉴于脂联素存在多种分子量不同的同工型,其各自的作用仍不清楚,目前尚缺乏研究评估特定脂联素同工型在IBD中的作用。
抵抗素最初在脂肪细胞中发现,但主要由脂肪组织内外的巨噬细胞表达。抵抗素通过调节NF-κB信号通路来上调IL-6和TNF-α的表达,从而表现出较强的促炎活性[18]。此外抵抗素还可促进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等黏附分子的表达从而引起单核细胞的聚集,导致炎症发生。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患者的抵抗素水平明显升高。但IBD和其他以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憩室病和大肠癌)之间的血清抵抗素并无明显差异,表明抵抗素可能是炎症的非特异性标志物。
内脏脂肪素作为一种新发现的脂肪细胞因子,具有模拟胰岛素样的降血糖作用,参与炎症应答、调节脂代谢和自分泌、旁分泌、内分泌等功能。与对照组相比,在CD和UC患者中发现血清内脏脂肪素表达明显升高。Starr等[19]在99例初治IBD患儿的结肠活检组织中发现内脏脂肪素的表达水平较高。此外,Moschen等[20]报道在UC和CD组织中内脏脂肪素表达均增加,还可上调单核细胞产生的IL-1、IL-6、IL-10和TNF-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内脏脂肪素可作为单核细胞和B细胞的有效趋化因子,以及抗原呈递细胞、吞噬细胞和T细胞的激活剂,这使得内脏脂肪素成为潜在的治疗靶标。
五、肠系膜脂肪与IBD临床病程及治疗结果
自从1992年Sheehan等[5]最早证明肠道脂肪包裹与溃疡、狭窄形成、壁厚增加与CD透壁性炎症有关后,陆续有学者证实了MAT与CD活动度的相关性。Li等[6]通过CT扫描量化,证实肠系膜脂肪与CDAI及CRP等CD疾病活动指标密切相关。此外,从PRISM数据库对482例CD患者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内脏脂肪(VF)的数量与发生穿透性疾病的风险相关[21]。在小儿CD患者中也有类似的趋势,Uko等[22]的研究显示,具有较高VF值的儿童发生瘘管和纤维狭窄的风险增加。同时,患儿住院的频率和疾病活动度也更高,需要更早的手术治疗。此外,内脏肥胖亦是接受肠道切除术后住院时间延长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前关于CD常见治疗药物对MAT作用的研究不多,Holt等[23]通过CT成像研究肠系膜脂肪组织和6-硫鸟嘌呤核苷酸(6-TGN)水平的关系,发现作为硫唑嘌呤的代谢产物,6-TGN的水平与脂肪部位为皮下或内脏无关,这表明巯嘌呤治疗对MAT的分布几乎没有影响。
相反,肥胖和生物制剂达到最佳疗效之间有相关性。研究发现,BMI增加1kg/m2,可使治疗失败和手术/住院风险增加4%和8%[24]。然而,来自4项大型临床随机试验的汇总数据显示,肥胖的IBD患者对英夫利西单抗的反应并没有更差,但该研究并未区分皮下脂肪(SF)组织和VF组织,而单凭BMI值无法说明问题[25]。一项对97例接受英夫利昔单抗诱导治疗的CD患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更低的VF是黏膜愈合的独立相关因素,而非SF[26]。该研究表明,生物制剂的疗效可能受体脂分布的调节。该团队还通过磁共振小肠成像(MRE)监测MAT,发现MAT的减少与临床症状和生化指标的改善相一致。
目前,在IBD中尚无专门针对内脏或MAT的治疗策略。近年来发现,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γ与MAT中的脂肪细胞增生有关,其在CD患者的MAT中表达上调,而在SF或健康对照者中则无此变化[27]。对PPAR-γ的刺激是多因素的,可能是由于肥胖、大量脂肪酸摄入以及细菌产品激活TLR4所致,以上均可导致CF的发生。然而,通过药物阻断CD患者中的PPAR-γ信号通路目前不可行,因为PPAR-γ对于维持上皮细胞表达β-防御素-1(DEFB1)是必需的。
六、肠系膜脂肪的临床检测和应用
在临床工作中,CF对鉴别诊断CD、协助诊断CD的疾病活动度和病变累及范围、预测疾病复发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超声、MRE和计算机断层扫描小肠成像(CTE)等方式来测定CD患者的VF面积,以间接获得CF面积并研究其与CD的关系。
肠系膜脂肪指数(MFI),即VF与SF的比率已被提议作为复杂CD的生物标志物。Erhayiem等[28]的研究结果表明,MFI为0.29对鉴定复杂C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3%和81%。
Ko等[29]用CT定量测量VF与SF面积,并计算两者的比值,发现CD与肠结核患者的VF/SF比值有显著差异,通过腹部CT分析CF可作为鉴别CD和肠结核的一种非侵入性且简单经济的方法。Frivolt等[30]通过磁共振(MR)脂肪定量证实腹内脂肪组织的扩张与疾病的复杂性及其持续时间有关。徐锡涛等[31]通过能谱CT定量分析,探讨回结肠CD的CF与炎症活动及预后的关系,认为能量谱CT定量分析CF是评价CD患者炎症反应的有效方法。
目前的影像学手段仍较难区分正常肠系膜脂肪与CF,因此仍期待一些更好的对CF进行识别和评估的新兴技术的开发,如MR波谱成像、基于人工智能的放射性组学等。
七、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无论在形态学还是细胞水平,MAT增生在CD发病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与CD的严重程度、并发症和预后密切相关。其通过改变局部细胞因子和激素环境,发挥炎症和免疫调节活性。随着对CD患者MAT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针对MAT的靶向治疗可能会成为CD治疗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