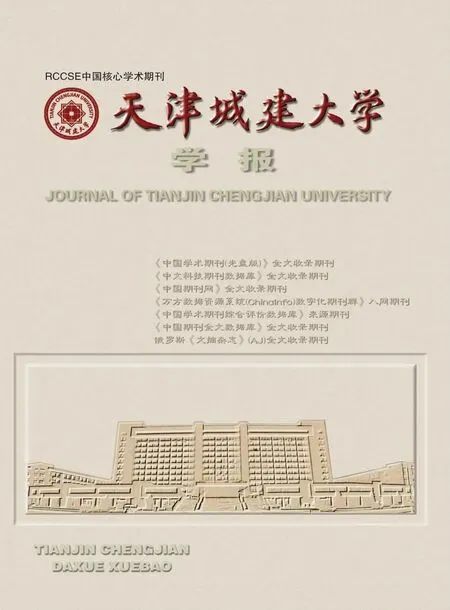艺术、理性与社会进步:贡布里希美术史思想的内部张力
张清莹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恩斯特·汉斯·约瑟夫·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于1909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信仰新教的犹太人家庭.1928年,贡布里希进入维也纳大学,师从施洛塞尔学习美术史,后移居英国.从1950年出版的《艺术的故事》,到在其去世后才出版的《偏爱原始性: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贡布里希发表了数十本著作和演讲集.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详细阐释了再现问题、错觉主义、概念图式、“先制作后匹配”、“观者的本分”、投射等问题和观点,这本书构成了其学术体系的重要基石,也奠定了他的思想家地位.中国著名的贡布里希研究学者范景中曾经提到,《艺术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2000年英美的几家杂志用民意测验的方法推选影响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百部著作,艺术著作入选的仅有这一部.它已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而中文译本竟有四种.”[1]毫无疑问,贡布里希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术史学者之一.
1 宏大叙事的“反叛者”
贡布里希出身在维也纳一个信仰新教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钢琴家,两位姐姐,一位是小提琴家,一位也是律师.1936年1月,贡布里希在恩斯特·克里斯的帮助下来到英国,1947年他加入英国籍.这样的经历使得贡布里希更加相信科学而非宗教的力量,或许这是他在世界观上选择波普尔式的、证伪和试错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而非源自神学的现代性场域所统辖的宏大叙事观念的原因.事实上,贡布里希的思想远非整个人类社会的元叙事,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承认有历史存在.他在《阿佩莱斯的遗产》中指出,艺术史是建立在连续的,后人学习前人技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艺术家都是在历史中通过不断学习前人再现世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绘画技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史”根本无法成立.但贡布里希没有止步于此,他对于(艺术)历史的建构性有充分的自觉反思.贡布里希指出,“无可否认,瓦萨里论述艺术手段的发展,有时加进了自己的事后认识.在几段文字中,他认为从前的艺术家对自己的技法不满,而这种不满只有他们能预见到后来的改进时才会感觉到.”[2]事实上,后来人对于再现自然的技巧其进步性并不由于满足了前人的遗憾而得以完成,相反,其合法性来源于“后来人”的自我叙述.他认为,后人虽然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绘画,但在历史中这常常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命名和界定——后人通过发展更加先进的技巧,将本来是学习对象的前人指认为落后的、缺陷的和不完满的,从而确定自身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我们不断在历史中,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中,在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中看到这样的故事,即后来者通过指认先在者为他者从而自我确认.
贡布里希并不相信宏大叙事下完整的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叙述中的因果逻辑和归纳总结始终持有怀疑,他反而是着重阐释历史建构中的裂隙.他提到,“瓦萨里没有告诉读者,他撰写历史时,是有意把十六世纪的艺术再生去映照古典世界已然见证过的模仿自然的进步.”[3]他在论述“偏爱原始性”的问题时将现代艺术归结为人类对于原始性的追求,但强调批判关于文化的进步逻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原始”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或许其意味着技巧的单纯性,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原始艺术作品的价值低于技巧先进的艺术作品.
贡布里希提到,文艺复兴之父乔托并非“从天而降”开启了美术新纪元,乔托正是受到被贬低为黑暗世纪(Dark Ages)的拜占庭艺术家和北方的雕刻家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艺术.贡布里希认为现代艺术也是学习先人再现方式的产物,而非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与传统艺术决裂的结果).因此,文艺复兴是复兴自古罗马也是一种说法而已.他指出,“在意大利人心里,复兴的观念跟‘宏伟即罗马’的观念的再生息息相关.……意大利人的那些观念事实上没有什么根据,至多也不过是对实际事件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化的粗略描述.”[4]
2 艺术、科学与社会进步
在出版《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也被翻译成《世界小史》)后50年,贡布里希写下《50年后的后记:我在这期间所经历和学习的》.在这篇后记中他反思了在维也纳度过的岁月里,他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多么不假思索:
“我的错误多么严重,多么令人遗憾,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当时没有料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战败国各国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信念,认为是一个骗局使他们陷入了悲惨境地的这种信念,使野心勃勃的蛊惑人心者有机可趁,将失望情绪变为愤怒和狂热的复仇心理.我很不愿意叫出这些蛊惑人心者的名字,但是毕竟人人都知道,我在这样说时主要想到的是阿道夫·希特勒.”[5]
贡布里希区分了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进步——很显然,贡布里希并不认为再现/绘画技术的进步会导致艺术品价值的提高.贡布里希曾经提到,黑格尔的目的“是要证明对普遍理性信仰的正确性,而这种信仰在他看来不但必不可少,而且宽慰人心.在他的哲学中,决定一切历史事件的乃是那些稳步进化的原理.黑格尔试图表明艺术的历史也可以根据这些原理来看待.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6]贡布里希沿用波普尔的哲学体系,对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他显然认为艺术并没有在价值上沿着某种道路前进并达到特定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贡布里希在演讲中常常用科学来类比绘画技术,“艺术技巧进步-艺术品价值”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文明进步”在贡布里希这里形成了某种同构的关系.在讨论艺术的本质时他提到,就像在科学领域强调“电”或者“能源”的本质非常无用那样,在讨论艺术概念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应当被摒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贡布里希明确地意识到,绘画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艺术本身的进步.但面对科学的进步,贡布里希几乎不假思索地肯定了理性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对于现代化进程、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贡布里希也曾经在《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中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提及原子弹作为20世纪文明尖端成就却成为了人类灾难的来源时,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的确遭遇了二次世界大战,遭遇了理性成果被运用到高效毁灭人类的行为之上,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也是科学和技术,是它们使有关国家得以至少部分地弥补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致使正常生活比人们敢于希望的还开始得早”[5].提到医学进步和现代化进程时,贡布里希进一步指出,“欧洲、美洲还有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因此而忘记,这也促成了多少福祉——是的,福祉.”[5]
相对于这两对存在巨大差异但十分明确的关系,贡布里希对于艺术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显得异常暧昧.首先,他认为艺术史记录的是艺术家们如何改进再现技巧的历史,而非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艺术并非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在艺术史上也体现为某种正相关的“艺术的进步”.另外,在他看来,即使艺术作为一个非时间性的整体,席勒所指认的美育对于人(和整个社会)的进步作用,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已经被证伪——太多的,如戈培尔、戈林等残暴的纳粹军官都具有相当深厚的艺术修养——如果我们认为艺术对于人的文明化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将无法面对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
与此相对的是,贡布里希自觉接受了“人文主义守卫者”的身份指认,而他的研究者(以及批评者)也普遍将他评价为“理性主义斗士”.杨小京在《偏爱原始性》的译者序中提到,贡布里希是一位原始主义者,他反对当下的道德相对主义并坚持要回到文艺复兴意义上的文明和理性概念,他始终持有(艺术史上的)保卫启蒙的立场[3].学者穆宝清也在论著《贡布里希艺术美学思想研究》中指出,“贡布里希强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始终受到各种非理性和狂热思潮的威胁,人文学者的责任就是借助理性的探索和科学的公正去抵制和反抗这些恐惧力量.[7]”
贡布里希反复强调他了解20世纪反思理性的风潮,强调对西欧文明中那些“可怕的东西”有充分的了解,但同时,他在演讲中提到他将“为西欧的传统文明而战”:
“我认为美术史家是我们文明的代言人:我们想对我们的艺术精华(奥林匹斯山)知道得更多一点.记忆那些精华是我们的责任,但还不仅如此.我批评过说我们逃避现实的人,如果我们不能逃到伟大的艺术中寻求安慰,那生活就不堪忍受.人们应该怜悯那些与往昔遗产脱节的人,人们应该为自己能够聆听莫扎特的音乐和欣赏委拉斯开兹的绘画而感恩,并怜悯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1].”
贡布里希将艺术对社会作用的暧昧解释为人在理性与感性徘徊时的不稳定性.当我们作为理性个体追求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时,艺术将成为我们求索的阶梯.而当我们耽于激烈的感情,不理智的情绪,那么即使艺术也无法将我们引入正轨——显然纳粹的罪行属于此类.
3 对“理性斗士”的反思
1989年,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
“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事实上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正常’所指的是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8]
在前文中我们梳理了贡布里希关于艺术、科学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巨大张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张力一方面动摇了贡布里希的原本牢固的“艺术技术进步与艺术非进步”观念,在另一方面,也无法在根本上处理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与遗产.
首先,贡布里希在晚期著作《偏爱原始性》中提到,“二十世纪人们对进步的价值有了根本不同的观点,不过,并不妨碍我们承认,技术的进步,科学的进步,还有战争手段的进步等,都是我们文明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3].结合上文中贡布里希对于科学技术的肯定态度,“发展”在贡布里希的话语体系中应当被指认为某种形式的进步——那么,贡布里希是否将艺术家对于再现技术的进步纳入技术的进步当中去?如果没有,在与艺术价值脱钩之后,我们又将如何评价再现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其次,贡布里希把极权理解为非理性的观念也并非坚不可摧.贡布里希指出,人类的非理性特质是20世纪暴行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20世纪的灾难是“我们还不够文明”的结果.他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与20世纪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艺术主张联系在了一起,认为自浪漫主义以来的感性狂潮与历史决定论的叙事一同成为了现代艺术的幕后推手,并导致了(如未来主义等)非理性艺术思潮.在艺术上,未来主义宣称要摧毁博物馆和往昔的遗产,对追求理性的传统艺术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就像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指出的那样,尽管浪漫的非理性主义者拒绝了“进步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哲学乐观主义”,他们仍然是在追求某种现代性论域中的立场[9].伯林也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指出,浪漫主义运动在当代的两类分支分别是存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即使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的对立面,它始终也无法摆脱其现代性的出身.
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贡布里希所指认的非理性狂热,正是理性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正如福柯在《“全体与单一”——走向政治理性批判》中所说,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并非清晰可鉴,甚至将理性和非理性对立起来的行为是徒劳的.福柯指出,“理性化与政治权力的泛滥之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联系.我们也无需等待科层制或集中营出现才来辨识这种关系的存在”[10].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看待大屠杀问题上,对于理性及非理性关系的普遍误读.他指出,大多数社会学家持有和他(在研究大屠杀历史)之前相同的看法,认为大屠杀在20世纪的发生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11].这样的观点认为大屠杀并不具有代表性,和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也并没有关系,只是人类文明调控的暂时性失效而已.
另一种相关的看法是,大屠杀是文化还没有能够完全抹除的、人类原始的“自然秉性”,由此,大屠杀成为了“人类不够文明”的例证.那么,使人类得以摆脱此类悲剧的方式就自然指向了回归理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贡布里希思想的影子,和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威尔海姆·赖希,后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受到压抑,在异化过程中产生的非理性排斥,20世纪的灾难是人性的灾难而非政治或者体制的灾难[8].
而事实上,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却正是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最普遍的性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明的结果,而非文明的对立面.种族屠杀计划本身并非如恐怖分子的行动那样,是为了死亡而死亡——相反,纳粹党制定的一系列惨绝人寰的计划,本身具有着现代意义上的优越性——这是他们能够想象的最有效率、最理性的计划,而他们也依靠最现代化的工具(如焚尸炉)完成了这样的计划.
4 结语
当贡布里希说,“如果我们不能逃到伟大的艺术中寻求安慰,那生活就不堪忍受”[1]时,已经在身体经验上不可避免地将理性当作生活的希望和慰藉.卡林内斯库曾经指出,现代性深植于现代化进程之中,而民族主义正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9].不仅民族主义,甚至是贡布里希所反对的当代艺术——那种普遍的享乐主义和对于瞬时快感满足的崇拜,其根源都在于作为一种体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复杂和含混也正是贡布里希的含混,当贡布里希选择拥抱理性的一端而否定另一端时,他所建构的美术史体系内部就已经暗含了张力与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