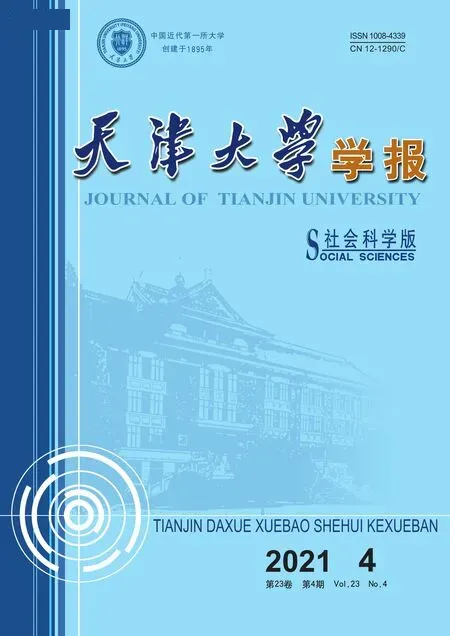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视域拓展
马知遥, 王明月
(1.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300072; 2.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传统工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为生活的日新月异而欣喜,也不免为传统工艺严峻的生存危机而感伤。幸而,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工艺出现了旅游工艺品化、艺术品化等新的发展趋势,在危机中发现了回归生活的多种可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尤其是2017年以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传统工艺振兴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工艺由此走上了复兴的“快车道”。
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并不是返回某一历史节点的工艺发展状态,而是以当代生活为落足点,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工艺获得新的广泛应用。在此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传统工艺走出原有的生活空间,在艺术界、时尚界等领域衍生发展;也看到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了工艺知识的多元化。可以说,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呈现出很多新的时代特点。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进程中,有哪些新趋势亟待传统工艺研究进行解答?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对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给予很多关注,但是对其给传统工艺研究带来的冲击仍然缺少更深入的探讨[1]。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案例,从文化、语境和人三个维度分析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亟待探索的问题领域,探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视域拓展方向,以期为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持。
一、 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时代诉求
1. 中国传统工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中国传统工艺历来是民俗学、人类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工艺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各区域的传统工艺展开了早期的民族志研究。诸如鸟居龙藏对贵州苗族蜡染技艺的记述、史图博和李化民对浙江畲族银饰制作技艺的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对湘西苗族传统工艺发展状况的描述等,都较为详实地呈现了当时各区域生活中手工艺品的制作与使用状况,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志基础。
在此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注重对中国传统工艺的理论阐释,形成了工艺文本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出发,探寻传统工艺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张道一等[2]学者较早便致力于探讨剪纸、印花布等民间工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义。这些研究对探索传统工艺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随着研究的推进,这种研究范式因为将传统工艺抽离出具体的时空环境,孤立地进行文献考据而受到质疑。此外,由于聚焦于工艺本体,作为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民众往往在这种研究中被忽视和遮蔽。
面对以上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传统工艺经历了由工艺文本研究向语境研究的范式转换[3]。语境研究将传统工艺置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解读其文化意义与功能,对于理解传统工艺与民俗文化的整体性关系具有重要价值[4],已成为当代传统工艺研究的重要范式。正是在回归民俗语境的过程中,学界逐渐意识到作为手工艺品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民众的主体性。正如张士闪[5]所言,再有力的国家行政运作,也无法改变民俗的民众主体地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民俗的民众实践性质与总体发展态势。近年来,学术界对民众的手工艺品消费[6]、工匠的造物活动[7]等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众逐渐在研究中凸显其重要性。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工艺研究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以语境研究为重要范式,注重传统工艺与民俗生态的整体性关系,强化对民俗主体——民众解读的研究特点。
2.传统工艺复兴背景下学术研究的视域拓展诉求
当代,在互联网技术和便捷交通的支持下,多元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各种文化元素超越了民族的、地方的时空限制,或走向艺术世界,或嵌入旅游产业,或融入时尚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在这富于流动性的生活中浸润于多元文化,拥有多元化的知识与资本,具备愈发强大的个体选择和行动能力。在这样一个多元、流动且异质的生活中,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也对中国传统工艺研究提出了视域拓展的诉求。
(1)传统工艺变迁的剧烈性。历史上,诸如纸扎、印染、造纸等传统工艺大多嵌入变迁节奏较为平缓的社会生活之中,工艺文化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然而,这种发展节奏被现代生活日趋快速的变革打破。各种类型的文化打破时空的界限发生紧密的互动,造成知识和技术大量而快速的传播,加剧了各领域工艺文化的变迁速度。如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的古法造纸技艺曾是当地民众重要的生存技艺,历史上石桥村的白皮纸制造技艺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工艺传统。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围绕古法造纸建立了古法造纸文化旅游景区,古法造纸开始快速变迁。基于游客的消费偏好和审美需求,当地工匠将花草植物与造纸技艺结合,创造了花草纸,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笔记本、贺卡、书籍等衍生产品。这些新的旅游工艺纸品已成为当地旅游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也使石桥古法造纸技艺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审美偏好给石桥村古法造纸带来了生产工序、产品种类与审美标准等前所未有的快速变革。一如石桥古法造纸技艺,很多传统工艺正处于这种愈发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在对传统工艺与民俗生态的关系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解释工艺文化的演变过程。
(2)传统工艺发展的多元性。传统工艺在国家、市场、民众等力量的综合影响下跨越了文化边界,在艺术、旅游消费、流行文化等领域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贵州丹寨蜡染①为例,丹寨蜡染本是表征其族群身份的重要符号,嵌入白领苗的文化中。近年来,在商人和设计师的介入下,白领苗蜡染技艺一方面被广泛应用于桌布、桌旗、文化衫等旅游工艺品的制作中。另一方面,它引起了设计师的广泛关注,他们运用时尚界的艺术手法对白领苗蜡染进行新的诠释,并将其融入到时装设计之中。2020年,丹寨蜡染服饰作为中华民族时尚的代表,登上了伦敦时装周,呈现出融入时尚文化的趋势[8]。事实上,类似于丹寨蜡染,很多传统工艺都在积极地融入多元文化领域,以此拓展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存空间,从而走上了复兴的道路。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原生语境和其他新语境中传统工艺的关系?又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当代中国传统工艺复兴对传统工艺语境研究提出的新命题。
(3)工匠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工匠是民众之中特殊的一类群体,他们是传统工艺的实践者,满足社会对手工艺品的需求。历史上,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曾高度整合着工匠群体,使其在社会地位、技艺知识、造物活动等方面具有相对的同一性[9]。然而,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复兴进程中,工匠走出了相对单一的生活空间,游走于多元的社会生活领域,经历了更加复杂的个体生命历程。他们在角色选择和造物活动等方面表现出日趋明显的个体差异。以天津东丰台木雕工匠GHS和GML②为例,二人曾在天津市外贸公司的组织下前往河北曲阳学习仿旧彩木雕制作技艺,学成归来后一同进入宁河区丰台镇美术雕刻厂,从事仿旧彩木雕的雕刻工作。1990年代,雕刻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GHS依靠做工时的私人关系与潘家园文玩市场的老板建立联系,此后10余年一直为其手工制作仿旧彩木雕,以此维持家中生计。直到2013年前后,他学习并掌握了棺材制作工艺,转行开起了棺材铺。GML在雕刻厂倒闭后带着木雕作品闯荡潘家园,同样为老板们制作仿旧彩木雕。不过,他并未满足于此,后来到浙江等地做木雕学徒,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经营经验,之后回村开办了雕刻厂。近年来,GML吸取浙江企业家的办厂经验,引进了全自动雕刻机,从事木雕工艺品的批量生产。可以看到,雕刻厂倒闭后,二人的木雕生涯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在木雕制作策略方面同样存在明显差异,这打破了人们对工匠群体的传统认知习惯。综上所述,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促使传统工艺研究对一些发展的新趋势予以更多关注。若能围绕这些新趋势,对传统工艺的文化、语境、实践主体等重要问题进行反思,拓展当代传统工艺的研究视域,无论对深化传统工艺的研究,还是对助推传统工艺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 从文化关系到文化实践:文化维度的视域拓展
当代工艺文化变迁的速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工艺文化研究迫切需要从文化关系研究向文化实践研究延伸,对当代传统工艺的动态发展过程作出更深入的解释。
1. 列举式文化关系研究的困境:布依族蜡染的研究反思
目前,传统工艺与民俗生态的整体性关系已经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张士闪等人[10]均提出过二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性,但是当前很多研究往往仅以一种列举式的方法说明传统工艺与其他文化元素之间静态的文化关系。这种研究取向在面对当代充满异质性而又剧烈变迁的工艺文化时,欠缺足够的解释力。笔者在对贵州省安顺布依族蜡染的研究中便经历过这种研究困境。
安顺布依族蜡染是布依族第三土语区民众广为使用的蜡染技艺,主要图案有狗牙纹、水涡纹、方块纹、散点纹等。这些图案依据布依族的文化传统有规则地排列组合,构成了布依族蜡染的图案结构。在调查之初,笔者希望理解这些图案的意义,想象着这些图案是否与当地布依族的族源历史、神话传说、民间信仰等存在联系。可是经过多日的调查,笔者竟然找不到一位能够对此作出解答的村民。最终,一位伍姓中年男子给笔者解答了这一问题。经过多日相处,笔者与这位中年男子逐渐熟悉,成为关系较好的朋友。他才向笔者坦诚,所有图案的意义都是他耐不住笔者的好奇心而杜撰出来的。蜡染图案的符号意义只有少数几位只会讲布依语的老人知道,其他村民只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婚礼和葬礼必须要使用它而已③。
这件事让笔者恍然大悟,布依族蜡染曾经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基本已被历史吞噬,几近消失,当地民众在乎的也只是蜡染对他们当下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与其追寻那些远离生活的意义,不如探寻当下布依族民众是如何看待蜡染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笔者了解到当地蜡染文化的基本形态,由于对汉装的广泛接受,布依族蜡染已经不再用于满足当地民众的实用需求了。不过,它仍然在布依族的婚礼和葬礼等重要的生命礼仪中得到保留。它被当地民众认为是生者与布依族祖先相互识别的符号,在布依族的婚礼和葬礼中承担着与祖先交流的功能。在婚礼中,布依族的新娘要身着蜡染盛装完成婚礼仪式。在葬礼中,逝者家的儿媳妇则要身着蜡染盛装为逝者“引路上山”。
当笔者认定这就是布依族当下的蜡染文化时,当地民众的蜡染文化实践再一次引发了笔者的反思。2016年11月30日凌晨3时,一场布依族婚礼正在安顺市镇宁县石头寨进行。新娘在进家门前一直身着西式婚纱,直到进家门的仪式中,才在婚纱外穿上布依族蜡染盛装完成了仪式。第二天的婚礼正席,新娘又换上了西式婚纱迎宾。笔者发现,当地民众在婚礼中并没有严格遵循他们所表述的布依族蜡染文化传统。新娘显然更喜欢身着西式婚纱,只有在进家门等需要与祖先沟通的仪式时才穿着蜡染盛装。可见,各种新的文化元素(如西式婚纱)已渗透到布依族的日常生活。面对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当地民众的蜡染文化实践远比他们所表述的蜡染文化传统更具选择性和变化性。而且,也正是在对工艺文化传统的“变”与“不变”的选择中,布依族蜡染与当代生活完成对接,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以文化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布依族蜡染,或许会寻找到布依族蜡染与当地布依族祖先崇拜、生命礼仪等方面的关联性。然而,当整合出布依族蜡染文化的这种“理想模型”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抹杀掉民众的文化实践,以及它所带来的布依族蜡染的动态发展特点。在工艺文化变迁愈发剧烈的当代生活中,这种列举式的文化关系研究显然有些捉襟见肘。
2.作为文化实践的工艺文化
布依族蜡染的案例反映出列举式文化关系研究困境的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新的路径。我们看到,布依族民众在主动进行文化选择与折中,这使布依族蜡染得以动态适应当代生活的节奏。它反映出工艺文化研究从文化关系向文化实践延伸的重要性。在工艺文化实践的视角下,工艺文化与民众的关系将发生调整。民众从曾经的工艺文化事象遮蔽下的无形傀儡,转变为主动调适工艺文化的实践主体。工艺文化的研究对象由此从工艺文化事象转变为民众的主体实践过程。民众如何在异质性的当代生活中运用并调适工艺文化,将是工艺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以民众的主体实践为轴心,看似静态的工艺文化转变为动态运转的文化过程,这便为解释工艺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剧烈变迁提供了路径。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当代复兴进程中传统工艺的发展轨迹与逻辑。
三、 多元语境联动:语境维度的视域拓展
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进程中,传统工艺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学术界需要以多元语境联动的理念进一步深入解释传统工艺多元语境共生的整体发展状态。
1.界限与关联:中国传统工艺的多元语境共生
当前,各语境中的传统工艺呈现为既相互区别又紧密互动的发展状态。以贵州省安顺小花苗蜡染为例,小花苗蜡染曾是安顺的苗族支系——小花苗在日常生活与重要仪式中大量使用的手工艺品,具有特定的蜡染制作工序和图案传统。20世纪60年代,小花苗蜡染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成为供国外消费者赏玩的出口创汇手工艺品。改革开放以后,小花苗蜡染则在设计师的包装下融入旅游产业,成为供旅游者消费的旅游工艺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花苗蜡染技艺又与国画、油画等绘画艺术结合,融入到蜡染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到21世纪初,安顺小花苗蜡染已经实现了在族群生活、旅游、艺术等多元语境的共生发展。
小花苗蜡染在各语境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存在形式与文化意义。在族群生活之中,蜡染被小花苗民众视为与祖先相互识别和沟通的重要符号,具有特定的工艺传统和审美标准。在旅游语境,蜡染则与旅游者的审美情趣紧密联系起来,转而成为满足旅游者异域风情想象的旅游工艺品。在艺术世界,蜡染则嵌入由艺术观念与专业性的艺术组织维持并运转的艺术体系之中,成为符合艺术审美标准的艺术作品。
以小花苗蜡染工匠为例,他们在族群生活中以生产销售小花苗传统蜡染为生。后来,一些工匠或转型成为从事旅游工艺品生产的蜡染工人、企业主和个体手工业者,或成为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或辅助画工。多元语境中的职业经历,让他们掌握了更加多元的工艺知识,获得了更强的创新能力。目前小花苗的彩色蜡染服饰便是一些工匠在旅游工艺品公司打工期间掌握化工颜料的使用技能后,以其改良小花苗传统彩色蜡染服饰的产物。这一创新活动并未因为化工颜料的引入而受到小花苗民众的指责,反而因为色彩更加鲜艳而受到认可,成为小花苗蜡染的新传统。
安顺小花苗蜡染的发展实则是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量的传统工艺正在或已经经历这种多元语境共生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民众在语境内部共享着一套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规范,这种规范限定了传统工艺的符号意义、制作和使用方式、受众群体、文化功能等。另一方面,民众持续在多元语境间流动,对传统工艺的相关元素进行频繁的借用和转化,从而使各语境构成紧密联系的整体。可以说,多元语境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状态,已成为当代复兴进程中传统工艺发展的常态。
2. 传统工艺语境研究的分析方式及解释效力
面对这种多元语境共生的发展状态,目前的传统工艺语境研究缺少足够的解释效力。具体而言,传统工艺的语境研究具有三种主要的分析方式:其一,有的研究以语境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单位,将各语境视为自成一体的社会文化领域,探讨语境中传统工艺的制作和使用状况。历史上,某些传统工艺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或许具有在单一语境中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安顺小花苗蜡染个案所反映的,在人口快速流动、市场全面渗透、信息快速传播的当下,民众跨语境的文化实践促进了语境间传统工艺的借鉴与转化。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孤立地分析各语境中传统工艺的发展。其二,有的研究以原生语境为依据,对其他语境中传统工艺的发展进行文化审视。这些研究以原生语境中的传统工艺发展形态作为参照系,将旅游工艺品化、艺术品化等现象视为对传统工艺的冲击,进而予以批判。客观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以原生语境为参照系审视其他语境中传统工艺的发展问题,反而需要对各语境中民众的行动逻辑予以充分尊重。其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传统工艺在多元语境中共生发展的事实。他们比较分析各语境间传统工艺的存在形态、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差异[11]。这些是极为有益的研究尝试。但若能在多语境横向比较的同时,进一步关注民众对传统工艺的跨语境传播、吸收与转化的过程,我们将会更深入地解读各语境中传统工艺共生互融的真实状态,目前类似的研究还比较少[12]。
3. 走向多元语境联动的传统工艺研究
基于此,笔者主张开展多元语境联动研究。所谓多元语境联动研究,就是回归于民众的工艺文化实践,在承认各语境相对自主的社会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关注民众在多元语境间对传统工艺的传播、吸收与转化过程,从而以更加开放的视角解读传统工艺多元语境共生的发展状态。
具体而言,多元语境联动研究有三个基本理念。第一,传统工艺的语境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和高下之别,应坚持语境之间的平等关系。第二,需要以传统工艺在各语境中的具体实践形态为研究基础,研究以各语境中民众的工艺文化实践为线索,归纳各语境中传统工艺发展的共时特征和演变逻辑,呈现传统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多元面向。第三,以传统工艺跨语境的传播、吸收与转化为研究重心,在掌握各语境中传统工艺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应着重观察并分析民众在国家与地方政策、市场运作、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对传统工艺的跨语境传播、吸收和转化,从而把握各语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最终对当代传统工艺的多元化发展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四、 从工匠群体到工匠个体:人的维度的视域拓展
需要承认,作为传统工艺的核心载体,工匠群体的共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柳宗悦[13]在《日本手工艺》中便如此评价工匠:“即使他们是渺小的个人,但传统则是伟大的力量,他们的工作是由传统驱使着的”。在柳宗悦看来,集体性的文化传统是主导工匠的关键力量,工匠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群体同一性。在当代复兴进程中,工匠个体日益凸显出强大的选择力和能动性。面对这种趋势,我们迫切需要将研究视域从工匠群体向工匠个体延伸,在对工匠的个体生命历程和造物活动的分析中,深化阐释当代工匠的主体性及其在中国传统工艺复兴中的作用。
1. 个体工匠能动性的增长
实际上,既有研究已经对作为个体的工匠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凸显出工匠个体在传统工艺发展中的重要性[14]。在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史中,作为个体的工匠是不可忽视的行动主体。天津木雕的发展便与一些工匠的个人努力紧密相关,朱星联和王树元便是其中的代表。当时,朱星联将中国花鸟画的构图技法融入到天津木雕的创作之中,带来了天津木雕构图传统的重要变革。王树元作为当代天津木雕工匠的代表性人物,同样以个人的创新带来了天津木雕的新发展。他苦心钻研多年,打破了传统木雕的边框限制,根据国画的章法创新构图,进一步突出了木雕造型的立体感,创新了“一体多层镂空木雕”。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工艺的集体传统仍然是相对稳定的,工匠个人的自主创新行为还是相对较少的。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15]所言,在曾经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特定角色所赋予的“标准化人生”,如今变成了“选择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相较于过去,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工匠个体正迸发出更强大的选择力和创造力。以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扁担山地区的两位布依族蜡染工匠WDF和WDB为例阐释如下。
WDF是扁担山地区凹子寨的布依族妇女,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布依族蜡染技艺。1990年,她通过北京老板的招工测试,到北京的蜡染厂做画蜡工人,是布依族蜡染工匠中较早接触蜡染旅游工艺品的人。1995年,她返乡嫁到凹子寨,重拾布依族蜡染技艺,经营布依族传统蜡染。2014年,上海一家蜡染服饰公司主动联系她,希望与她建立合作关系。早期做工的经历提醒她,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她便果断确立了合作关系,开办了蜡染作坊,用于设计并生产布依族蜡染风格的时装。进入时尚这一全新领域后,WDF经常向时尚设计师学习时装设计理念。经过与设计师的合作,WDF根据流行服饰的消费需求、审美观念和设计理念,提取布依族蜡染传统的狗牙纹、水涡纹、方块纹,设计了一批受到时尚界欢迎的布依族风格的蜡染时装。
WDB家住石头寨,自幼跟随家中长辈学习并掌握了布依族蜡染的制作技艺。2010年,WDB结束了在昆明回收废品的工作,返回石头寨,在附近景区做烧烤生意。考虑到布依族在婚礼、葬礼等仪式中要使用蜡染,对蜡染有很大的需求。因此,她在旅游淡季便以生产并销售布依族传统蜡染为生计。与村寨大部分做蜡染的妇女不同,她并未选择制作工艺相对粗糙、价格相对低廉但省时省工的蜡染百褶裙。由于对自己的蜡染技艺水平很有信心,她选择做工更加精细、售价更为高昂的蜡染袖子。WDB在蜡染袖子的制作过程中非常仔细,力求精确。她的产品也因此受到周边布依族民众的好评,销路很好。
可以看出,二人都在自主选择嵌入社会生活的位置与方式,个体差异正是在这种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而言之,在积极地实现个人价值与生活诉求的同时,她们也在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参与着传统工艺的秩序运转。可以说,在当代生活中,工匠个体与传统工艺整体发展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表现出一种以个体工匠的自主行动为重要构成的传统工艺发展秩序④。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工匠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向个体的工匠研究延伸。
2. 走向个体的工匠研究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社会型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15]21。个体工匠的研究并不否定或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工匠如何在流动、多元、异质的现代生活中通过选择、规划并践行自己的造物生涯,对传统工艺的发展施加影响。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传统工艺是工匠为了情感和生活诉求而开展的工艺传习与制造活动,是他们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个体的手艺生涯将是研究的问题主线,以之为线索,研究将兼顾社会规范与个人行动、集体工艺传统和个体造物策略,从工匠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与生活诉求、造物活动等方面入手,理解传统工艺对于工匠个体的生活意义,洞察工匠个体在当代传统工艺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这将对工匠群体的研究形成有效的对话与补充,对当代中国传统工艺复兴进程中工匠的主体性及其作用做出进一步解释。
五、 结 语
当前,中国正处在传统工艺复兴的关键时期。传统工艺在多元语境共生且富有流动性的当代生活中如何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那么这一问题由谁来解答呢?政府的政策实践与学术界的理论建构固然重要,但作为日常生活实践者的民众更为关键。正如高丙中[16]所言,民俗模式存储在文化传统里,只有主体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活动里,它们才能被赋予生机,进入生活过程。因此,手工艺品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民众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真正主角,他们的主体实践是弥合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裂缝、实现中国传统工艺复兴的关键动力。历代民众在享用和传承文化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创新和扬弃[17]。
表面而言,面对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传统工艺研究的问题在于难以充分解释工艺文化的急剧变迁、工匠的异质化发展和工艺的多元化发展等新趋势。但究其实质,传统工艺研究的问题在于,亟待更深入地洞察民众在多元而富有流动性的现代生活中的主体性。传统工艺研究在文化、语境、人等维度的视域拓展,正是以民众的主体实践为突破点。工艺文化的实践取向凸显了民众作为工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通过对其实践过程的分析来解释传统工艺的动态发展。工艺语境的多元联动取向则以民众跨语境的文化实践为重点,兼顾语境的边界与关联,解释当代传统工艺在多元语境间“和而不同”的发展状态。工匠的个体研究取向则聚焦于民众中的特殊群体——工匠,在承认工匠群体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关注工匠个体的手艺生涯和造物活动,剖析工匠个体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化解释当代工匠作为制作者的主体性。总之,作为三个视域拓展的理念内核,回归民众的主体实践,从中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对接理路,对于理解和推动当代中国传统工艺的复兴,将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① 蜡染是中国多个民族共享的手工技艺,本文先后使用了黔东南白领苗蜡染、安顺布依族蜡染、安顺小花苗蜡染作为案例。白领苗蜡染与小花苗蜡染都是苗族内部支系传承并发展的蜡染技艺,二者在工序上基本相似,但蜡染图案的风格和内涵均具有一定差别。安顺布依族蜡染则是布依族第三土语区民众延续并传承的手工技艺,其工序与前两种蜡染基本相似,不过具有布依族特殊的文化意义和功能。为方便读者区分,特在此说明。
②为保护调查对象隐私,姓名以首字母代替,特此说明。
③访谈对象:WWZ,访谈人:王明月,访谈时间:2016年7月6日,访谈地点:安顺市镇宁县石头寨WWZ家中。
④对于这种发展秩序,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做了系统分析,在此不做详细分析,可详见《后现代语境中工匠的全体重构与角色转变——以安顺苗族蜡染工匠为例》,参见《民间文化论坛》2021(2):114-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