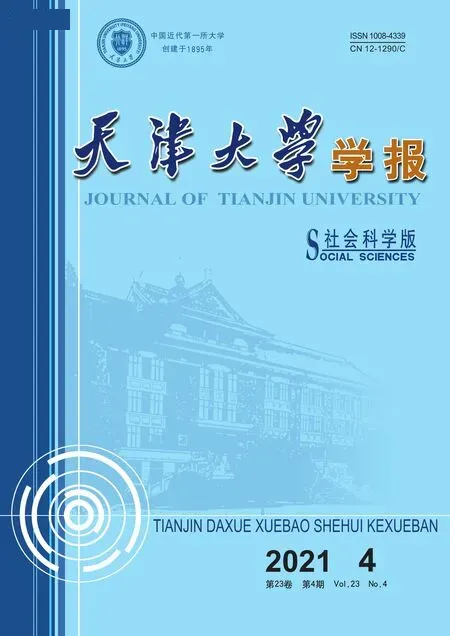《诗经》“伐木所所”中“所”字本义商榷
王业奇, 赵 卫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天津 300072)
一、 “所”在《诗经》中被用作象声字
关于“所”字本义,一直存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所”字的本义是表示伐木的象声字。这样解释“所”字,应该源于《诗经·小雅·伐木》里的诗句:“伐木所所(许许),酾酒有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以《诗经》为参照进行说解,释为:“所,伐木声也。从斤,户声。《诗》曰‘伐木所所’。”后来,许氏的这一说法被不少学者认可并被采用,较早的《类篇》《广韵》《集韵》都引许氏的说法。近代辞书不少亦从许氏说,比如,《汉字源流字典》认为“本义为砍伐木头的声音”[1]。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也认为:“‘所’字最早可能是个象声词。”[2]
《诗经》除了“伐木所所”,其中的“所所”表示象声;此外还有两处,即“伐木许许”和“伐木浒浒”,其中的“许许”和“浒浒”,也都表示象声。显然,“所”与“浒”“许”同为描述伐木声音的象声字。我们知道,“浒”是后起的形声字,“浒”“许”两字之作为象声字,当然只是使用了它们在当时的读音。“许”,从言,午声,本义为听从、允许;“浒”,从水,许声,本义指水边、岸边。“所”字之所以被作为伐木的象声字,自然也是使用了“所”字的读音。从《广韵》一系韵书看,“所”属生母鱼部,“许”“浒”为晓母鱼部,如此则“所”“许”“浒”韵音相近,所以《诗经》中,用这三个同韵的字共同表示“伐木”的声音,应该说是合理的。杨树达在《小学述林》中说:“所与许古音同,故《毛诗》作‘伐木许许’。运斤伐木有声谓之所,持杵擣粟人有声谓之许,字音同,故义亦相近矣。”[3]
早期学者对“伐木所所”中“所所”的认识也存在分歧。譬如:宋朱熹认为“许许(所所)”为“众人共力之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把“所所”释为锯木之声,清朱骏声亦从段说。由此看来,“所”为借音表达的象声字,基本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所所”为伐木的象声字,只见于《诗经》及《说文》所引《诗经》用例,并未在其他典籍中出现[4]。
“所”字在不同的辞书中,学者们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故训汇纂》把“伐木声”这一意义放在“所”字字义的第一个义项,并认定是“所”字的本义,之后才是与“处所”义相关的义项[5]。《中华大字典》同样把“伐木声”列为第一义项[6]。《汉语大字典》也是这样处理,处于第二位的是“处所”义[7]。《汉语大词典》把“伐木声”这一义项放到了第十六位,排在作为“姓”这一义项之前[8]。《中华字海》未收“所”字见于《诗经》的象声义。《辞海》(第六版)“所”字下的第一义项为“处所”义,未收“象声字”义项[9]。王力《古汉语字典》仅收录了“处所”义,未列“象声字”这一义项[10]。
二、 “所”字的本义不是象声
就我们所见到的古代文献而言,除在《诗经》中“所”字被用作象声字而外,其他多用为“处所”,或作连词、副词等虚词使用。西周晚期的《敔簋》铭文中有“所”字,铭文为:“夺俘人四百,廪于荣伯之所。”《庚壶》:“献于灵公之所。”《叔夷钟》:“又敢在帝所……是辟于齐侯之所。”此三处铭文中的“所”字,其义皆为“处所”,这也是“所”字作为名词“处所”义最典型的例证。之后,《周易》等文献中也见“所”字在多处用为“处所”或其引申义,如《周易》第五十二卦:“艮其止,止其所也。”《诗经》中“所”字表示“处所”或其引申义的用例也不少见,如《诗经·卫风·硕鼠》中的“爰得我所”、《诗经·商颂·玄鸟》中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通过对《国家语委古代汉语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所”字用例的统计分析,笔者注意到,表“处所”等义的“所”字,《周易》中出现30例,《诗经》中出现52例,《尚书》中出现13例,《周礼》中出现50例,《仪礼》中出现79例,《礼记》中出现500例,《左传》中出现467例。由此不难看出,在先秦文献中,“所”这个字,除《诗经》中的“伐木所所”是作为象声字,其他用法的意义均为“处所”或其引申义。
在汉语中,象声字是个特殊的字类。从来源和字形分析可知,汉字纯粹因声造字而后被假借为实词的例子十分鲜见。象声字通常是借他字或他字加义符来表示。现在常见的象声字,比如 “咣”“咚”“啪”“咕”“叽”“喳”等,皆是由于读音象声以此加义符所得。
《诗经》中的象声字数量较多,据统计约有70个,其中双音节字有62个[11],比如关关、丁丁、虺虺、肃肃、邻邻、沖沖、渊渊、阗阗、瑲瑲、令令、将将、活活、营营、逢逢等。毫无疑问,这些象声字的形体都是假借来的同音字,而所借之字已经存在,其本义并不表音。通过分析《诗经》中的其他象声字,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即表象声的字多半为假借,或者是在同音或基本同音的基础上添加“口”“氵”“钅”等义符造成。《诗经》中除了被误释的“所”字而外,本义是象声的字,后来又被假借为实词的情况,目前为止笔者未见第二例。从历史文献看,很多实例都说明,选用哪一个字作为象声字有着很大的“任意性”,《诗经》中所出现的不少象声字常常出现音同形异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赵爱武举出《诗经》中的“玱”“鸧”“将”“锵”四字便是这样[11]。具体说,这几个字用来模拟玉石之声,但用字不同。
三、 “所”字作为“处所”义
对于“所”字形体中的“户”和“斤”,不妨结合两个构形部件在其他字形中的作用及“所”字在文献中的意义加以分析。
早期文字多为象形字。“户”是,“斤”亦是。《说文解字》:“斤,斫木也,象形。”段玉裁注:“斤,斫木斧也。此依小徐本,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则谓之斤。”由此可知,“斤”既可作为劳动工具,又可作为武器。那么,“斤”在“所”字中所代表的是劳动工具还是武器呢?这一点确实也成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以致得出了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以斤斫门,为动词。康殷《文字源流浅说》云:“所,金,释所,像用斤锛斫门户之状,户亦声。”[13]康氏把“所”分析为以斤斫木,进而又引申为建造房屋,这种说法在笔者见到文献用例中未能得到佐证,而且与“所”字的引申义不相关联,尚不足信。另一种认识是以斤护户,“斤”代表一种威严、武力和权力,与“王”字中的“斧”有着同样的意义。“王”字甲骨文金文形体分别为、,形体像斧钺之形,以此象征着王权。
相对于第一种说法,“以斤护户”似乎更具说服力:一则符合“户”作为声符的示源功能,具有作为工具或武器的“保护”义;二则两个部件合而为意,指称需要特别守卫的重要部门也在情理之中。湛玉书就是根据“所”字的构形,直接推测“所”是有人持斧头守护的地方[14],所以后来很多具有行政职能的国家机关称之为“所”,如派出所、管理所等。固然,时下称之为“某所”的有些部门,从建制规模看,或许算不上宏大,但其职责所在无疑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从相对早期的文献用例看,“所”最初指称的处所具有明显的政治或权力特征。欧阳超很早就注意到“所”字隐含有这样的意义特征:朝廷、国家、当政、任职[15]。顺着这个思路,笔者搜集并分析了“所”字意义,注意到了其中隐含着的表示重要场所之意。前文所说金文中最早的用例“荣伯之所”“灵公之所”“帝所”“齐侯之所”,《庚壶》又有“庄公之所”,不难看出这里的“所”,均与贵族、大臣、帝王的居住场所有关。欧阳氏给出了《诗经》及其他先秦文献中的不少用例,如《诗经》中的“自天子之所”“献于公所”;《尚书》中的“君子所”;《左传》里的“公朝于王所”。铜器铭文及先秦文献中的用例,佐证了“所”为表示场所的名词,所指都不是一般的处所或住处,其中“献于公所”的说法,其义自见。历史告诉我们,帝王、贵族居住的地方都有卫士持械把守,由此,“所”字中隐含的防守、保护义便凸显了出来。
随着“所”字的意义在使用中不断地被引申、扩大,后来不再限于指称帝王贵族的住所,开始表示一般场所,如《诗经·硕鼠》有“爰得我所”,《国风·豳风·九罭》有“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等。但是,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从“所”字用法看,关乎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军队建制等重要部门,仍见采用“某所”的命名形式,如明代,国家根据地理形势和设防需要建立了许多“所”,同时还有“卫”,所有军队士兵都编入“所”和“卫”,其中百户所为112人,10个百户所又编为一个千户所[16]。这里建立的“所”皆为防御、守护安全的机构。直到现在,我国很多的部门,仍延续了这种命名方法,如前面所举派出所,此外还有拘留所、看守所、哨所等。
四、 “所”字本义当为动词“放置”
通过对“所”字形体结构乃至古代行政机构命名中“所”字使用情况的分析,可以认为,“所”字具有指称国家机关的处所义。但是,通过方言调查,我们注意到,“所”字的这个意义,或许并非其本义。
在河南商丘市、周口市和南阳市的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经常能够听到一个作为动词用法的字,其读音为[ʂuo24]。这个字,在上述三市的不同地区,声调的调值略有差别,但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阳平。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个字应该就是“所”字。商丘市、周口市和南阳市的方言说明了“所”字的一个共同用法,就是:“所”字作为动词,多用于表示把农具放置于门后,而且必须为“斜放”之义。例如:周口、南阳两市方言。
(1)锄头就所[ʂuo24]到门后吧。
(2)斧子在门后所[ʂuo24]着呢。
“所”字在商丘市方言的读音略有不同,如其中柘城话,“所”字有两个读音:读为[ʂuo24]或[fo24]。如:
(1)铁锨我就所[fo24]/[ʂuo24]到门后边了。
(2)那个长把儿斧子在墙角所[fo24]/[ʂuo24]着哩。
柘城话之所以存在[fo24]、[ʂuo24]不分的情况,这和商丘一带方言的语音发展有关系。在今包括商丘市在内的更大范围的豫东方言中,[ʂ]声母读[f]的情况比较常见。大体说来,中古遇、蟹、止、臻、通各摄的合口三等韵,山摄的合口二三等韵,宕摄的开口三等韵,江摄的开口二等韵,其中庄、章两组声纽的字,今普通话读为[ʂ]的,豫东方言都读[f][17],比如刷[fa24]、水[fei55]、说[fo24]、熟[fu24]、叔[fu55]等。“所”字在豫东方言的发音就属于这种情况,作为动词读[fo24]或[ʂuo24],作为名词读“所”[fo55]或[ʂuo55],“所”字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声调有所不同。
“所”字在今河南省部分地区的方言中作为动词,表示“放置”义。这个“放置”义与“保护”义有密切关系。可以设想,远古时期,我们的先祖筑有简单的房舍,那时家庭成员从事田间劳作或外出狩猎,放置“户”后即门后的“斤”即“斧头”,既是重要的劳动工具,又是重要的抵御敌人的武器。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把农具和武器置于“户”后,不仅取放方便,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遇有敌情,能够快速拿起进行抗击,守住门户。现在河南省很多地区,不少农村家庭仍然保留着把农具放置门后的习惯。或许可以说,古人门(户)后藏斤(斧)的这一生产生活习惯,为“所”字造字构形提供了事实依据。
在河南省许多地方的方言中,“所”字作为动词的用法,使我们想到:把“放置”(具体地说,当是倚墙斜放于门后)理解为“所”字的初始义,即本义,或许比较合理。特殊器物和特殊位置的“放置”义,使得“所”同时具有了“保护”义,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而获得名词义表示“重要场所”。当然,随着“所”字的广泛应用,意义不断地加以引申、扩大,“所”字早已开始指称一般性质的处所,如“刘庄卫生所”“韭菜研究所”等。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特别是通过对河南省商丘市、周口市和南阳市等地方言“所”字用例的分析,笔者认为:“所”字的本义当为“放置”,词性为动词。由于放置的器物是“斤”,即今所谓“斧头”(农具兼作武器),放置的地方是“户”后,即今所谓“门”后这一关键位置,以此,“所”同时取得了具有“保护”作用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所”字,很自然地获得了表示帝王、贵族居处乃至国家重要部门的特殊“处所”的意义。
时下,“所”字作为动词表示“放置”义的用法并不多见,但其作为名词表示国家重要部门的“处所”义,依然有所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泛化,用于表示相对普通的部门,例不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