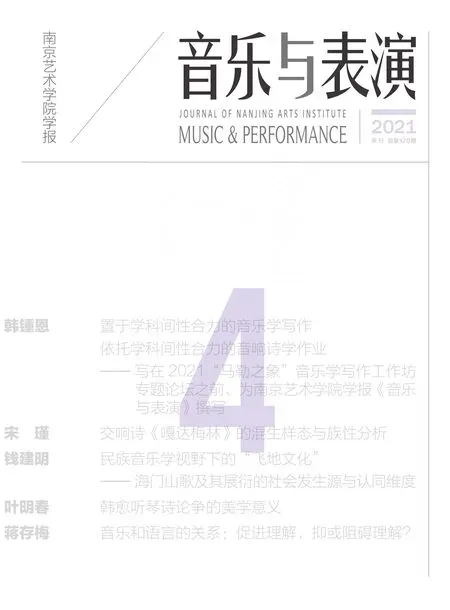韩愈听琴诗论争的美学意义①
叶明春(西安音乐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中唐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是一首描写古琴音乐的诗章,与白居易《琵琶行》、李贺之《李凭箜篌引》并称唐诗中极写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三大名作。但最有争议的却是韩愈《听颖师弹琴》诗(下简称“韩诗”)。争议从北宋欧阳修、苏东坡认为韩诗为听琵琶诗而予以否定韩诗,著名琴僧义海②义海:北宋太宗时琴僧,生卒无考。据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云:“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惠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转引自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700)据理力争肯定“韩诗”开始,围绕“韩诗”的是非得失问题打了将近一千年的笔墨官司,至今未有定论。清代学者蒋文勋在《琴学粹言》中把这一论争提高到“审美观的高度……”[1],其论述已触及了平和审美观与不平和审美观的关系问题。
蔡仲德先生于1987年8月在《人民音乐》杂志发表《聚讼千年的一桩公案——从韩愈听琴诗说到“平和”审美观》一文,使这一问题从1959年6月查阜西《溲勃集・欧阳修论琴诗之失与听琴之得》[2]之后在当代又被提到了较高的美学层面来讨论,认为“在这一公案中,聚讼双方并非旗鼓相当,否定韩诗、贬斥义海者占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我国历来以平和为美,不平和为丑,存在平和审美观”。“‘平和’审美观的问题在于把平和当作审美标准,用以否定不平之美,导致风格单一;在于否定‘促节繁声’,‘悦耳动听’,削弱音乐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在于推崇大雅之琴,贬斥琵琶筝笛之器,贬斥俗乐。这就必然阻碍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使之脱离人民,甚至使它有可能变为异己的力量。我国古代音乐之所以由盛而衰,终于落后于西方,原因之一在于此;古琴艺术之所以蹶而难振,沦为博物馆艺术,其原因更在于此;我国当代音乐之所以长期不能成为人民的心声,迟迟未能改变落后的状况,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鉴于此,窃以为为使音乐挣脱束缚蓬勃发展,为使音乐真正成为人民的心声,我们应该肯定平和之美而扬弃‘平和’审美观”。
1988年4月刘婴奇先生也在《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中和”审美观之我见》一文,对“蔡文”提出反驳,认为“……任何一种审美观都是有其审美准则的,都要有所否定,有所肯定。既然‘平和’是一种美,‘中和’审美观‘以平和为美’,这本身就有合理成分,就不该被全部否定掉。……”“刘文”还认为“蔡文”中“对‘中和’审美观的历史作用全以消极而论,显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再者,《聚》文关于‘中和’审美观成为导致我国音乐‘落后’的‘重要原因’的论断,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既然‘中和’审美观‘早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且‘长期占统治地位’,起着‘阻碍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的作用,中国音乐史上为什么还是出现了像唐代那样音乐发展的全盛时期呢?‘中和’审美观的惰性作用为什么在近代才成为音乐衰落的原因呢?……审美观念毕竟也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决定,是属于第二性的。……如果对我国音乐‘由盛而衰’,‘迟迟未能改变落后状况’,一定要从审美观念方面找原因的话,‘中和’审美观作为原因,也绝不是‘重要的’”。刘文还说,“‘中和’审美观并不像《聚文》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的;他关于艺术应该是合于规律性和合于目的性的统一的认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也并非是不可取的。在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今天,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和’这一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涉及一个对待音乐文化传统的根本态度问题。对于音乐文化传统,也还是那句老话,只能是批判地继承,除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这个批判地继承(加上对外来音乐文化的批判地吸收),就不能建设和发展起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的音乐文化。因此,象《聚》文对待‘中和’审美观那种一概否定、全部‘扬弃’(抛弃)的态度,绝对是不可取的”。
“刘文”关于对“中和”审美观“要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看法是合理的,但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刘文”并没有明确切指出。《聚》文说“平和可以是一种美,‘平和’审美观的问题在于把‘平和’当作审美准则,用以否定不平之美,导致风格单一;……”,“我们应该肯定平和之美而扬弃‘平和’审美观”,已明确对于“平和”审美观当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因此,“刘文”却说它对“中和”审美观“那种一概否定、全部‘扬弃’(抛弃)”,这是乎有公允。这是“韩诗”论争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交锋,其论争所涉及的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继承和改造等问题,至今仍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
笔者通过对“韩诗”论争绵延千年的整个过程的考察,认为“韩诗”论争并不是要得出韩愈《听颖师弹琴》到底是琵琶诗还是古琴诗的问题,其争论的实质实际上是两种审美观念之间的对立斗争,也就是说,“韩诗”论争的实质是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以平和为唯一审美标准,竭力否定以义海为代表的、以不平为美的、不平审美观一派,而义海等以不平为美、肯定“韩诗”,表现了对反主流思潮的艰难历程。我们现在来看待韩诗论争的实质,可以肯定地说,“平和”是一种美,“不平”也是一种美,不能因为“平和之美”否定不平的美,也不能以“不平之美”排斥“平和”之美。①2020年12月《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刊载了沈扬、钟振振《韩愈琴诗公案之再阐释——以两宋文人的争议为中心》一文,该文说明其是在蔡仲德、刘承华、查金萍、吕肖奂、关鹏飞等人基础上,对韩愈琴诗公案做了阐释。通过比较,笔者认为,除了本文论及蔡仲德、刘婴奇论文中讨论其美学意义之外,其他论文论域与本文有明显的差异,故保持本文初稿的基本概貌。特说明之。
一、韩诗论争的发展脉络
韩愈《听颖师弹琴》全诗如下: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耳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3]705
这首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是年韩愈四十九岁,官场失意,“被谗左降,有‘湿衣泪滂滂’之语”[4]。诗中的“颖师”生平无考,但据韩愈同时代的诗人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句可知,“颖师”当为中唐琴僧。又,李贺死于元和十一年,李贺“诗为罹病时作”[5],“韩诗”和李贺诗当作于同一年。清方扶南注云:“盖颖师以琴于长安诸公而求诗也。贺官终奉礼,役于元和十一年……”[3]705。艺僧以琴技“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6]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又由于唐艺僧地位低下,后世有关颖师生平的记述不详也是情理中事。
《东坡题跋・杂书琴事》云: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此退之《听颖师弹琴》诗也。欧阳文忠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诗故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为恨。[7]
苏轼的这段文字是最早对“韩诗”的评论,也是“韩诗”论争的导火线。笔者翻遍了能够见得到的资料,未能找出欧阳公否韩诗的直接依据之所在。在这段文字中,欧公之言似是随意语。
北宋琴僧义海对“韩诗”的释义与欧、苏相左。据蔡绦《西清诗话》云:
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尝问东坡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退之《听颖师琴》,公曰:“此只是听琵琶耳。”或以问海,海曰:“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脱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莫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来筝笛耳。”诗成欲寄欧公,而公亡,每以为恨。客复以问海,海曰:“东坡词气倒山倾海,然未知琴。‘春瘟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又特言大小弦声,不及指下韵。‘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宫角,岂独丝也?”闻者以海为知言。余尝考今昔琴谱,谓宫者非宫,角者非角,又五调迭犯,宫声为多,与五音之正者异,此又坡所未知也。①据《琴曲集成》第五册《琴书大全・诗下》。《西清诗话》: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西清诗话》三卷,题无为子撰,或曰蔡绦使其客为之也。宣和间臣寮言,其议论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其书已逸((转引自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700)。又据《宋诗话辑佚本》云《西清诗话》作者为蔡绦,本文从此说。其中文字又见收入《韩愈研究资料》(吴文治.韩愈研究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册,第10页。
义海从对诗的语义与音乐描绘之间的关系来看待韩诗,认为这是无品之琴才能表现的音乐,有品琵琶不可能如此,所以说“退之深得琴趣,未易讥评”。又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引《西清诗话》后评论说:
苕溪渔隐曰:“东坡尝因章质夫家善弹琵琶者乞歌词,亦取退之听颖师诗,稍加隐括,便就声律,为《水调歌头》以遗之,其自序云:‘欧公为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观此,则二公皆以此诗为听琵琶矣。今《西清诗话》所载义海辩此诗,复曲折能道其趣,为是真听琴诗。世有深于琴者,必能辨之矣。”
其卷二《国风汉魏六朝下》云:
永叔子瞻谓退之听琴诗,乃是听琵琶诗。僧义海谓子瞻听琴诗丝声,八音宫角皆然,何独琴也。互相讥评,终无确论。……②此据屠友祥校注《东坡题跋》(屠友祥.东坡题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卷二引自《韩愈研究资料》第一册第234页。笔者未能找到苏轼《水调歌头序》原文,但见彭庆生、曲令启选注《唐代乐舞书画诗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8页转引全文云:“欧阳文公尝问余:‘琴诗何者为最?’答以‘退之《听颖师弹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故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弹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诗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词云:‘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疑误)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可参照。
从上引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对韩愈《听颖师弹琴》诗的释义,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以苏东坡、欧阳修为代表的“否定派”,认定“韩诗”是“琵琶诗”,非琴诗;另一是以僧人义海为代表的“肯定派”,认为韩诗深得琴趣,是琴诗佳作。从宋代至当代,这两派就“韩诗”的释义、“韩诗”的得失以及义海与欧阳修论“韩诗”孰是孰非展开争论,此论争便成为聚讼千年的一桩公案。
据现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宋代除蔡绦《西清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支持义海之外,还有许顗的《彦周诗话》在同义海之言的同时,又从古琴的弹奏指法方面解释“韩诗”。其文云:
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此泛声也,谓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顺下声也。仆不晓琴,闻之善琴者,云此数声最难工。自文忠公与东坡论此诗作听琵琶诗之后,后生随例云云,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故论之,少为退之雪冤。①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此转引自《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第708页。《韩愈资料汇编》第249页也作收录。李祥霆先生认为“吟绎”之“绎”误,应为“猱”,是弹琴的一种指法,乃“欲上不上,欲下不下”之意。(据笔者“李祥霆先生采访录”之一)
清代薛雪《一瓢诗话》也有此意,其文云:
《颖师弹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写入神,乃“昵昵”二语,为似琵琶声,则“攀跻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除却吟猱绰注更无可形容,琵琶中亦有此耶?[8]
此外清代方东树《义卫轩文集》[9]②清代方东树《义卫轩文集》云:“《听颖师弹琴》‘浮云’句,泛声。‘喧啾’句,泛声中寄指声。‘分寸’句,吟绎 声。‘失势’句,顺下声。”可见“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一句,是琴“泛声”(左手食指帖弦,泛音,虚音),“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一句,是泛声中的“寄指声”(左手中指按弦,实音),“跻攀分寸不可上”,为左手吟猱之法,乃左手手指来回有规律的左右颤动,“失势一落千丈强”,左手从右至左顺势下滑。也从古琴弹奏方面赞同许说,肯定“韩诗”。
宋代赞同欧、苏之说,否定义海等人的还有吴曾的《能改斋慢录(卷一)・僧义海评韩文公苏东坡诗》,其文引《西清诗话》全文,然后评论说:
余谓义海以数声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谓真知琴趣,则非也。
昔晁无咎谓见善琴者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此泛声,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为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为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为历声也。数声琴中最难工。”洪庆善亦尝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岂义海所知,况《西清》邪?
……余考《史记》:“驺忌子闻齐威王鼓琴,而为说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听宫如牛鸣窖中,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故《晋书》亦云:“牛鸣盎中宫,雉登木中角。”以此知义海、《西清》寡陋,而妄为之说,可付之一笑。[3]709-710
至清中叶,有蒋文勋《琴学粹言・昌黎听琴诗论》推崇欧阳、苏轼,否定义海,认为韩愈《听颖师弹琴》意在贬黜颖师——“琴之下者”所奏“琵琶声”,更进一步认为琴是大雅之器,不应有“促节繁声,慆堙心耳”的郑、卫之音。其文如下:
《西清诗话》载欧阳公尝问东坡琴诗孰优,坡答以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公曰:“此只是琵琶耳。”坡公后作《听杭僧惟贤琴》诗,恨欧公不及见,盖因向日所举韩诗之失当也。三吴僧义海,号知琴,或以欧公之论问海,海曰:“欧公一代英伟,然斯语失矣。”群从附和者以为义海知言,欧阳失语。然朱乐圃《琴史》独载欧阳公而无颖师、昌黎,近日庄蜨(一作“蝶”)庵《琴学心声》于古独载嵇赋、欧诗而不登韩作,孰是孰非略可知矣。
韩文云:“世无孔子,余不在弟子之列。”又云:“轲之死不得其传矣。”盖文公之学,以道统自任,非特一代之名臣而已。不知琴不足以为公累,谓公深知琴不足为公重,而亦不暇讲之也。且知韩莫若欧,《卢陵旧本韩文后序》:“予为儿童时游州南李氏,于弊筐中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人之知韩,盖自公发之,岂有反不如彼一耳食之义海哉?
盖颖师非大雅名家,而于节奏定然悦耳动听。于頔嫂所谓“三分之内,一分琵琶二分筝”,抑知琴之下者未尝非琵琶声也?昌黎不过直赋颖师之琴耳。余谓不独“睨睨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如“小弦切切如私语”,“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如“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义海、洪庆善诸人未读下半首耳。“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琴有篁乎?此即东坡之“强以新曲求铿锵,数声浮脆如丝篁”也。“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直同于明皇之召花奴持羯鼓涤秽矣。昔师涓从卫灵公适晋,援琴鼓濮水所得之新声,未终,师况抚而止之,曰:“此商纣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亡国之音也,不可听。”文公之止颖师,亦此意也。不然,“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颖师之琴若果大雅,则必曰“莫辞更坐弹一曲”矣,何至未待终曲“推手遽止之”乎?且“遽”者,急骤之谓也,意必促节繁声,慆堙心耳,实有令人不能耐者。下曰:“湿衣泪滂滂”,夫琴声和畅,如东坡所云“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何至泪落如“江州司马青衫湿”乎?“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此二句贬词乎?褒词乎?昌黎《燕太学听琴诗序》云:“惟时醆斝(jia)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褒衣危冠,与与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来,历阶以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风》,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优游夷愉,广厚高明,追三代之遗音,想舞雩之咏叹。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请读是序,便知昌黎之黜颖师,而知余之论非偏袒于欧阳者。[3]698-700
蒋文勋的观点,既同于欧、苏,又不同于欧、苏,同在都否定韩诗,贬斥颖师,以及否定以义海为代表的“肯定派”;不同在于,不像欧阳修随意一句“自是听琵琶诗”,令人费解,而明确指出颖师之琴乃“琴之下者”奏出的“琵琶声”。认为韩退之之所以阻止颖师弹,正如师况之止师涓。其原因在于琴是“大雅之器”,琴声应是既平且和的,琴声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平和心”(苏轼《听僧昭素琴》),不应有“促节繁声,慆堙心耳”的郑、卫之音。
俞德鄰《佩韦斋辑闻》中则更为明确:“……合诗与序而观,其去取较然。抑其知琴者,本以陶写性情,而冰炭我肠,使泪滂而衣湿,殆非琴之正也。”[10]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包括蒋文勋在内的多数论者,都在就音乐的非语意性与韩诗语意性描绘方面的差异展开论争。许顗的《彦周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则从古琴弹奏方法的具体特征来看韩诗,涉及古琴音乐的本体特征。南宋楼钥在《谢文思许尚之石函广陵散谱》一文中说:“韩文公《听颖师弹琴》诗,几为古今绝唱。前十句形容曲尽,是必为《广陵散》而作,他曲不足以当……”[10]429这涉及“韩诗”的结构问题。20世纪50年代,著名琴家查阜西先生在《溲勃集・欧阳修论琴诗之失与得》一文中,在对“韩诗”的语意性描绘进行释义的同时,更明确地从琴曲的结构本身来看待“韩诗”。查文云:
《渔隐诗话》谓“古今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皆欲写其声音节奏,类以景物故实状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岂真知音者?但且造语藻丽为可喜耳”云云,夫子自道也。尤其首举韩愈听颖师弹琴诗为例最为荒谬。欧阳修谓此诗类言琵琶,僧义海即指其误(见《西清诗话》)。海之言曰:“‘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疏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脱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耶?”此就造型分析耳。余更为益之:
其一,颖师僧也(颖师之为僧有李长吉同体诗中“竺僧前来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之句为证)。未闻有僧以擅琵琶闻者,而擅琴者则比比皆是,欧阳修未见及此。
其二,从韩诗可以显然看出首二句为一式,第三、四句亦共一式,第五句复首二句式,第六句复第三、四句式;第七句为首二句之变奏,第八句为三、四句之强烈发展,皆琴之章法也。又自第九句以下韩愈感染至激动,言明不令终曲(“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颍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颖乎颍乎耳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琵琶无此结构。
其三,原题《听颖师弹琴》,欧阳修安得妄改?
然而义海评欧阳乃云“一代英伟”,惟斯语误耳。义海与朱文济、释夷中一脉相承,又读书能文,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沈括语,见《补笔谈》)。其于欧阳殆知之深也。[2]151-152
查阜西先生认为“韩诗”是听琴诗,其中所写的音乐结构只有琴曲才有,“琵琶无此结构”。这就否定欧、苏,而肯定义海。
从韩愈《听颖师弹琴》诗释义之争,可以明显地看出欧、苏一派和义海一派的音乐主张及其音乐美学思想。欧、苏、蒋文勋等人代表了传统古琴美学偏向于重虚、静、淡、雅,从淡情到禁情的传统,即以“中正和平”为美的主流思想,同时也代表了以“平和”之美否定“不平”之美的传统。而以琴僧义海及《西清诗话》为代表的一派继承和发展了以“不平”为美的思想,强调音乐作为表情艺术的特殊性,可以说义海一派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较为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平和审美观的局限给我们的启示
平和审美观的局限在于极力用“平和”审美标准恒定一切、否定一切,这是封建专制思想在审美观念上的反映。也就是说,在这种观念之下,人们除了只能以“平和”审美去欣赏音乐之外,几乎所有在审美上的欲求在观念上都属于“非法”。表现在中国传统音乐,又特别是在古琴音乐方面,便有《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禁淫邪,正人心”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琴音乐并未沿着“作为表情的艺术”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没有按照“音乐的特殊性”的方向,更没有沿着“音乐的主体性原则”①音乐的主体性原则强调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感情世界,强调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主体价值,确立人的主体地位。[11]的方向发展,而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消融人生,在寄情于大自然山水的“无情”之中,淡化世俗之情;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乐情篇》)的形而上——“道”的观念中寻求琴的“品性”“琴性”,追求“弦外之音”。形成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同时从淡情、无情到禁情的审美阶次中,取消个体人的所有欲念,取消音乐作为表情的艺术的正常发展规律,从而,把七弦琴艺术推向衰落的边缘。
平和审美观最初也并非不讲“情”,但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符合“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审美规范,规定这种“情”必须要有所节制,因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反对“纵欲”,主张“节欲”,用音乐的“中平”“中和”“中庸”的精神平息“人欲”,连主张“声无哀乐”的嵇康也认为“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无系于人情”(《声无哀乐论》),用平和之乐去“宣和情志”(《养生论》),平和的音乐有利于养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和审美观定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问题在于这种观念在东汉“独尊儒术”以后,被“名教”利用了。平和审美观所讲的“情”必须符合儒家强调的“礼”,音乐也必须服从“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的原则。从此,平和审美观的“情”永远也未摆脱“礼”的束缚。另一方面,《乐记》将“天理”与“人欲”对立统一起来,认为“天理”是“人道之正”,是上天赋予的“天赋善性”,是“父子君臣之节”(《乐情篇》),即封建的“三纲五常”,其特点是“静”“平和”“和顺”;“人欲”是喜、怒、哀、乐的外露。由于人心“感于物而动”(《乐本篇》),因而主张用“天理”来“平好恶”“节人欲”,主张“以道制欲”,“反躬”“反人道之正”[12]330。至北宋周敦颐则更进一步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融合儒道,在平和审美观的基础上提出“淡和”说[12]651-653,直到清代汪烜将“淡和”说发展到极点,古琴艺术也走到“禁情、禁声、禁欲、禁变”四禁的末路[12]803,就古琴音乐而言所有的情、声、欲、变(变革)都不复存在,平和审美观也走到了以“天”为本位”的“天理”、完全丧失“人性”的极端。
平和审美观是中国长期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闭关自守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平和审美观表现为中国传统文人追求“中正和平”“清虚淡远”,追求“弦外之音”,追求“道”的最高境界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塑造了中国传统音乐——又特别是古琴音乐。在这个意义上说,平和审美情趣是中国传统音乐——又特别是古琴音乐的特殊魅力之所在,就平和之美而言,这是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但从平和审美观的负面来看,平和审美观从“平和”——“淡和”(周敦颐)——“至淡”(汪烜)异化到“禁情、禁声、禁欲、禁变”四禁,取消了“音乐作为表情的艺术”仅有的“淡淡的情”,抹灭了琴乐中仅有的人性的因素,这是应当加以甄别并彻底否定的;另一方面,本文同意蔡仲德先生《聚讼千古的一桩公案》一文中的结论,也认为“平和审美观的问题在于把平和当作审美准则,用以否定不平之美”,因为这种思想是封建专制意识在审美观念上的反映,这种在审美观念上的专制意识已经不适应多元化审美并存的时代,阻碍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应当摒弃。因此,在韩诗论争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肯定传统音乐的平和审美情趣,解除平和审美观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专制”主义病毒,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步工作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不平审美观给我们的启示
《国语・晋语八》云:“平公说(悦)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三国韦昭注云:“新声者,卫灵公将如晋,舍于濮水之上,闻琴声焉,甚哀,使师涓写之。至晋,为平公鼓之,师旷抚其手而止之曰:‘止,亡国之音也。昔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后而自沉于濮水之中,闻其声者,必于濮水之上乎’”。“新声”实际上是春秋末郑、卫等国的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民间音乐[13],是一种体现不平之美的音乐。“平公悦新声”,是说平公喜欢“新声”,喜欢郑、卫之音。从这里可知晋平公、卫灵公、师涓均以不平为美,以表现不平之美为其审美趣味,但遭到师旷“音乐亡国”论的反对与制止。蒋文勋在《琴学粹言・昌黎听琴诗论》中也用了这个荒诞故事来解释韩诗“推手遽止之”一句,他说,“昔师鹃从卫灵公适晋,援琴鼓濮水所得之新声,未终,师况抚而止之,曰:‘此商纣师延所作靡靡之乐,亡国之音也,不可听。’文公之止颖师,亦此意也”。蒋文勋想借此说明韩诗意在否定颖师之弹,因此,从“平公悦新声”开始,如果说平和审美观是以正的面目存在的话,那么,不平审美观是一种“负的存在”。因为不平审美观从一开始便遭到了否定。因此可以说,不平审美观与平和审美观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早在春秋时期医和就提出了“中声”和“淫声”这一对对立的范畴,“中声”乃指宫、商、角、徴、羽五音及其运用,即“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左传・昭公元年》),其对立面“淫声”则是超越了这个度的不平和之音,即所谓“烦手淫声,慆堙心耳”的不平和的音乐。认为“淫生六疾”“过则昏乱”,从养生的角度否定“淫声”,在医和的审美观念中蕴涵了以平和审美观否定不平审美观的思想。又如,子产强调“淫则昏乱,民失其性”,用礼来“制六志”,即用“天经地义”之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来限制人们的“好、恶、喜、怒、哀、乐”,以“制六志”的音乐反对反映人们“六志”的不平的音乐。伶州鸠也否定“逞淫心,听之不和”的音乐,超过“中声”之度的不平之乐,在与周景王的对话中,主张“考中声而量之以制”,赞赏“大不越逾宫,细不过羽”的平和音乐,还说“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国语・周语下》),意思是说不平和的音乐,并不属于乐官掌管的范围。伶州鸠与周景王的对话蕴涵了不平和音乐的存在以及周景王以不平为美的思想,同时也蕴涵了伶州鸠以平和审美观否定不平审美观的思想。
至孔子“礼崩乐坏”时代,以不平为美的音乐已经相当普及,而这种音乐已经威胁到雅乐的生存,自然会遭到反对。因此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因为“郑声淫”(郑声放纵),妨碍“中正和平”的雅乐,所以孔子要“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从孔子对雅乐的肯定和郑声的否定之中可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孔子时代的共存境地,同时也说明两种审美观念的相互对立和斗争,也就是说,在孔子的言论中蕴涵了孔子以平和审美观否定不平审美观的思想。荀子继承孔子反对不平之乐的思想,有意回避“郑卫之音”,“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也蕴涵了以平和审美观否定不平审美观的思想。因此,从孔子呵护的礼乐反面来看,不平和审美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占有相当的地位,这种地位是在平和审美观的反对声中表现出来的。魏文侯曾对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乐记・魏文侯篇》)子夏的回答则以“德音之谓乐”为审美准则,即用平和审美观为准则来否定“郑卫之音”。这段对话也说明“中正和平”的“古乐”单调而呆板;不平和的郑、卫之音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所以魏文侯感到“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文献中,不平审美观的存在只不过是被作为平和审美观攻击的对象反映出来的,因此,相对作为主流审美意识的平和审美观而言,不平审美观是以一种“负”的面目存活的,是传统“主流”审美观之下的“暗流”,因此不平审美观是一种相对于平和审美观的“负的存在”。
然而,最早把不平审美观作为正面思想提出来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虽未涉及音乐美学的内容,但就审美观念而言,“发愤著书”说打破了不平审美观作为平和审美观“负的存在”的传统,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将不平审美观作为“正”的方面提了出来,他在《报任安书》中“主张被拘、受扼、放逐、失明、膑脚、迁谪、囚禁等人生不幸、人世不平的可垂之文书,肯定个人因遭不幸、不平而抒怨、发愤的合理性,认为历史上的伟大著作都是‘发愤之所作’,这是以不平为美,与传统的‘平和’审美观大异其趣,对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说教的超越与突破”[12]362。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段肯定不平之鸣,歌颂悲壮之美的文字:
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其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徴之声,士皆垂泪涕。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己不顾。[12]370-371
司马迁之后,将不平审美观从正面提出加以肯定的还有东汉的王褒和三国时蔡邕的“发愤作乐”说[12]691、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的思想,一直到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派等。王褒和蔡邕的“发愤作乐”说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发挥,李贽主张“诉心中之不平”(《焚书・杂说》),写“欲杀欲割”的真情,李贽可谓是将主情思潮与不平审美观熔为一炉之集大成者。
此外,在“韩诗”论争中,涉及了唐明皇以不平为美的思想问题,即蒋文勋在《琴学粹言》中说,“‘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直同于明皇之召花奴持羯鼓涤秽矣”一句。①唐南卓《羯鼓录》和南宋何薳《春渚纪闻・杂书琴事》,分别转引自《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下册)第702页注(16);第709页,其文云:“上(明皇)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琴,正弄未及毕,斥琴者出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唐明皇“不好琴”,以琴声为“秽”,宋代何薳笔记《春渚纪闻・杂书琴事》也引此事并加评论,其文云:“唐明皇雅好羯鼓,尝令待诏鼓琴,未终曲而遣之,急令呼宁王:“取羯鼓来,为我解秽!”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窪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眉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也矣”。唐明皇“雅好羯鼓”,以不平为审美价值标准,而以“平和中正”的琴乐为“秽”,因此“召花奴持羯鼓涤秽”。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唐明皇的不平审美观是从“正的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不平审美观的“正的存在”,而《春渚纪闻・杂书琴事》的作者何薳看待唐明皇的审美观时,仍然从传统以琴为“治世之音”的平和审美观的角度,贬斥唐明皇的“荒夷窪淫之奏”,贬斥唐明皇的不平审美观,因此,在何薳眼里不平审美观也是一种“负的存在”。
韩愈《听颖师弹琴》诗之所以引起千古聚讼,在于“韩诗”及颖师弹琴包涵了不平审美观,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平和审美旨趣古琴审美观,是一种以不平为美,以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生活、表现爱则痛哭流涕、恨则欲杀欲割为审美价值的体系。如前文所述,“韩诗”论争的历史意义还在于“韩诗”以及颖师弹琴蕴涵了人的主体价值,突出琴乐不同于传统以“平和”抑制“促节繁声,慆堙心耳”的审美准则,在强调音乐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方面,虽未能直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已蕴涵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蕴涵了音乐的自然发展方向——音乐的主体性原则。
这种主体性原则反映在“韩诗”论争中尽管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却是韩愈“不平则鸣”的音乐美学思想的辐射,同样也对后世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思潮产生巨大的影响。很显然,相对于“中正和平”以及“兴尽天理,灭尽人欲”的清规戒律来说,不平审美观强调表现个体人的主观情感方面俨然是对主流审美观的反叛,在强调与表现个体人的主观感受方面的意义来说,这一点与启蒙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相通的。
四、多种审美观并存的现状与前瞻
如前文论述,平和审美观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压制了不平审美观的发展,不平审美观只能以“负的存在”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作为“暗流”艰难“存活”。“韩诗”论争的整个过程正好是这种状况的一个缩影。但由于平和审美观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的解体,特别是西方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单一化的平和审美观念已成为历史,多种审美观念和多种音乐形态并存的状况已经形成,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应当看到的是,由于几千年的主流思潮的缓冲惯性,平和审美观沾染上的封建专制恶瘤并未在近现代音乐美学史上彻底的根除,以否定其他审美观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通过本文的学习与写作,本文认为这种在审美观念上的专制主义流毒不仅存在于“韩诗”论争中,同时还存在于现当代音乐生活中。比如所谓“学院派”对于席卷全球的流行音乐的抵御与排斥、自认为古典音乐流派的支持者们对新兴音乐流派的相互诋毁与排斥、持西方音乐审美标准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嘲笑、以及持传统平和审美观者对西方音乐的不屑一顾,等等,也都是在审美观念上狭隘的、功利的“专制”主义思想的在现代音乐生活上的反映。我们并不排斥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各种音乐形式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地说,以否定其他审美观为自身存在前提的现象对于当下发展多样性的中国音乐文化十分不利。
多元化的审美观念并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音乐审美“观念”的现代化和人们审美欲求的自由化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受“韩诗”论争的启示,本文在这里仅从审美观念研究的视角通过古琴音乐的传统审美窥视多种音乐审美观念并存的意义。
本文认为古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之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种,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其他艺术品种来说,古琴音乐所拥有的文化积淀最多,承受的包袱也最重。通过本文的陈述,可以看到平和审美观给予古琴音乐特殊的平和审美趣味、同时也使之沦为“名教”的工具,我们还应看到古琴艺术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博大精深的”琴学作为指导,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身专制主义“病毒”的蔓延——直至清代“禁情、禁声、禁欲、禁变”四禁的清规戒律中走入了绝路。正如蔡仲德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中所说“汪烜及其《通解》等著作说明,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音乐美学如要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另辟蹊径”①这里的《通解》,是指汪烜所著《乐经律吕通解》。[12]803。本文同意这个结论,但通过本文的写作,本文还认为,要根本改造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平和审美观,对平和审美观进行甄别,首先要除去的是平和审美观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沾染上的专制主义的流毒,就这个意义而言,传统审美观是必须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值得注意的是,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自由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并且应当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应该成为我们改造中国传统音乐审美观持有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准则。
第一个将“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是严复。他翻译的《群己劝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14]。平和审美观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自己的自由限制了不平审美观的自由。因此,在审美观念上的“自由主义”是中国音乐“全面现代化,充分世界化”[15]根本保证。
又,正如前文论述,韩愈是“不平则鸣”的极力主张者,在听琴诗中也表现了他的不平审美观,与此相对,韩愈在其他有关于琴乐的诗文中也表现了对于琴乐平和审美观采取的宽容态度。①韩愈描写古琴的诗文并不多,但从他写琴的诗文中可知其对于古琴艺术的深知程度。韩愈除写了充满宏伟壮烈之情的《听颖师弹琴》之外,还写了《琴操十首》《秋怀十一首・之七》,描写文人清高淡雅之情的诗篇。在《琴操十首》中唐代流行的十首“琴操”,如《将归操》《猗兰操》《别鹤操》等著名古曲。他听到的古曲,也是淡而近乎无味的“中正和平”之音,“再鼓声愈淡”,写出了韩愈秋夜听人弹琴时的深切感受,从诗中可见,在韩愈眼中,“平和”本身就是一种美。李祥霆先生认为韩愈在诗中表现了这样一种见识,即针对他所听到的“古曲”“事实亦必是古曲有淡者亦有浓者,新曲亦可写成淡而无味者,或奏成淡而无味者,是知韩愈于琴甚有见地”(《论唐代古琴演奏美学及音乐思想》(下),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这里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即韩愈一方面写宏伟激越的《听颖师弹琴》,另一方面却又写清高淡远之诗、推崇“广厚高明”“中正和平”的琴乐。这就是蒋文勋在《昌黎听琴诗论》中说“请读是序,便知昌黎之黜颖师,而知余之论非偏袒于欧阳者”的根本原因。韩愈在肯定不平审美观的同时,并不否定平和也是一种美。在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对待中唐同时存在的以表现“不平之鸣”的激越的“艺术琴”和主张“中正和平”“清虚淡远”的“文人琴”时,同样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因此,对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来说,一方面要做一个在审美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另一方面,又要做一个在审美观念上的“宽容大度者”。做到“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力”[14]。笔者深信,这两点是多种审美观并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多元文化并存的趋势之必然。
五、从韩诗论争说到古琴音乐现状
当代著名的古琴家龚一先生在其《对准时代之需要——我对发展古琴音乐的认识》一文中谈到古琴音乐在现当代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时,说古琴音乐缺少观众,古琴艺术之所以不被更多的人所理解的原因,他说:
……个中缘由倒还是千年前的古人道得入木三分,“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应是南风曲,声声不合今。”“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千年后的我们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中缘由”,竟然还能延续了千余年的原因。其实,部分琴曲的“淡无味”“不合今”“人不听”,是问题的表象,而关键是部分琴家的审美与大众审美的脱节,……(重点符号为本文所加)[16]
龚一先生认为当代琴家的“职责”在于努力使古琴艺术“能表达今天人们的思想感情,贴切地参与今天的社会生活”。他提出了达此目的的两项工作指标,一是“古曲的正确演释”,二是“反映现实题材的新琴曲的创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尽管古琴音乐“听众”层不多,但其确实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着,比如近代的“丝弦改钢弦”以及“线谱加减字谱”或“简谱加减字谱”的改进等,这在传统古琴“禁变”的戒律中已是相当大的革命了。直至今日还有许多琴家还在赋予这种古老的文化以“生命”,如果说“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人。人就是文化,文化也就是人”,[12]28尽管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革命”,但,中国人未死,传统文化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活着,古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存活”,海内外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关注着它的生命。
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艺术品种,古琴拥有的文化积淀最多,承受的包袱也最大。积淀来自特殊的审美情趣,包袱来自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
古琴艺术的发展在现当代确实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对其过高估价和过低评判都是错误的。人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总以传统音乐为例,而谈论中西音乐“话语系统”每以古琴艺术作比。我这里姑且不论所谓“主文化”与“亚文化”是什么关系,也不说中西音乐“话语系统”有无平等“对话”的可能,但古琴艺术——作为“活着”的文化,正如其他传统音乐品种一样确实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它的境遇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强烈撞击之下所遇到的境遇是相似的。冯友兰先生在《哥伦比亚答词》中曾经说过: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有两句诗:“周邦虽旧、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帮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17]429
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一文中又说:
《诗经》有一首诗说:“周邦虽旧,其命维新。”我把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
“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17]535
受冯先生的启示,本文认为古琴艺术具有三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积淀,是为“古乐”;而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是为“新命”。因此本文认为古琴音乐在现当代,也面临“古乐新命”的问题。
六、由“韩诗”论争引发的两点思考
第一,关于“中国音乐传统价值重估”的问题
“自性危机论”的主要代表是著名音乐学者沈洽先生和管建华先生。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引起的争论主要来自沈洽先生《二十世纪国乐思想的“U”字路》[18](下称“沈文”)和管建华先生《中国音乐传统价值重估的思考》《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两篇文章[19](下称“管文”)。沈文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在“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下走过了一条“U”字形的弯路,认为“我们中国音乐之‘基底’已经‘西化’了”,中国音乐存在“主体性”危机(或称“自性危机”),从而否定“五四”以来以萧友梅、黄自等创立的“专业音乐”“模式”。“管文”也认为20世纪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之后其音乐形态、音乐观念、价值体系等在中国取得了重要地位,而中国音乐“跟踪”的西方音乐“‘权威’技术话语线索趋于断裂”,因此中国音乐传统“也出现了危机和困惑”,“中国音乐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在音乐“平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建立与西方音乐对话的“话语系统”。认为这西方文化或西方音乐在当代遇到了危机,比如:“在西方新的记谱法猛烈地冲击着五线谱艺术创作范式的独尊地位,形成了历史性音乐观念的转变,并暗含了东方音乐记谱法价值的重估与重构意想”,因此“必须转变心态。20世纪中国音乐界对自我认识的一条思路是,以西方为参照找东方的‘落后’。现在我们是否能换一条思路,以东方为参照去找西方的‘落后’”。如此,等等。
邢维凯先生在《全面现代化,充分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15]一文中对“自性危机论”上述论点作了辩驳,本文不再重复多说,这里只需补充指出两点:一、“自性危机论”的如上观点是当前学术界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历史“循环论”在音乐界的表现;二、当前中西音乐并存,多种审美观并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怎能回避?“自性危机论”在“平等价值观”旗帜下再创“话语系统”,用以否定20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与融合,否定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把西方音乐先进的技法运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创新的实践与传统,而“另起炉灶”,是十分不现实而且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如果拨开“自性危机论”者的思想观念来看,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渗透着本文所揭示的“平和审美观”沾染上的“专制思想”的病毒,即自己的存在以牺牲他人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自性危机论”者在忙着创造“话语系统”与西方“对话”的时候却陷入自己的“悖论”。
第二,关于中国音乐文化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音乐文化必须面临现代化和世界化,这也是世界的潮流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大趋势。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根本标志就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经过众多苦难和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理。
事实上,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有机会坐下来考虑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出路问题的,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也基本属于农耕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小农经济,因而是一种求安定、求风调雨顺、求平和的农耕文化,其发展是在一种四平八稳的举步蹒跚之中,但是在一阵枪炮声中,以科学精神武装的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社会被强迫拉入近现代世界潮流,这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来得及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准备,又不得不遭受血与火的磨难,“这当中,整整缺少整理固有文化遗产的历史时期”。[21]在我们真正有机会和有能力来对待传统音乐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感叹传统音乐悄然而去,今之乐非古之乐了。针对这个问题黄翔鹏先生说:
历代都说古乐失传了。果真如此的话,现在还有传统音乐存在吗?我们现在讨论着的保存和发展的问题,它的对象是个空虚的幻影,还是实际的存在?这是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
11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张载说:“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为古乐为不知。”这话一语道破了历代文人同唱“古乐沦亡”滥调的病源。“太深”就是过于穿凿,指文人学士们辗转抄袭经义,远离音乐艺术实践,按照封闭的、凝固不变的既定标准来要求传统音乐。他们所追求的“古乐”,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并非客观存在的虚拟幻影,却将身边实有的、传自前代的音乐珍宝弃而不顾,不知加以承认、爱惜和保护。[21]
笔者认为在这种认识的面前“创立”中国音乐“话语系统”以及再高唱中国音乐“主体性”危机的论调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又沾染上了与“历代文人同唱‘古乐沦亡’滥调”。因“求古乐太深”,与西方“对话”心切而重新“抄袭经典”,盲目跟随西方后现代反主流思潮①这种思想在“自性危机论”者的代表文章里可以仔细论证,但本文这里不宜展开。,远离甚至抹杀20世纪以来的音乐艺术实践。其结果才是真正危险。更应该注意的是“自性危机论”者在反对或担心“最终就会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22],而在这个问题上却又陷入自己的“悖论”。
那么,中国音乐到底往何处去呢?
我们还是回到对古琴音乐的考察上去窥视吧!
据查阜西先生《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古琴曲有3,360多个传谱,650多个传曲,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今才有100多首打谱并用五线谱加简字谱的大部有名琴师打谱录音的琴曲,不足传曲的四分之一。[23]由于古琴艺术的特殊性,我们现在能听到一百多首琴曲,尽管大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大琴家,比如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等。他们“是‘传统琴人’的最后一代”[24],就古琴曲《广陵散》而言,虽不能说,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广陵散》的原貌。但是可以肯定从他们的音乐中可以感受到古乐的风貌,因为他们是“纯粹”继承古人传统的一代琴家。但由于他们的相继去世,“古乐”确实遇到了“问题”,在“自性危机论”者看来,新一代的琴家由于接受“欧洲中心论”教育体制的训练,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先天不足,以及他们文化出发点的‘不纯’,毫无疑问会影响打谱后果的‘真实性’”[24]。
但是,我们不幸只好如此,怎么办?
“自性危机论”者便在一旁感叹“今之乐非古之乐”,“中国古琴‘死了’”。其实,死掉的是“该死的”陈旧观念。正如成公亮先生在《打谱是什么?》一文中谈到新老两代琴家打谱的琴曲时所说:
……管平湖等琴家,他们的中国文化修养较高,所受的文化教育很“纯”。他们是“传统琴人”的最后一代,这是历史。新的一代琴人无论有多少“优势”:可能有多方面的修养,打谱时能记录五线谱和简谱,打谱时方便地使用案头录音机……,然而他们传统文化修养的先天不足,以及他们文化出发点的“不纯”,毫无疑问地会影响打谱后果的“真实性”。以上这些,都是从古代音乐面貌、精神如何真实地保存和再现的角度来谈,是偏于这一半的道理,如从不同时代音乐发展的角度来看,将又是一番风光,未必有那么多的“坏处”。
这里“不同时代音乐的发展”便是古琴音乐的“新命”。这种“新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共融中获得的,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种新命是在吸取古琴音乐从来未曾有过的新鲜“血液”,尽管很少一滴,但它早已撑起了“古乐新命”的风帆——那就是“科学的精神”和“自由主义”。
笔者坚信,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正是——通向中国音乐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