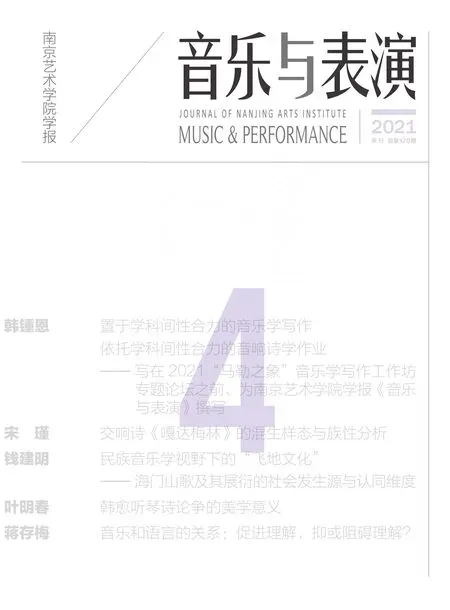从死亡“印象”到复活“映像”
—— 以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五乐章史料释证为例
黄 易(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引 言
适逢马勒逝世110周年,在收集马勒相关资料时,我发觉他在“自我阐释”时经常使用“情绪”一词表达作品内涵,因此产生了兴趣。情绪是获得刺激后生成的,但并非所有情绪都能留下痕迹,印象则是重要情绪的痕迹。我将通过刺激产生结果的过程概括为印象—映像的过程,又因其具有鲜明的死亡印象—复活映像指向,在此,仅采用《第二交响曲》第五乐章作为研究对象。
在前人文献中,关键词为“马勒”的相关研究有近千篇,包括李秀军的《马勒音乐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孙国忠的《论马勒的交响思维》等。关于“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研究有十几篇,包含任冰彬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研究》、张潇雪的《“殉葬式悲情”——以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第一乐章为个案探讨“c小调问题”》、陈云飞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复调技巧运用》等。其中任冰彬的文章是在分析上最为详尽的一篇,其中对马勒灵感来源的推测和交代也使我获得对于“印象”的进一步思考。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倒叙式”的:以映像(作品)为原点,在音响和谱本中寻找原初性印象的存在,再用史料和音乐分析的手段加以诠释。
一、解题
从马勒其人与《第二交响曲》创作背景看,“情绪”在马勒的创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将由此进一步引出印象与映像的概念,并对印象与映像的关系进行一定的重构。
(一)马勒:情绪的拥护者
马勒身处19、20世纪交汇的年代,作为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及指挥家,他的主要创作领域为交响曲和艺术歌曲。马勒的交响曲与艺术歌曲互相影响,《第二交响曲》就是马勒将声乐作品融入交响曲的开始。
1896年,马勒的评论家朋友马克斯•马夏克问他如何阐释《第二交响曲》的内涵,马勒回答道:
如果我发现有必要向你这样的听众解释作品中情绪的演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暗示,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按照我的设想,我着力详细描述的绝对不是事件,而是情绪。[1]
情绪一直是马勒创作的关键词,印象则是情绪的更进一步。多方面的影响促成了马勒情绪乃至印象的生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思潮或哲学理念是马勒创作的根据之一。当时唯意志主义①唯意志主义是将意志当作世界本原和发展动力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 流行于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的德、法、英和北欧等国,主要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 1819 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标志着唯意志主义哲学的产生。的各个主张对马勒影响颇深,在《第二交响曲》中主要体现为生死观的显现。此外,死亡、宗教思想也是谈到《第二交响曲》创作时不得不提的命题,在这部交响曲的创作过程中,他的亲人相继离世,马勒也不断在宗教信仰中汲取力量。
《第二交响曲》分为五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葬礼进行曲,c小调;第二乐章为三部曲式,舞曲,bA大调;第三乐章为回旋曲式,谐谑曲,c小调;第四乐章为三部曲式,bD大调;第五乐章为奏鸣曲式,出现合唱形式,标明谐谑曲速度、慢板,bE大调。
从作品布局可以看出强烈的对称性,并且,马勒根据自己的回答做出了相应的调性选择。作品中间三个乐章功能较为附属,重点是头尾两个乐章的质问和解答。
(二)印象(Impression):情绪的痕迹
如上所述,“情绪”成了马勒创作的关键词,然而,给予马勒灵感的事物并不仅仅是“情绪”(emotion),而是其留下的痕迹。为了让这种痕迹在感觉和作品中找到更准确的定位,我将以“印象”(impression)一词延展思路。
在英国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中,曾明确定义“印象”一词并加以运用。胡塞尔认为“印象”是一种行为,“印象”也可用来标识感知行为的特征或性质。休谟对“印象”的解释则与本文的“印象”概念更为接近,他在《人性论》中这样定义:
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impressions);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我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2]
休谟所谓“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即本文的研究重点——只取在艺术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印象进行阐述。
(三)映像(Reflection):印象的产物
映像是印象进入人的主体之后的一种产物,其中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反映。关于“映像”一词,从中文词意上有多个不同领域的解释,下文的阐释涉及胡塞尔现象学与物理学。
胡塞尔现象学的“映像”([德]Abbildung,[英]depiction)在反映论(Theory of Reflection)的根基上发展出独特性:“它被用来描述当下化(想象)行为的特征,从而与作为当下拥有(感知)的‘自身展示’(Selbstdarstellung)相对应,据此而可以被译作‘映像’。”[3]胡塞尔将现象学中的“映像”与反映论中的“映像”划清界限,并且强化了他所主张的意向性。
物理学中,根据光学原则,“映像”是由光线的物理反射作用产生的影像,并与参照物伴随发生。该定义与本文的映像很相似,简而言之,映像是由参照物(印象)通过反映生成的产物。
印象是一个开端,映像却不是结尾。人们能通过印象产出映像,又能通过映像产生新的印象,如此,印象如何化解在映像中就成了一个可求的问题。
二、从死亡印象到复活映像
之所以将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五乐章,作为从死亡印象到复活映像过程的释证,主要思路是在史料中寻找作曲家本人明确过的意图,再从音乐中寻找证据,通过对比、证实或推测,对此过程进行细节化表述。在此,将列举与分析有关死亡的音乐印象、宗教印象和哲学印象如何到达最终的复活映像。
(一)音乐印象—音乐映像
末乐章的“复活”主题由复活颂歌而来,是直接的音乐印象到音乐映像。
《第二交响曲》的末乐章,源自马勒在参加彪罗的葬礼时发生的故事:
当时合唱队从管风琴那边唱起了克洛卜斯托克的赞美诗《复活》!它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一切都清晰鲜明地立在我的灵魂之前!创作者在等待这道闪电,这是“神圣的受孕”![4]
经查证,颂歌其实是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Carl Heinrich Graun,1704-1759)②德国作曲家,先在德累斯顿的歌剧院合唱团工作,后移居不伦瑞克,写出最初的几部歌剧。1740年受腓特烈大帝邀请任宫廷乐长直到去世。他是与哈塞齐名的重要德国歌剧作曲家,所作均为意大利歌剧。作品在当时颇受欢迎,但今天已很少演出。所作。复活颂歌与“复活”主题的歌词一致,并且旋律型态很相似,均是“复活”(Auferstehn)时音区较低,“是的,你将复活”(ja aufersteh'n wirst du)时,旋律线条先上后下,“短暂的安息”(kurzer Ruh)时则继续向下至最低点。从音高位置、音程关系,到核心的旋律形态、词乐关系、音乐氛围等,二者拥有极高的匹配度。
复活主题在音乐中不断出现、变形,与其他主题衔接与交织,不仅在结构上达成了一定的比重与扩充性,也在情感上形成递增的趋势。以死亡印象—复活映像的角度来说,马勒接收了格劳恩《复活》颂歌的印象,从而加工成自己的复活主题映像,进而通过创作手段和音乐自身动力,与其他主题共同完成最终的宏大映像。
(二)宗教印象—音乐映像
第五乐章中,宗教印象是对马勒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我将“末日经”主题、“永生”主题和“耶稣升天”主题都归于宗教印象:“末日经”主题开头的四音动机源于罗马天主教仪式中常用的旋律,后两个主题则主要因马勒对歌词的编排和其在结构中的功能和导向性而划分。
末乐章采用《末日经》①《末日经》(拉: Die Lrae;英: Day of Wrath)又称“最后的审判日”“愤怒的日子”“震怒之日”,是罗马天主教仪式安魂弥撒(拉: missa pro defunti;英: Requier Mass)中的继续咏(Sequence)部分。的相关旋律作为主题之一,并将其作为结构性主题。
罗马教会的仪式中使用的《末日经》旋律,特征为四音动机,马勒的“末日经”主题(Dies Irae)就采用了这一印象。
马勒在末乐章中尤其重视“末日经”主题的运用与发展,不管是原型还是变形都存在感极强,如马勒将其进行上四度的变奏,由小提琴和长笛声部接连奏出,又或发展成进行曲风格,以小提琴声部奏出跳音。马勒的交响曲中乐思形成涌现之趋势,即使在同一乐章里,也常有莫测的风格变换。
“末日经”主题不仅预示着末日审判,还往往标志着“复活”主题的先现,这两个主题也是末乐章的基调构成元素,马勒刻意使其衔接、交织。可见“末日经”主题不仅只是发展、展衍功能的某一主题,而具有叙事结构性的功能,通过反复出现、变奏、与其他主体交织对抗等手段不断蜕变着。
除了具体的主题外,歌词也是马勒从宗教印象—音乐映像的有力佐证。在“永生”主题和“耶稣升天”主题上,马勒对歌词进行了思考性的编排和创作,他避开了自己认为与“复活”映像不够吻合的段落,选择亲自书写他认为歌颂复活所需的歌词。
在这部作品中,“上帝”与“神”代表的是一种信念,坚信灵魂必会找到归属、坚信一切绝非无谓。这就与当时的德国唯意志主义产生了关联。
(三)哲学印象—音乐映像
哲学印象在末乐章中体现为一种决定性的态度。马勒早年在维也纳时期参加了一个名为“培纳斯托弗成员圈”(Penerstorfer Circle)的团体,他们常研读当代重要思想家的论述,“其中最有影响力之一来自尼采,这位哲人的著作每每成为马勒灵感的来源”[5]。尼采那种直视死亡又带有激昂情调的态度,在马勒的音乐中一览无余。
作为一位音乐哲人,马勒在《第二交响曲》中的复活信念和对死亡的对抗态度是积极而肯定的。马勒在首乐章埋下疑问,而末乐章的第一句话——急速上行的C大调音阶,就是强有力的回答。自此,音乐材料不断呼应首乐章内容,比如“末日经”主题的再次出现与变形,再如第一乐章副部主题“希望”主题及第五乐章与之呼应的“希望”主题变形。
在调性上,从首乐章的c小调到末乐章的bE大调(c小调的平行关系大调)结束,贴合“葬礼”到“复活”的主题意图。马勒最终完成了精神涅槃,他也通过汲取生活苦难与学习经历中的养料,不断形成、加深宗教印象与哲学印象,从而完成音乐映像的反映过程。
三、印象和映像的属性与关系
结合音乐具体分析和释证后,笔者总结出印象与映像的属性与关系。首先,具有先后性,印象在前,映像在后;第二,具有再生性,印象—映像—印象的过程看似不断循环着,却并非回到本源,而离最初的印象与映像逐步变远;最后,二者之间存在异质同构的现象。
(一) 先后性
印象在前,映像在后,通常能同时在一个客体中伴随存在,但并不同时发生,本文将这样的属性称为先后性。
印象到映像的反映过程为:外界具有冲击力的感官事实在人脑中形成强烈印象并留下记忆,通过主体的加工,逐而演变成文本或音响实物。但主题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作曲家的音乐构思与音乐内部的生长力,如“末日经”主题在末乐章中形态多样,对原型的改变属于马勒对主题的编排,并非直接的印象到映像的过程。
《乐记・乐本篇》开头即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大意是人内心被触动是由于外界事物发生的影响,而后又能通过声音传达出来。其内容恰恰体现了印象与映像之间的先后性。
(二) 再生性
再生性是指印象产生映像之后,映像又能刺激出新的印象,以此类推。但印象—映像—印象的过程看似不断循环着,却并非回到本源,而是离最初的印象与映像逐步变远。作为听者的“我”感受到的“复活”与马勒的“复活”已不是同一物。其原因有两点,首先,异质同构再被解构之后,不同的质料不一定会回到原本的样貌和属性,内容和形式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第二,印象的生成也是重要的一环。由于各人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力和感知方向不同,各人对外物的接收所产生的情绪自然迥异,故其形成的最终映像也有所不同。
但也要明确,印象与映像无法形成完整的闭环,它只是在一些客观因素(如环境、时机)的发酵下,形成向外扩张或螺旋上升的走势。
(三)异质同构
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视知觉组织活动和人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
印象到映像的过程中,仅仅是印象的形成就有异质同构——客观事物与主观感知共同结合、存在。映像中也有异质同构的存在——作品中的一切音乐材料如结构形式或旋律音响等,能够与作者的情绪、灵感、印象形成异质同构,但同构中的各部分并非简单相加的结果。
从另一角度来说,映像又可作为客观事物去影响他人的印象,在听者处产生新的异质同构。在印象和映像中,发掘和鼓励异质同构是合理的,印象通过异质的方式使自我的表现力焕然一新,映像通过这种完形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与听者也能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启示。
结 语
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五乐章中,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印象是音乐印象、宗教印象和哲学印象,“复活”主题、“末日经”主题、“永生”主题和“耶稣升天”主题是末乐章中与本文内容最接近的四个主题,分别代表音乐印象与宗教印象对最终呈现的决定性作用,而哲学印象通常被归于一种宏观上的态度,比如首乐章到末乐章的转变。通过各类死亡印象的反映,最终的复活映像由此而生。印象与映像的属性有先后性、再生性,且此过程存在异质同构的现象。该乐章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描绘着世界的缩影,传达对生死的见解,将马勒的复活信念和个人意志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
本文中的印象是抽象物,是“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具有原初性。映像则多为具象物,可以直接理解为最终呈现,是经过原初性印象后反映、加工形成的,伴随印象发生。笔者意图定义和描述的概念和过程,都有解构和重构的意味。尽管笔者在行文中极力寻找史料和音乐中的证据以求实证,释证的倾向却难免穿插其中。故若本文中有所争议,均希读者再度讨论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