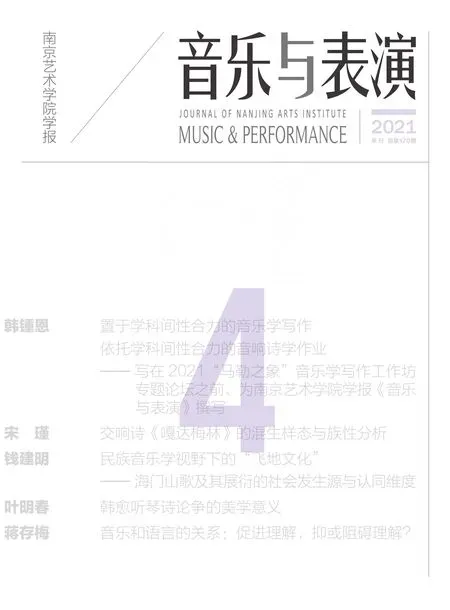从“无乐志”正史看中国正史“乐志”的撰写行为①
栗建伟(湖北科技学院 音乐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为何正史中十史无“乐志”?编辑《二十五史音乐志》的刘蓝给出两个解释,“最大的可能是某些史官的思想上认为:‘音乐算什么玩意儿,值得在正史里大书特书吗?’另外一种可能是编写史书的先生们缺乏音乐知识,只好空缺”,[1]5他认为某些正史无“乐志”,乃史官轻视、不懂音乐使然。本文认为,此说不解正史编撰体例及正史“乐”之含义,②正史“乐志”所载内容为历代音乐典章制度(如后文所引丘琼荪、徐元勇之说),以明政教知得失的礼乐为主,旁及部分俗乐,并不过多记述“音乐知识”(《隋书・音乐志》等略有论及)。知识、技能类的“音乐知识”多编录于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艺术类,而不是史部,更不是其“正史类”中。亦低估史官之史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礼乐教化,早被这些饱读经书的史官所熟悉。他们大多“深知礼乐之意”[2]127,亦知“礼乐之用为急”,③《汉书・礼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1027.此类言说又如:“为邦以礼乐为急”“六艺之中,礼乐为急”“《六经》之道,礼乐为急”“教化民众以礼乐为急”“王者政治之端,咸以礼乐为急”。因此,“‘礼乐相须以为用’已成为历代正史的编纂观念及传统”。[3]73他们岂会在正史中轻视之?又岂会在研经时忽视之?其实,原因并非如此表面与简单,而有多重情况。
正史“乐志”④此“乐志”含正史“礼乐志”“音乐志”“乐志”三类,与“律历志”无涉。乃记载历代音乐典章制度之重要体例,是后学了解当时音乐面貌的主要凭据。丘琼荪云凡:“有意于了解历代音乐概况者,有志于研究我国音乐史、乐律史、乐制、乐器、乐调、民族音乐、域外音乐,乃至歌曲、舞蹈、戏剧、散乐、曲艺等之兴亡隆替及其衍变流转情形者,请先于历代《乐志》《律志》中求之。”[4]9徐元勇也说,“正史中‘乐书’‘礼乐志’‘乐律志’‘乐志’‘音乐志’等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宫廷和当朝的用乐情况,是研究各个朝代音乐的最为可靠、最直接的音乐史料”[5]10“其记录的正统性成为音乐研究的坚实依据”。[6]91
而我们对正史“乐志”撰写传统尚无清晰认识,比如:为什么有的正史有“乐志”,有的则无之?在没有“乐志”的正史中,有何不同的原因使然?在这有无“乐志”的不同正史背景下,反映出正史编纂者什么样的“乐志观”?凡此均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内容。
一、正史“乐志”概说
史志乃纪传体史书记载典章制度之体例,若《食货》《地理》《经籍》《职官》《礼乐》《律历》之属。正史除《史记》为“书”、《新五代史》为“考”外,他史皆书为“志”,其实一也。正史之外若记、典、录说、略诸文体,皆与“志”同,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云:“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东观》曰‘记’,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
、 ,名目虽异,体统不殊”。①宋人郑樵《氏族略》全引此文,却于《总序》引此为“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与前者相比无“东观曰记”。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三与《总序》同,并云“旧作‘东观曰记’非”。
正史之乐与礼有紧密联系,故其“乐志”与“礼志”撰写体例或分或合,《河南通志・凡例》云:“司马迁《史记》载《礼书》《乐书》,班固《前汉书》载《礼乐志》,其后或合或分,具载国史。”诸书对其关系有两种处理方式:有将二者分而各为一篇者,若《史记》《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隋书》《明史》。《隋书》《旧唐书》称“乐志”为“音乐志”;有合为《礼乐志》者,若《汉书》《新唐书》《元史》。无论何种体例,均礼在乐前。传统学者似乎偏爱礼、乐分述之体例,如四库馆臣讥《元史》,“礼、乐合为一志”体例“不合前史遗规”。[7]42赵明正亦赞扬:“沈约对《宋书・乐志》的体制结构作了调整,放弃班固《汉书》礼、乐合志的形式,礼、乐各为一志,扩大了乐志编撰的自由度。”[8]80
若论各部正史“乐志”断限问题,历代因对正统之不同认知而有不同断限标准。总而言之,历代“乐志”多以记录当朝乐事为主,故明人朱明镐讥《宋书》《隋书》过多补录前代志为不合史法,“在史法宜改”,[9]328质问道:“律以史裁,则两史均讥。书名《宋书》而杂载吴、晋、蜀、魏之事可乎?书名《隋书》而杂载梁、陈、齐、周之事可乎?”[10]488赵翼谓《隋书》“既曰《隋书》,而纪、传专记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实殊不相称”,称其兼志前代之文,多是赘词。[11]174朱明镐此说乃袭刘知几“断限”体例,《史通》卷四《断限》主张,史书记事必须在时间范围上“明彼断限,定其折中”,不能记载超出时间范围的内容。[12]477其实,历代典章制度多有沿革,正史“乐志”不可能做到仅录该朝乐事,某些正史对有些前朝“乐志”亦有追述。总而言之,“乐志”追述前代乐事大抵有溯源流、[13]145辨正统、补前佚三种目的。《宋书》有蜀、魏、吴之志,《隋书》有梁、陈、齐、周之志。刘知几《史通・断限篇》总结云:“《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朱明镐云:“《宋书》以陈志无志,《晋书》未成无志,并蜀、魏、吴、晋四国之志而入于《宋书》之中。《隋书》以《梁》《陈书》无志,《后齐》《后周书》无志,并四国之志而入于《隋书》之中。”[10]487张舜徽认为,此乃史志义例特点,正史“虽是断代为书,然而志的写作,多半是贯通今古。这是由于典章制度,有它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叙述原委时,不可能割裂截断的缘故”。[14]396
二、正史“乐志”撰写的两种行为
正史多是以“隔代修史”“易代修史”传统形成的前代王朝史,其撰写“乐志”目的乃通过弘扬正统雅乐、评判前朝雅乐,以标榜当朝政治合理性。此与历代修史“明正闰、辨僭伪、定正统”目的相类。为此目的,历代对前朝乐志采取“撰写”与“不撰写”两种处理方式。前者乃肯定前朝礼乐,后者则为否定之。有的正史因多种原因而无“乐志”,后世则对其补阙、辑佚。至于那些没有撰写“乐志”之正史,虽无文本可依,仍可从相关文献研究其撰写行为与思想。我们相信,通过对“乐志”撰写行为之研究,能更好认识这些文本所反映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二十四正史中,七史无“志”,九史无“乐志”。无“志”者,若《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无“乐志”者,除上七书外,又有《后汉书》《新五代史》。《史记・乐书》因与《礼记・乐记》的复杂关系,亦可视《史记》为无“乐志”。如此,则二十四史中有十史无“乐志”。顾炎武将有无志书作为史书优劣之标志,云:“无志不得为完史。”[15]1447故本文力求在通观正史“乐志”撰写传统基础上,对无“乐志”正史进行专题研究,分析其无“乐志”原因,并整理其补录工作。
我们希望藉正史(二十四史)“乐志”撰写者之撰写行为角度,研究此“乐志”文本的撰写传统。历代正史“乐志”皆遵循统一撰写传统,此传统包含“撰写行为”的传统与“撰写内容”的传统二层面。第一层面指自汉至清历代撰写正史“乐志”体例的行为与特点,所据材料以当今“无乐志”的正史文本为主。即通过“无乐志”现象,来反观正史“乐志”的撰写行为;第二层面指历代“乐志”撰写的基本内容与特点,所据材料以“有乐志”的正史文本为主,来认识正史“乐志”的撰写内容。本文主要关注第一层面。
因此,正史“乐志”撰写行为传统,有“撰写”与“不撰写”两种状态,前者指某部正史撰写者有撰写“乐志”行为,后者指某部正史撰写者没有撰写“乐志”行为。前者在今天留存情况,包含“传世”“亡佚”与“散落”三种状态。故今本正史无“乐志”者,主要有“不撰写”和“亡佚”“散落”三种原因。
三、正史无“乐志”的四种原因
正史中七部无志,王锦贵认为,主要有撰者史料匮乏、认知偏差、才疏学浅三种原因[16]234,此说甚是。然其说仅指正史中“不撰写”状态,没有涵盖“无乐志”的后两种情况。
无“乐志”的十部正史中,“乐志”撰写行为“写”与“不写”的两种状态,反映在当前正史无“乐志”的原因,主要有难而不可写、鄙而不足写、已写而亡佚、写而编于他处四种情况。前两种情况指的是“不撰写”状态,后两种情况指的是“撰写”状态。第一种情况,较本纪、列传等体例,志最为难写,故略而不写,若《三国志》《南史》《北史》;第二种情况,认为该朝礼乐不发达,不足以写志,若《史记》《新五代史》;第三种情况,本已写毕,而后亡佚,若《后汉书》;第四种情况,已写而附于他书,若《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四书“乐志”载于《隋书・音乐志》。
(一)难而不可写
正史诸体例中,志最为难写,故江淹云:“修史之难,无出于志”[17]2,张之洞亦云:“作史以作志为最难,读史以读志为最要。一代典章制度,皆在其中。”[18]514其难者主要在于对资料掌握的广泛性,“作史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闳览博物者不能为。其考定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不能遍”[15]1447,故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
因资料不足而难写者,《三国志》《南史》《北史》即为此例。
1.《三国志》
晋陈寿撰《三国志》最大不足在于体例不全,仅有纪传而无表志,更无乐志。学者认为此书缺点之一即“家乘国志未及广采”[10]459,“尤史笔之欠”[19]25。对此书无志的原因,人们多认为资料不足而难写,故陈寿阙之。认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三国志没有志表,正是因为材料不足”。[20]1缪钺、刘琳[21]6、杜经国[22]6、杨耀坤均有此说。“陈寿大概是因为资料搜集的不够所以没有作志”[23]16,“资料欠缺是难以完成的”,“这可能因陈寿资料搜集不够而未作”[24]107。仅凭陈寿一人之力,若欲穷尽三国典章制度,达到如纪传相同的“文质辨洽”[25]100确属难事。此外,恽敬认为,是陈寿有意不作,则“现已无从确知了”[24]28。
因是书无志,后人多有补撰。若欲明三国之志,多据此载。元人郝经《续后汉书》:“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阙”[7]124,三国时期,“礼乐废缺”,若“不为考定,则散无统纪”[26]252,故作八录以补之。八录即八志,有《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金毓黻云:《续后汉书》所撰八录“是就《三国志》所原无者,而悉为补撰”[27]230。亦有专补一志者,若补《疆域志》者有清人洪亮吉、谢钟英、金兆丰、汤玉芬,补《艺文志》者有侯康、陶宪曾、姚振宗,补《食货志》者有陶元珍。
独无专篇补“乐志”者,多于其他正史“乐志”中兼补。最早为补撰魏、晋二国“乐志”,如《晋书・乐志》载有魏晋之乐,独不写吴国乐志,对此现象,何承天认为乃因“吴朝无雅乐”[28]541。《宋书》否认此说,又补三国“乐志”。明人朱明镐《史纠》云:“并蜀、魏、吴、晋四国之志而入于《宋书》之中。”[10]487《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总结云:“《晋书》尚未修成,沈约《乐志》二卷凡载魏晋乐制颇详。惟是吴蜀并称三国,乐制何无一传。岂兵戈扰攘,礼乐日有不暇给耶,抑史官佚其文耶?何承天云世咸谓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惟云倡伎日夜不息,则无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又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①据《宋书・乐志》此有脱文。(梁)沈约.《宋书・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541.,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附志于后以补三国乐制焉”[29]352。
因此,《宋书・乐志》载魏晋乐事,正是补《三国》无志之行为。郑瑷谓《宋书》:“诸志载及魏晋以来之事,盖以备前史之未备”[30]250,顾炎武谓:“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15]1447,余嘉锡谓:“沈约《宋史》,上括魏朝,盖因《三国》无志,用此补亡,斯诚史氏之良规”[13]146,张舜徽谓:“可以利用《宋书》八志来弥缝这一缺憾”[14]396,凡此皆肯定其补志行为。郑锦扬也说为何此“断代史设通史性的志书”?“不是其不懂史体,而是其有意所为”,乃“为补前代史书之不足”“《宋书・乐志》之设和贯通汉魏晋宋”“是其补《三国志》无乐志之缺”[31]29。
2.《南史》《北史》
《南北史》皆李延寿撰,《南史》记南朝宋、齐、梁、陈四国史事,《北史》记北朝魏、齐、周、隋四国史事。对《南史》《北史》无志原因,历有多说。其一,认为李延寿没必要写志。“唐修《五代史志》或隋志,李延寿是参与其事的。他是在这同时编修南北史的,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再修南北史志”[32]78。其二,认为李延寿没能力写志。修史时史志最为难写。柴德赓认为,李延寿撰史长于本纪列传,而对主载典章制度之史志则“不能理而董之,故一概不录”“延寿不修南北史志,或由于此”。继而认为此乃二书缺憾之一。柴说并非孤例,古人多认为李延寿拙于官职研究,王盛鸣谓其:“学浅识陋,才短”“全不识朝廷官爵体制。”①柴德赓著.史籍举要,《大家小书》系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32、138.[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91,407.对于陈寿是否有才学之事多有争论,本文不做过多展开。
我们认为,李延寿曾参与修撰五代史志,他自己亦谓:“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33]3345,说明他对史志并非完全不懂。《南北史》无志,当是其已参与撰写五代志,曾庆鉴认为“《南北史》之所以只著纪传而没有再作史志,除了别的原因外,可能就是有了《五代史志》的缘故”[34]391。且正史中南北八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皆有志,凭其一己之力撰出超越他人之作,确属难事,故于此略之。
故欲明南北史乐志,可于《隋书・音乐志》求之。赵翼谓若:“观南北史者,当参观《隋》志也”[11]174,张舜徽云:“今人每苦读《南北史》时,无志可稽,其实《隋书》十志,可以补《南北史》之不足”,《隋》志:“自然可以当《南北史》的志来读。”[35]396亦可从南北八书中求之,唐代开元中洋州刺史赵匡曾建议开科取士考《南史》《北史》时,要求将二史与南北其他史志结合一起,凡“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36]423。
后世有为南北史补志者,清人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凡十三卷,有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诸志。后录于《二十五史补编》,可以参考。
(二)鄙而不足写
此例认为,该朝礼乐粗鄙而不发达,达不到周代礼乐标准,没有为其写志必要,故略而不写。即后文方苞所云:“汉之乐既无可次”“无可陈者”、郭嵩焘所云“不足言”。
此类现象的撰写与否,是在该朝礼乐是否合乎周代正乐观念之下做出的取舍,是古人崇雅斥郑之表现。前文所记何承天说吴朝无雅乐,故《晋书・乐志》无吴乐事,亦是这一表现。
《史记・乐书》《新五代史》即为此例。
1.《史记・乐书》
《史记・乐书》文本与《礼记・乐记》几乎相同,涉及汉代乐事者不多,此亦可视为无“乐志”之表现,②关于《史记・乐书》与《乐记》之关系及司马迁对此排撰态度比较复杂,有不同说法。本文姑从此说。故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谓:司马迁原著此篇乃“有录无书”。究其原因,世有多说。或曰是篇已撰而后亡佚,褚先生补之,若张晏谓迁没后亡十篇;③《汉书・司马迁传》“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记》《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2724.或曰汉无雅乐可写,故司马迁不得已而转载他文。此说以沈约、方苞、茅坤、郭嵩焘、魏元旷为代表。本文从后说。
沈约在《宋书・志序》云:“《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止抄举《乐记》”。方苞认为,司马迁如此写作原因在于汉无雅乐,写时无可依据,只能“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于《读〈史记〉八书》云:“汉之乐,自文景以前习常肄旧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虽尔雅,然自《青阳》《朱明》《西皥》《玄㝠》而外,多谀诞,且非雅声。其甚者如《太乙马歌》,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盖伤汉之兴,几无所谓礼乐也。故于四时之歌明著其旨,曰:‘世多有,故不论’,则非为之而未具明矣”,故其乐“无可次”。又谓:“序乐至此,则更无可言者矣”。并认为司马迁否定汉家礼乐制度,其《礼书》:“是篇之义,盖痛古礼遭秦而废,历汉五世而终不能兴也”。又认为汉代所行礼仪与周代礼仪不合,无可书之事,“太史公序《礼》《乐》而不条次为书,盖以汉兴礼仪仍秦,故不合圣制,无可陈者,郊庙乐章并非雅声”。只能记录古代礼乐,以阐发汉事。唯《太一之歌》与己意相符,故录之。[37]309、319因此,方苞之意并非说司马迁认为汉代无乐事,而是这些乐事“所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不合圣制”“叙述出来很可能对后来人发生不良影响”[38]519,故略之。
茅坤亦认为:“汉时古乐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时已无可求矣,故太史公作《乐书》,特述《乐记》之言而成文”。[39]郭嵩焘认为,司马迁本意在于,三代礼乐无可证明,而秦后礼乐又与古不合而不足言,故于《史记》仅立其篇名而空其文字,并载《乐记》文而明礼乐之义。谓:“太史公《礼》《乐》二书,皆采缀旧文为之。仅有前序,其文亦疏缓。礼乐者,圣人所以纪纲纪万事,宰制群动。太史公列为八书之首,而于汉家制度无一语及之,此必史公有欿然不足于其心者,故虚立其篇名而隐其文,盖犹《叔孙通传》鲁两生之言‘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但与明其义而已。三代礼乐无复可征,秦汉以下不足言也,此史公之意也。”[40]124魏元旷亦谓:“汉武之乱,正以礼乐不修,其礼乐不修,正以诸儒不达礼乐之旨。故详其意,不详其器,非独慨汉之礼乐不兴,亦修明其说,使后之诸儒不惑也。”[2]127
2.《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全书有本纪、列传、世家而无志,更无乐志,仅有与书志相同的《司天考》《职方考》。
(1)无乐志的原因
对于欧阳修不为五代史写“乐志”的原因,人们认为欧阳修贬斥五代礼乐。此书无乐志,与欧阳修对五代礼乐的认识有关。欧阳修认为,五代时期混乱割据、礼崩乐坏,其于《新五代史》云:“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41]188,其“礼乐文物皆虚器也”[40]333“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40]173。感叹:“呜呼,五代之乱极矣”[40]369。五代十国时的礼乐制度无甚可取,故此书无礼乐之志,于卷五八云:“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清人何焯从其说,云五代“纲纪文章扫灭无余,所不毁者,惟天地而已”[42]396。赵令志说:“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考虑到五十几年辰光,经历了五个朝代,实在政局混乱不堪,制度不全,也难为后世所效法,所以中立《司天》《职方》二考,考即为志,把其他制度一概删除不写。”[34]151
《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是《新五代史》体例设计的重要原则”。然五代时期与此相反,“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40]370“也正因此,《新五代史》人事的‘不正’使礼仪无所措,故缺言人事之志”。[43]82这与北宋崇尚春秋学、尊王攘夷观念有关,使有宋一代对君臣纲纪混乱的五代持否定态度。五代“从宋代开始,一直被视为黑暗时代,文物毫不足观”。[44]68除欧阳修外,宋人对五代之事亦多有微词,如李照云:“五代之乱,雅乐废坏”。[45]2948王安石亦贬低五代之事,曾劝欧阳修不要写《五代史》。后世记其言为:“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46]14或记为“荆公曰‘五代之事不足书,何足烦公”。[47]35
其实,五代尤其后周时期,亦有重要的礼乐之事。如窦俨等《大周正乐》在后世有很大影响,宋人陈旸《乐书》、李昉《太平御览》、元人马端临《文献通告》等均有其大量引文。故欧阳修只肯定五代中的后周礼乐,于《周本纪》云:“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在《周臣传》云:“世宗之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制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之遗文。”他肯定王朴所定雅乐对宋代的深远影响,云“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其所作乐,至今用之不可变”。
(2)后世批评其无志
欧阳修对五代的否定受到后世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五代典章制度有承上启下地位,而是书不载,于此而言,不及《旧五代史》。谓:“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于文献。”[7]34今人亦批评其言过其实,认为他,“说得太过分了,而且太不符事实”[43]68“把五代十国的经济文化成就,全部抹杀”[48]35。
(三)已写而亡佚
此类正史“乐志”本来已经写成,嗣后流传过程中亡佚,形成该史无“乐志”现象。《后汉书》即为此例。今本范晔《后汉书》无乐志,据文献记载,《后汉书》当有《礼乐志》,后亡佚。
1.写作情况
今本《后汉书》本纪、传由南朝刘宋范晔撰,八志乃南朝梁人刘昭①八志: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和舆服志。宋人陈振孙、清人钱大昕、邵晋涵、赵翼、王鸣盛、李慈铭等对此志何时由何人并入,有多说(又若北宋孙奭)。本文姑从此说。从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取补,中有“礼仪志”而无“乐志”。故沈约谓:“马彪《后书》,又不备续”[27]204,乃“对司马彪《续汉书》不续《乐志》更引以为憾”[8]81。王先谦谓其:“《礼仪》不言乐”“与范之《礼乐志》殆必不侔”,故此补亦“未足弥范氏之憾”[49]179。
范晔撰写是书体例本有十志,然未全部完成。且其本已写出《礼乐志》,后因刘义康案而亡佚。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云:“范氏撰《后汉书》,原定十纪、十志、八十列传”[48]175,说明他有写志之意。范氏尤崇《汉书》之志,云其:“唯志可推耳”。遂有意仿《汉书》体例作志,谓:“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①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殿本《后汉书》将此作为序刊于书末。认为须兼《汉书》所有之志而作,说明他最初已打算写《礼乐志》。唐人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云:“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50]90
沈约认为,《后汉书》志是谢俨受范晔之托而写,于《谢俨传》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②[宋]范晔撰《后汉书・皇后纪下》“在《百官志》”李贤注引,中华书局,1965:457. 今本沈约《宋书》及李延寿《南史》均不见《谢俨传》。《郡斋读书志》:“晔令谢俨撰志”、《四库全书总目》:“以志属谢瞻”及徐元勇云范晔:“与友人谢俨合著《礼乐志》”[51]24皆由此而来。学者若王先谦、谭绪缵[52]175、力之[53]279等人多怀疑《谢俨传》之说,当是“范晔实欲自作十志”[54]59。刘汉忠亦怀疑此说,并举如下理由:(1)《南史》无《谢俨传》托付之说。认为,凡“《宋书》所载稍详之人物,《南史》均有传”,且《南史》有“好载异闻”之特点,若《宋书》有此传、此说,《南史》亦当有所反映;(2)与李贤同时代的刘知几无此说。李贤注《后汉书》时引用此文,然刘知几仅云:“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3)极为自负的范晔不可能托付谢俨此无名之辈来撰写;(4)范晔曾明言自己欲作志、于卷内发论,不可能托付给他人。(5)刘昭注《后汉书》时亦无此说。最终,刘汉忠认为此说:“盖章怀一时疏忽而张冠李戴。”[55]121
沈约认为十志已全部写完,《谢俨传》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56]457,认为范晔委托谢俨撰写,谢氏已经“捜撰垂毕”即已经撰写完毕。后因范晔下狱而死,谢俨惧受牵连而将志稿销毁。王先谦认为沈说不可考而存疑,范晔没有将十志全部写完,且后来全部亡佚,“纪、传先成,十志未及遍作,久遂全佚”。至于谢俨所毁者当非十志全部,而是未写完成的篇章,“特指余志未成者也”。因为据《南齐书•文学传》,在齐代尚能见到范晔《百官志》,一直到梁代方亡佚。范氏已完成之志的数量,王先谦总结有《百官志》《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五志,云:“范有《百官志》已见《帝后纪》,有《礼乐志》《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有《五行志》《天文志》见《蔡邕传》。”[48]175除此五篇外,刘汉忠据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认为又有《律历志》《郡国志》。③刘汉忠.说范晔《后汉书》之“志”[A].张越.后汉书、三国志研究[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23。又,唐初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曾引“《后汉书・郊祀志》”之文,又题为“出范晔《后汉书》”。刘先生认为此条不足信,第126页。(原载《文献》1997年第4期)如此则其十志已撰七志,而非王先谦所云:“十志已具其六。”[48]179
我们认为,至少范晔部分书志如《礼乐志》等已撰写并载录于《后汉书》。范晔撰《后汉书》时,沿用司马迁发明的“互见法”:“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写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相互补充”,即凡“本传不载或略载该传主的某事件,而详见于其他传记”[57]80。范晔用此法作史,若与志互见者,凡在纪、传中提及某典章制度时,均建议读者参考相关书志。如在《皇后纪下》注明若欲知皇女“职僚品秩事”事,建议参考该书《百官志》。“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在《光武十王列传》注明若欲知刘苍与公卿议修礼乐之语,建议参考该书《礼乐志》《舆服志》。“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在《蔡邕传》注明若欲知蔡邕论灾异变故之事,建议参考《五行志》《天文志》。“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此互见体例直接说明范晔至少写出以上五志,且已随纪、传并录于书,并用“互见法”贯串三体。
因此,范晔原本《后汉书》本有《礼乐志》,只是在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亡佚。故刘昭援司马彪《续汉书》补志时,将其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而谓“寻本书当作《礼乐志》”[58]2。此即据范书体例而审《续汉书》志。郑樵《通志・总序》谓范晔:“不敢作《表》《志》”“似为偏激之词,而非确切之论。”[59]12
2.《后汉书・礼乐志》内容
此志虽已亡佚,然在《后汉书》他篇间有提及。其可考者,若刘苍与公卿议修礼乐之文,《东平宪王苍传》载“(永平二年)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李贤注:“其志今亡。”[55]1433故此“乐志”当有光武庙中登歌及舞佾的记载。
3.写作特点
对于此志体例,范晔自己总结:“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认为包括《礼乐志》等十志有如下特点:(1)事简而文义尽显,强调对文义的重视。(2)为突出其文义,遂于文中因事而论。(3)文义的主要内容与目的是为了明政教、正得失。
具体到编撰《礼乐志》的指导思想,当为“崇雅斥郑”的儒家礼乐思想。据《宋书》本传,范晔自幼通“晓音律”,尤“善弹琵琶”[27]1819、1820。对自己这一音乐技能,他在自述中评价为“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55]2。他以自己弹奏琵琶这一俗乐器而自责悔恨,说明其礼乐思想仍以周代雅乐为最善,而以俗乐为讥。
(四)写而编于他处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皆仅有本纪、列传而无表志,其志编于《隋书》,即“志则总之于《隋书》”[11]174, 故《隋志》即“五代史志”。同样,其“乐志”编于《隋书・音乐志》。
梁、陈二代典章制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陈寅恪云:“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60]1,认为二代是隋唐制度的本源之一。然而记载二朝历史的《梁书》《陈书》却无“志”以载之,究其原因,臧世俊认为是撰者不重视史志使然。以《梁书》为例,是书经姚氏父子两代耗时几十年撰写而成,若他们有意为梁写志,至少当有初稿,然史书并无对其志及初稿任何记载。说明父子二人对志并不十分重视。[61]29-33《隋书・音乐志》载有梁、陈乐事,“这些记录多少可补梁、陈两史不设乐志之失”[62]207。
以上仅论个别史书,且认为是该书体例之弊。其实就唐初修史体例而言,此当史官本来规划之结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书(《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修成,仅有纪、传而无志。贞观十五年诏修《五代史志》,①十志三十卷: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是配合五代纪、传而修”[63]47,“可以看做上一阶段五代史编纂工作的延伸”[64]95。此补记五代乐事,后入《隋书・音乐志》。故五史与五志修撰之始即已规划出体例照应之事,“当时发凡起例必有成说也”[65]409。
五代史志合编于《隋书》之因,首先,便于追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赵翼谓:“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11]174其统于《隋书》者,乃因“特以隋于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7]28,《经心书院续集》云:“五史并修于唐而隋居其末,志附于隋,盖以后而统前也。”[66]317顾炎武亦云:“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杨宁校曰:“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15]1447其次,与贞观年诏修五代史体例规划有关。五史纂修计划本为撰成一书,故与其对应之补志亦合为一书。十志纂修之初便是与纪传合编一书而撰,五代史志“当属稿之初已议定编入《隋书矣》”。[67]3《隋书・礼仪志》“事见谨传”语,乃“互见法”对应《周书・于谨传》之明证。刘知几云太宗:“命学士分修”,书成而“合为《五代纪传》”,然“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遂又诏史官撰志。[49]96故四库馆臣驳前人《隋》志“兼载前代”断限之讥,乃“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后人五史各行”,[7]28吕思勉亦云:“《隋书》未与《梁》《陈》《齐》《周书》分也。”[68]1101辛德勇谓五者:“按照最初的纂修计划,本来应当是统一分工纂修并合编在一起的一部书”,而“‘五代史志’本为上述五‘书’之志”“此十志本来并非专属于《隋书》”“按照原定编纂体例,纪传和志这两大部分内容,本来应当合编为一书面世”,辛德勇对此有详细考辨[69]207、209、210,此不赘述。
故张舜徽谓“《隋书》十志”:“实为梁、陈、齐、周、隋五代作,所以又称‘《五代史志》’。”[14]90后人每论五代史书,多拆《隋》志随代附于其后。赵翼主张似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各史之后,以成完书,[11]174张舜徽谓此说:“最为有识”[14]90,范文澜亦谓:“其见甚卓。”[70]70《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谓:“梁乐制在《五代志》中,载于《隋书・音乐志》,今附记于梁后,以便稽考。陈、北齐、北周仿此。”[28]356
因先有《隋书》后有《五代史志》之“乐志”,纪传、志修撰者与时间皆异,遂有二者义例、内容首尾互不照应之差缪。首先,义例名称不对应,《隋书》列传三处称其《音乐志》为“音律志”,这“就是因为是纪传与志分写的结果”[71]60。如《牛弘传》有“事在《音律志》”;《郑译传》《裴政传》有:“语在《音律志》”之语,钱大昕谓:“今《隋史》有《音乐志》,有《律历志》,无所谓《音律志》也”,故讥之,云:“史不出一人之手,欲其首尾义例无一踳驳,固是难事,然不应如是之甚也。”[72]448其次,内容安排不对应。裴政本传载其:“尝与长孙绍远论乐,语在《音律志》”,而今本载:“裴政论乐事,见《周书・长孙绍远传》,不见本书《音乐志》”[73]1567,此亦说明修撰《隋书》时之体例与后来《五代史志》内容的不统一。
同时,《隋书》此体例不一亦说明贞观十年所修是书,在原初体例规划时已有随书设“乐志”之安排,只是因为某种原因罢省而统于《五代史志》。谢保成谓:“如果作一点猜想,或许诏修《隋书》纪、传时即有修志的设想,设想之中有音律、舆服、威仪等志,因而在传记中才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有三卷书、三人传记都用‘在《音律志》’的说法,似乎在当时确有某种约定。”[62]51至于其他四史最初是否如《隋书》,则不可考。
四、结 语
历代正史“乐志”是我们了解该朝代乐事的主要依据,历代“乐志”撰写行为是其对该朝代“礼乐观”的集中体现。因此,欲究历代乐事,不仅要关注有“乐志”的史书,也要关注那些没有编录“乐志”者。在这有、无的取舍中,反映了该时代礼乐的真实面貌。
以上正史虽无“乐志”,然通过对不同原因的梳理,亦可窥见该朝礼乐之事,亦可知道古代编史者礼乐思想。因此,我们在研究历代乐事时,不仅要关注那些有“乐志”之正史,也要关注那些没有“乐志”之正史及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