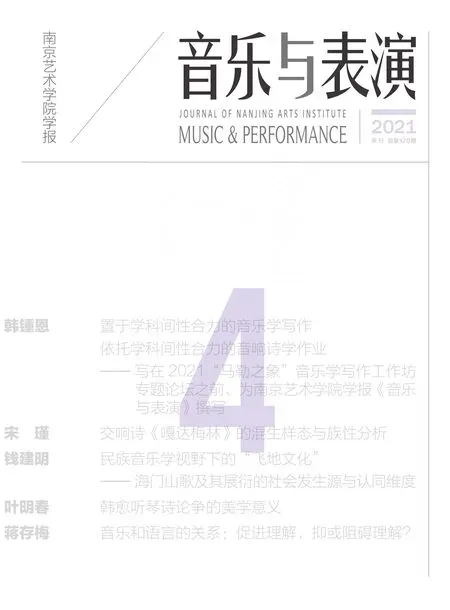从“新潮”到“返朴”:1979—2019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述论
芮 雪(中国音乐学院 附中,北京 100101)
引 言
20世纪的中国,从纷乱的硝烟战火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走过。中国音乐,也由此经历了从传统音乐一元发展到现代专业音乐多元格局的演变。受西方专业音乐创作思维影响,1915年,刘天华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首二胡独奏曲《病中吟》,标志着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开始走上中西结合的创新创作之路。1918年,郑觐文创办的“琴瑟学社”以改造旧乐、创造新乐为目标(后更名为“大同乐会”),主张中西互补,提出“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挚其精华,提其纲领,为世界音乐开一新纪元,以完本会大同二字之目的”[1]的宗旨,重在乐器改革基础上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转型建设,影响深远。1935年前后成立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队,提出“采纳西洋管弦乐队的组织法原则,建立了环绕弓弦乐器为核心的立体式乐队声部结构”宗旨,主张以弦乐器为乐队核心,集聚了大批优秀演奏家,包括后来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初创和建设期的开山人物甘涛、彭修文等均出自该乐队组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中国民族器乐发展进入全面探索的建设阶段。这一时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戏曲研究院等专业研究院所相继建立,还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馆、艺术馆、音乐工作组等机构,民族乐理论研究和民族乐器演奏专业教学迅速发展。同时,在由各级政府组织的民间音乐汇演中,涌现出大批优秀民间演奏家,如弹拨乐代表赵玉斋、高自成、罗九香、林石城、卫仲乐,吹管乐代表冯子存、赵松庭、刘管乐、任同祥,拉弦乐代表孙文明、张长城,以及古琴代表管平湖、吴景略等。1950年以来,北京、上海先后建立了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乐队(1952)、中央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中国电影乐团民族乐队(1953)、上海电影乐团民族乐队(1956)、上海民族乐团(1957)、中央民族乐团(1960),以及由各省区组建的较具完整建制的专业乐团二十余支。早期这些乐团大多依托电影配乐、广播艺术的初创背景而成长,作品方面以彭修文、顾冠仁等改编、移植和创作的《春江花月夜》《秦•兵马俑》《图画展览会》《东海渔歌》等为代表。中国民族器乐在作品创作领域不断向西方学习,通过模仿、移植、改编再到融合中西进行作品创作的前沿探索,不断拓展和丰富了作品的体裁、题材、技法,为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背景下的 中国民族器乐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1979年以来的四十年间,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在时代荡涤中,完成了从探索向纵深发展的过渡与转型。以乐器类种为划分依据,在大型协奏曲创作方面主要代表作如下:

作品类型 作曲家、作品名称及创作年代琵琶协奏曲 顾冠仁《花木兰》(1979)、赵季平《祝福》(1980)、唐建平《春秋》(1994)、王丹红《云想·花想》(2013);古筝协奏曲 李焕之《汨罗江幻想曲》(1980)、刘锡津《北方生活素描》(1980)、何占豪《临安遗恨》(1992)、周煜国《云裳诉》(2002)、王丹红《如是》(2011);二胡协奏曲吴厚元《红梅随想曲》(1980)、刘文金《长城随想》(1982)、关乃忠《第一二胡协奏曲》(1987)、《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2002)、《第三二胡协奏曲-诗魂》(2006-2007)、《第四二胡协奏曲-爱恨情仇》(2008)、《第五二胡协奏曲-辛亥百年祭》(2011)、《风雨思秋》(2011),王建民《第一二胡狂想曲》(1988)、《第二二胡狂想曲》(2001)、《天山风情》(2001)、《第三二胡狂想曲》(2003)、《第四二胡狂想曲》(2010);竹笛协奏曲 郭文景《愁空山》(1991)、杨青《苍》(1991与交响乐队、1998与民管乐队)、程大兆《陕北四章》(1996)、王建民《中国随想No.1》(2013);扬琴协奏曲芮伦宝《第一扬琴叙事曲-莫愁女》(1981)、《第二扬琴叙事曲-文成西行》(2001)、《第三扬琴叙事曲-香妃情》(2004)、《第四扬琴叙事曲-吴越随想》(2006),刘寒力《金翎思-满乡随想》(1989),房晓敏《莲花山素描》(2001)、《清风明月》(2018),王丹红《狂想曲》(2011)
这些作品具有宏大的规模,多以表现厚重深刻的历史、悲悯交织的爱情、奇幻绚丽的传奇、秀美多姿的风光等题材。自1980年代以来,大批具有扎实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学习背景的专业作曲家成为创作主体,他们“以更为扩展的音响表现手段,置身于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新的发展之中”[2]:在作品题材选择方面,多以中、西方哲学思想或理念为切入,进而在作品内容的表达中展开一系列或关于时代与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思考与感悟;在创作技法方面,往往打破前期老一辈演奏家群体中西结合、以传统为主的创作思维模式,在西方音乐作品创作思维指导下,颠覆性“反叛”传统,创造性地将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新思潮渗透其中;在演奏技法的具体运用方面,则追求对音响效果尽可能多样化地呈现与把握,也因此创造出许多新奇的特殊演奏技法和乐器组合方式。除上述大型协奏曲之外,以谭盾、郭文景、陈怡、杨青等为代表的作曲家还创作了包括《双阙》《觅》《竹迹》《野火》《中国狂想曲》《圈》《灵动》《原风》《圈》《心灵》《狂想曲》《阿曼尼沙》《德音》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在音乐语汇和技法运用方面,不断打破传统乐器固有性能和演奏技术难度,民族器乐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得到大幅提升。此外,大型合奏作品的创作也蓬勃发展起来,主要代表作有:何训田《达勃河随想》(1982)、彭修文《秦•兵马俑》(1984)、谭盾《西北组曲》(1985)、唐建平《后土》(1997)及赵季平创作团队(韩兰魁、陈大兆、景建树、张坚等)《华夏之根》(2005)、《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2012)等。这些作品有的具有现代音乐的绚丽多姿,有的融汇古典文化的静谧典雅——对中国民族器乐整体作品质量提升,以及演奏技术和艺术表现力的进一步挖掘,具有积极意义。
1980年,胡登跳创作的《欢乐的夜晚》为当代小型民族器乐重奏作品创作打开了新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一批基于各音乐院团的演奏家、教育家先后建立起“五朵金花”“丝弦女”“华夏”“卿梅静月”等不同类型的民族乐器演奏组合。由中国音乐学院十几位演奏家于2008年组建的“紫禁城”室内乐团,多年来不断深入民间采风,对传统乐曲《寒鸦戏水》《线戏》《上楼下楼》等进行了再度诠释,同时改编《梅花操》《夜深沉》《华州韵》等乐曲;在现代作品创作与演绎方面,邀请高为杰、秦文琛、高平等作曲家创作了《风声》《听谷》《四不像》等作品;在乐器组合方面,打破传统界限,纳入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音乐或满含对中国传统文人情怀的追思与感悟,或倾注对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思考与感知。“紫禁城”室内乐团根植传统音乐文化,在作曲家与演奏家的合作中,积累起涵盖不同种类和风格的作品,成为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深具传统文化传播活力与影响力的室内乐团。这一时期另有各院团组合先后创作演出了《阿里里》(王建民曲)、《心雨》(唐建平曲)、《悠然》(艾利群曲)、《竹枝词》(郭文景曲)、《敦煌》(姜莹曲)、《独克宗》(李博禅曲)、《皮五辣子》(徐之彤曲)、《翡翠》(王丹红曲)、《折桂令》(符译文曲)、《芬芳》(朱琳曲)、《秋日舞蹈》(芮雪曲)、《太阳•玄鸟》(李复斌曲)等作品。
2013年起,中央民族乐团先后推出了《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玄奘西行》三部民族音乐剧目,借由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器乐演奏家饰演人物角色,将演奏与剧本、舞台情景相结合,为新时期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发展和作品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2017年,王丹红为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创作的时长近90分钟、包括序《信天游》《壶口斗鼓》《祈雨》《五彩的窑洞》《刮大风》《赶脚的人》《朝天歌》及尾声《永远的山丹丹》等八个段落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永远的山丹丹》,运用了多种曲式和表现形式,融合陕北民歌、道情、碗碗腔、唢呐、说书等黄土高原民间音乐及其固有体裁,将来自民间的陕北信天游原生歌手、说书人以及四十余人的大唢呐乐队纳入演奏群体,实现了唱、奏交互。其中,《五彩的窑洞》以弹拨乐为核心,弦乐和管乐为辅,旋律来自《三十里铺》曲调,乐段简洁精练,表现了陕北人民清秀淳朴的个性。该段虽然只有7分钟演奏时长,却起到了重要连接与调适作用;《赶脚的人》一段以黄土高原地区代表性民间乐器板胡为领奏,采用《兰花花》《脚夫调》《泪蛋蛋抛在沙嵩嵩林》音调并予以必要延伸,突出板胡质朴明亮的音色特质。整部作品的创作保留和强调了地域音乐的原生特质与精神内涵,作曲家以其深入的实地采风,扎根民间音乐的肥沃土壤,深入学习与研究黄土高原地区民歌音调结构,成为这部作品最终得以深刻诠释地域文化而广受赞誉。
二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3]历史的道路从不平坦,却总有人能够坦荡无畏走过艰险荆棘,坚持弘扬民族文化的崇高和壮美。1981年刘文金的二胡与乐队协奏《长城随想》创作完成,1982年由闵惠芬首演,上海民族乐团协奏。该作品创作缘起于作曲家访美期间触景而生的乡情,采用标题性的《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乐章宏大体量,表现中华儿女气动山河、不畏战火的坚忍顽强精神,作品语汇凝练戏曲音乐元素和板式变化与展衍方法,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民族器乐作品的长篇协奏创作模式,自此大量史诗题材的长篇、中篇规模民乐协奏作品逐渐涌现。作品开篇【关山行】在民族管弦乐队合奏的宏大背景中,引入二胡“庄重而缓慢”的主题乐段,旋律凝练戏曲音乐元素,深沉悠长,由描绘“长城”形象抒发对家国河山历经沧桑巨变的追忆、热爱与崇敬之情。作品二三乐章由开篇发展而来,借鉴京剧鼓板节奏变化和速度的快慢对比,在乐思推进中巧妙形成二胡与乐队间的错落细腻对话,缅怀先辈奋斗精神,砥砺吾辈前行。行板段运用了跨度较大的音程和连续的三连音,在继往开来的行进中引入乐曲终章。
2004年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完成一部反映山西音乐风土的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由作曲家赵季平、景建树、程大兆、张坚、韩兰魁联合创作。他们多次深入晋地记录民间曲调,听音寻根。第六乐章《古槐寻根》的创作即缘起于赵季平先生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的采风体验。作曲家秉承“创作要到老百姓中去”的理念,取材晋中秧歌曲调,作品结构严谨,朴素深情,如苍翠古槐般,淡然看尽世间万象,守护着游子心中的一片柔情故土。作品引子部分长达52小节,运用大量弦乐长音与休止,这样的创作思维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远近虚实和意境渲染相合。清代笪重光《画荃》中讲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绘画中的留白与书法中的“计白当黑”和中国戏曲舞台的动静虚实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所强调的意境之美,也体现了中国文人淡然风雅的朴素情怀。作品慢板—快板的连接句由二胡和笙先后完成两个乐句,这样的布局突破繁复变化,于清丽淡雅中,诉说人世沧桑和家国兴衰,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歌谣文理,于世推移。”1992年郭文景三乐章竹笛协奏曲《愁空山》创作完成。这部作品创作缘起李白《蜀道难》,用竹笛乐器特有的颤音技巧和气息控制,突破性地运用了大量持续的半音进行,横向和纵向不协和音程的进行在传统民乐作品以及当时的创作类作品中都较少使用,以诗入乐,以山水“比德”,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追寻器乐声腔化的音响探索与实践,为作曲家们打开了跨入挖掘中国民族器乐音响效果的新世界大门。作品第一乐章Lento,使用了9小节长时值二度上行单音模进,这种引入方式极具诗人气质,之后紧接的是一段由连续二度、三度三连音下行和三度、四度的上下行跳进,与之前45拍单音持续形成疏密有致的色彩渲染,每两小节出现一次的半音长颤音,充分发挥了乐器音色特质,竹笛乐器与演奏气息的微妙控制,形象塑造了蜀道行路的艰难以及蜀地风光的奇幻朦胧与蜀人无畏自得的淡然洒脱气质。
1987年作曲家王建民应邓建栋之邀创作完成《第一二胡狂想曲》。作品一经推出便因其创新性的打破传统音调束缚又不脱离调性的整体布局以及在二胡演奏技术上的实验性探索而引起轰动与讨论,至2019年《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首演,王建民“狂想曲”系列已然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二胡艺术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
《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作品创作秉承了作曲家一贯的创作理念,每部狂想曲均取材一方民间音乐,然而主题音调从不是来自具体的某一地区传统某一个单一曲调,取之民间而又归跃然固有传统,取材蒙古族长调和短调音乐核心音型和羽调式色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奏展衍。另外,该作品有别于以往四首还在于它的标题性——赞歌,是作曲家用音乐的方式对新中国70年辉煌的由衷致敬。该曲第一部分Andantino以弱起的八分音符四度、五度上行至小字三组2的三拍长音,这种音型与北方民歌中的“上长音”相仿,意在开篇抒怀,而后六度、五度下行至七拍长音持续和再度上行,主题旋律在悠扬的心态中逐步展开,来自蒙古族民歌所特有的苍劲深沉无疑为作品铺陈了厚实稳健的曲风。“狂想曲”系列拉开了现代二胡演奏技术训练的新要求,实现了作品创作与表演实践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快速跳进与同音型反复在推进作品整体乐思发展的同时,为二胡演奏者提出了技术训练的无限可能,这种实验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乔建中在《20世纪的中国器乐艺术》一文中提道:“传统与现代、技艺与观念、继承与创新,既是乐曲创作必须面对的选择, 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个社会进行音乐文化建设必须严肃对待的三对关系。”[4]上述作品的创作理念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和美学思想,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乐思发展、语汇展衍等方面无不体现深厚的人文情怀。同时,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深耕民间,与时俱进,在意境勾勒渲染和演奏技法与乐器音响音色实验性探索与挖掘方面,创造性地打通了音乐与美术、戏剧、文学等门类艺术壁垒,既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为民族器乐艺术的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实现了从创作到技艺传承的于良性循环。
三
“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基于“五四”以来的初创(1900—1949)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二十年(1949—1966)的全面探索和建设,彭修文、顾冠仁等老一辈音乐家将毕生精力汇聚于创作实践的最前沿,积累了大量富于创新时代精神的经典民乐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器乐艺术从作品、演奏到教学、实践与理论诸方面逐步走上更为多元和系统的再度发展期。1979年后,更多具有全面西方音乐学习背景的专业作曲家开始介入民乐创作领域,谭盾、瞿小松、陈怡、秦文琛等人的作品以西方文化新思潮为指导,打破传统边界,创作了许多新潮作品;刘文金、赵季平、关乃忠、高为杰、王建民、王丹红等跨越老中青三代的作曲家,对不同地域民间音乐品种的来源、特征和风格有着深入了解与认识,他们根植传统,以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为基,运用多元的技术手法创作完成了大量的独奏、重奏、合奏作品,创造了中国民族器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相关作品难度和广度的提升,促使演奏家们的演奏技术不断精进,大量的艺术实践,同时也促进了民族乐器制造包括形制、结构、音域、音质等方面的改良工作。迄今,由文化部、中国音协组织举办的中国民族器乐作品评选已过八届,每届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涌现,也为许多富于才华的青年作曲家创造了作品推广的良性平台,从中央到地方各专业民族乐团在连续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也积累了众多经典曲目而促使乐团建设趋于完善。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的代表性著述有李纯一《上古出土乐器综论》、高厚永、李民雄《民族器乐概论》、刘东升等《中国乐器图鉴》、袁静芳《民族器乐》、王耀华《三弦艺术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查阜西琴学文萃》《中国古琴珍萃》等。自1987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编撰“中国音乐年鉴”,收入乐谱出版物、有声数据出版物以及专著文论等。
“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5]2017—2018年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各高校及相关出版单位共同召开了三次有关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立的学术研讨,就理论到表演体系建立为题,从不同学科研究视野下对当代民族器乐从教学、创作到表演实践进行了系列讨论。老一辈音乐家用他们扎实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时代以怎样的姿态迎来高速多元的冲击与碰撞,中国音乐都该走出属于自己的教育传承发展之路。中国的作曲家也应扎根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本土音乐为根,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专业音乐作曲技术,创作属于中国特有的具备中国音乐符号特征的音乐作品。中国作曲家作为创作主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就多年来的作品积累与创作实践进行必要的整理与反思,新时期的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也应该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