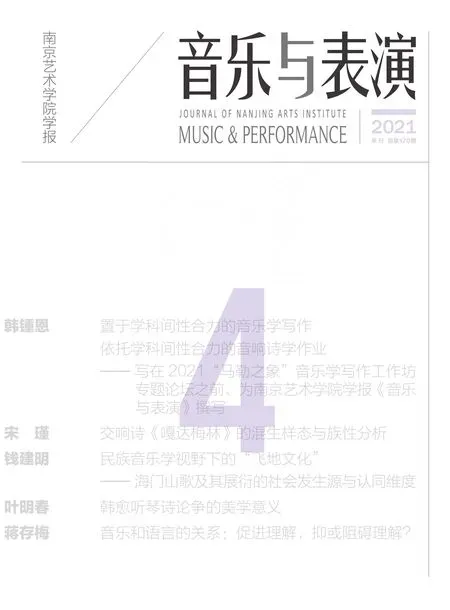探究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崇高之美
张智慧(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引 言
针对作曲家晚期创作的研究一直深受音乐学界的重视,马勒作为浪漫派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不仅突显出独具主体色彩和人性魅力的审美旨趣,而且还呈现出处于时代转折点所赋予音乐风格和技法上的混合性和开创性。《第九交响曲》作为马勒最后一部完整的大型音乐作品,它承载着马勒对世界、人生和死亡更加深刻的思考,在音乐语言和形式的安排与乐曲所传达死亡、告别内涵之间相互映衬,黄键以《第九交响曲》音乐文本中死亡内涵的显现方式作为切入点,探究马勒音乐死亡内涵的源起[1];张晨和维拉・米奇尼克通过不同角度揭示了该交响曲所传达的“告别”叙事逻辑[2][3];弗朗西斯卡・德劳恩通过解读第二乐章谐谑曲中兰德勒和华尔兹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探究该交响曲中的阶级、性别与现代性的问题[4];朱利安・约翰逊探讨了马勒《第九交响曲》中主体地位的问题[5]。但这些研究成果都未涉及基于感性聆听之上进行的音乐审美特性的研究,在对马勒生平事迹的整理和对《第九交响曲》的聆听体会的前提之上,本文选用“崇高”这个审美范畴,通过对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整体篇幅、配器编制、主题动机、调式运用、音响空间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研究,探究这部交响曲中所生成的崇高是如何体现的?又具有什么内涵?
一、“第九”崇高于外在体量上的显现
“崇高”(sublime)作为西方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产生于人与“他者”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诞生于从否定自我到肯定自我的转变之后,它的发展脉络与人类的不断自我觉醒、自我革新、自我反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面对存在,人类反观到自身的有限和荒谬、自身的虚无和悲哀,感受到真正的恐惧,继而在恐惧中不断体悟和超越,正是在超越之中,崇高之美相伴而生。崇高作为人类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的构成,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艺术内在思想,都可以发现隐匿其中的崇高,也显示出对其对象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外在结构上的无限大和内在思想上的超越性两个方面。至此,探究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崇高之美,应当着眼于该作品的外在体量和内在构成这两个方面。
(一)宏大的交响套曲
保罗・亨利・朗说:“他们认为表现工具的大小是和思想意念的大小成正比例的。”[6]《第九交响曲》是马勒经受了生活中的美好和苦楚之后对生命本身给出的回应,这是他直面恐惧、直面死亡、直面人性的一次呐喊。正是这部交响曲承载了深邃、伟大的内涵,唯有选用大型的音乐体裁才能与之匹配,才能在音乐中诠释对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思考。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马勒意图在音乐中囊括整个世界,传达来自他内心最深处的声音。无论是三重身份所给予无家可归的宿命感,还是所处时代所承受的失落感和无助感,或是死亡常伴身侧的恐惧感,都使他内心深处对死亡和命运有着深入的见解和感悟[7]。但唯有死亡真的来临时,这种直面死亡而产生的恐惧和无奈才催生了他对生命和死亡意识的最后升华,他开始面对自身的命运,面对“第九”的死亡传说,在1908年完成《大地之歌》之后,就争分夺秒地进入到《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中,并于1909年8月完成[1]19。
通过对众多指挥家所呈现版本的统计,《第九交响曲》的演奏时间平均为85分钟,可见这部交响曲的体量之大。该交响曲由四个乐章构成,分别为“第一乐章是慢速的、扩充的奏鸣曲式;二乐章是诙谐仿作性质的连德勒舞曲;三乐章是一个拙劣滑稽的回旋乐章;四乐章则是慢速带有变奏性质的终曲。”[1]22从乐章构思中可以看出,马勒并不拘泥于传统交响奏鸣套曲的形式,而是根据自我创作的需求精心安排、随心而扩,把交响套曲结构发展到极致,尽可能通过音响表现他内心所思所想,期于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急慢相衬、刚柔并济中构建一个宏伟的音响世界,使听者身临于这个亦真亦幻、无边无际的场域中,感受着乐曲所带来的震撼感和压迫感,在情绪层层递进中,并反观一切,同时又在反观中自我消解乐曲所带来的不快感,达到超越境界进而获得崇高感。故而,崇高感的产生需要宏大的音响效果和复杂的情感流变,而这两者正是需要音乐时长的不断积蓄和结构的巧妙设计。
(二)庞大的乐队编制
精雕细琢的时间长度是《第九交响曲》生成崇高感的一个重要载体,但对于一部音乐作品,这只是横向思维的显现,除了宏大的时间跨度以外,乐曲纵向布局和构思也是在外在形式上生成崇高感的另一个关键点。康德对“数学的崇高”给出这样的定义:“我们把那绝对地大的东西称之为崇高。”[8]康德还指出崇高的“大”属于鉴赏领域,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具体大小,绝对大是无限的,给人一种不可企及的广阔感,面对它时,我们心灵受到震撼,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9]而《第九交响曲》之所以能使人感受到无限之美,不只是因为马勒对乐曲广度的考虑,也得益于他对乐队编制的扩充和乐器运用的构思设计。
作为一位配器大师,马勒深知如何通过乐队编制和乐器使用来渲染气氛和刻画形象,进而勾勒一个宏伟世界。在《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中,马勒为了更好诠释生而为人的矛盾和对死亡的态度变化,对各个乐器组都进行了扩充和编排。在弦乐组中,除了五声部弦乐组之外又加上了两架竖琴,在整部乐曲的发展中隐射出马勒悲剧式生命中所经历的温情美好的回忆,为乐曲增加了色彩感和层次感;马勒钟爱的铜管组是由四支圆号、四支长号、三支小号(其中两支为F调小号)以及一支大号组成,他尽可能挖掘乐器的表现空间,以此获取更多丰富的音响色彩渲染,利用音色的对比来烘托出他面对死亡时犹豫不决的态度;木管组的配置就足见乐队的巨大,其由四支长笛、一支短笛、四支大管、三支单簧管、一支低音单簧管,以及一支小单簧管和四支双簧管构成,该乐器组在第二乐章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表现,如象征死亡内涵的大管上行音阶动机、单簧管所演奏的具有告别意味的主题旋律等;打击乐组一直是马勒交响曲创作中特殊音色的主要来源,它是由定音鼓、低音大鼓、镲、三角铁、铜锣、三支铃和钟琴组成,该乐器组成为了乐段结构划分的重要标示,同时加强了乐曲空间的深度和广度。[10]综上可知,《第九交响曲》的配器超出浪漫主义早期乐器设置,其庞大的乐队编制成为了诠释宏伟音乐内涵的载体,也为该交响曲崇高感的生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九交响曲》崇高之美的生成得益于大型体裁和乐队编制所烘托的震撼感和广阔感,在所构建的音响空间中,欣赏者感悟到了无限,心底油然而生一股振奋和感动,但崇高之美的生成也离不开内部构成上所展现出的令人沉思的人生命题,即从对死亡的恐惧到直面恐惧再到超越恐惧的人性诠释,也就是在这部交响曲的外在和内在的相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音乐世界中,欣赏者感悟无限,面对有限,超越虚无,在超越中获得无限的、最高的美,也就是崇高之美。
二、崇高于内在构成上的体现
笔者认为《第九交响曲》崇高之美在内在构成上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零散发展的撕裂感
第一方面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割裂式的动机和旋律;二是取消乐章之间的联系。在《第九交响曲》中,音乐语言上并不是以往交响曲中宽广、流畅的歌唱性旋律,而是在动机和旋律上呈现出碎片、零散的发展特征,动机之间往往被休止符所割裂,其长度大部分仅在一小节之内。[11]在乐曲开始处象征马勒心脏衰竭的“死亡动机”①该动机出现在乐曲第一小节,由小提琴和圆号共同完成象征死亡的切分节奏(X•X 0X•),这个节奏是马勒因患心脏病、不规则的心脏跳动而产生的,故称之为死亡动机。这一诠释最早是由威廉姆・里特(William Ritter,1856-1944)提出,其后,伦纳德・伯恩斯坦和查尔斯・阿曼塔也认可该观念。参见黄键.马勒音乐死亡内涵源起考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导师:王文澜.就极具代表性,一小节的长度因休止符的介入,类似于没有规律的心跳声,暗示了马勒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他在音乐语言风格上的拓展,更是他在情感体验和生命思考上的一种印证,显示出生而为人的矛盾感和撕裂感。这个表现手法贯穿于第一乐章,阿多诺称之为“分化和溃散”(disassociation and disintegration),并认为这是马勒晚期创作中最主要风格。[11]
此外,降低乐章之间的关联性也呈现出不集中的发展特征,马勒以往交响曲写作中乐章之间动机和主题的贯穿、乐章之间的关联和首尾乐章之间的呼应等多种表现手法,在《第九交响曲》中几乎不存在。②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在末乐章中马勒引用了第三乐章中的“环绕动机”。每一个乐章都有其自身的自主性,并在乐曲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其中最鲜明之处就是马勒在第四乐章的调性安排上并没有回归D大调,而是安排在bD大调上,显然是马勒为了贴近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情绪而精心设计。于他而言,D大调代表的是悲剧式的现实世界,bD大调象征着自我升华的澄明之境,意味着从对死亡的恐惧到超越恐惧而获得精神上的坦然和升华。这种零散发展的创作手法无疑是马勒所处时代、漂泊灵魂以及矛盾人性的体现。
(二)死亡意蕴的恐怖感
由上文可知,《第九交响曲》在创作上并没有采用以往交响曲中会使用的一些表现手法,相应就会降低该交响曲的统一性,但事实上这部交响曲的完整性是有目共睹的,那马勒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零散发展的交响曲具有统一性的?贝克尔认为:“(第九交响曲)每一乐章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交响曲的统一是仅仅通过整部作品建立起来的画面(气氛)来实现。”[12]而这个贯穿始终的气氛就是对死亡而产生的恐怖感。
第一、二乐章的呈现途径主要通过主题动机的发展喻示对死神的恐惧,在第一乐章中除了“死亡动机”不断涌现,该乐章中出现的大篇幅由连续小三度构成的“浮云动机”尤为阴森,该动机制造出不稳定性的摇晃感来预示内心的惴惴不安,同时也为第一乐章营造出源源不断的恐怖气氛。第二乐章中“大管的音阶动机”是由C大调中主到属而构成的五度音阶,演奏的文字说明为“笨拙而且粗鲁的”,像刻画了一位迈着沉重步伐的野蛮的死神形象,再次深化全曲的死亡内涵。第三乐章是通过采用代表死亡的a小调对死亡主题亦有喻指,对于马勒而言,调性不只是作为音乐发展的表现手法,而且也是音乐内涵的象征符号,a小调作为本乐章的核心调,同时与第二乐章C大调为平行大小调,无论是象征形式,还是音乐情绪上都表现出对死亡主题的诠释。末乐章是通过对《亡儿之歌》旋律的摘引呈现对死亡内涵的喻示,这部声乐套曲是马勒为他离世的至亲而创作,其音乐主题引用在末乐章中,不仅体现了至亲的死亡对马勒的持久影响,也表明了马勒对恐惧本身的直面和超越。四个乐章所营造出的恐怖气氛不仅增强该交响曲的统一性,而且还成了剖析全曲思想内涵的隐性线索。
(三)缓慢流动的超越感
从乐章布局来看,《第九交响曲》在马勒所有完成的交响曲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首乐章的行板和末乐章的柔板都采用了慢板乐章,而中间使用了两个较为活跃的乐章,马勒认为慢板是较于快板有更高的表现形式,如此安排也就把全曲的焦点集中在首尾两个乐章,马勒旨在通过音乐形式的创作表达对死亡的深度思考,为听众建立一个自我内省的空间,而慢板无疑是最适合的。相较困囿于死亡恐惧的首乐章,末乐章缓慢的速度更多是直面死亡的果敢和自我超越的升华,虽然首乐章中出现了“不完整的告别动机”③该动机开始于乐曲的第六小节最后一拍,由#F-E组成的下行大二度,笔者称之为“不完整的告别动机”,原因是完整的“告别动机”是由两个下行大二度构成,马勒引用的“告别动机”是出自贝多芬《告别奏鸣曲》(Lebewohl Sonata,Op.81)中的告别主题,由G-F-bE 组成的连续大二度下行,并在三个音节对应之处标明意为“告别”的“Le-be-wohl”,而连续两个大二度下行的“告别动机”出现在马勒《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第3小节,由F-bE-bD组成,笔者称之为“完整的告别动机”。[13],也未能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坦然,只是笼罩在死神梦魇下的无奈。
在经历第二、三乐章中与死亡和世俗的反抗之后,第四乐章出现了完整的“告别动机”和具有温情意味的“环绕动机”,两个动机都展现出马勒对内心恐惧的接受和安然,展现出对死亡深沉的思索和有限生命的超越,末乐章作为斗争之后的平静,慢板的使用毫无疑问为乐曲主题的深化和崇高之美的生成推波助澜。同样具有深刻表现手法的是末乐章大量使用了“逐渐消失”(morendo)的文字说明,出现次数不少于8次,熟悉马勒的人都知道,为更好贴近内心深处的音乐表达,他喜于对音乐作品进行详尽的文字说明,这种在慢速度的基础之上音响逐渐消失的表现方式是完成自我超越的关键一步,音响逐渐变薄、变小,营造一个分不清声响和寂静、几乎透明、至纯至净的超然世界,在这个生命共融的磁场中获得超越感,继而生成崇高之美。这种表现手法也展现出作曲家马勒将音乐个性化和复杂人性化的极致结合。
(四)生命叙事的崇高感
生命叙事是叙事的重要形式,指叙事主体表达自己对生活和命运的感悟、经验、体验和追求。生命叙事的起点及归宿都是对蓬勃的生命状态的渴望和追求,它把叩问人类心灵的意义、探求人类精神的出路作为自己的使命。[14]优秀的文艺作品都不会缺少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和追问,经典的大型音乐作品亦如此。笔者基于马勒的生命经历、分析《第九交响曲》音乐文本蕴含的隐喻、领会音乐传达的内涵,不难发现这部交响曲中有一条清晰的叙事思路:从第一乐章中对死亡的无休止恐惧,到第二乐章被死亡控制下的挣扎,再到第三乐章与死亡正面交锋的果敢,最后到末乐章对死亡坦然直视的无谓,体现出生命叙事以个人的方式追问整体性命题的特性,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用个性化的音乐语言把对死亡的恐惧、反抗和超越这一系列的内心变化呈现出来,表达出对生死和存在等问题的追问和体悟。
“生命叙事既要切入又要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以获得对人类生存本身的苦难的同情和超拔。”[14]在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深植于对命运的深切体验,以死亡作为叙事的线索,重视对生命存在和精神境界的探索和思考,通过生命叙事的方式展现出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过渡,显露人性深处和存在本身的复杂性,并在超越自身和虚无的同时获得崇高感,至高之美由此产生。
结 语
《第九交响曲》崇高之美的生成不只是因为马勒对整体篇幅、乐队编制、音响空间、音色搭配、力度对比以及叙事逻辑上细致入微的把控,更是因为这部交响曲所具有的艺术旨趣和思想内涵,它给予听者的是基于对人性刻画的一种动态的心灵运动过程,是从面对有限到感悟有限再到超越有限的生命诠释。正是在这超越之中,崇高之美得以生成,而这崇高之美就是面向个体存在的心灵回声,是直面人性弱点的生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