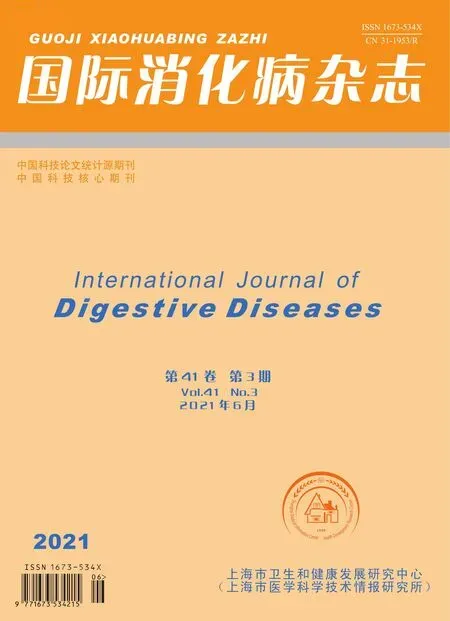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肠道免疫影响的研究进展
郑倩婷 孟立娜
人体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肠道菌群可促进肠道免疫应答、维持免疫稳态并防止病原体定植,参与了宿主免疫系统的发育、成熟,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系统共同进化,以维持肠道健康[1]。肠道菌群失调会造成肠道免疫系统平衡的破坏,而肠道免疫失衡与肠道炎性反应及疾病相关,如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合征(IBS)等[2]。有研究报道,肠道菌群可通过降解食物、生物转化、分泌物质等产生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胆汁酸等,这些代谢产物可影响宿主肠道免疫系统。本文就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肠道免疫影响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SCFA
SCFA是指碳链上的碳原子数<6个的有机脂肪酸,包括甲酸、乙酸、丙酸、丁酸和戊酸。膳食纤维经过肠道菌群发酵产生SCFA,SCFA通过多种途径进入肠上皮细胞:(1)被动扩散;(2)由转运蛋白运输,如钠离子偶联的单羧酸转运蛋白1(SMCT1)和单羧酸转运蛋白1(MCT1);(3)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GPCR)[3]。SCFA作为肠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可影响肠上皮屏障和防御功能所必需的基因表达,并可调节天然免疫细胞及T细胞、B细胞介导的特异性免疫[4-5]。GPCR主要包括GPR109A、GPR43、GPR41和OLFR78,在绝大多数免疫细胞中表达。SCFA通过介导GPCR,激活控制免疫功能的信号级联反应[6]。SCFA介导的调控是通过激活GPCR、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刺激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T)活性及稳定缺氧诱导因子(HIF)来实现的[7]。在细胞水平上,SCFA可通过改变免疫细胞的基因表达、分化、趋化、增殖和凋亡,从而影响全身性免疫反应,参与不同的炎性反应过程[3-4]。
乙酸与树突状细胞(DC)的GPR43结合,诱导B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A(IgA),GPR43缺乏的小鼠肠道中IgA水平较低[8]。此外,乙酸还可诱导DC中产生维生素A转化酶的基因ALDH1A2表达升高,将维生素A转化为其代谢产物维甲酸,促进乙酸诱导B细胞产生IgA[8]。丁酸可直接或通过抑制HDAC诱导肠上皮细胞中维生素A转化酶的表达,将维生素A转化为维甲酸。肠上皮细胞产生的维甲酸可影响DC表型,诱导DC表达CD103+,形成耐受性DC(CD103+DC)[9]。反之,这些DC自身可产生维甲酸,能诱导Treg细胞和生成IgA的B细胞[8-9]。丁酸可抑制HDAC3活性,促使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mTOR信号通路具有促进物质代谢,参与细胞凋亡、自噬的作用。丁酸可通过改变巨噬细胞的代谢并诱导mTOR依赖性自噬相关蛋白——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LC3)相关的宿主防御,LC3相关的宿主防御与抗菌肽产生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了抗菌活性[10]。经口服丁酸处理的小鼠在感染沙门氏菌后,在肠系膜淋巴结(MLN)、脾脏和肝脏中的细菌播散程度均较未处理小鼠轻[10]。因此,丁酸盐不仅可促进单核细胞向具有较强抗菌活性的巨噬细胞分化,而且可阻遏致病菌的传播。B细胞诱导成熟蛋白-1(Blimp-1)可促进B细胞发育成浆细胞,并且在T细胞(包括Th1细胞和Th17细胞)分泌IL-10中起关键作用[11-12]。丁酸可通过激活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和mTOR通路,诱导Th1细胞表达Blimp-1以产生IL-10[11]。Th1细胞可诱导结肠炎的发生,但其分泌的IL-10可抑制Th1细胞对肠道炎性反应的驱动。经戊酸处理的Th17细胞糖酵解增强,使IL-10分泌增加,从而抑制HDAC活性,使IL-17A表达降低,导致Th17细胞的代谢和表观遗传重编程及致病表型的丧失[13]。戊酸既可促进IL-10分泌,又可抑制调节性B细胞(Breg)凋亡,从而减轻炎性反应[14]。在研究小鼠体内戊酸对Breg细胞影响的实验中,在Rag1基因缺陷小鼠(T细胞和B细胞缺陷小鼠)体内植入经戊酸及Breg细胞共同处理后的原始CD4+T细胞,结果显示小鼠的体质量未明显降低,免疫病理得到改善,结肠固有层和MLN中CD4+效应T细胞的数量减少[13]。
IBD患者粪便中丁酸盐水平显著降低,克罗恩病(CD)患者的产丁酸盐细菌减少[15],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肠道菌群对黏蛋白型O-聚糖的利用减少[3]。黏蛋白型O-聚糖作为产丁酸盐细菌的发酵产物,可促进丁酸盐生成。由此可见,CD、UC与SCFA、丁酸盐介导的宿主免疫有着密切的关系。
2 胆汁酸
胆汁酸是一类特殊的甾体。肝脏分解胆固醇生成初级胆汁酸,初级胆汁酸通过胆道系统的输送释放入肠道。在回肠末端,类芽孢杆菌、梭状芽孢杆菌、乳杆菌和双歧杆菌这些厌氧菌表达的胆盐水解酶能使一小部分初级胆汁酸在侧链上发生脱酰胺作用,随后由梭状芽孢杆菌表达的7α-脱氢酶进行7α-脱氢作用,从而产生次级胆汁酸[16]。此外,一些细菌有助于不同的生物转化:拟杆菌、梭状芽孢杆菌、大肠埃希菌、消化链球菌、鲁米诺球菌等可催化胆汁酸中羟基的氧化和异构化,这可能是胆汁酸的酯化反应。拟杆菌、梭状芽孢杆菌、消化链球菌和假单胞菌还能在特定条件下使胆汁酸发生脱硫反应[17]。
所有胆汁酸都是信号分子,通过激活核受体超家族成员法尼醇X受体(FXR)、维生素D受体、GPCR超家族等调节自身合成、糖代谢、脂质代谢及炎性反应过程。
胆汁酸可影响先天性免疫,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GPBAR1)和FXR在循环单核细胞和从肠、肝中分离的巨噬细胞中均有表达[18],GPBAR1在肝驻留巨噬细胞(Kupffer细胞)中表达[19]。人和啮齿动物巨噬细胞中这些受体的激活,能有效抑制巨噬细胞的促炎活性。GPBAR1和FXR可调节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性小体,在肠道中,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DCA)和石胆酸(LCA)可通过激活GPBAR1内源性抑制NLRP3炎性小体的激活[20]。DCA和LCA可导致NLRP3炎性小体依赖的GPBAR1/环磷酸腺苷(cAMP)/蛋白激酶A(PKA)通路的泛素化,从而抑制其活化。LCA是FXR的弱配体,即使在没有GPBAR1的情况下,LCA也可抑制NLRP3炎性小体的激活[20-21]。LCA有两种代谢产物:3-oxoLCA和isoalloLCA,可调节小鼠T细胞功能;3-oxoLCA可作用于Th17细胞,抑制其分化,从而显著减少IL-17的分泌;isoalloLCA可促进Treg细胞分化,使Foxp3表达升高[22]。由此可见,胆汁酸代谢产物可通过调控Th17细胞与Treg细胞的平衡,从而调控宿主免疫。
Treg细胞常表达转录因子 Foxp3,研究发现CD4+Foxp3+Treg细胞可同时表达转录因子RORγt[23]。另有研究表明,饮食和肠道菌群可影响肠道胆汁酸库的组成成分,从而通过胆汁酸调节Foxp3+Treg细胞群表达RORγt[24]。尽管Foxp3+RORγt+Treg细胞群表达了RORγt及其他与Th17细胞相关的基因,但其并不分泌IL-17,该Treg细胞群具有强大的抑制免疫反应的能力[23]。胆汁酸代谢途径的基因缺失可显著减少RORγt+Treg细胞的数量。恢复肠道初级胆汁酸库可增加结肠RORγt+Treg细胞的数量,减轻宿主结肠的炎性反应。在小鼠实验中,敲除肠道共生菌(如多形拟杆菌、脆弱拟杆菌)的胆汁酸代谢途径后,可抑制小鼠产生结肠RORγt+Treg细胞的能力;此外,在营养不良的无菌小鼠中,恢复肠道胆汁酸库(即补充特定组合的初级或次级胆汁酸),可经胆汁酸/维生素D受体通路增加结肠RORγt+Treg细胞数量,从而降低宿主对结肠炎的易感度[24]。
3 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
L-色氨酸(L-Trp)不仅可作为肠道营养物质,而且在肠道免疫耐受和肠道菌群维持之间的平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rp代谢分为内源性代谢和细菌代谢。具有Trp酶的肠道细菌均可代谢Trp产生吲哚及其衍生物,如普通变形杆菌、副大肠杆菌、拟杆菌等;肠道菌群可直接或间接调节宿主的Trp内源性代谢,反之Trp代谢的变化也会对肠道菌群的增殖和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IBS、IBD、结直肠癌等疾病与Trp代谢的变异性有关[25]。
由肠道菌群代谢产物Trp产生的吲哚和吲哚乙酸可通过激活芳香烃受体(AHR)或相关信号通路来增强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免疫功能[26]。给猪仔饲喂Trp后,其盲肠和结肠中的AHR被激活,肠道中TNF-α和IL-8的mRNA水平降低,维持肠黏膜屏障和通透性的两个关键紧密连接蛋白ZO-1和Claudin的丰度增加[26]。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募集结构域家族成员9(CARD9)是IBD的易感基因。CARD9基因缺乏小鼠的肠道菌群不能将Trp代谢成AHR的配体;CARD9基因缺乏小鼠接种3种能代谢Trp的乳杆菌或用AHR激动剂治疗后,肠道炎性反应减轻[27]。由此可见,CARD9基因可通过促进肠道菌群代谢Trp产生吲哚衍生物,以激活AHR,从而增加IL-22的分泌,促进结肠炎缓解。
吲哚可调节先天性免疫反应介导的炎性反应,减轻肠道炎性反应[28]。生孢梭菌和肉毒杆菌可降解Trp,分泌代谢产物吲哚丙酸(IPA)。IPA可通过结合并激活孕烷X受体(PXR),提高IL-10的表达水平,从而降低TNF-α的表达水平,减轻肠道炎性反应[27]。IPA水平下降会导致免疫细胞数量增多,并且IPA可降低肠道通透性,增强肠道屏障功能,从而减轻肠道炎性反应[29]。IPA可减弱MLN中DC诱导Th1细胞分化的能力,并可促进分泌高水平IL-10的1型调节性T细胞(Tr1)分化,以增加IL-10的分泌,促进MLN中CD103+DC的产生,从而增强宿主肠道的免疫耐受[30]。
4 丙酮酸和乳酸
表达CX3C趋化因子受体1(CX3CR1)的小肠单核细胞(CX3CR1+细胞)可调节免疫反应[31]。CX3CR1+细胞可将树突伸入肠腔来摄取肠腔中的抗原,从而增强免疫反应。在小鼠研究中发现,细菌代谢产物丙酮酸和乳酸通过GPR31介导在CX3CR1+细胞中诱导树突突起[32]。此外,经乳酸或丙酮酸处理的野生型小鼠表现出免疫应答增强,以及对肠道沙门氏菌感染的抵抗力增强[32-33]。丙酮酸还能通过糖酵解途径调控巨噬细胞的表型分化,促进单核细胞向调节性巨噬细胞分化;调节性巨噬细胞经脂多糖刺激后可分泌大量IL-10[34]。IL-10是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研究发现IL-10可阻止巨噬细胞中由炎性刺激引起的代谢程序转换,因此IL-10被认为在终止炎性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35]。
5 小结与展望
随着各项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肠道菌群功能及作用机制已被发现。然而,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肠道免疫的作用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可能还有很多其他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人体产生影响。目前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通过发酵膳食纤维、分解胆固醇及代谢Trp等方式,分别产生SCFA、胆汁酸、吲哚及其衍生物等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经多种途径介导免疫细胞的基因表达、分化、趋化、增殖和凋亡,从而影响宿主的肠道免疫。综上所述,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影响肠道的免疫发育和免疫平衡,其作用机制的揭示可能为未来开发新的预防或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