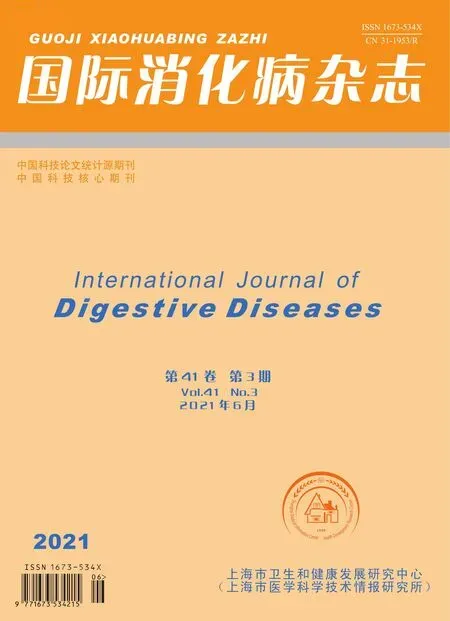CD26与炎症性肠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郭 蕊 罗 娟 缪应雷
炎症性肠病(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两种类型,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目前仍缺乏有效的诊疗方案。反复发作的症状和高昂的治疗费用给IBD患者带来了生理、心理双重压力,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探究IBD的发病机制,开发新的有效诊疗方案任重道远。有研究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IBD患者的血清可溶性CD26(sCD26)水平下降,而作为淋巴细胞膜表面抗原的CD26表达水平升高;且sCD26水平与IBD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1]。另有研究表明,高血清sCD26水平可提示治疗反应良好[2]。动物实验显示sCD26抑制剂具有减轻肠道炎性反应的作用[3-4]。上述研究提示CD26参与了IBD的发生、发展,可能成为新的IBD治疗靶点。本文就CD26的水解、非水解作用与IBD的相关性,以及CD26在IBD临床诊疗中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CD26的结构和功能
CD26是一种高度糖基化的Ⅱ型跨膜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110 000,由两个同源亚单位组成,主要结构包括由6个高度保守的氨基酸组成的胞内区、由22个氨基酸组成的跨膜区和由738个氨基酸组成的胞外区。胞外区分为N端糖基化区、C端水解区、富含半胱氨酸区这3个结构域。N端糖基化区可与腺苷脱氨酶(ADA)、微囊蛋白-1(Caveolin-1)结合,胶原蛋白、纤连蛋白、纤溶酶原和链激酶可与富含半胱氨酸区结合。CD26胞外区可被剪切、释放至血清,具有水解作用,这种sCD26又被称为二肽基肽酶-Ⅳ(DPP-Ⅳ)。CD26广泛表达于体内多种组织器官,主要发挥两种功能:(1)丝氨酸蛋白酶水解功能 作用于氨基末端第2个为脯氨酸或丙氨酸的多肽,并剪切氨基末端前的两个氨基酸,改变底物的生物活性;其底物具有多样性,目前研究已发现的是胰高血糖素样肽(GLP)、神经肽、血管活性肠肽等[5]。(2)非水解作用 即受体和共刺激因子功能,参与细胞信号转导,诱导T细胞活化和细胞迁移、黏附、侵袭等病理、生理过程[6]。由此可见,CD26参与了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2 CD26的水解作用与IBD
2.1 CD26在IBD中对GLP的水解作用
在受CD26水解作用调节的底物中,被研究得较为深入的是GLP。进食刺激肠道L细胞分泌GLP,主要是GLP-1和GLP-2,从而促进胰岛素释放,延迟胃排空,控制血糖水平。GLP在体内的半衰期极短,主要由sCD26水解失活或由肾脏清除。近年来研究发现GLP还参与了免疫调节[7],这使得GLP和sCD26备受关注。Keller等[8]发现活动期IBD患者的胃肠排空延迟且GLP-1水平升高;Xiao等[9]发现IBD组患者血液中GLP-2活性形式GLP-2-(1-33)水平较健康组显著升高,而sCD26水平较健康组显著降低。上述研究表明IBD患者的GLP水平发生了改变。
目前对GLP-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方面,而在GLP-1与胃肠道的关系方面则鲜有研究。Yusta等[10]发现GLP-1基因敲除小鼠的肠道微生态紊乱,且IL-1β、IL-6、IL-12、三叶因子1(TFF1)、TFF2表达异常。Anbazhagan等[11]用GLP-1治疗由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模型小鼠,虽未观察到肠道炎性细胞浸润程度减轻,但观察到肠上皮杯状细胞破坏程度明显减轻;此外,GLP-1治疗组小鼠的腹泻情况缓解,DRA蛋白表达升高,DRA蛋白在维持细胞内外离子平衡,防止肠道液体丢失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GLP-2可维持肠道黏膜屏障,参与肠道炎性反应。GLP-2的促生长作用较表皮生长因子、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更强,并具有肠道特异性[12]。Drucker等[13]用GLP-2类似物治疗由DSS诱导的IBD模型小鼠,发现其可显著逆转小鼠的体质量降低,并可使小鼠结肠及肠腺体长度增加,以及黏膜炎性反应减轻。Gu等[14]用DSS诱导建立小鼠IBD模型,治疗组予重组GLP-2二聚体,对照组予生理盐水,结果显示治疗组小鼠的体质量增高,肠道炎性反应减轻,肠壁通透性较对照组降低,干扰素-γ(IFN-γ)、TNF-α、IL-1β、IL-6等促炎因子表达降低,结肠组织中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性小体及环氧合酶-2(COX-2)蛋白表达降低,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减弱。GLP-2的治疗作用在由TNBS和乙醇混合液诱导的IBD模型小鼠[15]、IL-10-/-模型小鼠[16]、人类白细胞抗原-B27(HLA-B27)转基因模型小鼠[17]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2006年一项GLP-2类似物Teduglutide治疗CD的Ⅱ期临床试验纳入了100例克罗恩病疾病活动指数(CDAI)为220~450分的CD患者,随机给予患者3种剂量(每日0.05 mg/kg、0.10 mg/kg、0.20 mg/kg)的Teduglutide或安慰剂皮下注射治疗8周,8周后CDAI评分<150分视为治疗完全缓解,CDAI较基线下降100分视为治疗有应答,结果显示Teduglutide组的缓解率为55%,安慰剂组的缓解率为33%,且缓解率与药物剂量呈正相关;由于该试验中剂量梯度分组较少,故未发现Teduglutide的最佳治疗剂量[18]。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GLP可能成为IBD的潜在治疗靶点。然而,GLP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极短,主要由sCD26水解失去活性,由此推测可通过抑制sCD26的水解活性延长GLP的半衰期,以达到减轻肠道炎性反应的目的。有研究建立了小鼠IBD模型,比较sCD26抑制剂治疗组与安慰剂组的疗效,发现sCD26抑制剂治疗组小鼠的疾病活动度低于安慰剂组,腹泻、直肠出血、体质量下降等症状较安慰剂组明显改善;肠道细胞增殖加快,肠壁厚度较安慰剂组增大;此外,sCD26抑制剂治疗组小鼠的肠道腺体缺失、炎性细胞浸润、杯状细胞破坏程度均减轻,促炎因子释放减少,GLP水平升高且半衰期延长[3-4]。由此可见,sCD26抑制剂可通过抑制GLP水解发挥减轻肠道炎性反应的作用,sCD26抑制剂可能是潜在的IBD治疗药物。
2.2 CD26在IBD中对其他物质的水解作用
除GLP以外,CD26还可作用于其他底物,如神经肽Y(NPY)、血管活性肠肽(VIP)等。研究显示NPY、VIP可能是胃肠道保护因子[19]。Baticic等[20]为观察结肠炎机体中CD26是否参与调节神经内分泌因子,分别给予野生型(C57BL/6)小鼠及CD26-/-小鼠直肠注入TNBS和生理盐水构建IBD组和非IBD组,结果显示由TNBS诱导的两系小鼠的炎性反应相关病理学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仅野生型TNBS组小鼠的Lieberkuhn隐窝的宽度恢复较慢;野生型TNBS组小鼠和CD26-/-TNBS组小鼠的血清、结肠、脑中的VIP水平及血清NPY水平均升高,CD26-/-TNBS组升高幅度更大;在炎性反应急性期和恢复期,野生型TNBS组小鼠的结肠和脑中NPY水平升高,而CD26-/-TNBS组小鼠仅结肠中NPY水平升高且升高幅度较野生型TNBS组小鼠小。该研究结果提示:(1)血清、结肠、脑中神经内分泌因子变化的差异表明IBD发病机制中脑-肠轴调节的存在,sCD26参与调节IBD机体神经内分泌因子变化,恢复期野生型小鼠较CD26-/-小鼠更需要NPY水平升高,提示CD26基因缺乏对于结肠炎可能存在潜在的保护性作用;(2)与野生型小鼠相比,CD26-/-小鼠并未显示出明显的肠道炎性反应减轻,CD26-/-小鼠脑中NPY水平的变化,表明sCD26在IBD中的调节机制复杂,不仅仅是水解作用。
3 CD26的非水解作用与IBD
CD26的非水解作用与其结构密切相关。CD26是T细胞活化所需共刺激信号来源,T细胞表面CD26与抗原递呈细胞(APC)表面Caveolin-1连接,促使Caveolin-1胞内区结合的Toll相互作用蛋白(Tollip)和IL-1受体相关激酶-1(IRAK-1)解离,IRAK-1磷酸化,介导APC表面CD86表达上调并结合T细胞表面CD28,协同活化第一信号,活化抗原特异性T细胞。此外,CD26胞内区尾部可结合CARMA1的PDZ区域,激活NF-κB,诱导T细胞分泌IL-2[4]。CD26胞外区的富含半胱氨酸区可结合胶原蛋白、纤连蛋白,介导T细胞迁移[21]。众所周知,IBD存在复杂的特异性免疫调节过程[22]。CD26的非水解作用可能参与了IBD的免疫紊乱。目前关于敲除CD26基因对小鼠结肠炎影响的研究报道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CD26-/-小鼠造模会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结肠炎性反应[23],而另有研究显示CD26-/-小鼠结肠炎病理表现与野生型小鼠之间虽无明显差异,但其结肠炎症状较野生型小鼠轻[24]。细胞分子层面的研究采用DSS诱导CD26-/-小鼠建立结肠炎模型,发现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增强,NF-κB亚单位p65水平升高,脾脏CD8 T淋巴细胞占比升高[25]。不同于CD26对于T细胞活化、迁移作用的理论,也不同于前述研究的结论即sCD26抑制剂可缓解小鼠结肠炎,敲除CD26基因并未表现出对于结肠炎的保护性作用,敲除CD26基因与使用sCD26抑制剂对于结肠炎结局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有研究显示sCD26抑制剂Teneligliptin除可抑制GLP水解外,还可直接与CD26竞争Caveolin-1的结合位点[26]。此外,有研究发现CD26-/-结肠炎小鼠体内丝氨酸二肽酶-9表达升高了约1倍,使得体内sCD26样水解作用即丝氨酸蛋白酶对相关底物的水解功能并未受到CD26表达缺失的影响[27]。由此可见,CD26在IBD机体中不仅可通过影响底物水解水平起作用,其非水解作用也非常重要,具体作用有待深入研究揭示。
4 CD26与IBD的临床诊疗
研究显示血清sCD26水平与IBD疾病活动度[1]、治疗反应性[2]相关,提示临床上检测血清sCD26水平可协助评估IBD活动度及预测疗效。Yazbeck等[28]采用改良13C同位素呼气分析法测量sCD26水平,这一无创、简便的检测方法为血清sCD26的临床检测开辟了道路。目前IBD治疗主要是依靠生物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水杨酸类等药物减轻肠道炎性反应。sCD26抑制剂具有促进肠黏膜修复的作用,可能成为IBD的一种辅助治疗方案。除IBD外,目前sCD26抑制剂在短肠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结肠癌、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也在研究中[29],这对于有复杂合并症的IBD患者的药物研发具有提示作用[30]。
近年来,应用sCD26抑制剂是否会升高糖尿病患者的IBD发病率引起了广泛关注。Kim等[31]检索了2005年至2013年的美国保险理赔数据,比较了分别以sCD26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与以非sCD26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作为起始降糖治疗方案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风险,发现在以sCD26抑制剂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的患者中,包括IBD在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风险明显下降。2018年英国一项纳入141 170例糖尿病患者的观察性研究显示,sCD26抑制剂升高了75%UC患病风险[32]。2019年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16项有关sCD26抑制剂对IBD发病率影响的研究,共198 404例患者,结果显示sCD26抑制剂暴露并未导致IBD风险显著升高[33]。2019年一项队列研究对比了895 747例服用sCD26抑制剂的糖尿病患者的IBD发病率,发现短期sCD26抑制剂治疗并不会升高IBD风险[34]。目前CD26对IBD的影响尚未明确,今后需开展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揭示。
5 小结
CD26与IBD的相关研究显示,CD26可通过水解作用和非水解作用调节机体细胞因子的生物活性,介导T淋巴细胞的活化、迁移,参与IBD的发生、发展。CD26可能成为IBD诊断和治疗的新靶点。然而,目前研究多集中于阐述CD26对GLP类似物的水解作用对IBD的影响,对CD26与IBD发病机制关系的相关研究尚有限,sCD26抑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有待临床观察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