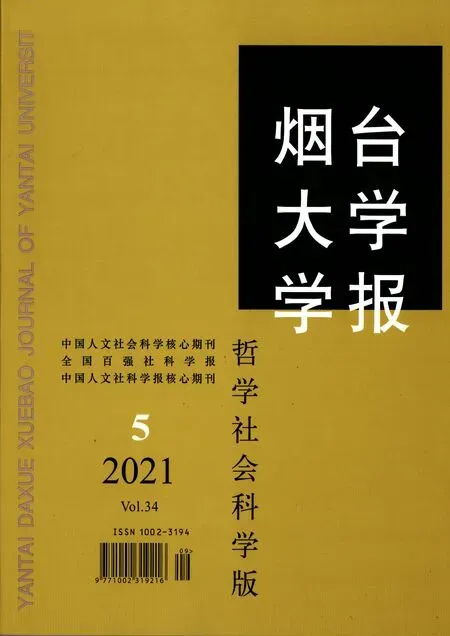以更开阔的视野深化中国古代和亲史研究
雷振扬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烟台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教学研究团队,以数十载之不懈努力,在中国古代和亲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走在了学界前列。读过《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之后,对作者用功之深、钻研之精、贡献之大,深感敬佩。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古代和亲史研究还能做些什么?这是笔者在读书时所思考的一个问题。这里谈几点肤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少数民族视角与古代和亲研究
我国古代的和亲,是基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原王朝或割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军事集团)、朝贡属国之间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量,以公主(或皇亲贵戚之女)“下嫁”或“上嫁”为形式,缔结姻亲关系的政治行为。和亲的动因和表现形式多样,但都是一种双向的嫁娶行为。因此,对古代和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理应从嫁和娶的双向度展开。但目前国内已有的古代和亲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基于古代王朝视角的历史文本的研究。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正史(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历朝官方史籍、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其中包括了《魏书》《周书》《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的史籍,基本上是从王朝正朔的视角,依据正史记载的史实进行言说。总体上看,基于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和亲研究少,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引述少。
中国古代和亲研究所据史料之畸轻畸重,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代王朝重视统治者生活起居和理政活动的实录,设置有专门的官职和相关制度性规范,对包括和亲史实的记载较为详实;基于吸取前朝治理经验教训的立场,新建王朝对前朝史的编撰也极为重视。因此,我国古代王朝正史文献不仅一脉相承,而且相当丰富,为古代和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权威、方便获取与利用的历史文献。二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或政治军事集团大多地处偏远,那里生境恶劣,特别是一些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政权更迭也频繁,再加上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复杂(许多还没有文字),书写载体不稳定,保存条件受限(或因战乱、自然灾害等而损毁流失),因此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稀缺,使研究者难以获得。
研究文献这种实际的状况,对于古代和亲史研究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或缺憾。它使相关研究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言说,缺少双向度或多向度的支持与论证,也使相关研究成果缺少丰富度、延展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大多数和亲仪程完成之后,“下嫁”或“上嫁”公主的生存状态、所作所为、生养儿孙的状况等记载阙如、不可追述,形成和亲故事的缺失。这种状况,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研究来说,也是一块短板。问题在于,与古代和亲相关的少数民族史料的“稀缺”,是否就等同于相关史料已经穷尽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严肃对待的科学问题。
最近,笔者读葛兆光等著《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一书,颇受启发。该书谈到,可能通行于6—8世纪我国西域的一种语言——“土火罗语”,在新疆库车的龟兹研究院藏有一批此语言的木简,当地一些石壁上也刻有铭文,这种语言遗存在焉耆、吐鲁番地区也有发现。大多数“土火罗语”文献被收藏于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和京都等地,季羡林先生曾是我国唯一通晓吐火罗语的学者,但在欧洲、日本“懂这种语言”“研究这种语言”的却后继有人。笔者以为,这种“土火罗语”通行的6—8世纪,跨越了大唐百年盛世,是中原王朝开拓、经营西域,与游牧民族冲突往还的重要时期。从汉文古籍记载可知,在唐之前,隋朝就曾多次与西域突厥和亲(千金公主、安义公主、义成公主等),唐朝与突厥、回纥的和亲政策亦延续二百余年。既然这一时期西域的政权相对稳定,且西域又有语言文字流传近三个世纪,那就很难说没有以文字为载体的史料存世。“土火罗语”文献与和亲有无关联,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些信息至少提醒我们,历史上曾经在西域通行的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尚有相当大开掘拓展的空间,这类文献可能尚待人们去发现或解读。除了“土火罗语”之外,敦煌宝藏之中多有与西域社会文化相关的文献,已发现的文献就包括了不少民间文书、宗教典籍等。那么,近世被西方列强掠走的文献中,是否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呢?依笔者浅见,这也是值得相关研究重视的一个方面。
除少数民族文献之外,笔者还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古代和亲史的研究能否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从人类基因组合方面入手,开展相关工作。和亲在历史上可能是基于政治或军事的目的,但婚配的直接结果却是生儿育女和后代的繁衍。如果能够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验证中原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在基因、血缘上的联系,这不仅能弥补少数民族史料的不足,对古代的和亲研究起到决定性的支持作用,而且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古代族群与现代人类DNA的检测对比研究,应该成为遗传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值得古代和亲史研究着力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周边视角与古代和亲研究
中国古代的和亲,既发生在中原王朝(或割据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也与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国家相关联。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朝贡国家的整体或局部,可能是中原王朝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区域。比如,越南(古代曾称为安南)在历史上就曾经历过几种角色,朝鲜半岛(古代曾称为高丽、百济等)也有类似经历。其中,一些地区在历史上也曾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和亲关系,或与其他地方政权、酋豪之间发生过和亲关系。因此,他们的和亲行为构成中国古代和亲史的组成部分。其和亲的史实与遗存、当代对和亲的研究,都值得国内学者予以重视。此外,从周边国家看,日本由于历史上受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对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多有学习借鉴,加上文化(文字)的交流,历来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极为重视,文献典藏丰富、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古代和亲历史文化的研究,应当重视从周边的视角切入,特别要关注日本、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献发掘,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的引进,以弥补国内文献的不足和打破研究视角的局限。
以日本的相关研究为例。对“内亚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研究,是日本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但现有中国古代和亲史研究对此关注明显不够。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该书的史料考辨与运用十分精细。其中,作者根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五的记载,介绍了癸未五年(元至元二十年)“遣人送安姿公主(圣宗季妹)于脱欢,欲舒国难”的和亲史实。据载,1285年,已经建立元朝的蒙古军队第二次攻打安南,陈朝为了争取对抗的机会,提出效仿汉朝和匈奴和亲,让陈朝公主与蒙元王室和亲。于是“奉纳国妹”,以陈太宗之女安姿公主嫁给“镇南王”脱欢。(1)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毕世鸿、瞿亮、李秋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1页。安姿公主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外嫁的公主。
当时,陈朝是上国,而占城是“大越”的属国,占城向陈朝进贡。陈英宗兴隆九年(1301)二月,占城国王阇耶僧伽跋摩三世向陈仁宗请婚和亲,陈仁宗答应将女儿嫁给他,以结秦晋之好。兴隆十三年(1305),占城国王以乌、里二州为聘礼,翌年六月陈仁宗将妹妹玄珍公主嫁给阇耶僧伽跋摩三世。陈朝将占城聘礼乌、里二州更名为顺州和化州。这是古代属国(朝贡政权)与其属国之间的和亲案例,也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和亲案例,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对属国的影响。
再如,1937年日本为全面侵占中国做准备,由东亚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一书。该书谈到,“清朝君临中国本部,有才干的汉人官吏归附清朝者增多,便采取了以公主下嫁其中特别有势力者的政策,如对吴、尚、耿三藩,都把清宗室的公主下嫁给他们。但在清朝的政治基础奠定以后,像三藩那样必须加以怀柔的强大势力已不存在,满洲人的自觉便加强起来,而且满洲妇女的人数也已减少,因此从雍正朝以后便没有公主下嫁的事例。当然,为了怀柔蒙古诸王,依旧对他们实行了这种通婚政策。”“满洲皇族娶汉女的似乎远远多于满洲皇族之女嫁给汉人的人数。”(2)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张廷兰、王维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45页。该书将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称为“异民族统治”,是别有用心的。其所提及的史实,可能不属于中国古代“和亲”的范畴,但它无疑是一种对历史上和亲策略的采借,显然也不应排除在古代和亲研究的视域之外。
以上是译介到我国的域外与古代和亲研究相关的两则史料。显然,域外相关研究远不止这些。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视野,需要更多懂日、越、韩、蒙等语言的专家加倍努力,需要通过专家外访和与相关国家的学者、机构合作,来译介更多相关研究资料,了解更多国外学者对古代和亲史的评价与思考。
三、“三重证据法”与古代和亲研究
正确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在学术共同体中早有共识。但具体到研究个案之中,是否能够正确运用适宜的方法,却往往对研究形成困扰。
从研究类型和研究范式来说,古代和亲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长期倚重纸质古籍,文献研究成为最基本的论证与言说方法,研究重点也集中在“解经史奥义、考礼制本末”。直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传入、中西学术交融的发生,以及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考古新发现的面世,史学研究方法才发生革命性变革。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正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对此,陈寅恪先生有所发挥,他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8页。此后,随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西方社会学方法的引进和中国化,我国学者又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重证据法”,也就是结合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调查所得之“民间资料”“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了相关学科建设。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和亲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即主要通过对传统史籍特别是正史文本的爬梳、考据、诠释等,来言说古代和亲的史实,或是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现有研究很少引述相关考古资料,“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除引述一些民族民间传说之外,也很少关注和引述民间的相关碑刻、墓志、族谱、民间文书等。《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引注中至少涉及4方碑刻、3种墓志、1份族谱、1份方志、3种敦煌文书,如《突厥文阙特勤碑》《立智理威忠惠公神道碑》《高昌王世勋碑》《唐蕃会盟碑疏释》《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康熙“御制”固伦雍穆长公主墓志铭》《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封氏闻见录》《敦煌本历史》《敦煌古藏文写卷960号文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汉魏遗书钞本》等。在今后的古代和亲史研究中,希望看到有更多学人采用“三重证据法”,使研究的成果更加厚实,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四、价值取向与古代和亲
古代和亲研究并非与价值无涉。现有研究大多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立场,将古代和亲解读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以探究和阐释其历史与时代的价值。这是一种大情怀、大格局的研究进路,是一种偏重现代民族建构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切入视角和研究进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但是,“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页。史实纷繁复杂。“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为了读者,他则必须断定确实发生过的事情。”(6)《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5页。如果对古代和亲不加甄别,一概予以过高的政治评价,过分强化其政治建构功能,不仅有失偏颇,而且可能影响古代和亲研究的多向度深入。因此,古代和亲研究不仅要有民族与国家情怀,而且要重视基本史实的考辨与具体问题的探究。没有史实的支撑和具体问题的解析,宏大叙事就可能难以构筑起坚实的根基。
以古代和亲中的女性研究为例,可以讨论和亲中的价值问题。历朝历代的和亲,无论是真和亲或假和亲、主动和亲或被动和亲、政治联姻或军事联姻,无疑都是以女性为“介质”或“货品”,以牺牲女性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历史时空背景之下的和亲,可能一时缓解了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创造了条件,甚至为文化传播与民族认同提供了契机。但正如崔明德教授在《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中所指出的,不应对和亲公主无限拔高,不要以为“她们个个都是含笑颜而出塞,都是自始至终为双方友好关系而奔波而呐喊”。(7)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这些公主们,肩负“国家重任”,但个人命运悲惨,是悲剧性人物。我国著名边疆史专家马大正先生就认为:“承担和亲大任的女性其个人命运极具悲剧色彩,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8)马大正:《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马老的这一论断,值得我们重视。
现有的古代和亲叙事,对当事女性(女主角)的研究较少,讲得较多(并不等于研究较多)的是王昭君、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几位女性。对其他和亲女性的关注与研究明显不够,对她们在异域他乡的生存状态、情感变化、所作所为、生儿育女等很少论及。即便是对于王昭君、文成公主等光耀史册,成为千古美谈的和亲女性的感情与家庭生活,后人也知之甚少。这种对和亲女性主体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和亲叙事的效果。如果古代和亲研究能在“和亲公主”身上多做文章,发现更多和亲公主的“事”与“迹”,揭示她们生活中的悲与欢,后代子孙延续的脉与络,必将使古代和亲的故事更加精彩动人。这方面研究的深化,不仅能丰富对和亲历史与和亲功能的认知,而且有助于揭示封建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本质。当然,历史研究的对象越具体细微,对史料的要求越高,难度越大。尽管如此,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乃是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