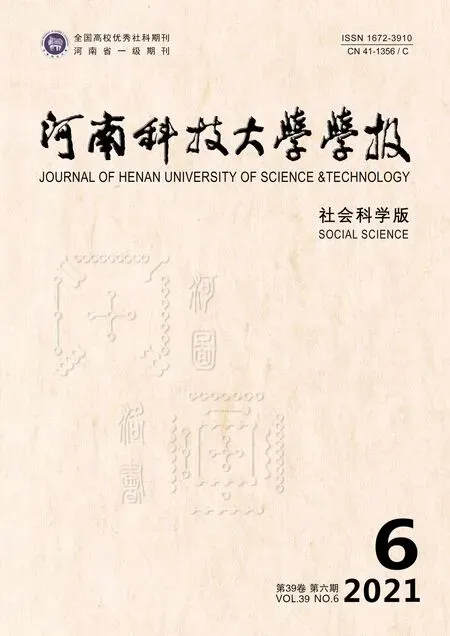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中国登山灾难片的类型化路径
——以《攀登者》《冰峰暴》为例
乔 慧
(山东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 济南 250300)
2019年,《攀登者》作为三大国庆献礼片之一,被认为树立起中国登山类型片的觇标,屡屡入围当年各类评选组织电影榜单十强。紧接着,《冰峰暴》同样聚焦珠穆朗玛峰灾难题材,呈现了跨国合作顶峰互助的雪山惊险。两片共同将中国灾难类型片在登山灾难的题材表述内,推向电影工业美学生产体系下类型生产的盛重开篇。它们不约而同将故事发生地置于8 000多米高的珠峰,推进了中国灾难片在叙事角度与影像风格上的新开拓,并映射出现代性的理想价值形塑。两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下、在中式登山灾难片的类型化路径上做出了有益探索。
一、世俗神话:灾难电影的传统遵循
灾难片是“以自然界、人类或幻想的外星生物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恐慌、惊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的电影类型”[1]315。作为充满强烈戏剧性的故事片类型,叙事是灾难片之核心,生死危机是最具张力的戏剧性前提。纵观中外灾难类型电影,不同的故事中有着不断复沓出现的叙事序列与意义单元,形成该类型电影独有的形式特征,并以其类仪式性的叙事推进方法来实现意识理念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巴赞等曾经把类型电影称作当代神话。《攀登者》与《冰峰暴》两部中国登山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对传统灾难类型范式有着严格的遵循。
(一)营造灾难类型的时空之限
在灾难电影中,“高强度时间压力和封闭式空间成为叙事情境创设过程中最为显著的重心元素”[2],因而这类电影大都对时空进行限制,以营造“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类型效果。《攀登者》的主叙事线索在珠峰一地,在短暂的窗口期时限内完成登顶升旗测绘一事;《冰峰暴》的主叙事线索也是在珠峰一地,在喜马拉雅和平峰会举行前的72小时之内,完成杀谍自救毁掉机密文件等任务。
两部电影的时间是连续的,都是从预备登山到最终登顶的顺时序叙述。《攀登者》以窗口期的结束倒计时,《冰峰暴》以会议召开时间倒计时,用时间形成关乎成败生死、甚至关乎国家荣誉、世界和平的死限,契合了灾难片中时间元素的作用。因登山的题材设定,两部电影又结合珠峰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时间推移迫近死限的佐证:前者以海拔、温度、风速、云涌等结合“大本营”“北坳”“大风口”等地理分区为人事与局势的推进划定时间流逝的节点,后者以倒计时的时钟提醒与第一、第二乃至三四营地的海拔与气象显示一起,将灾难片的惊险化为赫然在目的跳动数字;以时倒数,以地逼近,形成登山灾难片的独特韵律。
在空间上,虽则这两部电影不是以往的列车或者密室、城市等局限性明显的空间,但本身开放性的喜马拉雅山脉在与人的对峙中成为更具威压感的囚牢之地。两部电影均以大幅度横移运镜与空镜头、大俯拍来表现雪山广袤峰顶接天,茫茫雪野和一行人物被构图为移动的点与无限外扩的面,孑孓行走雪泥鸿爪。不同于过往灾难片中死神将临的晦暗景象,白色化作空无的象征。这种无法掌控的地域设定,突破了以往外国灾难片中未来叙事神秘主义的间离之感,却又以真实存在的雪山危难、与常人无干的陌生边地,来平衡奇观消费和现实焦虑的分寸之感,立足于世俗,阐发于神话,形成新灾难类型片的特定景观。
(二)组合前因后果的双序列叙事模式
灾难电影作为一种世俗神话叙事类型,“文本结构通常是两个功能序列的重合”[1]34。在主线索顺时序叙述之外,两部影片也具有非常类似的次生结构:《攀登者》开篇写1960年初次登顶,后接一个15年后发生的故事;《冰峰暴》开篇写姜月晟与小袋子初次相遇,故事推进中隐含了另两段5年前的往事。15年或者5年的时间跨度,除了叙事接续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功能序列的重合:第一个是国家或者世界的证明与拯救神话,“为国登顶寸步不让”和避免国际战事。在证明与拯救的过程中,善恶对立或者人与自然的搏斗形成功能叙事序列。第二个是现代思维现代文明时代大众文化影响下的自我神话,《攀登者》是兄弟二人重新找回信念与爱情,找回生命与荣誉的取舍之度与谅解之心,《冰峰暴》是长者与年轻一代找到最终的归宿。也即形成第二个自我疗愈与救赎的神话功能序列。
这两部登山灾难影片中,两个功能序列的叙事模式既让情节高潮迭起,也使情绪铺陈延宕交错不至于一直紧张。第二个序列中的个人视角,又为第一个序列中的追逐后果作了情理上的交代,使其不流于主旋律的空洞叙事和超级英雄的非凡形象,形成前因后果、交织互助、张弛有度的双序列叙事逻辑。“读中国叙事作品是不能忽视以结构之道,呼唤和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是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的双重构成的。”[3]据原始类型而搭建的群体生命,被救与施救是技巧性结构;据现代意识而创造的个体心理的被救与施救,成为中式登山灾难片的哲理性结构。
二、中式现代转向:类型变奏、价值新塑与现实转喻
类型电影的深层内核,有赖于“现代人的心理矛盾和价值崇尚,以及某种在自由交流中发展、显现的大众心理密码”[4]。灾难片作为已成规范的电影叙事作品,召唤吸引着该类型固有的观众,而类型得以延续的原因,则是电影导演在与时代俱进、与现代共存的创作中,将固有的模式与内核一再推陈出新,给予观众不俗套的观影快感和共鸣。中国的登山灾难片在其思维内核,即故事主角的矛盾抉择与叙事主题的价值崇尚方面,掀起了崭新形塑与现实转喻的内隐性类型变更。
(一)悲情基调与反传统英雄的个人塑造
两部影片都将好莱坞类型叙事中常用的大团圆结局转换成了悲剧性基调。东方影像执着于塑造“一种真理”以献祭治愈伤痛的超验魔力,这与我国传统的“苦情叙事”传统相关。《攀登者》与《冰峰暴》是用属于东方的生命消亡与爱情挽歌,做灾难过后的结局注脚,和平时期没有碾压性的政治悲情,高高在上的大义感化被英雄的个人悲剧命运的冲击代替,随之而来的是自由的“主体”被明显确立,舍己为国、舍己救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遭遇“为什么”的理性考量,个人意志与救世爱国先是混同一体,成为主序列的意识形态输出表象,又在次序列中显露出“为个人”的本原欲求:《攀登者》中徐缨一路追随死于登山途中,浓墨重彩的爱情戏份将生命的逝去归结为因爱付出;方五洲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心情超过了为国争光的责任心。《冰峰暴》里为世界、为和平的动机并不明确,被间谍发现想要灭口因而反击的个人原因似乎更为迫切;翼小组与间谍的生死对抗则更多是因为面临“你死”或“我亡”。这两部影片聚焦于当代个体在个人主义语境中的欲望叙事,是中国新时期的灾难片对现代性个人主体意识的时代性关注。
(二)伦理因素的叙事势能
西方灾难电影越来越倾向于个人救世的英雄主义狂想,或异世力量的神秘不灭,显现出与人与世疏离的弊端。这种与己无干却慨然承担的慈悲有无上的美,同时也有毫无根源的虚,使灾难类型片完全沦为消费品而丧失其价值观弥合的意义。而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文明,文明的凝聚力很大程度是靠家庭日常生活的凝聚力逐渐扩展到社会来实现的”[5],世俗化的情感需求,使之无法对异于常人的、超人类的援助产生亲和,因而与整部影片产生旁观间离。《攀登者》与《冰峰暴》都有意识地规避了宏观叙事下的英雄形塑方式,采用了伦理化的处理方法,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叙事变异势能的作用:《攀登者》分手又重逢,催生出登山进度与情绪节奏的数次急缓转折,爱国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达成有赖于伦理亲情;《冰峰暴》和平隐患的消弭、殉道精神的达成,都有赖于伦理亲情。伦理因素使牺牲有了合理缘由,并因“情”之变动引发叙事脉络的接续,和情绪节奏的张力变更。“寻找更多的观众个人化情感宣泄感体验的创作方式,是现代中国类型电影探索的一个重要的方向。”[5]当然,影片在对日常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采用了典型化方略,但并不是超脱性的离奇的神话处理,而是现代社会中互帮互助的新式家庭伦理的变奏反映。
(三)和平诉求与“再度想象中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做出了时代主题的调整与转变,推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决策,对战争的抗拒和对和平的珍视已经融入国人血脉,进而被投射到电影中。和平情怀与我国古代“非攻”“仁爱”思想一起,影响了我国灾难类型片故事创作的解决方式和理想化的结局处理。李仁港导演早在《天将雄狮》中就表达了“维和共存”的主题思想,《攀登者》则继续坚持了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意识。作为一部国庆献礼片,这种意识的表现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暗喻其中的,观众可以在与尼泊尔以登峰划定国土、与苏联切磋学习中寻找到与邻国和平非战的蛛丝马迹;《冰峰暴》搏斗的动机就是阻止敌方间谍获取机密引发战争,是个人之战求世界之和的故事。
随中国发展而变化的国家形象认知体现在这两部电影中的,还有讲述有关全球关系的故事时的高度民族认同。之前的好莱坞类型片,受基督教与自认“天选之民”的影响,其英雄设定闪现着对基督耶稣宗教文化语境的回应,更投射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自信甚至是自负心理,屡屡以美国式的世俗神话集中表现融汇个人主义、道德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一体的美国精神,而将其间的中国人与中国形象以微弱的他者身份当作美国救世情怀的见证。自《流浪地球》开始,中国电影中逐渐显现出关于全球政治伦理的全新想象。《攀登者》与《冰峰暴》拍摄于“四个自信”备受强调的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支撑下,在文化自信的影响下,中国导演们开始“再度想象中国”[6],在电影文化寓言中投射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攀登者》中的第二台阶处众人拼死而设的梯子,在此后1 300名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通过这一梯子登上地球之巅,中国梯是中国登峰的烙印,也是中国无私奉献的又一个符号;《冰峰暴》更是设置了一场世界战火风险,却被小袋子扼杀于无形,在类型叙事奇观影像的表象下,大国气度与大国自信的输出意识浸染渗透其中。
(四)中式审美思想与意象意境的影像达成
灾难电影多靠“奇观”取胜。在电影表意层面,《攀登者》与《冰峰暴》深谙我国美学意象与意境营造之道。《攀登者》是重意象的:首先是“蓑羽鹤”开篇,契合我国古典美学起兴的修辞特点。旁白曰“每年冬天蓑羽鹤……遇到风暴它们会成千上万地死去,可它们依然顽强,要飞越这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至结尾又复沓出现蓑羽鹤北归的影像画面,以不畏艰险的蓑羽鹤象征坚韧不拔的攀登者,前后呼应。其二是“摄影机”的使用,李仁港以摄影机为线索连接全片:开头方五洲为救曲松林而舍弃摄影机铺垫冲突,后因没有照片引发二次登顶的叙事主线……导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一道具,将之作为串联影片的线索,更作为具有特殊传承与见证作用的意象,借助留下照片对登顶被认可的重要性,赋予其完成国家使命的重要内涵,也借助几代队长之间友谊传递以命相托的几次转交,赋予其承担人文情怀、爱国情怀、生命关怀的深刻意蕴。《冰峰暴》是重意境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传奇神秘的白鸟座,它代表重生:一个故事的结束,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小袋子倚着营帐独坐仰望,唯美营造出“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的悲情意境。爱森斯坦曾经用中国造字六书中的“会意”来解释他的理性蒙太奇理论,其含义“都不是指外在物象的单纯描摹或单层面的自然再现,而是一个‘意义层深’”[7]84。《攀登者》与《冰峰暴》受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运镜构图与意象意境都体现出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内在美学特征——写意抒情、写意传神。
三、电影工业品质:效果加成、科技角色与产业思维
类型电影生产的前提是完整系统的电影工业体系。类型电影本身是电影商业化生产、流程性作业的规范性产物,作为工业产品的过程涵盖了制作、营销、发行、周边开发等流水线产业链环节,深具工业品质与工业特征。21世纪以来,观众对文化产品的审美需求日益严格,陈旭光等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美学体系概念,将电影作为现代工业体制下的产物分析对待并进行美学阐述。李仁港作为有十余部作品傍身的香港商业电影导演,余非作为前法国游戏巨头GAMELOFT公司的副总裁,本身对电影的商业性与技术性等工业因素与美学因素都有着精准到位的把握。
(一)视听奇观的设置与呈现
“电影是视听综合艺术,必须给观众的视听以真实、强烈、震撼的感受。好莱坞‘梦幻工厂’的比喻,其背后也是工业观念。”[7]84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灾难片属于最典型的“奇观电影”。《攀登者》与《冰峰暴》带给观众的观影快感来源有二:一是挑战灾难的奇观故事,即人类凭借强大的信念和传奇般的技巧攻克珠峰险要赢得人对战自然的成功;二是灾难本身的奇观场景,如珠峰耸立入云端、悬崖峭壁、雪崩、冰裂、极寒。而后者的美学达成对现代电影工业的依赖毋庸置疑。“电影工业观念还强调电影生产的系统性,尊重电影生产的工业生产特性,例如可预算性、可控性、规范性、制度化等”[8],李仁港挂帅《攀登者》之时距离国庆档期已经仅剩15个月,时间紧迫,各部门的分工协作统筹运作才保证了电影如期上映。为遵循“理性至上”原则,还原真实质感,《攀登者》选址、布景、表演、特效都力求做到真实: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团队斟酌取景,在高达5 254米的西藏刚喀什雪峰实拍与天津废弃矿区造景之间平衡真实美学与技术美学的取舍结合,从制作规格到技术使用上都尽力还原了珠峰的瑰丽惊险险峻多变;天津废弃矿区造景以表现珠峰高可接天风起云涌和巉削陡峭的雄奇景观,用从头到尾从未离场的航拍机器记录众演员登上珠峰环视所见的群峰地貌。
随着观众视野的开阔与国外大片的冲击,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对视效、画面、音效方面有了近乎吹毛求疵的高标准要求,形成高端消费需求,这就亟待我国电影制作方以供给侧改革求生存求发展。另一部珠峰灾难电影《冰峰暴》则是继《双子杀手》后首部在CINCTY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21世纪以来这短短20年,电影行业内对数字电影、CGI制作、3D电影、4K高清、高帧率电影技术迭代的速率令人应接不暇,堪称技术爆炸的电影时代已经来临。《冰峰暴》辗转中国、尼泊尔和加拿大三个国家之间取景,通过实地拍摄获得了雄浑壮观的视觉效果。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冰洞,深不可测的冰川裂缝,世界第三极得天独厚举世无双的璀璨星河,在诸多大全景镜头的呈现下,宛如超现实的神秘梦境。高质量、高饱和的冰天雪地,在CINCTY的广色域画面上呈现,让《冰峰暴》的自然景观和动作场面的效果完全凸显。各种不同制式所能提供的视听感受,让《冰峰暴》满足了不同观众对不同电影制式的视听期待与偏好。IMAX巨幕令风雪中的奔跑、徒手飞跃悬崖的画面跃出银幕如在眼前,惊心动魄。曾为《攻壳机动队》《叶问》创作配乐的顶级作曲家川井宪次量体裁衣再次奉献精彩配乐与震撼音效,在不同影院技术的加持下震撼心灵,闻者心旌摇曳沉浸其中,加上制作过《狼图腾》《战狼2》的知名特效公司聚光绘影,《冰峰暴》真实与技术之美都堪称精良。“电影工业观念还包括对电影的技术保障,对电影技术性的要求,对电影声音、画面等工业化程度的要求等”[8]。综合来看,这两部影片无疑是复合电影工业美学所要求的工业产品样态标准的。
(二)工业发展期待与“它”主沉浮的科技角色
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产物,必然带有反映当前社会的特点,其表现倾向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也有其选择的合逻辑性。而中国各种题材的灾难电影,鲜有对过度破坏或科技之恶的描述。所以灾难源头不由恶的动机引发,也不由对科技的贪婪反客为主,是偶然性的无恶的目的的巧合,不约而同构成国产灾难电影偶然而非必然的灾难景观。当西方电影反映出对过度开发的畏惧,体现为对失控的恐慌时,中国的灾难电影则表现出对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的憧憬,体现为对“发展”的想象。类型片故事不外乎各种简单却经典的二元对立,并往往在其二元设置的过程中概括统一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攀登者》与《冰峰暴》基于戏剧冲突的需要依然采用了矛盾对立的叙事模式,但变更了传统的正邪观念。《冰峰暴》与《攀登者》之中,珠峰作为对立面的“恶”也不同于之前西方外向侵略性的“灭世—重启”灾难,而是被动的、间歇性的“险”。为荣誉或者为乐趣挑战极限,珠峰的“险”在这种意义上本身就不足为“恶”,二元对立的强烈戏剧性在矛盾核心的根本上被消解,反而在被对抗一方的逐渐弱化中转化为和谐衬托的“助”:珠峰在《攀登者》中为英雄之证,冠国土之名;在《冰峰暴》中则为爱侣归宿,为间谍坟冢。
由于对“恶”的悖反处理,这两部灾难片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灾难片中的“科技反思”态度,表现为对科技的信任与依赖。它们设置了女性英雄,但作出贡献的真正力量或者说是决胜因素是隐匿于其后的科技角色:《攀登者》两次登顶,胜利的过程有赖于徐缨所学到的气象知识,胜利的结果有赖于摄影机的证明;《冰峰暴》翼小队的出动有赖于直升飞机的帮助,韩敏胜得以生存是因为找到了通讯设备的存在。反思技术之力,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待科技,也代表了如今国人的祛魅化理性思辨:迥异于西方的科技灾难而成科技救世角色,以科技主沉浮。
以科技崇尚定理性态度,所以电影中还蕴藏有符合中国现代现阶段思维形态与思辨自觉的反思。在这两部登山灾难片中,“英雄归来”被赋予了全新的选择余地与现代意义。两部电影中,现实问题不再按理想设定迎刃而解,而是依赖与科学思维与科学手段,这种“与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演进方式”在工业机制引导下在灾难类型的表象修辞里草蛇灰线,埋藏了属于后现代性的深层秩序反思:福柯找到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经验的无能,从而验证了人的有限性,《攀登者》与《冰峰暴》扭转了之前中国电影人定胜天精神能量的无限主观能动性。
(三)杂糅融汇的类型创新与产业意识
如今消费时代语境下的电影,“在生动显映出社会情绪、价值理想、审美情趣、时代风尚及伦理道德的同时,也会在工业生产和技术应用上滋养出创造之美和风格之美,并在类型现代化和生产标准化的基础上探求中国电影的稳定性且可持续的发展思路”[9]。类型电影本为商业利益而生,随时代变化观众需求必然取众类型之长处,发现创新点,将不同类型元素杂糅混合,并在体制规则下寻求产业化道路的可持续发展。
1.爱情稻草与合理利己主义。爱情片表现爱情的萌芽发展风波起伏,以展示恋人的心心相印双宿双栖、或天各一方甚至天人永隔为主要叙事线索,对爱情的追求与受阻成为此类型电影的二元冲突叙事动力。郝建教授认为当把电影所属类型与时代气质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就能了解电影类型的仪式性功能。徐缨与小袋子都是爱情部分里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爱情波折带动叙事的推进,为爱情付出构成爱情片的浪漫风景,同时又标榜女性的新时代属性:知识青年、不落人后的专业技能。徐缨对爱人的理想期待,激发方五洲觉醒并以其专业引领其二次登峰的成功,小袋子以其对爱人的追寻途中邂逅一场挽救和平事业的斗争。对影片主题的达成来说,这两个女性形象对男性其人、对事业其事,都承担了爱情稻草的重要作用。另外,在反传统英雄的塑造上,爱情使得徐缨的奋勇牺牲有了更合理的支撑,使小袋子的向死而活有了更感人的浪漫,家国大义的宏大主题在爱情力量下有了合理利己主义的伦理动因,从而使世俗化的英雄具备与观众具备更多共情的可能。这是爱情片独有的魅力。
2.已知真实、类型快感与悬念游戏。惊险片是让观众欣赏悬疑、享受惊悚情感体验的电影类型。《攀登者》与《冰峰暴》 的任务都是始终处于危险中的,观众带着对主人公生死的担忧进行观影体验。两部电影皆以非线性叙事为手段,过往与当下,回忆与现时,前因与后果子在十五年或五年的时间段里穿插叙述,引发观众对已知情节的思考、对未知信息的推测、对故事整体的完型填补。以《冰峰暴》为例,属于惊险片亚类型的谍战电影或许不多,但谍战电视剧最近两年占有很大比例,有一大批观众对这一类型影片持期待心理。正义人士与敌特分子的斗争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敌特身份遵循冒名顶替的类型范式。观众对类型片的熟识,对后续情节发展揣测的成就与把控之感,本身成为类型片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也即类型快感。如何在这种快感基础上做出拓展或者反转,则是惊险片的另一引人入胜之处——悬念游戏。《冰峰暴》小袋子一方正义必胜是不可改变的结局,悬念是小袋子的死亡选择。在这一方面,《攀登者》则更为典型:二次登顶的胜利是已经存在的、在“开学第一课”被当做精神教育素材的一个当代史片段,观众带有对已知真实的节点期待,期间的李国梁牺牲、梯子抵抗风暴、徐缨之死等种种惊险刺激,就是与观众共谋的悬念游戏——结局已定,只能在细节和副线里旁枝斜逸。
3.迎合民族心理的武舞神话。贾磊磊曾将中国武侠片(武打片)进行三分,其中之一是“以特技技术为主要表现方式”,其中之三是“以纪实手段展现真实武功”[10],有神化与写实化的分野。《冰峰暴》是纪实武打,而《攀登者》堪称特技武打与写实武打的融合。武舞不分家,随环境艰险事态艰难不断迸发奇崛动作,配合急促流畅的节奏,用武舞神话将暴力转化为抒情奇幻的摹写,并将珠峰环境做壮阔雄奇的唯美展现,更新了武打片的视觉图谱与环境造型风格。中国的武打片是有别于西方动作电影的,在经典动作后蕴含的文化心理内涵使其在无意识的情感宣泄与有意识的思想询唤中间找到自然不刻意的交点,使影片在中国式的侠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产生奇特效应,符合民族观影心理,从而带动民族观影热情,这其实是产业化的类型创作选择。同时,工业生产系统下新科技手段的运用与大量明星演员的加入,极大地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电影工业美学是工业和美学的一个折中,不是一种超美学或者小众精英化、小圈子化的经典高雅的美学与文化,而是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11]。
《攀登者》与《冰峰暴》在2019年下半年前后相继以登山灾难类型登上银幕,开启我国此类型电影的新纪元。尽管囿于类型的大众消费特点,两部影像本身对叙事的演进、对武舞的审美、对类型的变奏、对市场的把握,都反映出我国电影在新题材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上的开拓探索。它们以工业化产品品质与审美精神相协调,可谓在新类型的立足与繁荣上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