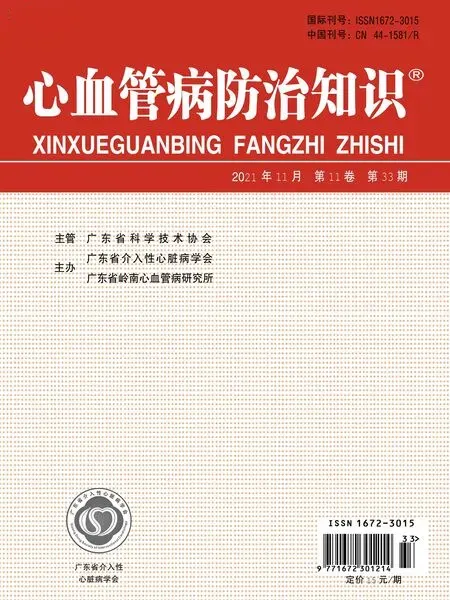PAH的未来治疗方向
张传寿 谭 虹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80)
1 炎症和免疫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肺血管细胞局部过度分泌炎症介质(例如,IL-1β、IL-6、LTB4、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和TNF-α等)以及免疫应答失调是伴或不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PAH肺血管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1-3]。已在PAH动物模型中成功检验了IL-1R拮抗剂、IL-6抗体、麦考酚酯、地塞米松、环孢菌素、他克莫司、LTB4通路抑制剂和TNF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等几种免疫调节方法的疗效,但尚未将其用于CTD-PAH以外的PAH治疗[2]。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阿那白滞素(anakinra,重组IL-1受体拮抗剂)可抑制IL-1α和IL-1β功能,并已被证明对PAH患者有益[1,3]。另一个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托珠单抗(Tocilizumab,IL-6R阻断性单克隆抗体),目前也正处于PAH临床试验阶段[1]。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抗CD20单克隆抗体,选择性靶向B淋巴细胞并诱导其裂解。在SU5416诱导的PAH大鼠模型中,利妥昔单抗可减少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增殖和RV重构,降低mPAP。最近一些研究还表明,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和皮质类固醇)与PAH特异性治疗联合使用可作为重度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PAH的桥接治疗[1,3]。
在动物模型中,抗TNF-α药物依那西普可预防和逆转野百合碱(Monocrotaline,MCT)-PH大鼠mPAP升高,并降低肺中TNF-α和IL-6的水平;改善SU/Hx诱导的PH。高选择性TGF-β配体陷阱,如索他西普(Sotatercept)和卢帕西普(Luspatercept),在体内被证明可有效预防PAH。此外,正在进行两项II期临床试验以评估索他西普在PAH临床治疗中的疗效(NCT03738150和NCT03496207)3]。
NF-kB也是目前研究的治疗PAH的靶点,抑制NF-kB可预防PH小鼠的RV重构并改善血管闭塞。研究提示,甲基巴多索龙(bardoxolone methyl,一种NF-kB抑制剂)在多种动物模型中可以减轻PH。最近进行的一项临床试验(NCT02657356)显示多巴多索龙治疗24周可改善CTD-PAH患者的6分钟步行距离(6MWD)。另有两项评估甲基巴多索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研究(NCT02036970,NCT03068130)也已完成,结果应该很快公布[3]。
最后,酪氨酸激酶参与多种不同生长因子(如PDGF)的信号转导,可能被认为是通过调节炎症途径治疗PAH的潜在治疗靶点。虽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已知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和其他疾病)治疗在2期试验中显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但3期试验的低获益/风险比和严重副作用导致其未获得FDA批准其治疗PAH[3,4]。
2 激素
2.1 雌激素信号通路
女性的IPAH和遗传性PAH发生率高于男性,而男性PAH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升高。在临床试验中,抑制雌激素信号作为一种治疗策略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对RV肥大有积极作用。用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anastrozole)等抑制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的药物降低雌激素水平,或用氟维司群(fulvestrant)或他莫昔芬(tamoxifen)等药物阻断雌激素受体可能是新的有前景的治疗靶点[5]。在一项小型“原理验证”试验中,阿那曲唑在男性和女性PAH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并显著降低了E2水平,改善了6MWD,但未改善RV功能[5]。此外,脱氢表雄酮(DHEA)是一种可调节内皮功能的类固醇激素,具有抗炎作用,促进肺血管舒张,使细胞凋亡/增殖平衡正常化,并通过减少氧化应激改善RV功能,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进行研究,代表了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1,2]。
2.2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不仅在调节血压中起主要作用,而且在肺部疾病炎症、增殖和纤维化的调节中也起主要作用。在小鼠模型中证实,刺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2/血管紧张素(Ang)1-7/Mas受体通路可通过催化AngII水解为Ang1-7而对抗ACE/AngII/AT1R通路,可能是治疗PAH的一种策略[1,2]。另一方面,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在临床已用于PAH的体液管理。在动物研究中,醛固酮拮抗剂表现出很好的降低PVR的作用,可减弱或部分逆转PH[1,2],同时还有其他改善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的作用[1]。目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该通路作为PAH靶点的潜在用途。
ACE2不仅可转化Ang I和II为Ang 1-9和1-7,还可降解其他血管舒张因子,如apelin。在PAH患者中发现ACE2水平降低和ACE2自身抗体[2]。一项关于PAH患者单次输注重组人ACE2后急性血液动力学反应的开放性初步研究显示,CO改善,mPAP或体循环压力无显著变化,氧化应激和炎症应激标志物减少[6]。一项剂量递增研究目前正在招募PAH患者(NCT03177603)[2]。
2.3 血清素能系统
已知5-羟色胺(5-HT)与PAH的发生有关,介导PASMC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PASMC的迁移和成纤维细胞的基质沉积[7]。抑制5-HT2A和5-HT2B受体可抑制小鼠PH的发生。但5-HT1B受体是PAH肺动脉中表达最多的5-HT受体。先前PAH的II期研究中,5-HT2A和5-HT2B受体抑制剂虽未显示临床获益,但预设亚组分析显示,接受ERA背景治疗的PAH患者的PVR得到了改善[2]。因此,5-HT生物合成的限速酶-色氨酸羟化酶1(TPH1)的选择性抑制剂可能是更好的研究方向。已有研究显示,TPH1抑制剂与安立生坦而非他达拉非联合给药可显著降低PH动物模型的肺动脉压,并显示出叠加效应。TPH1抑制剂KAR5585的1期临床研究显示可降低循环5-HT水平且安全性良好[2]。
2.4 心房利钠肽
心房利钠肽(ANP)和脑利钠肽(BNP)分别由心房心肌细胞或心室释放。利钠肽可增加肾脏钠排泄,通过释放cGMP引起血管舒张,并减少心脏纤维化。利钠肽可被金属蛋白酶脑啡肽酶降解。研究显示,单独抑制脑啡肽酶或与PDE5抑制剂联合可减轻慢性缺氧大鼠的PH,而不影响体循环血压[2]。最近一项RCT显示,脑啡肽酶抑制剂消旋卡多曲(racecadotril)单次用药可增加PAH患者血浆ANP和cGMP水平,轻微降低PVR,mPAP和循环血压、血浆内皮素水平均无显著变化,提示PVR降低可能主要是由CO升高驱动的[2]。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血管扩张剂对PAH的影响。
3 线粒体代谢障碍
肺血管特别是血管内皮细胞对氧水平的最轻微变化非常敏感,缺氧可导致线粒体在PAH细胞核周聚集,细胞核内活性氧(ROS)水平升高。相应地,在PAH患者中也观察到ROS产生增加和线粒体功能障碍[2]。目前ROS非特异性抑制的研究尚无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在开发的Elamipretide是一种新型线粒体靶向药物,可通过结合心磷脂(线粒体内膜的主要磷脂)而减少线粒体ROS的产生,已被证实能减轻结扎小鼠主动脉诱导的PAH[1]。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被证明可以改善衰竭心脏的线粒体功能[8]。
PAH期间肺血管细胞发生从氧化磷酸化转变为糖酵解和乳酸生成的代谢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Warburg效应。这导致有利于细胞增殖的代谢物生成增加,而SMC过度增殖是PAH发生的关键过程。DCA抑制线粒体丙酮酸脱氢酶激酶(PDK),可逆转这种代谢开关,重建葡萄糖氧化。在大鼠模型中,DCA治疗逆转了MCT-PAH和RV重构,同时也阻止了新生内膜病变的形成[1]。在IPAH患者进行的一项开放标签的试验显示,应用DCA治疗4个月后,mPAP和PVR下降,运动能力提高,但部分患者治疗无效,且部分患者出现了神经性不良反应[9]。尽管DCA可能不是治疗PAH的好选择,但新的线粒体靶标或DCA的优化替代品,仍然是PAH治疗的一种有前景的方法。
此外,其他如以细胞对氧化损伤反应的关键调节因子-核因子红系2相关因子2(Nrf2)为靶点的新药物,抑制黄嘌呤氧化酶而减少氧化应激的别嘌呤醇等,正在作为有前景的PAH治疗进行研究[1]。最后,临床前数据也支持使用抗胰岛素抵抗药物如罗格列酮、二甲双胍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作为PAH的潜在治疗策略[10]。
4 表观遗传学途径
表观遗传学定义为染色质可遗传的变化,导致基因表达变化,而DNA序列并无改变。这些变化部分是通过被称为表观遗传标记的特定表观遗传修饰介导的,包括DNA或组蛋白的甲基化、乙酰化和磷酸化,及非编码RNA的调节。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不良反应较多。
DNA甲基化已被证明与基因表达的抑制和沉默有关。既往研究报告,肺组织中BMPR2表达减少可增强细胞增殖,并可能足以诱导PAH。而hPAH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中发现了高甲基化的BMPR2启动子[11]。动物研究显示,靶向DNA甲基化的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可抑制细胞增殖和凋亡抵抗,可能是恢复SOD2表达和抑制PAH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治疗选择[12]。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是一类从组蛋白中移除乙酰基的酶,影响染色质致密化和转录因子对DNA的可及性可调节参与许多生物学过程(如细胞存活、增殖、凋亡、DNA修复和细胞代谢)的重要代谢途径,在PAH患者和PH实验模型中表达上调;其同工酶SIRT3功能丧失与人类PAH发生相关[13]。在PH大鼠模型中,HDAC抑制剂(丙戊酸)通过显著抑制RV重构和改善RV收缩功能证明了有益作用[12]。这提示在PAH患者中使用HDAC抑制剂可能具有抑制血管重构、RV肥大并改善心脏功能的治疗潜力。PAH中SIRT下调可能由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1活化所致。在实验性PH模型中,在标准联合治疗(ERA+PDE5抑制剂)基础上抑制PARP1表现出比单独使用标准联合治疗更大的疗效[14]。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PARP1抑制剂奥拉帕尼正在进行一项PAH的临床研究[13]。
溴结构域蛋白4(BRD4)控制参与各种生物学功能(如细胞凋亡、增殖、迁移、分化、细胞周期和炎症)的必需基因的表达。近来研究发现,BRD4在人PAH和PH大鼠模型中显著过表达,可导致人致癌性NFAT、Bcl 2、Survivin和p21的上调,并触发PAH PASMC中的增殖/凋亡失衡的癌样表型表现。采用BRD4抑制剂或敲除BRD4可恢复血管壁内的增殖/凋亡平衡,减少血管重构,改善PH模型的mPAP、RVSP、心输出量等血流动力学,及RV功能和远端肺动脉重构[12,13]。一项在PAH患者中I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13]。
5 干细胞
已证明内皮损伤和功能障碍可诱导PAH时的细胞凋亡抵抗,并促进闭塞性丛状病变的形成,在PAH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干细胞治疗旨在修复和克服内皮损伤和功能障碍,同时恢复远端肺血管。已经描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干细胞治疗:1-内皮祖细胞治疗、2-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和3-诱导多能干细胞治疗。
临床前研究显示,内皮祖细胞(EPCs)可直接整合到远端肺循环中,在MCT诱导的PH大鼠模型中预防PH进展,显著降低RV压力;而转导了人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EPCs可显著逆转MCT诱导的大鼠PH,BMPR2增强的大鼠骨髓源性内皮样祖细胞可使MCT诱导的PH大鼠肺中BMPR2表达及其下游信号显著增强,缓解了PH,血流动力学的改善、血管重构的减少,血管厚度和肌化显著减少均证明了这一点[12]。PH和血管生成细胞治疗(PHACeT)的I期试验证明,在PAH患者中,过表达eNOS的EPCs的递送在血流动力学上耐受性良好[13]。然而,虽然6MWD有明显改善,但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量的改善有限。基于先前的实验数据,对EPCs的进一步试验表明,自体EPCs移植可减轻MCT诱导的大鼠PH[15],也表明该疗法可能对特发性PAH患者的运动能力和肺血流动力学具有有益作用。其他研究也表明,特发性PAH患者的EPCs数量减少,与血流动力学参数明显相关。最近,一项针对先天性心脏病引起的PAH儿童的试验发现,EPCs可能成为mPAP较高儿童的有效治疗和保护因素[16]。尽管这些初步研究证实了安全性和疗效,仍需要更广泛的长期随访试验来进一步证实这些结果。
间充质干细胞(MSCs)具有显著的再生潜力,并在组织修复和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MSCs相对容易培养,具有免疫相容性;且有抗炎、促血管生成和抗凋亡特性。在临床前啮齿类动物模型中MSCs显示了逆转和预防PAH发展的有前景的结果:MSCs可改善MCT诱导大鼠PH的右心室收缩压(RVSP),减轻中膜增厚,降低肺胶原蛋白以及抗炎和抗凋亡标志物,并可改善RV肥大和RV射血分数[12]。
诱导型多能干细胞(iPSCs)是通过转导确定的转录因子,从成体体细胞遗传重编程为胚胎干细胞样状态的成体细胞。基于iPSCs的治疗可显著改善MCT诱导PH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和肺小动脉血管重构,降低RVSP并减少RV肥大[12]。
总之,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很有前景,但在干细胞常规临床应用之前还需要进行强有力的优化和进一步研究。
6 基因靶点
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2型(BMPR2)属于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超家族,是肺动脉高压的重要易感基因,BMPR2/BMP信号通路则是重要的病理机制干预靶点。约70%的HPAH患者和约20%的特发性PAH患者中报告了BMPR2基因突变。目前已发现BMPR2有400多种突变,其中约30%为无义突变。大量证据表明,BMPR2基因突变和低表达与疾病发病机制、进展和结果有关[12]。因此,通过恢复BMPR2表达及其下游信号治疗PAH的可能性是合理的。
以腺病毒载体靶向递送BMPR2可缓解啮齿类动物实验模型的缺氧性肺动脉高压,显著降低右心室肥大、右心室收缩压、平均肺动脉压,改善缺氧诱导的血管肌化[12]。但尚缺乏有效的避免中和免疫反应的方法。直接传递BMP9是恢复BMPR2/BMP信号通路的重要方法。BMP9预处理的PAECs可阻止内皮细胞凋亡和通透性增加。在小鼠和大鼠体内注射BMP9配体可逆转已建立的MCT和SuHx诱导的PH[17]。
新型免疫抑制剂FK506(tacrolimus,他克莫司)可激活BMPR2介导的信号传导和内皮特异性基因调节。在大鼠PH模型以及条件性BMPR2缺失小鼠模型中,FK506治疗可逆转已建立的重度PAH,表现为RVSP和PAP降低,中膜肥大或新生内膜形成减少[12,13]。另一项随机分组、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a期试验[18]显示,低剂量FK506在PAH患者中的疗效证据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
Ataluren(一种用于治疗Duchenne肌营养不良症的药物)可使核糖体对因无义突变产生的终止密码子不太敏感,可恢复全长BMPR2的表达。Sotatercept则是一种新型activin受体融合蛋白,能够通过抑制TGF-b通路来增加BMP信号通路的活性,抑制细胞增殖;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改善血管重构的强效作用。这些药物未来均有望带来临床获益[13,19]。
7 GPCR途径
7.1 Rho相关蛋白激酶
Rho相关蛋白激酶(Rho-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ROCK)属于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家族,可通过GTP酶RhoA被包括GPCR在内的几种细胞受体激活,而GPCR受各种血管活性物质如血管紧张素II或5-HT的刺激。ROCK参与许多细胞功能,例如平滑肌细胞收缩、细胞迁移和应力纤维形成,并参与PAH的发病机制。ROCK抑制剂在动物研究中显示了有希望的结果。但是,在一项临床试验中,ROCK抑制剂法舒地尔没有改善6min步行距离。目前,新型ROCK抑制剂正在开发中[13]。
7.2 Apelin
Apelin是一种内源性血管舒张和正性肌力肽,通过G蛋白偶联的Apelin受体发挥作用。Apelin在人PAH中表达下调,并在动物模型中抑制PH。但apelin的T1/2较短和全身血管舒张作用,其用于PAH可能具有挑战性[13]。最近在一项小型临床试验(NCT01590108)结果仍待定。
8 肺动脉去神经支配(PADN)
PADN是一种新型的基于导管的消融技术。自2013年以来,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均显示了PADN在改善PAH方面的功效,包括快速显著降低PAP,改善血液动力学参数,增加运动能力,减少PA重塑等[20]。PADN可以减少再次住院,PH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的发生率,是一种有效的治疗PAH的方法,特别是那些药物难治的PAH患者。但目前对人肺动脉交感神经的精确分布、PADN的远期疗效、适应证和禁忌症尚不确定[21]。现阶段更多的临床试验正在验证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9 辅助设备
CardioMEMS(植入式肺动脉压监测系统):重度PAH伴RHF的死亡率较高。除常规治疗外,是否有任何可用于失代偿性RHF PAH患者的支持器械?CHAMPION试验[22]发现,使用CardioMEMS将心力衰竭患者的肺动脉压维持在10-25 mmHg范围内是有希望的。这项研究还发现,在17.6年的时间内,HFrEF患者的再住院率降低了50%。但是,报告的不良反应增加,如肺动脉损伤和咯血,应通过改善入选标准和手术技术来解决,以降低未来并发症的发生率。
体外膜肺氧合(ECMO):如果患者被定义为中度或高风险,将建议到心肺移植(HLTx)中心进行进一步治疗。建议肺移植后PAH患者使用ECMO,以尽量减少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或建议晚期PAH患者为肺移植做好准备。一项小样本研究发现,肺移植后重度PH的1年生存率超过96%。然而,有证据表明,与其他情况相比,围手术期即刻移植存活率较差。在肺动脉和肺静脉或左心房(PA-LA)之间植入的无泵膜氧合器是支持右心室的另一种常用方法[20]。
10 介入治疗
对于不适合肺移植的患者,可给予体外生命支持(ECLS)策略作为替代疗法,帮助患者在移植前忍受紧迫的状况。经导管灌封分流术可能是降低返回心脏右侧负荷从而支持心肺功能的适当选择。其他介入治疗,如房间隔造口术(AS)和球囊房间隔造口术(BAS),仅可尝试缓解和桥接肺移植间隔,且仅在有经验的心脏中心进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