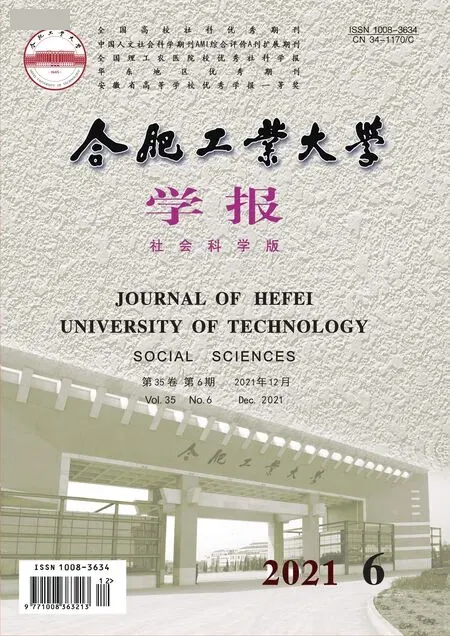精神分析棱镜中的本雅明历史哲学
许秩嘉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600)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无疑是一位带有浪漫诗人气质的独特哲学家。在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梦境文学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追忆文学的影响下,本雅明的文字中往往充满了感性破碎的闪烁意象和隐晦朦胧的影射色彩,但其蒙太奇式的隐喻意象背后却始终凝聚着一股清晰有力的历史哲学精神。在《历史哲学论纲》等著作中,本雅明多次阐释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以说,批判资本主义、追寻人类解放的信念是其变幻意象背后的不变支撑,是其蒙太奇影像背后的投影源:“阶级斗争所争夺的是粗鄙的、物质的事物,但没有这些粗鄙的、物质的事物,高雅的、精神的事物就无以存在。”[1]40
本雅明表达其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方式是极具隐喻象征性的,且多次借助了精神分析的概念与逻辑。无论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还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奴役的批判,都潜在地运用着文明与性压抑、集体无意识、恋母情结、醒与梦、移情、死本能等精神分析的思想范畴,形成了“历史主义的妓院”“集体无意识的储蓄所”“商品移情”“无生命物的性诱惑”“商品的灵魂卖淫”等诸多带有弗氏印记的意象或概念。透过精神分析的棱镜,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本雅明朦胧幽深的历史哲学观,继而理解其奇异浪漫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法”
借助精神分析的性象征意象和性压抑逻辑,本雅明多次对“历史主义”开展批判,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下”属性。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划清界限——后者对历史的理解遵循的是纵向的连续性的自然时间线,而前者所遵循的是横向的非连续性的本质时间线;后者的历史编写法是“叙事”以形成胜利者书写的“普遍历史”,而前者的历史编写法是“建构”以形成被压迫者呐喊的“阶级历史”;后者的是用过去来解释当下,而前者是用当下去重构过去。“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的意识。”[2]297这一“打破历史连续性”的历史理念无疑是本雅明《柏林童年》中的时间观在历史领域的展现。对童年的回忆不应遵循自然时间的序列、从过去来到当下,而应遵循对当下产生潜在影响的内在本质关联、从当下建构过去,以此来祛除被意识编码了的意愿记忆之遮蔽;同样,对历史的“回忆”也不应遵循历史主义的连续性梳理,而应从对当下影响最深的内在本质关联——“经济”范畴出发来回忆历史,以当下为端口为过去注入意义。换言之,如果说历史主义遵循连续的自然时间线来记录从过去到当下的历史影像,历史唯物主义则以一种“新的历法”来反推历史,撷取其中的关键影像,剪辑成一部主题鲜明的人类历史大电影:“革命阶级的特性在于,他们在行动之时能够意识到他们即将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大革命引入了一种新的历法。新历法的第一天以一种类似延时摄影的方式表征着历史。”[1]48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蒙太奇化阐释中,本雅明运用了“妓女”这个在其作品中广泛出现的象征意象:“历史唯物主义听任别人被那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妓女淘空耗干,自己却不为所动。他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足以将历史统一体炸个粉碎。”[1]48-49在此,妓女成为了历史主义线性时间叙事的化身,它会耗干历史的性精力,阻碍文明的前进。本雅明在此处无疑潜在地运用了弗洛伊德“性压抑是人类文明发展之动力”的文明演进观——人类文明要想获得前进的动力就必须对性本能作适当压抑,将节制下来的精力转移升华至生产性活动中,而不能任凭其停留在性活动里寻欢作乐。他用“妓女”这一意象来形象表明,历史主义会用“过去”来消耗社会演进的精力,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拥有面对诱惑不为所动的“当下”定力,它能够舍弃安逸的享受,将节制下来的精力转化为推动文明演进的经济革命力量:“对恩格斯的那些话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明白,任何对历史的辩证论述都是以舍弃安逸为代价的,而安逸正是历史主义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舍弃历史中的叙事因素。”[2]296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下性出发,本雅明才强调惊颤闪现的现代艺术品不是艺术本身内在历史传承的产物,而是机械复制时代的生产方式在艺术领域的自然反映,应从当下入手来建构艺术史的意义,从现实的社会根源入手来理解新的文化形态。“妓女”作为历史主义的象征,成为了本雅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当下性”的批判对象。
二、集体无意识记忆的“新生”
除了性象征意象与性压抑逻辑,精神分析的集体无意识、恋母情结等思想概念将本雅明进一步引向了一个朝向“新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在每一个时代都憧憬着下一个时代景象的梦幻中,后者融合了史前的因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因素。关于这种社会的经验——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与新的经验相互渗透,产生了乌托邦观念。”[3]6在本雅明的理论视域里,人类对新奇未来的梦幻憧憬是扎根在集体无意识中的——作为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形态回应着人类史前无阶级社会的潜在呼唤。对巴霍芬母系社会研究深感兴趣的本雅明很自然地将史前社会的无阶级形态作为一种伊甸园般的原始记忆置入了人类对未来的乌托邦梦幻中。原始记忆中储蓄着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经验,但这一经验并不存在于清醒意识中,而是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经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潜意识材料在记忆中的经常性聚集,而非根植于记忆中的事实的产物。”[4]因而,“新奇”作为一种人类不懈追求的未来幻想,是“完全属于由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意象。”[3]22正因人类对新奇未来的幻想是扎根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记忆的,本雅明才在描绘“历史的天使”时说:“这正是历史天使的模样。他的脸扭向过去。”[1]43
但是,若因此就将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未来构想理解为原始社会无阶级形态的再现则无疑是浅薄的。本雅明借助精神分析的集体无意识概念阐明了原始社会对人类乌托邦梦想的潜在遗传性影响,但并非认为这一梦想就是对原始社会的简单复归。相反,其根本意图是以此激发读者关于未来的集体意识和乌托邦渴望——无阶级社会是刻在人类文化基因中的永恒梦想。但集体意识中的无阶级社会不再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无阶级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缺乏现实基础的单纯梦想,也不仅是藉解放于梦境体验的超现实主义呼唤,而是梦与醒相互贯通的历史辩证法:“因此,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关键。实际上,每一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也在梦幻中催促着它的觉醒。”[3]30历史唯物主义者用阶级斗争来实践无阶级理想,用觉醒来实践梦幻,经过辩证法的“正-反-合”,安全但不自由的原始和谐被安全且自由的新和谐所取代,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被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像花儿向日一样,过去——受一种隐秘的向日性的驱使——努力面向历史的天空中冉冉升起的太阳。”[1]40显然,冉冉升起的太阳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象征,而“隐秘的向日性”则是推动集体无意识中的“史前因素”向新世界转变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历史性素材这块土地一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翻耕,当代在这块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就能够发芽。”[2]30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天使”的脸虽是扭向过去的,但他却被从原始和谐天堂中吹来的“进步飓风”所裹挟,奔向“背对着的未来”,即一个全新的无阶级未来。而这飓风无疑便是打破安逸幻想、迎接历史新生的马克思主义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本雅明同样用极具性色彩的象征意象展望了这一人类历史的“新生”:“性的满足,将男人们从自己的秘密中解脱了出来……这个秘密就像是拴住男人生命的绳索。女人剪断了绳索,男人便不再恐惧死亡,因其生命已经失去了这个秘密,并从此重获新生。当他心爱的女人将其从母亲的魔咒里解放出来,她们真正地斩断了其与大地母亲的联系,就像助产士切断了由自然秘密编织成的脐带。”[5]97-98这段表述即是弗氏恋母情结的隐喻表达,性爱对象的出现则斩断了其对母亲的原始依恋,使男人勇敢地逃离母亲的温暖,踏上“重获新生”的生命旅途。而母亲则不仅仅是血缘母亲,更是“大地母亲”,即那个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社会,一个尚未异化的伊甸园。正如性爱孕育了新生命,性爱活动在割裂了人的原始链接、摧毁了人的原始温暖后也孕育了一种全新的温暖链接,即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社会。在此,性隐约地成为了本雅明笔下人类历史重获“新生”的原始动力,其身上的弗氏影响可见一斑。
三、“商品妓院”的性诱惑
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时,本雅明同样运用了“妓女”的性意象,以及移情、死本能等精神分析的概念逻辑。在他笔下,“卖主和商品集于一身”[3]22的妓女是生命全面商品化的典范象征——妓女不仅将自己视为展览橱中迎合男权时尚审美的艳丽商品,还通过搔首弄姿的浮夸表演来自我叫卖,甘心成为机械时代的批量复制品,失去了性爱本真的审美灵韵。必须指明的是,本雅明笔下的“妓女”形象并非是具象化的性工作者,而是文化意义上我们每个人的商品命运象征:“如果说它(妓女的生活)有道德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无异于我们自己生活的意义。”[6]21换言之,妓女的形象就是每个甘心将自己降为商品的生命的真实写照:“她就是我们的形象。”[6]21在此,本雅明以精神分析的“移情” 概念为基础提出了“商品移情”概念,以此解释人沦为商品并进行自我售卖的心理过程。商品世界的缤纷绚烂使现代人陶醉在梦幻般的新奇刺激中,无生命的商品身上被投射了生命体的情感寄托,成为宗教般的陶醉与依赖对象。此时商品具备了人的情感属性,“商品本身就是说话的人”[7]78,它向每个路过的陌生人平等地投掷博爱与温情。但商品与人之间的这种“博爱”并非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而恰似妓女与嫖客之间的感情——商品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循着赤裸裸的货币规则,人付出抽象的货币价值,商品回馈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是被货币价值所衡量界定的,正如嫖客眼中妓女的性爱价值是被货币价码所衡量标注的;橱窗中奢华耀眼的精致商品对其面前的穷汉子毫无兴致,“它们不会对他移情”[3]123,正如妓女绝不会向没有钱的嫖客付出“感情”。商品是人的妓女,正如妓女是人的商品。
而商品移情的本质是一种“对无生命物体的移情”。在本雅明看来,“时尚”确定了人对商品的移情方式,并经由世界博览会进一步扩大着自己的控制力,但“时尚是与有机的世界相对立的。它把生命体与无机世界耦合在一起。面对生命,它捍卫尸体的权利。这种屈服于无生命世界色诱的恋物癖是时尚的中枢神经”[3]43。这段论述显然是将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观点运用到了对商品的属性分析之中。人将自身的有机生命移情给了无机的商品,因而人对商品的情感依附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分析语境中的“恋尸癖”,是人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任凭其被无生命物所鞭笞的受虐欲望折射,这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等人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开展的权威人格与人类破坏性剖析是异曲同工的。而巴黎这个“19世纪的都城”则因这一恋物癖的泛滥而成为了一首“充溢死亡的田园诗”[3]21,一座尸体堆积的建筑废墟。本雅明要做的,就是在这看似光鲜但实则衰败的历史废墟之上找寻救赎的希望。
在“商品移情”的背景下,本雅明对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移情现状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城市大众已经普遍沉迷在了对商品的移情活动之中。若要恢复生命的有机活力、恢复爱的尊严,就必须与城市居民保持一定距离,既要观察着人群的沉迷景象、体验着人群的陶醉,同时又能时刻保持清醒与克制:“他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即生产体制强加给他的生存方式认识得越清楚,他越使自己无产阶级化,他就越感受到商品经济的逼人寒气,也就越发不会移情于商品。”[3]126而能既参与人群又远离人群、既与城市亲近又保持疏离的,只有在城市中拾荒的“游荡者”。游荡者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体验着拱廊街的歌舞升平,目击着现代性的日新月异,但他们始终是穷困潦倒的、与商业大潮和现代规则格格不入的城市边缘人;他们“从社会退出一半”,因而既能记录建筑风景背后的历史记忆,也能抗拒商品移情、客观冷静地发现城市最深处的秘密;他们被朝不保夕的现实所囚禁,但同时也享有一种独特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显然,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即是自己这类既深入体验了现代性又能保持清醒意识的革命阶级的隐晦象征。
相反,普通的城市居民则不可能真正地逃离对商品的移情,不可能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看清自己的真实命运:“大城市几乎永远不能在将它直接呈现出来的居民那里得到表达。”[7]82而城市居民中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只跟一个妓女有了性关系”[7]205,因而必然将无产阶级革命者视为敌人,但“《共产党宣言》结束了这伙人的政治生命”[7]205。显然,和小资产阶级发生性关系的就是作为现代妓女的商品,小资产阶级从中享受到了资本的甜头。但事实是,这种甜头只是一种暂时的、有限的、没有权力作支撑的享乐,它从不真正属于他们,正如他们也从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人。因此,小资产阶级若想真正地为自己的命运做主,则必须成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命运,摒弃在“商品灵魂的卖淫“中获得的短暂的性满足和虚幻的安逸享受,将节制下来的精力转移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中。
四、身体意象的性革命话语
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本雅明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性的扭曲和资产阶级虚伪的性道德,试图通过“身体革命”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商品逻辑的蔓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爱普遍沦为了一种性交易,人们在选择性爱对象时遵循着最为简单且“公平”的价值标尺——金钱。这一标尺将一切有机生命的价值加以量化评估,用抽象的同一性轻易抹平了文化、审美等感性世界中的非同一性距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名义上呼喊着性解放,但实际上却隐蔽地实施着最为严酷的性压抑。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使现代人获得了狭义的性解放,但人的“广泛的性欲”,即广义上的内在自然欲望却被现代社会文明所愈发强烈地压抑,而其中的反抗情绪则被“当权者”提供的“最为合适的对象”的幻想满足所消抹。
本雅明的这一思想与其研究所的同事霍克海默、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极为相似,他们都在弗氏的人格结构理论的影响下控诉着同一性文明之超我对欲望本能之本我的压抑,试图激发性本能的革命功能,构建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因此,本雅明在批判爱德华·福克斯时说:“福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带有着道德主义的痕迹,这一道德主义,即使是心理分析也没能使它动摇……对资产阶级排斥纯性欲,排斥以或多或少的想象力产生性欲的做法进行真正怀疑,对福克斯来说是陌生的。”[2]326上述话语清楚表明了他的两点态度:资产阶级实施着性压抑,但被福克斯等资产阶级学者所美化;心理(精神)分析拥有动摇资产阶级虚伪性道德的潜能。
既然现代社会已被资产阶级的性压抑窒息,那么性革命即是重要的革命之路。赖希、马尔库塞等人都试图通过性革命来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奴役,但本雅明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是在“身体”意象的象征空间中开展本我对超我之反抗的。在《单向街》中,“身体”是人类和自然对话的重要中介,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就通过身体来展示精神的力量,也通过裸露身体等诸多仪式来了解生命实践的真谛、感知无法控制的未来:“当西庇阿摇摇晃晃地踏上迦太基的土地时,倒在地上,伸开双臂高呼胜利:‘拥抱你,非洲的袤土!’他用整个身体去贴近命运中的凶兆所展露出的令人畏惧的面容,于是他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主宰。古代,诸如节食、禁欲和守夜等苦行,从来就是在这一点上达到其最高境界。”[8]65借助上述神话意象,本雅明隐晦表达了其图腾禁忌观:身体是原始社会的图腾载体,它表述着人类的自然欲望,也表述着人因敬畏自然而生的欲望控制——图腾禁忌即是人类通过主宰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敬畏的方式。在这一观点中,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的印记再为明显不过——弗氏眼中的图腾禁忌即是原始人在弑父以满足性欲望后缓解负罪感、表达对已逝父亲敬畏之情的心理寄托。图腾禁忌使原始社会中的身体处于自我掌控之中,维护着“生殖”(广义上生命力量生长的象征)的秩序。
然而,当人类走出原始无阶级社会的前自然和谐,走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身体便在异化现实的压抑下逐渐失去控制。人类打破了图腾禁忌,不再敬畏自然、敬畏命运,身体因而遭受惩罚而变形扭曲,其生殖功能遭到了破坏:“如果身体及其力量被滥用而据此去掂量和战胜命运,同样也会受到惩罚。这些情形出现的时候,就是让命运和身体受辱的时刻。”[8]65而当人类的理性文明高度发达、对自然的控制能力高度发达,毁灭式的世界战争却将人类掷入自己亲手挖掘的深渊,身体也彻底走向癫狂。因此,若想反抗资本异化力量对现代人的剥削奴役,则必须首先反对其对自己身体的摆布奴役,恢复人类的身体自控力。只有当身体的创伤获得了治愈、身体的能量获得了控制、身体的生殖功能获得了康复,人类才能真正满足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幻想,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更人道的“新生”乌托邦:“当所有的革命张力控制了身体的集体神经,当身体的集体神经成为了革命的释放途径,现实才会超越自己,达到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程度。”[5]239而治愈和控制人类身体的任务,无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无产阶级是从天堂吹来的飓风,是将身体从资本的生殖压抑中解救出来的弥赛亚救赎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是衡量身体康复状况的标尺。如果身体不被这一力量的法则深深攫住,任何和平主义的辩论都无法使其获得拯救。有机生物只有在生殖的狂喜中才能战胜破坏的狂怒。”[5]104
综上,借助文明与性压抑、集体无意识、恋母情结、醒与梦、移情、死本能、图腾与禁忌等精神分析的思想范畴,本雅明从“当下”和“新生”两个维度阐释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奇异理解,从“商品移情”和“身体政治”两个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奴役,在蒙太奇式的历史隐喻空间中构建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神奇交汇。之所以说“神奇”,是因本雅明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糅合方式既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式的借鉴运用,也不同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式的概念融合,更不同于哈贝马斯式的解释学缝合,而是一种感性梦幻的隐喻式链接——精神分析为这一链接提供了烧炼材料,马克思主义则为这一链接提供了炼烧模具,二者共同在他的隐喻熔炉中锻造出一把现代性救赎的文艺美学之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本雅明无疑是一位具有浪漫诗人气质的独特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表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推演与理性沉思,而是充满了浓厚的弥赛亚救赎情怀和文艺美学的朦胧影射色彩。本雅明用独树一帜的诗学方式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风采,用感性破碎的象征意象绘制了异样的资本主义批判景观。借助精神分析的棱镜,我们得以理解其浪漫幽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感知其历史哲学中散发的诗意救赎之光,继而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阐发路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束诗意救赎之光终归也只是一道一闪而过的意识形态革命幻想,并未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的内在生产肌理。它在丰富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的同时,也极易引发各类歧义误解,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本真意义的背离。本雅明将商品比作妓女、将无产阶级比作飓风、将资本主义的异化过程比作身体的扭曲失控过程、将共产主义历史进程比作割断恋母情结的性爱旅程,这些意象虽然鲜活新奇,但却看不见丝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追求,因而在革命实践层面必然是虚弱无力的。临终前,本雅明写道:“我们的幸福幻象永远和赎罪的形象绑在一起……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一样,我们都禀有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9]支撑本雅明在绝望废墟上寻找希望光影的,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伟岸身躯,和这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本雅明流寓海外初探
——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