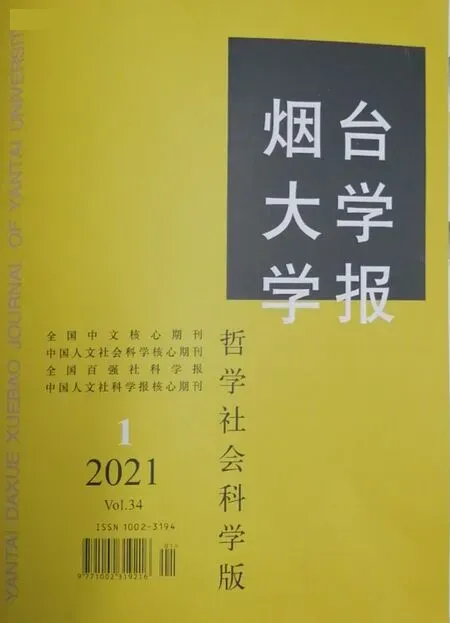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刘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其中,位于中亚的这些国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中国西部重要的邻国阿富汗(2)通常认为,其历史上大约有三个名称:古代称谓为阿亚那(Aryana),中世纪称谓为呼罗珊 (Khurasan),近代以来的称谓为阿富汗(Afghanistan)。关于阿富汗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尚无定论。有的学者把唐代慧立彦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载的“阿薄健国”,看成是最早提到阿富汗斯坦的根据。有关“阿薄健国”的描述可参见慧立彦撰,孙毓堂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是“一带一路”通往中东、中亚、南亚次大陆和远东所要经过的重要节点国家,帕米尔山脉的延入将中国与相关地区连接起来。(3)Marwat , Fazal-Ur-Rahim, The Evolution and Growth of Communism in Afghanistan (1917-79):An Appraisal,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97, p. xiii.作为潜在的重要区域贸易枢纽,以及世界范围内仅有的矿产资源超过1万亿美元的五国之一,阿富汗在经济、安全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作为庞大基础设施项目网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组织对阿富汗的投资环境及社会状况开始给予关注。同时,阿富汗也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在政治、经贸、文化、思想互鉴和城市发展等领域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多族裔国家”(4)multi-ethnic state,学界通常认为,由于历史等原因,阿富汗境内现有的大约50个族体(ethnicities)包括部落、部族联盟、部族、“历史民族”等不同类型的族群,将之称为“多民族国家”尚存争议。这里的“历史民族”(people across boundaries)并非指同一民族。但是,从文化和历史方面看,又曾是同一个民族,这里专指在历史上具有政治统一性或最终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在现实中被分成了不同民族的“跨两国或两国以上国界而居的人民”。,其因族际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使得阿富汗战后重建举步维艰。在过去大约40年间,阿富汗饱受战争的摧残,其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设计、社会文化进步和人民生存健康等诸多领域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及外部挑战,争取实现国家和平与稳定成为今日阿富汗的当务之急。与大多数曾被殖民的“多族裔国家”一样,阿富汗社会长期处于“族体众多,语言多样,民众通常具有多重或多层次身份认同”的状态。(5)Shahrani,Nazif M. ,“War Fac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4, no. 3(September 2002), pp. 715-722.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阿富汗各族民心涣散,政治版图陷于四分五裂境地,其“国族(Nation)”(6)近代以来在欧洲形成的概念,指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建立现代国家的民族,即民族国家的统治民族。直接与国家概念或一定程度的自治观念相关联。它具有比民族更深厚的国民共同体含义,可能包含多个民族、多种语言、习俗、信仰等,并在国家共同体层面形成认同和体制化组织形态。认同和国家凝聚力问题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经几近关乎国家政治生命力的地步。(7)Rais ,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pp.17, 32-35.
但是,在谈及族际关系问题对于阿富汗社会动荡的影响时,人们所持的观点却屡屡相冲突。通常说来,大致包括两种意见:一是部分学者、记者和政府官员等,把阿富汗动荡的症结归类为族际之间的冲突;二是大多数阿富汗政治家出于其自身的部落出身等因素的考虑,否认了族际关系在阿富汗公共事务中可能发挥的重要影响。(8)参见Rashid, Ahme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ieck, Andreas, “Afghanistan’s Taliban: An Islamic Revolution of the Pashtuns”, in Orient , Vol. 38, no.1(1997), pp.121-142.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族际关系的视角,通过研究阿富汗族际关系衍生的历史脉络、族裔群体的组成、战争对族际关系的影响,族裔群体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可能得到满足的路径,以及族裔断层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走向,讨论相关因素对阿富汗重建的重要影响。希望通过本文的初步尝试,使更多的人关注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并为阿富汗早日找到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路径,也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供点滴理论参考和个案支持。
一
多年来,关于阿富汗各族的起源问题,往往与诸多猜测和传说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学者认为,阿富汗各族古已有之,是比较稳定的文化单位,后被人为地设置了族际边界,并在数百年里不断卷入冲突之中。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则认为,阿富汗各族大多是在20世纪形成甚至“创造”的,其族源不可视为阿富汗国族身份认同的参考。(9)Mshahran, Nazif, “State Building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in Afghanist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li Banuazizi & Myron Weiner (eds.),Th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74.
值得注意的是,“国族”一词在19世纪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基本上是陌生的。许多学者在描述阿富汗人口的族裔结构时,都使用了部落、准部落和部落联盟等族裔共同体的称谓。有人甚至将“种族”等同于阿富汗“国族”,并将阿富汗居民分为8个主要族群,即帕坦人(普什图人,Pushtun, Pakhtun, Pushtuns)、优素福扎伊人(Yusufzai)、阿夫里迪人(Afridi)、哈塔克人(Khattak)、达塞人(Daticae)、吉尔吉斯人(Ghilji)、塔吉克人(Tajik)和哈扎拉人(Hazara)。这些族群中的大多数族体今天都被打上“普什图标签”。(10)参见Bellew, Henry Walter, The Races of Afghanistan; Being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Nations Inhabiting that Country, West Bengol:Calcutta, 1880.
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才开始根据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将阿富汗各族加以识别。法国人类学家在研究阿富汗社会结构时,首次使用了“族群(groupe ethnicique)”一词,并将阿富汗各族分为若干群体。(11)参见Dollot, R., “Afghanistan: Histoire, Description, Moeurs, et Coutumes: Folklore, Fouilles”, in Istorija Afganistana, Vol. 2, 1964/65.1950年代中期,有学者将阿富汗各族的分类名称引入英语文献,并根据文化习俗等创建了新的族体分类标准,以“比较准确地识别”各族的界限,并由此识别出努里斯坦人(Nuristani)、帕夏人(Pashai)、阿伊马克(Aimaq)、塔吉克(Tajik)和山地—塔吉克(Mountain-Tajik)等。(12)参见Wak Foudation for Afghanistan,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Afghanistan: A Six Year Survey and Research (1991-1996),Kunhar River Rafting Enterprise:Peshawar, 1999.在对阿富汗各族进行识别的过程中,不乏西方学者的主观想象成分。比如,“塔吉克”一词,用于社会交往时,被用于指称不属于普什图人、哈扎拉人的群体或个人,体现着一种反对族裔歧视的观念。同时,塔吉克族被用于指称所有讲波斯语的逊尼派村民或没有部落背景的部分城市居民,塔吉克族建构的共有历史信念基础因此难以得到巩固和加强,帮派分立、相互倾轧的现象时有发生。
阿富汗的土著人口很少,至今没有建构起“国族”,也未能形成具有“共同特质”的国族文化,(13)Dupree, Louis, Afghan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57-65.阿富汗重建因此屡遭挫折。长期被当作世界几大列强争夺的“猎物”的结果之一,就是其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族体,人口最多的两个族群均未超过总人口的25%,另外有五个族群人口均占总人口的5%左右。从历史上看,雅利安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莫卧儿人和印度人都曾征服过阿富汗,他们的后代遍布今日阿富汗版图之内。因此,在阿富汗同一个省份看到北欧、南亚、东亚和南欧人的后裔是很常见的现象。依据语言、宗教等差异而确定族际界限,则该国四个主要族群分别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有学者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阿富汗的北半部一直是波斯的一部分”。(14)Dubow, Benjamin, “Ethnicity, Space, and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in Urban Studies Programme: Senior Seminar Pape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cember 29,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repository.upenn.edu/senior-seminar/13.在1747年杜兰尼帝国(15)18世纪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伊斯兰强国。1747年,由普什图人中的阿布达里部落萨多查伊部首领杜兰尼创立,是阿富汗历史上的第一个独立政权,全盛时期领土包括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东北部和印度旁遮普东部。崛起之前,民族志中的“阿富汗”或“阿富汗斯坦”开始成为族群的名称。(16)Smith, Anthony D., The Ethnic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6.虽然,当时法国人类学家将阿富汗人分为几个族群,但是直至19世纪,“阿富汗族”才开始正式被用于文献中。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学界和政府尚未根据语言、教派、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为阿富汗社会的族裔类别作出系统的划分”。(17)Boboyorov, Hafiz, Henerik Poos & Conrad Schetter, “Beyond the State-Local Politics in Afghanistan”, in Bon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Feb. 26-28).
杜兰尼帝国建立后,在奥克斯河和印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当时被称为“普什图人”的族群,占了阿富汗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阿契美尼德帝国(18)又被称为“波斯第一帝国”,古波斯地区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鼎盛时期的领土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帕米尔高原,南到埃及、利比亚,西至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达高加索山脉、咸海。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所灭。灭亡之后,曾有多个国家在现在的阿富汗领土上起起落落。(19)Saikal, Amin, 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New York: Fifth Avenue, 2006, pp. 17-18.阿富汗的族际关系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成为该国内战的主要导火索之一。阿富汗各族在这一地区生活了5000多年,并多次联合起来反对大英帝国和苏联等大国势力的入侵,为捍卫国家独立而展开不懈的努力。阿富汗的战略位置不断吸引世界列强为了赢得或保护各自利益,反复利用族际矛盾在阿富汗境内挑起族际冲突。该国族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不断得以加强,并成为阿富汗主权国家进步的障碍。同时,不同族体之间在“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居住地理环境和语言”等方面差异的长期存在,也使得各族的特征得到不断强化。
二
在近代之前,阿富汗的领土上居住着诸多族群,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外,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共性比较有限。事实上,阿富汗的族群是根据地理边界划分的比较牢固的文化单位,多年来一直处于冲突之中。(20)Shahrani, Nazif M. , “State Building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in Afghanist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li Banuazizi and Myron Weiner (eds.), The State, Religion and Ethnic Politics: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6-29.从社会地位上讲,阿富汗普什图人“享有最高统治地位,所有的国王都来自这个族群”。18世纪前,阿富汗国家基本呈分裂状态,印度的德里苏丹国统治多数地区,族际关系问题基本未成为阿富汗政治中的重要问题。(21)Rais, Rasul Bakhsh,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eighbors”,in Ethnic Studies Report, Vol. XVII,no. 1(January 1999).但是,阿富汗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族际之间的传统权力平衡。今天,非普什图族群比20年前表现得更加强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富汗这个国家可视为因英国和俄罗斯等敌对殖民国家在19世纪末共同推动而建立。由于普什图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其“民族国家”概念中一直倾向于彰显普什图元素。“阿富汗”一词在波斯语与普什图语中为同义词,即“普什图人的地方”。普什图语一直是阿富汗的通用语言,阿富汗历史也大都是从普什图人的立场出发而编撰的。普什图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采用了“排他性”部落统治模式,其在国家不同地区、政府不同领域中都享有特权,获取了占有公职等大批公共产品的机会。塔吉克人往往被允许在经济和教育部门任职,而哈扎拉人一般被边缘化。有关各族的刻板印象随之产生:普什图人被认为是“好战的人”,塔吉克人被认为是“吝啬的人”,乌兹别克人被称为“野蛮的人”,哈扎拉人被认为是“文盲”或“穷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尽管在阿富汗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呈现出一定的族群等级现象,但是族际冲突尚未经常发生。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农村地区的居民对首都喀布尔的政治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族群概念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并未将之作为集体行动的依托,也没有表达摆脱国家政体内存在的族群等级制度影响的政治意愿。此外,许多阿富汗人坚持认为,民族国家是以武力干预其社会生活的一个负面存在,而不是他们获得土地等资源的关键因素。
当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族群成为主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交战各方均试图通过增强各自掌控的军事力量的族裔色彩,来提升其影响力和战斗力。苏联领导人希望通过将某些享有文化权益的族群提升为享有政治特权的民族(Nationality),将其绑定到自己的战车上。(22)参见Jadwiga, Pstrusinska, “Afghanistan 1989 in Sociolingustic Perspective”, in Central Asian Survey Incidental Paper Series, Vol. 7, 1990.更重要的是,组织起乌兹别克武装力量等具有族裔归属感的民兵部队。伊朗和巴基斯坦也利用了族际冲突的潜在因素,伊朗建立了在什叶派哈扎拉人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伊斯兰解放党”,巴基斯坦则支持普什图人所主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组织塔利班。
过去十几年中,在阿富汗军事和政治行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冲突各方,或多或少都得到“境外同胞”的支持。交战各派的领导人促使其支持者不断意识到,其过去和现在都因其族群归属问题而受到政治及经济上的欺压与盘剥,“本族”的生存受到“他族”侵略行为的威胁,并通过开展一系列蛊惑宣传活动,在交战各派民众中激发起了集体焦虑、仇恨和嫉妒等情绪。此外,交战各方还以本族的名义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经济与政治资源,在根据其族群人口和领土规模向国家提出政治诉求的同时,其军事行动亦往往被诉诸族裔概念。1992至2001年期间,族裔清洗或灭绝事件时有发生。(23)参见Roy, Oliver ,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今天,阿富汗族裔识别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一是西方学者所“创造”的族群自身,至今大都并不了解或接受“被给予的族裔标签”或族裔身份。比如,曾任阿富汗赫拉特省省长的伊斯梅尔·汗,有时被认为是塔吉克人,有时被认为是普什图人或波斯人,但是他本人一直拒绝接受相关的族裔认同。二是阿富汗现行的族裔识别标准,基本为西方人类学家所制定,与社会现实多有不符。比如,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普什图人讲普什图语,但是事实上前国王查希尔·沙阿等在坎大哈和喀布尔地区的什叶派普什图人,经常一句普什图语也不会讲。三是许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阿富汗人,声称自己具有与被识别的身份相异的族裔认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族裔识别的难度。比如,阿富汗前总统巴巴拉克·卡尔马尔曾多次强调其自身具有普什图血统,但是许多阿富汗人都认为他是塔吉克人或克什米尔移民的后裔。四是制定族裔识别标准的西方学者来自不同学科,所采用的族裔分类方法也多有不同,得出的结论各有特点也在情理之中。比如,德国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阿富汗大约有五十余个族群,而苏联的一项研究声称阿富汗有200个族群。(24)参见Orywal, Erwin (ed.), Die ethnischen Gruppen Afghanistans, Fallstudien zu Gruppenidentität und Intergruppenbeziehung, Wiesbaden: Ludwig Reichert Verlag, 1986.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实际上很难准确识别和计算出阿富汗族群的数量及其规模。因此,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阿富汗“族际问题解决办法”中,“应从族群规模等方面关注阿富汗诸族诉求”等方案也便难以落实。
在没有准确的官方人口普查的情况下,阿富汗主要族群的人口统计数据极具争议。1970年,阿富汗几个主要族群人口数据统计如下: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爱马克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和努里斯坦人,人口分别为700万、350万、150万、130万、80万、60万、30万、10万和10万。(25)Hyman, Anthony, Afghanistan under Soviet Domination: 1964-83, London: Macmillan, 1984, p.11.现在,通常被采用的族群人口比例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爱马克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及其他,分别占比42%、27%、9%、9%、4%、3%、2%和4%。(26)Youngerman, Barry& Shaista Wahab, 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p.14.
除了位于南部和东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以外,阿富汗的其他地区很少呈现族群聚居程度较高的状态,即使在普什图人聚居区也存在族群杂居现象。(27)Maranjiian, G. & Cheskie Issle dovaniia,“The 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Groups in Afghanista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10, 1966, p.263.几个世纪以来,在众多的族群混居地区,许多族群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族际交流交往交融现象,以及随之出现的族群成员体质上的“异族化”态势。当高加索人和蒙古人之间经过长期接触后,在阿富汗北部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中间,遂出现了红发或金发与内眦褶和高颧骨相结合、蓝色或混合色眼睛相组合的体质特点。许多肤色较深的俾路支人和布拉灰人,也开始长有蓝色、绿色或混合色眼睛。(28)Dupree, Louis , Afghan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7, 65.
阿富汗各族群的起源都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一些猜测和传说的影响。(29)Youngerman Barry & Shaista Wahab, 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 p.15.由于族体成分、宗教和语言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长期存在,阿富汗人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族裔国家”方面,一直受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有学者认为,阿富汗国族由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爱马克人五个民族以及几十个族群组成,其中许多族体尚未得到很好的识别与研究。(30)Newell, Richard, “Post-Soviet Afghanistan: The Position of Minorities”, in Asian Survey, Vol. 29, no.11(November 1989), p. 1094.
普什图人主要集中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是该国最大的族群,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部落之一,占阿富汗总人口的50%至54%。尽管亲属关系是部落组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普什图人已开始认识到,“这种古老的纽带并不像过去那样牢固和令人珍视”。(31)Ruttig, Thomas, 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 Kabul,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June 30,2010, Retrieved from http://aan-afghanistan.com/uploads/20100624-TR-ExecSumHowTribalAretheTaleban.pdf.自18世纪中叶以来,他们在阿富汗社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32)Hanley, Colonel Robert, “Ethnic Violence, Impact on Afghanistan”,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e Barracks, PA, April 8,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559961.pdf.其部落联盟主要分作两个,分布范围延伸到该国的南部和东部,但两者间互有敌意。普什图人部落遵循严格的“普什图人准则”(Pashtunwali)。他们往往因其严格的社会阶层分工而被诟病,比如妇女经常被禁足于自己的家里等。(33)Youngerman, Barry & Shaista Wahab, 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 p.15.随着苏联入侵引发的部落之间的政治分裂,以及其他族群被赋予的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新兴权力结构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开始有所下降。
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族群。其26%至30%的人口受过较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与苏联之间的战争以及与阿富汗普什图人的内战,使塔吉克人走到阿富汗的政治前台。他们在后“9·11”时期仍然具有影响力。
乌兹别克人约占总人口的8%,是阿富汗人口较少的族群之一。其集中居住的地区在中亚占据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自土耳其人入侵阿富汗以来,作为逃离军队攻击的难民以及中亚苏联驻军麾下的“战斗人员”,他们在阿富汗定居下来。(34)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2-35.虽然他们与居住在乌兹别克的乌兹别克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他们把达里语(Dari)(35)也作达利语,是阿富汗、伊朗和塔吉克的官方语言,也是部分乌兹别克人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36)Smith ,Harvey H. (ed.), Area Handbook for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 75.
哈扎拉人与乌兹别克人不同。他们并非“土著居民”,而是“13世纪成吉思汗入侵该地区留下的部分后裔”。他们占总人口的7%,定居在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并将达里语或波斯语作为他们的语言。他们是该国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族群。(37)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p.17, 32-35.
爱马克人主要居住在西部赫拉特和东部哈扎拉贾特高地之间的地区。他们讲波斯语,人口约在50万至75万,内部分为4个部族。(38)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p.31-34.
土库曼人、努里斯坦人和俾路支人占总人口的4%,他们都属于“历史民族”。阿富汗土库曼人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土库曼人在历史上曾为同一共同体,在族性和语言上具有共性。而努里斯坦人则与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卡夫里斯坦地区的卡夫尔人共享文化和历史记忆。他们在19世纪皈依伊斯兰教,该地区随之被改名为努里斯坦。而俾路支人则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俾路支人具有共同的祖先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认同。(39)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p.34-35.
三
阿富汗在当代历史上内战频仍,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内战的长期存在是其践行“族裔歧视”理念的重要产物。投身战火的族群通常认为其彼此是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他们渴望获得比“对手”更高的权力并控制国家。爆发在不同族群之间的长期内战所引发的破坏性,令其倍感恼怒和失落,既有的族裔认同随之得以强化。同时,一些族群则从中体验了一种真正或想象中的赋权感。阿富汗的战争,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平衡。
今天,阿富汗各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其各自的族裔认同。阿富汗人对抗“共产主义政权”和苏联入侵的应对力量,或多或少是在部落和地方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把一些国家的派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赶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从而在本族政党领导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具有某种自治意义的政府。族裔因素随后在“圣战者”群体中制造了政治上的“极化”现象,使其在“共产主义政权”被推翻后陷入了争夺权力的痛苦斗争。(40)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17.政治“极化”造成了具有极端性价值取向的宗教派别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抗,并逐渐转变为普什图人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部分人因担心失去既有的权力,而与来自北方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结盟,后者在喀布尔随之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喀布尔政权传统上一直为普什图精英掌控。在现代主权国家行政机构未能正常运作的情况下,阿富汗冲突各方始终难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或维持稳定的联盟,国家统一屡遭破坏。同时,普什图人与其他族群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以及信奉“传统伊斯兰教”和信奉“革命伊斯兰教”的政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了其共同敌人——苏联撤军后内部滋生的多种冲突。
“塔利班运动”的兴起,旨在通过军事征服寻求部分普什图人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其致力于建立神权路线指引下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带有比较鲜明的普什图人的色彩。他们发动的军事进攻,将人口较少的族群推向社会边缘,甚至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规定的人权标准。塔利班统治结束后,政治安排更偏向于阿富汗北部的非普什图族群。随着“新宪法”的出台以及中央和地方议会选举活动的开展,阿富汗的政治制度越来越体现出多族裔特点。虽然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重建而逐步得到缓解,但是国族认同和区域利益建构问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阿富汗社会各族寻求和解,重建统一的多族裔国家的路径选择,已成为相关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先决条件。(41)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18.
世界各地族群的文化特色不尽相同,但是在族裔身份认同建构依据方面,却具有一定的共性因素,比如亲属关系就是确定族裔身份的重要因素。当谈及发生在阿富汗版图上的“暴力统治”和“内战”等相关话题时,族际关系通常被视为事关阿富汗历史发展的重要条件,并对当今阿富汗国家重建的态势与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甚至认为,阿富汗族际关系的恶性发展“可能导致暴力统治的重现”(42)Hanley, Colonel Robert, “Ethnic Violence, Impact on Afghanistan”, in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e Barracks, PA, April 8,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559961.pdf.。事实上,阿富汗各族之间在土地和水权问题上的持续冲突,一直困扰着阿富汗社会。(43)Isby, David,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Empires: A New History of the Borderlands,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0, p.189.比如,就农业治理而言,农村塔吉克人与城市普什图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农民与普什图牧民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这些族际之间的敌对性行动,对相关地区的社会稳定提出了诸多挑战。(44)Isby, David,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Empires: A New History of the Borderlands, pp.191-196.总的说来,阿富汗各族对于族裔特征的反复强调,进一步加剧了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之间,以及非普什图诸族之间的分裂,相关冲突与叛乱活动直接威胁到阿富汗国家统一与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自“9·11事件”发生以来,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面对阿富汗混乱的政治及军事局势,开始将其社会动荡归因为族裔冲突的结果,并强调族裔问题是分析阿富汗冲突的最重要出发点。事实上,虽然族裔问题可视为认识和理解阿富汗冲突的主要抓手,但并非引发冲突的唯一原因,对于相关冲突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中还应考虑其他几个方面:其一,在阿富汗战争中,族裔问题对于军事和政治凝聚力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比如,曾任阿富汗副总统的哈吉·卡迪尔和反塔利班统治领导人阿卜杜勒·哈克等诸多武装部队指挥官,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数次改变了他们对本族身份的认同。其二,虽然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阿富汗族群理解为等同于可以代表某一群体利益的政治族体,但是阿富汗领导阶层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基本未从各族利益出发给予相应的考量。其三,虽然族际矛盾可视为阿富汗冲突持续存在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并非可以涵括冲突各方的所有分歧。比如,根据联合国做出的解决阿富汗冲突的权力分享安排,按人口规模制定的部长人选构成是:11名普什图人、8名塔吉克人、5名哈扎拉人、3名乌兹别克人和3名未任命的部长。虽然,这种各族都有代表的政府体制安排,理论上应比较充分尊重了阿富汗各族的利益,并且哈米德·卡尔扎伊最终成为过渡政府总统人选也是各方基于其普什图族出身的考量,但是,普什图族政治精英并不承认卡尔扎伊为其代表,卡尔扎伊因此在普什图人中并未得到有力支持。
四
平等和谐的族际关系的实现,只能是基于族群生存与发展同步性和持续性的存在,当然,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各族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力达到绝对公正状态。虽然,阿富汗各族从形式上看在“资源或代表权”等相关问题上,似乎并未发生重大冲突,但是,普什图人实际上长期依据部落联盟管理方式治理主权国家,通过武力征服把持阿富汗国家上层建筑长达两个多世纪。(45)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pp.17, 32-35.阿富汗社会精英基本上都是普什图人。
族际交往交流交融在阿富汗的版图上并未真正停止过。“波斯语言和文化在波斯帝国统治该地区数百年后,远播至阿富汗和中亚,给包括塔吉克人和阿富汗普什图政治寡头们在内的当地人民,留下了持久的记忆。”(46)Herzig, Edmund , “Regionalism, Iran and Central Asia”,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no.3(May 2004), p.511.实际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两侧的普什图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非普什图人的社会伦理、风俗和官方语言,他们所使用的波斯语,因其在方言和语调方面与普什图语的差异,而称之为达里语或达利语。
20世纪的阿富汗领导阶层是否试图建构具有民俗、现代文学等表现形式的文化,从而可以显现阿富汗各族共性的国族认同,是值得商榷的。一些从事阿富汗现代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研究的普什图族学者认为,阿富汗各族大多承认“阿富汗国族主义和认同存在,并赋予其清晰的国族特征”。然而,非普什图族的知识分子则普遍认为,阿富汗国族身份的建构是以普什图人为社会基础的一种理念与实践的结合,驱逐、庇护、复仇和瓦利(47)是阿富汗普什图人所推崇的神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尺度,包括崇尚荣誉、好战,好客、庇护、复仇等。等普什图人的历史、政治与社会文化符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普什图人比阿富汗其他各族更易接受阿富汗国族认同,主要是因为普什图人的舞蹈、音乐等族裔文化符号被其视为国族文化的象征。(48)Ahady, Anwar-ul-Haq,“The Decline of the Pashtuns in Afghanistan”,in Asian Survey, Vol. 35, no.7 (July 1995), p.622.
自1919年签署《拉瓦尔品第条约》(49)1919年8月,阿富汗和英国在印度的拉瓦尔品第(今属巴基斯坦)订立了双边和约。主要内容包括英国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阿富汗政府承认已故国王与英国确定的阿富汗与印度的边界线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阿富汗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尝试建构单一民族国家即“普什图民族国家”,包括加强普什图族掌控的中央政府在阿富汗社会不同领域的行政能力,建立植根于普什图族文化的统一教育结构,以及在弱化族裔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不断巩固以普什图文化为基础的国族特征。但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和许多其他人口较少族群,并没有“以普什图人为基础建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来看待自己。他们因自己族裔特性不被承认,并被排斥在国族认同建构进程之外而感到愤怒,但是他们难以获得表达不满的渠道,更难以越过掌控阿富汗寡头政权的普什图精英圈层以获得权力资源。(50)参见Ali, Mehrunnisa, Pak-Afghan Discord-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ocuments 1855-1979), Pakistan Study Centre, Karachi : University of Karachi,1990.
在君主政治制度主导下的阿富汗,“有关国家和国族的脚本为专制制度中的主流族群所描摹,专制政治本质的排他性因此得以彰显”。(51)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 London: Verso, 1977, pp. 462-550.由于诸多族群利益的表达或代表性民主处理机制从权力结构场景中消失,国家领导阶层关注的只是“利益获得者得到权利和财富的数量”,关于地方主义、部落主义的“神话”遂获得赖以滋生的土壤,“神话的存在感”也因人们难以寻求政治参与机会而不断得到维护。(52)参见Hobsbawn,E.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诚然,阿富汗各族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历史由来已久,他们为争取国家独立作出的巨大牺牲举世公认。(53)参见Rubin, Barnett R.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 From Buffer State to Failed State,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至少在阿富汗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中存有一定的国族认同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没有影响到阿富汗广大的农村地区,对农村人口每天的现实生活来说,国族身份认同问题,“仍然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其生活密不可分的家庭、氏族、亚部落、部落和地方息息相关”。(54)Mousavi, Syed Askar, The Hazaras of Afghanistan: An Historic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y, Surrey: Curzon, 1998, pp.168-74.
如何在集权和分权坐标轴上定位阿富汗国家重建取向,各族意见不尽相同。军阀或地方领导人领导的割据势力的现实存在表明,今天的阿富汗尚未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有人将过渡政府称为“喀布尔市议会”,其权威几乎难以超越首都喀布尔的边界。可以设想,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同时,可能导致该国陷入新一轮暴力冲突的各种隐患,始终未能销声匿迹。需要注意的是,各族中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离心力,一直阻碍着阿富汗国家重建的进程。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能够体现族裔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一系列可以覆盖整个阿富汗的统一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在近期很快建立起来。
关于能否通过采取民族联邦制作为阿富汗治理模式,人们已进行了许多讨论。众所周知,阿富汗如果实行民族联邦制,需要具备如下基本前提:一是如果一个政府以族裔为基础加以建设,首先就必须表明如何确定区分阿富汗各族的标准,即政府必须完成族群识别工作。二是必须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族群规模,鼓励无视族群存在的阿富汗人加入官方承认的族群系列。需要指出的是,因个人选择取决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族群身份识别会随之频繁发生,相关“代表配额”遂将难以确定。三是在相关人口普查中,要解决属于未获官方承认族群人口的族裔识别问题,族群识别因此会成为阿富汗政治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四是平衡各族利益诉求。族群或部落领导人不仅会以某族的名义在过渡政府中主张一定比例的部长人数,而且对特定的核心职位会提出诉求。根据彼得斯堡协议,外交、内政和国防部的核心部门都被交给了潘杰希里斯,(55)参见Wilber, Donald N., Afghanistan: Its People, its Society, its Culture, New Haven: HRAF Press,1992.这加深了有关“族裔歧视”存在与否的猜疑。比如有人提出在阿富汗部委中应有一个乌兹别克人职位的要求,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同时,许多人主张每一个核心部委都应由各族的政治家担任,认为包括俾路支人、土耳其人、锡克教徒或印度教徒等在内的非普什图族群,也是阿富汗的重要族体,虽然其人数不多,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联合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中,迟早会在中央和省政府中要求享有政治代表权。对现今阿富汗政府而言,要平衡各族的相关诉求可谓勉为其难。
可见,阿富汗重建如果选择民族联邦制路径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方面,阿富汗没有一个省份是单一族裔居住的区域,一省之内往往有若干族群的成员居住在不同的村庄或山谷。实行民族联邦制,可能会促使主权国家内部少数族群所难以容忍的现象滋生。如同发生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族裔同质化”“清洗异族”的想法和政治实践,可能很容易降临到相关地区。另一方面,自进入21世纪以来,阿富汗国内政局仍处不稳定状态,在其北部驱逐普什图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主张改变省界或建立自己的新省,成为非普什图族精英获取部分民众支持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将阿富汗分为北部、塔吉克—乌兹别克区和南部普什图地区,或肢解阿富汗,将其各地分别纳入邻国的主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陷于雪上加霜的境地。此外,需要关注的是,实行民族联邦制需要对即将建立的国家进行新的行政区域划分,原本可以用于国家政治重建的国民既定地区身份证明会被废止,而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1964年建立省份时所确定身份证明(而非族群或部落出身证明),已成为在过去多年中被国家法律所承认的身份证明。
除了民族联邦制外,关于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讨论,也得到部分学者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有观点认为,阿富汗可以仿效印度或瑞士治理模式,联邦之内的行政实体单位不完全或主要根据族裔界定,沿袭其历史上的一些自治传统,实行省或地方自治。其观点还强调,曾经建立的各省或地区应继续充当联邦制度下的行政版图基础,其中部分“地方习惯法”“宗教名人”等法规或个人,可以在法律、语言、宗教或文化领域发挥既有效力、行使既有权力。这一观点也指出,如果进行司法改革,在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典,并阻止通过宗教法院等非国家渠道诉诸司法,会违背基本民意。(56)Schetter,Conrad, “Der Afghanistankrieg-Die Ethnisierung eines Konflikts”,in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Vol.33, no.1-2(2002), pp. 15-29.
事实上,在阿富汗实行任何形式的联邦制,都可能使阿富汗国家重建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如果任由在关于阿富汗国家重建模式的辩论中主张权力下放的军阀或部落领导人把持地方机构,可能意味着军阀割据状态的长久存在,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军阀或部落酋长一定会履行现代主权国家体制下的省长等职责。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多元化法律体系”,即上诉法院在全国不以同一法律主体为基础,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规定的基本人权法得以并行,那么就会严重破坏现代国家建设,摧毁平等和防止暴力等基本原则。研究表明,实行民族代表制,确定各族在国家权力中心的代表名额,可能意味着增加冲突而不是减少冲突,从而对阿富汗重建有负面影响。(57)参见Isby, David , Afghanistan Graveyard of Empires: A New History of the Borderlands, Pegasus Book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职位的族群配额的设定,预示着某一族群左右国家治理危险的长久存在,并为各族在争取每一个官方职位时“任意玩弄数字”提供了可乘之机。普什图族非政府组织“阿富汗瓦克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普什图人占阿富汗总人口的62—63%。相反,在波恩会谈中被任命为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则反驳说,普什图人只占阿富汗人民的38%。阿富汗各族在联邦体制之下,会通过“数字战争”的道路解决相关问题,这是早有迹象的。(58)参见Saikal, Amin,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 London: I.B.Tauris, 2012.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反对塔利班的战争中,开始尝试“结交经过时间考验的敌人的敌人的策略”。(59)Rais, Rasul Bakhsh, Recovering the Frontier State: War, Ethnicity, and State in Afghanista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7.阿富汗“北方联盟”(60)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军事政治联盟组织“拯救阿富汗斯坦全国统一伊斯兰阵线”,由一些相互敌对的阿富汗军事派别联合组成。其曾推翻苏联扶植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国。1996年,该政权为塔利班武装推翻。2001年,在美国、英国等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它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了大部分阿富汗领土。作为超级大国的“天然盟友”此时挺身而出,提供了诸多可以提供的帮助。因为美国和“北方联盟”在粉碎塔利班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具有塔利班背景的普什图人因此对其自身“在后塔利班权力安排中的代表权”的担忧遂逐步提升。2001年11月,来自塔利班故乡坎大哈的普什图人哈米德·卡尔扎伊出席了波恩会议(61)在德国波恩召开的国际性组织的会议,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官员和代表与会。该会议就南极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公约等问题展开国际谈判,也重点讨论了美军撤离之后的阿富汗局势,以及同塔利班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此举并未消除普什图人对权力被美国支持的塔吉克军阀所限制等问题的担忧。他们坚持认为,卡尔扎伊实为美国所操控的傀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发展成为其采取强化打压“非我族类”手段的不同理由。在他们看来,“在政治上分裂和被边缘化的并非一直是人口较少的族群”,“即使在历史上执掌过国家权力的族群,随着其他社会群体所享国家治理权的提升,其既有权力的分量则会下降,其族裔身份亦会被政治化”。(62)Nagel, Joane & Susan Olzak, “Ethnic Mobilization in New and Old States: An Extension of the Competition Model”, in Social Problems, Vol. 30, no.2(December 1982), pp. 127-143.总的说来,“北方联盟”开始控制喀布尔,普什图人之间久存的利益冲突依旧难解,普什图人抵抗组织政党与基层社会民众长期脱离,西方大国开始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中最强大、最严密组织“伊斯兰党”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反政府力量,阿富汗邻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加剧阿富汗冲突各方矛盾等,这些因素在普什图人权力衰落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3)Ahady, Anwar-ul-Haq, “The Decline of the Pashtuns in Afghanistan”, in Asian Survey, 1995 (July), pp. 621-634.
今天,阿富汗境内塔利班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活跃。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相关政策,大都是在同非普什图人合作中完成的。研究表明,美国对非普什图族的关注要多于对普什图人的关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64)Haq, Farhat, “Rise of the MQM in Pakistan: Politics of Ethnic Mobilization”, in Asian Survey,1995 (November), pp. 990-1004.美国这种政策倾斜或选择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曾被塔利班民兵赶出喀布尔政权的非普什图人,远比为塔利班提供强大政治和族裔基础的普什图人更欢迎和支持美国军事力量。总之,在后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来自普什图地区的一些部落领导人,以及具有地方或区域影响力的部落首领,基本都与外国势力通力合作,而阿富汗国族建构基本停留于“空想”状态。
五、结 语
在当今世界,无论地区还是国家的族裔结构均难以呈现完全同质状态。不容忽视的是,阿富汗各族对族裔事实上的忠诚,通常比对国族的忠诚更为强韧,并在不同的族群利益诉求中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动员力。对于“非我族类”采取暴力灭绝、清洗等政策,在阿富汗多族裔社会中始终未能销声匿迹。由于多年内战、外国势力的不断干预和国家经济体系的崩溃,阿富汗建立平等、和谐族际关系方面一直举步维艰。随着国家重建成为“当今阿富汗的首要政治议题”,其国族认同建构遂被视为重建实践中难以回避的重中之重,包括赋予未成年人切实享有国民权,以及使得各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平等代表权制度化等。占阿富汗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必须认识到,重建国族身份认同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族际关系融合而非“互斥”的国家。尊重各族在国家生活诸领域内平等表达意愿的合法性,将在国家权力安排中产生令各族振奋的政治影响。可以预想,随着国力的提升、国家生活不同领域的重建项目的跟进以及乐观的政治效果的出现,阿富汗各族之间将来可能会出现新的团结和谐气象。
实践表明,国际环境可以决定地缘政治的锚定,既能够阻碍也能够扩展对抗性族际关系的滋生程度。阿富汗地处内陆,资源基础薄弱,并位于世界政治的边缘,因此难以获得足够的经济或政治支持以抵御外部力量干涉其内部事务。它在从“历史缓冲区”转变为苏联盟国的过程中,逐步被视为远离世界权力中心的“弃子”。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持续受到政局不稳定、政权两极分化、地区权力更替和内部对抗不断的影响,同时相关事态发展的后果大都是以族际冲突为表征得到体现。但是,据此认定阿富汗国内暴力冲突的持续存在应归咎于族际关系问题,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毫无疑问,族际矛盾的存在是事实,但不是引发阿富汗内乱,并导致其四分五裂的唯一因素。
在今天的阿富汗,国际社会一再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的阿富汗尚未构成关系到其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当今阿富汗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武装冲突的主要推手。因此,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如此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任何以利用族际关系作为争取自身利益的出发点,从而支持或反对阿富汗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都会招致列强在巴尔干干涉族际冲突的相似后果,对解决阿富汗冲突难以产生任何助益。
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有参与其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治理观,(65)《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日,第1版。对于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各种纷繁事务的新理念。“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应是阿富汗各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所在。阿富汗各族只有“多谋团结之策,多行共赢之举”,才能推进国家重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安居乐业,以期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