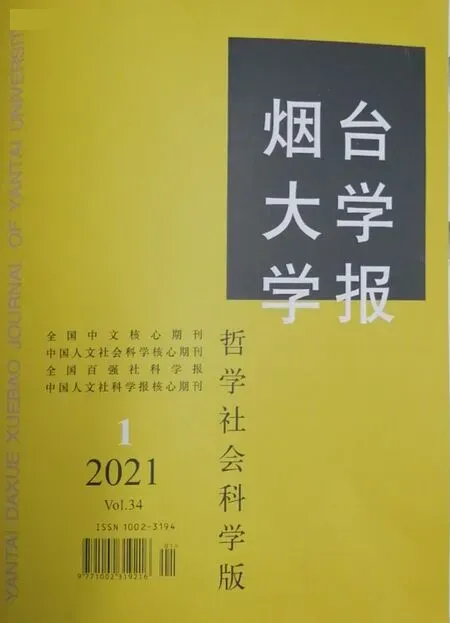论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义和团运动”
丛新强,于欣琪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一、从鲁迅文章的一则注释谈起
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上刊登了鲁迅与陈铁生的一组通信,二者针对“中国拳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陈铁生一文主要驳斥鲁迅对于“中国拳术”的否定态度,盛赞拳术有“回生起死之功”(1)陈铁生:《拳术与拳匪——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二者的分歧在于中国传统拳术是否含有糟粕,鲁迅先生所关注并批判的是“鼓吹拳术”背后的一系列封建守旧的社会现象,而非中国拳术本身。不过双方对于“义和团”的看法却出奇一致,皆认为这属于“鬼道主义”的范畴。清朝末年,时人多称“义和团”为“拳匪”,其中,批判之音不绝于耳,认为“乱天下者,义和团也”(2)林纾:《剑腥录》,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6页。。然而,庚子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却在后世文本中随时代更迭而发生转换。我们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作品集所收录的《关于〈拳术与拳匪〉》(原标题《拳术与拳匪》)(3)关于文章标题,在2005年对《鲁迅全集》进行修订前的版本中,皆遵循唐弢先生在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时所拟定的题目——《拳术与拳匪》,后经考辨,其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时本无标题,而是“置于陈铁生《拳术与拳匪—— 驳〈新青年〉五卷五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一文之后”,所以,在2005年《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中,将题目拟定为《关于〈拳术与拳匪〉》。见韩之友:《〈鲁迅全集〉第八卷修订述要(上)》,《上海鲁迅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中对“拳匪”一词的注释,即可窥探一二。
此文在被收入唐弢先生所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以及1959年发行的重编版《集外集拾遗》时,并未对“拳匪”一词进行解释。(4)参见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第194-200页;鲁迅:《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73-77页。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下文简称《征求意见本》),注释工作分别由辽宁、山东两地的注释组负责。其中,有关“拳匪”一词的详细注释节录如下:
“拳匪” 这是反动派对义和团的侮称。十九世纪末,义和团最初兴起于山东,名义和拳,他们设立拳场,练习武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清秘密组织,后来发展为遍及华北几省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时,义和团奋起抵抗,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是由于义和团没有看清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实质,对帝国主义还只有感性认识,表现为笼统地排外,结果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联合镇压。(5)鲁迅:《拳术与拳匪》,见《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 》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89页。
注释点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表现出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统治”的否定态度。注释工作组曾明确表示:“在注释工作中,同志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认真看书学习放在首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6)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佚文)》注释组:《山东新华印刷厂和山东师院共同组成三结合组进行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佚文)〉注释工作》,《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4-5期。因此,将“拳匪”一词评价为“反动派对义和团的侮称”正是延续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而在1981年正式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关于“拳匪”的注释则大幅度删减:
拳匪,一九〇〇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7)鲁迅:《拳术与拳匪》,见《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1981年版的注释较《征求意见本》更为简洁客观,这是由于注释工作的科学性有所提高,但同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读者对象发生了转换——《征求意见本》的“编印说明”中提到:“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 》上卷“编印说明”,第1页。显然,该版本的鲁迅作品集要求适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从注释工作队伍到读者受众,都体现了群众路线。而1981年的注释工作则规定:“《鲁迅全集》以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为读者对象。一般不作题解,有些篇如必须题解的,可在该篇的注一中作类似题解的说明。”(9)《关于〈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工作的意见(草案)》(未刊稿),转引自谢慧聪、李宗刚:《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体例及其文学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题解的取消以及读者对象的转换,使得注释也相应发生改变,不过,仍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从1978年的“侮称”到1981年的“诬称”,直至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问世,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性质与价值判断才逐渐隐去,李新宇因此评价:“《鲁迅全集》2005 年版的注释在1981年版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尤其是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10)李新宇:《〈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沉重历史》,《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鲁迅全集》2005年版的这一注释有了明显变化:
拳匪,1900年(庚子)我国北方爆发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他们以设拳坛、练拳棒和其他迷信方式组织民众,初以“反清灭洋”为口号,后改为“扶清灭洋”,被清朝统治者利用攻打外国使馆,焚烧教堂,后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共同镇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的上谕中始称他们为“拳匪”,此前的上谕称“义和拳会”。(11)鲁迅:《关于〈拳术与拳匪〉》,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03-104页。
从鲁迅与陈铁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通信里,可以看到当时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而通过不同版本的鲁迅作品集关于“拳匪”一词注释的变化,也可以推断出不同时代主流话语对这一“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12)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3页。在本雅明的历史观念中,时间不是被割裂的过去,而是置于“此时此刻的存在”中被认知。历史的结构化使得“历史记忆”在不同时空中被重组,由此,弗朗索瓦·阿赫拖戈得出“‘我们的记忆’为历史所改造”(13)弗朗索瓦·阿赫拖戈:《历史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24页。的结论。
那么,二十世纪以来,文学文本中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叙写因何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罗生门”式的面貌?改写这一“历史记忆”的发生机制和话语策略是什么?从“1900”到“新世纪”,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触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叙事”,其内部呈现出的情感结构与叙事构造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从“拳匪”到“英雄”的转化
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的上谕中,已经用“拳匪”一词指称“义和团”(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不过其态度摇摆不定,仅在农历五月的短短一个月内,上谕对“义和团”的称呼就经历了“会匪”“拳民”“拳匪”“义和拳民”的不断转换。一方面,从上谕对其称呼的反复变化可看出统治者对待“义和团”的暧昧态度;另一方面,其时国人对于“义和团”的评价各异,这也反映出晚清时局的变幻不定以及这一民众运动的复杂态势。有学者通过对“义和团”相关文本的搜集整理比较,得出“义和团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不断转化”(15)王先明、李尹蒂:《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的结论。显然,时代的更迭与历史语境的变化使得“义和团”形象产生了两极化的差异,“拳匪”与“英雄”的转化,不仅经由文学叙述从而为历史赋形,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所造成的断裂也成为介入历史的途径。
(一)“拳匪”话语:“民气可用”与“民智可忧”
清末民初,对“义和团”进行叙写的文本中,大多用“拳匪”一词定义其性质,(16)王先明、李尹蒂:《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义和团”往往是以作为“国变之祸端”的形象跃然纸上。1902年,李伯元曾著《庚子国变弹词》,全景式地再现晚清“庚子之乱”的衰败景象,展现“义和团”的起端发迹。作者在序言中说道:“愁形惨状,荟萃一编,有不伤志士之心,而亡国民之气者,无是理也。”(17)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01页。创作这篇曲艺作品意在感伤时事,绘时局之“愁形惨状”。而其中尤提及“国民之气”,实际上晚清以来“民气之说”愈发盛行。1900年,《清议报》就曾刊登先忧子的政论文章《论中国民气之可用》,其中论述“义和团”时,虽有批判,但肯定了善用“民气之盛”,内可立国,外可抗侮:
或又曰义和团之起事也,其气亦不可谓不盛。然横挑外衅,适足以速召瓜分。盖民气固未必有益于人国也。曰:无文明之思想者,则举动皆若野蛮,勇悍适以败国,而为天下之乱民;有文明之思想者,举动皆循公法,坚劲足以立国,而为天下之义民。(18)先忧子:《论中国民气之可用》,《清议报》1900年第57期。
按此论述,“义和团”即是“野蛮之乱民”,在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烧杀掠夺的“拳匪”也是有迹可循。“文明之思想”成为划分“乱民”与“义民”的核心标准,这其实正是清末文人藉“拳匪”形象所要阐述的重要主题。忧患余生(连梦青)在《邻女语》中写尽“拳匪”之“愚”,书中有一细节:“义和团”领袖张德成用黄纸化咒符祭坛,写上五个大神名目,分别是关公、孙悟空、李白、黄天霸和毓贤,但是,“却把‘毓’字忘记笔画,写成一个‘流’贤”(19)忧患余生:《邻女语》,上海:上海文化出版公司,1957年,第66页。。因此,作者曾多次提及“读书之用”——“招募山西文人秀士,入堂读书,要使文明之化,普及众生,以后永免再有民教冲突之案。”(20)忧患余生:《邻女语》,第61页。此句与阿英编选的《庚子事变文学集》中的版本有出入,《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删去了“要使文明之化,普及众生,以后永免再有民教冲突之案”这一部分,而阿英本人也曾在“例言”中提到:“由于阶级立场与时代局限,当时作者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有所限制,对情况掌握也不够全面,部分甚至有意歪曲,与事实出入很大。”作为一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集,编选者显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作品进行了删改,由此,更加体现出不同历史语境中对“义和团”的叙写和塑造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例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页。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借黄龙子之口探讨“北拳南革”之乱,以强调“开文明”之重要性:“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逼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逼出甲寅之变法。”(21)刘鹗:《老残游记 附续集 外编残稿》,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134页。刘鹗主张通过“变法”的途径,使“文明大著”,其中鲜明流露出作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从而也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开文明”的渴求。
“民气可用”的背后,相应而来的是对“民气如何用”的反思,“义和团运动”正是时人反思的一个切入点。1904年,《东方杂志》从创刊起便陆续刊登“民气说”的相关论述。(22)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东方杂志》1905年第8期;《论中国民气之可用(录乙巳六月十三日时报)》,《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梁启超:《论民气》,《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气”是与“国民性”话语相对应的一个本土概念,也是构成晚清国民性问题的重要话题。(23)周新顺:《“民气”“民智”“民德”:重返晚清国民性问题讨论的话语现场——以〈东方杂志〉为考察中心》,《东岳论丛》2017年第11期。然而,“民气”积弱,难以使国家兴旺;“民气”过激,又会引致祸端。北方“义和团运动”造成暴乱景象,南方“愚民”仇洋仇教以致焚毁学堂,因此,《论民智不进可忧》一类的社论也是频频出现。(24)《论民智不进可忧》,《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苟他日民智大开,则义和团争论之质点,必发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25)《主权篇》,《中国旬报》第三十三期,转引自段云章、桑兵:《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与改良的消长》,见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二集,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第43页。“拳匪”话语体系中的“义和团”一方面承担了“乱世之祸端”的历史罪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近代文人对改良“民智”、倡“文明之思想”的思考,是晚清知识分子触及后世所谓“国民性”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
(二)“英雄”话语:革命语境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生成
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叙写中引入“英雄”话语的契机,正是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语境。1901年,《开智录》第六期上刊载了郑贯一的一篇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文中写道:
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而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26)贯公:《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7页。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义和团”在“排外抗侮”方面的积极影响。而在1924年,《向导》周报于《辛丑条约》签订二十三周年之际推出“九七特刊”。其中,刊发了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政论文章,意在肯定“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以纪念国耻、赞扬“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起义活动的形势,促成“革命动员之目标”(27)李里峰:《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其实,早在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就已经将“义和团”纳入“革命”语境之中展开分析。只不过他将“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作为两种革命类别,而把“义和团运动”归于前者进行批判。(28)王先明、李尹蒂:《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为何同属革命语境,邹容对“义和团”的看法会与后来《向导》周刊中的论述产生如此大的差别?解释这个问题,是探讨关于“义和团”的叙写如何从“拳匪”话语转入“英雄”话语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拳匪”与“英雄”作为一对相悖的概念之所以能共存于“义和团”之上,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按照同一评价标准来进行定义的。换言之,“拳匪”与“英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中。邹容对于“义和团”的批判,是基于“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他以“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的对立得出“革命之前,需有教育;革命之后,需有教育”的结论。(29)邹容:《革命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1页。这与《邻女语》《老残游记》等作品中所提出的“开文明”的要求相互呼应,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大力批判“鬼道主义”的重要原因。而在国民革命时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周刊所推出的系列文章中,淡化了“义和团”之“野蛮”的一面,(30)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到:“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从1918年的《克林德碑》到1924年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陈独秀对待“义和团”的态度转变不是一种推翻自我的纠偏,恰恰展现了他从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和传统文化到作为中共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需求上的变化。见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1924年第81期。从而将关注重心从“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层面转移到民族的对立与阶级的对立中去。这一转向,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义和团”,或者说如何使用“义和团”的话语资源,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
1958到1959年间,《民间文学》集中发表一系列由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传说故事”,随后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形式出版。此时,文本中的“义和团”形象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不仅成为各个故事的主人公,更以“民间英雄”的身份实现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封建王朝统治者及其官僚、地主阶级等压迫势力的反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斥为“文明”对立面的“鬼道主义”,在“义和团传说故事”中却成为塑造“民间英雄”传奇色彩的质素。无论是《红缨大刀》中腾云驾雾、能以刀抗枪炮的“神兵”,还是《铁金刚》中被龙王赋予“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本领的铁二怔子,都展现出“义和团”已经不再作为“拳匪”和“乱世之祸端”而被理解。蔡翔在研究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时,曾经提出“革命中国”的概念,指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与文化实践”。“革命中国”无疑是追求“现代”的,但这一“现代”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现代性,其差异在于“它从‘民族国家’力图走向‘阶级国家’;下层人民的当家做主,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尊严政治;对科层制的挑战和反抗;一种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分配原则,等等”,这种追求“现代”却又具备“反现代”性质的阶段,营造出一种新的“革命语境”。(3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在一种新的“革命语境”之中,这些“义和团”形象成为从底层民众那里汲取能量的爱国主义符号,其反抗与颠覆式的能指被无限放大,甚至由“造鬼”走向了“造神”的一端。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冷战”的国际语境之中,“反帝爱国”成为一种主流倾向,在建国后出版的不同版本史书中,也是着力突出“义和团”的这一特质;(32)张圣典:《白云苍狗话庚子——论中国百年来“义和团小说”书写之演变》,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年,第30页。另一方面,“‘主体的颠倒’是新中国文艺改造的首要步骤”,(33)白惠元:《金猴奋起千钧棒:从“力敌”到“智取”——新中国猴戏改造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既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途径,同时改写了传统文艺创作和生产的模式。毛泽东在1944年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提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34)《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新中国文艺创作提供了政治导向。以《民间文学》发表的“义和团传说故事”为例,在作品内容上,集中表现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之“正直、英勇和机智”,赞扬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革命的正义性”(35)陈白尘:《为义和团恢复名誉》,《民间文学》1959年第4期。;在创作形式和方法上,则是将文艺生产运作下沉民间,通过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以及针对当地群众进行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最终改写成现在所能看到的“传说故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性”并不等同于“人民性”,但在这里,“民间”为“人民”的主体化进程赋能,具有传奇性色彩的情节不断为群众反抗压迫提供正义性和合法性的依据,用以达到“对今天的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36)河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张士杰搜集整理:《义和团故事选 托塔李天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编者的话”第2页。。
(三)历史记忆与现实焦虑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关于“义和团”的叙写始终被置于“英雄”的话语体系中。无论是段承滨的故事组剧《黑宝塔传奇》、老舍的话剧《神拳》,还是小说《义和拳》《叛女》与《庚子风云》,都将“义和团”的形象塑造成反抗压迫的革命先锋,借讴歌“历史”来为现实革命造势。在某种程度上,创作者和评论家将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记忆朝着主流意识形态所希望的方向改写、编排,甚至对展现“义和团”负面性质的作品大加批判。戚本禹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中将40年代末香港上映的影片《清宫秘史》对于“义和团”之“野蛮”的刻画斥为一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卖国主义”,(37)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红旗》1967年第5期。这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文学文本对“义和团”的叙写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对此,一方面存在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思想解放大潮”为“义和团小说”的书写提供更为开放的时代环境;(38)张圣典:《白云苍狗话庚子——论中国百年来“义和团小说”书写之演变》,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年,第42页。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80年代重新解读“义和团”,使得“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再度趋于紧张”(39)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如何摆脱“新文化运动时期给义和团贴上的‘迷信’标签和20世纪20年代给予义和团‘反帝爱国’美誉”(40)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第248页。,成为“革命”语境退却后的一个显著的叙述障碍。
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可以发现,“拳匪”与“英雄”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从《义和拳》《神灯前传》到《神鞭》再到《单筒望远镜》,冯骥才对“义和团”叙写态度的转变,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从为“政治需要”树立“革命典型”,到自觉进行历史思辨、回归文化趣味,已经很难用统一的话语模式再度概括这一历史事件。1985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小说以半虚构半纪实的方法描绘了轰动一时的“5·19事件”。针对这一事件,香港《信报》将其评价为一次“义和团精神的发作”,而刘心武则借助主人公滑志明的视角把这次事件与“义和拳的排外”区分开:
据事后回忆,滑志明确实不记得他自己和别的闹事者特意地选择了有外国人或港澳同胞的乘坐车来拦截。他们的心态,确实有别于八十五年前的“义和拳”。……他们其实恰恰是香港通俗文化和东洋商业文化的最积极的吸收者;他们之所以在“5·19”那天闹出一些针对外国人或港澳同胞的不雅之事,充其量不过是对外国人或港澳同胞在北京所显示出来的某些特权和优越感,喷发出他们潜意识中回荡、压抑已久的不理解、不谅解、不满与嫉妒而已。(41)刘心武:《5·19长镜头》,《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再往前推导,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以“足球”为载体的现代化国家想象,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遭遇危机,民众自然而然会产生“自发的民族化行动”(42)张伟栋:《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刘心武纪实小说〈5·19长镜头〉解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义和团”在这里成为反观现实的一个参照系,不仅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想象建构的焦虑,更折射出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心理空间”所面临的危机。
而王朔发表于1989年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同样引用“义和团运动”这样一段历史记忆。作品延续“义和团”的历史,着力塑造“唐元豹”这样一个被“包装”的“当代民族英雄”的荒诞形象。王朔所塑造的“民族英雄”,显然是对历史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形象的颠覆与瓦解。为“雪国耻”而进行的拳击赛,最后沦为奇观化的展览和表演。唐元豹在众人的注视下、在电视机的转播下撕掉自己的脸皮,更是对人的异化的揭示与暴露。小说一方面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对民族文化符号的利用。赵航宇等人对唐元豹的训练、包装甚至是性别的改造,正是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对爱国主义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反叛。所谓的“民族英雄”不过是博人眼球的小丑,经过不断塑造之后的“大梦拳”最终也沦为只能观赏的“花拳绣腿”。小说从沉痛的近现代史中获取资源,以所谓的“民族矛盾”(实际只是拳击赛的失败)来激起“民间”对于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本质上不过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难以解读时代和解读自身的一种表现。
黄子平在分析西西的小说《肥土镇灰阑记》时曾经抛出一个疑问——作家并未贴近历史去叙述历史,那么她为什么要借用《灰阑记》这个古老的故事来完成自己的叙述?由是,黄子平得出了一个结论:“西西的小说,发展出一个将现实焦虑引入传统故事共同发声的叙述结构,最终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情节可能只是一个荒谬的解决。”(43)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页。对历史的“借尸还魂”,其背后往往贯穿着当下的意识形态——企图用历史记忆诠释现实所激发的焦虑状态。因此,有关“义和团”的叙写也从统一而宏阔的历史语境中,被不断拆解到细微的当下现实里,并在其中获得新的阐释。
三、历史叙事的维度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将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解读划分成三个部分,以阐明历史书写的多重意图。那么,通过文学作品重述这段历史的作家们显然成为柯文笔下的“神话制造者”,不再是凭借“知识层面的确定性”来还原历史真实,而是以“后代的回声”的形式来呈现过去与现在之关联。(44)郭宝军:《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焦灼与妥协——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读后》,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大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1页。从历史记忆转而进入文学创作之中,有关“义和团”的叙写不仅经历了“拳匪”与“英雄”的形象演化与反转,更通过其中所包含的内在情感模式、外在时空结构以及历史的深层隐喻,展示出文本中的历史叙事如何成为可能,历史记忆如何在想象与虚构的层面上展开并重新被塑造。
(一)内在情感模式的转变
综观20世纪初期描写“义和团运动”的文学文本,可以发现,这些靠近“历史现场”的作品在以“拳匪”对“义和团”进行定性的同时,常常着意书写动乱之苦与世道之艰。《恨海》在第七回写到伯和一众外逃避乱时,刻画了如此场面:
从此伯和便在这里避乱,每日只听得外面枪炮声响,到了夜来,只见红光烛天,幸喜都在远处。……约莫过了有一个月光景。忽然一天,听得外面枪炮震天,比从前响的格外厉害,隐约听得外面有许多哭喊的声音。……伯和逾墙出了米栈,走出了小巷口,只见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45)吴趼人:《恨海》,见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292-293页。
逃难、救劫、灾祸、离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话题,时人更将此衰败局势与社会乱象归结于“义和团”的兴起——“庚子遭荒乱,皆因是义和神团”(46)《庚子纪略》,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3页。。不仅在写实性文本如《庚子国变记》中以史书笔法书写社会惨状,在当时所谓的“写情小说”中,“情”与时局的互动关联同样成为作家介入历史的途径。回到《恨海》,其中隐含的脉络大致呈现为:乱——离——悲,而“义和团运动”成为推动一切情节发展的肇始与源头。在小说中,“情”的断裂与道德的失序,背后所体现的是时代的危机,作家有意无意地将小说激发个体之“情”与实现“群治”之功能联系起来。但换个角度来看,从1900年这一特殊时刻反观作家对于“情”的刻画,恰恰展示出挣脱封建秩序、步入现代的艰难。在小说结尾处,当棣华面对伯和的死亡选择以“出家”的方式为其“守节”时,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向着传统礼教的复归。但通过与父母的对话,她痛感“不孝”却仍遵从个体之情,坚定“出世”而隐匿山中,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女性主体走向‘现代’”(47)冯妮:《“情感”与“道德”:晚清时局下的双重危机——吴趼人〈恨海〉的另一种解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的表现。吴趼人在《恨海》中将个体之情与时局之悲并举,追求“情”与“礼”的圆满,最终却随主人公的归隐走向不知所踪的虚无。在这种情感基点之上所建立的历史观,实际呈现出一种悲观的状态——“我们可以将主人公这一路旅程视为一种‘匮乏’,一场‘噩梦’,他们所作的一切主观努力都是在试图克服这种匮乏,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回到故事原初的圆满和谐状态。”(48)冯妮:《“情感”与“道德”:晚清时局下的双重危机——吴趼人〈恨海〉的另一种解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在这个过程中,“义和团运动”造成时局的失序,由此导引出人物间的离情。显然,面对“如何修补在转向‘现代’的过程中行将崩坏的道德体系”这一巨大的历史难题,作者也无法提供有效性的方案,悲剧结局的形成看似充满矛盾,却可以追寻出一条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在另一批以“英雄”话语塑造“义和团”形象的文学文本中,其情感基调则从个人与时事的悲情中跳脱出来,转而去渲染更为浓烈的国仇家恨,并且以“反抗”“复仇”“雪耻”作为情节推动力,从而展开历史叙述。比如张士杰整理的“义和团传说故事”里,民众与洋人间的民族矛盾,与官府、财主间的阶级矛盾成为所有故事构成的核心要素。最终,民众或自发聚集起来合力对抗压迫,如《梁三霸团》《砍马二爷》等;或借助神怪之力予以反抗,如《红缨大刀》《托塔李天王》等;或凭借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传奇性结局收尾,如《张头和李头》《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等无不显示出民众在抵抗强大势力时所具有的天然的合法性以及凝聚力。在义和团故事组剧《黑宝塔传奇》中,至亲的“血泪仇”不仅是整部戏剧的前提背景,更是人物团结在一起的情感基础,“两个苦瓜一条蔓”(49)段承滨:《黑塔归团——义和团故事组剧:〈黑宝塔传奇〉之一》,《剧本》1961年第11期。,黑塔和陶五娘对“活阎王”的“恨”,使得这两个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成母子,并由此激发出一系列的戏剧冲突。
服务于“革命教育”或融合进“革命话语”的文学文本,如何展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叙述?在内在情感模式方面,往往通过国仇家恨切入,将人物划分成不同阵营,以二元对立的“反抗”模式推进情节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作品中对于男女之间个人情感的刻画有时不再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甚至为了突显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爱”与“憎恶”的个人情感偏向也潜移默化地转化成为斗争的武器。在鲍昌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庚子风云》中,主人公李大海对于女性人物宛芬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作者巧妙地透过人物的眼睛对宛芬的外貌进行刻画,从而把李大海心里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而大海则看清了她那双白得吓人的纤瘦的手,以及她今天特为大海而换上的一件长衫。这件绮霞缎的长衫是天青色的,衣襟和袖口处都缝有卍字纹黑色缎条。……当宛芬提起茶壶离开的时候,大海又照了一下她的后影,看到她仿效那城里入时的女人,梳了一个灵蛇百绾髻,上面插饰着蝶翼形的珠花、嵌着金花的银钿,与一根长长的玉簪、两根象牙副笄,组成了繁缛复杂的“头面”。(50)鲍昌:《庚子风云》第一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82页。
李大海对于宛芬的反感凝聚在对其穿着打扮的看法中,在李大海眼中,宛芬的穿着是“炫耀阔气”的表现,而作者在此加入了一个注解:“旧社会中,女人头上各种复杂的首饰,总称为‘头面’。”(51)鲍昌:《庚子风云》第一部,第82页。贫与富、新与旧,对于不同阶级、新旧社会的价值评判隐现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世界苦、阶级仇、血亲恨”的情感基调所左右,政治激情反身进入家庭伦理、情爱伦理之中。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将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帝国主义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削弱了不同情感所具有的本真内涵。引发“苦”“仇”“恨”之感的人生体验所具有的强大势能,遮盖了血脉亲情与两性之情,而这种置换与错位的背后恰恰是“革命话语”的介入。那么,基于这种情感模式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在将“人民”提升至历史的主体地位之时,也冲击着其作为个体之“人”的精神内核。
而在80年代,随着文学创作逐渐脱离革命语境、从统一而宏大的时代主题中解放出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叙写也日趋多元。无论是通过冯骥才从《义和拳》《神灯前传》到《神鞭》再到《单筒望远镜》的转变,还是《千万别把我当人》《檀香刑》中对“义和团”形象的颠覆性刻画,都可以看出,历史叙事不再为时代的动荡和革命的狂热所困。在跳出相似的情感模式和价值观念的限制之后,作家反而能历经沉淀作出新的反思。
(二)介入历史的方式:两次“北上”之路
在众多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文学文本中,有两部作品具有特殊的代表性,一部是1903年连载于《绣像小说》的《邻女语》,一部是徐则臣出版于2018年的长篇小说《北上》,两者的创作相隔100多年,却都以主人公的“北上”之旅展开对这段历史的叙写。
在《邻女语》中,金不磨为救“宗国”、“拯拔”北方百姓于“水火之中”,“变卖产业只身北游”。(52)忧患余生:《邻女语》,见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2集·第8卷·小说集六》,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7-8页。“北上”之旅亦即他的“救世”之旅,从江苏镇江出发,一路途径山东、河北、天津,进而入京,通过路上所见所闻,展现时局之动荡与世事之艰难。随着主人公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一幅乱世之景跃然纸上,“游”成为叙事的连接和纽带。通过小说人物“游”的行动和轨迹,可窥探彼时社会众生相。阿英认为这部作品中“最优秀部分”当属“写沿路所遇着的逃难的京官、骚扰抢劫的士兵,于一幅逃难图中,活画出清室已达到非覆灭不可的程度,指出这一班人物出京的时候,是懦切得不堪。但一到南方,马上就换了样子,在船上挂起‘大人’‘正堂’旗帜,‘打着京撇子’骂人,要送人‘到衙门’。及至听到所停泊的地点仍是‘租界’,却又‘噤若寒蝉’了”(53)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2页。,作者对于京官们南下逃难整个过程的刻画,实际上展示出金不磨“北上”之旅的终点——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已然成为当时社会动乱的核心,暗示着封建王朝统治的腐朽倾颓。
作者在小说中划分出了一个内在的“南北之界”,充斥着租界洋场与通商口岸、远离政治核心和“义和团运动”核心的“南方”,成为当时民众逃离劫乱的一个选择。与此同时,“中”与“西”的关联也隐藏其中。“北上”之旅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主人公们,其共同身份是“具备西学素养的‘南人’”(54)乔以钢、林晨:《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在《邻女语》中,无论是年少时习得“西国文字”的金不磨,还是在“西人”中有极高声誉的黄中杰,其自身的西学背景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反观晚清社会的视角。王德威在论述小说中对于“人头桃林”的刻画时,谈到忧患余生“在砍头事件里发现了中国文明‘内里’循环不息的野蛮性”(55)王德威:《“头”的故事:历史·身体·创伤叙事》,余淑慧译,《东吴学术》2012年第1期。,这一“野蛮性”不仅通过民众之愚表现出来,更通过“王纲道统”的衰败、官僚阶层的腐败无能展示出彼时中国社会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传统已经处于无序的状态,这正是“中国进入现代所面临的重重危机”,而作者的选择则是通过西方文明的介入,来寻求一个获得“拯救”的答案。
而《北上》则从2014年的一次考古中所发现的“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件”(56)徐则臣:《北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页。展开叙事。这两个时间节点刚好昭示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和及至当下的演变,“关于运河的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是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叙事,这一点特别重要。必须把关于大运河的故事放到一百年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去讨论和观察,才能见到这个作品背后厚重的历史意识和它的现代性”(57)杨庆祥:《〈北上〉:大运河作为镜像和方法》,《鸭绿江(下半月版)》2019年第2期。。因此,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北上”之旅不仅通过空间的位移来实现此前文学中对社会之动乱的现实观照,更凭借叙事时间的交错展开来完成一系列关于“现代”的故事。在1901年的故事里,主人公不再仅仅是《邻女语》中身兼传统士人精神和西方文明熏陶的“金不磨”,作家徐则臣选择了多个人物视角来介入:既有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谢平遥,也有加入“义和拳”以谋一口饭吃的孙过程兄弟,更有小波罗、大卫·布朗这样的外国人视角,甚至通过马福德的“中国化”,来展现文明之间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与“西”、“南”与“北”,不再是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相互割裂的“他者”,而凭借“大运河”这样一个意象获得了凝聚成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的可能。
(三)“性”象征——历史深处的隐喻
冯骥才曾在访谈中表示:“义和团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它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是这座城市前三辈儿人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一定要再写一部关于义和团的著作。”(58)李远江:《义和团是心中的一个结——专访〈义和拳〉作者冯骥才》,《看历史》2010年第5期。于是,在201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延续了《义和拳》《神灯前传》《神鞭》中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关注,再次触及这段历史。显然,冯骥才展开历史叙事的方式不同以往,甚至构成所谓的“一次反刍性的写作”(59)周立民:《一树槐香飘过历史——评冯骥才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意在说明作家在将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反复“咀嚼”之后所流露出来的新的思考。其表现在于,作家悬置对历史的评判,转而以隐喻的方式重构历史的复杂性。其实此前在《神鞭》之中已然可以透露出作家对于如何叙述历史的探索:
正因为鞭子本身的启示,也因为小说特定的时代,恰恰处在中国从闭关锁国到海禁大开之际,如何对待祖宗和如何对待洋人,这个复杂的在今天看来很荒诞的民族心理的反映,表现得十分充分。这就使我着意刻划出在对待祖宗和对待洋人不同态度的各式人物,展开他们在“剪辫子”这个事件上的烦恼,矛盾心情,愚昧和偏执,醒悟和革命性。既写他们历史的真实性,也写历史的荒诞性。我把这些合成在一起,不就构成了那时代特殊的、至今依旧明灭可见的复杂的某种民族心理特征吗?(60)冯骥才:《鞭子的象征与寓意——〈神鞭〉之外的话》,见《案头随笔》,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辫子”作为历史的喻体,将时代的晦暗不明之处囊括其中。而在《单筒望远镜》里,“性”接替“神鞭”的职能,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诠释历史的剧变:
从这天起,他们几乎天天在兀立白河边这个荒芜的小楼里相见,相拥,亲昵,厮缠,纵欲,尽情地欢乐。对于他们,小楼不再是荒野一座废楼,而是他俩的天堂。在这里,各自的世界不再具有魅力,一切魔力都在他们自己的肉体上。他们甚至不再需要那些纸片上的文字了。他们好像天生就会阅读对方,用本能的肢体的行为畅快无比地交流着。这种伟大的天性的交流居然超越了一切文明的障碍。(61)冯骥才:《单筒望远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欧阳觉和莎娜二人在肉体上的交合所带来的快感与狂欢,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动荡时局带来的不安之感。与此同时,“性”本身更是冲破中与西、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历史隐喻。而通过小说中的重要意象“单筒望远镜”,不仅可以窥视二人间的私人情欲,更由于其所属者是莎娜之父——洋人进攻天津的指挥官,从而被赋予了一种观察历史的复杂视角。
同样以书写“性”来展露世纪之交的历史伤痕的作品,还有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以及叶兆言的《花煞》。在《张马丁的第八天》中,张王氏为延续香火在狱中与张天赐发生关系,又在娘娘庙中向张马丁“借种”,两次行为成为小说串联的重要节点。“性”的发生与人物的生死紧密相关,张天赐因在保卫娘娘庙的行动中“误杀”教堂执事张马丁而被官府判了斩首之刑,张马丁“死而复生”之后又被张王氏错认为张天赐的转世,所以在娘娘庙中交合以求留下张天赐的“种子”。在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里,实际隐含着晚清社会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国民众、清政府、列强以及西方传教士之间相互制衡与对抗,激烈的矛盾冲突导致一系列悲剧的发生,而“义和团运动”只是乱世景象的一个缩影。“血腥狂热的义和团运动像一场巨大的龙卷风,把这一切残忍地纠缠、碰撞在一起。张马丁和张王氏就是活着的耶稣和菩萨。当活着的耶稣和菩萨来到这个无恶不作的人间,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和折磨,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绝望,是所有人的现世困境,是所有人的耻辱和惩罚。”(62)傅小平、李锐:《万劫不复的此岸(代后记)——〈张马丁的第八天〉访谈录》,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李锐试图通过小说再现一种困境——当人面对信仰中的神圣天堂与现实里的人间炼狱这样巨大的错位与断裂之时,该何去何从?化身“圣母娘娘”的张王氏将“生育”作为生存和精神的依托,但“转世”与“借种”不是历史的新生,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循环。以“生育”作为终极目标的“性”隐喻着时代的苦难和历史的伤痕,张马丁在与张王氏交合时不停祷告:“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用的羊羔”(63)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第144页。,这使得“性”成为一场献祭,充满了历史的悲剧感。
叶兆言在《花煞》里虚构了一座“梅城”,描写了从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发生在这座小城之中的历史记忆。“性”成为贯穿整部小说始终的一个主题,“性”与侵略、“性”与暴力、“性”与饥饿、“性”与权力、“性”与文化……“性”几乎参与每一个重要情节的构成。与张天赐有着相似命运的胡大少临死前在狱中“留种”、胡天胡地的诞生、梅城妓院的建立与兴盛、文森特与哈莫斯在中国的罗曼史——“性”的狂欢映衬着末世之景,同样也以一种人的本能冲动的形式提供了文明交融的入口。叶兆言表示:“西方文化是强大的,它将一个中国小城变成这样。可是中国文化也同样强大,它最后竟将哈莫斯这样一个纯粹的西方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东方人。文化的相互交融确实就有着与性相似的东西,哪两种文化杂交,是很重要的。”(64)叶兆言、姜广平:《“传统其实是不可战胜的”》,《西湖》2012年第3期。将“性”与“文化杂交”同构,暗含了文本在表现特殊历史时期时所设下的深层隐喻。在《花煞》中,“梅城”虽然远离“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但却同样叙写着世纪之交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以及中西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第一卷在描写“梅城教案”的惨剧时,曾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石膏做成的十字架,插在了沃安娜的阴户上,像一个男人的阳具似的十分可笑地翘在那里。”(65)叶兆言:《花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4页。这种充满亵渎与侵犯意味的行为,不仅体现着人性的残忍与民众的野蛮,其实更是以肉身承接历史的暴力。凭借这种极端的形式,展示出不同文明间的互斥与被迫融合。
“义和团运动”所处的特殊历史节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阶段,是被强制纳入世界的一个过程。老舍在剧本《神拳》的后记中写道:“文明强盗又来了。”(66)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文明强盗”四个字恰恰体现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特征——现代文明与非理性侵略的同时发生。人民的“暴动”、群起的反抗所具有的两面性,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被知识分子笔下“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捕捉,于是,“义和团”作为“拳匪”和“英雄”的形象交替生成。通过对百年来文学关于“义和团运动”叙写的个案梳理,可以发现文本中的历史叙事无不投射着作家的观念、化身时代的缩影。如何书写历史,其实也就是如何书写当下,而文学对于历史的介入,不仅实现了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更以“历史叙事”中的新质反映出时代的新变。从“1900”到“新世纪”之后的“百年之变”使得“义和团运动”的历史面貌愈发多样,也从一个难以叙述的“巨大创伤”转化为一个反思的入口,进而得以重新审视这个充满断裂的“中国现代经验的起源”(67)王德威:《一个人的“创世纪”》,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序”,第3页。。